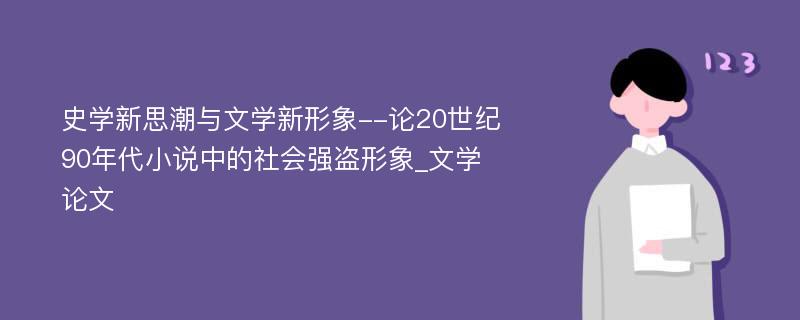
史学新思潮与文学新形象——论90年代小说中的社会土匪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思潮论文,土匪论文,年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叶上叶,是中国历史上匪患最猖獗的时期,“民国时期的土匪以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大、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却为其他时代所未有,而且它的存在和发展又同民国相始终。这一切都成为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1〕50年代初, 随着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作为旧中国残余的邪恶势力的土匪在大陆上基本被根除。这一历史壮举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实际上对土匪的性质作出了历史性的结论:土匪是祸国殃民的社会“恶人”。从此,对土匪的看法就由以往的道德评判转为政治评判了。在人们的观念里,土匪是凶杀、抢劫、奸淫、残暴的狂徒。1957年,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出版,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认识,并把这种观念转换成一种普遍相识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映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当代小说中,《林海雪原》以典型化的写法,第一次全面集中地描写了各色恶匪形象。这些土匪形象的影响之深之广,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围。《林海雪原》的土匪形象既成了艺术的范本,为当代小说描写土匪形象提供了模式,又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土匪属性进行政治界定的形象演绎,对土匪“恶人”的本质作了透彻的解释。自此,土匪形象基本定型。
然而,到了90年代,一批新的土匪形象出现在众多小说中,如《五魁》的中唐景、五魁,《白朗》中的白朗,《十九间房》中的春麦,《匪首》中的姬有申,《白鹿原》中的大拇指、黑娃,《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大头,《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等等。这些民国时期的土匪形象一改往日丑恶凶狠的面目,良善义气,重情重德。把土匪写得有人性,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进而有限度地赞美他们,是这些小说共同的艺术倾向。这么多严肃性的小说不约而同地描写出新的土匪形象,实为90年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
为什么恰恰是在90年代的前几年里猛然出现这么多新的土匪形象?新的土匪形象有何意义?这些追问的提出,以及对这些追问的回答,必然要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联系起来。
一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新的治史态度”,许多年轻的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的史学仅仅注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倾向,他们提出历史学家应当关心普通民众。在这一史学思潮的背景之下,英国社会史著名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6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土匪》的专著。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开拓性的内涵不仅使它具有神话般的特性,而且确定了它成为人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和研究的对象。自从此书问世以来,学者们已经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土匪活动的现象。〔2 〕也是在这一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英国学者贝思飞积十年功夫,撰写了《民国时期的土匪》,于1988年出版。西方学者称该书是“民国土匪活动第一部综合研究专著”。事实确是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有过不少记载,但史学界对此却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没有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根据《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版和1983年版)公布的《1912—1948年中国历史书目》,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中,从未有过一本土匪史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比较注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以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形成一片空白。”〔3 〕只注重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而从70年代末开始的民国史研究,对土匪有时也有所涉及,但都不是以土匪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对象。进入90年代,学术界正式开始了对土匪一类下层社会和社会病态现象的研究,并很快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近代中国土匪实录》、《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中国帮会史》、《中国地下社会》、《流氓的变迁》等。不过,这些研究还处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水平,而当前小说对土匪形象的描写,一上来就进入艺术创造的审美水平。中国的学者和作家对民国时期土匪的关注,在时间上竟然如此一致,足以让人思索。在我看来,他们的一致并非纯属偶然巧合,而是受人文思潮潜在影响的必然。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土匪?土匪,在人们的观念里,是强盗的又一种称呼。他们通常被理解为是以抢劫为生,遍施烧杀奸淫的邪恶之徒。但是,对旧中国的土匪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土匪是个十分复杂又十分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来源混杂,目的不一,类型有别;他们的动机不一样,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行动;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乏精神的、思想的力量支持。旧中国土匪的成因、来源相当复杂:有为贫穷所累的善良百姓;有纯为报仇雪恨的复仇者;有受官府或地方恶霸豪绅欺压凌辱,被“逼上梁山的”;有为匪胁迫不得已而为匪的。还有做孽犯了罪,为匪躲罪的;有赌博借债不能还,入匪消债的;有趁世混乱,伺机而起的社会渣滓;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流氓无赖、残暴成性的邪恶之徒;乡霸恶绅往往摇身一变成为匪首。另外,历次战争中的残兵败将、散兵游勇也构成了土匪的一个重要的来源。〔4〕
土匪来源混杂,目的不一,但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土匪”。霍布斯鲍姆在《土匪》的第一页明确的指出:他只研究一类土匪,“他们不是被经公众舆论当作单纯的犯罪分子……而是作为英雄、战士、复仇者、保卫正义的斗士,也许甚至是解放运动的领袖,总之,他们受人赞美,值得帮助和支持。”〔5 〕这类土匪就是“社会土匪”,中国百姓常常将他们称为“绿林好汉”。他们自己也经常以绿林好汉自诩,高举劫富济贫的义旗。这类土匪若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和组织形式,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要求,同时又有超越地方狭隘眼界的领袖人物,就会演变为农民起义,其主要人物就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或英雄人物。第二种类型是恶匪。恶匪多为歹毒成性、欺压良善、滥抢滥杀的邪恶之徒。第三种类型是纯为生计所迫,在小范围内进行一般性抢劫,但不欺压良善,不烧杀奸淫的“季节性”土匪。当然,更多的土匪是混合型的,难以明确归类。
贝思飞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他以大量的令人信服的材料和周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土匪的猖獗正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对于大多数土匪来说,当土匪乃是万不得已之举,是“逼上梁山”。然而,就土匪活动的性质来看,土匪既不是造反,也不是革命。人们当土匪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总的说来不是为了自我生存就是为了自我改善。土匪活动不包括改变社会的价值观,不要求改变社会的等级划分,因此,当他们采取行动时,其矛头不是对准整个统治阶级,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直接的压迫者。总的说来,“土匪是复仇者,他们的斗争目标不是对准压制他们的社会制度,而是对准各种滥用这种制度的人。”通常,“他们并不要求社会有什么变革,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他们(包括同村的乡亲)所遭受的苦难讨还血债。”〔 6〕但就土匪行为本身来看,他们既反抗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及各种恶势力,同时又干出许多丑陋勾当。因此,贝思飞认为要辩证地看待土匪,如果把他们一视同仁,“这无疑是感觉迟钝、眼光短浅的社会分析”。〔7 〕土匪行为是一种抗争的表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不过是对遭受贫困和战争蹂躏的一种反应。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也致使道德崩溃,使坚持传统规范变得无关紧要。在土匪世界中,存在着“好的土匪”(社会土匪)和“坏的土匪”(恶匪),于是,他们的活动就有了“好的暴力”和“坏的暴力”之别。前者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百姓的愿望,后者及其活动直接侵害百姓。
在史学新思潮的大背景下观照90年代小说中的社会土匪形象,会使我们对这些土匪形象及其意义获得更准确的理解。当然,社会土匪形象的出现,从文学发展方面看,它们的产生与80年代的文学对人的理解逐步深入的创作思想,以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思潮密切相关。我们还看到,这些小说对土匪的描写与评价,在总的思想趋向上与贝思飞的观点很接近。它们的区别在于:一着眼于整体研究,另一注重于个体描写;一从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土匪,另一从人性和美学角度塑造土匪形象;一研究各种各样的土匪,另一尽管也描写了诸如金豹、苟百都、黑老七等恶匪形象,但主要描写的是“好的土匪”形象,即社会土匪形象。
二
拆除先在的政治界定,把社会土匪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纳入“客观事实的叙述”的写实语境中,辩证地看待他们,理解他们,进而同情他们,成为90年代小说描写社会土匪形象最基本的艺术原则。
这些小说描写了土匪们为匪的经过,写出了他们的无奈与悲伤、愤恨与反抗,揭示了他们为匪的合理性;他们的不幸同样让人同情。一代巨匪枭雄白朗走上为匪之道纯属被迫。安福寺的小和尚白朗发现主持奸淫良家妇女的秘密,引导怒不可遏的村民捣毁了寺院,并亲手处死了淫贼。为躲避官府的捕杀,他一气之下,上山落草为匪。《白鹿原》中的土匪头子为匪的经过更具社会性与合理性。大拇指原名芒儿,是一位安份守己的农家子弟,12岁拜师学木匠。由于他聪慧机灵勤快,深得师父、师母及女儿小翠的偏爱。两位师兄嫉妒,设计陷害他和小翠。小翠嫁给杂货铺王家儿子的第二天,新姑爷当街辱骂小翠不贞,二师兄从旁帮腔证实。小翠受不了这般侮辱,上吊自尽。百日之后,杂货铺王家儿子又娶新媳妇,芒儿趁婚庆之机刺死新郎,然后又刺死二师兄。为躲官府追捕,他出家当了和尚。白鹿原爆发“交农事件”,他领头起事,愤怒抨击社会的黑暗。交农事件平息后,他被关进监牢。一次又一次受到官府的迫害,失望之际,他换了另一种反抗形式:上山当土匪。
黑大头、黑娃为匪直接与土匪有关。为人良善的庄户人黑大头,家境殷实,突然遭土匪抢劫。在土匪逼着他回家取财物时,他趁机砸死了强盗头子。没想到,群龙无首的土匪拥戴他当头儿。《白鹿原》中的黑娃,经历复杂,思想复杂,他既参加过革命活动,又当过土匪;既是国民党保安团的军官,又是弃暗投明的起义者;既是封建道德的叛逆者,又是封建道德的归顺者;既嫉恶如仇,又同恶势力为伍;刚正倔强仗义,但缺少斗争经验。黑娃形象的复杂性折射了人性的复杂和他所处时代社会现实的复杂。黑娃有过一段为匪的经历,而他的为匪又是那么顺理成章。国民革命军习旅战败,旅长的贴身警卫黑娃在逃难中落入匪穴,心甘情愿地当了土匪。
纯粹为爱情的原因当土匪的,是五魁。贾平凹的中篇小说《五魁》不是土匪小说,五魁也不是以土匪的角色来表现的。小说只是在结尾处留下一个深沉醒目的远景特写:一年后,五魁成了威震四方的匪首。整个小说,实际上写五魁与柳少奶奶“畸形的爱”。五魁深爱柳少奶奶,但从不敢有娶她为妻的念头。他两次冒死救柳少奶奶,也仅仅止于爱慕她的美,同情她的不幸,即使是在荒山野岭他们一起生活时也是这样。柳少奶奶爱恋五魁,当她将爱一次又一次奉送给五魁时,五魁惶恐,不敢接受。“我怎么能配上她呢,一个高贵的柳少奶奶!”自卑自贱映衬出他人格的卑琐,从而也压抑了他真纯的情感。五魁不能从情感上解救柳少奶奶,这样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女人生存的希望,致使柳少奶奶性变态,最后含怨坠崖自尽。柳少奶奶的死毁灭了他的希望,在一切绝望的情况下,五魁当了土匪。
把土匪当作普通人来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某种固定的由社会身份决定的“类”来看待,正确地理解他们,显示了作家们对人的研究的深入。土匪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处于社会边缘的一个阶层,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就这种性质而言,土匪是社会的恶人,为人们所指责。但具体到个别,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土匪中除真正的强盗恶魔外,还有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绿林好汉,备受欺压侮辱的受苦人。理解并同情这部分人,实在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人道主义是近代思想革命的产物,“人道主义代表着一种关于宇宙、关于人的本性、关于如何对待人的问题的明确的、直接了当的见解。”〔8 〕同情被压迫被侮辱与受苦受难的人,是人道主义的中心内容,人道主义这个层面的内容在文学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成为文学持久不衰的主题,至今,它在文学中仍然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好的恶人”、“好的罪人”该不该理解并予以同情呢?这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命题。在世界文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的文学中,对恶人、罪犯的理解与同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例如,19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描写了江洋大盗、杀人魔鬼唐·若瑟和吉卜赛风流女郎嘉尔曼犯罪的合理性,以及他们放荡不羁、视自由为生命的个性和坦率真诚的品质,表现了作者对不幸的罪人的理解、同情与美化。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对罪犯冉阿让的同情、赞美,深化了雨果在以往许多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德伯家的苔丝》、《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流浪者》、《复活》等众多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倾向。
中国是一个传统道德思想极为深厚的国家,到如今,时代虽多有变化,新思想层出不穷,但传统道德仍是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尺。从传统观念看土匪,土匪毫无疑问属于社会的恶人。这些小说不囿于简单的静态的道德判断与政治判断,而是辩证现实地描写土匪,揭示社会土匪为匪的合理性,同情他们的遭难与不幸,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人的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三
不仅理解土匪,同情土匪,而且把土匪写得有人性,突出他们行侠仗义、良善重情、英武刚勇等品质,使这些社会土匪形象具有广泛认同的艺术旨趣与审美价值。
这些社会土匪多为绿林好汉式的人物。例如生相凶恶,为人良善,义气刚正的黑大头,被逼为匪之际提出的三个条件的第一条就是要做个行侠仗义的好汉,“做强盗也可以,只是要做个义盗,不能干这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勾当”,“想咱们的乡党,安塞的高迎祥、米脂的李自成、肤施的张献忠、丹州的罗汝才,当年何等英雄榜样,咱们要做个强人,就要做这号强人。”黑大头重情重义,“凡事得讲个义气”,当曾经搭救过他的杨作新来到后九天时,外貌粗鲁心却细如丝的黑大头一眼便窥破杨作新的身份。于是,报恩之情与提防之心并生,然而黑大头快人快语,“我黑大头历来自作主张。我同情共产党,喜欢这些不顾身家性命,敢和当今政府作对的青年学生”,“贤弟此来,来得突然,我料定是那一路人派来的,所以不得不防。弄明白了共产党,心中倒有几分放下心来。只是话要说到明处,贤弟若为这百十杆枪而来,那么大哥我不能留你。款待一段后,以礼相送;如果确实看得起我黑大头,来此落草,那么从此不分你我……”黑大头这番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映照出他豪侠义气的形象。这类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和武侠小说中常见。
土匪形象到了贾平凹的小说里,便变成了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美男子。如果说,黑大头、大拇指等人物给我们展示的是社会土匪形象的某些侧面,着重描写他们重情重义、忠勇刚强的品质,而将他们的其他性格与行为推向背景或掩去,那么,贾平凹笔下的唐景、白朗形象则是多层面的,他们既有一般社会土匪所具有的扶弱抑强、劫富济贫、仗义疏财、讲义气的品质,又充满人性,有情有义。如果说,黑大头、大拇指等土匪更接近传统小说和武侠小说中的“草莽英雄”或“山大王”形象,那么,唐景、白朗则是绿林好汉与风流倜傥的雅士融为一体的形象。《五魁》中的匪首唐景只露过一次面,然而他的形象却相当生动。唐景,一个年轻的枭雄,白风寨的匪首。他打败官军,在白风寨安营扎寨。在别的村庄山寨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但在白风寨他却大受拥戴。他不骚扰这个山寨以及山寨四周十数里地的所辖区的任何人家,而任何官家任何别的匪家也不能动这地区的一棵草或一块石头。他从不忌讳自己的杀人抢劫,但他却不允许在他的辖区有任何违反人伦的事件。外边传说他有三头六臂,凶狠恶毒,当五魁冒死独闯白风寨救柳家新娘时,看到的唐景竟是一个“朗目白面的英俊少年”,并且“随和客气”,“不像个凶煞”。他的这个直觉判断是正确的。唐景见五魁是条汉子,真诚相待,遂放五魁和柳家新娘下山。
白朗形象是唐景形象的延伸与丰富,他是贾平凹小说中最具魅力的一个土匪形象,也是社会土匪形象中最丰富最出色的形象。白朗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农民起义的首领。 1911 年至1914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四年,纵横豫、鄂、皖、陕、甘五省,攻克了许多城镇,打击了无数的官军和富豪,被百姓称为“英雄”。
贾平凹以赞美的笔触演义了白朗,使其成为一个美的艺术形象。白朗是一代巨匪枭雄,又是一个英俊的男子。白朗是狼牙山寨的大王,赛虎岭十二个山大王中最厉害的一个。他第一个在赛虎岭树起义旗,又独自一家攻克了官军把守的盐池。这位叱咤风云十年,纵横方圆百里,威风八方,有数千人马,闹得石破天惊,官府闻之丧胆,人们想象中的“凶神和恶煞”,意是“玉面英雄”,有着“如菩萨一样的花容月貌”。白朗是义匪,多少年里,在方圆百里的地面上,他和他的大小兄弟杀恶人,劫豪舍,战官军,将劫来的财物分给穷人。他率领队伍攻下盐池,杀官军救盐工,让终年吃不上盐的百姓家家有盐。女人,常常是土匪凌辱的对象。白朗与别的土匪的最大区别,是他不迷女色,严禁侮辱奸淫妇女。正是由于这一点,致使狼牙山的二寨主和三寨主、他的结帮兄弟刘松林、陆星火与他反目远走高飞。又是由于这一点,使被他搭救过的女人对他产生爱慕之情,并为营救他而献身。至此,白朗形象获得了飞扬。
四
两点结论:
第一,新的土匪形象是相对中国当代小说而言的,这就决定了这种形象是在特定的艺术语境中被解说的。如果放开看,新的土匪形象与《水浒》等传统小说及武侠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艺术的长链上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深入透析,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首先,《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既是威震江湖的绿林豪杰,又是替天行道的社会叛逆者、造反者,他们有较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其次,武侠小说和其他小说中的绿林侠士,专注于伸张正义、惩恶助弱、仗义疏财,并以此作为生存方式。白朗、黑大头等土匪虽然也有“梁山好汉”和绿林侠士的种种行为和品质,但他们终归以生计与自救作为他们的生存方面,这也是他们为匪的原因。
第二,新的土匪形象突破当代以往小说描定土匪形象的模式,但作家并不以此否定其他类型的土匪形象,有意进行价值消解或价值削平,而是以自己所刻划的形象所揭示的价值显示价值的多元性。新的土匪形象突破了当代以往小说构造的土匪模式,但并没有以此作为一个明确的新模式,这样,就为继续描写更加丰富的土匪形象开掘了种种通道。
注释:
〔1〕〔3〕余子道:《民国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代序)》,见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引自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详见《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土匪实录》, 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第四章。
〔6〕〔7〕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351页。
〔8〕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华夏出版社 1990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