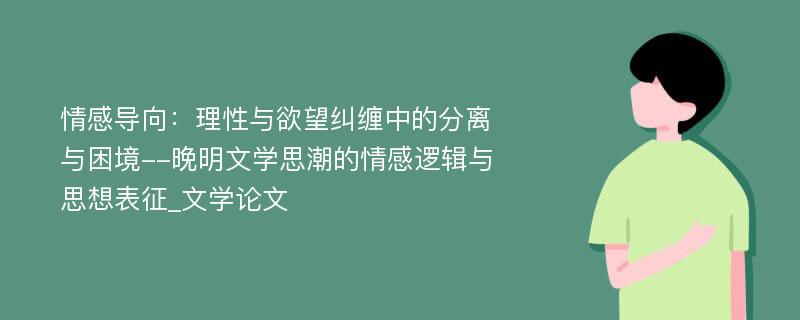
以情为本:理欲纠缠中的离合与困境——晚明文学主情思潮的情感逻辑与思想症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为本论文,情思论文,离合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私”、“欲”成为晚明思想史上的主要探讨的话题,“情”则成为晚明时期文学界的关键词。在晚明的文学界,以徐渭、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高扬“本色”、“童心”、“性灵”、“情至”、“情教”的旗帜,鼓吹“性情”,在当时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飚突进的文学革新运动,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主情思潮,流波所及,一直延续到清代。情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化所讨论的重要问题,甚至有学者称中国哲学为情感哲学①,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情感思维,②中国诗学更是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③那么何以在晚明之后,情感问题重新凸现为一个新的问题?
从思想史而言,先秦儒家中,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其伦理道德本体的建构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孔子讨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孝、仁、礼、仁政、道等观念,是以人们日常的世俗情感为关切点,直接从世俗之“情”中加以引申。如《论语·阳货》章关于“孝”的讨论,即以亲子之情来说明“三年之丧”的合理性,表明孔子已经注意到“情”和“礼”之间的渊源。同样,在孟子那里,其仁义礼智普遍道德本性的确立也是通过人自然情感的端绪扩充完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④从而将人的自然情感作为道德建立的前提和因缘。虽然孔孟思想中没有涉及对人性自然情感的直接讨论,但在我们今天发现的处于孔孟之间的儒家文献郭店楚简中,却集中探讨了性情问题,并且明确将“情”视作“礼”的内在根据,使得孔子与孟子之间从世俗情感到道德情感建立的内在理路线索得以清晰呈现。楚简《性自命出》篇认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汤一介先生以为这里的“道”不是指“天道”,也不是指老子的“常道”,而是指与“礼”相关的“人道”⑤,“人道”也就是当时的“礼”,对此,竹简中其他的篇章有更明确的提法,《语丛一》中有“礼因人情而为之”⑥。《语丛二》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⑦。《性自命出》篇中还指出:“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⑧这些都表明竹简所代表的原始儒家对人的情感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情”作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展示,和心性本体相即不二,同时还作为现实社会中善、恶、忠、信的依据和尺度,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成为社会秩序(“礼”)的起点。
但遗憾的是,孔孟以及竹简这一尚情思想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一直隐而不彰,取而代之的是对“情”贬抑和改写的历史。从荀子开始,“情”站在了“礼”的对立面,被赋予了否定的意义。虽然在“情”和“礼”的关系上,荀子同样主张“礼”因人情而设定,但由于他是持“性恶论”者,因而和孔孟走的是相反路径,“礼”不是为了疏导和顺应人情,而是为了对治人情的恶而出现,“礼”和“情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冲突与矛盾:“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⑨和荀子以“恶”名“性情”不同,后来儒者吸收先秦以来就存在的“性静情动”的观点,用喜怒哀乐“未发”、“已发”来分别性情,以“善”名“性”,而将“恶”归之于“情”。汉代的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说引入儒学,以阴阳说性情。人有性有情视作如天之有阴有阳,而性情之有善有恶,正是由于禀阴阳二气所致,而“阳气爱而阴气恶”⑩,由“性阳情阴”引申出的却是“性善情恶”论。唐代的李翱,吸收佛教的“一心二门”对立转换的结构,提出“灭情复性”的理论:“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11)这一理论直接成为程朱理学贬抑情感的理论先导。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性静情动”、“性明情暗”、“性善情恶”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并以“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情理尖锐对峙的极端方式表达出来。
虽然在思想领域,情感几乎没有容身之地,但在中国诗学中,却给予了情感自由表达足够的空间。以“言志”与“缘情”为标志的诗学纲领确立了情在诗学中的本体地位。“诗道性情”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正如清人边连宝在《病馀长语》卷六中所指出:“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情是诗发生的动因,也是诗的基本内容,也当然构成诗的本质规定。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诗文在“载道”与“言情”之间存在一定的消长起伏,但却始终不能背离情这个根基。在思与诗之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中国人的情感在“立身先须谨重”与“为文且须放荡”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默契与平衡。但是在南宋理学大兴之后,理学对文学领域进行了全面渗透与僭越,打破了这种平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风气与存养心性、复归性理的诗学理念严重偏离了文学的抒情本质与审美精神,也使得传统文化原本就狭窄的情感空间被严重挤压,造成长时间感性人生的逼仄与枯槁,从思想演进的逻辑而言,必然会引起对此理性僭妄的历史反拨。
从宋代理学创立的深层历史境遇而言,程朱所试图建立的高悬于生活之上的天理源自同一性吁求,是在寻求世俗政治权利制度之上批评与监督的正当性理由。“在宋代的士人风气中,弥漫着一种用唐虞三代之制批评汉唐以降的制度改革的氛围,其核心问题就是:新制仅仅是功能性的制度,而不是包含了道德性的礼乐。在制度本身不再提供道德资源的情境中,对道德的追究却变得更为强烈了,在这一情境中,道德评价不得不诉诸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制度关系的力量。这就是天道观和天理概念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12)因而天理建立,最初是体制外知识人以道统反抗政统或者说以道德抵抗制度的一种宏大的文化企图。但在具体生活世界之外,确立一个统摄一切的理性本体,形成对生活世界的理性审视和僭妄,以一种高度的统一性取消了人的差异性,在确认终极本原与确认宇宙万物之间,在否定或轻视具体的知识与世俗情感之间造成的紧张,注定会导致巨大的冲突。这其实是所有的伦理本质中心主义路径都无法避免的结果,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经验的现实世界(基于宗教性要求而形成的)与视此世界为一有意义之整体的概念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人的内在生活态度及与外在世界之关系上、最强烈的紧张性。”(13)但是在西方,理性中心主义并不直接体现为政教纲常,所以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内在的心理冲突。但是在程朱哲学那里,由于将这一种超越性的意义本体直接等同于封建的伦理纲常,“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14)这样一来,在本来封建政治集权制度高度强化的背景下,尤其是明代将其设定为定于一尊的国家意志的时候,直接将一种原本的内在冲突变成制度对人的感性凌夺,其压制的本质变得更加明显,不但消解了理学原有的批判初衷与思想活力,相反其内在痼疾消极的一面会成倍地释放出来,造成了当时思想僵化、士风沦丧等严重的社会后果:“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之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15)程朱之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16)。
为了弥合朱子理性本体和感性个体之间割裂所造成的思想问题与社会弊端,后来王阳明揭橥良知,重建心体。阳明所谓的心体,既以普遍之理为内容,而这种普遍性的理又必须通过个体的肉身性得以实现,“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17),将个体之身视作普遍之理的前提,也就必然包含着对人的感性情感之维的肯定:“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这样一来,相较于朱子学以绝对的理性本体对感性生命的凌夺,阳明的心学显然内在蕴含了对感性欲望肯定的因子。尽管阳明的“良知说”有肯定感性甚而率性而行的这个层次,但是其创立新学的缘起恰恰是针对人欲泛滥的社会现状而发:“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19)所以克制人欲乃是其理论建立的初衷,和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最终目的并无二致,只不过他反对朱子那种通过建立客观天理的外在权威来驯服人心,而是试图将克制人欲的希望交给个体自身,通过自我内在世界道德之维的开启与焠炼在根源处堵塞人欲放纵的可能。因而他虽然承认“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又要求“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认为诸如欣戚爱憎之情会障蔽人们对至理的体认,故应压制情感的宣泄、意气的发扬,保持心境的宁静平和。在对文学的认知上,阳明和之前的理学家轻视文学的态度并无根本区别。以为词章之学“侈之以为丽”(20),惑人心智,且合于道者无几;作者对文字的刻意营构,亦是出于沽名钓誉之心。对早年耽溺辞章之事,心存芥蒂:“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尔,茫无可入。”(21)阳明心学的这一立场,通过挺立心体,凸显主体精神给予后来文学主情论者巨大的精神感召和师心自用的勇气,但其对情欲的禁忌以及诗文的轻视表明文学领域的革新还需要新的资源。
与阳明在思想领域展开对朱子哲学改造几乎同时,在文学领域,李梦阳、王世贞等代表的前后七子派也展开了对理学的清算运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纲领,绕开宋元,直追汉唐,试图解除“理”对于诗文的羁勒,重新恢复诗歌的抒情本质。对于诗文主情,七子派几无异议。李梦阳在《梅月先生诗序》、《张生诗序》等文中屡次标榜“诗发之于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何景明《明月篇序》亦云:“夫诗,本性情而发也,其切而易者莫如夫妇之间”;徐祯卿在《谈艺录》中以为:“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凡此种种,突出了“情”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性。但七子言情基本上没有突破中国言情的诗学传统,相反在实际的创作中,他们常常有“情寡而工于之词多也”(22)的感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过于强烈的“刻意古范,铸形宿模”的复古思想和操作路径。七子的情感论乃是服从于格律论,表现出明显的“以格统情”的倾向。这一倾向,具体而言就是强调文必有法式。
李梦阳自述其少壮时“振羽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23)这种尺寸古法的复古路径无疑严重影响了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本来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对理学的反动,但其通过格调诗法而求诗情的操作思路和朱子通过“格物致知”探求“天理”的工夫理路却如出一辙。况且在明人看来,诗法格律本身就是宋人主理的产物:“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24)而正是这种向外驰求工夫理路日后成为颠覆朱子之学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阳明心学的创立,在学理上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首先在对朱子工夫理路的质疑中转而颠覆其整个哲学根基。因而,复古派通过格调恢复文学本质的企图,某种意义上,是在反对理学中却吊诡落入了理学的窠臼,在反抗束缚中因其褊狭最终又沦为了束缚,为后来的文学革新运动以及主情思潮的崛起提供了解放和桎梏的双重面孔。
在阳明心学及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李贽、袁宏道等代表的晚明文人,以复古派的主情思想纠阳明心学对文与情之蔽,以阳明心学尤其是王畿“现成良知,不待修正”的工夫进路纠七子的重在格调摹拟剿袭之偏,突破心学的道德本体界线而标举自然人性,扬弃复古派的法式古人而主张不拘格套,张扬性情,鼓动私欲,展开了一场情感解放的革新运动。
晚明时期的主情思潮,无论李贽的“絪緼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袁宏道的“独标性灵”,汤显祖的“世总为情”,冯梦龙的“情生万物”等等观念,在中国诗学史上都是一种全新的表述。它一方面将原本蛰伏在德性之下的“情”放逸出来,赋予其形而上的本体意味,使得原本只在诗学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情”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取代原先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理”,一跃而成为个体和社会安身立命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引入之前文化观念中被摒弃的个体的感性欲望,肯定世俗生活和欲望的合理性,使得情具有一种强烈的当下人间色彩,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上都改造了情的观念。但是在情的激进和高扬之后,却在某种历史的机缘之后,归于一种合“理”离“欲”的理性之路。
晚明主情思潮对“情”最重要的发现是确立情的本体地位。在先秦的郭店楚简中虽然有“道始于情”的说法,但这里的“情”并非是作为终极依据,楚简乃是顺着天—命—性—情—道的格局来设定天人模式的,所谓“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表明世界最后的根据乃是“天”。而且这里言“始于情”而非“生于情”也是有差异的。(25)后来的儒家学说,对楚简的这一重情思想也没有有效地继承。在诗学的观念中,“情”所具有的某种本体意味,完全只是针对“诗”而言的,只是在文学领域,“情”才拥有这种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对“情”的这种宽容和推崇很少越过文学的疆域。而在晚明的主情思潮及其历史余绪那里,情不只是文学的先天依据,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的依据和目的。
絪緼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26)
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废饥寒,穷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动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27)
上天下地,资始资生,罔非一“情”字结成世界。(28)
在明清的诗学文本中,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这些表述对于先前的历史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将“情”抬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形而上的层面确立了情的世界本体地位。
从上面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情本体的内涵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1)人和世界诞生的本源;(2)人类社会制度确立的依据;(3)审视和评判世界以及人的价值尺度;(4)具有永恒性和超越性;(5)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6)“情”最高的体现者是人。
当主情论者将“情”确立为人和世界的依据目的时,就已经越出了文学的边界,显示了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思潮,更是一场社会革新思潮。作为阳明心学精神的延续,主情思潮一样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当程朱理学已经不能再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庇护之后,中国人需要重新为自己的文化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一寻求中,主情论者找到了“情”这个古老的资源,或者说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情”。虽然中国哲学被称之为情感哲学,在诗学有漫长的抒情传统,但是那是一种被清洗被阉割掉了的情感,在一开始就没有给个人和欲望留有空间。尽管儒家学者一再强调,圣人乃是“缘情制礼”,但实际上,礼的制定却是为了要将私人情感导向社会人伦,导向王纲政教,名义上是“缘情制(订)礼”,实际上却是“缘礼制(约)情”。在主情论这里,则彻底颠覆了先前的情理关系:“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29)“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30)将先前一直蛰伏在德性之下的“情”放逸出来,赋予其本体地位,使得原本在诗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情”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试图取代先前“理”在社会中的位置。
晚明主情思潮一方面把情感提升到形而上高度而赋予本体性意义,以反对寡情去欲的伦理主义腐“理”和化情归性的先验主义空“性”;另一方面,又注重情感的形而下意义和突出情感的私人性和日常生活化的特征。正如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一书中所指出的,明清思想迥异于先前的中国思想的两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欲”和“私”的标举和肯定。(31)同样,明清时期“情”之内涵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欲”和“私”的融入,这使得“情”在明清具有强烈的世俗人间色彩。
欲望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被压制和清洗的对象,如果说历史上对于“情”的问题还具有某种包容和游移的态度的话,那么在对待欲望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那就是一贯的节欲寡欲乃至于无欲。对于晚明社会而言,欲望勃兴却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表现出来的突出表征,面对这一汹涌而来的世俗大潮,主情论者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同和肯定,公然在理论上为之辩护。李贽将欲望视作人的本然,以为“势利之心,亦吾人之禀赋自然矣。”(32)主张“千万其人者,各得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千万人之欲。”袁宏道的“夫闻道而无益于死,则不若不闻道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为灰尘,何若贪荣竞利,作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乎?”(33)主张以及追慕“五大快活”的人生理想;袁中道的“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的人生表白(34);无不是赤裸裸的欲望张扬。在明清文学中,除了对好货重利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特别揭示和肯定外,彰现欲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男女之情受到广泛的关注以及在这种关注中情欲的公开展示。以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一明清重要的言情文本为例,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爱情其实是源自于一种自然的情欲,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一唱三叹的情感交流碰撞,他们的爱情就迅疾地直奔主题,直接进入身体交往。因而《牡丹亭》中的“情”与其说是热烈的爱情,不如说是火一般生命的欲望,使杜丽娘产生情爱冲动的“是一个男性,一个年青而有蓬勃活力的男性,但却并不必然是某一个特定的柳梦梅。”(35)同样使杜丽娘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至情”其实也是生生不已的生命欲望。对这种裸露的情欲进行更大限度展示的是作为晚明主情思潮变奏的情色文学,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情色文学的高峰期,在这些文本中,那种公然为情欲辩护和展示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这些现象说明,在明清时期,将“欲”视作“情”中应有之义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晚明主情思潮以“情”摄“理”的观念本身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性(私)的张扬。“天理”及其世俗表现形态的纲常伦理乃是一种普遍的理念形式,这种理念本身就是对于差异和个体的漠视,当“情”成为世间礼法产生的依据时,因其首先缘于个体,表明个人重新成为社会的起点,不是个体顺应规则,而是规则顺应个人,“礼”那种定于一尊的强制性和普遍性因而被消解了,评判的尺度交回了个人:“礼者,人人各具,人人不同。”(36)当个体成为自身的依据和理由时,文化的重心就不再是如何呵护一个共同的“礼”,而是如何维系和保存个人的“真”,如果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那么原先中国文化所要求的复归“性情之正”的“正”也就无从谈起。这样一来,之前一直困扰中国诗学的“性情之正”和“性情之真”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什么是“真”以及如何更好表达“真”才成为晚明诗学关心的课题。朱东润先生以为“明代人论诗文,时有一‘真’字之憧憬往来于胸中。……自其相同者而言之,此种求‘真’之精神,实弥漫于明代之文坛。空同求‘真’而不得,则赝为古体以求之;中郎求‘真’而不得,则貌为俚俗以求之;伯敬求‘真’而不得,则探幽历险以求之。其求之之道不必正,而其所求之物无可议也。……明人或以赝求‘真’,其举措诚可笑,然其所见,论真诗,论诗本,论各言其所欲言,不误也。自明而后,迄于清代,论诗言及明人,辄加指摘,几欲置之于不问不闻之列而后快,此三百年来覆盆之冤,不可不为一雪者也。”(37)诚哉斯言!晚明文学中,徐渭的“真我”、“本色”理论,尤其是袁宏道的“性灵”理论都是对情感表达中真实个体的关注。中郎自谓:“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决不肯拾人一字。”(38)这种主张并不只见于形式,也在于其无所禁忌的常常惊世骇俗的个人思想情感。正如陈文新所指出的那样:“至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无论是反映生活内容,还是表达思想、情绪,都不忌讳私生活——私人的故事,私人的情趣,私人的七情六欲。”(39)
与对个体关注相关联的是主情思潮中所表现出来的“自适”意识。阳明心学兴起时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是要解决士人在失去王权政治庇护之后个体如何安顿的危机问题。宋明以降,由于君权在纲常伦理中独尊地位不断强化,加之纲常天理化观念的推波助澜,造成原本礼意本旨的“亲尊并列”观念的失落(40),使得君权对于社会的控制日益加剧,越来越挤压民间社会的活力空间。通过理学与科举结合,士人阶层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越来越依附于权力中心,不得不走“得君行道”的上层路线,寻求庇护。但是维系这种和谐幻想的前提是政统与道统的合一。而皇权本身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以及随时可能挣脱道统的乖戾本质,暗示了这种归附的脆弱特质。晚明士人的感性生活转向很大的程度上源自于皇权乖戾和疏离的绝望心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皇权的疏离就是封建时代士人人生根据的抽离。(41)但其实对于阳明而言,作为其学术和人生转折的“龙场悟道”,最切近的个人因缘是应对在政治危机中险恶的生存境遇,寻求个体在失去王权庇护后的安顿问题。而作为晚明主情思潮灵魂的李贽,其问学初衷也是“穷究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42)。主情论者往往通过消解文学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将其视作自适的个人事件和个人言说方式。如李贽即坦言:“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43)袁中道声称不愿做“出世”之人,而要做“适世”之人,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44)。
因而,晚明主情思潮对“情”的张扬,从文学而言,是对文学的救赎,从思想而言,是对情感的救赎;从社会而言,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是主情思潮这种以欲望为情的安顿之路,在李贽以七十六岁高龄自刎于狱中这一象征事件中,似乎就注定了其必然夭折的命运。其理论困境在于,提倡一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直心而动”当下自然生存方式,将之视作人生的本然之途,该如何面对人性中负面因素恣睢的可能?当李贽认为“本心若明,虽一日享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的时候(45),又该如何认定人欲放纵和自然性情之间的界限?这也许是所有从经验世界企图引申出意义世界的思路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在中国文化之初,当孟子从“恻隐爱敬”这种自然情感中寻求人性至善的道德依据时,就已经为中国文化留下一个无法弥合的缺口。因为这种“爱敬之念”的道德感情,是否能直接证明人性至善的普遍原则,在理论上是有疑问的。明人对“现成良知”的质疑就适用这个命题:“良知事亦不可不理会。观小儿无不知爱亲敬兄,固是常理。然亦有时喜怒哀乐不得其正时,恃爱打詈其父母,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岂可全倚靠他见成的?”(46)但是如同王畿等对罗念庵“世间岂有现成良知”的质疑的回应一样,罗念庵的这一观点本身未免是对人性至善的怀疑,由此便会引起这样的反问:良知不是现成的,难道是“做成”的?(如耿天台、刘元卿等)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主张“现成的”都是良知,难道恣情人欲等等也都是良知?对此的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这样悖论式的推论只能说明价值世界是无法从一个经验世界角度得出的。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所反复说明的,就是依据康德的理路表明这样一种思想:如果道德和伦理旨在教化、更正和发展人的德性,它就不可能从实际存在的宇宙世界和人性状况的描述中推演出来。任何按照知识的路径追寻道德法则的努力都将走向歧途。因此孟子的人性至善论,本是从道德上确立人的依据,却又将其混同于一般生理上的自然情感,使得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上纠缠不清,导致两难境地。“在伦理学问题上,当我们想到一个人‘作为人’时,并不是在人类学和生理学意义上去理解‘人’的概念,而是在目的论中理解人,即人是指合目的的人。”(47)在孟子那里,进入道德的至善境界毕竟要经过一番“存养”的工夫,这样就和自然情感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从而也保证了其道德境界的超越性质。这种“存养”工夫也就是后来王阳明“致”的功夫。它表明人性完善和理想的自由至境是一个在时间的川流上一点点推进的过程,这一漫长的过程永远不能被超越。而当李贽主张任性而动,遵循王学左派以“现成”打通本体功夫的理路时,就是将一种终极理想的人生境界无中介转换成现实人生的操作方式,一方面,它使得中国人一直企羡的大自在变得唾手可得,自然引起“后学如狂”。另一方面,它将终极境界无中介转换成当下的生活,无疑为人的恶欲恣睢提供借口,尤其在中国文化缺乏对一种欲望肯定和引导的思想机制的历史语境下,将人生终极解脱智慧迫不及待地操作成现实生活,所引发的就只能是人的欲望的放纵。正如顾宪成所指出的那样,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重在一“为”字,略去“为”字不讲,在人与尧舜之间直接划上等号,则不免陷入“猖狂无忌惮”。
正是以欲言情的理论困境和欲望放纵在当时引发的人伦溃败的忧虑,晚明之际的主情思潮经历了一个因历史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造自身的过程,在狂飚突进、风靡一时的理论高扬期之后,最终回归于某种历史的理性精神。不但前后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主情论者或在同一阶段也是歧义纷呈相互抵牾。在和理、欲的关系上,并非一味的斥理崇欲,而是如黄卫总所发现的那样,大致存在一个情与理先分后合、情与欲则先合后分的吊诡(48),转向一种努力弥合理欲的倾向。这种取向在汤显祖的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表述中已见端倪。在冯梦龙的“无情化有,私情化公”的期待中,已经明显表露出将李贽、袁宏道等张扬的私情重新纳入纲常伦理的救世企图。而当孟称舜拈出“情正说”,以为“情至之人可以为义夫节妇,即可为忠臣孝子”的时候,情的内容已经被抽空,那种原本的情理的抵牾,被圆融地达成了想象性的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其实就是融“情”入“理”,是情对理的彻底归顺。尽管孟称舜等人仍然坚持“盖性情者,礼义之根柢也”的主情立场,但这只是为纲常礼教披上一个更人性化的外衣而已,在没能对封建纲常名教有根本反思和触动的前提下,情必然要被其掏空和置换,最终还是要落入程朱“天理”的覆辙。
正是“情”面对“欲”和“理”的双重困境,所以在主情思潮落幕的《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曹雪芹一方面如何拒绝纲常名教,另一方面又如何排斥淫欲的侵蚀,在抽空了情的概念中所蕴涵的“理”和“欲”的内核之后,情注定徘徊无依,所以“红楼梦之梦,不止是痴人忏情之告白,也是一个文化心灵逡巡挣扎的告白。”(49)在一种悬于霄壤,上下无依的飘零中,“以情补天”的豪情最终落入佛禅的幻灭。佛禅的归趋表明了士人精神的陨落和从是世界隐退的迹象,“禅宗和审美一样,通常都是政治上的弱者和退缩者的选择。”(50)而这种退缩和幻灭感,宣告了主情论者为中国文化重新寻求安身立命根据之路的失败,表明在整个封建大厦最终坍塌之前,中国人内在情理世界的尴尬状态。
注释:
①蒙培元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里集中讨论中国情感哲学的问题(参见蒙培元:《论中国传统的情感哲学》,《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其实早在80年代初,李泽厚就提出“情感本体”论,将儒家文化本体称之为“情感本体”(李泽厚:《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②参见柴尚金:《中国古代哲学的情感思维》,《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4期。
③“中国的抒情传统”这一概念最早由陈世襄提出(参见《陈世襄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高友工则试图建立此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参见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此后,孙康宜、林顺夫分别从断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吕正惠以及余宝琳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刻画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形成和演变;张淑香则对此一传统之本体作了思辨。萧驰将“中国抒情传统”概括为“于西方文化之神性拯救的宗教精神传统之外,由古代东方心灵所开辟的以审美方式克服异化之精神遗产。”(萧驰:《中国抒情传统之谱系研寻——代序》,萧驰:《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④《孟子·告子上》,《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7页。
⑤参见汤一介:《“道始于情”的哲学阐释》,《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⑥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⑦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203页。
⑧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1页。
⑨《荀子·性恶》,《荀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4页。
⑩《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7页。
(11)李翱:《复性书中》,《李文公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078册,第110页。
(12)汪晖:《天理之成立》,《中国学术》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页。
(13)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14)《朱熹集》卷五九《答吴南斗书》,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45页。
(15)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页。
(16)颜元:《习斋记余·寄桐乡钱生晓城书》,《颜元集》,第439页。
(17)《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18)《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1页。
(19)《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56页。
(20)《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第55页。
(21)《朱子晚年定论序》,《王阳明全集》,第127页。
(22)《空同先生集》卷五十《诗集自序》,台北:伟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437页。
(23)《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第1747页。
(24)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李东阳集》第二卷,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30页。
(25)依据丁原植先生的理解,在中国古典哲学观念中,“始”与“生”的作用是不同的。“a生于b”,是说a直接由b产生,也就是在a(应为b)的内涵中,就具有产生b(应作a)的必然。而所谓“b始于a”,是说b以某种特定的要求而设定以a为根源,是一个非确定性的设定(参见丁原植:《资料辨析与解义》,《楚简儒家性情说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2年,第48页)。
(26)冯梦龙:《情史类略·情史序》,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页。
(27)张琦:《衡曲麈谈·情痴寤言》,《中国古典戏曲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3页。
(28)种柳主人:《玉蟾记序》,《玉蟾记》卷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2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5页。
(30)《情贞类》尾评,《情史类略》,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36页。
(31)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32)《道古录》卷上,《李贽文集》第七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
(33)《袁宏道集笺校》四一《为寒灰书册寄郧阳陈玄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25页。
(34)《珂雪斋集》卷三《咏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64页。
(35)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36)《道古录》卷上,《李贽文集》第七卷,第363页。
(37)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8-89页。
(38)《袁宏道笺校》卷二十二《与冯琢庵师》,第781-782页。
(39)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40)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章。
(41)作家毕飞宇在《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中指出:晚明文人的狂放绝非什么人性的觉醒,“而是第一,因‘宗法’的混乱所带来的极度恐惧,第二,因‘道统’的大崩溃而形成的彻底绝望……是对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毕飞宇:《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读书》2000年第1期,第84页)王毅也认为,晚明放纵的社会风气乃是由于政治的“黑洞化”所引起的(王毅:《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
(42)《续焚书》卷一《答马历山》,《李贽文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3)《续焚书》卷一《与袁石浦》,《李贽文集》第一卷,第45页。
(44)《珂雪斋集》卷二十四《答蔡观察元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4页。
(45)周应宾:《识小篇》,厦门大学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5页。
(46)《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三,《天关语通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75,第123-124页。
(47)赵汀阳:《论可能生活》,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147-148页。
(48)Martin W.Huang,"Sentimentts of Desire:Thoughts on the Cult of Qing in Ming-Qing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20(Dec.1998),pp.153-184.
(49)张淑香:《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
(50)谢思炜:《唐宋诗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6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李贽论文; 国学论文; 言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