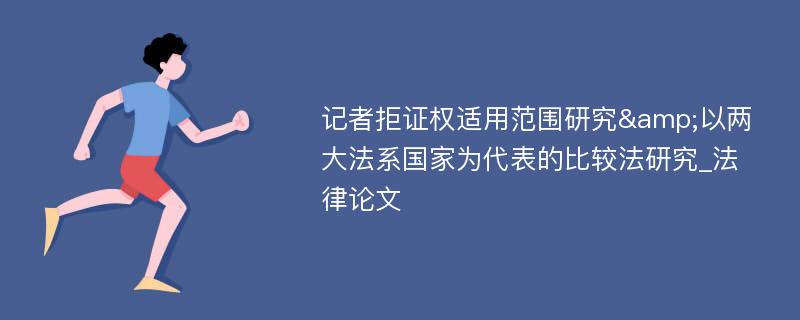
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研究——以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为对象的比较法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法系论文,两大论文,适用范围论文,代表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拒证权(The Reporter's Privilege),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享有的如下权利:拒绝出庭作证、拒绝提供消息来源和可导致消息来源暴露的信息、材料等;免于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等权利——这些权利,是基于职业的特殊性、稳定性和公共利益的原因而享有的拒证权的一种。①
在我国,不仅法律未确立记者拒证权,②司法解释还将提供新闻材料者作为侵权责任人。③而目前,我国法学界和新闻学界对记者拒证权制度的研究,仍停留在呼吁与介绍层面,对该制度的核心问题即适用范围问题,则极少触及。事实上,适用范围问题不仅是记者拒证权的理论难点,也是该制度的立法核心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入快车道、证据制度作为必定修改部分之际,④对此问题的研究可消弥不必要的顾虑,从而更具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即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和大陆法系的德国、瑞典。
一、记者拒证权的相对性和适用原则
(一)记者拒证权的相对性
记者拒证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包括秘密消息来源的人身、财产安全,记者的职业稳定、表达自由及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现代社会确立记者拒证权,⑤既源于理性的考量,也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但该权利并不是绝对性权利,这是由以下矛盾和冲突决定的:
1.就记者和媒体而言,是新闻伦理、私法上的民事实体责任与公民意识、公法上的程序义务的冲突
为消息来源保密,尤其是为内容涉及公共利益的消息的提供者保密,是记者及媒体的职业道德所在,是国际公认的职业伦理准则。1954年,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新闻道德信条》第3条指出:“关于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秘密获得的信息来源,应保守职业秘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围内作最大限度的运用。”⑥2002年,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6条规定:“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应恪守职业秘密。”此外,诸如1934年美国记者工会通过的《记者道德律》、《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德国新闻业准则》、挪威《新闻业务道德准则》、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都有类似规定。
更重要的是,记者不履行保守秘密的承诺,可能导致侵权民事责任。消息来源的身份得不到保密时,其人身、职业稳定和财产往往遭受损害,或面临现实的危险。从侵权构成要件而言,记者是一种故意的侵权,即明知披露消息来源的身份可能导致前述损害或危险而为之,故有过错;而违约披露消息来源的身份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记者与媒体的披露行为与消息来源遭受他人损害或者面临现实的危险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总之,记者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过错、违法行为、损害、因果关系,无一不备,故其侵权责任的成立无疑。而消息来源在得到物质赔偿的同时,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记者的职业身份伴随的职业伦理、民事义务要求其为消息来源保密,但在没有确定记者拒证权制度的国家,记者的普通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要求其履行如实作证的义务,而且,几乎各国诉讼法对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行为都规定了从罚款、训诫到拘留甚至判刑的强制措施——职业道德、法律责任与公民义务、公民意识冲突的结果,使记者面临选择的矛盾。
2.就法官而言,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
法律真实是指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即司法程序中,法官以当事人提供和法庭收集的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所能认定的案件事实。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首先是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法官所能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可能还原客观事实;其次是因为某些可以得到的证据因为其取得手段、方法与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如以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手段或未取得搜查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即违法而不能被采用。显然,法官得到的事实信息即证据越接近“真相”即客观事实,其裁判越能保持公正,然而,囿于上述原因,法官所掌握或所能采用的证据中,可能缺乏查明客观事实所需的关键证据。在一些案件中,这些证据可能掌握在记者或媒体手中。法官天然有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趋向;而记者或新闻媒体出于各种原因,可能并不愿意提供这些关键证据。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在没有得到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其不得不依据与客观真实有距离甚至距离很远的法律真实进行裁判。
因此,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对客观真实的追求程度与对法律真实的认识,反映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裁判依据的矛盾。
3.就立法者而言,是在记者拒证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与强迫记者作证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及司法公正之间的抉择
一个健全的、处于良性运行状态的社会,不仅需要表达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纠正社会弊病,也需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环境安全、公民人身财产等安全,还需要公正的司法以解决纠纷、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平衡社会利益。在市民社会中,三者缺一不可,弱一不可。记者拒证权蕴含的矛盾,表层是其保护的表达自由、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深层次上还有其与公共安全等上述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它使立法者在数种公共利益间面临艰难抉择。而一旦缺乏良好的拒证权制度设计,新闻记者与司法权力发生冲突就不可避免。⑦
在前述矛盾与冲突中,记者拒证或者法律真实、新闻伦理、表达自由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永远都大于记者作证或者客观真实、公民作证义务及司法公正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因此,记者拒证权只能是一项相对性权利而非绝对性权利。
当然,记者拒证权绝对说的主张者的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其认为,只有赋予记者绝对的拒证权,才能真正保护记者和消息来源的信任关系;而记者拒证权相对说的主张使该权利的适用严重依赖于法官的利益衡量和自由心证,这无疑增加了该权利适用的不确定性,秘密消息来源不能对自己是否会被“出卖”有确定的判断,因此,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其只能保持缄默⑧——显然,记者拒证权绝对说的这种担忧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考虑,其事实上对立法与司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承认该权利的相对性即其适用有一定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
(二)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原则
在判例法中,如何衡量适用记者拒证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事实不清导致的“司法不公”所减损的公共利益,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制定法中,即使确定了该权利的适用范围,仍然需要原则的指导——在两大法系相关国家中,这个问题有共同的指向。
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Branxburg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要求记者在大陪审团面前出庭并披露相关信息的申请方必须证明:一是有相当理由确信记者所掌握的信息与被诉事实与行为有明显关联性;二是其所寻求的信息不能通过其他对第一修正案损害较小的渠道获得;三是该信息中包含迫切需求和压倒性的利益——关联性、唯一性、至关重要性(overwhelming),这种衡量方法后来被称为“三步检验法”(three-part test)。⑨另外,尚未走完全部立法程序的《联邦盾牌法》的参议院版本规定了一个“公共利益平衡”标准,即对记者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与不披露的公共利益进行比较。⑩显然,该标准与“三步检验法”中的“压倒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美国“三步检验法”中的“压倒性的利益”的标准也为欧洲人权法院认同,其认为:法院裁定披露相关信息提供者身份的做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的规定,是对言论自由的干涉,除非有压倒性的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的例外情形要求披露消息来源,否则不能要求记者公开消息来源。(11)
虽然美国的“三步检验法”与欧洲人权法院“压倒性的利益的要求”均未排除个人利益,但考虑到公共利益一般高于个人利益,而且刑事诉讼中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公共利益往往也受到侵害,所以,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原则应该是“压倒性的公共利益”原则,尽管这个原则还需要适用范围即具体案件类型与适用客体的诠释。
二、记者拒证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从理论上看,记者拒证权在民事诉讼中应该得到普遍适用:
首先,当事人平等与法官中立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处于相互对立、抗争的地位,“在他们之间展开的攻击防御活动构成了诉讼程序的主体部分,法官对通过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而呈现出来的案件争议事实做出最终判断。”(12)而在当事人对抗的过程中,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义务,平等地主张、陈述、提供证据、防御、抗辩——这种机制是保障当事人最充分展示自己所掌握案件信息,查清案件事实,从而使诉讼程序得以推进的“源动力”,(13)在此程序中,法官中立即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也是民事诉讼架构的题中之义。而如果为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强迫记者作证,无疑使对抗的其中一方明显处于劣势,使民事诉讼的基本架构发生倾斜,从而破坏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其次,如前所述,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原则是压倒性的“公共利益”优先,而绝大部分民事诉讼案件为私益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低于公共利益。在这种案件中,更没有理由与依据去破坏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平等与法官中立的基本原则,让记者为一方的私益提供证据。
第三,如前所述,没有公共利益为依据的记者作证即披露消息来源的行为,因其对消息来源的人身和财产构成伤害或威胁,而可能导致民事责任。因此,对仅涉及私益的民事诉讼,记者拒证事实上是一种义务。正因如此,瑞典对无法律依据的记者相关披露行为进行惩处,其《出版自由法》第3章第3条与《表达自由法》第2章第3条规定,记者一旦泄漏秘密消息来源,应处以罚金或1年以下的监禁。(14)
由于上述原因与依据,在民事诉讼中,立法者没有在数种公共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艰难,法官没有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进行衡量的苦恼,而记者则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拒证权,记者拒证权的相对性在民事诉讼中并未表现出来,或者说表现出一定的绝对性。只不过,英美法系国家针对记者在民事诉讼中身份是证人,或是当事人,在记者拒证权的适用方面有所不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并未区分这种不同。
在美国民事诉讼中,记者的拒证权受到法官慷慨的保护,无论是联邦法院系统还是州法院系统,法官一般会对要求记者披露秘密消息来源适用严格的标准。如果记者不是案件当事人,而只是掌握对诉讼当事人有意义的证据,其通常不会被要求作证。在“水门事件”的余波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诉迈克德案中,该委员会想从侵入水门饭店的盗贼那里获得赔偿,向法庭提出在报道“水门事件”时获得秘密资料的记者披露消息来源的申请,但被法庭拒绝。(15)而且,尚未走完程序的《联邦盾牌法》显然想加强记者拒证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根据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在民事案件中,对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大于不披露的证明责任,由申请记者出庭作证的当事人承担。(16)
但是,如果记者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通常是诽谤案的被告)而不服从法庭命令,拒绝披露消息来源,其可能面临两种不利情况:一是被法官裁定藐视法庭从而被罚款甚至被判刑;(17)二是败诉风险,原因很简单:其不能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18)当然,作为被告的记者因拒绝提供消息来源而被判处藐视法庭的案例极少,所以,尽管美国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需要考虑记者在法庭上身份的不同,但其适用总体上仍然可称普遍。
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其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并未区分记者的当事人或证人身份,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的规定,对因包括新闻在内的职业、职务而产生的证人拒证权的保护,比对因血缘和亲属关系产生的拒证权的保护更为严格:对后者,法官还可以讯问相关信息;对前者,法官连讯问的权力都没有,即法官不能询问记者是否愿意提供消息来源。而且,德国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客体也非常广泛,其《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5项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有权拒绝作证:由于职业上的原因,现在从事或过去曾经从事过定期刊物的编辑、出版或发行工作,或广播工作的人,关于文稿和资料的著作人、投稿人或提供资料的人的个人情况,以及关于这些人的活动的内情……”的规定,对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客体显然未区分秘密与否。
当然,民事诉讼并非全部为私益案件,在环境保护、性别歧视及相关社会伦理秩序的婚姻家庭(如亲子关系、赡养、抚养、扶养)等诉讼中,都涉及到公共利益。但是,对此类民事诉讼中的记者拒证权,各国立法尚未有规定,司法也未见有益的借鉴。
三、记者拒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中的犯罪本身就是对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侵犯,而且许多犯罪行为直接威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制止此类行为具有急迫性。所以,记者拒证权在刑事诉讼中较民事诉讼中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刑事诉讼中也有保护人权的需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中同样重要的两种价值。因此,记者拒证权涉及的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与衡量,在相关国家的刑事诉讼中更为复杂。
当然,记者拒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也并非无规律可寻。从两大法系相关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有三种方式或角度来限定此适用范围:
1.通过规定适用客体进行限定
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客体,以是否经记者采访、加工或创造而言,可分为记者工作成果(经记者采访、加工或创造而来的资料或作品)和非工作成果(指他人向记者提供、未经记者加工或创作的各种类型的信息);以是否需要保密而言,可分为秘密消息来源和非秘密消息来源。两大法系国家记者的拒证权制度,针对不同的客体,有不同的适用情况。
美国39个有“盾牌法”或者规定记者特权法律条文的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19)对记者拒证权的保护各不相同: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一些州规定,对所有消息来源予以保密,无论其是否属于秘密;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代表的一些州则规定记者只能拒绝公开秘密信息来源。(20)而司法实践显示,美国法官对秘密消息来源原则上是予以保护的,根据美国相关统计数据,记者接到传唤其出庭作证的传票,仅有3-5%的比例是被要求就秘密消息来源进行作证的,其余则是关于非秘密消息来源。(21)另外,美国各州记者拒证权的适用是严格区分工作成果与非工作成果的:对前者原则上不予保护,对后者则予以保护,因为法官通常认为:工作成果往往并不涉及秘密消息来源(22)——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美国对民事诉讼中的记者拒证权的原则性保护态度,对消息来源秘密与否的区分,事实上主要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亦即:即使是刑事诉讼中对记者拒证权的限制,也只是针对非秘密消息来源。
而在英国,学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蔑视法庭法》第10条的规定的出发点是“旨在对秘密消息来源进行保护”。(23)
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对记者拒证权客体的规定,也是工作成果、非工作成果与秘密消息来源、非秘密消息来源两种分类方法交叉并用,其记者拒证权适用客体不仅包括非工作成果,也包括工作成果,但是,如前所述,其第53条第2款第2项在具体犯罪类型中对记者工作成果的拒证权进行了限制。与此同时,为保护秘密消息来源不至于暴露,其第2款第3项又进行了平衡规定:“如果证人的陈述会导致揭露稿件或文件的作者或投稿人,或其他消息来源的人的,或关于依第1条第1款第5项所做的通知或其内容者,仍可以拒绝证言”——可见,德国刑事诉讼中一定案件范围内对记者工作成果的拒证权的限制还附有一个条件:不得暴露秘密消息来源。因此,在德国,作为相对性权利的记者拒证权中也含有绝对性因素,即:秘密消息来源的保密是绝对的。这使德国刑事诉讼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体现出“肯定→限制→限制中的平衡”的设计思路。
记者拒证权的原始目的是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对记者工作成果未给予绝对保护,也正因为部分工作成果不涉及秘密消息来源问题。这也符合德国学界提出的基本权核心领域判断基准的“残余论”观点。“残余论”目的是使基本权保有最起码的内容,而不至于被剥夺殆尽,其采纳“核心绝对论”意见,认为对基本权的限制必须从“量”与“宪法政策”两个角度衡量:“量”的问题指可以限制某些人之基本权,但不可以限制所有人的某种基本权利和某些人的所有基本权利;在宪法政策上,则应考虑对基本权的限制是否使该权利名存实亡。(24)
可见,前述国家记者拒证权在适用客体上的共同点,都在于保护秘密消息来源,是否属于秘密而非是否属于工作成果,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2.通过列举违法或犯罪类型进行限定
通过列举违法或犯罪类型对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进行限定,是一种原则性的把握,事实上是立法者对某一类违法或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记者拒证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进行的利益衡量,其蕴含的判断是:前者优于后者。而这种方法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概括性地将某类违法犯罪行为与具体的罪名结合起来规定,对记者拒证权进行限定,美国、英国和瑞典属于这种类型。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因为与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被告人有权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证词的规定有关,在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受到保护的可能性很小。(25)但是,尚未走完程序的美国《联邦盾牌法》的众议院版本和参议院版本显然想改变上述情况,所以原则上承认记者拒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然而两个版本都“塞满了例外”(26),而这些例外事实是通过列举违法行为类型对记者拒证权的适用范围进行界定,如该法的众议院版本规定,在以下情况下记者拒证权不能适用:为阻止恐怖主义行为、可能立即致人死亡或重伤的行为;为确认泄露他人商业秘密和医疗信息的人的身份;当记者目睹了刑事犯罪或侵权行为。根据《联邦盾牌法》的参议院版本,在刑事案件中,对不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大于披露的证明责任,由记者承担。
而英国的立法并未对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范围进行专门规定,只是从其《蔑视法庭法》第10条“除非法院确信,进行某项披露是为了正义、国家安全,或为了预防骚乱或犯罪所必需的,否则法院不可要求某人披露其所负责的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信息的来源,任何拒绝此类披露的人也不能因此被判处犯有藐视法庭罪”之规定中,可以明确推断出,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骚乱犯罪中,记者拒证权不能适用。
瑞典《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法》对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有限制:首先,如果国家雇员,包括军人告诉媒体的信息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媒体有义务披露消息来源。其次,在不涉及出版者(包括记者、其他作者)本人的刑事案件中,以及在披露消息来源为压倒性的公共和私人利益所要求时,对出版者拒证权的保护可被撤销。尤其是,当消息的收集和泄漏构成或涉及叛国、间谍或其他相关行为,以及严重犯罪时,记者不享有拒证权。(27)
二是以具体明确的罪名对记者拒证权进行限定。德国属于这种类型,其《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第2项规定,在涉及破坏和平罪、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或叛国罪、危害外交安全罪、妨害性自主罪、洗钱罪、隐匿不合法取得资产罪的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不适用。当然,记者拒证权在涉及这些犯罪的诉讼中被禁止适用的范围,也仅限于非秘密消息来源,其对秘密消息来源仍然适用。
总之,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立法与司法传统的不同,其限定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时列举的具体违法和犯罪类型,既有一致性,也有不同,其一致性体现在:违反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犯罪及对他人人身及财产构成现实的重大威胁的犯罪,是共同选项。
3.通过列举具体情形限定记者免于搜查、扣押权适用范围
鉴于搜查、扣押的严厉性,免于搜查、扣押权是记者拒证权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而相关国家限制记者此项权利时,均列举具体情形。以这种方法限定记者免于搜查、扣押权的适用范围,目的主要是预防迫在眉睫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查明犯罪事实,其当然也蕴含着立法者的一种价值判断:所预防和需查明的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优于记者拒证权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美国国会于1980年制定的《隐私保护法》第42篇第21章第1分章A部分在规定非记者工作成果绝对免于搜查、扣押的同时,(28)对于记者工作成果的拒证权做了限制,规定下列情形下可搜查、扣押:(1)有理由相信该新闻媒体人员已犯或正在进行与该文书有关的犯罪;(2)有理由相信立即搜查、扣押是防止死亡或重伤害的必须。对于非工作成果的搜查、扣押,除满足以上两项条件外,还需满足以下两项条件;有理由相信以命令形式要求新闻记者提交会导致资料的灭失、变造或隐匿;经法院下达命令仍拒不交出,且用尽司法程序仍不遵守,或再对其下达命令将危及司法正义——这两项条件强调的是相关信息获得渠道的唯一性,或者说前两项是搜查、扣押记者非工作成果的必要条件,而后两项是充分条件。
而这种观点在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也得到体现,其第11条规定,对于“某人秘密持有的新闻资料,包括文件或者文件以外的记录”,都禁止相关扣押。当然,记者并非对所有秘密消息来源均享有拒证权,根据《蔑视法庭法》第10条规定,为了国家安全、预防骚乱、预防犯罪,对记者拒证权可限制,当然也可对记者进行搜查,对相关资料进行扣押。
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97条第5款规定的对记者搜查、扣押的条件与美国《隐私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很相近:必要条件是当记者具有共犯或有庇护、藏匿犯人嫌疑,记者掌握的资料等物品是以犯罪行为获得的,或实施犯罪行为时使用的,或计划用来实施犯罪的;充分条件则是“不能或者很难以其他方式调查事实或者查明罪犯的居留地点”。只不过,德国强调了考虑到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这种搜查、扣押必须是“不超出与案件的关系”,这就是学界所谓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适用中的“比例原则”,它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符合合法性、妥当性与目的实现重要性三要素。(29)
可见,上述国家限制记者免于搜查、扣押权的共同点在于:当记者涉嫌犯罪时和为了预防将要发生的犯罪。
与通过列举违法或犯罪类型限制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的法定性相比,通过列举具体情形限制记者拒证权明显带有法官自由裁量性,也就是说:对公共利益重要性的衡量由立法者决定,而记者拒证行为究竟是否会使相关犯罪发生即伤害相关公共利益,则由法官判断。
总之,在刑事诉讼中上述限制记者拒证权适用的三种方法中,规定适用客体的方法是立法者或法官基于记者的利益或消息提供者的利益,对该权利的核心与基础部分进行保证,其既是记者拒证权的起点,也是该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列举具体犯罪或违法类型,及规定不适用免于搜查、扣押权的情形的方法,则是对该权利的限制。这三种方法基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勾画出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范围。
四、结论与建议
记者拒证权是相对性权利,但这只是起点,关键问题是对该权利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为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
1.我国记者拒证权适用原则
借鉴前述国家记者拒证权制度的经验,我国记者拒证权制度的原则应该是:实现压倒性公共利益的原则。此原则可表述为:信息与案件重要事实密切相关;该信息对案件审理极其重要,以至于缺少该信息将会直接导致较新闻自由更大利益的严重损害。
就适用范围而言,借鉴前述国家的经验,在我国记者拒证权制度的建构中,应在前述原则下,以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为基本分类标准,对记者拒证权适用范围进行界定。
2.我国记者拒证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在相关环境保护、性别歧视、婚姻家庭纠纷以及一些大规模侵权导致的群体性案件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中,应该引入“公共利益平衡”标准,即记者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与不披露的公共利益的比较,但是,对前者重要于后者的证明责任,由申请记者出庭作证的当事人承担;而法官对此应该有自由裁量权——在此情况下,记者拒证权应规定为一种权利,如果记者放弃,不应承担责任。
在涉及私益的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应规定为一种义务,如果违反,应承担民事责任。
3.我国记者拒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我国未来刑事诉讼中记者拒证权的适用范围的界定,也可采通过列举违法和犯罪类型、列举其他具体情形及规定适用客体3种方法,具体为:
在涉及以下违法、犯罪等情形中,禁止或限制记者拒证权的适用:(1)涉及叛国、间谍、恐怖主义等涉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犯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危害公共卫生、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以及严重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犯罪;(2)为阻止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的行为、对他人人身或财产构成重大威胁的行为(此时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应符合谨慎原则);(3)当记者目睹了刑事犯罪或侵权行为;(4)当记者或秘密消息来源涉嫌参与正在调查的刑事犯罪活动时;(5)其他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大于不披露秘密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的情况——在上述情况下,对不披露消息来源的公共利益大于披露的证明责任,由记者承担。
而鉴于搜查、扣押的严厉性,在限制记者免于搜查、扣押权时,除需满足上述条件外,还需由控诉方承担对于记者披露是获得相关信息唯一渠道的证明责任。
就适用客体而言,应确立作为非犯罪行为参与者的秘密消息来源不被披露的原则。但考虑到“残余论”观点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上述(1)、(2)、(4)项情况不适用此原则。
注释:
①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医生对患者、神职人员对忏悔者、律师对委托人、公证人员对客户等在职务活动中了解到的信息,可免于在司法活动中的作证义务。
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然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④《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在紧张进行中。而无论该法是大修还是小修,证据法部分的修订都将在2013年之前完成。见胡雅君:《民诉法修订面临艰难决定 公益诉讼或年底入法》,《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14日。
⑤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以法律形式授予记者拒证权的是1896年美国马里兰州通过的《保护秘密消息来源法》。参见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第13版(张金玺、赵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73页。
⑥RCFP (The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The Reporter's Privilege Compendium,http://www.rcfp.org/cgi2local/privilege/item.cgi?i=intro,20082 08221.访问日期:2011年1月2日。
⑦根据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的统计发现,从1984年至2006年,美国有17名记者因拒绝透露消息源而被捕,被捕时间大多是几个小时,少部分是几天;至于被法院传唤作证的记者,从2001年至2006年共有65人。参见RCFP,The Reporter's Privilege Compendium[EB/OL],and Jailed Reporters.See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EB/OL].http://www.rcfp.Org.访问日期:2011年2月10日。
⑧Branzburg v.Hayes,408U.S.665 (1972).
⑨Branzburg v.Hayes,408U.S.665 (1972).
⑩Rcfp,Federal shield law efforts,http://www.rcfp.org/shields_and_subpoenas.html#num-ber,访问时间:2010年10月18日。
(11)Goodwin v.UK (1996) 22EHRR123.
(12)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构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8页。
(13)唐力:《民事诉讼构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47页。
(14)冯军:《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论要》,《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
(15)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v.McCord,356F.Supp.1394 (1973).
(16)Rcfp,Federal shield law efforts,http://www.rcfp.org/shields_and_subpoenas.html#humber,访问时间:2010年10月18日。
(17)唐·R.彭伯,张金玺、赵刚译:《大众传媒法》第1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65页。
(18)Downing v.Monitor Publishing,415 A.2d683(1980).
(19)RCFP,Confidential Sources and Information.http://www.rcfp.org/privilege/,访问日期:2011年2月12日。
(20)Outlet Communications,Inc.v.Rhode Island,588A.2d 1050 (1991).
(21)Jayie,Randall,Comment,Freeing News gathering from the Reporter's privilege,114 YALEL.J.1827.(2005).
(22)Delany v.Superor Court,249 Cal.Rept.60 (1988); Minnesota v.Kutson,523 N.W.2d 909 (1994).
(23)[英]萨利·斯皮尔伯利,周文译:《媒体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6页。
(24)陈新民:《论宪法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236页。
(25)唐·R.彭伯,张金玺、赵刚译:《大众传媒法》第1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66页。
(26)Rcfp,Federal shield law efforts,http://www.rcfp.org/shields_and_subpoenas.html#number,访问时间:2010年10月18日。
(27)冯军:《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论要》,《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
(28)The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ornell Law School,"Searches and Seizures by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Employees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igation or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Offenses,"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42/usc_sec_42_00002000-aa000-.html,2008-11-23.
(29)林孟皇:《新闻自由与媒体特权(上)——以新闻记者的刑事诉讼上特权为中心》,《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7年第6月号,19-35页。
标签:法律论文; 刑事诉讼法论文; 民事诉讼当事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法官职业道德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比较法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