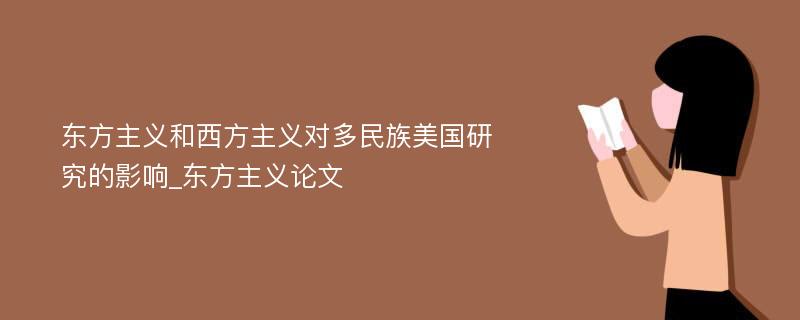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对跨国性美国研究的影响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其大意是:当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不是令人快乐吗?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从远方来到这里结交新的朋友,不是令人快乐吗?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一堂,为此要对各位表示感谢,欢迎你们。能够在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同行面前做主席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我认为,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大家而言意义重大,并且不乏挑战。我要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亚洲”以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学者而言,身处在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如此强大、甚至是难以逾越的背景之下,他们所从事的跨国性学术交流会受到何种影响?
一
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为什么决定同大家一道思考这个问题。在筹划这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的时候,我(们)在每个环节都曾遭遇到,或者说是引发了时而是隐性、时而是显性的划分行为,例如对中国与非中国、“西方”与“东方”(本人在下文中还会提及这两个词)、欧洲/北美与亚洲的地域范围划分问题。有时,这些概念上的划分只是名称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划分却具有其他的根源。我们是否能够对这种划分现象进行解析,以便理解得更清楚呢?
我将举几个筹备过程中的例子来为我们在未来三天内将要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些思想的框架。最后,我要呼吁大家采取行动,去抵制某些条条框框可能会对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以免影响对未来的希望。然而,讨论这些话题并非易事。我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有时候,这些问题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因此而有所收获,承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这次会议不仅会激励我们去应对这些问题,而且也是一次机遇,让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并取得突破。
在探讨是否可以在中国举办这次会议的时候,我首次意识到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的思维可能会成为问题。当时有几位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惊讶地说:“没有人会参加的!”然后他们又抱怨说:“太远了!”结果对于第一种担心的回应是:与会者虽然与以前的会议——像在荷兰的莱顿、加拿大的渥太华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召开的前三次大会——有所不同,没有那么多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但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这次会议。这次有许多中国学者与会,而参加前几次大会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对于第二种忧虑——“太远了!”——我的回答同时也是问题:离哪里太远了?!
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界——也许是一种想象,但却是必要的想象,因为我们所憧憬的是全世界的学者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会有预先设定的近与远,其中的远近关系应该是复杂的。在这样的世界上,有多个中心、多个边缘,它们之间所有的这种远近关系都是在不断变换的条件下,根据相互的关系计算出来的。譬如说,我所说的“近处”也许是你所说的“远处”。我开展学术和日常活动的中心也许处于你的活动中心的边缘。
这些担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与欧洲和北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充满热忱的学者群体。学会创立之初,我们建立的关系都是我们熟识、信赖的人。关于全球性学者组织的设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设想克服了美国研究、拉美研究中的国家性格局,或者说是地区性格局。我们感谢首任主席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先生,以及到意大利的贝拉焦出席第一次大会并讨论筹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同行们。他们把梦想变为了现实,从而使我们的讨论跨域了多种界限,如国家、地区、南北半球、语言以及学科的界限。
然而,在亚洲举办我们的大会确实是一项新的挑战——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正在逐渐壮大。但是,这在许多方面让我们感到不舒服。首先,我们要说服参加前几届大会的同行们来参加这一届的大会。这意味着,要计算从巴西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巴西飞往里斯本的票价做比较;要计算从旧金山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旧金山到莱顿的票价相比;而且,要向来自以上地区的学者们证明,虽然机票贵一些,但与前几届相比,这里的住宿费、餐饮费、会务费要低得多。我要求助手在理事会召开之前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可是,我明显感觉到,人们所感知到的并非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思想上的距离。为此付出时间和金钱是否“值得”?使这种距离感愈加强烈的是,在欧洲和北美,并无多少人读过从事美洲问题研究的知名中国学者的著作。2005年,在香港举行的由中美教育基金会(US-China Education Trust)主办的中国美国研究联络会(China American Studies Network Conference)上,资中筠教授曾就知识流动的不平衡状态做出过这样的总结:“在对相互的研究和著作的熟悉程度上,中美学者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我们的美国同行几乎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美国研究著作”。①
确定了会议地点之后,开始实施计划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办事方式和“国际的”办事方式相关。当时,我们已经面临太多由于使用各种名号所造成的思想及政治上的困境。对于我们来说,部分的挑战在于要理解隐含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影响到了大的观念,又如何影响到了更加细微的内容,以及实际表现。比如说,我们所筹办的是邀请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参加的中国会议,还是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组织会议的规范是要遵循中国的模式,还是另外一种模式(我所说的“另外一种”指的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在荷兰、加拿大和葡萄牙召开的前三届大会的模式)?膳食的准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5月,当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会议做筹备工作时,主办者曾经向我解释说,他们会为所有与会者提供膳食保障,而餐费包含在会务费当中,因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惯例。在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所举办的往届大会中,与会者会自行负担餐费,并自行选择是否出现盛大的宴会。如果与会者决定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数额就会增加;而不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用就会减少。我们最后选择的是包括一切费用的会务费模式。
第二个差别是关于发言者的时间分配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也值得思考。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时间一般都是30分钟,这样听众就不会感到厌倦(我希望自己没有让大家感到厌倦)。但是,例如在美国,主题发言的时间一般至少有40至50分钟,之后还会有深入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感到乏味,还是要待下去!)在此次会议上,我们只在全体会议的环节中遵循了美国的惯例。
贯穿着这些细小问题的主线就是,主办者与非主办者在处理事务方面的区别。也许无论身处何地,都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认为,这些现象所隐含着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确定,这次会议会成为一次中国的会议,或是一次“西方的”(我在此使用了一个隐含着最大危险的词汇)会议……或者是兼具东西方风格的会议——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调和。我还将谈到使用“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的问题。请允许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证明我们合作时所遭遇的挑战。
在对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进行分组的时候,由来自印度、新西兰、土耳其和美国的代表所组成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项目委员会代表收到了两份表格。这些表格是由李期铿教授细心准备的,他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两份表格中,一份是为“国际”学者准备的,另一份是为中国学者准备的。第二份表格中的姓名是用汉字书写的,而只有一位国际美国研究学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通晓汉语。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是一个应用多种语言的组织,我们的成员使用多种语言来交谈、写作和阅读,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英语,或者应该说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在此,我想明确一点,我并非要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我只是注意到,在这个会议现场,与会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共有十余种,而英语是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
两份中英文论文提纲的汇总表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内外有别的思维模式。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的同时,我们在尝试着一道工作、一起思考、充分信任对方,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努力从多种角度、多种学术立场来理解我们共同的研究对象。在最近出版的《萨方迪:南非与美国研究》杂志上,我把这种观点称作“多棱镜式的美国研究”。②
我认为,细致入微、切合实际,而又并不出乎意料的处理方法有益于本人今天所要发起的规模更大、更加艰巨的学术事业。把世界分为两种模式的思想是由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所造成并维系着的,我们是否仍然深受这些思维模式的约束和限制?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这些思维模式又将如何限制我们彼此之间,以及对彼此的学术成果的期望,又将会如何制约我们在未来团结一心、创造新知识的理想?
二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概念。虽然表面看来,这两种相互补充的思维方式仅标示出两个地区,但这却把大部分的世界排除在了研究范围之外。非洲大陆上国家、种族、语言众多,但这片大陆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在殖民语境的中心地区被培养起来的精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世界主义”的一部分,但那些贫穷、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人口难道就不属于想象中的“西方”吗?拉丁美洲该属于哪里呢?当然不是东方(尽管在巴西和秘鲁,有大量的人口都有日本或中国血统),但确切地讲也并非是“西方”一词的通常所指。或者说,当地的城市知识分子和精英属于“西方”,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则不属于“西方”?
“西方”究竟指的是哪里?从其所指意义而言,某些地区和人口无疑“属于”这一类别。如瑞典、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但美国的一些后殖民时期的领地,如关岛,也许不属于西方?)……日益壮大的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属于西方?(那么斯洛文尼亚呢?波斯尼亚呢?)穆斯林是否属于这一虚构的“西方”的一部分?或者,西方所暗指的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世界?南美洲是否属于“西方”呢,比如乌拉圭?如果西方并非是一个地域,而是一种观念,那么东方又是怎样?哪里是确实属于东方的?中国当然属于东方,还有日本(虽然日本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和东南亚。那么,印度和伊朗是否属于东方呢?俄罗斯的东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否属于东方?阿留申群岛以及当地居民是否属于东方?塔斯马尼亚岛呢?
“东方”和“西方”是宽泛的概念划分。倘若着手搞清楚这两个词所指的是哪部分人口、哪些区域,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我们还会认识到,在部分意义上,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模糊性。同时,这两个概念的“核心”所指总是由其模糊性所造成的。这样一来,世界就被分成了两半——但同时却有一大部分世界因此而被忽略。我们新近使用的术语,如南半球国家(the Global South)和北极圈周围的原住民因纽特人和萨米人,已经突破了以上两个概念的疆界。但在历史和影响方面,新近出现的术语却不能和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词语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概念是东西双“方”在长期的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中所留下的遗产。
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主义》中,爱德华·萨义德明确而细致地向我们证明,东方和西方是二元对立的。萨义德在其著作中深入剖析了长期以来由欧洲和欧洲裔学者所描述“东方”的特点,并由此证明,他们所描述的东方不是惹人喜爱的,就是令人厌恶的,他们的判断都是武断的。③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仅描述了欧洲学者对其所说的“东方”地区的猜想。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而言,东方主义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认识(episteme)的整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东方主义:它是一系列假设、事实、虚构和思想意识,它们构成了却又自称解释了一种学术和政治的想象,在此所指的是对欧洲以外的某个地方的想象。
萨义德着重研究的是支撑欧洲对于“东方”认识的信念,而他所重点关注的“东方”是中东(又一个问题多多的名词,因为这明显会引出一个问题,即中东是指“哪个地区的中间地带”?)中东是在什么的中间,是在谁的中间?然而,萨义德也可以把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地区对于欧洲的这种东方主义的认识具有长期、丰富的影响,而且这些地区与中东地区对欧洲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甚至对于美国及广大美洲地区的东方主义的认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于这种认识,萨义德称之为“对于现实的政治性解读,而这种解读造成了熟悉的一方(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一方(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④这种“虚构的地理”⑤制造并维系一种两个相互差别的世界,并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关系的基石。⑥虽然萨义德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的各种学术话语中,这种认识和假设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他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一种势力强大的“隐伏的东方主义”。⑦目前,在学术界内外,这种隐伏的东方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萨义德认为,几个世纪以来,隐伏的东方主义的影响一直明显存在。在30年后,萨义德的论断是否仍然正确、仍然具有意义呢?
用来描述神秘“东方”的特点有:“东方”据说是原始、幼稚、非理性、混乱、神秘、落后、奇怪和暴虐的。另一方面,对于东方的典型描写还有:感性、性感、智慧(正如“东方智慧”的观念),而且东方也是超越想象的古老之地。东方是美、欲望和智慧的源泉,但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断中,东方和东方民族并不值得信赖。在信仰和习俗方面,他们与在东方“以外”的地区为之著书立说的人截然不同。东方人总是沉浸在或是辉煌、或是耻辱的过去之中。
不言而喻,东方主义的观点也描绘、创建了一种对于非东方的“西方”的理解方式。东方主义的观点所指出的某些特点暗示着,被称为“西方”的神秘之地与东方恰恰相反:它是理性、现代、直截了当、值得信任的,还拥有透明、公正的法制体系。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知道,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观点没有在发挥作用呢?
这些观点当然仍然存在,只是现在不那么明显,而是更加隐晦了,而且是以一种自我认知的形式存在着。每当我们以主体的身份提及“东方”或“西方”,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假设——以及认识——来讲话。
如果像萨义德所说,我们仍然相信东方主义,那么西方主义又怎样了呢?目前,对立场的界定愈加复杂了。如上所述,所谓的“东方”的特点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神秘可能是正面的——令人着迷,超凡脱俗;也可能是负面的——不可了解、不可预测,因此也不值得信赖。虚构中的“西方”也同样具有正面和负面的特点,因为西方可能被看作是现代而富有的,或者被看作是恃强凌弱、贪得无厌、道德沦丧、专横傲慢的。是可爱的,还是可鄙的,这取决于发言者的身份、发言的目的,当然也取决于比较的基础。
与东方主义相伴而生的是西方主义,陈小媚在其著作《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反话语理论》中对西方主义进行了探讨。⑧陈小媚认为,作为内涵丰富的认识型,虽然“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形成对照,虽然西方主义强调了东方主义所忽视的内容——但西方主义可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正如东方主义的概念一样,西方主义可以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批评欧美的势力,或者被反对者用来批判“东方”。例如,某些政府或团体可能会对他们眼中的“西化”现象进行批判,因为这会导致不道德的世俗化,或是强取豪夺的资本主义。但是,西方主义一词也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渴望,即对那个想象中的“西方”之特征的渴望,而这些特征与当地的本土“东方”特征是如此不同。在某些国家,开展“西方化”的号召可能会被用来促进民主政府体制的形成。或者,如果使用“西方”一词的说话人来自与虚构“西方”相联系的地区,它就会是一种自我认可的话语。例如,有人可能会说:“作为西方人,我一直认为……”
在“西方”,也可以见到对“东方主义”的类似用法。在此情况下,既定的差别可能会被用来支持当权的一方——通过与“东方”的情形相对照而褒扬西方主义。反过来,也可以用与虚构的“东方”相联系的价值观来批判主流的思想、哲学和艺术实践。在美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东方智慧”在嬉皮士的印度印花床罩上得到了体现,受到了诸如约翰·凯奇等著名实验艺术家的欢迎,在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等著作的推动下普及开来。当然,波西格的书更多是与哲学相关,而与摩托车并无太大关联。以上列举的只是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几个例子。
三
这些认识普及面广,而且影响巨大,作为学者的我们是否会免受其影响呢?许多观点促成了这些认识的形成,而只要接受这些观点,我们就会站在西方人或东方人的主体立场之上,那么我们是否会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呢?我们的东方化或西方化的过程是自发的吗?既然这类话语影响力巨大、影响面广,如果我们能免受其影响,那着实令人称奇。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这些话语的功能?它们对于我们的学术交流和研究会产生何种不利的影响?首先,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话语,更加全面地掌握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赖以依存的文化互动工具。下面,我想着重谈一谈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关系。
在美国,阿里夫·德利克是研究中国史的专家。1996年他撰写了一篇十分具有说服力的论文,题为《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在文章中,德利克从元历史的角度对东方主义进行了考量。⑨他认为,虽然东方主义属于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部分,但也应该被看作是亚洲的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而这在部分上是由亚欧知识分子在“接触区域”(Contact Zone)⑩的活动造成的。
德利克对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虽然彼此的影响并不对等,但他认为:“如果说在19世纪初,东方主义已经成为了‘西方’思想的一部分,那么‘西方’的影响也包括欧洲对于东方的认识给亚洲社会所造成的影响。”(11)在论及最近的一段时期时,德利克指出:“正是在20世纪,欧美的东方主义观点和方法成为了中国自身形象塑造和中国理解历史的一个明显的因素。民族主义的崛起促成了这个过程。”(12)德利克认为,东方主义具有化约的性质,它类似于民族主义运动中经常采用的对于文化复杂性和文化冲突的化约方式,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类似于文化主义层面的东方主义,而目前这表现在民族的层面。”(13)
如果民族主义的话语经常是通过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我们”区别于“他们”)的自我主张实现同质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产生于欧洲的“东方主义”的认识如何会在中国等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正如“西方”的观念被用于美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之中,从而把美国描述成所谓的“西方化的现代性”的顶峰。对于自我的定义就是非他者。同样,在民族的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区分和比较的过程,这是构建文化独特性的话语的一部分;它被用于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之中,而这经常掩盖了各个次民族团体的变化、交流和区别的历史复杂性。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怎样呢?德利克进一步指出,“(目前)发生了改变的不是东方主义的消亡,而是中国与欧美(14)之间的权力关系。”(15)换言之,“新中国”的崛起——经济、军事、政治实力急剧增强的当今中国大陆——并不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东方主义思想将会在“西方”或“东方”终结,而是意味着东西方的重新建构和格局分配。例如,德利克认为新儒学“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16)当然,要对这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需要中国问题专家的专业知识,我本人并不在行。我在此所举的例子只是需要继续研究的众多问题之一。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东方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和美洲也同样没有消逝,而是正在重新抬头;这也是需要我们分析和记录的问题,因为“新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2008年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所展现的一样,中国已经重新“登上了舞台”。同样,外界对于“中国”和新“东方”的理解也有待于改变。
德利克认为,东方主义在中国并不是被否定,而是被重建;本人认为,即使面对着当前的新格局,“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认识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如果以上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意味着我们面临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其人数约占此次世界大会与会者总数的一半),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美国问题研究者(人数占此次大会与会者总数的另一半),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会影响我们对于对方研究成果的评价。在我们的会议中一定会存在着多种学术传统。例如在我们定义何为“好”观点,何为学术“论据”,以及何为合适的研究问题时,这些学术传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学术常规并非个人的选择,而是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各种学术环境的明确或隐含的假设。因此,正如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rdieu)可能会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些学术常规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风格中、在我们用来分析评价学术成果的标准之中已经成为了“信念”(doxa)。
1997年,在德利克的论文面世一年后,清华大学英语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也对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17)王宁指出,虽然中国并非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的重心所在,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义在中国的反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王宁认为,不断地建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无论“西方”被视为主宰者还是被主宰者)所造成的是一个没有胜者的局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以外,难道没有其他出路了吗?”(18)王宁对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话语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西方主义“就其对于学术的影响和表现程度来讲,并非像东方主义一样成熟”。他认为,西方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反应——“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19)无论其来源与历史如何,我认为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同样可能会令人裹足不前。王宁告诫我们说,西方主义的持续存在可能会“不利于我们与西方和国际学术界的文化沟通和学术交流……既然(西方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仍然存在……这就值得研究和分析。”(20)王宁在10年以前这样告诫我们,那么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局面是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何种策略会有助于我们改变这种局面?
2008年,在德利克1996年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朱耀伟在其论文《中国身份的重要性:全球现代性时代中的东方主义重塑》中再次探讨了这些问题。(21)在分析全球新世纪中的“中国形象”问题时,他首先否定了中国形象的“真”、“伪”概念。他着重分析的是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特别是由中国大众传媒塑造的但却在中国以外地区传播着的中国形象。朱耀伟观点的细节及他所探讨的大众传媒的背景并非不属于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重塑时期,何为“中国”一词的内容和所指?同时,我想从反方向来表述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期里,“何种内容和所指是非中国的”?
在我看来,我们的部分挑战在于:我们的教育方式、引证体例、分析过程,以及阅读书目会构成框架,在我们思考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亟待展开的研究、合理的论证方式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时,这些框架会影响到我们。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在我们对于知识生产的政治历史认识的基础上展开。要具有开放的眼光,努力理解不同于我们(无论“我们”所指的是谁)自身背景的复杂的学术研究认识和历史。要创建一个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接触区域,要拥有共同研究对象,要拥有并不完全相同、部分重合而又部分矛盾的生产模式的框架——在此所指的是知识生产模式的框架。(22)
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来自不同的学术团体,却在今天汇聚一堂。我们跨越了学科的界限,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工作,我们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合作,我们从国外获得学位,我们在国外以客座身份授课,我们在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天都活动于某一个知识团体之内,这个知识团体对我们形成了最大的影响。就我本人而言,我归属的学术团体、著作出版地点及著作规范、全部的学位、大部分的职位都属于美国,我也在美国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进行这种分析。我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背景所影响,因为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明确指出来的一样,知识总是被从某处创造出来的。我要补充的是,这些创造知识的所在源远流长,并具有政治的框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学术行为。当然,我们对此都了然于心。但是,在未来三天的讨论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对以上的认识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此,我呼吁大家能够倾听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的呼唤,追随爱德华·萨义德的脚步,去努力挣脱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束缚。萨义德鼓励我们要努力实现“一种关怀世界的伦理体系”("an ethic of cosmopolitan care")。(23)很多批评家都在探讨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这两种对抗性范式的存在与运作的强调,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萨义德对此加以强调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在萨义德的晚期著作中有所阐述。正如特纳所指出的:“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世界主义,因为在全球化、文化杂合,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传统东方主义日程进行重写的政治背景下,世界主义已成为学者的世界观。”(24)
但是我想补充的是,秉持世界主义的人所面对的并非是不受政治影响的乌托邦,他们个人也并不能自由地跨越任何疆界。我并不否认过去与现在的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我们作为不同团体的成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各种哲学传统和知识传统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传统是由不尽相同的政治历史所造就的。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经典,也有许多反经典的活动。然而,无论是以含蓄或是以明确的方式提出“西方”和“东方”的观念,事实上都在维护笼统的论断,掩盖和抹杀特殊性。作为学者,我们需要避免这种笼统的论断,除非是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我们以自省的方式把这种笼统的论断作为研究的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跨越学科、语言、民族和认识论的疆界,寻求和展开对双方都具有挑战性的对话、辩论和争论,还可以同时对这种局面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在当前的物质、政治格局下展开——从H1N1流感的爆发,到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到仍在持续的中东地区的战争,这些只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中的几个而已。我们有幸可以成为临时的移民,但这并非出于经济、人权或政治的原因,并非是为逃避某种局面而发生的迁移,而是要在相互改变、相互挑战的合作式知识创造过程中真诚合作、迎接挑战。萨义德所提出的“关照”伦理观及其所暗含的尊重,标志着为促成这种相互关系所需要的元素。
学术会议实质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学术氛围,要进行争论,要交换观点,而不只是交换名片,当然最好还能够创造新的知识。这次大会成功举办并非易事。事实上,这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相信,在某些时候,来自多个国家的大会组委会的所有成员都希望能够少一些繁琐、少一些差异,少一些挑战、多一些共同的设想。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在实现全球化的组织,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有时,我们的路途不免坎坷,也许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断崖,甚至遇到巨石挡道。但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挑战和宗旨正在于此。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组织形式为知识分子积极地创建了一个“接触地带”。实际上,在我们聚集到一起时,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学术团体,也不是各自的大学。我们是以个人的身份选择了在一个共同的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地带,以专业的态度进行互动。感谢大家参与这个真正的共同的事业。我们能够在此会聚一堂,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三天里能够聚精会神……要运用杜波依斯(Du Bois)所谈到过的那种双重视角,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之中,同时又能够站在交流过程之外,观察交流过程——留心我们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就何为好的学术观点、何为有趣的学术问题,以及何为需要了解的内容做出最明确的判断,并且能够尽量发现,如果——这只是假设——我们对对方的预期或者我们与对方的接触被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双重势力所影响,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些思想似乎削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或是限制了我们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那么应该暂时后退一步,暂时抛弃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我们一道争论、研讨、评估和分析的过程中,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论调一定会出现。我希望我们的学术交流能够像今晚的盛宴一样令人满意。我们在这里的交流会开创很多的可能性,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便使接触地带在大会结束之后仍然长期存在。
注释:
①Zi Zongyun,"How Far along the Road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Have We Come?" in Priscilla Roberts ed.Bridging the Sino-American Divide:America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7),p.46.
②Jane Desmond,"Towards a Prismatic 'American' Studies'," Safundi:The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and American Studies,Vol.VIII,No.1 (January,2007); pp.5~13.
③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④Edward Said,Orientalism,p.43.
⑤Edward Said,Orientalism,p.90.
⑥Edward Said,Orientalism,p.5.
⑦Edward Said,Orientalism,p.206.
⑧Chen Xiaomei,Occidentalism: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2nd ed.(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9).
⑨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 (1996),pp.96~118.
⑩这个简洁的术语是由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 出的,它所指的是一个长时间以来所使用的人类学概念。其所指的是经常在极端不对等的境况下所展开的文化接触、交流、变革与混合。参阅Mary Louis Pratt,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e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2).
(11)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p.104.
(12)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p.106.
(13)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p.106.
(14)在德利克看来,欧美一词所指的并不是欧美人本身,而是欧洲和美国所构成的集团。
(15)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p.109.
(16)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p.109.
(17)Wang Ning,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New Literary History,Vol.28,No.1 (1997),pp.57~67.根据1997时的资料,当时王宁在北京大学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方向的教授。
(18)"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p.64.
(19)"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p.66.
(20)"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p.66.
(21)Chu,Yiu-Wai,"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hinese:Orientalism Reconfigured in the Age of Global Modernity," Boundary2,Vol.35,No.2 (Summer,2008),pp.183~206.
(22)Bryan Turner,"Edward W.Said:Overcoming Orientalism," 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Vol.21,No.1(2004),pp.173~177.
(23)Bryan Turner,"Edward W.Said:Overcoming Orientalism," p.174.
(24)Bryan Turner,"Edward W.Said:Overcoming Orientalism," p.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