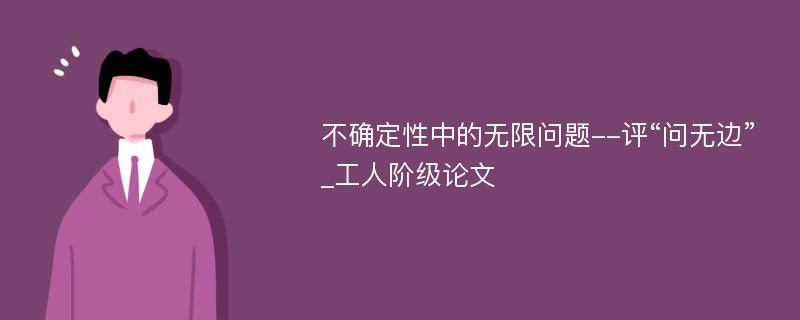
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评《问苍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苍茫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曹征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密切关注着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不是那种花团锦簇、莺歌燕舞似的时代装饰物,也不是貌似揭露、实际肤浅的所谓“官场文学”。他陆续发表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以及这部《问苍茫》等,在以“现场”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激变的同时,更以极端化的姿态或典型化的方法,发现了变革中存在、延续、放大乃至激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承继了百年来“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特别是劳工问题的传统。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小说”,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下展开实践的,它既是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需要,也是启蒙主义必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劳工神圣”是不二的法则,劳工利益是启蒙者或现代知识分子坚决维护或捍卫的根本利益。但是,到了曹征路的时代,事情所发生的变化大概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尽管“人民创造历史”、“工人阶级”、“社会公平”、“人民利益”、“劳动法”、“工会”等概念还在使用,但它们大多已经成为一个诡秘的存在。在现代性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中,这个诡秘的存在也被遮蔽得越来越深,以至于很难再去识别它的本来面目或真面目。无数个原本自明的概念和问题,在忽然间变得迷蒙暧昧甚至倒错。于是,便有了这个“天问”般的迷惘困惑又大义凛然的《问苍茫》。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究竟该如何评价曹征路多年来的关注和焦虑,究竟该如何指认曹征路的立场和情感,该如何评价曹征路包括《问苍茫》在内的作品的艺术性?这显然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现代性过程中的另一种历史叙述
《问苍茫》在《当代》杂志发表的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各个领域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或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央视推出的13集电视纪录片《改革开放30年纪实》。央视在介绍这部电视片时说:
这是一部全景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它高度浓缩了三十年来中国在农村、国企、经济体制、收入分配、金融、对外经贸、政治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就业体制、国防军事、统一大业、对外交往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向世人展示出“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与精神内涵。①
30年,各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这样一起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客观地说,30年来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就连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改变,是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一起发生的。因此,肯定成就是我们的前提。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还有没有被叙述的历史,还有另外的历史也同时在发生。这个历史,就是《问苍茫》中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我们首先感到“苍茫”的不仅是那些还在使用的“知识”和“理论依据”,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和“理论依据”与现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面对现实它的阐释是否还有效。
1918年11月15日、16日,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参加大会的有三千余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了会议并两次发表演讲。在16日的演讲中,他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向人们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三天后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期间李大钊在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他在文章中说:“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特别是6月3日以后,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屈服,“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从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工人阶级一直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主导力量而存在,毛泽东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主张。但是,无论是阶级问题,还是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过程中,因其模糊性遭到了质疑。《问苍茫》中来自四川的五级钳工唐源曾向“知识分子”赵学尧“请教”:“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不对?对呀。既然是初级阶段,那阶级斗争在啥子阶段熄灭的?”“从前没得多少工人的时候,全国也不过两百万的时候,天天都在喊工人阶级,劳工神圣,咱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广东省就有几千万工人,怎么听不到工人阶级四个字了?我们是啥子人?是打工仔,是农民工,是外来劳务工,是来深建设者,就是不叫工人!”
这样的问题是赵学尧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回答的。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上的这些问题因“不争论”被悬置起来。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有道理的,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机械、僵化的理论框架内的争论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争论,中国的改革就难以实践。但是,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现实出现问题逼迫我们作出理论解释的时候,我们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于是,当工人罢工时,身为宝岛电子厂书记的常来临说:“你们有意见就提,公司能满足就满足,不能满足就说清楚。不要动不动就闹罢工,那个没意思。你们有你们的难处,老板也有老板的难处。老板就不困难吗?为了找订单,她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没有订单,我们就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大家都没有钱赚。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当年李大钊的“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理论在这里没了踪影。常来临书记的立场非常明确:老板的难处就是大家共同的难处,没有老板大家就都没有钱赚,大家都不能活命。因此,老板才是“本位”、资本才是“本位”。当然,包括宝岛电子厂的工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们来自贫困的乡村,是为生存不惜任何代价讨生活的。“工人阶级”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现实的全部复杂性使90多年过去后,不再困惑我们的问题才又一次浮出水面。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缩影。那么,是谁创造了深圳新的历史?冠冕堂皇的回答是“人民”创造了深圳的历史。但是,《问苍茫》中的柳叶叶、毛妹们创造的历史就是为了创造自己一贫如洗有家难回的处境吗?就是为了创造毛妹因救火负伤没人负责只能自杀的绝望吗?事实上,究竟是谁创造历史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家曾经争论的问题,那些有思考能力的作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一个主人公、画家Z提出的问题是:“是谁创造了历史?你以为奴隶有能力提出这样的问题吗?……那个信誓旦旦地宣布‘奴隶创造了历史’的人,他自己是不是愿意呆在奴隶的位置上?他这样宣布的时候不是一心要创造一种不同凡响的历史么?”“他们歌颂着人民但心里想的是作人民的救星;他们赞美着信徒因为信徒会反过来赞美他们;他们声称要拯救……比如说穷人,其实那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么?这事业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穷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们因此而承认他们在拯救穷人,这就够了,不信就试试,要是有个穷人反对他们,他们就会骂娘,他们就会说那个穷人正是穷人的敌人,不信你就去看看历史吧,为了他们的‘穷人事业’。他们宁可穷人们互相打起来。”“历史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人世间不可能不是一个宝塔式结构,由尖顶上少数的英雄、圣人、高贵、荣耀、幸福和垫底的多数奴隶、凡人、低贱、平庸、苦难构成。怎么说呢?世界压根儿是一个大市场,最新最好的商品总会是稀罕的,而且总是被少数人占有。”②
《问苍茫》所提出的问题比《务虚笔记》要现实和具体得多,曹征路要处理的不是哲学或历史观的问题。他要处理的是深圳30年来被建构起的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是被遮蔽但又确实存在的历史。在发现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作为作家的曹征路同样充满了“苍茫”和迷惑,他试图展现这个历史而不是确切地判断这个历史。这是一段切近的历史,在近距离的考察、表现这段历史的时候,迷惑、困顿甚至茫然,就是我们共同的切身感受。
二、情感、立场和内心的矛盾
“底层叙事”、“新左翼文学”或被我称作的“新人民性文学”发生以来,评论界和创作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这本来属于正常的现象。当“总体性”的文学理论瓦解之后,文学作品就失去了统一的评价尺度。因此,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思想界的“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已持续多年,至今仍未偃旗息鼓。文学界对这一论争的接续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新左翼文学”的命名被隆重推出。无论是褒贬,曹征路都历史性地站在了最前沿。2004年5期的《当代》杂志发表了他的《那儿》,一时石破天惊。在《那儿》那里,曹征路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立场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流露了他的矛盾和犹疑。我当时评论这部作品时说:《那儿》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着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③事实上,朱主席的处境也是作家曹征路的处境:任何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都显得进退维谷莫衷一是,你可以不随波逐流,但要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儿》里的工人阶级是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也只有产业工人才能做出朱主席这样决绝的选择。但是,在《问苍茫》中,“工人”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柳叶叶、毛妹五姐妹,还是唐源等技术工人,他们都来自边远的乡村,这些还不具有“工人阶级”意识、也没有产业工人传统的农民,是为了摆脱贫困或为了生存来到深圳幸福村和宝岛电子工厂的。因此,无论面对劳资冲突,还是具体的人与事,这个群体都存在着盲目性和摇摆性。需要指出的是,不具有产业工人意识和传统的“农民工”,首先也是人。是人就应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小说中,这些女孩子还没有走出山区,就遭遇了“开处”的侮辱,而且是乡长、村长老爹送来的,“怎么折磨都行”。进入工厂之后,每天是十几小时的劳动,还有随时被解雇的威胁;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有的堕落做了妓女,有的嫁给了曾给自己“开处”的马经理风烛残年的父亲;毛妹则因救火重伤毁容,无人赔偿甚至栽赃嫁祸被逼自杀……这就是《问苍茫》中工人的处境。曹征路描述和关注了底层如此严酷的生活,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情感和立场。这是宣告“新新中国”和“告别悲情”时代到来的人所不能体察和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征路在情感和立场倾向于工人的同时,他并没有采取早期民粹主义者的思想策略,不是为了解决立场问题简单地站在“劳工”一面。事实上,对柳叶叶等宝岛电子厂工人存在的软弱、功利、现实、盲目甚至庸俗的一面,同样实施了批判。初来的柳叶叶不知道罢工的真正含义,在她看来,罢工就有机会穿漂亮衣服到街上逛逛,同时又担心拿不到“加班费”;机会主义分子常来临因为没有参与“开处”使柳叶叶免遭一劫,这不仅在道德层面使柳叶叶感佩不已,同时也被他空洞高蹈的话语煽动所迷惑:她爱上了他。这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正在成长的“新人”形象,我相信作家也是按照这样的形象来塑造的,不然就不会将“打工诗人”、潜伏记者等都安插在她身上。但是,曹征路还是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发现了这个“新人”难以蜕去的先天的巨大局限。这些都表明了曹征路面对“底层”时的巨大困惑和矛盾,也正是这样的困惑、矛盾和焦虑,赋予了作品真实性的力量和时代特征。
同样,《问苍茫》在塑造常来临、陈太、赵学尧、文念祖、何子钢、迟小姐等人物时,都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尤其是常来临这个人物,这是我们在其他作品中未曾谋面的人物。他的特殊性、独特性的发现,是曹征路的一大贡献。
事实上,常来临的问题和他的全部复杂性,远不止柳叶叶经验的那样简单。当“资本霸权”的现实和“资本神圣”的意识形态已经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时候,常来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做出朱主席那样的选择,因他不是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他虽然是个充满了变数的机会主义分子,但同时也有让人同情之处。他和文念祖、赵学尧等人毕竟还不是同一层面上的人。值得肯定的是,曹征路没有道德化地评价人物和历史。一个道德品质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在大时代能够明辨是非担当道义。道德在这个时代的力量不仅苍白,同时也不是评价人物唯一的尺度。因此,对常来临这个人物,虽然诉诸了作家的批判,但也同时表现出了曹征路对这个人物的些许犹疑和矛盾。
三、《问苍茫》的文学性或艺术力量
几年来,对包括曹征路在内的书写“底层”的小说文学性或艺术性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诟病或指责最大的理由除了“展示苦难”、“述说悲情”、“底层”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概念之外,就是“底层写作”的文学性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在“专业”范畴里的讨论,对这个文学现象普遍的指责就是“粗糙”。对“底层写作”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大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说清楚“文学性”究竟是怎样表达的。这个问题就像前几年讨论的“纯文学”一样,文学究竟怎样“纯”,或者什么样的文学才属于“纯”,大概没有人说清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曾经是不战自胜,“政治正确”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合理性。但是,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看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同时,也必须用文学的内在要求衡量它的艺术性,评价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学经验。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年以来,能够引发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学性”,恰恰是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一现象多么合理,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告知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读者对文学寄予了怎样的期待、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不仅激发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情感要求,同时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底层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就像在文学领域没有可能认同的“中国经验”一样,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底层文学”特征。
《问苍茫》书写了“底层”,但它的内涵要远远大于“底层写作”;这部作品可能有些“粗”,但它是“粗砺”而不是“粗糙”。“粗砺”与书写对象有关,写小姐的牙床和草莽英雄,写时尚的“小资”与下岗的女工,在作家的笔下肯定是不同的。因此,“粗砺”只是一个风格学的形容词,而不是评定一部作品的尺度,尤其不是唯一的尺度。在我看来,《问苍茫》之所以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甚至轰动,不仅在于作品全景式的反映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另一种历史,同时也在于小说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小说在整体构思上,以“幸福村”作为主要场景,以地方、家族势力作为历史演进的支配性线索,事实上是一个隐喻。无论深圳如何被描绘为一个“移民城市”,如何“现代”,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深圳当然也是如此。无论有多少外商、外资和内地各色人等的涌入,地方势力在基层都是难以撼动的。文念祖虽然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小说中他是左右幸福村真正的主角,他是幸福村真正的“王”。无论是台商、教授、军转干部、情人还是地方领导,事实上都是以他为中心构建的社会。他成为中心不止是他拥有资本,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族构成的地方势力。他的言谈举止、内心需要等,与农民出身的“王”有极大的相似性:有了钱就要编外太太,甚至猖獗地生了孩子,始乱终弃;有了钱就要显赫的身份,要教授陪伴左右装点门面;最后就是将金融资本兑换成政治资本,要到“台上坐一坐”。深圳无论表面上再“现代”、再“文明”,也不能改变文念祖深入骨髓的“王朝”观念。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看到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洗礼、只有物的浮华,距离真正的现代该是多么遥远。文念祖这个人物的深刻性,是通过作家具体细微的体察和纤毫毕现的生动描绘表达出来的。如果没有杰出的艺术工力,人物的深刻性是无从表达的。
小说中还值得提及的是陈太这个人物。这是一个优雅、时尚、温情、充满女性深长意味的女台商;作为商人,她奔波劳碌筹款定单,给两千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为了赚钱,她也可以在试用期未满就解雇工人,赚取转正前的差价;风月场上她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但温婉多情的背后又隐含着欲说还休的无尽苍凉。弟弟病势、罢工风潮、资金周转等各种问题终于使这个优雅的女人彻底崩溃不辞而别。小说只是客观地呈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似乎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没有憎恨也没有意属。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人物,无意间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陈太身上的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们或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是她的气质高贵、风韵犹存、多情善感、红颜薄命?似乎在是与不是之间。在我看来,陈太作为一个“注意力人物”的抢眼之处,是在与周边的人物比较中突显出来的:常来临的变数、文念祖的粗鄙、赵学尧的萎缩、迟小姐的功利等,这些人性的缺陷在陈太身上似乎都没有,但她也不是一个让人倾心的人物。她有可爱之处,但似乎又隔了一层什么,一种难以言说或名状的距离,使我们在远观的时候只能欣赏却难以亲近。曹征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拿捏的恰到好处。遗憾的是最后将陈太处理成了一个商场上的“娜拉”,在人物塑造方法上落入窠臼,有简单化或取巧之嫌。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样,那还是陈太吗!
在小说中,曹征路没有商量地下了“狠招”和“猛药”的人物就是赵学尧。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学者、教授、一个知识分子。他初来乍到深圳时,还多少保有一点作为书生的迂腐,还有一种难以融入的身份或道德障碍。但经过学生何子钢的点拨训导、特别是初尝“成功”的快意之后,焕发或调动了他身上所有的潜能。无论是对权力、女人、金钱、利益,都以百倍的疯狂攫取。但在获得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卑微、萎缩和工于心计,都暴露无遗。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全部丑恶他都聚于一身。他为文念祖处理情妇迟小姐的事情,为文念祖登上政治舞台舞文弄墨捕风捉影,没有廉耻地拼凑“新三纲五常”,居然还和文念祖的太太发生了性关系。难怪迟小姐评价他说:“你自以为很有学问,其实你也不是个东西。别以为你喜欢谈意义就很有意义了。你不要我的钱就说明你干净了?你比我还不如,我还敢做敢当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挣的什么良心钱?你鞍前马后跑的是什么?那都是太监干的活儿”。曹征路是大学教授,他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德行实在是太了解了。被“阉割”的赵学尧教授当然不是当今知识分子的表征,但曹征路却以写意的方式刻画出了知识分子的魂灵的某些方面。
《问苍茫》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有很多。但仅此而已足以证明了《问苍茫》在当下小说创作格局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但我依然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变革的大时代,真正敢于触及现实问题,表达我们内心不安、焦虑、矛盾和犹疑的作品,要远比那些超拔悠远、俊逸静穆的作品更有力量更给人以震撼。曹征路在一篇创作谈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小说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关注作审美展开的耐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当代文学何日能恢复它应有的尊严。但毫无疑问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④曹征路的上述表达,没有悲壮但却决绝。
苏珊·桑塔格在《静默之美学》中说:“每个时代都必须再创自己独特的‘灵性(spirituality)’。(所谓‘灵性’就是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⑤曹征路在他的系列小说中,在某种程度上再创了我们时代独特的“灵性”。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中,他发现或意识到了我们言说或表达的困境,这个困境事实上是我们的思想危机,在彷徨和迷茫中才会有“苍茫”的发问。这既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叩问,也是对个人精神领域的坦诚相见。他没有信誓旦旦地专执一端,在情感、立场倾向底层的同时,他也表现出了内心的犹疑、矛盾和真实的焦虑。但他感时忧国、心怀忧患,敢于触及当下最现实和敏感的社会问题,显示了他作为作家未泯的良知和巨大勇气。在“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能够读到《问苍茫》这样的作品是我们的幸事。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历经百年但仍有薪火相传。于是我再次想到了鲁迅先生为殷夫《孩儿塔》序中的名言:“这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⑥因为这文学属于别一世界。
注释:
①CCTV.COM,2008年12月18日。
②史铁生:《务虚笔记》第十九“差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③见拙文:《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文艺争鸣》,2005年3期。
④曹征路:《我说是逃避,也是抗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刊》,总第22期。
⑤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5页。
⑥《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