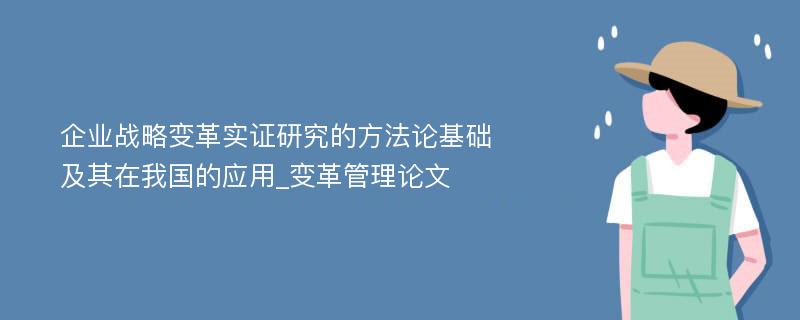
企业战略变革的实证研究方法论基础及在中国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企业战略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5)08-0127-06
一、国内外学者战略变革研究方法的简要回顾与总结
目前在国内研究战略变革的文献中,研究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案例研究。秦志华[1]以在改制中的一家国有企业为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企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二是描述性分析。陈传明[2]、薛求知[3]从企业战略变革程度大小的视角,把战略变革分为渐进式、突变式两种类型;或者根据变革的性质,又可以分为诱导式、命令式两种,并分析了企业战略变革发生的原因与障碍。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很少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战略变革。在国外,西方学者鼓励使用定量的分析方法。纵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等世界一流的管理学期刊,大多采用了定量的分析方法。在很多学者看来,定量的分析方法更有利于创造与积累知识。[4]
定量分析研究不足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战略变革难以定义。二是战略变革研究包括哪些内容不是很清楚。以上这两个问题对于战略变革的定量研究最为重要,但很少有学者给出明确的解答,大多是泛泛而谈。三是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得到定量分析数据的途径一般有两个:第一,利用第二手资料,如公司或政府的公开出版物、图书馆文献资料、杂志、报纸、电子光盘等。客观地讲,在国内,进行战略变革的研究使用第二手资料,理论上不是不可以,但这些资料很不系统,而且也不全面,比如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属于二手资料的范畴,但这些资料大多是财务数据。笔者曾经查阅过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但关于战略变革的数据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关于本公司目前实行的战略类型,而且还是零星涉及。如我国家电类上市公司在阐述本身近年来多元化或专业化战略的转变时,一般用如下语言:“本公司的产业类型包括普通家用电器、房地产、医药,等等……”。而“等等”两个词语过于模糊,给研究者增加了定义上的困难。所以,利用二手数据进行研究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
第二,除了利用第二手资料外,利用问卷调查、访谈的方法使用第一手资料进行战略变革的研究也是一种可选的方法,比如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等。但如何使用第一手资料来研究战略变革,很多学者缺乏方法论的指导。
这里要明确一点,研究方法论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论,是指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而方法,是指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或程序。[5]本文所指的是前者,强调对企业战略变革的研究方法进行一般性的归纳与总结。
二、战略变革的研究方法
1.编码(coding)的方法
该方法是专门对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这是研究战略变革的常用方法。二手资料专门指国家或政府出版物、新闻机构的出版物、图书馆文献、企业公开的许可使用的内部资料等。使用该方法时,首先组成不超过5个人的团队:1个主持人,3~4个参与人。首先,在主持人的指导下,其它人员参与,参考国外文献,针对二手资料的具体情况,进行编码,制定结构式(structural)问卷或半结构式(semi-structural)问卷;其次,由参与人根据二手资料的叙述情况填写问卷。但要注意,为了保证参与人填写问卷的信度(reliability),即保证问卷人填写问卷主观态度的一致性,必须计算问卷人之间的主观态度稳定性(interrater reliability)。
国外学者很早就进行了此类研究。Miller[15]针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说法语的企业,专门应用加拿大权威的出版物,指导自己的三个博士研究生,研究了当企业成功之后企业“惰性”的演变,在“惰性”变化的过程中,企业战略很难发生变革。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首先是成本低,简单易行。而且该方法弥补了当前我国二手资料的缺陷。目前我国学者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来进行战略变革的研究还不是很理想,但除了上市公司数据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战略变革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呢?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该方面的尝试,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贾良定[16]用《大败局》、《大逆转》两本公开出版物,运用编码的方法,对企业家的战略类型进行了定量分析,从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既然编码的方法适用于战略类型的研究,那么,当然也适用于企业战略变革研究,只要有一个团队与几本权威的二手出版物,就可以运用该方法。但该方法对研究团队的素质与二手资料的权威性要求比较高,受研究者主观性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该方法仅仅对特定的对象、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研究,所以缺乏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即很难把该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普通总体。比如贾良定等的研究,仅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研究,而如果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而言,则未必适用。
2.调查者推断(investigator inference)的方法
该方法与方法(1)的相同点在于,都是采用基于研究者本人的判断而对战略变革进行打分。不同之处在于,该方法主要是研究者利用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在操作时,研究者首先对企业适用的战略类型进行分类,然后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根据“高管”人员的回答,研究者就可以推断企业所采用的战略类型,进而对企业战略变革进行研究。
本方法被案例研究者广泛采用,比如Eisenhardt[17]以四个电子企业为案例,最终归纳出了这些企业所采用的战略类型。该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研究者比除高管人员之外的大多数人都了解企业的情况,而且,结合一个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者能够非常客观地对企业战略变革进行定义。该方法最大的缺陷是研究时所使用的样本往往很少,而调查者很难深入到企业内部的决策,大多只能依靠猜测。
3.被调查者自我打分(serf-typing)的方法
本方法克服了调查者推断方法的缺陷,利用被调查企业的“高管”来对该企业的战略变革进行打分。因此,该方法属于应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前提是该方法必须让管理者具备研究者关于战略变革分类的定义与知识。该方法实际上可以应用调查量表的形式进行。国外学者认为,应用第一手资料,主要有三种方法:访谈(interview)、观察(observation)与量表调查(questionnaire)。被调查者自我打分(self-typing)的方法主要是指第三种方法:[4]实行该方法时,首先需要被调查者理解关于战略分类的知识,然后由其对被调查企业进行打分,其方法与一般的量表调查无异。
Coleman应用Miles & Snow(1978)[11]关于战略类型的四分类方法,在一项对27个食品加工与27个电子公司的研究中,首先进行一次访谈,向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介绍了这四种战略类型,然后再对这些战略类型的变化进行研究。而Snow & Hrebiniak[18]以邮寄调查表的方式,同时在量表中附带了一份关于Miles & Snow四分法的说明资料,而以此对战略变革进行研究。但有一点要说明,在对战略类型的事先说明资料中,不能以创新者、分析者、防御者、反应者术语的形式表示,而要经过设计,用通俗易懂的方式。Boeker[13]以美国硅谷30个半导体企业为研究战略变革样本,用也采用了该方法体现。他首先对战略的类型进行研究,先后参考了Miles & Snow[11]的四分法、Porter[10]的三分法、Maidique & Patch[12]的战略四分法,最后采纳了Maidique & Patch的方法。然后由这30个企业的经理对企业的战略类型采用百分制的方法进行打分。首先回忆企业最初创立时的企业战略偏重程度,然后思考企业目前的战略偏重程度,再用各种战略类型的前后相减得到的差值来表示战略变革的大小。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克服了编码(coding)方法的缺陷,能够结合大量样本进行说明,因此结果的精确度比较高。但该方法也有以下缺陷:一是许多企业高层管理者都认为,本企业的战略具有独特性,是难以用研究者本人对于战略的分类概括的。实际上,该方法恰恰是战略管理中资源学派(resource-based approach)的反面,因为根据该学派的观点,企业的战略是独一无二的。但该方法却假设某种战略适用于很多企业。二是该方法的误差也很大。Snow & Hrebiniak[18]发现,当采用该方法使用调查问卷对企业进行调查时,企业内部的不同管理人员对于该企业到底采用什么战略存在分歧,这就削弱了答题者之间的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进而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三是该方法仅仅是企业内部人员对于该企业战略的看法,而该企业实际执行的战略按照企业外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因此,该方法也缺乏企业外部的验证性(external confirmation)。
4.外部评估(external assessment)的方法
该方法主要是利用企业外面的专家对企业的战略变革进行打分。这些专家可能包括企业的竞争对手、咨询公司专家、行业分析师、大学该研究领域的知名教授、政府人员等。Myer对医疗护理产业的全美医院进行战略变革的研究,选用了包括大医院的CEO、医疗器械代理商、当地政府主管人员、行业咨询师、医疗护理专家、大学教授等来对各大医院的战略进行打分,结果,这些专家打分相互之间的一致性非常高。而Hambrick[19]也应用了专家组对健康护理、高等教育、保险三个行业进行战略评估,同样发现,专家组对这三个行业各企业战略类型的打分上一致性非常高。
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结合了专家们的意见,相对来说比较具有权威性与企业外部验证性。但是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该方法应用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企业的战略类型来说,最准确的判断必定是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研究者、企业外部专家对于企业战略的共同认可。就是说,假如以上三方对于企业的战略类型存在共识,则企业的战略类型判断准确度就比较高。然而,在这三者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非常小。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研究者所指的战略类型是Mintzberg[6]所说的意图型战略(intended strategy),而企业外部专家所指的战略类型往往是已实现战略(realized strategy)。二是该方法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最理想的战略变革研究应该是用足够的样本,并采用随机的取样方法。但在该方法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如果采用随机的方式大量抽样,则外部专家的个人判断毕竟是有限理性的,所以未必很熟悉随机选择的样本而导致对战略类型的判断失误;但是如果专门选择专家熟悉的企业,则往往会破坏取样的随机性。
三、中国式背景下战略变革研究方法论的应用
如前所述,目前在中国,战略变革的实证研究是不多见的。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战略变革的研究主要从样本与测量变量两方面入手。
1.研究样本
在国际上流行的战略变革研究中,所采用的样本类型选择很广泛。有的是非赢利组织,如医院、学校等事业机构,也有的是赢利组织,如IT行业。采用非赢利组织作为战略变革研究的样本主要是因为这些非赢利组织的政府主管部门每年都会出版详尽的行业资料,比如美国的航空产业、医疗护理产业、高等教育等产业,这些产业里的机构经常被美国的研究者作为战略变革研究的样本。
之所以采用这些机构或单位作为研究的样本,首先是因为这些样本的资料在美国非常容易获得,而且,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或州政府针对这些产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航空业的解除管制、高等教育机构中文科学位的日益重视、医疗护理行业的打破垄断等,这些政策都导致了这些行业里的单位或机构必然要进行战略变革。所以,选择这些行业的单位作为研究战略变革的样本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另外,战略变革的测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衡量。比如用大学学科的变化、学位授予类型的变化等变量来表示在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战略变革;用医院里各种服务类型的变化或重视程度来表示医院的战略变革的变化等。而在中国进行战略变革的研究,样本的选择主要应该考虑好两个原则、两个条件。
(1)取样的原则
①可获得性原则。在中国的各行业,官方统计数据的详尽程度比起美国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以上三个行业的详尽数据在我国是很难获得的。所以,可获得性原则是研究者应当密切关注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战略变革研究应尽量选择盈利性商业企业作为样本。
②科学性原则。如前文里所讲的战略变革四种测量方法与测量角度,选择样本也要尽量扬长避短。笔者看到,战略变革的编码方法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在应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该方法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大的难度。研究者推断方法与内部人员打分法是进行中国式研究可以借鉴的方法,而且这两种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第四种方法目前还很少有人使用。这表明,这种方法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笔者推荐第二、第三种方法。
(2)所选择的行业
对于所选择的行业,主要应该把握住两个原则:
①尽量选择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在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时,尽量选择政策出现巨大变动的行业,该行业应该是一个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程度非常高的行业,比如家电、IT行业等,而不能是垄断性的行业。
②尽量选择一个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一个行业的企业作为样本最具可比性。而且,不同的行业所选择的战略分类明显是不同的。如国外学者Boeker(1989)[13]在研究中选择IT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时,专门比较了各种战略的分类方法,最后确定Maidique & Patch[12]的战略分类方法最符合行业的实际情况。
2.测量
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了战略选择的不同表示变量:
(1)战略变革的类型变化。Ruelf[19]的研究中,把战略变革分成两种类型:影响程度非常大与影响程度非常小的战略。前者称为“大战略”(strategy),包括企业购并、设立或撤消子公司/分公司;后者称为“小战略”(tacit),包括价格战、产品服务模式的变化、分销渠道的整合,促销方式的变化等。这种大战略与小战略的分类方法可以在我国推广使用。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当企业选择“大战略”时,可以设置战略变革的变量为1,而当企业选择小战略时,可以设置战略变革的变量为0。比如当企业文化的惰性非常强时,一般企业倾向于采取小战略。
(2)战略选择力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借鉴Boeker的方法,先选择行业适用的战略类型,然后验证这些不同类型的战略在战略变革前后企业重视程度的变化,来表示战略变革力度的变化。
(3)战略倾向性的变化。比如战略的攻击性或防御性,在研究时可以假设,当企业的组织结构比较僵化或企业文化的惰性很强烈时,战略可能倾向于防御而非攻击。这些倾向性变量都可以在国外成熟的量表中找到,而且量表适用于中国。
3.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国内外关于战略变革的测量中,方法论上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中比较常见,而且在国际权威的战略管理学术期刊中,也屡见不鲜。
(1)区群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区群谬误是指在研究中,研究者用一类分析单位做研究,而用另一类分析单位做结论的现象。在某些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所研究的样本个体本来是企业,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却以企业中的员工为样本个体。比如一个企业中若干员工每人都填一份调查问卷,而一份调查问卷就成了一个样本个体。这导致了一个企业可能有许多样本个体,而研究者也采用这些结论适用于整个企业。这实际上是犯了以个体的结论来适用组织的情况,艾尔.巴比称之为区群谬误。比如在Boeker(1989)[13]针对硅谷30个半导体公司的研究中,发放问卷的个体是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但得到的结论却适用于企业。显然,个人与组织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2)层次混淆。该方面的问题表现出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战略变革的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产业层次(industrial level)、企业层次(corporate level)、业务层次(business level)以及具体运作层次(operational level)。产业层次是国家或政府部门从产业规划的立场去研究战略变革。企业层次是指站在董事会的视角来看问题,重点关注企业如何提高市场价值。比如母公司与子公司战略的协调、业务的购并等。而业务层次是指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或企业如何在具体的市场上进行经营。比如Philip.Kotler所说的4P's策略:产品、价格、分销渠道、促销,就是指的业务层次的战略。而在一个具体的公司各职能部门内部,比如市场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指运作层次的战略。而中间两个层次目前是国际理论界的主流。在我国目前关于战略管理的研究中,理论界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不是很清楚,动辄称“发展战略”或“战略变革”,而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很多研究都是产业层次上的或者是运作层次上的,这与国际主流的战略变革研究领域不是很相容的。[7]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问题。该缺陷在国内的研究文章中反映比较明显。现在,国内很多文章在研究战略管理问题时还在大量地运用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等一些最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7]国外很多研究者已经证明,方差分析更加适合实验研究,而不太适合问卷调查、编码等基于一手资料或二手资料的非实验研究[8]。因为相比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说,该方法的精确度不高。而描述性统计按照国际的研究标准,并不能称为规范的实证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