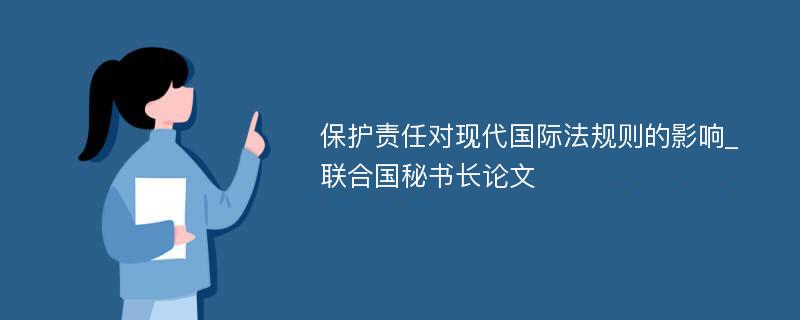
保护的责任对现代国际法规则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规则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7)1-101-03
“保护的责任”,即国家首先承担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但如果国家出现某些相关情由且有关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其害时,国际社会有权通过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干预。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具有广泛影响。
一 “集体安全”困境与“保护的责任”缘起
任何社会都需要良治和规则。“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有序的司法执行制度来确保相同情况获得相同待遇,那么正义也不可能实现。”① 就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来说,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其重要的目标和宗旨,而保护人民、促进发展则是其价值所在。在后冷战时代,诚然,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但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走私特别是地区局势、国内动荡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无疑更直接、更频繁地冲击着和平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卢旺达、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等国家内部的纷争动荡导致的血腥杀戮及其引发的国际国内问题使这一挑战更显紧迫。
非洲的索马里扼守红海通向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位置十分重要。冷战后,随着外部控制势力的退出,索马里陷入了国内各派武装力量争权夺利的混乱之中。到1993年初,索内战共造成35万人死亡,100万人逃往国外,200万百姓处于饥饿状态。为应对人道主义危机,1992年12月安理会通过第794号决议,断定“这种灾难由于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受阻而进一步加剧,从而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特遣队”与后来接替它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随后采取了武力维和行动,但加剧了维和部队与当地军阀之间的冲突,造成较大伤亡,导致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最终遭遇重大挫折,被迫结束。
索马里挫折影响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决心。1994年卢旺达总统空难引发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规模空前的部族大屠杀:百日之内约有100万人死于非命,200多万难民逃往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令世界震惊的人间惨剧。在此次事件中,国际社会没有采取任何强力行动。实际上,当时有一套可靠的战略可以用来防止(至少是大大减轻)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然而安理会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其后果是给卢旺达带来了人道主义灾难。……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情况充分表明,不采取行动是非常可怕的。”③
事物的发展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卢旺达事件相反,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局势的超常规干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约200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人占90%。1992年,在前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阿族人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运用暴力手段谋求独立,而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当局则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反制。1999年3月24日,因南联盟拒绝在北约单方拟定的朗布依埃和平协议上签字,北约绕过安理会擅自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袭,持续78天的轰炸使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加深。
在上述事件中联合国的前后表现是很不一致的。到底人权、主权与干涉的关系如何?出现大规模屠杀时要不要干涉?如何规范、操作?这些实际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层忧虑和思考。在1999年54届联大上,安南秘书长警告说,“如果人类的共同良知……不能在联合国找到它最大的讲台,那么就会有人们到其它地方去寻找和平和正义的严重危险。”在一年后的千年报告中,秘书长再次重申了这方面的挑战:……如果人道主义干预确实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对主权的攻击,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某一个卢旺达、某一个斯雷布雷尼察作出反应?对破坏同我们的共同人性基本原则的有系统的侵犯人权事件,怎样处理?
二 “保护的责任”的提出与发展规范
危机孕育革新。上述系列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促使人民理性思考。同时,冷战后的形势有了很大改变,安全概念被刷新。过去的“安全的概念一度等于捍卫领土,抵抗外来攻击,今天的安全要求则进而包括保护群体和个人免受内部暴力的侵害。”面对挑战,国际社会成立了种种机构进行研讨应对。
(一)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报告:《保护的责任》
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加拿大政府宣布建立“关于干预和国家主权问题的国际委员会”。一年后,《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报告》正式出台。报告在传统“人道主义干预”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保护的责任”。认为“干预”一词在本质上更具对抗性,而用“保护的责任”取代传统的“人道主义干预”,能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主张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免遭大规模屠杀和强奸,免遭饥饿,而当它们不愿或者无力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由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在授权干预的程序上《保护的责任》进行了“防范性规定”。一方面肯定安理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规定如果安理会拒绝或未适时审议有关决议,则可选择其它替代方案:或者由联大依“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程序,以多数票决定之;或者由地区组织根据宪章采取行动,随后再请求安理会授权等。
《保护的责任》首次提出了国家和国际的全面“保护责任”,但针对安理会授权效能可能的不足提出的体制外措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议论和担忧。
(二)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对“保护的责任”的回应
2003年3月,美国以“反恐”为名,绕过安理会,悍然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进攻。战争对联合国的权威构成了重创,使国际社会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④。为应对挑战,安南宣布成立“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小组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对“保护的责任”作出了回应。指出安理会和广大国际社会已逐渐承认,为寻求一个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集体责任新规范,安理会可批准采取行动,以纠正一个国家内部极为严重的弊害。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干预”,而是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那些身陷本来可以避免灾难的人。
作为联合国改革、发展提供咨询的高级别机构,名人小组的报告通过对《保护的责任》给予一定肯定,赋予了“保护的责任”更高的权威,也使“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逐渐向国际共识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干预的授权程序上,名人小组的报告只肯定了“由安理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批准进行”,实际上否定了安理会授权体制以外的选择措施。
(三)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有关保护责任的规定
2005年3月21日,为准备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安南提前发表了《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报告赞同上述两个文件都认同的“新的规范,即集体负有提供保护的责任”。同时认为宪章第51条充分涵盖了紧迫威胁的情况,主权国家对此有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但对威胁并非紧迫而是潜在的情况下,认为《宪章》只充分授权安理会使用军事力量,成员国无权自卫。⑤
秘书长的报告一方面在名人小组报告的基础上,概括肯定灭绝种族、族裔清洗和其他类似危害人类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此情形下,“集体负有提供保护”的第二顺位责任,使“保护的责任”在实体部分有了更明确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武力的使用区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与并非紧迫的潜在威胁两种情况,并各依不同方式行事。反映了既想照顾某些大国对紧迫威胁进行“自卫”的主张,同时又想对滥用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进行限制的思想,实际上是对现状的妥协。
(四)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达成的有关“保护责任”的共识
200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会议成果以最高首脑会议的形式对有关“保护的责任”进行了发展和规范。确认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而如果和平手段不足,而且有关国家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其害,则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安理会采取及时行动。会议重申《宪章》有关条款足以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威胁,肯定安理会维护、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⑥
首脑会议成果是各国意愿的集体宣示,具有引导国际社会前进的旗帜性作用。作为前述文件的发展与规范,“成果”肯定了国际社会的代位作用,并在安南秘书长《大自由》中提到的灭绝种族、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上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罪的保护责任,使有关“保护的责任”经前后四个阶段的发展逐步得以承认、规范和定型。首脑会议肯定了联合国的中央作用,重申《宪章》的条款足以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威胁,实际上对联合国体制外的行动再次进行了否定。会议也重申了联合国大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相应作用,这对加强安理会的效率、透明度和问责性提出了现实要求。
三 “保护的责任”对现代国际法律相关规则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作为世界首脑会议最后规范达成的共识,宣示了国际社会新的立法动向,对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相关规则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保护的责任”对国家主权的规制
主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让·博丹1576年发表的《国家论六卷》里。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正式确立了国家的主权地位。1928年,胡贝尔法官指出,主权“在国家间关系中意味着独立。涉及地球某一部分的独立就是在这一部分行使一个国家职能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排除任何其它国家的”⑦。但在现代社会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它需要受习惯法、条约和国内宪法安排的限制和制约。
人民是国家的当然主人,作为人民主权的必然,主权内在地包含保护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职责。安全概念从国家安全转向人民安全的关注,本身意味着主权出现从作为控制手段的主权向作为责任主权的变化。“主权意味着责任”,既向国内人民负责,也因承担的条约义务向国际社会负责。这既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也是国际责任的要求。国家一旦不能或不愿履行自己的责任,造成人民本该避免的深重苦难,国际社会有权依法进行替代保护。这些法律基础包括《宪章》有关条款、《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人权两公约,以及《种族灭绝公约》、《日内瓦公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等。所有这些协议和公约不仅构建了人权保障体系,增强了保护人权的效力和针对性,而且促进了国家主权豁免理念向国家责任形式过渡。
因此,“保护的责任”实际上对国家主权进行了新的规制,国家管治面临国际社会的适当“监督”,国家主权也包含国家受国际法的约束协调、国际合作、担负共同责任等含义。正如安南秘书长所说的,“如果从事犯罪行为的国家知道边界并非绝对的屏障;如果它们知道安理会将会采取行动制止反人类的罪行,那么它们就不会从事这些行动,也不会期望基于主权的罪行豁免”⑧。也正如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和平纲领》中所说,“国家的根本主权和完整是取得国际任何共同进步的关键。但是,绝对和专属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是了解这一点,设法平衡兼顾国内良好政治的需要与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的需要”。
(二)“保护的责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影响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是尊重国家主权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明确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除国家根据协议而产生相应义务的那些事项外,各国可以根据主权自由处理本国的一切事项,彼此间不得干涉。国际社会确立“保护责任”的规则,却意味着一旦国家内部出现相关情由且有关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其害时,国际社会有权通过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干预。
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300多年前,格老秀斯就宣布,“如果国内司法管辖表现为对人类施暴,则它的排他性就不复存在了”⑨。现代以来随着国际联系的日益增多和广泛,即使地处遥远的国内动荡也可能开始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而影响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共同利益。因此,所谓内政的范围也面临动态界定的困境,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1923年“关于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法令问题的咨询意见案”中所明确指出的:“每一事项是否纯属国家管辖范围之内是一个本质上相对的问题,其答案决定于国际法的发展”⑩。而《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例外,即当各种事态(包括人权灾难)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安理会依宪章第7章规定的执行办法例外。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1991年指出,人们现在日益感到,不能把不干涉国家国内管辖权的原则视为可以大规模或系统地侵犯人权的保护性屏障。现任秘书长安南在2005年的“大自由”报告中也强调指出,任何法律原则,甚至主权,都不应成为掩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大规模苦难的幌子。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了挑战。而在全球化以及相互依存如此密切的世界中,甚至很难再找到“本质上”完全归属于一国管辖范围之内的事项。
(三)“保护的责任”对传统人道主义干涉的限制
“保护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就相关局势对主权国家进行干预,是要规范解决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即主要根据一外国的道德判断,如果一国确有违反“基本人权”而对其内政进行的干预。很明显,“人道主义干涉”如果被个别国家作为一项权利针对另一个国家加以行使,它就可能被滥用,成为达到私利的幌子。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人道主义战争”就与美欧的势力扩张相关。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理念与基督教传统的所谓“正义战争”思想密切相关,由于那时候还不存在主权国家,进行战争主要是出于道德理由,即所谓“圣战”。(11) 然在当代,讨论战争的道德准则已不可能回避国际法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宣布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于国际法原则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具有强行法的地位,因此只有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相矛盾的道德准则才有可能视为正义原则,符合《宪章》“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和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的情形,而回避国际法规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国际法上是难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的。首脑会议规范的“保护的责任”通过对保护的范围和保护的方法进行规范,事实上从实体与程序方面对各种“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限制,使各种新老干涉主义在新的规范面前无所遁形。
四 结语
主权既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屏障,也是责任和义务的象征。在现代社会,“除非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坚实基础,否则任何安全议程和发展行动都不会成功”。首脑会议成果与2002年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则相互呼应,例如都明确规定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属于国际补充管辖的范畴,都可通过安理会行使普遍管辖权等,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期间广大缔约国与安理会某些成员国在相关领域的分歧,从而在国际决策机构与国际司法机构之间架起了某种共同语言的桥梁,不仅使首脑会议成果规范的“保护责任”具有了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使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安理会的相关管辖变得相对便利和畅通,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S.C.Res.794,U.N.SCOR,47thSess.,3145mtg,at2,U.N.Doc.S/Res/794 ( 1992) .
③Se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by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P.1;
④参见李杰豪:《析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制的冲击与影响——兼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改革》,《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⑤http://www.un.org/chinese/largerfreedom/part3.htm
⑥http://www.un.org/chinese/ga/60/docs/ares60_3.htm
⑦Record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Vol.2,p.838.
⑧John H.Jackson,Sovereignty-Modern:A New Approach to an Outdated Concept,97A.J.I.L.782 ( 2003) .
⑨L.Lauterpacht," 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1946,P.46.
⑩PCIJ Publications,Series B,No.4,P.24.
(11)参见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61页。
(12)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古祖雪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