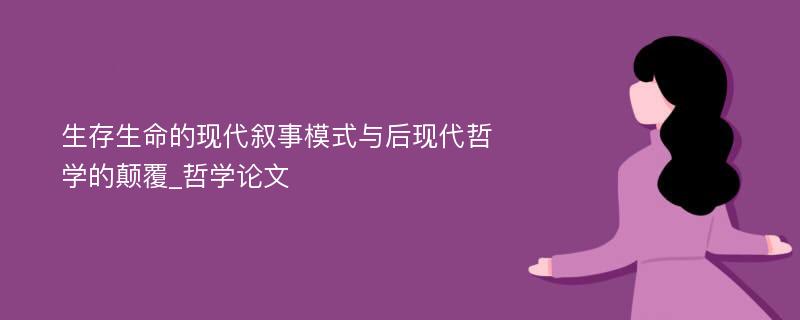
生存命义的现代叙事方案及后现代哲学对它的颠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1-0013-05
一、生存命义的现代叙事方案
时下,面对精神家园失落、人文价值理性低迷、人的生存品质下滑的时代困惑,当代 生存论者以马克思实践人学为基础并借助西方存在主义的理论资源,谋划了对生存命义 进行现代性叙事的种种方案,主要有:
1.生存命义的世界化叙事。有人指认,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内在地相关联,不论是“ 先生存才有发展”或者“以发展求生存”,都表明生存与发展不可分离,互相依存。因 而,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把握,不能脱离发展问题,相反,应将生存问题置于人、人类的 发展视域中加以理解,即将之置于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宏大背景中 加以考察与审视,才能洞见生存哲学的当代命义。[1]可见,生存哲学作为一个时代性 的新论域,一个在新思想中回应时代最实际的呼声的哲学体系,必须“回到事情本身” 即切入当代面临的两大主题,为解决或立意解决人、人类面临的各类生存危机和发展困 境作理性思考,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和理论论证,而不能只停留于 观念领域中,从既有的理念出发,进行逻辑的、概念式的推展。这种世界化的宏大叙事 方案,意在为生存哲学营造一个宏大的、宽泛的世界性理论背景或文化氛围,并凭借凸 显生存哲学与当代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的内在的价值勾连,来强化生存哲学存在的合法 基础和重大的时代感。
2.生存命义的辩证性叙事。与上述宏伟叙事不同,有人主张对人做微型叙事,认为生 存与发展之所以内在地关联,并非与世界性的主题有什么价值上的牵连,而是取决于人 的生命悖论自身。生存与发展是人的生命的两极即生死问题与超越视域:人作为自然存 在物,只有存活才谈得上发展,生存乃发展之基;作为有意识、有理性的存在物,人的 生存价值和意义,是在发展中自我展现、自我生成与完善的。人的生存的真谛在于谋求 发展,发展是生存的高度自觉和超越指向。人的生命是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的统一 ,也就是生存与发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人悟解到自己的有限性与永恒性的终极悖 论。也正是这种统一,使人觉察到自己的悲剧性的终极宿命和向死而生的无畏力量。可 见,这种内蕴于人的生命悖论中的辩证性叙事,具有一种将人的生存引向人的全面发展 的召唤力量,召唤人在社会现实的生存活动中,要以发展求生存,并在发展中克服非本 真的生存,使人从任何虚幻的幸福承诺之梦想中惊醒,将人的所有关系和本质归还给人 自身,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
3.生存命义的历史性叙事。有人认为,生存哲学就是一种关于自我意识如何增长的理 论,其根本旨趣在于凸显当代人的自我觉解,并由此出发而刚强人的自我心灵,赋予人 战胜各种各样的生存矛盾和生存危机的勇敢无畏的力量,让人在灵魂深处去正视人的生 存的全部事实,并以人的全部生命力量,义无反顾地直面这些事实和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从而实现人的自我觉醒。同时认为,生存哲学还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运动。生存 哲学与任何本质主义的形上理性有别,它反对以任何终极性的理性来对人揭密,反对以 任何超历史、非历史的东西对人诠释,而主张人应摆脱任何外在的依凭,尤其应摆脱任 何理性的虚妄,去回归自己的本真生存,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生命。人根本就不应 允许有任何理性存在物在场,否则,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将成为无意义的和多余的 ,人的自我生成用不着借助任何理性来表达。[2](P86)可见,人的价值的自我生成、人 的本质的自我塑造,不仅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依赖于人的历史意识的觉醒 。人只有彻悟自己是历史性的存在即历史性的有待完成者,才能真正摆脱各种理性的纠 缠和各种物欲的羁绊而获得永生。
4.生存命义的现象学叙事。该叙事主张,生存哲学开启的生存论路向(或转向),并非 意欲构建一个新的哲学部门或样式,亦非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哲学问题或研究对象,而是 立意在终结旧的形而上学过程中实现哲学自身的决定性生成,为之开辟一个新路径,借 以凸显哲学研究主题的根本转换——对人的超越指向性作现象学的描述:哲学从人的当 下生存境遇的领会或反思出发,揭示“作为人的人”的价值和意义,让人通过“去”存 在、“站出来活”来展示自己并成就自己。[3](P148)换言之,哲学不在于关注人之外 的所谓终极性的本质或规律,但又不能让渡出“思”,而是让“思”切近于人的当下生 存,对人进行终极性的自我设问,这种设问并不是身份之问或功能之问,而是无由设定 之问。正是这有力的一问呈露了生存理由的幽暗不明,使人从生存性状(现象)中悟出了 自己的有死性、有限性;也正是这有力的一问,摧毁了人的虚饰和沉沦的一生,使人开 始从沉沦于世的平常态出离并对自我进行超越性的追寻。生存哲学作为对人的本质的“ 思”,引人踏上了自我生成、自我超越的漫漫长路。可见,生存哲学不是语言的、理性 的、逻辑的,而是实践的、亲证的、行动的,它并非通过逻辑的推演去揭示人的本真生 存,而是通过实践性事件的自我启示让人回归到生存的内在本源处,解蔽去蔽,先行到 死,向死而在。
5.生存命义的生活化叙事。这种叙事根据生活中的“存生之理”,认为生存哲学应当 向生活本身寻求支持,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远离生活本身而谋化出的各种各样残缺不全的 理性方案,克服这种病态的理性对生活的缠绕,而张扬一种生活至上、唯乐主义的生存 理念,并将之播撒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去占满日常生活中的各个空间,用鲜活的 生活内容照亮并揭示人的生存真谛。人从天性上讲,“食色性也”,人的欲望、意志、 情感、思想及行动都是由现实生活本身引发的。趋乐避苦、追求幸福是人之自然本性, 唯乐原则是人之生存的永恒的人性法则。生活哲学立意直面生活现实本身,倡导人合理 的欲望宣泄和合理的利益谋略,摆脱原有虚妄的生活信念给人带来的虚幻满足,用理性 的手段为生存谋划,为人提供生存应对技巧方面的学问,让人人都能过上幸福而自由的 生活。可见,生存哲学介于并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一方面,它倡导理智地应对生 活,反对将人引向非理性的疏芜之境,引向具有内在性、个体性的生存体验、生命感悟 和生存信念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张扬了个人本真的生存,反对超验的形上理性对人的 现实生活意境的遮蔽,和对人性自身的缺陷和弱点的掩饰。因为,形上理性虽然能引导 人向善向上,从而给人鼓起生活的风帆,坚定生活的信心,但它通过给人期许一个终极 性的理想王国,而助长了人的天真和简单的乐观,助长了人的虚骄和妄想,从而使人走 向否定自己尘世生活和肉体生命的歧途。形而上学则将人的本真生活作为庄严的祭品奉 献给了终极理性,从而成为人的生存的毒汁。生存哲学正是有感于理性对人的自我缠绕 和毒害,才主张生活至上主义并倡导唯乐原则的。诚如张世英先生在批判封建道德理性 时所说,形上理性把属于人的理性,抽离人本身而使之成为客观独立的东西,变成神圣 不可侵犯的神话,从而演绎出了一幕幕“以理杀人”的人生悲剧。[4](P120)
6.生存命义的语言学叙事。有人以海德格尔生存论为依托,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人的认 识功能及其表征的工具,更是人的天性。这是由于,语言总是内在地使人的本真生存开 敞,对语言的反思将触动人的生存的最内在的命义。质言之,人在语言中有他最本真的 居处。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的生存之家。但,这里说的语言并非指传统形而 上学的那种理性化的、逻辑化的语言。因为,这种高度符号化的语言严重遮蔽了人的生 存真义,泯灭了人之为人的高贵而善良的天性,是人通达自己的生存真谛的理障。符号 语言的发现和运用,使人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陷入了边缘化、荒诞化,人丢掉了自我, 人认识和可以创造的只是一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又功能性地使人的生存具有了某种意义 ,人完全符号化了,符号把属于人的东西拿走了,世界成了符号语言独霸天下的语言牢 笼。可见,真正的生存论语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学话语。因为思与诗内在相通,其 共生于人的生存的内在发源地,人诗意地栖居,只有借助诗意的表述,人才切近于自己 的生存命义,也只有在朦胧的诗意中,人才能由语言本身所蕴含着的内在丰富性的内容 所引导,聆听并回应这种本然所是的生存语义,并在其中感悟人的生存命义,使人的生 存本质走出晦暗。[5]
诸如此类的现代叙事方案还有很多,如文化叙事、价值叙事、历史叙事、社会叙事、 人类学叙事等等。在致思人生价值、追问人生命义时,这些叙事方案都先行为人预设了 一个现成的本质,并认为借助现代性的理性框架及其至上权能,就能对人的生存命义及 其本质作出完整性的诠释,从而一个个以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语言等各种不同身 份的现代性主体相继亮相,这一切总汇起来,便构成了当代中国生存哲学言说人之生存 命义的特有谱系。从总体上看,这一谱系的研究路向及其成果,对建构当代中国人学体 系十分必要。事实上,人是一个具有多种存在属性的“复合体”,[6](P276)若将之诠 释为单一的“自然存在物”或者“社会存在物”、“理性存在物”或者“非理性存在物 ”等,[7](P7)都只能看到一个个残缺不全的人;但是,若离开这些片面性的表述,又 只能揭示出一个抽象性的“人”。这种理论表述上的悖论实质上是人的生存悖论的自觉 的心灵观照,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人学情结。正是由于当代学界弥漫着这样一种浓厚的生 命意识、存在情绪和精神特质,才围绕人生悖论并借助西学话语对人的存生之理制订出 了各式各样的叙事方案。正如人在地上走出的路,不是一条而是有许多条一样,对人的 生存命义的切问而编织出的人学图景,也不只是一种,而应有许多种。正是这个多种图 景的组合方案,才使人的生存命义及本质得以朗显:人之生存并非苟生性地活着,而是 “站出来活”,积极地、自觉地自我生成;人是生成着的自由存在物,人的生存命义和 本质并非是既成的或者可以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状态(如语言、价值、文化、历史等), 而是播撒于自己有意识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的自成目的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过程之中 ;一句话,人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物。集对象性与非对象性于一身的实践活动,使人能 自成目的又自作手段,从而确证并不断刷新着人的生存命义和本质。[8]
二、后现代哲学对现代叙事方案的颠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在中国人学、生存哲学中的大量引介, 目前基本上已确立了独具时代风貌和中国品格的后现代人学立场及生存指向。在持这种 立场的人看来:对人的生存的种种现代性叙事方案,作为一种理性的表达,都行之未远 且最终都复归到了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路向,实质上是对形上理性的各种变相的拯救,因 而,仍然带有对人的生存产生各种压制的理性主义的总体性踪迹,作为对人的整体记述 ,仍显现为一个整体形象、一个大写意义上的“人”。而具有后现代主义指向的当代人 学,虽然压根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或学派,只表现为一种思潮、运动或文化 现象,但它以特有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瞥见到了现代主义人学叙事方案中的各种弊病 ;虽然由于对这些弊病没有找到切当的救治良方而采取了极端的做法或者干脆躲在一边 ,然而它却呼唤出了一种相应的生活态度、生存样式和生活情调,[9](P38)触及并影响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文化时尚,早已深入人心并确实成为了当代人生存的 构成要素。
西方后现代意义上的生存论具有一种特有的人学气质,这集中表现为:对一切崇尚中 心、秩序、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摧毁,对一切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的颠 覆,立意消解关于人的生存的一切从根本上带有总体性倾向的终极希望;强调个体化、 碎片化的个人的自我关切、自我体认、自我修养与自我打造;倡导个人自由地选择自己 的生存风格,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艺术品,兢兢业业地创造自己的大美人生,用 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生活内容来美化自己的生存,尽心尽力地选择并打造出一种集真 善美于一身的,令人尊敬、羡慕和难忘的伦理习惯,给他人留下了可敬的生活的记忆。 可见,后现代生存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如何使人学建立在对一种生存风格的个人选择之 上,而非对一切人的伦理重负如何这般地有效。
而我国的现代生存论同样既护持“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个体性、本己性,也刻意追 求使人成其为人。但在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人看来,人的生存的现代性叙事所护持的人 ,是大写意义上的“人”,是一种类意识。这种所谓新人学的取向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 取向,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恋。作为一种语言暴力,个体人的生存命义仍然被 钳制着、压制着;现代生存论同样不缺乏对生存异化的批判指向,而且深刻地觉察到人 为物役、道为技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过度现代化”所引发的物欲主义、工具理性 的膨胀、人文价值理性低迷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渴望通过现代理性的自我纠偏 、自我矫正而拔高人的生存境界、生存品质,使人走出现代理性所埋设的理智洞穴和情 感陷阱而成为有健全人格的人。但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囿于现代性框架之内根 本不能克服异化而只能制造新的异化。因为,现代理性一旦进入生活,则以体系化、经 典化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自我解构、消除异化的生命力受到钳制,并最终 演变成压制人的生存的强势话语,使人的生存命义再次处于晦暗之中。因而,现代生存 论的批判向度,在日常生活中恰恰充当了形而上学自我纠偏的调节剂,作为一面镜子, 照出了现代生存论者的一脸无奈。简言之,它的批判锋芒被生活磨平了。
传统的现代生存论以“限制导致新生、自由引向死亡”为由,将人抬高到万物中心和 最高主体的地位,并期望通过创设具有规训作用的各种制度、规范,让人遵循和肯认, 从而把人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在一定的有秩序的范围内,做理性的人。这样,人的主体性 作用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也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显现;而后现 代主义则认为,现代生存哲学只能培养人的奴性,不利于张扬人的个性,各种典制的规 训只能让人听命于官僚机构或话语权威。生产和再生产压制人性的差异,使人在幻觉中 生存。相反的观点认为,继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主体死了,人也死了,人不再 是一个统一的主体,而是一个祛中心的、碎片化的主体,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欲望流, 人成了零散化、空洞化的指意符号;[3](P92)而且在过度现代化的物流中,人“耗尽” 了自我形象,体验的将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物化的、变形的梦 幻般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没有了自己的存在和生存,属于人的一 切都消失了,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人被边缘化了。换言之,人被后现代化掉了。
传统的现代生存论者都有一种语言学情结,认为语言是人的天性,人活在自己的语言 中。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质言之,人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而后现代人学则认为, 人被语言所吞没。因为,的确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但人的生存命义不是在语言中开敞 ,而是在语言中死亡,语言使人活在一种终极性的幻境中,一种理想性的世界中。理性 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导致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但由于它的合法性并非由它自身 内在地加以说明,而是从外部即从人的终极幸福的承诺上或者从最终解放的宏伟叙事上 寻求支持,尤其是由于它在创设理想境界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谋略),进行 了种种编码和伪装,通过掩饰或压抑个人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矛盾、生存悖论、生存危机 ,诱导人们相信是自己主动选择了过未来幸福生活的生存信念,并相信在这种理想性的 世界中,自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主体。因而,对语言吞没人的生存、泯灭人的语义,竟 然一无所知。而在后现代人学看来,这种自我指认恰恰是一种误认。话在说人、话在造 人之时,也在挤压着人、异化着人。
其实,生存命义的哲学叙事方案是否切当,是一个内在地规定着能否解决所有关联着 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根本问题,它既是人的一切生存活动中的首要活动,也是生存哲学 反思和探究的核心问题。其实,对于人的生存命义的致思,不论以何种方式表述往往都 内在地隐藏着表述者对这一问题的先见或理解;换言之,一个人对生存命义如何表述, 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勾连出了他的生命观、生存观及人生价值观。对生存命义的不同叙事 方案,实际上塑造了为解决人的生存困惑、生存悖论和生存矛盾,而拔高人的生存境界 和生存质量所形成的不同的自我形象。对生存命义进行现代表述的种种叙事方案,立足 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将唯物性、辩证性及历史发展性等现代理念引入到人 的生存观中进行理论上的推展,为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 确证人作为人的最高主体的至上权能,可谓十分到位;尤其是回归人的生存的内在本源 处——社会实践中,能开敞出了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内在本质。尽管这些 表述方式之间不乏互相攻讦和相互抵牾之处,但由于人的生存命义的表述问题是一个永 远无解的难题,人究竟应该诉诸工具理性而做一个现实关怀的“某种人”,还是基于价 值理性而自我打造成一个有终极牵挂的“人影”,抑或是回归现实生活本身、“即世间 而出世间”,做一个“现实的全人”等,诸如此类的表述方式都不具有终极权威性,都 只能具有平等的价值,都是对人的生存命义的某种切身性的表达。这种表达还会继续下 去且永远“在途中”。而西方后现代主义人学虽然是对现代生存论的一种重振或重写, 发现了囿于现代性框架内而不曾发现或被忽视的许多重要问题,且对矫正这些现代理性 的弊病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作为理性的自杀、自虐行为,是一场精神性的大萧 条,其前景日暮途穷。因为在后现代者眼中,人不仅是“无用的热情”,不仅陷于虚无 和荒诞,而且人早已丧失了身份,成为一个下落不明的“物”。既然如此,那么人的生 存命义的表述则完全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人的生存本质再次沉陷于晦暗之中。这种 零趋向的未来走势,的确成为那些急于建权“中国后现代主义人学体系”的学者们的一 块抹不掉的心病。诚然,后现代人学虽无任何建设性内容,也并非一无是处。但,诡异 的是它的意义正在于它的缺陷,它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价值;换言之,正是借助于它的 缺陷,才为生存哲学的未来发展排除了歧路,从而从相反方面推进了中国当代人学的发 展。
总之,我国现代生存论者对生存命义所作的各种叙事方案,其根本的理论旨趣在于为 现代人确立某种生存根据,即确立现代性的人文立场和生活基础。但是,由于它的科学 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思考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它只是对实践作了人学 上的理解,承诺了一个实践本体,而没有同时对人作实践上的理解,没有找到解决人学 困境的实践途径,因而,它确立的人学基础很不牢固,不同程度地带有传统人文主义的 某种病症。[10]而那种试图借助西方后现代人学资源对之进行整体性颠覆的努力,由于 也是理论上的,而没有诉诸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因而不仅不能颠覆它,反而用后现代 的方式加剧了这种人学危机,或者说用另一种理性拯救了、成全了人学危机。其实,人 学危机并非仅仅是现代理性的危机,而更是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方式的总体性危机 。只要产生这种危机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整体性的改变,任何理论上颠覆的努力都只能 是徒劳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把人的问题交给实践去解决,即通过实践并借助实践的 力量,才能一方面实现对传统人学的根本超越,另一方面也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集中凸 显现代人的生存命义。
收稿日期:2003-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