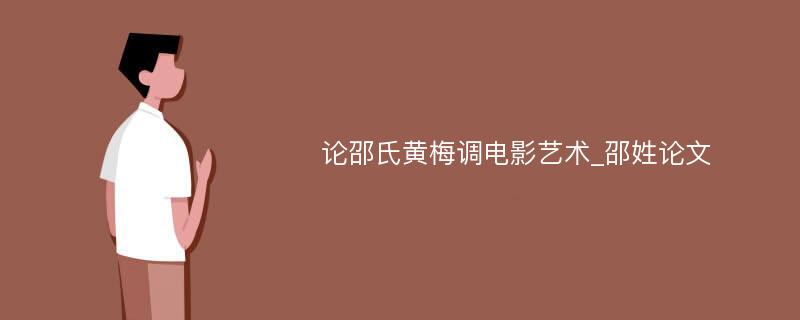
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邵氏论文,艺术论文,电影论文,黄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特征缘起
邵氏黄梅调电影虽然仅是戏曲电影片中的一个类型,但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电影类型。可以这样说,在电影工业理念下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尝试了走现代性格的戏曲电影之途,为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转换做了有益的实验。香港导演张彻说得很深刻:“香港的国语片,第一步‘起飞’便是由于拍摄传统戏曲‘黄梅调’。在邵逸夫主政下的邵氏公司,开始注入大量资金来拍国语片,第一部大成功的是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以前国语片在香港的卖座以‘万’为单位,此后才以‘十万’为单位(《江山美人》似是收入四十余万元),而到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造成高峰,全香港的影片,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可说传统戏曲影响最大也最表面化的一个时代。”[1] (P16)张彻的这一描述直接道出了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最本质意义:用电影拍摄传统戏曲是因应电影市场的需要,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便也直接与电影的“卖座”挂钩。很显然,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美学的特征,也是一种建筑在电影工业理念/邵氏电影工业理念上的艺术特征。所以,有了邵氏黄梅调电影,我们才知道戏曲电影这一中国/华语电影所特有的电影片种,其中在如何看待戏曲与电影的结合,以及两者如何结合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造成了不同风格类型的戏曲电影,也是造成今天对戏曲电影的认识仍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局面。
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这一点——因为缺少对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关注而最终导致了我们对戏曲电影在类型意义上缺乏完整的认识与科学的把握。其实在中国戏曲电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倒确实存在“史”(现实)与“诗”(诗意)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戏曲电影类型:“将戏就影”——以电影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及“将影就戏”——以戏曲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前者是戏曲迁就电影,后者却是电影迁就戏曲。或者又可以说,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古典的。邵氏的黄梅调电影是以电影为主导的戏曲电影,费穆等尝试的戏曲电影和大陆的戏曲电影实践则是后一种以戏曲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只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对戏曲电影类型的铸造历来没有受到重视罢了。
从20世纪50年代戏曲电影的兴起开始,中间经“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阶段,再到20世纪80年代戏曲电影的再次崛起,“将影就戏”几乎成了大陆戏曲电影的主流,如崔嵬、陈怀皑、应云卫等执导的《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洲》、《宋士杰》、《武松》、《追鱼》等,全都是因为精确地反映了戏曲电影的这一类理念而成了当时戏曲电影的范本。特别是1960年由崔嵬执导的《杨门女将》,被看作是在大陆拍摄的戏曲电影中没有一部能出其右的精品,以致受到当时政府总理周恩来的推崇。[2] 崔嵬在《拍摄戏曲电影的体会》一文中说,“戏曲片是戏曲与电影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但“主要应该是电影服从戏曲”,“电影要服从戏曲,不能离开戏曲这个基础,既要保持舞台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打破舞台框框。要利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更加发挥戏曲艺术的特点,力求做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人”。[3] 显然,“电影服从戏曲”成了大陆戏曲电影的主流观点。
虽然邵氏黄梅调电影乃至香港的戏曲电影是由大陆黄梅戏电影的香港演出而“激发”出来的,但两者的戏曲电影观念并不一致。将内地一个不属香港的地方戏曲剧种与香港的电影产业相结合,其创造的电影类型——黄梅调电影,由于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它不但与早期费穆的戏曲电影理想不相同,而且与其“源头”——大陆黄梅戏电影,在戏曲电影的理念和特征上更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之所以选择黄梅戏而非其他更有传统文化味的京剧、昆剧,说明了其中包含的资讯——对戏曲电影的自身看法。因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念。黄梅戏的发生、发展,与京剧、昆剧等戏曲不同,表现出非常的特殊性。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是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当黄梅采茶在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两小戏”和“三小戏”,并在20世纪30年代因进入上海等城市而最后衍化成戏曲剧种时,它实际上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戏曲(京剧、昆剧等)完全不同的路:其时,中国京剧、昆剧和其他声腔剧种(如梆子、秦腔、川剧等)业已成熟,黄梅戏却还刚刚走上它由歌舞向戏曲的嬗变——向中国戏曲和西方话剧两方面借鉴学习的尴尬之路(两种完全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戏曲这一角度考察,黄梅戏的“传统”部分并不完整,并且还保留了很多民间歌舞的东西,如剧目《打猪草》、《夫妻观灯》等。黄梅戏的这种特色俨然成了邵氏拍摄戏曲电影的最主要选择依据。
二、艺术特征: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亮点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布烈松曾尖锐地指出,“舞台剧和电影书写结合只会共同毁灭”,“用两种艺术结合而成的手段不可能有力地表现什么,要么全是一种,要么全是另一种”。[4] 他认为舞台艺术和影像艺术在艺术的本质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融合”的可能。但对中国的戏曲来说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毕竟有了还算成熟的黄梅调/黄梅戏电影,况且戏曲电影也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实践,所以,“对于戏曲来说,影视起先只是摄录手段,渐渐地,它们便以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独特的镜头技巧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征”。[5]
然而,布莱松从他导演实践产生的想法,也从另一方面告诉了我们,黄梅戏/戏曲与电影的结合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种障碍直接导致了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犹豫”和尝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戏曲电影美学观。建筑在电影产业基础上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基于黄梅戏自身独特的发生历史和电影的大众性质,采用了一种非常实用的美学原则:“将戏就影”,一切以电影为主,因此而造就了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最本质艺术特征,即它的现代性格,也可说就是黄梅戏的民间性和电影的大众化的双叠后的性格。从这点出发,我们说,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首先反映在其银幕结构上是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其二是它的通俗流传,这是因为其好听易唱的黄梅曲调;其三是它的写实风格,体现在其写实时空与写实动作造型上。
1.银幕结构: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
结构就是“叙述”故事的总体框架,银幕结构也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在叙事上的基本态度。它可以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是将传统戏曲的分场结构衍化为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从而从基本的结构形态上完成“以戏就影”的构造;第二是将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尽可能地“塞”进银幕中而非舞台中,从而使故事的“传奇”是银幕般的“奇”而非舞台式的“奇”。
传统戏曲的连场结构形式表现的是点状的矛盾冲突,根据戏剧情节和冲突的要求,分别采用不同的场子,如正场、过场、圆场、转场,以及大场、小场等。在这里,一系列的动作被化成为大大小小的单体动作,按顺序作线性的排列,一个场子基本就是一个中心动作,以完成一次矛盾的冲突。对于传统戏曲结构的这种基本特点,非邵氏戏曲电影一般都“敬之如神”,因为改变了它就等于是动了“戏骨”。以费穆拍摄的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电影《生死恨》为例。《生死恨》是费穆和梅兰芳两位艺术家自觉地“尽量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6] 的力作,前后拍摄时间达半年。梅兰芳事后曾说:“对于舞台艺术进入彩色电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打了冲锋,作了大胆的、带有冒险性的尝试,因而是值得加以记述的。”[7] (P234)可见,由于有了梅兰芳的关系,《生死恨》在费穆拍摄的戏曲电影中电影理念是比较“冒险”的,但尽管如此,《生死恨》的连场结构形式在电影中基本没有变动,仅是作了某些删节:“我和费穆都主张拍《生死恨》,因为这出戏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编演的,曾受到观众欢迎,戏剧性也比较强,若根据电影的性能加以发挥,影片可能成功。大家都同意,就决定拍摄《生死恨》。我把剧本拿出来和费穆研究,他说:‘舞台剧搬上银幕,剧本需要经过一些增删裁剪,才能适应电影的要求,我先把它带回去琢磨一下,过几天再来商量。’我说:‘我们共同斟酌修改,彼此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来讨论。’我们经过研究,根据舞台剧本进行了修改,台词、场子方面有增有删,有分有并,从舞台剧的二十一场改成十九场。”[7] (P215)对于这样的结构,梅兰芳和费穆都满意,认为是“利用电影的纪录,或者合乎目前的需要”。[8] 梅兰芳甚至说,《生死恨》“在剧本改编方面,在舞台艺术如何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方面……都是有成绩、有收获的”。[9]
与此不同,邵氏黄梅调电影几乎是将戏曲的分场结构完全打碎、推出,用主唱段来作为分割结构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弱化”了戏曲的色彩而加重了银幕感——电影的结构。如果将邵氏《天仙配》加以比较与大陆拍摄的黄梅戏《天仙配》加以比较,两者在结构上的差异就更是一目了然。特别是《王昭君》,唱段、琵琶曲相继组合,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表现出来的电影的节奏,一定不是戏曲舞台的节奏,而是电影节奏,或者说就是音乐的节奏。邵氏《三笑》因是1969年的后期作品,其结构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戏曲连场的任何痕迹,而是标准的电影结构——连唱段的结构作用也被推到了银幕之后。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这种结构方法也反映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故事叙述上。应该说,无论是邵氏黄梅调电影还是另一种戏曲电影,都是将耳熟能详的戏曲/传说故事当作自己的基本剧目。因为剧目故事的丰富——“唐三千,宋八百”,本来就是中国戏曲的一大优势。而通过中国传统戏曲/传说故事的引入,激发的是它们背后的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戏曲电影吸引观众的一个主要动因。但由于邵氏黄梅调电影的结构需要,它一般避开舞台式的叙述故事,将戏曲在叙事上的特长——所谓“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通过演员的动作表演来讲述故事/推进剧情——推倒不用,以避免“戏曲化”。譬如《江山美人》改编了京剧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结尾,李翰祥用文人的视野将大团圆结局改为悲剧,李凤最后死在日思夜想的皇宫前。如果以戏曲思考,这一场电影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巨大的宫殿和人群,会“扼杀”演员的“戏曲”表演。但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用不着“腿”,用群唱的“嘴”很自然地表现了人物,推动了剧情,加上庞大华丽的景,一下子就将故事推向高潮。
可见,邵氏黄梅调电影的银幕结构叙事从根本上排斥了戏曲叙事的可能,而使自己成为当时标准的大众娱乐的电影——而不是已日益丧失观众的银幕上的“戏曲”。
2.通俗流传:好听易唱的黄梅曲调
唱腔曲调是戏曲电影的灵魂。音乐片/歌舞片中的音乐与电影中的音乐是“名同而实不同”。音乐片/歌舞片是音乐叙事,而电影中的音乐——主题歌、插曲、主题音乐、场景音乐和背景音乐等,却是为叙事服务。戏曲演唱在电影中的功能是:独唱能推动剧情和矛盾的发展,塑造人物性格;而群唱(旁唱)则可以渲染和强化气氛;间奏曲主要是承担了电影音乐的功能。不仅如此,长短交替或反复的演唱能推进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性格/感情的变化。这一切可说是戏曲电影音乐的共性。但这还不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对音乐的要求。邵氏对黄梅调电影音乐的态度是其主旨的需要:适应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为大众所喜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邵氏黄梅调电影虽然标明是“戏曲”的唱,但实际上,这种戏曲的“唱”已变成了城市民曲——一种通俗的、好听易唱的、能广为流传的“时尚”曲调。
邵氏黄梅调电影不称黄梅“戏”而称黄梅“调”,虽有种种其他解释,但黄梅戏旧称“调”时的民间歌唱性质,也可说是其不经意的一种本根性原因。张彻在他的《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一书中说:“传统戏曲向以京戏为主,有人(不记得是谁,但当时我在场)问邵逸夫,即拍传统戏曲,为何不拍京戏而拍黄梅调?邵先生说:‘京戏不是自然发音,不懂的普通一般人不能接受,黄梅调是自然发音。’我从未发觉过邵先生研究传统戏曲,但这话极有见地,我也从未听到任何‘专家’发觉这一点。昆曲和高腔绑子发音比京戏更远离自然,故其衰落也早。如我内人全不懂传统戏曲,(她是出生在香港的),可以看越剧而全不能接受京戏,也是越剧是自然发音而京戏不是之故。”[1] (P16)可见,邵氏掌门邵逸夫何以不以“京”、以“昆”入影(电影),其最原始的动因就是黄梅调能给普通人听,京、昆等剧的唱/唱腔曲调却是“普通一般人不能接受”。这是何等干脆明了的说法。“梅调电影的音乐风格自‘黄梅调’抽象化、广义化,晋身为一种现代化、精致化、时代流行曲化的传统戏曲、江南小调的代称,柔和元素包括黄梅新旧腔调、京剧、昆曲、山歌民谣、越剧、评弹、蹦蹦戏、川剧、粤剧、都马调等”,[10] 这种判断无疑是对的。黄梅调不仅仅是移用了黄梅戏的基本曲调,还将中国其他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以及民歌的曲调,只要是大众乐意接受的全部都拿来“为我所用”。但更为重要的是,邵氏黄梅调电影中的“黄梅调”,已经不是原来黄梅戏中的“黄梅调”,而是经过了“改造”的“黄梅调”——一种现代乐人的本地化、通俗化、简易化的处理,变得易学易唱易传。所以,黄梅戏曲调本来所具有的民间性、亲情感和咏唱力,经过现代音乐理念的处理,使之更加适应了今天的审美需要,特别是切合了现代都市型的香港民众的娱乐要求——一种现代都市的民间性。
作为一个反证,大陆1955年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和1959年拍摄的《女驸马》,前者的曲调和演唱还留存歌舞“三小戏”时期的痕迹,显得民歌味稍强;但在《女驸马》中,曲调和演唱就带有了更浓的戏曲/京剧腔。这也可见戏曲电影一旦强调“以影就戏”——电影服务戏曲,那么,戏曲最根本的唱腔曲调就一定会首先“戏曲化”起来而排斥“电影化”。这也是为什么在邵氏黄梅调电影中,一般是电影演员(非戏曲演员)参加演出,演唱的演员(即使在幕后)也可以不是戏曲演员,而从费穆开始一直到大陆的戏曲电影拍摄,却是非戏曲演员本人参加不可,甚至是这一剧目演出的最著名演员,如黄梅戏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这是因为: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唱”是电影的“唱”,大陆黄梅戏电影的“唱”却是戏曲的“唱”。所以,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演员的表演基本上是“电影”的,不仅在唱上以幕后代唱为主,即使在演唱表演上也基本上可归属为“电影”式的,而大陆的主要戏曲电影(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一般上由戏曲演员参加演出——而且都是在群众中有影响力的演员,不但在唱上是本人的“真唱”,更主要的是,演员的表演也无时无刻都透露出扎实的戏曲演唱基本功。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戏曲电影观,一个是从电影切入戏曲,“以戏就影”;一个是从戏曲切入电影,“以影就戏”。惟其如此,我们又可以说,邵氏黄梅调电影主要是运用戏曲的音乐——“唱”来叙述故事的电影,在一定意义上说,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唱”仅是叙事的工具,而非艺术的特征。
3.写实风格:写实时空与写实动作造型
“戏曲服从电影”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决定了它在处理银幕时空上的写实风格。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戏曲/黄梅戏对于虚景与实景、唱词与动作的舞台辩证原则,全部依据电影的艺术原则作了修正:表演/演唱对景的“表现”功能——戏曲的舞台时空观,全部被推出了银幕之外。换句话说,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时空表现依据的是电影的时空观,而非戏曲的时空观。我们不说这种实验是否成功过,单就后人对这种尝试的犹豫就已很能说明问题了。著名导演吴祖光就曾认为:“传统戏曲表演的虚拟、写意的手法是突破时间和空间,诱发观众驰骋想像力的最高明的表演方法。立体布景和笨重的道具只能束缚住演员的手脚。”[11]
邵氏黄梅调电影写实风格的追求,为它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方便。金碧辉煌的搭景与风光无限的实地取景,都保证了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场景的争奇斗艳,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将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推到一边,打开了审美的另一扇大门。电影的娱乐性毕竟不能完全用艺术的尺码来做唯一的衡量标准。连台湾杜云之的《中国电影七十年》也将邵氏的《貂蝉》、《江山美人》等电影称为“布景宏丽古装宫闱影片”,[12] 可见邵氏黄梅调电影当时在布景上的用力和写实倾向。
写实的景物布置带来的必然是表演上的写实风格,所以在戏曲中至关重要的虚拟表演,邵氏黄梅调电影基本上是推出银幕之外的。虚拟表演的基本内涵是:在虚掉了角色的对象时(如《拾玉镯》中的线和针,《盘夫》中的门),依靠演员的手势和人体动作通过模拟来“还原”这一被虚掉的对象,观众则通过演员的形体动作感知这对象(针线、门窗、山水)的存在。例如《南天门》的走雪,是通过演员瑟缩战栗的表演,使观众意识到他们是行走在大雪纷飞、朔风凛冽的冰天雪地之中。《御碑亭》的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是通过演员步履维艰的滑步、跑步、圆场表现出来。可见,虚拟表演是一种为“还原”虚掉对象的舞台表演。这也就是戏谚所说的“景”在演员身上。
但邵氏黄梅调电影对此并不领情。戏曲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戏剧(话剧、歌剧等)在表演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景在角色/人物身上——运用虚拟的表演(做、念、唱、打)来表现景与物,在邵氏黄梅调电影中基本上是被“舍弃”了,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电影与戏曲的“结合”仅是部分的“结合”,是电影“为我所用”的结合——适合电影原则的则用,不适合电影原则的则一律舍弃。譬如在黄梅调电影《王昭君》中,最后昭君投江时,是站在搭出的景——山上,向江中跳下。如果在舞台上肯定不会这么表演。但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好处是,在此处,它不要你看投江的虚拟身段动作,而是要你“听”那段感人肺腑的唱。审美的用力处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说明了在对待戏曲与电影的结合上的根本态度:从时空、结构、表演等各个方面弱化戏曲的特征而强化电影的特征。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不是在最大限度保存戏曲传统的基础上来“电影化”,而是在充分保证电影呈现的条件下,把黄梅戏中“好看”、“好听”、“好玩”的统统拿过来为我所用。这大概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留给我们的经验。
三、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历史意义
戏曲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为特殊,也是仅为华语电影所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虽然香港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是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出品的《借亲配》,但开香港黄梅调风气的却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黄梅调电影是邵氏电影或邵氏影业王国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片种/类型,也是邵氏电影或邵氏影业对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做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邵氏黄梅调电影不仅对中国/华语电影的类型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电影的类型发展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是因为中国电影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开始,其发生就与中国的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二是因为中国电影一百年来所追求的民族风格一直与中国戏曲的民族风格形成了拆不了的因果关联。其三是因为戏曲电影(当然包括邵氏黄梅调电影)是中国/华语电影创造的唯一一个所无法替代的电影类型/片种。邵氏黄梅调电影的美学观和电影处理手法,对电影与戏曲结合的分寸掌握,甚至对电影特性与中国戏曲的把握,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戏曲是可以而且应该“电影化”的,但甚为可惜的是,传统戏曲的这种艺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电影化”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美学观。传统戏曲的虚拟化、程式化表演是“以假作真”,电影的镜头运用则是“以真作真”,一个是以身体作材料来“写”世界,一个却是以镜头来“艺术”地记录世界,从理论上来说,戏曲强调演戏是对生活的虚拟——舞台造型,电影强调的则是生活本身的再现——影像再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化”的基础。从另一种角度说,传统戏曲的虚拟化表演和写意性特征——执一根马鞭在舞台上“趟马”表现骏马奔驰;用一支木浆唱、念、做、打,就可以表现荡舟江河;同一座舞台可以当作疆场,也可当作陋室;一张椅子可以代表一座山,两面旗子便是一辆车,如果用电影手段(各种镜头语言、蒙太奇等)改变了,那它就不是戏曲,如果仅是“量”上的放大、变慢等等,那充其量只是用摄影镜头进行艺术处理的舞台表演记录。再如戏曲与电影的时空观是完全不同的时空观。不管电影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其时空表现都是纯粹物质的和可见的。换句话说,无论电影画面如何转换,镜头如何运动,其时空表现都是“显现”的,时空的快速跳跃只是时空场景的“剪辑”——精简时间和空间。但中国传统戏曲却根本不同。中国戏曲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并不独立存在,它与演员的唱做念打共存亡——景在人身上。戏曲舞台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唱做念打——演员的表演,就只剩下一块一无所有的面积,它具有长、高、宽的三度空间,但却没有舞台的时空。因此,中国戏曲与电影在时空观念上的根本不同,并不简单地在于运动与固定,假定与非假定,诸如此类。其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中国戏曲要求观众采取反观的审美方式,其归宿在人,电视剧却要求观众采取正观的审美方式,其归宿在物。所以,戏曲的舞台时空环境是“表现性”的,电视剧的时空环境则是“再现性”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里相送”,演员通过唱、念、做等程式化的表演,显示了池中游鱼、水中鸳鸯、参神、渡桥等一系列时空环境,如果用电影镜头处理,有了实景,再用演员的虚拟表演表现,岂非矛盾滑稽?所以邵氏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把这些虚拟表演统统废而不用。可见,在时空的表现上,戏曲和电影根本无法调和。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戏曲电影的特征是戏曲艺术某一部分特征与电影艺术某一部分特征的相加而不是“相融”,因为对这类戏曲电影来说,“相融”是不必要的,戏曲电影只是电影的一种类型,所以从根基上来说,戏曲电影的特征是建筑在电影艺术特征基础上的部分戏曲艺术特征。虽然,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戏曲电影至今尚未完全定型,但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电影存在,就一定会有戏曲电影的实验,戏曲电影从清光绪年间丰泰照相馆为谭鑫培拍摄京剧《定军山》的尝试开始,作为电影(指剧情片)艺术的一种类型,戏曲电影就不断地尝试至今。
人类已进入了新的传播时代,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国戏曲,如何因应21世纪,如何在当下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是理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界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于戏曲电影这种类型是否已经真正形成,是否已经有了自己反映生活的独特方法,仍然有待社会的继续实践和戏曲电影自身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戏曲电影毕竟是人类的一个创新——一个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与一个最现代的大众化的电子艺术的结合,是人类对艺术的一次探索,探索突破艺术的分类原则后的艺术生存状态。
虽然邵氏黄梅调电影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戏曲”,但邵氏黄梅调电影自身的艺术“空间”,却给了我们创新的可能,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对传统艺术的改造,无论成功与否,它都显示了人们对艺术概念的重新思考。只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在进行戏曲电影类型的建构时,一定要想到邵氏影视帝国的黄梅调电影,因为它曾经从电影的本体——大众的市场面思考和实践过“现代性”的戏曲电影:一种建筑在电影基础上的“以戏就影”的黄梅调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