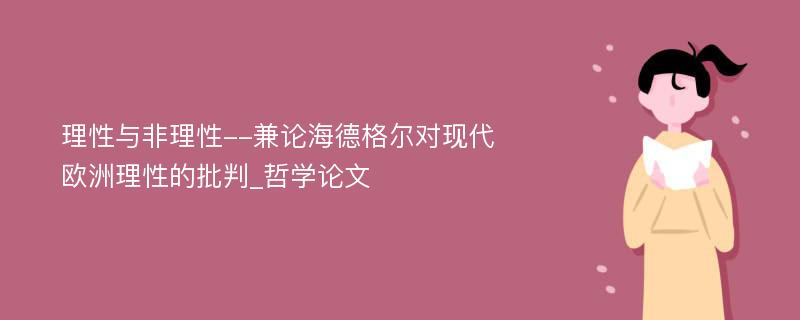
理性与非理性——兼论海德格尔批评欧洲近代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海德格尔论文,欧洲论文,近代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理性”概念的演变,揭示了“理性”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不同哲学家对此均有不同见解,持有巨大歧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欧洲近代理性以及有关海德格尔是“非理性主义”的流行见解,提出了独到的相反观点,指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在使人类的文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显示了其悖论与背理性之处,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造成严重威胁;而海德格尔正是看到了欧洲近代理性的历史局限而对此加以拒绝,他倡导的“思想”已包含了对“理性”的新的规定。
“理性”一词,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都被看成是一个褒义词。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称某人是理性派或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是一种很高的褒奖。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理性”的具体含义经历着惊人的变迁。笛卡尔、斯宾诺莎都是欧洲近代著名的理性派哲学家,他们认为只有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才是靠得住的,才是真理。就他们强调了人的某一必然的认识过程——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而言,他们在近代西方认识论史上是有功绩的,但他们只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并由此否认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否认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来源,因而他们的观点带有很大片面性。他们所说的“理性”与黑格尔所说的对立面统一的“理性”相比,含义亦显然不同: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是对立面的统一,并不带有上述片面性。还应该看到,笛卡尔、斯宾诺莎所代表的理性派哲学是在近代数学、几何学、力学首先得到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明显带有机械唯物论的特点。例如,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著名论断,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采用了几何学的方法,把人的思想、情感、欲望当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来加以研究,提出定义和公理,然后证明,进而演绎。以后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从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的论断进一步发展出“人是机器”的论断。由此,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所说的“理性”,明显地打上了17世纪机械唯物论的烙印,它与黑格尔在近代进化论和事物辩证发展的基础上所阐述的“理性”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再以康德与黑格尔相比较为例。康德的三部主要著作中的两部都冠以“理性”的名称,即《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很显然,康德也是以“理性”来命名自己哲学的哲学家。黑格尔这样评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康德哲学看来,“对于意志说来,除了由它自身创造出来的、它自己的自由外,没有别的目的。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上面”。①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这种自由是空洞的,它是一切别的东西的否定,康德的道德律是空无内容的,“除了只是同一性、自我一致性、普遍性之外不是任何别的东西”。②康德的形式的立法原则没有任何内容、任何规定,“这个原则所具有的唯一形式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同一。这种普遍原则、这种自身不矛盾性乃是一种空的东西”,③是抽象的同一性。“康德对于义务的定义,除了同一性、自身不矛盾的形式外,什么东西也没有”。④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原则的缺点,它纯全是形式的,冷冰冰的义务是天启给予理性的胃肠中最后的没有消化的硬块”。⑤由于康德的“道德律是形式的,本身没有内容,它便与主观的冲动和嗜好相对立,并与外界的独立的自然相对立,⑥“道德正包含在理性对感性的对立里”。⑦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把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冲动、嗜好、自然)对立起来,追求的只是抽象的同一性,理性仅停留在对感性的对立上。由于康德在其哲学中处处把对立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总评价是:“这完全是知性哲学,它否认了理性。”⑧黑格尔对康德的“理性”概念的批评与评论,明显地表现出康德和黑格尔对“理性”这个概念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以及“理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所发生的巨大演变。
黑格尔早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即在法兰克福时期,就开始了对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批评。他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以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相对立,用普遍的义务命令(理性)去压制特殊的东西(嗜好),康德的理性是冷酷的道德命令。黑格尔在当时自己的著作中有意回避使用“理性”这个概念,以求与康德的“理性”概念划清界线,而代之以意义模糊、令人费解的“爱”和“生命”的概念,从中寄托自己的对立面统一的思想。更有甚者,黑格尔有感于当时流行的反思哲学(主要指康德、费希特、耶可比的哲学)皆固执对立和分离,固执二元论,在理性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处处造成割裂,为了与之划清界线,青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故意不提“哲学”这个词,而代之以宗教,把宗教放在高于反思哲学的位置上,并在宗教中寄托了在分离中求统一的辩证思想。也就是说,黑格尔用宗教与反思哲学相抗衡,宣扬超出反思哲学的新的辩证法哲学。于此可见,当一位哲学家批评另一位哲学家的“理性”概念、或批评某一时期的“理性”概念时,我们不能轻易认为这位哲学家是非理性的或非理性主义的,而应看一下他的批评是否包含着新的哲学和新的思想——对以往的“理性”概念的批评,往往是新的哲学和新的思想的生长点。
上述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例子,表明了正像真理是具体的一样,“理性”这个概念也是具体的,正像在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一样,在历史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理性”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哲学家必然会对以往的“理性”概念提出非议与批评,要求增加新的内容与含义,或对之进行根本的改造,这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我们再来着重探讨一下如何看待欧洲近代理性主义。
按我国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发展史。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是西方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因此,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往往被看作是西方理性的唯一典范,凡西方现代思想有违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都被视为非理性主义。因而,这些研究者认为在黑格尔以后西方盛行着非理性主义的各种思潮。确实,西方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在批评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时,丢掉了欧洲近代理性主义中的许多合理的东西,例如,有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丢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大力宣扬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如新黑格尔主义);有的专门强调意志(如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有的专门强调个人的生存(如基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就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这些哲学流派无论如何比不上笛卡尔和黑格尔等欧洲近代理性主义者。所以,把西方现代这些哲学流派称为非理性主义是比较公允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凡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提出批评与异议的都是非理性主义,似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是西方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是理性的唯一标准。个别特殊情况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这里介绍一下后期海德格尔如何看待欧洲近代理性主义。
后期海德格尔是一位公开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唱对台戏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明确地说:“只有当我们得知几百年来受颂扬的理性是思想的最顽固的对手之后,思想才能开始。”⑨“几百年来受颂扬的理性”,指的就是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即欧洲近代理性主义。而“思想”则是后期海德格尔所倡导的东西,他在1964年写有《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一文,认为西方的哲学已经走向终结与完成,应该由思想取而代之。后期海德格尔把欧洲近代理性主义视为“思想”的最顽固的对手,只有在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斗争中才能伸展“思想”,使“思想”得以开始,于此可见后期海德格尔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所作的批评之尖锐。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进行猛烈的批评?我们先来看在《通向语言之路》中海德格尔与一位日本人所进行的谈话。两人谈到,自近代以来有一个地球和人完全欧洲化的过程,许多人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理性的胜利进军。理性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时期作为女神被召唤出来。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对这个女神的崇拜中走到如此远的地步,以致于任何思想如果把理性的要求作为非本源的要求加以拒绝的话,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只被作为非理性而遭到诽谤。日本人说,人们认为欧洲的理性的统治由合理性(Rationalitat)的成果加以证明,技术的进步每时每刻看到了这些成果。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冲昏头脑的状况甚至使人们不再看到,人和地球的欧洲化如何损耗着一切本质性东西的源泉,似乎这些源泉该枯竭了。⑩海德格尔与日本人的这段对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欧洲近代理性的统治和胜利进军,致使地球和人完全欧洲化,其成果就是技术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对话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进步未予赞扬,而是认为冲昏头脑的人才会盲目赞扬技术的进步,才会看不到人和地球的欧洲化如何损耗着一切本质性东西的源泉。在这段对话中,海德格尔把欧洲近代理性的要求作为非本源的要求加以拒绝。这里包含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即海德格尔为什么认为不应盲目赞扬技术的进步?欧洲近代以来的技术文明逐渐遍及全球,使人和地球完全欧洲化,那么,在技术时代和技术世界中,海德格尔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巨大危险?
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框架(Gestell)。他用“框架”这个词规定近现代技术的本质,意思是说,近现代技术像框架一样完全把人束缚住,使人仅囿于技术的视野,只知道一味从事技术制造与技术生产,一味把自然事物作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一味利用和剥削地球和自然,毫不顾及这样做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海德格尔把西方技术文明时代称为“着魔”的时代,西方技术世界中的人听凭受制于技术生产和技术制造的无限制的统治。(11)他列举了:在技术时代,莱茵河已被纳入预定的发电和输电的系统,仅作为水压提供者,失去了它曾有的开垦土地、供人居住的作用;(12)现代技术不像古代的风车那样顺其自然地利用风能,而是强行向自然索取可被开采和储存的能量;(13)自然已成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唯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14)人们为了科技上的需要,弄倒开花的树,不让它在它应该站立的地方站立着。(15)在30年代,海德格尔就已经预先看出:“科学的进步将使对地球的剥削和利用……达到今天还无法想象的状况。”(16)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在对艺术的沉思中,海德格尔极力恢复自然和大地(地球)的本来面目。他说:“希腊人早已提到了Physis(自然)。后者同时澄明了人把他的居住建立于其上和其中的东西。我们称这个东西为大地”。(17)“历史的人把他的在世界中的居住建立在大地上和大地中”。(18)这些话表明,海德格尔把大地(地球)和自然看作人类的居住地和生存的基地,是不应该遭受干涉和破坏的。现代技术掩盖了大地(地球)和自然的本来面目,把大地和自然作为能源和工业生产的原料库加以利用和剥削,大规模干涉大地(地球)和自然,严重威胁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与生存,使人类面临失去家园的巨大危险。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不能盲目赞扬技术的进步,在1936至1938年写的《哲学论文集》中,他就发出了“拯救地球”(19)的紧急呼吁。在海德格尔1976年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向西方技术世界中的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20)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即海德格尔为什么把欧洲近代理性的要求作为非本源的要求加以拒绝。
对这个问题,可以先作一个简明的回答。欧洲近代理性的要求只体现在人充当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上。自从欧洲人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后,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人应该向大自然进行索取”。正是在这样的根本观念指引下,欧洲近代理性表现在人用近现代科技去向自然进行大规模索取的本领上,最后导致在20世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欧洲近代理性只表现在人充当自然的主人向自然进行索取的本领上,没有认识到自然作为人类的居住地的本来面目,而是纵容近现代科技严重干涉和破坏人类的居住地——自然,所以,海德格尔把欧洲近代理性的要求作为非本源的要求加以拒绝。出于对当代生态危机的预感,海德格尔预先敏锐地看出了欧洲近代理性的历史局限性与片面性,宣告了欧洲近代理性必将产生转折,转向另一个新的开端。
在欧洲近代理性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欧洲近代理性创始人笛卡尔曾说,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能通晓火、水、空气、星辰、天空和我们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正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工业者有多少行业那样清楚,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把它们作各种各样的应用,从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21)欧洲近代理性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晦涩的语言也表达了人的主观性是自然客观性的主宰:“在理念的否定的统一里,无限统摄了有限,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2)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然只不过是理念的外化,或者只被放逐到逻辑学的注释中去。
在海德格尔对单纯算计的思想的批评中包含着对传统的“理性”概念的批评。他把单纯算计的思想看作技术时代中的严重危险。“算计”这个词的德文是Rechnen。“算计”不可以倒过来理解为“计算”,因为“计算”只意谓着与数目打交道而已,而“算计”则意味着进一步有所图谋,总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向自然进行索取。海德格尔说,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已被排除之后,地球上的人仍处于危险的境地:“刚刚说出的命题适用于多大的范围?它就如下情况而言是适用的,即在原子时代中滚动而来的技术革命能用一种方式去束缚、蛊惑、迷惑和蒙蔽人,因此总有一天算计的思想作为唯一的思想在活动并起作用。那么,以后哪一种大的危险来临了?以后,与算计性的计划和发明的最高的和最有成效的才智相并行的是对深思熟虑表现出漠不关心,是完全的漫不经心。那么以后又怎么样?以后,人就会否认和丢弃他的最独具的东西,即他是进行深思熟虑的生物。”(23)算计的思想如果作为唯一的思想而起作用,那么,这将导致地球上的人处于危险的境地。人在算计性的计划和发明中虽然可以表现出极大的才智,但又面临着对算计所产生的后果不加深思的严重危险。海德格尔把人规定为深思熟虑的生物,这一定义明显地与传统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相对照。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的“理性”概念恰恰表现在算计的本领上,人总是把理性看成工具性的理性,用以谋算(Berechnung)和算计自然事物,大肆地向自然界进行索取,不计后果,致使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了“技术动物”。(24)海德格尔有意避开了用传统的“理性”去规定人的本质,而改为用“深思熟虑”去规定人的本质,他的用意显然在强调传统的“理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在《充足理由律》一书中,海德格尔对西方人喜欢追求理由作出了评论。西方思想界从古以来就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看作是要求说明理由和给予说明理由的生物。按这样的规定,人通过追求理由而力图统治和利用自然事物。鉴于这种情况,海德格尔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我们问道:上述的规定——人是理性的动物——详尽探讨了人的本质吗?由存在所能说出的最终的话就是声称存在叫作理由?或者,人的本质,人对存在的从属关系,存在的本质,始终还并越加令人惊讶地不是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放弃这值得注意的东西而有利于放纵单纯算计的思想及其巨大的后果?或者我们坚持找到这样的道路:在这道路上,思想能够与值得注意的东西相符合,而不是受算计的思想的迷惑而忽略考虑值得注意的东西?”(25)海德格尔从充足理由律中看到西方传统一直宣称“存在就是理由”,把追求理由和单纯算计的思想当作追求存在,看到了西方传统的这种把存在等同于理由的做法的后果。海德格尔向以理性(追求理由、追求算计的思想)规定人的传统哲学发起挑战,目的在于使人们注意到追求理由、追求算计的思想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如果“理性”仅意味着向自然进行索取,那么,“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没有详尽地规定人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充当一切存在者的主宰,而在于“看护存在”,即看护自然事物的存在从而又看护人的存在,维护人类长期生存的基本条件。
我们可以对全文作一个总结了。
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仅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主宰,把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大肆向自然进行索取,最后导致破坏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威胁自然,充分显示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否定的方面。曾使人类获得文明和进步的科学和技术,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包含着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这正是以科学和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欧洲传统理性的悖论与背理之处。海德格尔的有关批评揭示出欧洲传统理性的重大缺陷。他对欧洲传统理性的批评与拒绝,正像年轻的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批评与拒绝康德的理性一样,都是看出了已有理性内涵的重大缺陷。针对欧洲传统理性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主宰、大肆向自然索取的做法,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人应该有看护自然事物的存在和看护人的存在的“思想”。虽然海德格尔因对欧洲传统理性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从而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正面使用“理性”一词,但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这种“思想”,本身已包含了对“理性”的新规定。身处生态危机中的现代人,早已不再把向自然索取看作是理性,而把保护自然环境看作是理性。有些中国研究者仅看到海德格尔批评与拒绝欧洲近代理性而未弄懂海德格尔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把海德格尔归入非理性主义的行列。现在已到了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作出正确判断的时候了。
注释:
①⑧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9、290、290、290、291、292、293、306页。
⑨ 《林中路》,1980年法兰克福版,第263页。
⑩ 《通向语言之路》,1985年法兰克福版,第98-99页。
(11)(16) 《哲学论文集》,1989年法兰克福版,第124、156-157页。
(12)(13) 《报告和论文集》,1978年弗林恩版,第19、18页。
(14) 《冷静》,1977年弗林恩版,第18页。
(15) 《什么叫思想》,1971年图宾根版,第18页。
(17)(18) 《林中路》,第28、31-32页。
(19) 《哲学论文集》,第412页。
(20) 《出自思想的经验》,全集第13卷,1983年法兰克福版,第243页。
(21) 《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欧洲哲学史》编写组编写,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7页。
(22) 《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3页。
(23) 《冷静》,第24-25页。
(24) 《哲学论文集》,第98页。
(25) 《充足理由律》,1978年弗林恩版,第210-211页。
标签:哲学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康德论文; 笛卡尔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