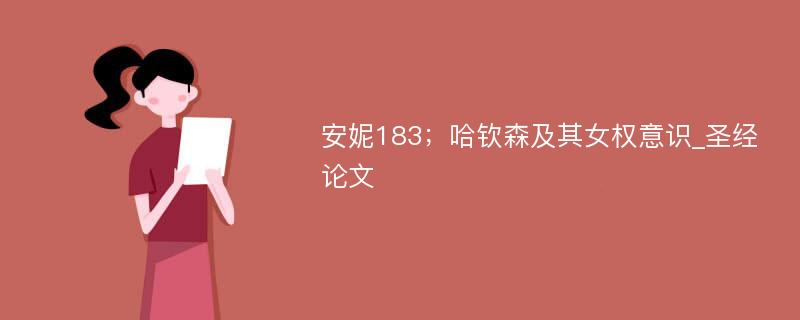
安妮#183;哈钦森和她的女权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妮论文,女权论文,意识论文,哈钦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前,安妮·哈钦森一直在美国被冠以“唯信仰论”的宗教异端(The Antinomian Heresy)之名,人们几乎不注意她的女权意识。一些人认为,安妮是拥有荒谬观点的最恶劣和最危险的异教徒[1] (p.37),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妮是一个具有感召力和流利演说才能的巫医[1] (p.37),或者是另一个圣女贞德[1] (p.37)。不可否认,安妮·哈钦森是一个坚定的清教正统派反对者,并以她唯信仰论的宗教观而闻名。但是,她提出其宗教主张的目的,就是不甘于清教社会中妇女传统的屈从地位。换言之,如果她像当时大多数英格兰妇女一样,以顺从、屈服作为她的行为准则的话,她自然不会有反抗意识,也自然不会以殖民地女界第一人的角色去倡导宗教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美国学者研究安妮·哈钦森的视角由纯宗教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他们开始注意到安妮·哈钦森的女性反抗意识。以学者莱尔·科赫勒为代表,就指出:“正是由于许多妇女被安妮·哈钦森的事业所吸引,以至‘唯信仰论’才成为她们广泛表达不满和忧虑的诱因。”并明确说安妮·哈钦森“通过含糊其词的申明和攻击保罗关于女教徒应该无智识、保持沉默的教条的合理性,表达了一种早期的女权主义”[1] (p.37,47)。到20世纪90年代,肯定安妮女权意识的观点日益明确和增多。理查·布肯汉姆在他的文章中说:“虽然安妮·哈钦森在历史上被文件证明是作为一个宗教反对者而被放逐,但迫害她的真正动机是,她通过表达她的宗教信仰向清教社会中传统的妇女屈从地位挑战。”[2] (p.1)国内学者也认为,“在殖民地时期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要求的女性是安妮·哈钦森。她宣传妇女应与统治马萨诸塞生活和思想的男子平等。她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3] (60页)。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安妮·哈钦森的女权意识几乎没有研究。因此,研究安妮·哈钦森的女权意识,一方面可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另一方面可以探究美国女权主义的渊源,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及女权运动。
一、安妮·哈钦森及其宗教活动
安妮·哈钦森于1591年出生在英格兰林肯郡阿尔弗德城一个牧师家庭。当时英格兰正处于清教与国教(又名安立甘教)斗争的动荡年代。安妮的父亲弗兰西斯·马伯里是一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清教牧师,一直反对国教的腐朽。这种家庭环境成为培植安妮女性宗教反叛思想的土壤。安妮从小就受到其父精心教育,阅读了《圣经》和她父亲的许多宗教著作,从而成为一个知识丰富、能诗善辩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其父神学观理解的加深,安妮日益关注清教的发展。
1612年安妮与商人威廉·哈钦森结婚后,其宗教思想和女权意识开始形成。一方面,阿尔弗德城周围几位不合法的女传教士的活动,激发了安妮对女性地位的思考,产生了妇女为什么不能像男子一样传教的疑问。另一方面,青年牧师约翰·科顿的清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安妮,为安妮女权意识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思想内容和神学理论形式。约翰·科顿是林肯郡波士顿伯托菲教区牧师,他同安妮的父亲一样,由于崇信加尔文教并受过良好教育,也反对安立甘教。科顿的宗教观主要认为,道德行为不应该作为“可见的圣洁”的最初资格;有罪的人们只能通过完全信仰上帝来获得拯救,他们的信仰比他们的行为更重要。这种观点来自于神恩契约(the Covenant of Grace)。神恩契约认为,人们可以自己判断自己,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他(她)自身,而不是取决于教会的要求。这与安立甘教主张的行为之约(注:教会的行为之约强调根据神恩的外部信号来支配人的需要。据此,要为人们确定一系列行为准则,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些准则,就要根据其行为进行裁判,只有好的行为才能获得拯救。)(the Covenant of Works)相对立。神恩契约是清教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正是这一思想深深吸引了安妮。为了聆听科顿的布道,她与丈夫不辞辛劳,每周日都要远行24英里去波士顿。在日益着迷于科顿的布道之时,安妮逐渐形成了以科顿讲道为源泉的、以研究《圣经》为基础的、接近浸礼派(注:浸礼派发源于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运动,初为公理宗的一支,反对儿童受洗礼,主张成年人方能接受洗礼。1639年,罗杰·威廉斯在罗得岛创建北美第一个浸礼派教会。)的宗教观,并在以后近20年的宗教活动中日趋完善。可以说,当安妮来到北美殖民地时,她的宗教观已经成熟。安妮的宗教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个人可以感觉自己的灵魂得救,而不必通过熟读《圣经》或牧师撰写的经典来获得拯救。2.内心的圣灵是灵魂得救的保证。3.灵魂拯救的一切职责属于救世主。4.不应该只将星期日作为主日。5.“预定论”无事实依据。6.圣灵寓于每个基督徒体内,并与个体融合。7.教会律法应根据个人的良心要求进行阐释。8.不应该对孩子施洗礼。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信仰本身可以使人获得拯救,人可以与上帝直接交流。这就等于弱化了教会作为交流的工具,降低了牧师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自然要被安立甘教斥为非正统观念。
1634年,安妮与丈夫及13个子女,为了寻找宗教自由和追寻她最敬重的导师科顿的足迹,来到北美马萨诸塞殖民地。然而,安妮并没有在这里找到宗教自由。马萨诸塞虽然是英格兰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于1630年创建,但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清教分离派公理宗(注:清教从不统一,分长老派(主张废除大主教和主教的教阶制,改行长老制)和分离派(又名独立派,要求彻底脱离国教而独立)。分离派属激进派,因主张政教分离,信徒有权决定本教堂的教义、礼仪、礼拜程序、并民主选举牧师而遭镇压。其中有的分离派主张在教会组织上实行公理制,而称公理宗(Congregational Church)。1620年分离派在新英格兰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而马萨诸塞则以公理会为主流,称公理宗。公理宗与分离派有相通之处,但无后者激进,在组织原则上更倾向长老派。)的活动场所。马萨诸塞公理宗一方面强调教会管理体制民主化,全体信徒有平等权力管理教会事务;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秩序,以纯洁信仰为确立高度统一社会的保障,以致在宗教上实行强烈的封闭和排挤;同时,它还奉行行为之约。所以在马萨诸塞早期,清教教会要参与政治生活,他们通过为全体社会成员制定行为准则、过问各种刑事犯罪和任何过失来获得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力。据此,17世纪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形成了一种偏狭、严酷的宗教环境,这必然埋下清教内部分裂与斗争的祸根。事实上,先于安妮来到马萨诸塞的著名分离派罗杰·威廉斯,在1634年就与公理宗发生了冲突。安妮·哈钦森激进的宗教信仰表明,她与公理宗的冲突也不可避免。不过,初期她并不清楚当地的环境,再基于清教徒在英格兰受迫害的经历,因而她对马萨诸塞抱有宗教自由的希望。在抵达波士顿时,她就向波士顿第一教会提出了入会申请。此后,她作为教会正式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但后来安妮发现,她越来越无法赞同牧师们的清教观点。当时只有牧师有布道、施教、主持宗教仪式、召集一般宗教聚会和解释《圣经》等权力。安妮为了表示女性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的信仰,又不违反清教的规定,便采取了家庭私人聚会的方式表达她的看法。起初,聚会主要讨论上星期日牧师们的布道,后来逐渐转向讨论《圣经》。在这一过程中,安妮发表了自己的宗教观。她的观点新颖、合理、宽容,再加上她流利的口才、对《圣经》的娴熟、聪明的才智、高雅的气质,使她的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与此同时,安妮一直从事为产妇接生的活动,也获得了当地人们的普遍赞誉,于是,很快她的家庭聚会便发生了变化:从一周一次发展到一周两次,从纯粹的妇女聚会发展到男子加入,从吸引普通平民发展到吸引绅士、学者和官员等有影响的人物,从十几人发展到60—80人的规模。至1636年,安妮得到科顿、殖民地官员亨利·文、其姐夫约翰·惠尔莱特牧师及许多教众和波士顿人的支持,在殖民地逐渐形成新反对派,引起正统派代表人物约翰·温斯罗普的警觉。温斯罗普是一个狂热的清教徒,马萨诸塞殖民地创建者之一,首任总督。他一直企图建立一个信仰统一、稳定与和谐的清教社会。因而对各种宗教异端极为反感,遂联合约翰·威尔森(被安妮批评的波士顿第一教会牧师)反对安妮,他们得到波士顿外许多教会牧师的支持。温斯罗普等人将安妮的思想定名为“唯信仰论”(注:“唯信仰论”,又称“道德律废弃论”。“唯信仰论”早在宗教改革期间就已形成,后来通称主张基督徒不受道德法律约束的一种信仰,被行为之约论者视为异端。),把安妮的追随者称之为“唯信仰论者”。事实上,安妮他们并不相信内心圣灵能免除他们遵从道德法律之义务。他们只是反对按行为之约布道,而主张遵从神恩契约。
1637年5月温斯罗普击败亨利·文,当选为马萨诸塞新一任总督后,随即颁布法令,阻止新的“唯信仰论者”移居波士顿,其中包括安妮的兄弟及许多朋友。当年8月,又召开宗教会议,宣称“唯信仰论者”犯有82个异端错误,并禁止所有私人聚会。在遭到安妮的抵制后,温斯罗普便在11月,组成以他为司法长、陪审长和首席大法官的大法庭对安妮和惠尔来特进行审判。他们指控安妮的主要的罪名是:1.安妮因为不尊重她的父母官(指殖民地官员)而破坏了第五条戒律。2.安妮妄称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并从上帝那里接受启示。3.安妮召集私人聚会,将她的异端思想传染给别人。4.安妮诋毁牧师和他们的职位。最后安妮被判决逐出马萨诸塞。由于怀孕,冬季无法出行,殖民当局才将她暂时软禁以待来年春天的第二次审判。1638年3月15日,波士顿宗教会议的长老们对安妮进行了近9个小时的审问,他们再次指责安妮犯有29个错误。这次,她最敬重的导师科顿完全转变态度,攻击安妮。安妮毫不退缩,她说:“你们的裁判并不等于上帝的裁判,宁愿被逐出教会也不愿否认基督。”[4] (p.312)
安妮被放逐后,和丈夫、孩子以及60个追随者来到纳拉甘西特湾,建立了阿奎勒克定居点,1639年发展成朴茨茅斯小镇,以后成为罗得岛殖民地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不仅实行宗教自由,而且签订契约,组建自治政府。1642年威廉·哈钦森去世后,安妮移居到荷兰殖民地纽约。次年她和5个年幼孩子被印第安人所杀。
二、安妮·哈钦森的女权意识
安妮作为一个教会成员和接生婆,其女权意识体现在一系列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因此,她的女权意识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和个人化特征,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要求女性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安妮从离开英格兰起,就有了对宗教事务发言的意识。在乘坐“格利芬”号船前往马萨诸塞的途中,安妮便对该船引导牧师泽查理·西蒙斯的布道表示异议。此后,安妮要求妇女发言权与参与权的意识日益强烈。
家庭私人聚会形式本身就体现了安妮的女权意识。安妮是受男人们召开各种会议的启发而采取这种形式的,这说明安妮并不满意教会禁止妇女举办宗教会议的规定,这正如安妮在第一次审判中,回答温斯罗普的质问时所说,“对我来说,它(家庭私人聚会)是合法的,召开宗教会议是你惯常所为,对此,你为什么可以为自己找根据而来谴责我呢?……在我来到这里以前,(清教徒)召集会议(在英格兰)普遍存在,我并非第一个”[4] (p.314)。这明确表现了安妮内心深处的男女平等意识。不过,她深知这种心理与当时社会歧视妇女的状况相悖,所以,她的聚会形式是有限的。从私人家庭聚会的内容来看,安妮是以《圣经》为依据,通过引用经典来分析和评价牧师们的布道,进而阐述《圣经》,这不仅使她的聚会内容新颖独特,而且向与会者展现了她不同于波士顿牧师的神学理论观,这对长期接受牧师布道的波士顿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安妮指出,“大多数波士顿牧师都是(不依据《圣经》)随意布道。而上帝说,一个誓约的产生就是所有争论(指牧师不同的布道)的结束。虽然现在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做,但是他们仍然如此,因此我希望他们遵从誓约”[4] (p.327)。因为马萨诸塞就是清教徒依据《圣经》签订的契约建立的,所以安妮认为波士顿牧师就应该依据《圣经》来布道。又如,安妮指出,牧师强调个人只能通过教会这个媒介才能与上帝沟通,但事实上,她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并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进而宣称,她曾经正确地预示了到达马萨诸塞的日期。由此安妮证明,多数牧师宣讲的教义不是《圣经》的真正内容。因此,许多制约人们思想行为的教规是不合理的。她说,宗教法规不是神圣、虔诚的信号,真正的虔诚来自内心对圣灵的体验,并进一步宣称,在波士顿只有二个牧师被上帝选中和获得拯救,即约翰·科顿和惠尔莱特。安妮的神学观得到了聚会者认可,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在宗教活动中应有地位与作用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安妮的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安妮家庭私人聚会的内容又转为鼓励和参与马萨诸塞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如,安妮在聚会上引用《圣经》赞同威廉斯、科顿和惠尔莱特的教义,指出,只有他们宣讲的教义才是正确的,当权牧师约翰·威尔森派的教义是错误的,并反对波士顿当局驱逐威廉斯和打击惠尔莱特派。从家庭私人聚会的效果来看,安妮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充当了“女牧师”的角色。因为家庭私人聚会规模的扩大、层次的增加和单一性别结构的改变,就是安妮宣讲其教义的结果。另外,安妮由聚会召集人变为聚会的主要发言人之后,常常要站在高凳上向众多的听众演说,并且还主持一系列祈祷仪式,与上帝进行内心的交流,并接受启示,这些都表示安妮在进行有限的传教活动。而且,安妮的布道还通过聚会者传播到外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追随安妮,以至在马萨诸塞一度出现了妇女攻击牧师,仿效安妮布道和进行预言等现象。安妮的同代人爱德华·约翰逊说,柔弱的女性将安妮树立为一个“牧师”,然后蜂拥尾随[1] (p.39)。安妮的反对者和审判者之一,牧师休·彼特嘲讽安妮选择作一个“女传道士”来树立她行为的榜样,“你宁愿作一个女传道士而不愿作一个女听众”,目的是为了“迷惑”更多妇女[4] (p.383)。莱尔·科赫勒认为,“安妮选择作……‘女传道士’,是为了树立女英雄的形象”,“一个坚强女英雄的榜样是认可个人力量所必须的”[1] (p.42)。
安妮从行动上挑战男性的权威和介入男性公开的宗教与社会斗争,这也是安妮要求女性发言权与参与权的重要表现。她不顾科顿劝告她“在这里闭上嘴巴是明智的做法”[5] (p.87),在禁止妇女发言的教堂上讲话。尤其是,在威尔森起来布道时,她勇敢地离开了教众会,以示拒听。1636年夏,亨利·文当选为殖民地新任总督后,安妮利用他和科顿的力量,联合她的追随者拥护惠尔莱特取代威尔森出任波士顿第一教会牧师。此举给威尔森以很大威胁。不得已,威尔森发表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分裂危险”的演讲,得到温斯罗普等殖民地上层人士及官员的支持,才保住职位。1637年3月当温斯罗普的法庭审判惠尔莱特时,安妮及其追随者在法庭外举行抗议示威。在同年5月的总督选举中,安妮又和她的追随者支持亨利·文,反对温斯罗普,由于当时妇女没有选举权,使这次支持以失败告终。
安妮的举动大大违背了男权优势的殖民地社会传统,因而引起温斯罗普等人的极大反感和愤恨。他们极力攻击安妮的家庭聚会。温斯罗普说:“由一个妇女以预言的方式,通过解决神学问题和阐释经文来发挥她的作用,则是混乱和目无法纪的。”[6] (p.40)约翰·科顿将安妮的聚会描述成“一群不分婚姻关系的、乱七八糟的、污秽的男女的聚会”[7] (p.4)。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安妮的行为进行控告。温斯罗普说:“只要你支持和鼓励了那些违法者(指惠尔莱特和威廉斯等人),你就同样有罪。”[4] (p.313)休·彼特说安妮的行为使她“更像一个地方官而不像一个臣民”[4] (p.383)。威尔森更是充满仇恨地说:“我以耶穌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把你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赶出教众会。……把你交付给撒旦。”[8] (p.100)
第二,安妮反对殖民社会在知识上对女性的歧视,要求承认女性的知识平等权。在17世纪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虽然中上层女性一般接受教育,但仅限于初步的计算能力和文字阅读能力的培养。像安妮这种具有很强阅读力、分析力和理解力的女性是极少数。当时普遍观念认为,女性天生低贱,应尽量“避免书本和智力的训练,因为这种活动可能增加她们柔弱大脑的负担,不利于满足她们丈夫的意愿”,“阅读和写作是心智强大的男人的专利”[1] (p.37)。不仅如此,根据基督教使徒保罗的教义,还“要注意不让妇女学习、传教和侵越男性的权威”[1] (p.37)。据此,清教正统派力图树立一种智识低下的淑女风范。对于有才智的女性,正统派总是毫不留情地攻击,说她们丧失了理智和理解力,无法履行妇女的起码职责。安妮对正统派的做法非常不满,所以她总是力图通过自身的例子来树立知识女性的尊严与地位。由于《圣经》是安妮当时能获得的唯一读物,故而安妮主要是通过讨论《圣经》和在审判中的自我辩护来展露这种愿望的。如前所述,安妮对《圣经》的理解和分析所展示的智慧,得到了与会者的钦佩,实际上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公众对安妮知识女性形象的肯定。安妮还利用1636年宗教集会对她的审查,暗示她有必要的知识来判断神学的正确性。在1637—1638年的两次审判中,安妮公开宣称她拥有正确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例如,在第一次审判中,当温斯罗普攻击安妮的行为不适合她的性别时,安妮立刻说她与温斯罗普在智力上是平等的,并引用《圣经》说:“在《提多书》中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年纪大的妇女应该引导年青妇女,因此我必须有一个这么做的机会。”温斯罗普无话可说,便宣称“我们必须制止你继续布道”。安妮机智地说:“如果你能从《圣经》那里为你的做法找到一个规定的话,你可以这么做。”[4] (p.316)当温斯罗普试图引诱安妮承认自己施教男人,违背了保罗的禁令时,安妮则说这是正当合理的,并反问:“如果任何人来到我房间请求依《圣经》指教的话,我必须按什么规定抛弃他们呢?”进而她嘲讽地说:“你认为我指教妇女不合法,为什么你还召我来指教法庭呢?”[4] (p.315)温斯罗普被安妮的机敏辩护挫败而恼羞成怒,“我们是你的法官,而你不是我们的法官”[4] (p.316)。事实上,安妮的出色辩护使反对者也不得不暗自承认她的才智。温斯罗普曾这样评价安妮:“尽管她在理解和判断上不如许多妇女,但她却表现出狂热、傲慢的姿态,拥有敏捷的才智、能动的精神、流利的口才和比男子更勇敢的行为。”[4] (p.263)当然,他们感到这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作为知识领袖和社会代言人的自我形象。为防止其他妇女仿效安妮追求知识,他们极力攻击安妮的智识表现是撒旦的行为,并宣称知识行为不适合妇女。
第三,安妮追求家庭平等,主张妇女突破家务限制,谋求“职业”活动。17世纪殖民地妇女的主要事务是家务,另外还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和宗教活动。殖民社会一般严格限制妇女的社会活动和独立性。安妮虽然承认妇女的家庭职责,但她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她一方面通过举办家庭私人聚会来突破家务、关注社会,向人们传递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例如,聚会上男女混合相坐,讨论中男女平等发言,没有尊卑贵贱和性别歧视,有思想的发言者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她通过当一个义务的“接生婆”,作为她某种程度参与社会的方式。她把为妇女接生作为自己的职责,不以谋利为目的。这既加强了与其他妇女的联系,增进了她们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使“接生婆”成为她的一种“职业”,传播了她的家庭平等观念。莱尔·科赫勒说:“安妮·哈钦森作为妇女中最直率的发言者,在从事接生婆的职业和一周二次家内布道的过程中,依靠广泛的接触,将她的意见传播到所有阶层。”[1] (p.39)这无疑是对安妮要求“职业”的一种肯定。安妮最终被波士顿妇女公认为中产阶级妻子的典范,也获得了丈夫的尊敬和信赖,并奠定起夫妻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为许多妇女所羡慕和仿效,当然也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伦理,导致正统派的忿恨。休·彼特公开指责安妮没有履行适当屈从的、非才智的女性角色,说安妮“更像一个丈夫,而不像一个妻子”[4] (p.383)。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安妮违背传统习惯的思想行为归咎于唯信仰论男性的懦弱和无能。温斯罗普就说安妮的丈夫是一个“性格温和、软弱的次要角色,完全受他妻子所操纵”[1] (p.45)。其他反对派也认为威廉·哈钦森是一个才智和判断力差的男人。其实,反对派攻击安妮的言论正好从反面证实了安妮要求家庭平等和“职业”活动的意识。
应该说,安妮的女权意识在罗得岛也得到充分表现。据记载,当安妮被驱逐来到罗得岛后,其女权要求得到实践。例如,安妮她们在罗得岛进行公开的传教和布道,男人们也注意倾听妇女们的要求,并保护她们教书、布道和选择社会活动的自由。因而,妇女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一个名为约翰逊的人在1638年曾写道:“一些认为使徒保罗禁止妇女聚会和布道的规定太严格的女性,把她们对女权的要求带到这里(罗得岛),在这儿自由传教,这完全是来自于女性内心对女权热烈的渴望。”[1] (p.46)在罗得岛以后的岁月中,安妮还继续为捍卫民主、自由和平等而斗争。1639年,当朴茨茅斯的最高长官威廉·科丁顿试图进行独裁统治时,安妮便联合塞缪尔·戈顿反对他,否决了他的最高长官职务。安妮事实上已成为罗得岛的精神领袖。
三、安妮女权意识的影响及评价
安妮女权意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这可以从反对者的话得到说明。约翰·科顿曾说安妮的意见“像坏疽一样在侵蚀,像麻风病一样在传染,将吃掉宗教的内肠”[7] (p.11),从而将妇女引入歧途。约翰·温斯罗普说安妮“引起了丈夫和妻子之间以及其他亲属之间意见的分裂,直到弱者让位于强者,否则,将转变成公开的斗争”。“一切事情在我们中间都被搞颠倒了”[4] (p.253)。其次,据史料记载,有一批妇女受安妮的影响而成为其女权意识坚定的追求者。这批妇女既有中上层富人,也有下层穷人。理查德夫人珍妮·霍金斯来自于中产阶级,是安妮最亲密的女朋友之一,温斯罗普斥责她是“亲近魔鬼而臭名昭著的人和主要的女权主义者”[4] (p.281),大法庭在1638年禁止她发表意见,并于1641年将她处以鞭笞刑罚后逐出马萨诸塞;玛丽·奥利弗是萨勒姆一个贫穷轧光机工人的妻子,据说她的演讲才能、热情和献身精神胜过安妮,玛丽·奥利弗在1638年和1650年间,先后六次当面表达对牧师和地方官权威的蔑视,温斯罗普说她对殖民地“造成了伤害,不过她因贫穷而并不熟悉神学”[1] (p.40);在这些妇女中最有名的是妇女头饰商威廉·戴尔的妻子玛丽,温斯罗普评价她是一个“拥有高傲精神的人”,“特别醉心于启示”,“受哈钦森夫人臭名昭著的错误的影响”[1] (p.39),其实,玛丽·戴尔是一个追求执着和意志坚强的女性,1638年她追随安妮来到罗得岛,安妮死后,她的激进信仰使她转变成贵格教徒,并最终为其信仰而献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反叛”妇女,如:威廉·科丁顿的妻子、富裕地主理查德·邓梅的妻子、萨拉·克妮、哈蒙德夫人等,都在公共集会中仿效安妮进行预言,并蔑视地方官与牧师的权威。安妮的言行还影响了一些男性,当安妮被驱逐的时候,波士顿有75名男子抗议这一判决。
毫无疑问,安妮的主张反映了马萨诸塞妇女的要求,才引起了妇女们的共鸣。1636年安妮具有女权意识的神学理论的提出,给她们提供了可行的神学形式。依据这一理论,妇女在清教社会中的地位跟男子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权威可言。同时,安妮蔑视权威,并不把自己归为正统派所谓的“有价值的高尚妇女”之列的行动,也影响妇女去超越旧的传统习俗。美国学者萨拉·埃文斯说:“(安妮)用自己的内心体验美德的说法使妇女有权表达各自的宗教体会,有权拒绝接受世俗权威的意见,这种含有妇女解放成分的可能性,促使妇女大批前往哈钦森那里聚会,当然也吸引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男人。”[9] (29页)其实,妇女对自身屈从地位的不满也是安妮女权意识传播的“群众基础”。另外,马萨诸塞清教本身也给安妮女权意识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出于发展清教的目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一般允许妇女公开参加清教活动,这作为妇女当时唯一合法的社会活动,使妇女往往倾注极大的宗教热情。罗杰·汤普森说:“清教英格兰妇女以强烈的宗教热情而闻名。”“波士顿教会在1630年至1649年接纳的成员表显示,有411名妇女,……379名男子”。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肯定,妇女必然在英格兰清教主义的女英雄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10] (p.93,94)。
为了彻底摧毁安妮的形象及其思想意识,清教正统派在驱逐安妮的同时,还散布安妮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撒旦,变成女巫的言论。为了增强这一言论的可信度,他们列举了安妮的追随者玛丽·戴尔早产“怪胎”之事,以此说明,这一畸胎就是安妮她们男女混杂、道德堕落后,上帝对她们进行惩罚而降的灾难。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安妮也是“被上帝视作的一个娼妓、一个‘荡妇’”[5] (p.108)。当1643年他们获悉安妮遇害的消息时,更是欣喜地宣称,“上帝的手已及于此”,对“荡妇”安妮进行了惩罚,“骄傲的‘荡妇’终于被推倒了”[5] (p.137)。从而,他们断定这是安妮女性反叛意识与唯信仰论死亡的信号。毁损安妮名誉的做法在马萨诸塞颇显成效。至17世纪40年代,几乎很难再听到妇女要求女权的声音。
当然,不可否认,安妮的女权意识并不成熟,具有浓厚的神学性,女性的地位是建立在上帝对妇女的恩赐基础之上。而且其女权意识没有系统完整的理论观点和群体意识,突显个人作用,缺乏对妇女屈从地位的根本性思考等。这正如莱尔·科赫勒所说,安妮生活在以神学为基础的社会,她自然很容易在宗教争论中,把自己与神结合起来表达她的自信和女性意识。虽然她“已意识到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落后性”,但她“并没有打算通过加强群体活动来改善妇女被压迫的地位。她的女权主义意识完全是由个人主观认可的自身力量和才能所构成的”。[1] (p.42,47)。因此,从倡导争取目标明确的群众性运动的角度来说,安妮算不上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也并未形成明确的女权思想。但是,从美国女权主义的渊源来说,安妮可以算作美国早期的女权主义先驱,是领导美国公众为宗教多样性和女性平等而斗争的第一位美国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