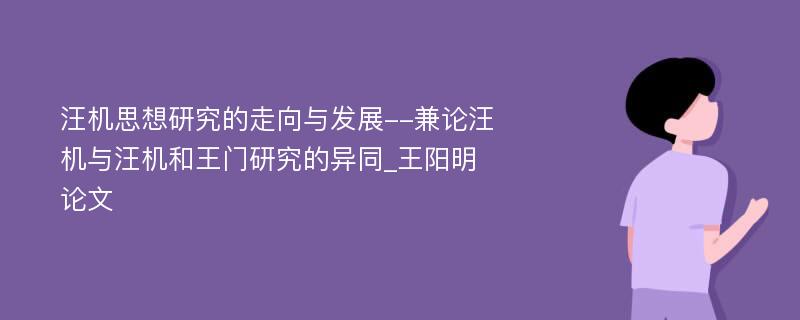
王畿心学思想的走向和发展——兼论王畿与王阳明及王门后学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门后论文,走向论文,思想论文,心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畿(1498—1583年),字汝中,别号龙溪,浙江山阴人。王畿从学阳明较晚,但他是师门中悟性天分颇高者,与钱德洪一起深受阳明的赏识,被称为“教授师”(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又因学术上的建树,与王艮齐名,并称二王。他一生致力于宣传“致良知”学说,以良知立论,不加掩饰地援禅理入儒,被后人批评为“跻阳明而为禅”,(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但又对师说多有创发,形成了以“四无”说、“良知当下现成”、“一念之微”、“君子之学,无念为宗”、“格者,天然之格式”和“一念良知范围三教”等为基本内容的心学思想体系,成为王门后学中左派狂禅一脉的一代硕师和开创者。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王畿说:“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本文将王畿置于明代理学思潮之中,着眼于心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轨迹,从王畿提出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出发,剖析和阐明其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并通过心学一系的纵横比较研究,重点阐发王畿与王阳明及王门后学之间的异同,意在揭示和判定王畿心学思想的创见特色及其走向与发展。
一 “四无”说与良知当下现成
王阳明在“天泉证道”中,把“四句教”首句的“心之本体”规定为“无善无恶”,要求人们通过在意念上的“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工夫,逐渐地恢复心的本体,强调为学和修养之道是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并由此而分别肯定了王畿的“四无”说和钱德洪的“四有”说。但是,王阳明又特别地叮嘱王畿,顿悟之法固然从理论上可以这么讲,但“不宜轻以示人”,否则难免会使人造成“空想本体,流入虚寂”(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天泉证道记》。)的弊病。而实际上,王畿把王阳明的“四句教”引申为“四无”说,这本身就昭示着王畿心学与王阳明心学的某种分野及其衍化路向(注:参见拙文:“四句教”与王学分化,《湖湘论坛》1998年第3期。)。王畿在《天泉证道记》中指出:
……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着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注:《王龙溪先生全集·天泉证道记》。)王畿着眼于从本体上说工夫,“从心上立根”,把自己的“四无”说称为“先天之学”,而将其同门钱德洪的“四有”说看成是“从意上立根”,称为“后天之学”,主张是“先天统后天”,(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处处以“悟”阐扬自己的学说,并援引和借用儒家经典《周易》与佛教中所共用的“密”、“圆”、“寂”、“神”等字眼,来进一步诠释心、意、知、物,以强调“悟”的重要性。王畿十分凸显和强调人之主体的意识或情感的“自性流行”,把“自性流行”说成是“动而无动”,即程颢在《定性书》中所提出的情顺万物而“定”的境界,而把“着于有”视为“动而动”,即意念上执著于善恶的区别、肯定与否定,从而指出心之所发的意念上的有善有恶与承认心体的无善无恶是相矛盾的。在这里,王畿肯定心、意、知、物为一事,都是就无善无恶可言,从理论逻辑上讲,意味着把作为本体的“良知”与已发之意念看成是无实质差别的同一层次的概念范畴;同时,既然承认本体与意念都无善无恶,那么为善去恶的“致良知”的工夫也就失去了必要性。这看似强调本体与意念的合一,避免本体与已发的后天经验之域的分离,但实际上是以当下的意念为本体,一方面消解和弱化了良知道德本体的形上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本体的自觉性意识,即为善去恶的道德意识的体认和践履成为多此一举。王畿的“四无”说在突出先天的“心体”与后天的“意念”之间的一致和合一的同时,又逻辑地演绎和包含着以先天的良知为当下现成(见在)的结论。
王畿的“良知当下现成”的观点就是在“四无”说基础上展开的”。他解释“良知”说:
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当下现成,不假功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以“无”来说良知,强调良知永远是“当下现成”的,无须假借工夫修证,提出了“良知现成”说,他又从体用关系上来界定“良知”,提出:“良知原是无中生有。……虚寂原是良知之体,明觉原是良知之用。体用一源,原无先后之分。”(注:《王龙溪先生全集·滁阳会语》。)就本体而言,良知的本体是“虚寂”,即良知的先天性;就作用或工夫而言,良知的作用是“明觉”,即主体对良知道德意识的自觉。王畿认为良知本身就是体用一源,没有先后之分,即强调先天与明觉的合一,其根本意蕴是要彰显先天即明觉、本体即工夫。依照王畿的理解,所谓的“现成良知”,这也就决定了主体具有的不学不虑、天之所为的“自然之良知”自我能够在现实的道德践履中,像爱亲敬兄一样“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注:《王龙溪先生全集·致知义辨》。)因此,王畿不同意罗洪先否认世间有现成良知的观点,提出:
念庵(罗洪先)谓世间无有见成良知,非万死功夫,断不能生。以此较勘虚见附合之辈,未有不可。若必以见在良知,与尧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证,而后可得,则未免矫枉之过。(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承认罗洪先的修证说有勘定某些俗辈以“虚见附合”之功,但如果由此就完全否认常人与圣人有着共同的现成良知,那么这也难免是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在他看来,良知是人人所具有的,常人与圣人在现成良知上也是相同的,即“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损而后全”(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从这里可以看到,王畿与王阳明各自对“良知”的理解和看法有所差异:前者强调良知是先天与明觉的合一,主张从心体上来明觉,把致良知视为当下现成的顿悟;后者则着眼于良知的本然(即先天)与明觉的区分,认为主体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吾心先天固有的本然良知,必须着实地经过后天的致良知的工夫过程。王畿还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独知”论,把“独知”视为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他说:
良知即是独知,独知即是天理。独知之体,本是无声无臭,本是无所知识,本是无所粘带拣择,本是彻上彻下。独知便是本体,慎独便是工夫,只此便是未发先天之学。(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论学书》。)
照王畿的理解,从体悟良知本体的当下性来说,独知既是本体,也是工夫,其原本就是贯通“彻上彻下”的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他进而把“独知”诠释为人们“先天灵窍”具有的清净本心,将“慎独”工夫说成是保护或复归此先天灵窍所具有的“清净”本心,(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论学书》。)显然是受佛家禅理的影响,表现出王畿的“独知”的理解与王阳明不同。王畿还认为“当下本体”原本就像“空中鸟迹,水中月影”,似有似无,若现若浮,具有“神机妙应,当体本空”的性质,人们无从具体认识,惟有以“悟入”为方法,才能真正的体认和把握“良知”本体这个“无形象中真面目”,而这看似无须丝毫用力中,却正是我们切实下工夫的“大着力处”。(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论学书》。)这里必须指出,王畿所谓的悟“无”,只是借用佛教概念,其本意并不是指虚幻空无的非实在,而是要从本体意义上来描述“良知”的本来状态,凸现良知所具有的空灵无滞的本性。有鉴于此,王畿又进而将“悟”界定为是要“忘是非而得其巧”(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即使吾心恢复到良知本体的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意识状态,从而强调顿悟就是把“种种嗜好,种种贪著,种种奇特技能,种种凡心习态,全体斩断,令干干净净,从混沌中立根基”。(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所谓“混沌中立根基”,就是要求从良知本体的无分别、无是非、无善恶处立论,无所执著。惟有如此,才算“始为本来生生真命脉”,才算是“志真”,才算是“功夫方有商量处”。(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因此,王畿评论陆九渊所写的“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两句诗,指出其学不是从本体悟入,而是“学得力处全在积累”,即从积累入手,从而表明自己学说与陆九渊心学的不同:从“最上一机”,(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即心体着手,强调对心体混沌本无境界的“顿悟”,且是当下悟得,一了百了,从而肯定和彰显良知本体的当下、见在和现成的作用。他强调自己“在先天心体上立根”的顿悟法与世人“在后天动意上立根”的渐修法不同,力求直截彻悟心体的学问,认为心体至善,只是由于动于意念,才有一切世情嗜欲的不善,假如人们能够当下体悟心体,“世情嗜欲自然无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简省力”,否则,难免“致知功夫,转觉繁难”。(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就本体与工夫关系而言,王畿反对脱离本体而谈工夫。指出:
若果信得良知及时,只此知是本体,只此知是功夫。良知之外,更无致法;致良知之外,更无养法。良知原无一物,自能应万物之变。(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认为体认或信得良知,就是知此良知即本体即工夫。人们终日去学习思虑的也只是要去恢复那不学不虑的良知本体,王畿称其为“无工夫中真工夫”,倡导为学“工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尽便是圣人”。(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针对刘狮泉认为本体与工夫“必兼修而后可为学”的观点,指出“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良知即是主宰,又是流行,致知的工夫,“只有一处用”,(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即归一良知本体。王畿进而还对当时王门后学各家持论的良知诸说进行了剖析和评判,以阐扬自己对良知的系统看法。他说:
良知宗说,……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符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终始。此皆论学同异之见,不容以不辨者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列举和点评了同门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六种主要看法:其一,把良知视为非主体意识的自觉,主张必须在静中涵养方可始得,就如同明镜照物;王畿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寂”为心之本体,以“照”为用,是顾体而忘用,即“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用也”。其二,反对良知见成,即认为没有先天的圆满自足的良知,良知是在后天的的长期修养中形成的,如同金子必须在烈火中锤炼熔铸一样;王畿从孟子讲“四端之心”是不学而能、当下具足的,指出“谓良知由修而后完”的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挠其体”,即从本体上否定了良知的先验性。其三,主张良知是从已发上立言,没有阐发《中庸》中所讲的“未发”、“无知”的学术宗旨;王畿从“良知原本是未发之中”的立场出发,指出如果将良知当作已发,于良知之前“复求未发”,那么就必然流于“沉空之见”。其四,坚持良知本体原本无欲,可任心而行,不必去做克私销欲的工夫;王畿认为古人立教,原本就是“为有欲设”,致良知就是使人具有的当下现成的、圆满的良知得到充分极至的表现,必须有克除私欲蒙蔽的工夫过程,即“销欲正所以复还无欲之体”。其五,主张心之主宰谓之性,心之流行谓之命,性即体,命即用,从体用上来言良知,反对只讲良知现成,强调随时运化良知、致用良知;王畿从“体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出发,认为此种观点,从为学的工夫论来说,是立体以养其主宰,致用以随时随事精察,将工夫割裂为二。其六,主张为学方法贵在有序,就“求”而言,有“本末”之分,就“得”而言,“无内外”之别,倡导以致良知的工夫来区别终始;王畿强调指出,所谓“求”是“得”的原因,所谓“得”是“求”的证悟,“始终一贯,不可得而别”,(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如果刻意于本体与工夫的区分,其结果必然导致繁琐支离。王畿在这里对良知异说的归纳和概述,据史料可查证的,分别指来自其同门、友人聂豹、罗洪先、钱德洪、王艮、刘邦采、李材等。(注:参见《明儒学案》中的《江右王门学案二》、《江右王门学案三》、《浙中王门学案一》、《泰州学案一》、《江右王门学案四》、《止修学案》等。)
从王畿对良知异说的批评和阐发中,我们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了解王门后学对王阳明良知说的不同理解,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分化、发展、衍变和影响,而且可以从相比较中,展现和凸显出王畿自己对良知理解的重点和特点。如果说王阳明的良知说,肯定心与理、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重点在强调致良知的工夫和知行合一中的“行”的话,那么,王畿主张良知的先天与明觉的合一,倡导本体即工夫,突出良知的当下现成性,则更重视就本体谈工夫,从“心上”或“无处”来专论良知本体,从而使良知本体的超验性越来越趋向于现实的境域。从这一点上来讲,王畿以当下现成论良知,还未完全脱离王阳明的思维理路,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差异仅表现为侧重点不同而已。但是,王畿的良知当下现成说是颇具理论特色的学说。王畿主张先天之学,注重良知本体的圆满天成,高扬良知本体当下现成的旗帜,强调从“一念之微”或“真几”上实证,突出地反对率任现成良知,指出此观点否定良知与情欲的区分,借口现成良知,肆无忌惮地放纵私欲,以情欲为良知,忽视了克除私欲之功,从而表明和彰显自己与王艮为代表的被视为学术“异端”之间的区别。王畿在《书同心册》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良知者性之灵根,所谓本体也。知而曰致,翕聚缉熙,以完无欲之一,所谓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于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于天成,本来真面目,固不待修证而后全。若徒任作用为率性,倚情识为通微,不能随时翕聚以为之主,倏忽变化,将至于荡无所归,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再三强调良知在人,完全是出于不学不虑的“天成”,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不必通过后天的修养实证的工夫来获得的,强调良知本体在工夫上的当下现成,进而批驳“任作用为率性”的观点是以情识为通微处,没有在心体上进行收敛聚合的涵养工夫,必然导致致知之功的逐物累情,流荡于情识而无所归宿,名存实亡。
就理论的内在逻辑而言,王畿把“四无”的设定与良知的当下现成相结合,强调本体即工夫,挺立人的良知道德主体意识,这就不仅意味着当良知本体被赋予现成形式、见在作用的同时,良知本体也就或多或少地被消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意识之中,即很难把良知与日常生活中的意识严格区分,而且也使后天的致良知的工夫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引向了本体对工夫的兼融和消解。这与王畿援禅理入儒相联系,使他确实受到“近禅”的指责和批评。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洪先在《寄王龙溪》的信中就颇不客气地指出:
以为良知无内外,无动静,无先后,一以贯之,除此更无事,除此别无格物。……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指为外道,恐阳明先生复生,亦当攒眉也。(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三·论学书》。)罗洪先将王畿的良知当下现成说概括为“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在一定程度上,其批评显然是颇中肯綮的。难怪黄宗羲也说王畿是“谈本体而讳言工夫,识得本体、便是工夫”。(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五·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忭》。)诚然,王畿不满于致良知的“致”,认为“致”就是工夫修证,违背了良知自然之则,倡导随处用力,无分动静,即发用即收敛,只依良知而行,就是“致良知”,反对良知之外还有“致”的工夫。但是,如果我们系统考察王畿的良知当下现成说,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矛盾,或者说他在与同门师友的学术切磋中,特别是随着泰州学派中自然主义的泛滥,率任现成良知,走向了视情识为良知而忽略克私销欲之功的弊端,使得他在良知“见在”、“现成”的问题上有所警觉和顾忌,后来在对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上有所注意和修正。王畿曾提出:
圣人自然无欲,是即本体便是工夫。学者寡欲以至于无,是做工夫求复本体。故虽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尝废困勉。……舍工夫说本体谓之虚见,虚则罔矣。外本体而论工夫,谓之二法,二则支矣。(注:《王龙溪先生全集·答季彭山龙镜书》。)圣人与常人所不同的在于“气习”和方法:圣人本体无蔽,也没有不道德的欲念,所以圣人不必以正意念为工夫,圣人体认本体本身就意味着工夫,但圣人不否定工夫,即所谓“论工夫,圣人亦须困勉”;常人被“气习”所染蔽,就如同明镜被尘埃所蒙污,必须经过抹擦灰尘的工夫,才能恢复明镜本体,所以重在工夫,但是如“论本体,众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机直达”。(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认为本体即工夫或以工夫求复本体,是“兼修之功”,不可废缺。
综上可见,王畿虽然反对脱离本体言工夫,但也并不是一概地不言工夫。实际上,王畿并不像泰州学派那样撒手自在,而是有着其自己的工夫,他既讲经世,又讲从动静顺逆的现实生活中去煎销磨炼,方能真有得力处,从而表现出其心学理论的特色。王畿一方面自视为“利根之人”,力主先天顿悟之学,坚持“良知是天然之灵机,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何尝照管得,又何尝不照管得”;(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中根以下之人必须进行后天的渐修之功,“须信各种嗜欲皆是本心变化之迹,时时敌应,不过其则,方为锻炼”。(注:《王龙溪先生全集·答赵尚莘》。)这里,王畿所倡导的良知当下现成说中的内在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又恰恰表明了其学术个性及风格所在。同时,王畿把王阳明的良知说发展为良知当下现成说,将其“致良知”改造成“良知致”,借以自立思想体系,而这些又都在后来泰州学派的王艮那里得到具体的发展和体现,从而表明王畿与泰州学派之间在学术发展上的某种一致性。
二 一念良知范围三教,圣学以“无念”为宗
王畿心学思想的又一大特点是,既援道入儒,又援释入儒,主张“三教”归一,倡导学者做糅和道、释之儒。他在《三教堂记》中就明确指出:
三教之说,其来尚矣。……良知者,性之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范围三教之枢,不徇典要,不涉思为,虚实相生而非无也,寂感相乘而非灭也;与百姓同其好恶,不离伦物感应而圣功征焉。学佛老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注:《王龙溪先生全集·三教堂记》。)儒、释、道“三教合一”说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的儒、释、道之间的论争。魏晋南北朝时,学林士子援佛入儒或引儒入道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于是就有了儒、释或释、道相融的学说,特别是梁武帝萧衍提出“三教同源”的理论更是成为日后“三教合一”思想之滥觞。宋明时期是“三教合一”论的重要发展时期,理学家大多有出入释、老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大多吸取和运用释、道的思想内涵及其修持方法,具有会通儒、释、道三教的强烈倾向,如无论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还是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无不糅禅融道,但他们却在表面上俨然以正统儒学自居,不遗余力的排解释、道。王畿则不同,反对将释、道简单的视为“异端”,他不仅重在从义理上来疏释“良知”本体论的三教同源,而且还顾及从道德践履和内心修养的工夫论上来阐发三教的兼容并蓄,认为“良知”作为人性的灵根,本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范围三教”的关键。就本体而言,“良知”既不曲从于典籍,又不牵涉于人的思虑作为,其本身具有“虚实相生而非无”、“寂感相乘而非灭”的特点;就工夫而言,“良知”作为先天内有的道德准则,圣人百姓同其好恶,只要能顺依良知准则以适外物感应,就能使“伦物”(即事)具有道德的秩序,这也就是作圣之功。因此,王畿号召人们学习佛、老,从工夫论上讲,就是以恢复、扩充和涵养人心固有的良知本性,只要本着复性的宗旨,没有沦丧于幻灭妄念,就能做一个糅和道、释之儒。
王畿在公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同时,他还从心学的立场来阐发道教“调息”与儒学养心之“真息”的关系,认为真息是“动静之机,性命合一之宗”,(注:《王龙溪先生全集·东游会语》。)且“圣学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灵机”,只要人们能在存心中涵养良知,即通过致良的过程,就能使“真息自调,性命自复”,而调息只能起到定气收神的养生作用,既不能使人彻悟良知本体,又不能代替在意念上的“为善去恶”的工夫,即与圣学强调“致中和工夫终隔一层”。(注:《王龙溪先生全集·留都会记》。)王畿从“心息相依”的角度,进一步阐明调息、数息和真息之间的区别:
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使心有所寄,神气相守,亦权法也。调息与数息不同,数为有意,调为无意,委心虚无,不沉不乱。息调则心定,心定则息愈调。真息往来,呼吸之机,自能夺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谓息息归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范围三教之宗。(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论学书》。)王畿认为调息能使人静坐收心、神气相守,但作为圣学入门还只是一种权宜之法。因为调息与数息的根本差别在于:数息是人有意识地去数呼息,逐渐地达到静心,但却不能使心意达到虚无的境域;调息则是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去呼吸运气,使心趋虚无,气沉而不乱,达到调节呼吸顺畅而心定如常的目的。但是,就圣学之道的修身养性而言,单把握数息、调息之法还不够,必须提升至“真息”这一更高阶段,从“一念微明”、“一念真几”入手。而这一念,就是良知,就是“常惺常寂”,它包容三教的宗旨。这里,所谓“常惺常寂”,是王畿用释、道二教中的“惺”、“寂”概念,来描述和阐明良知本体具有明察物欲、分辨是非、清静而安的内在本性。依王畿的看法,以致良知证悟圣学,是心息相依、合一的修养过程,既能涵养道德本性,又可养身卫生,这也就是“彻上彻下之道”,为“性命合一”之学。
从一念良知范围三教出发,王畿论学,大都标举禅理。他在解答陈献章之学与师门之学同异时,指出师门入悟的“三种教法”,即“从知解而得”、“从静中而得”、“从人事练习而得”,分别称其为“解悟”、“证悟”和“彻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认为君子之学,贵于得“悟”,悟门不开,无以证学。王畿进而倡导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主张“无念”就是“一念”。他说:
圣狂之分无他,只在一念克与罔之间而已。一念以定,便是缉熙之学。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注:《王龙溪先生全集·趋庭漫语付应斌儿》。)“一念”就是禅宗中所说的“无念”,即不着一念。假若人们持定于一念良知,那么这就是心体光明的圣人之学。因为,在王畿看来,良知一点灵明,“便是作圣之机”,人们只要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使其日日不致桎梏亡灭,便是“致知”。(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还与“良知当下现成”说相联系,以“当下”、“见在”来规定“一念”的内涵,强调当下一念、见在一念。他在《念堂说》中具体阐发了对“一念”范畴的理解:
念有二义。今心为念,是为见在心,所谓正念也。二心为念,是为将迎心,所谓邪念也。正与邪,本体之明,未尝不知,所谓良知也。心为见在之心,则念为见在之念;知为见在之知,而物为见在之物。见在则无将迎而一矣。(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认为“念”有“正念”与“邪念”二义:所谓“正念”,就是强调人们对外物所作的本能的当下的意识反应,即见在一心的念头,又可称其为“一念”或“初念”;所谓“邪念”,则是指人们起了“将迎心”,以二心为念,违背了当下见在的“一念”之心,又称为“转念”。王畿认为判别“正念”与“邪念”的标准是心体“良知”,见在一念的“正念”,以“无将迎、无住著”(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为主要特征,而“邪念”则正好相反,以有将迎、有住著为主要特征。这里,王畿对“念”之正邪的区别和界定,所着重的不是从道德意义的层面,而是以人心是否“将迎”、“住著”来划分,当下见在的“一念”既无将迎又无住著,正是“良知”本体所具有的“无善无恶”的意识状态的体现,与他在“四无”说中所主张的“无意之意则应圆”相一致。因此,王畿又特别强调人们在为学中对“一念之几”范畴的认识和把握,以凸现“良知”即体即用、当下现成在格物致知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当下保此一念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谓之格物;不欺此一念灵明,谓之诚意;一念廓然,无有一毫固必之私,谓之正心。此是易简直截根源。(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
千古学术,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违,不违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独)(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一念之几”,王畿有时又称为“一念之微”、“一念灵明”或“一念真几”。王畿吸取和发挥先师王阳明将“感应之几”视为“良知”的观点,从体用合一的角度来阐发良知说,认为“无善无恶”是良知本体,“一念之几”或“一念之微”则是重在良知之用,是指良知即体即用、即隐即微之本体的自然发见、自然明觉。他给“几”下定义说:“良知者,自然之觉,微而显,隐而见,所谓几也。”(注:《王龙溪先生全集·致知义辨》。)依照王畿的看法,良知本体是常寂的,良知既是主宰又是流行,“其机不出于一念之微”,(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而“一念之微”就意识的产生而言,并不是讲“已起”思虑,而是“未起”思虑,即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无念”,而是指主体当下见在的一念,处于“无起无不起”(注:《王龙溪先生全集·万履庵漫语》。)的意识状态。王畿十分强调“一念之几”或“一念之微”的重要性,认为千古圣学与学术皆只在一念之微、一念灵明中识取和求证,因此涵养、保有此当下见在的一念,也就是为学之道、格致之功。他倡导人们涵养和坚持一心正念,克除二心邪念,即不能产生“有一毫纳交要誉恶声之心”的转念;只要人们按照正念去思虑、去践履,就能使“一切运谋设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尝有所起”,(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达到万虑一致而本心自然的境域。
如果我们将王畿对“一念之几”或“一念之微”的看法与前面所论“四无”说相观照,那么就可以看到其二者之间的联系:从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说,凸现“一念之几”,无疑是从工夫论角度对“四无”说的具体的展开,其旨在强调良知本体之用,即当下现成性。王畿指出:
若信得良知及时,不论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顺在逆,只从一念灵明,自作主宰。自去自来,不从境上生心,时时彻头彻尾,便是无包裹;从一念生生不息,直达流行,常见天则,便是真为性命;从一念真机绵密凝翕,不以习染情识参次搀和其间,便是混沌立根。(注:《王龙溪先生全集·答周居安》。)这里,彼此、好病、顺逆等都表现为外在的客体之“境”,而“良知”作为自我主体在与客体之“境”的关系中,并不表现为消极地被动地受客体环境的影响,而是居于主宰的地位;因为自我主体是以“一念灵明”为内在根据,一念灵明自作主宰,表明主体能够对外在的客体之“境”的行为自觉地加以省察、判断和抉择,从而避免消极地随“境”而转化,张扬主体的自觉精神。王畿认为,就认识的工夫论而言,一念灵明自作主宰,来去自由,既“不从境上生心”转念,也没有“习染情识”搀杂,为学涵养之道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仍然是以“无念”为宗,从混沌立根,即“从无处立根基”。既然“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那么致知的工夫,也只能觉悟良知。也就是“一念自反,当下便有归着,尤为简易”。(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基于此,王畿对“格物”提出了自己的新解。他说:
格物是致知下手实地。格是天则,良知所本有,犹所谓天然格式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论学书》。)
良知是天然之则,物是伦物所感应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则;有视听之物,斯有聪明之则。感应迹上循其天则之自然,而后物得其理,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理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为物。意到动处,意流于欲,故须在应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欲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王畿把“格物”之“格”径直训释为天则、天然格式,即良知自我主体所固有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而把“物”训解为“事”或“伦物”,即使主体中固有的良知得以呈现的外在事物,主要是指父子、君臣等人伦关系。在王畿看来,良知是作为道德准则的主体,物或伦物是良知意识活动的认识对象,所谓“格物”,从工夫论上说,就是人之主体遵从良知法则以顺应外物感应的过程,只不过就当下见在性而言,格物的工夫过程本身即是获悟良知本体。从此意义上讲,王畿虽然也承认“格物”是“致知”的实地下手处,实际上是将“格物”与“致知”相等同,指人之主体必须自然地遵从和顺应良知法则去体悟、去践履;只有这样,表现为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关系的“伦物”才能各得其理,获得道德意义的规范和秩序,即“物得其理”而谓“格物”。王畿进而从人生在世易受物欲浸染的现实角度,强调格物还须在事物应迹上进行寡欲的着实工夫,使人心欲念寡至极处,达到“无”的意识状态。这里,如果将王畿对“格物”的阐释与王阳明的格物说相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师生在学术旨趣和方法上的异同:一方面,王畿承接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所阐述的“格物致知”的思想,将致知的“知”解释为良知,训“格”为“天则”、“物”为“伦物”,把格物的过程视为规范人伦关系的过程,从认识和道德修养合一的角度,凸现主体格物的条理性和道德意义,力图将格物归结为一种纯粹的道德践履,此是其相同之处;另一方面,王畿强调主体格物的工夫过程本身就是良知本体的当下呈现,不仅是对朱熹格物论中知性成分的摆脱,而且是对王阳明“正事”、“正心”观点的深化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消解了主体格物的工夫过程,特别是王畿主张有父子关系才有慈孝之则,有视听功能才有聪明之则,显然在名实关系上是对王阳明“不成去君上上求个忠孝的理”的观点的突破,此是其相异之处。而这相异之处则恰恰体现王畿格物说的理论创见和特色。与“格物”说相关系,在知行关系上,王畿继承和发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知行皆有本体和工夫,不可分割,必须从“一念”良知上加以取证。他辨析说:
天下只有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有本体有工夫。……本体原是合一,先师因后儒分为两事,不得已说个合一。知非见解之谓,行非履蹈之谓,只从一念上取证,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即是知。知行两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为立说以强人之信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所谓“知”,并不是指通常所说的“见解”,而是指良知;“行”,也并不是“履蹈”的意思,指依照良知的准则去实行。因此,知行都只有从一念良知上去切实地取证,做到知能“真切笃实”,行能“明觉精察”,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依王畿看法,在就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而言,可分为在事为上、在意念上、在心上用功的三种方法,但只有从心上用功“防于未然,惩心忿,窒心欲,方是本原易简功夫”,如果仅“在意与事上遏制,虽极力扫除,终无廓清之期”。(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语录》。)
可见,王畿公开主张良知范围儒、释、道三教,将儒学的宗旨也归结为虚寂或虚无,并对王学中的诸如“良知”、“一念之几”、“格物”等概念范畴,每每赋予新意,多有发明,且发展至极处,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世俗知见的否定,从而表明其心学思想所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因王畿独标一帜的创新,使其影响甚巨,在王学中极富号召力,促进王学的深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因他突破了王学营垒固有的藩篱,不仅招致同门的不满和反对,而且在客观上也引发了王学内部的分化,以至崩溃瓦解。因此,王畿作为一代心学宗师,后人对其学说既有“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注:《明儒学案·师说·王龙溪畿》。)近于禅、老的批评,又有其“多有发明”成就的肯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