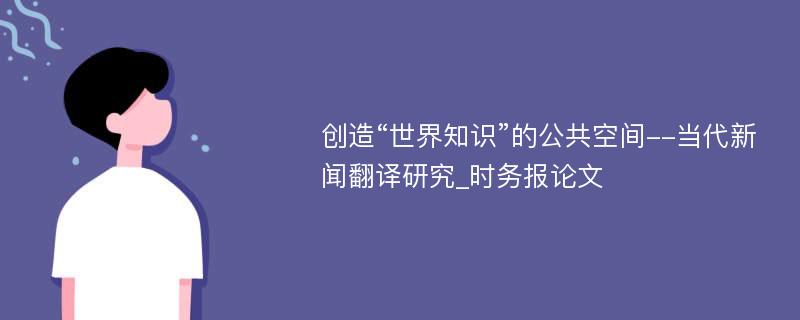
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稿论文,时务论文,知识论文,世界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5-0001-18
一 前言
曾是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之一的高凤谦(梦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还只是蛰伏于福州一隅,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士人。由于兄长高而谦的好意,帮他订了一份《时务报》,①就此成为它的爱读者。高凤谦自称曾经“涉猎译书,又从出洋局学生游”,因此对“泰西建官、设学、理财、明刑、训农、制兵、通商、劝工诸大政”,都有所略闻。②所以当他读到了《时务报》之后,对它蕴载的丰富内容深有所感,却同时也对它可能招致言祸,颇表担忧。好比说,《时务报》所刊载的“《民权》一篇,及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倡民主各事,用意至为深远”,可是,“风气初开,民智未出,且中国以愚黔首为常,一旦骤闻此事,或生忌惮之心,而守旧之徒更得所借口,以惑上听。大之将强遏民权,束缚驰骤,而不敢少纵,小之亦足为报馆之累”。所以他写信给《时务报》的“总理”汪康年,③劝说道:“此等之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④
《时务报》上让高凤谦觉得“用意至为深远”却又忧虑可能会以言贾祸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它的工作团队各献己力的心血成果。所谓“《民权》一篇”,指的是汪康年自己动笔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⑤是篇当时即引起不少回响的名文;⑥至于所谓“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倡民主各事”的文章,则都是列名为《时务报》“东文翻译”的日本人古城贞吉提供的译稿,⑦为什么会让高凤谦觉得“守旧之徒更得所借口,以惑上听”,倒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这个例子看来,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⑧即使早已是学界注意的研究对象,⑨成果丰硕;只是,见诸《时务报》的文字,除了诸如汪康年与梁启超等名家作手的堂皇议论文章之外,它的篇章里蕴藏的讯息材料(例如,古城贞吉提供的这两篇译稿),则显然还别有天地,值得史学工作者细细琢磨。本文即拟以《时务报》发刊的各式各样的译稿为对象,初步分析这些译稿提供的讯息,⑩并尝试述说在晚清中国开创关于“世界知识”(11)的公共空间(12)的过程里,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所能扮演的独特角色。
二、媒介、翻译与追寻“世界知识”的可能性
1898年3月21日的夜里,一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伏案工作,修改儿子皮嘉佑的作品《醒世歌》,(13)盖在此刻,仍然有不少中国人犹且欠缺一般的地理常识,(14)何遑论及认识世界局势?皮嘉佑的《醒世歌》,刊诸《湘报》,如是声言道:
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15)
皮氏父子的努力,明白反映出维新之士企图透过《湘报》这份媒体,并以通俗歌词灌输地理常识与世界局势之认识的用心。(16)可是,《醒世歌》刊出后,正如皮锡瑞自料“人必诟病”的预期,旋即遭受反弹,(17)日后被贴上“保守派”卷标的士人如叶德辉,即对《醒世歌》的观点进行严厉的驳斥,倡言“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不以《醒世歌》“中国并不在中央”的观点为然。(18)可是,皮锡瑞与叶德辉的“对决”,并不是见诸现代意义的媒介,而是透过私人书函往返或是面谈或是辑为书籍的传统样态,公之于世。这样看来,现代意义的媒介在这个时分的中国作为介绍新知识/新观点的例行化工具,即使已然激起涟漪无限矣,不同观念思想之间交锋的物质样态,还是新旧杂陈。
然而,皮锡瑞对于《醒世歌》见诸《湘报》“人必诟病”的自知,与叶德辉旋即起而驳之的反弹行动,显示了现代意义的媒介在士人的读写世界里,已有一席之地(故《醒世歌》见诸《湘报》后,即为叶德辉读之,乃发驳论)。盖自中西海通交流以来,中国士人对西方现代世界的诸般样态闻见愈多,知晓愈广,像报纸这样的现代媒介的意义与作用,迅即广泛地成为他们倡议大清帝国开展改革事业的参照要素。如改革派士人先驱之一的郑观应将“日报”看成是“泰西民政之枢纽”,并举证历历地论说西方各国“报馆”数目之众,作用之大,“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效果:“是非众着,隐暗胥彰。”(19)康有为亦将报馆看成是足供“见闻日辟,可通时务”的工具,所以应该奖励民间设立;(20)他更在可供为“知敌情”之资的脉络下告诉清德宗:英国的“《太唔士》”与美国的“《滴森》”是西方“著名佳报”里“最著而有用者”,应该命令总理衙门“译其政艺”,不但成为皇帝取读之资,“可周知四海”,也该“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寮咸通悉敌情”。(21)至于生平还莫知其详的王觉任倡言“开储材馆”,将“各国新报”列为应该翻译的材料之一,使进入“储材馆”的精英能够“以广学识”。(22)这些意见,展现了这样的态势:有意识地翻译西方的信息材料,作为汲引来自异域的知识/观念/思想(乃至于“敌情”)的手段,并使之透过像报纸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介形式广泛流布,俨然已蔚为社会共识。(23)
这样的社会共识,并即得到了付诸实践的尝试。康有为等于1895年8月17日创设《万国公报》于北京,(24)就是维新派士人迈出的第一步;随后,北京强学会设立(1895年11月中旬),(25)又于1895年12月16日开始刊行《中外纪闻》,便把翻译来自于西方的新闻信息当成是这份刊物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外纪闻》的《凡例》即曰:
本局新印《中外纪闻》,册首恭录阁钞,次全录英国路透电报,次选译外国各报,如《泰晤士报》、《水陆军报》等类,次择各省新报,如《直报》、《沪报》、《申报》、《新闻报》、《汉报》、《循环报》、《华字报》、《维新报》、《岭南报》、《中西报》等类,次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次附论说。(26)
从知晓“英国路透电报”(即今日所谓“路透社Reuters Telegram Company新闻”)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列为选译之首,可以想见,在这群维新士人的认知里,“路透社新闻”占有的“权威”地位。盖路透社确实可以说是大英帝国最关键的信息掮客(the information broker),(27)它在1889年时便开始提供关于“中国与印度的特别服务”,(28)《万国公报》亦尝译载其消息,(29)信之尊之,良有以也。(30)迄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又开始刊行《强学报》,它刊出的第一篇论说《开设报馆议》也将“先开报馆”视为强学会的首要工作,并以“译外国报,叙外国政事地理风俗”列为这份刊物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并认为这样可以达成“士夫可通中外之故,识见日广,人才日练”的“广人才”之效。(31)
《时务报》灵魂人物之一的汪康年,在1894年下半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因为当时上海报刊对于战事的报导“附会神怪,妄诞不经,无一可信”,即萌生了办报的念头,(32)那时他想要办的便是名称为“译报”的报纸。(33)他与各方友朋磋商,并拟订了招股细则,以集众资而行己愿,煞费心力。(34)迄乎汪康年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1896年初合流,携手共进,准备开展《时务报》的共同事业之初,(35)关于它的具体操作形式,众方友朋的意见不一。如邹代钧主张要开办的是一份“专译西政、西事、西论、西电,并录中国谕旨,旬为一编”的报刊,如此“其开风气,良匪浅鲜”;(36)汪大燮则提议:应该要翻译“俄、法之报”的消息,如此“必多异闻”,应可避免只得英文西报“一面之辞”的弊病,且有“兼听易明,情伪可推敲而得”之益。(37)当汪康年等人在1896年6月22日的《申报》上刊登即将“新开时务报馆”的广告,把创办的讯息将公之于世的时候,则宣称道:
今风会方开,人思发愤。宜广译录,以资采择。本馆拟专发明政学要理,及翻各国报章,卷末并附新书。坐落上海石路南怀仁里。择日开张,先此布闻。(38)
《时务报》的实践,也证明了自己确实做到了“宜广译录”的自我宣称。(39)
这样看来,不论是在意识上或是行动上,中国士人都肯认了翻译西方信息材料的必要性,并在自身创办的现代传播媒介上努力做去。当《时务报》第一册出版首度与大众见面时,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便是梁启超的论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不无激情地对心目中的理想报馆应该涵括那些内容,有这样的自问自答:
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径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法律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40)
在梁启超的期许里,报刊媒体承负的任务既繁且众,读者将进入的是一个可以无所不知的天地:既拥抱“五洲”“全地”的世界,又可知悉“各省新政”、“新法”的利益,也得以知晓“国体不立,受人嫚辱”的国族之耻,打造国族认同,还可以进入“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以外“实学”知识的殿堂。归结言之,像《时务报》这样的媒体,被其主导者期许着能够扮演好这个供应“世界知识”的载体的角色。
三 媒介、信息与“世界知识”的制造
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传播学大师的Walter Lippmann讲过这样的故事:1914年,某大洋不通电讯的岛上,住着几位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邮轮大约60天来一次。那年9月,邮轮还没来的时候,这群人的共同话题是Madame Cailaux枪杀Gaston Calmette案的审判结果。到了9月中旬,邮轮终于来了,他们涌向码头,想从船长那儿知道这件案子的结果。没想到,他们知道的却是过去6个星期以来,英国、法国正在和德国开战。在这6个星期里,这群人就像朋友一样相处,实际上他们却已经成了敌人。Walter Lippmann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提醒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认识是多么的迂回曲折(indirectly)。(41)确实,媒体享有支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无限权力,已然成为媒体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42)《时务报》作为供应“世界知识”的载体,刊布其间的1706篇译稿、(43)58篇“路透电音”,(44)究竟提供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的面世,又是为了什么目的,依据什么样的来源,被谁制造出来的?生产制造这些信息的流程速度如何?透过对于《时务报》这些翻译文稿的析论,或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1.《时务报》翻译文稿的分类
从梁启超的期许来说,理想的报刊应当承负起“广译五洲近事”的职责,好让读者可以知晓“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然而,媒体提供的讯息不可能无所不包,媒体构成的关系网络更是极其复杂。简单的新闻传播模式是:世界上发生了新闻,报纸(媒体)报导之,大众消费之。然而,这个模式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更为复杂的。所谓有新闻,其实是透过如政府、警方、股市,乃至于通讯社(the wire services)等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来源收集提供的。报纸的报导可见诸世众,同样是不同的从业员工作的结果。得有记者、编辑、印刷工人乃至于报童的“通力合作”(律师、会计师与市场行销专家,也许一样会插上一手)。消费新闻的大众,则会由于性别、年龄层、种族、阶级、收入、宗教信仰等等因素而显现出零碎分散的样态。好比说,《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关系作用之一就是以波士顿为根据地的美国职业棒球队:红袜队(the Red Sox)藉以维系它与球迷之间的关系(其它面向,则不多言)。从这个意义而言,报纸(媒体)就是物质性关系(material relationships)的联合。除此之外,报纸还展现了另一种可称之为再现关系(represented relationships)的关系网络。何谓再现关系?往往即是报纸本身设定自己所要扮演的媒介角色。通常像是“报纸是人民的耳目”、“报纸是自由(liberty)的守护神”之类的“真理”,是这种再现关系的理想表现形式,让报纸(媒介)可以说自己和公民的关系就是它是公民的斗士,可以说自己和大众或私人机构的关系就是它乃是它们的看门狗。这样的再现关系,自然有助于物质性关系的运作。(45)
由是观之,《时务报》提供的译稿讯息,绝对不可能涵括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的新闻消息,它们应该都是经过《时务报》的编者/译者进行“筛选”工作的结果,它们反映的其实既是《时务报》的编者/译者的关怀所在,也会受到讯息取材来源的制约。就前者言之,关于中国的讯息,仍是《时务报》译稿之最大宗,其它在19世纪90年代中末期正向中国展开疯狂侵略行动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消息,则为其次。其详如表一:
表一 《时务报》译稿关于国家(地区)分类总表
国家(地区) 篇数比例 国家(地区) 篇数比例
中国
450
33.7%
夏威夷
3
0.2%
台湾231.7%荷兰2
0.1%
俄国
165
12.4%南非2
0.1%
英国
143
10.7%波兰2
0.1%
日本
139
10.4% 特兰斯仆耳国【特兰斯法耳】2
0.1%
美国896.7%
墨西哥
1
0.1%
德国624.6%
葡萄牙
1
0.1%
韩国463.4% 义火可握国 1
0.1%
法国443.3%瑞士1
0.1%
暹罗241.8%
乌拉圭
1
0.1%
土耳其 171.3%挪威1
0.1%
西班牙 161.2%埃及1
0.1%
印度110.8%波斯1
0.1%
意大利
90.7%
巴拿马
1
0.1%
奥匈帝国 80.6%巴西1
0.1%
古巴 70.5%丹麦1
0.1%
加拿大
70.5%欧洲
23
1.7%
瑞典 50.4%非洲2
0.1%
越南 50.4%美洲1
0.1%
希腊 50.4%澳洲2
0.1%
比利时
50.4%
菲律宾
40.3%
国家(地区)总篇数 1334
以中国为主题的篇数既众,可以想见,《时务报》提供的是以外国报刊为“眼睛”所看到的大清帝国,可以将这些以中国为主题的译稿再分类,如表二:
表二 《时务报》译稿以中国为主题者分类表
类别篇数 比例
帝国主义在中国215 47.4%
总论(变法维新主张)
19
4.2%
内政
18
4.0%
边疆事务6
1.3%
经济/财政/商务
87 19.2%
海关
14
3.1%
交通(铁路.火车/电线)19
4.2%
邮政3
0.7%
外交(含使节人物) 26
5.7%
军事
38
8.4%
社会(人口/烟毒/缠足)4
0.9%
华侨3
0.7%
教育2
0.4%
总篇数454
从它的选择题材来看,《时务报》即使借着异域之眼反观自身,亦屡屡表达它自己独特的观照。像是《时务报》上颇不乏翻译外国关于中国内部动乱的报导,(46)然而,对于曾被视为“匪酋”的孙中山,当外国媒体报导他在伦敦遭受“劫难”的事迹之际,《时务报》给予更多更广泛的关注,刊登了许多关于孙中山这场遭遇的译稿。盖《时务报》主事者梁启超等,和孙中山早有往还也,(47)如此的关注,显然实非将孙中山与一般“匪乱”视之。(48)《时务报》也借着外来的译稿为正在炽热非常的变法维新运动张目,如从《伦敦东方报》译出《中国不能维新论》,指陈变法维新的可能路向:
中国欲求维新之道,必自裁撤都察院及翰林馆始。既撤,然后削总督之权,或径除总督名目,仅设巡抚已可矣……若不维新,则凡遇不论如何凌辱之者,亦惟有耐受而已。
文末并有附语谓:
以上二篇皆英报之说,因照译之,以见外人窥察我国之意。至其说之是否,阅者自能辨之,无待赘言。(49)
又如,译自上海《字林西报》的文稿,既声言道“中国宜亟开民智”,并提出具体方案曰:“应广布浅近有用之学,如各国政治形势之类,于考试时以之策士;而由国家编辑各种初学读本,散布民间。”(50)等于是为当时甚嚣尘上的“开民智”运动,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入手方案。
从表二更可得见,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各项相关举措,实为《时务报》刊布译稿再三致意的课题,几占篇数一半之强。兹就“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主题的译文再详为分类,如表三:
表三 《时务报》译稿以“帝国主义在中国”为主题者分类表
子类别 子类别篇数比例
“租界”事务188.4%
各通商口岸情况 198.8%
经济/关税等经济事务交涉104.7%
借款/外债 104.7%
英国33
15.3%
俄罗斯 32
14.9%
日本167.4%
法国136.0%
德国 31.4%
“胶州湾事件” 198.8%
“教案” 94.2%
其它 10.5%
总篇数 215
从表三可以得见,就当时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各项相关举措而言,势正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与向来窥伺中国不已的俄国,实为《时务报》刊布译稿最为重视的对象;德国的篇数虽少,但若联合以她为挑动者的“胶州湾事件”而论,则又超越日、法两国的篇数,也显示了《时务报》作为定期提供信息的媒体对现实事务的灵敏度。从这些的译文里,《时务报》的读者所可感受到帝国主义的野心跃然纸上,“瓜分”危机好似迫在眉睫。例如,《时务报》从日本的《东京日日报》里译出了一则述说“俄国将吞噬亚洲”的文稿,述说“《泰晤士报》驻俄京访事人来函”指陈俄国的《士尾也报》有这样的论议:
不独中国为俄所有,彼波斯也,皮路斯坦也,印度也,亦必速为俄国所有也。是盖天意所属付者矣。
《时务报》特别加附按语曰:
是说岂吾中国所忍闻。然实今日所应虑及,故特译之。(51)
清楚展现了翻译这等文稿的用心,在于提醒读者应该注意俄国的扩张。又如,从日本《国民新报》翻译过来的《德国海军及殖民政策》便述说德国对中国与土耳其“垂涎”久矣:
六都维都男爵常云:德国须得殖民地于中国及土耳其,斯足以强国而富民也。何以独注意于此二国哉?盖诸雄相向,二国瓜分之日已不在远也。《虞连斯伯度报》者,德国殖民党所赖以发其议论者也,尝着论云须割斯密儿那地方于土耳其以属德国,然恐为俄、法所阻碍也。德国垂涎于中国,盖非一朝夕之故,往岁(即言千八百九十五年也)其干涉日本之事亦为此也。麦是亚儿男爵尝论于议院云:中国瓦解之日近矣,我德国不可不先干预以成其志,则唯在备大海军以力待之耳。德人频用权谋术数,欲以夺舟山岛为得属地于中国之起点,其意盖欲效英人经营印度之谋也。……(52)
这是“胶州湾事件”发生(1897年11月)之前刊出的译稿,表明了《时务报》提供的信息意向所指,具有防患于未来的作用。《时务报》又大量地刊出19篇与“胶州湾事件”相关的译稿,其中甚至包括胶州湾形势地图,(53)以及某位“现驻日本”的中国人的愤慨反应,把国遭此辱之源所在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只知道“私妻子,保富贵,暖衣饱食”的“吾国家在位有司”。(54)这样,《时务报》提供的不仅仅是“胶州湾事件”发生的讯息而已,更可能激起读者进一步的联想与思考。(55)当时关于中国情势的各式各样报导,五花八门,如翻译了取材自《香港每日报》的信息:
目前东方情形:其北界将为俄国所有;德既据有胶州,是山东已归掌握;法之所占,必在福建。中国当另立新国,建都南京,以英为保助之国。然英亦必占据云南、湖南、四川三省要隘云。(56)
国族濒临惨遭瓜分豆剖之命运的讯息,在《时务报》的篇章里屡见不鲜。Benedict Anderson指陈出版在创造“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报纸的被消费,正是那个想象的世界根植于日常生活里的绝佳例证。(57)对抟成中国国族的“想象共同体”而言,《时务报》译稿刊布的消息,应亦可视为其动力来源之一。
《时务报》译稿里关于世界主要国家讯息相关者亦众,论及各国情势的方方面面更是多元繁富。大致而言,各国“经济财政商务农业展博物会”的项类(即与财经领域事务的讯息),都占有最高的比例:
国家
比例
备注
日本 38.1%
美国 25.8%
法国 22.7% 与“科学”项类并居首位
英国 17.5% 与“国际关系”项类并居首位
俄国方面,以“帝国主义”项类居首位(18.2%),“经济财政商务农业展博物会”项类则居次位(15.2%),显示《时务报》译稿选材对于俄国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注意力;德国方面,却以“国际关系”项类居首位(19.4%),“军事新武器”与“政治”项类则居次位(17.7%),“经济财政商务农业展博物会”项类反居三位(12.9%)。不过,就德国的“国际关系”项类内容而言,12篇里有1/3的分量是关于德国前首相俾思麦“泄露机密”(即其述说德俄订定同盟之故事)的新闻,(58)“政治”项类11篇里有6篇是关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讯息,(59)焦点过于集中。
然而,受限于技术,报纸的新闻未必是“新”闻。在电报发明以前,能以新闻故事(news stories)的方式所描述的新闻事件,都是最近发生在身旁的,事件发生的地点越远,它被报导的时间就越迟。所以,远方新闻往往以“地理包扎”(geographical bundling)的形式面世。例如,欧洲捎来的新闻材料,完全由船打包送来,而且就以它们在包裹打开后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来自伦敦的船到了,所以就有它带来的新闻啦。”(60)从《时务报》关于“胶州湾事件”的译稿,即可一窥它讯息接收与传递的速度。当德军于1897年11月15日进占胶州城,16日德使海靖向总理衙门就相关事宜提出各种要求。(61)在上海的《时务报》方面虽然在10天之内即知此事,(62)稍后于11月24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6册,则以消息不通,未载此事,(63)在12月4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7册里,迅即从外来资料里报导此事。(64)显见即使新闻消息传递速度受到技术层面的制约,《时务报》仍尽速将这件事公之于众。就西方国家的情势而言,新闻的传递速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大英帝国为例,19世纪50年代从不列颠本岛到澳洲的新闻传播要三个月之久,即使后来到了60年代使用蒸汽轮船了,两地之间仍需45天。(65)1850年,英、法之间首先搭起了海底电缆,由此开创了让新闻在世界快速传播的可能性,此后十年更建立了海底电缆的环球体系。就大英帝国而言,这项工程大大改变了帝国的核心与边陲之间的空间关系(the spatial relationship),各式各样的信息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里散播开来,让人们可以想象自己就是某个国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员,维系了帝国认同。实时的新闻,让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长于帝国领地(the Dominions)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同各种帝国事务与政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66)以日本而言,电信事业作为“社会基盘”(infrastructure),既提供了经济活动里迅速传达情报的效果,(67)也让日本新闻媒体可以广为利用,(68)甚至在1877年“西南战争”的新闻报导战里,电信更是大起作用。(69)从《时务报》译稿接收与散布速度来说,它能在半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向中国公众传播“胶州湾事件”的讯息,也可能带给中国士人许多震撼,(70)让士人申论中国处境之危急,便引征“胶州湾事件”为立论之一。(71)各种传播媒体可以让它的阅听人享有一种“现在感”(a sense of the present),正因为它们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而非历史)快速地传达给阅听人,让他们就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感受到它(它们),也认为自己参与了事件,或是可以立即讨论它(它们)。(72)《时务报》的读者,也应可享有如是的感受。
2.《时务报》翻译文稿的知识作用
在“西潮东渐”的背景下,晚清士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嬗变的空间,域外地理知识与现代地理学的导入,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逐渐扩大,便是其中的成果之一。(73)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架构里,中国处于所谓“世界秩序”的核心地位。这样的观点,不过是个被建构出来的“神话”。(74)在中国被迫和西方国家开始密切互动的19世纪,支配人心的则是这样的观念和过往与“蛮狄”交往的“历史经验”。随着中国士人逐渐了解世界局势,逐渐知道中国也只是世界诸多国家之一,并不特居优越地位。中国固然物盛地广,“蛮夷之邦”却同样也是花花世界(甚至繁庶广博,犹而过己)世界局势变动如奕棋,《时务报》的译稿提供了大量的列国彼此交涉的讯息。例如,述说英、德之间往来交涉,彼此合纵连横的错综复杂情势;(75)大量报导关于“美西战争”的情况(76)(甚至附有“战场图”(77)),可能开启了让读者了解世界列国彼此交涉样态的信息/知识空间。《时务报》翻译这些文稿,有自身的特殊用意,如在英国《太母士报》译出的关于英国下议院议论如何因应土耳其内部动乱的稿子里,《时务报》即特别添加按语曰:
土耳其之乱,各国恐震动全局,不敢干与其乱,遂无已时。各国为之牵制,此固欧洲之患,未始非东方维新图治之候也,因详译之。(78)
俨然提醒读者注意世界局势的变动,可能引发的骨牌效应。
《时务报》的译稿,也可能扩充了读者对于世界地理的认知。像是译稿里涉及与过去的地理认知不同的词汇,便屡屡提醒读者要改变自己的既存观念。例如从《东京日日报》译出的述论“东洋大局”的稿子里,有如是的按语:
文中谓东洋,非特指日本,东方亚细亚洲一带皆是。中人特称日本曰东洋,而不知已亦国于东洋也。(79)
后来一篇取材自《东邦学会录》述说俄国外交政策历史的译稿里,在言及“东洋”的段落,也附加按语,说所谓“东洋”的意义是:
指东方亚洲而言,非指日本也。中国在亚洲,是亦居东洋之中也。人每误以日本为东洋,故附辨焉。(80)
人们表达对于外在世界之认知的词汇,是如何形成的,本即是历史与现实纠缠绕结的课题。好比说,“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乃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学者创造出来的名词,同时用来指称美洲这方土地上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的人们。就在此际,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统治下的法兰西帝国正企图在这里开创一个新帝国,所以,“拉丁”这个概念的实质,乃是要把法兰西与这些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国家拉在一起,让这等企图显得是如此顺理成章,自然之至。正如布贺岱(Fernand Braudel)之所谓:“‘拉丁美洲’是法国约在1865年首先使用的,大部分是由于她自己的理由,而后,竟为整个欧洲所接受了。”(81)中国人从将日本称为“东洋”,转变到认识“东洋”乃“指东方亚洲而言”,而且中国亦位于“东洋”之中,这样的认知变迁,显示了中国人对于地理/空间的概念变化的轨迹;《时务报》在这道轨迹上刻画了一道镂痕。
《时务报》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转换地理/空间概念的可能空间,也让中国人对调整时间坐标的认知,提供参照系统。它告诉读者,当阅读讯息的此际,不只是中国本身的纪年而已,还更有一个“普世”的标准。在一篇述说英国驻北京公使向本国禀报中国通商各口岸“商务情形”的译稿里,标题采用的是大清帝国纪元(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却明白告诉读者:光绪二十一年即是“一千八百九十五年”;(82)另一篇述说土耳其情势的译稿里也指出“西人以百年为一世纪”,(83)在介绍“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关于中国财政意见的译稿里,则更明白以按语指陈:“西人以百年为一世纪,现世纪即公历千八百年也。”(84)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在某些方面,其实可能是个单一的世界(a single World),拥有共同单位的经验框架(a unitary framework of experience),好比说,基本的时空坐标(basic axes of time and space),即为一例。这可以说是“现代性”(modernity)的特征之一,媒体在形塑/创造现代性的这个面向上,即有着重要的贡献。(85)《时务报》透过译稿(并添加附语)来促使中国人转换地理/空间的概念,调整时间坐标的认识系统,实亦可视为中国被编织进入“现代性”样态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面向。
媒介提供的信息,制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凭借。中国士人屡屡信笔立言,痛陈中国人好似“地理文盲”(geographical illiteracy)(86)一般,必然得遭受失地亡土的国族之耻:
若夫度数地图之事,虽极浅近者,未尝稍问津焉。然以帖括之故,得掇高科,而跻权要,则有以词馆之英,而问四川之近海与不近海,日本之在东在西者;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门在星架坡之外者;若亲藩极贵,问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则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可谓从古割地未有之事,而中朝若不知之,其它割黑顶子帕米尔于俄,分缅甸土司于法,刳野人山于英,皆茫然于其名,况于抚有其地哉?……(87)
那么,像《时务报》这样的媒介快速制造/提供的“世界知识”,俨然可以成为打造中国人对于“中国”乃是一个“地理体”(geo-body)的信息泉源。(88)
四 “世界知识”的确证与转向
光绪廿二年七月廿四日(1896年9月1日),一直关心《时务报》的邹代钧,终于收到了它的第一期。披读之后,深为“狂喜”,大加赞誉,也期待它可以“精益求精”,提出了不少意见。像是翻译文稿的“西报地名”有不少都是他未得知之的,所以建议应列出“中西文地名表”,如此,“阅报之人都知地名所在,其获益良多”。(89)邹代钧是晚清地理学名家,(90)如果连他对《时务报》译稿里言及的地名,都有这样的困扰,遑论其它读者?邹代钧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报馆方面的公开响应:
来书有谓:所译各报地名前人已译有定名者,宜仍勿改;未译定者,宜注明经纬度或附注西文于下者,此最精密之论。惟十日三万字,为期极速,而办事人少,实难逐处查明。且翻译自幼即习西文,故于中国旧译之名多不详悉。若按注西文,则非钞胥之所克任,处处须翻译自写,实觉不胜其劳。……
其苦衷如此,应可得到读者的谅解。《时务报》方面也努力实现这项建议,先在翻译稿里以双行夹注的方式加以解释,如《时务报》第4册的《路透电音》报导“善齐拔”这个国家的“国主”逝世的消息,便注明道“善齐拔”是“阿非利加东南一小国也”;(91)从第13册则开始刊登“中西文合璧表”,(92)以便检索(以后各册并不定期刊出;从第47册起,则将地名、人名以中英对照并列的方式刊出,“以便阅者一目了然,不烦查检”)。(93)对《时务报》的编者来说,关于地名的翻译与确证或许不是件难事,(94)要他们把《时务报》译稿述说的异域大千世界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以一致的词汇表达出来,并让它的读者可以知其义涵,却没那么简单。好比说,《时务报》第3册刊载了一篇它的日文翻译古城贞吉从日本《经济杂志》译过来的稿子,主题是美国共和党为角逐1896年白宫主人宝座而提出的政纲,其中涉及外交方面的主张即是“门绿政治”:
我党现拟遵门绿遗意,伸明其理:若有欧洲诸国侵略在美洲内我友邦,友邦请我干涉时,我国应速诺之,是实我国之权利也。欧西诸国现有版图在美洲内者,我党固不与之生事,然必不许藉端狡焉思启也。……(95)
可是,同一位译者在从《东京日日报》译出,述说英国海外政策的稿子里,谈到英国虎视眈眈于亚美利加之地而为美国抗争的段落,则说美国抗争的理由是“门绿律旨”,且未加任何解释。(96)另一位译者张坤德在《时务报》第31册发出一篇从《温故报》译过来的文稿,主题是“德国有整水师之议”,述说德、英、美国之间的军备竞争,文中说明了美国所采的外交政策大略一直还是依循“孟绿道理”,则有按语解释“孟绿道理”的意义:
按,美前总统孟绿者曾倡言美洲地土概不准外人干预,后人遵守其言,即谓之孟绿道理。(97)
就我们当下的认识言之,不论是“门绿政治”或是“门绿律旨”也好,“孟绿道理”也罢,意涵所指,乃是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于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从整体的脉络来看,当时的媒体上并不缺乏“门罗主义”的讯息与解释。例如,1896年2月出刊的《万国公报》在翻译自“英伦电报”的一则讯息里即有“若论委内瑞拉事,我非以孟绿民主之道为不合也”一句,也便附加按语曰:
美洲本欧国之新疆,华盛顿既立美国后,有民主孟绿定美国及巴西、委纳瑞拉等皆为民主国,不许欧人再至美洲展拓新疆,欧美人目为孟绿之道。(98)
对它们的译者而言,相互之间,并未意识到将这个词汇进行“统一”的需要;对它们的读者来说,要厘清“门绿政治”、“门绿律旨”、“孟绿道理”与“孟绿民主之道”/“孟绿之道”的意义是否相同,恐怕得费上好一番工夫。当时梁启超即提出编辑“名物书”的主张,以为“尽读群书,无不能解者”之助,(99)良有以也。在我们当下的读书活动里,百科全书或是字典/辞典之为用,且统一译名规范的行动与呼吁仍持续不辍,(100)可以想见,在导入西方词汇/思想……的历程里,类似读书/知识实践遭遇的困难和化解之道,实有其历史的连续性。
在现代高度发展的新闻交换体系之下,好似“天涯若比邻”,震惊世人的大事,迅即为我们共知同晓,把国外的事务国内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面向。然而,在这个“国内化”的过程里,却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国内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编码,以自己的观念/语汇来解读/认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国新闻。(101)例如,《时务报》刊出一篇从日本《时事新报》译出的文稿,介绍“俄相儿那巴拿弗”(应即Prince Aleksei B.Lobanov-Rostovskii)(102)之事迹,将他比喻为“其外交权术与拿破仑等”,居然“甘作民贼,毒痛四海,囊括宙合,方遂厥志,殆魏武帝、张献忠、李自成之流亚欤”,然而他能够“安内攘外,掠地取邑”,是“当今之世,罕有伦比”的人,“揆诸申、韩,未遑多让”,可谓“才士”。(103)这篇译稿以拿破仑、魏武帝、张献忠、李自成、申不害和韩非这等新旧杂糅的样式为这位人物做出形象譬喻:魏武帝、张献忠、李自成、申不害和韩非,并不是中国读书人陌生的对象,拿破仑则是19世纪时分方始进入中国的异邦人物。(104)显然,在译者看来,以他为譬喻,读者应可知晓其意也,亦实显示像拿破仑这等来自异域他邦的人物,已然成为晚清历史舞台上的“公众人物”之一的潜流样态。(105)因此,当论者动笔为文劝说中国人应该知国耻而奋起的时候,与拿破仑相关的历史事迹,便可成为具体的例证(而为读者同知共晓),像寿富即以拿破仑如何鼓动了英国和普鲁士以为论说之资。(106)在这样的状态下,可以想见,晚清以降中国士人的读书与知识世界,实已显现出相当的混杂性格(hybridity)。
可是,如果将这些译稿和原刊形态进行对比,则可发现译稿传递的讯息往往会是译者自身创造出来的。从比较宽广的脉络来说,自从晚清以降,又一波的翻译活动浪潮勃兴,各式各样的新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沛然而生。惟则,即如刘禾的论说,在这等“跨语实践”的历程里,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107)《时务报》刊出的译稿,正展现了这等样态。就以这篇述说“俄相儿那巴拿弗”的译稿而言,如取日本《时事新报》原件对比,(108)即可见它非但删减原来的小标题,关于“殆魏武帝、张献忠、李自成之流亚欤”,“揆诸申、韩,未遑多让”等表述,更根本是原稿所未见者。(109)印度学者Tejaswini Niranjana既从历史也从殖民脉络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尝阐述曰,翻译作为一种实践,它如何在殖民主义的操作之下,塑造了并且也得以成形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110)这等“翻译的政治”的思想视野,确实提醒我们应当注意西方的思想霸权,如何透过翻译,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展自我理解,可能产生的权力作用。(111)然而,与其说《时务报》这篇述说“俄相儿那巴拿弗”的译稿是对原稿的“误译”;不如说,这是“俄相儿那巴拿弗”的形象,必须透过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才能被解释阐明。因此,“翻译的政治”的知识权力关系的形塑过程,绝对不会是殖民者单向的施为,看似居于弱势的,得仰仗翻译以汲取新知的(文化思想上的)被殖民者,(在特定的文本里)还是有某种主体性,笔下绝未完全臣服于西方的思想霸权(即便这篇译稿的生产者是日本人古城贞吉)!(112)
从《时务报》的译稿屡屡被当时论者引以为论说之资的情况,也可展现它作为读其书者皆可自由取用的公共空间的面貌。例如,《时务报》载有大量的科学知识等资料(共145篇),其中如引介“曷格司射光”(即X光),(113)即为论者引用,作为讨论中西医术差别的一个方面。(114)《时务报》介绍“海底行船新法”(即潜水艇)的文章,(115)也成为主张讲求制造武器入手而始可立海军的论者所征引的对象。(116)当论者声言应该以日本为榜样来“变通学校”的时候,《时务报》的译稿也可以成为阐释日本学术情况的依据之一。(117)在解释各种与农学相关的知识时,也说出现了各种新耕具尚有新法,《时务报》即已译介了“电犁牛机器”(即耕耘机)一说,“余俱未闻”。(118)奉《时务报》译稿刊布的科学新知为论说依据,正可显示它提供的信息,俨然被视为可堪信任的知识;在政治、社会、外交方面的信息,也有类似的样态。高凤谦认为《时务报》“翻译美总统出身”的文章“用意至为深远”,的确,当时便有论者可能依据这篇得到高凤谦赞誉的文章(119)开展论说,指陈“美国总统起家法律者,十居五六。西人之重法律如此”。(120)当德国拒绝黄遵宪为大清帝国驻德国公使的消息见诸《时务报》的译稿,(121)消息为论者得知,愤愤不平,即引《时务报》的另一篇译稿里对黄遵宪的赞赏,批评德国的举措失当。(122)
从这些样态看来,《时务报》的译稿,在当时的读书界里确实占有某种“权威”的地位,成为值得论者再三参照征引的对象。因此,《时务报》的译稿即为当时的各种论著纂辑成编,好比说层出不穷的各类《经世文编》,(123)便屡屡收录之,不仅显示了这些译稿被视为是可资“经世”的权威知识,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的“思想边界”的扩张样态,表明“经世思想”与时代互动,因应现实需求的“实用”意义。例如,陈忠倚编辑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卷73“洋务五”里有一篇总篇名为《外洋国势卮言》(124)的文章,其实乃是汇集《时务报》的各篇译稿而成的。可是,究其实际,这些文章只具有短期信息的意义,如《俄国添兵论》篇提供的只是1896年“其驻东方之水师”的情况而已,(125)其兵力部署,不可能永恒不变。这样看来,收录这些文章也许正反映了“经世思想”蕴涵的实用主义面向。(126)
同样的,晚清时期汇集世界地理与局势之文献于一编的大书——王锡祺纂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27)也从《时务报》的译稿里取材,既展现了这些译稿的“实用”价值,也反映了编者把这些稿子提供的信息当成永恒不移的知识。好比说,《古巴岛述略》一文言及其人口“计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人”,(128)这个数字,如何可能永不增减?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都是“新闻”变成了“知识”的具体表征。
从论者依据《时务报》的译稿立论成说,也从各类《经世文编》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将之汇编为书的情况来看,张元济说读者对于《时务报》所刊载的“西事均不甚留意”(129)的观察,可能只是一孔之见。《时务报》的读者,从这方可以任意自由取用的公共空间里,找到自己关心的信息,成为开展自身独特思考/悬想/读书/编书的活动历程的起点。这些活动,既是对于《时务报》提供的“世界知识”的确证,也是中国士人转向媒体,以之作为知识探索对象的表征。
五 结论
新闻媒体传播的内容与阅听人的反应,向来错综复杂。可是,一旦“新闻作为公共知识”(news as public knowledge)的样态问世,它便如音响的扩大机一样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扩大作用,引发了公众的注意。(130)《时务报》刊发各式各样的译稿,激起的回响固然不一而足,它提供的“世界知识”,则俨然为大清帝国的变迁前景,在思想层域积蓄了无数的可能潜在动力。
当然,《时务报》提供的讯息,未必产生直接而现实的单线效果。就如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而言,可能过于简易乐观。人们不会只从一个管道得到各式各样的“世界知识”而已。就大英帝国及其领地之间的情况而论,Benedict Anderson的论点可能会忽略了各地区的地方认同与利益也处于持续不断的打造/维系过程,人们阅读的,不见得是在帝国范围内的全国性报刊(也不会只阅读一份而已),许多区域性的报刊其实会鼓动极其复杂的认同面向。例如,身兼报人与加拿大参议员 (Senator)二职的Grattan O' Leary,是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移往加拿大的爱尔兰人后裔,即回忆说在 Quebec成长的青年时分,阅读的多是爱尔兰人的报纸,“从Dublin来的《自由人》(Freeman's Journal),从New York来的《爱尔兰世界》(Irish World),从Minneapolis来的《爱尔兰标准》(Irish Standard)”,所以他说:“我们知晓的不列颠的政局,尤胜于加拿大。”也就是说,他正是从这样特别的视角积累关于不列颠政局的知识。(131)晚清士人知道国族危难/世界变局的渠道,也可能多重复杂(正如前述,孙宝瑄、宋恕与皮锡瑞如何知悉“胶州湾事件”的讯息,目前尚不可得知。参见第11页注⑥。),他们得到的认知也是千样万态。更何况,媒体的报导不见得就是“真相”的再现,也不可能无所不包,《时务报》译稿提供的讯息,应该都是经过《时务报》的编者/译者进行“筛选”的结果;文稿的展现,用字遣词也屡屡不一,更会让读者可能“一头雾水”,莫识其妙,显示出“跨语实践”的困境。(132)
无论如何,就晚清的读书世界而言,像《时务报》这样的媒体刊布的译稿可以快速提供的讯息,非但可以让读者尽速地掌握世局之变,也成为他们理解/认识/阐释世界的依据之一;显然,以传教士为主要工作者的中译西书,不再是他们获得“世界知识”的最主要泉源。正如James W.Carey所谓,报纸与其它媒体扮演的角色是“建构与维系一个井然有序而又意义无穷的文化世界”,在他看来,阅报的最重要的效果,并不是读者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事实信息,而是他或她可以“作为观察者,参与了一个各种力量相互竞逐的世界”。(133)《时务报》作为供应“世界知识”的载体,正容许晚清士人自由进出,共享同润,并开展自身独特的精神/思想活动,读者对于它的响应,更是千样万态。(134)就这个面向而言,在 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为打造中国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源。如果选取与《时务报》同期存在的其它媒体(如《万国公报》、《知新报》等)提供的翻译讯息来相互对比,那么,我们对于晚清时期关于“世界知识”的多重样态,对于当时士人读书世界的构成,对于当时公共空间的表现风貌,应当可以有更形丰富精致的认识。
注释:
①《高而谦函(3)》,《汪康年师友书札》(以下简称《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1579。
②《高凤谦函(1)》,《书札》,2:1608。
③据《时务报》第3册的“本馆告白·本馆办事诸君名氏”,影印本第1册,第199页。
④《高凤谦函(2)》,《书札》,2:1610。
③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廿一日〔1896年10月27日〕,影印本第1册,第556-559页。
⑥赞誉者如吴品珩说:“昨登参用民权一篇,尤为透切,痛下针砭,佩服佩服。”(《书札》,1:341)陈延益则谓:“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澈。”(《书札》,2:1997)批评者如梁鼎芬则说:“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权一万板。”(《书札》,2:1900)
⑦占城贞吉译《美国总统出身》(东文报译/译大阪朝日报西九月十二日),《时务报》第8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十一日[1896年10月17日],影印本第1册,第526-527页;古城贞吉译《欧洲党人倡变民主》(东文报译/译国民报西十月十四日),《时务报》第10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初一日[1896年11月5日],影印本第1册,第677-678页。据沈国威的考证,从1896年夏天到1897年底的大部分时间,古城贞吉都在上海逗留,担任《时务报》“东文翻译”的工作。见沈国威:《关于古城贞吉的〈沪上销夏录〉》,《或问》(大阪: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发行,2004年10月30日),第155-160页。
⑧《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至1898年7月26日出版第69册,宣告停刊。
⑨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专著部分最重要者,主要有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另有两篇硕士论文,张明芳:《清末时务报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68)、孙承希:《戊戌变法时期之〈时务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韩裔学者尹圣柱则将《时务报》视为张之洞个人掌控的官僚体制(the private bureaucracy)的延伸,见Seungjoo Yoon,"Literati-Journalists of the Chinese Progress(Shiwu bao)in Discord,1896-1898",in Rebecca E.Karl & Peter Zarrow edited,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48-76。在一般中国新闻史的专著里,亦必包括对《时务报》的述说,例如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篇。关于《时务报》的两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启超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更是不可胜数,如崔志海:《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廖梅:《〈时务报〉三题》,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226页;廖梅:《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9,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216页。研究其它各方人物与《时务报》之关联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如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黄士芳:《康有为与〈时务报〉》,《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以《时务报》为主体探讨其间蕴涵的思想观念之作,如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⑩关于《时务报》发刊的译稿的分析,闾小波已着先鞭(参见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52-175页),本文则立意将这些译稿“历史化”,还原到它们在晚清时期的知识脉络里来理解它们的意义,尽可能避免以当下的后见之明开展述说:惟本文未可地毯式地述说《时务报》译稿的全面样态,幸识者宥之。
(11)“世界知识”是笔者杜撰的词汇。恰如当代英国文化/媒体研究巨擘霍尔(Stuart Hall)之论说,现代媒体提供的首要文化功能是:供应与选择性地建构“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能认知“诸种世界”、诸般其它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并且,我们也才能把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以想象方式建构成为某种可资理解的“整体的世界”(world-of-the-whole)和某种“曾经存在过的整体性”(lived totality)。参见Stuart Hall,"Culture,the Media and 'ideological effect'",in James Curran,et al.,ed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Beverly Hills,CA:Sage,1979),pp.340-341。笔者师法其意,将关于透过媒体提供的各式各样具有帮助认识/理解外在现实世界之作用的(零散)讯息/(系统)知识,统称为“世界知识”。
(12)关于“公共空间”或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自然取材于J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9)。他亦有比较简要的述说,参见Jrgen Habermas,"Public Sphere:An Encyclopedia Article",in:Critical Thory and Society:A Reader,pp.136-142。从概念史角度言之,Habermas的论述自有其先行者,如Hannah Arendt、Carl Schmitt与Reinhart Koselleck。相关的理论论述脉络,参见J.L.Cohen & A.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2),pp.178-254。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脉络来批判Habermas的亦不乏其人,认为他宣称的“批判的理性公共”(critically reasoning public),不过只是资产阶级霸权(bourgeois hegemony)的伪装,他们控诉Habermas忽略了伴随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之兴起而出现的真正平等的公共领域(the truly egalitarian public sphere),参见Peter Uwe Hohendahl,“Critical Theory,Public Sphere and Culture.Jrgen Habermas and his Critics,” New German Critique,16(Winter 1979):89-118,亦可參見T.Mills Norton,"The Public Sphere:A Workshop," New Political Science,11(Spring 1983):75-78。女权主义史家则也将注意力放在1789年之后妇女如何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境,进而声言,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其实只是营构了性别关系的新秩序而已(个中名著,参见Joan B.Landes,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1988)。至于检讨反思Jrgen Habermas的理论与具体历史研究操作的文献亦众,如Benjamin Nathans,"Habermas' s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6,No.3(Spring 1990):620-644; Dale K.Van Kley,"In Search of Eighteenth-Century Parisian Public Opin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9,No.1(Spring 1995):215-216;Jon Cowans,"Habermas and French History: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French History,Vol.13(June 1999):134-160(不详举例)。结合理论脉络和具体历史研究之思考,并涵括Jrgen Habermas本人回应的文献,见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2)。至于Nick Crossley与John Michael Roberts合编的文集,则扬言要超越Habermas的理论架构,另开思路,寻觅另类选项(alternatives),见Nick Crossley and edited,After Haberma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ublic Spher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The Sociological Review,2004)。在中国史研究脉络言之,导入“公共空间”及“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亦多,不拟详论,参看孔复礼(Philip Kuhn)著,李孝悌、沈松侨译《公民社会及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3月,第77-84页;陈永明:《“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北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11月,第90-97页。惟则,近来以具体的报刊研究进行讨论者亦众,如Rudolf G.Wagner,"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1:1,pp.1-34;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至如其他地区的反思探索,亦颇有可堪借鉴之处,如三谷博以创刊于1875年而于翌年惨遭官方依据《太政官布告》第98号遂被封禁的《评论新闻》为分析对象,释论日本的“公论空间”(见三谷博:《公論空間の創發—草創期の“評論新聞”—》,鸟海靖、三谷博、西川诚、矢野信幸编《日本立憲政治の形成と變質》,东京吉川弘文馆2005年版,第58-85页)。三谷博还另编辑以讨论以日、中、朝鲜为主的“东亚公论”的形成及其历史经验的文集《東アジアの公論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如印度史方面,Francesca Orsini则指陈不要将公(public)与私(private)看成二元对立的范畴,相对的、可能存在着的是:公与私可以及称之曰惯行(customary)的三种范畴,见Francesca Orsini,The Hhindi Public Sphere 1920-1940: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Ntionalis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Veena Naregal则(主要以语言和文学领域)探讨在大英帝国统治下接受英语和印度自身语言双语的西印度精英,如何建构出“殖民的公共领域”(colonial public sphere),见Veena Naregal,Language,Politics,Elites and the PublicSphere:Western India under Colonialism(London:Anthem,2002)。总之,关于人类社会里的“公共空间”的历史经验与理论议题,显然已蔚为学术产业,本文难以一一深究彼等趋同殊异之处,惟望出以精细的探索取向,提供个案的述说。
(13)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廿四年二月廿九日〔1898年3月21日〕:“灯下为吉儿改《醒世歌》,颇有趣。”(《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据皮锡瑞致湖南学政徐仁铸(研甫)函,皮嘉佑作《醒世歌》,系承徐氏之命。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廿四年七月十二日〔1898年8月28日〕:“小儿前承明示,嘱为诗歌,开导乡愚,免招敌衅,爰命小儿拟作,名为《醒世》……”(《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页)
(14)如刊于《湘报》的《南学会问答》即有“善化龚佩泉”问:“地若圆转,人物岂不倒旋?地若旋转东西,岂不有时移易?”见《南学会问答》,《湘报》第4号,光绪廿四年二月十八日〔1898年3月10日〕。
(15)皮嘉佑:《醒世歌》,《湘报》第27号,光绪廿四年三月十六日〔1898年4月6日〕。
(16)如皮锡瑞日记自述:“见本日《湘报》,《醒世歌》已刻上,人必诟病,但求唤醒梦梦,使桑梓之祸少纾耳。”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廿四年三月十六日〔1898年4月6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17)皮锡瑞致湖南学政徐(研甫)函亦言:“妄庸睹此,痛加诋諆;平等一说,尤肆掊击。……”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廿四年七月十二日〔1898年8月28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41页)
(18)叶德辉:《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版,第20A-23A页(总第417-423页)。不过,叶德辉此函所引《醒世歌》之文辞,与原文略有不同。此后皮、叶之间对此事续有面谈与书函往来,不详述。
(19)原文是:“泰西……日报盛行……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其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见闻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议,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346页。
(20)原文是:“《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康有为:《上今上皇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96页。
(21)原文是:“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唔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寮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康有为:《上今上皇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全集》第2册,第180页。按,“英之《太唔士》”即The Times,至于“美之《滴森》”,则尚莫知其详。
(22)原文是:“并大购外国政治、艺术、农工、商矿图书及各国新报,令通者翻译,以广学识。”王觉任:《开储材馆议》,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1“内政部五·育才”,第16B页(影印本第714册,总第1330页)。
(23)当然,从新闻实务的角度言之,晚清时期既存的报刊应当是促成这股社会共识的基础。如1871年起,上海、香港与欧洲之间的有线电报接通,中国报纸开始刊登以电讯传递的新闻,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申报》则于1882年2月23日首先刊登利用中国的电讯传递的新闻稿,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1884年初问世于广州,只存世不到1年的《述报》则引用日报所译的西字报消息来报导“俄国深谋”,见李磊:《述报研究:对近代国人第一批自办报刊的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主导下的《万国公报》亦屡译载西方报刊的消息。随意翻阅19世纪90年代的《申报》,且可得见已刊有各式各样的外电译稿。本文强调的是,当时的士人如何有意识地在言论层次开展鼓吹。
(24)(25)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2、27页。
(26)转引自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31页。
(27)参见Simon J.Potter,News and the British Worid:The Emergence of an Imperial Press System,1876-192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8。
(28)参见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Cambridge:Polity,2002),p.138。
(29)例如《万国公报》卷83(1895年12月)辟有“电书佥载”专栏,即刊有“伦敦露透总电报局致电上海云……”等讯息,见《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5册,总第15715页。至于《万国公报》何时开始译载路透社的新闻消息,待查(译载其消息之专栏名称,屡有不同,亦不详述)。
(30)关于“路透社新闻”导入中国及其传播情况的简述,参见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报坛逸话·路透社在中国”,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9-52页。其它新闻史著作的叙述,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版,第565-567页,大多依胡道静本文而裁剪成篇,不再一一征引。
(31)原文是:“古者诸侯万国有万报馆,今直省州县皆宜令设报馆,以达民隐,而开民智。本会先开报馆,其体有六:一、纪谕旨奏折;二、纪京师掌故时事;三、纪直省民隐、吏政、水旱、盗贼;四、考地理边务;五、译外国报,叙外国政事地理风俗;六、附论说。其余商贾琐事姑从缓及。其利亦有六:一、士夫可通中外之故,识见日广,人才日练,是曰广人才。……”《开设报馆议》,《强学报》第1号(1895年12月16日),第2B-3A页(影印本第1册,第4-5页)。
(32)汪诒年:《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198页。
(33)《汪大燮函(72)》,《书札》,1:743;这是汪大燮得到新开报馆定名为《时务报》讯息时表示“未谓然者”的反应,他认为,汪康年“初意名为《译报》,其名未尝不足倾动人,而名实相符……”。
(34)关于汪康年当时的努力过程,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页。
(35)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43-45页。
(36)《邹代钧函(19)》,《书札》,3:2648。
(37)《汪大燮函(71)》,《书札》,1:739。
(38)《新开时务报馆》,《申报》1896年6月22日(影印本第53册,第340页)。
(39)据戈公振观察,《时务报》“域外报译独占篇幅至二分之一而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5页。
(40)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影印本第1册,总第6页。
(41)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York:Free Press,196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p.3。
(42)或者,用Stuart Hall持续关心的课题来说,即是大众传媒与霸权(hegemony)的关系。讨论Stuart Hall论说的相关文献不可胜数,例如Nick Stevenson,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2nd ed]),pp.34-46,不详举。
(43)《时务报》全帙69册的译稿里,单论一国(地区)者共1334篇;涉及世界列国彼此交涉讯息相关者共227篇;其它科学知识等资料共145篇。
(44)在《时务报》全帙69册里,第32、34、45册未载“路透电音”,自第62册起则由“中外电音”栏所取代。
(45)参见Kevin G.Barnhurst and John Nerone,The Form of News:A History(New York & London:Guilford Press,2001),pp.2-3。
(46)例如曾广铨译《直隶严防土匪》(西文译编/中外杂志/北中国每日报西一月十九号),《时务报》第51册,光绪廿四年正月廿一日〔1898年2月11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495页;曾广铨译《粤闽土匪蠢动》(西文译编/中外杂志/北中国每日报西二月五号),《时务报》第52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561页;曾广铨译《琼州土匪为患》(西文译编/中外杂志/北中国每日报西二月十号),《时务报》第52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562页。
(47)关于《时务报》述说孙中山事迹的各篇译稿,可参见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671-166页。
(48)例如,同样依据路透社新闻的报导,《时务报》的译稿里称孙中山是“中国变政党人”(“路透电音”,《时务报》第10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初一日〔1896年11月5日〕,影印本第1册,第660页);《万国公报》的译稿则称孙中山是“在广东谋反之医士”(“电书月报”,《万国公报》第94卷〔1896年11月〕,影印本第26册,总第16480页)。
(49)张坤德译《中国不能维新论》(英文报译/译伦敦东方报西七月初十日),《时务报》第3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152-153页。
(50)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中国宜亟开民智论》(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十月初一日),《时务报》第43册,光绪廿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2933-2935页。
(51)古城贞吉译《俄国将吞噬亚洲》(东文报译/译东京日日报西三月廿三日),《时务报》第24册,光绪廿三年三月廿一日〔1897年4月22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637页。
(52)古城贞吉译《德国海军及殖民政策》(东文报译/译国民新报西八月十七日),《时务报》第39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廿一日〔1897年9月17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670-2675页。
(53)曾广铨译《胶州湾图说》(西文译编/译亚东四季报西正月),《时务报》第54册,光绪廿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13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696页。
(54)古城贞吉译《中人愤言》(东文报译/译大阪朝日报西十一月二十九号),《时务报》第49册,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2月2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364-3365页。
(55)汪康年亦撰有《论胶州被占事》,申论因应之道,并批判道:“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内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见汪康年:《论胶州被占事》,《时务报》第52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527-3531页。夏曾佑读此文后即谓:“观五十二册中,尊处之谤政府亦云甚矣,不知政府见之,又作若何面目相向也。”(《夏曾佑函(18)》,《书札》,2:1330),可见一斑。
(56)曾广铨译《论各国于东方用意所在》(西文译编/中国时务/香港每日报西一月十三号、北中国每日报西二月九号),《时务报》第52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影印本第4册,总3543-3544页。
(57)班纳迪克·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1999年版,第35-36页。
(58)即张坤德译《德相泄露机密》(英文报译/译伦敦东方报西十月三十日),《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060页;张坤德译《又德相泄露机密一则》(英文报译/译伦敦东方报西十一月初六日),《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060页;张坤德译《论德相泄露机密》(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十二月廿一日),《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060-1061页;古城贞吉译《德皇召前相俾思麦》(东文报译/译大阪朝日报西十二月十三日),《时务报》第17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161页。
(59)即古城贞吉译《德国君臣不协》(东文报译/译时事新报西九月初四日),《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1896年9月2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394页;古城贞吉译《德皇政策》(东文报译/译东京日日报西二月廿三日),《时务报》第21册,光绪廿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97年3月2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439-1440页;古城贞吉译《德皇大失民心》(东文报译/译国民新报西七月初四日),《时务报》第34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1897年7月29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324页;古城贞吉译《德皇演说》(东文报译/译国民新报西十月初八日),《时务报》第45册,光绪廿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085-3086页;古城贞吉译《论德皇》(东文报译/译反省报西十月初一日),《时务报》第46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164-3166页;古城贞吉译《德皇几罹不测》(东文报译/译日本新报西十月廿五日),《时务报》第46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166页。
(60)参见Susan R.Brooker-Gross,"The Changing Concept of Place in the News",in Jacquelin Burgess and John R.Gold,Geography,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1985,p.63。引自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p.25-26。
(61)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266页。
(62)例如,张元济于1897年11月15日即致函汪康年,告知德国“今忽自我开衅”,但汪至24日始收到此函,见《张元济函(25)》,《书札》,2:1716。本函系年为光绪廿三年十月廿一日〔1897年11月15日〕,函末署“十月廿九到”(即11月24日收到)。
(63)例如,《时务报》第46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所载之《路透电音》,起自1897年11月5日,止于11月11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153-3154页),并无此事之新闻(由此亦可一窥《时务报》接收的路透社新闻,与它原来发出的时间,略有2周的时间差距)。
(64)即曾广铨译《论德人有志于山东胶州》(西文译编/译中国北方每日报西十一月十八号),《时务报》第47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97年12月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203-3204页。本册的“中外杂志”一栏刊有亦译自《北中国每日报》(应即亦为《中国北方每日报》,即《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1月22日的一则新闻。《北京近闻》(影印本第册4,总页3220第),同册的《路透电音》亦译载此事(影印本第4册,总第3226页)。
(65)(66)参见Simon J.Potter,News and the British Worid,p.27/p.28。
(67)参见藤井信幸:《明治前期にぉけゐ電報の地域的利用狀況—近代日本と地域情報化—》,《近代日本研究》1990年第12期,第138-156页。
(68)参见里见脩:《通信社の發逹—國内通信かぅ國通信への模索—》,有山辉雄、竹山昭子编《メディア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东京世界思想社2004年版,第139页。
(69)参见石井宽治:《情報·通信?近代史:近代日本の情報化と市埸化》,东京有斐阁1994年版,第108-109页。
(70)当然,这并不是说《时务报》是当时中国士人知晓“胶州湾事件”讯息的惟一管道。例如,身处上海的孙宝瑄于光绪廿三年十一月三日〔1897年11月26日〕即与宋恕讨论过此事,感慨曰:“不知无脑国何以应之?”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人在湖南的皮锡瑞则亦于同日知悉此事,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廿三年十一月三日〔1897年11月26日〕条,《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3页。至于孙宝瑄、宋恕与皮锡瑞如何知悉此事,不可得知。
(71)例如,尚莫详作者与原来出处的文章即如是言之:“……德人强占胶州,俄人思踞旅顺,骨肉有限,剥削无已。天下大势,岌岌可危。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此后事机益紧,发难愈速,将见海外各国效尤……”见《西人为患中国之由》,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02“通论部三”,第22A页。
(72)参见Daniel Woolf,"News,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and",in Brendan Dooley and SabrinaA.Baron,edited,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Routledge,2001),pp.80-118。
(73)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4)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版,第1-19页。
(75)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德人仇英》(英文报译/译横滨日日西报西八月三十日),《时务报》第40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715-2716页。
(76)《时务报》涉及“美西战争”的报导甚众,不详举,如述说其始末的译稿是:古城贞吉译《美西开战始末》(东文译编/译民友报西五月十号),《时务报》第64册,光绪廿四年五月初一日〔1898年6月19日〕,影印本第5册,总第4337-4340页。
(77)《美日战场图》,《时务报》第64册,光绪廿四年五月初一日〔1898年6月19日〕,影印本第5册,总第4327-4328页。
(78)张坤德译《英国下议院议论土乱及英国应如何办法》(英文报译/译太母士报西七月初四日),《时务报》第5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十一日〔1896年9月1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302页。按,这篇译稿全文在《时务报》连载三期:张坤德译《英国下议院议论土乱及英国应如何办法》(英文报译/译太母土报西七月初四日),《时务报》第5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十一日〔1896年9月1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297-302页;第7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436-440页;第8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十一日〔1896年10月1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505-508页。
(79)古城贞吉译《港报论东洋大局》(东文报译/译东京日日报西十一月初十日),《时务报》第30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896年12月5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882页。
(80)原文是:“是时中人横行黑龙江,断东洋(指东方亚洲而言,非指日本也。中国在亚洲,是亦居东洋之中也。人每误以日本为东洋,故附辨焉)至西伯利亚内地之要路,于西伯利亚内地之贸易不能畅销……”古城贞吉译《俄国外政策史》(东文报译/译东邦学会录),《时务报》第48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298页。
(81)参见Martin W.Lewis and Karen E.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81。
(82)张坤德译《中国通商各口二十一年份商务情形》(英文报译/译伦敦东方报西十月初二日),《时务报》第13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896年12月5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853页。
(83)古城贞吉译《土耳其论》(东文报译/译东京日日报西十月廿二日),《时务报》第11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十一日〔1896年11月15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735页。
(84)古城贞吉译《俄将论中国财政》(东文报译/译东邦学会录),《时务报》第14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96年12月15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931页。
(85)参照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pp.4-5。当然,Giddens也承认,各式各样新式的分殊与散裂形式亦被创造出来。此题涉及广泛,非本文所欲详究。
(86)引自Martin W.Lewis and Karen E.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Preface",p.x。
(87)徐勤:《中国除害议》,《时务报》第42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廿一日〔1897年10月16日〕,影印本第4册,第2842页。
(88)“地理体”的观念,依据Thongchai Winichakul的论述,他藉由暹罗国族情境(nationhood)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例子,具体显现出地理这门科学及其最主要的致知方式:地图的绘制,如何为国族的建构提供了基础。就鉴别一个国家的最具体的特征而言,领土(territory)所至(包括与之相关的价值与实践),或可名之曰“地理体”(geo-body),其实乃是被创造建构出来的。如其所述,暹罗自身实有其传统的认识空间的知识和技术,但在“现代”地理知识的“入侵”之下,“传统”知识被赋予“科学”形象的“现代”地理知识所取代,但这不只是个纯粹“知识”领域或“学术”里的结果,更还是与以战争及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外交/政治实践的结果。就某个国家的“地理体”的内容而言,相关的概念、体制与实践,包罗广泛,诸如领土完整与主权的概念:也包括边防、武装冲突、侵略、战争等事件;余如领土范围以内的经济活动,生产、工业、贸易、税收、海关、教育、行政、文化等等皆是。然而,不该只把“地理体”视为用以指涉领土或空间的对象,它乃是某个国家之生命的成分(a component of the life of a nation),是国家骄傲、荣光、忠诚、赤忱、热情、憎恶、理性与非理性的泉源,当它与其它国族构成要素结合起来的时候,更可以创造出其它许多的概念与实践。因此,可以把地理学看成是一种类型的调解者(mediator),它提供的不是在地球上某个角落的对象,而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是对某种被认定为客观的实体的概念抽象(a conceptual abstraction),是一套有系统的象征(signs),是一个论述(discourse)。参见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承沈松侨教授提示注意此论,特谨深致谢意。
(89)《邹代钧函(23)》,《书札》,3:2658。张元济亦说:《时务报》“所译地名,每无一定之字,能熟外国地理者有几人,似宜留意。”见《张元济函(9)》,《书札》,2:1685。
(90)参见翟忠义:《邹代钧》,《中国地理学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423页。
(91)张坤德译《路透电音》,《时务报》第4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初一日〔1896年9月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239页。
(92)“中西文合璧表”,《时务报》第13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896年12月5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889页。
(93)《本馆告白》,《时务报》第47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97年12月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247页。
(94)其实,邹代钧对《时务报》的地名译文前后不能统一,还是有所批评,如他说“波斯湾”一辞在“十二册报中忽又作布斯湾”。见《邹代钧函(43)》,《书札》,3:2697。
(95)古城贞吉译《美国共和党宣论新政》(东文报译/译经济杂志西七月廿五日),《时务报》第3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174页。
(96)原文是:“……英人又见亚美利加之地,以尼加拉虞运河开通之期在即,欲得一要冲之地于其旁边,情焰如燃。前年注目于尼加拉虞东岸,藉名布教简派宣教师矣,于晃达拉士无故而以兵力拓境矣,于威尼结儿借口于境界不明,派探险队以将占有金矿,及阿米那河口矣。然皆为美国执门绿律旨以抗之……”见古城贞吉译《俄人论英国海外政策》(东文报译/译东京日日报西八月二十日),《时务报》第4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初一日〔1896年9月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248页。
(97)原文是:“……美国近言孟绿道理(按,美前总统孟绿者曾倡言美洲地土概不准外人干预,后人遵守其言,即谓之孟绿道理)已屡说不一……”见张坤德译《论德国有整水师之议》(英文报译/译温故报西四月十五日),《时务报》第31册,光绪廿三年六月初一日〔1897年6月30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103页。
(98)“电传竿牍”,《万国公报》卷85(1896年2月),影印本第25册,总第15858页。
(99)梁启超:《论学校.五.幼学(变法通译三之五)》,《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175页。
(100)例如,呼吁“统一精神疾病诊断名称的中文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见林家兴:《精神疾病诊断名称的翻译问题》,http://www.tap.org.tw/public/mag002/mag002-13.htm【2004/11/21】。教育部设有“国语推行委员会”,其职掌之一即是“关于统一中外译名音读标准之订定事项”,见http://140.111.1.192/mandr/rules/1-6-1.html【2004/11/21】。
(101)参见Michael Gurevitch,Mark R.Levy and Itzhak Roeh,"The Global Newsroom:Convergences and Diversit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elevision News",in Peter Dahlgren and Colin Sparks edited,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London:Routledge,1991),pp.206-207。当然,本文主要以电视新闻的报导为论述对象而指陈这种趋向,本文借用其论述,无意深究其论述涵括之全面样态。
(102)秦郁彦编《世界诸国の制度.组织.人事(1840-1987)》,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第367页。按,据《时务报》上同样由古城贞吉担任译事的另一篇译稿云,“儿那巴拿弗”为“俄国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见古城贞吉译《俄国首相逝世》,《时务报》第7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464-465页。至如《时务报》上由刘崇惠担任译事的另一篇译稿则将其官职与名讳译为“俄国外政大臣鲁马能务王”,见刘崇惠译《俄国外政大臣鲁马能务王事略》(俄文报译),《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071-1074页。不过,《时务报》从登出刘崇惠的译稿后,凡涉及此君之译稿,其名讳皆统一为“鲁马能务”,如:古城贞吉译《俄前相鲁马能务逸事》,《时务报》第36册,光绪廿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897年8月18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452-2453页;古城贞吉译《鲁马能务王遗策》,《时务报》第46册,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897年11月24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163-3164页。
(103)古城贞吉译《论俄相儿那巴拿弗》(东文报译/译时事新报西九月廿五日),《时务报》第9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廿一日〔1896年10月2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595-597页。
(104)关于拿破仑在晚清的形象,参见陈建华:《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汉学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第321-352页。
(105)试举一例,刘永福所撰《谕黑旗将士檄》即谓:“法酋拿破仑第一颇善用兵,其国人称之天神……”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2“兵政八·兵机二”,第8B页(第751-2册,总第788页)。
(106)原文是:“更观地球百年以来,拿破仑席卷西欧,逞其权力,英人耻之,合全国之力,与之周旋海上,卒乘其敝,英人至今执欧洲牛耳。普鲁士见弱于拿破仑,法人视之如奴隶,普人耻之,合全国之力,讲武兴学,卒摧强邻,虏路易,围巴黎,一战而霸,法人至今不能报,法人耻之……”寿富:《知耻学会后叙》,《时务报》第40册,光绪廿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762页。
(107)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37页。原著为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08)《外交のナポレォン》,《时事新报》1896年9月25日,复刻本第15卷第5册,第253页。
(109)限于时间因素,本文尚未能一一对比,仅取略相关述说,对照如下:
日本《时事新报》:公は外交のナポレォンなり:或は公を評レて其大望心の盛なろはィグナチ一フ將軍に酷似すれも彼か如く寛容人を親しましむゐ度量を備へぎゐふそ即ち人望を收攬すゐを得ぎりし所以なれ實は公は其心死灰の如く絶て人情を顧みず世の平和を攪擾すゐ無遠慮冷血の人物なりも云ふ者ゅれぞも甚だ其當を失ひたろ批評にして假會ひ多少の欠點はふりもすゐも大政治家もしては今日實に露國のみならず他の國々にも比肩す可さ俊才ながゐ可し……
《时务报》译稿:其外交权术与拿破仑等,至雄心之盛,酷似伊官拿次呼将军,而宽容稍逊。惟丰裁峻整,度量酷隘,故不能允协舆情,此其弊也。然窥其宗旨,甘作民贼,毒痡四海,囊括宙合,方遂厥志,殆魏武帝、张献忠、李自成之流亚欤。夫武健严酷,仁者羞言;然安内攘外,掠地取邑,当今之世,罕有伦比,揆诸申、韩,未遑多让。如儿那巴拿弗者,可谓才士也。……
(110)Tejaswini Niranjana,Si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111)关于这一方面的考察,成果尚称繁多,笔者捧读受益甚众者,有刘人鹏:《“中国的”女权、翻译的欲望与马君武女权说译介》,《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75-126页。如至刘禾则以国际法(及其文本)在中国的实践/翻译/应用为例,提示曰:我们对这样的情境首先得思考的是一部被翻译的文本如何(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在不同语言的论述脉络(the discursive contexts)之间生产意义,亦颇称胜义频出。参见Lydia H.Liu,Tne Clash of Empires:Tn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08-139。余不详引。
(112)关于这等“翻译的政治”的课题,涉题广泛,笔者未可多所阐释,然而笔者同意Arif Dirlik之倡言历史的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的观点。他认为,这样的认知,至少澄清了现在如何利用/误用“过去”的方式(the ways in which the present uses and abuses the past),也可以提醒我们思考自身的历史性(historicity):我们现在的所言所为,为什么和过去人们的所言所为,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参见Arif Dirlik,"Is There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Globalism,Post Colonialism,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in idem:Postmodernily's Historie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p.63-89。
(113)《时务报》刊出的文章共计4篇;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曷格司射光》(英文报译/译美国格致报西七月廿四日),《时务报》第38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589页;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又曷格司射光一则》(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八月十九日),《时务报》第38册,光绪廿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影印本第3册,总第2590页;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曷格司射光》(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十月十三日),《时务报》第43册,光绪廿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2947-2948页;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曷格司射光》(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十月十九日),《时务报》第44册,光绪廿三年十月十一日〔1897年11月5日〕,影印本第4册,总第3017-3018页。
(114)原文是:“……若夫全体之学扎割之法,有回光镜以代哥罗多……有曷格司射光以照脏腑。”(《时务报》第38册),见黎祖键:《弱为六极之一说总论》,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通论下”,第18B-21B页(影印本第21册,总第186-192页)。
(115)张坤德译《海底行船新法》(英文报译/译英国公论报西十月初九日),《时务报》第13册,光绪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896年12月5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866页。
(116)原文是:“……《时务报》译英国《公论报》纪海底行船之法云:……观此知泰西制造之法,真可谓层出不穷矣……”见《论欲立海军宜先讲求制造》,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81“经武部十二·海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2辑,第12A-12B页(影印本第718册,总第3347-3348页)。
(117)如谓:“问:今日变通学校,不盭今,不悖古,当以何国为善?曰:日本哉!日本哉!日与我同洲之国,又同宗孔教……其人聪明,其俗悍劲,其政专制,其操业勤,其用财俭,大类吾华。其学或祖程朱……或宗阳明……或守汉学(《使东述略》:维新以来,犹有硁硁守汉学者;《时务报》亦译有《汉学再兴论》),或主实用……”见《日本学校变法详述问答》,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学校下”,第10B-11A页(影印本第21册,总第422-423页)。所谓《时务报》亦译有《汉学再兴论》,即古城贞吉译《汉学再兴论》,《时务报》第22册,光绪廿三年三月初一日〔1897年4月2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502-1504页。《使东述略》应或即何如璋的作品(待确证)。
(118)原文是:“……各种耕具其它新法,祗得《时务报》(第三册)所译电犁牛机器一说,余俱未闻……”见《农学论》,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7“农政上”,第3A-17A页(影印本第21册,总第559-587页)。按,即张坤德译《电犁新法》,《时务报》第3册,光绪廿二年十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161-162页。
(119)即古城贞吉译《美国总统出身》,《时务报》第8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十一日〔1896年10月1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526-527页。
(120)《交涉学》,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46“外交部一·交涉”,第14A页。作者“阙名”。
(121)即张坤德译《论德国不接华使》(英文报译/译上海字林西报西十二月十四日),《时务报》第16册,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初一日〔1897年1月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061-1062页。
(122)原文是:“……案:英国《公论报》(《时务报》译)云:中朝新简罗君丰禄充使伦敦,因材器使,人与事宜,其与同时使德者有黄君。在华人中能洞知西人心思,通晓西国文字者,首推两君,噫!英人之推服甚至,德与中向称和好,何以固执若此?或曰:此事不出自德廷,然则彼国驻华之使失国体,违公法,不且为环球诸国所窃笑乎!……”见《公使觐见原始》,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5“交涉”,第27B-28A页(影印本第22册,总第1192-1193页)。所谓“英国《公论报》(《时务报》译)”,即张坤德译《论新派驻英钦使》(英文报译/译英国公论报西正月廿二日),《时务报》第20册,光绪廿三年二月十一日〔1897年3月13日〕,影印本第2册,总第1349-1350页。
(123)关于各类《经世文编》的讨论,参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9月,第83-96页。相关研究讨论,参见丘为君、张运宗:《战后台湾学界对经世问题的探讨与反省》,《新史学》第7卷第2期,1996年6月,第181-231页。
(124)《外洋国势卮言》,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73“洋务五”,第22A-23B页(影印本第15册,总第1093-1096页)。
(125)张坤德译《俄国添兵论》,《时务报》第9册,光绪廿二年九月廿一日〔1896年10月2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574-576页。
(126)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3-19页。
(127)参见潘光哲:《〈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与晚清中国士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讨论会论文,2001年11月4日(待刊)。
(128)古城贞吉译《古巴岛述略》(东文报译/译日本新报西八月廿六日),《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1896年9月27日〕,影印本第1册,总第391页。《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同。
(129)《张元济函(19)》,《书札》,2:1682。
(130)这是Michael Schudson对于美国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等)的反省,他提出了“新闻作为公共知识”(news as public knowledge)的论说。在他看来,媒体向公众提供了某条新闻,它就被授与了某种公共正当性(public legitimacy),阅听人在公共论坛上便可一起讨论它,这样新闻报导不仅是散布传播而已,更是产生了像音响扩大机一样的扩大作用,引发了公众的注意力。参见Michael Schudson,The Power of New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21。当然,他亦指陈,这是在人们相信稳定可靠的民主体制之下,公民应随时获得有效信息的理想情境下的论说。
(131)引自Simon J.Potter,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p.215。
(132)“跨语实践”的识野,自然首推刘禾的引路之功。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133)James W.Carey,Communications as Culture,pp.18-20。转引自Jeremy D.Popkin,"Media and Revolutionary Crises",in Jeremy D.Popkin ed.,Media and Revolution:Comparative Perspectives(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5),p.23。
(134)参见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60-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