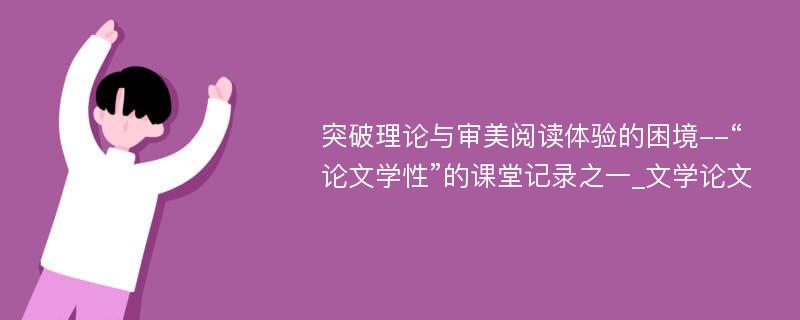
突破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的困境——《论文学性》课堂实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敌论文,困境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课堂实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7)01—0005—09
我们这门课程叫“文学性”。有关文学理论的课程已经很多了,有“文艺理论”,有“西方文艺理论史”,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为什么又要来这么一门课程呢?说句老实话,我对这些课程有看法。说得客气一点,没有一门课是令我满意的;说得粗暴一点,许多理论是与我的审美阅读经验为敌的。我进大学中文系,就是为了懂得文学,成为文学的内行,本来以为“文艺理论”这门课,会讲出许多有趣的艺术奥秘,让艺术感觉精致起来,让我会欣赏艺术,甚至提高文学创作水平。但这门课一上来就讲艺术的起源——起源于劳动,不是起源于游戏——我就觉得失望,讲来讲去,始终没有讲到形象是怎么回事。接着讲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就更令我丧气。大家都在生活之中,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成为艺术家,而大多数人却不行呢?当时流行一个权威命题,叫“美是生活”,我觉得这是废话。(活跃)我想,反过来说,美不是生活,难道就没有道理吗?这种理论实在太让人烦了。(众笑)我在心里抬杠,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你回答说,花是土壤,肯定会遭到人们的嘲笑。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你回答说,酒是水果或是粮食,人家会觉得你神经有问题。(众笑)但当你问艺术或美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美是生活。说这话的人反而成了大理论家,岂不是咄咄怪事!其实,说这话的人,不过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名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句话出自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是1860年。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样一句包含着明显偏颇的话,居然被当作神圣的经典来崇拜,叫不叫人郁闷?叫不叫人委屈?(众大笑)
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过去了。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形势并没有好转,流行的理论更干脆,说,文学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话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哲学、历史、经济理论不也是意识形态吗?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家的回答,就是给你当头一棒,根本没有文学性这回事。人家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还有加缪、德里达,先后宣告了它的虚幻。很快,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某种统一的文学性,成为一代人的共识。你这个孙绍振是不是昏庸老朽了,居然选了这么一个落伍的课题?
否定文学性的理论,天花乱坠,异彩纷呈,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可否认,每一种理论都有理论本身的价值。其中有些有纯理论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可是,用它来解读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常常是无效的,是文不对题的;硬要用一下,也是削足适履。这一点,我起初感到了,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一向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众笑)但是,后来读到李欧梵先生的一篇文章,才感到自己并不太愚蠢。李欧梵先生在“全球文艺理论二十一世纪论坛”的演讲中提出,西方文论流派纷纭,却很难实现对文学文本进行有效解读的目的。李先生以挑战、怀疑西方权威为荣,而我们文论界却以服膺、崇拜西方大师骄人,这种对照不仅有趣,而且发人深省。李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幽默,我来念一段给诸位听听:
话说后现代某地有一城堡,无以为名,世称“文本”,数年来各路英雄好汉闻风而来,欲将此城堡据为己有,遂调兵遣将把此城堡团团围住,但屡攻不下。
从城墙开眼望去,但见各派人马旗帜鲜明,符旨符征样样具备,各自列出阵来,计有武当结构派、少林解构派、黄山现象派、渤海读者反应派,把持四方,更有“新马”师门四宗、拉康弟子八人、新批评六将及其接班人耶鲁四人帮等,真可谓洋洋大观。
文本形势险恶,关节重重,数年前曾有独行侠罗兰·巴特探其幽径,画出四十八节机关图,巴特在图中饮酒高歌,自得其乐,但不幸酒后不适,突然暴毙。武当结构掌门人观其图后叹曰:“此人原属本门弟子,惜其放浪形骸,武功未练成就私自出山,未免可惜。依本门师宗真传秘诀,应先探其深层结构,机关再险,其建构原理仍基于二极重组之原则。以此招式深入虎穴,当可一举而攻下。”但少林(按:解构)帮主听后大笑不止,看法恰相反,认为城堡结构实属幻象,深不如浅,前巴特所测浮面之图,自有其道理,但巴特不知前景不如后迹,应以倒置招式寻迹而“解”之,城堡当可不攻而自破。但黄山现象大师摇头叹曰:“孺子所见差矣!实则攻家与堡主,实一体两面,堡后阴阳二气必先相融,否则谈何攻城阵式?”渤海(按:读者反应)派各师击掌称善,继曰:“攻者即读者,未读而攻乃愚勇也,应以奇招读之,查其机关密码后即可攻破。”新马四宗门人大怒,曰:“此等奇招怪式,实不足训,吾门祖师有言,山外有山,城外有城,文本非独立城堡,其后自有境界……”言尚未止,突见身后一批人马簇拥而来,前锋手执大旗,上写“昆仑柏克莱新历史派”,后有数将,声势壮大。此军刚到,另有三支娘子军杀将过来,各以其身祭其女性符徽,大呼:“汝等鲁男子所见差也,待我英雌愿以崭新攻城之法……”话未说完,各路人马早已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如此三天三夜而后止,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失惊,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谢天谢地。[1]
李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检验理论的重要路径是是否能有效地解读文本,理论出了一大堆,旗号那么多,文本的解读却毫无进展,理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李先生的说法可能有一点极端了,也许不是这些学派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像林彪所说的那样,没有“活学活用”。这个我们一时说不清,暂且不去管它。
在别的课堂上,一些课程专门讲理论旗号(当然有它的自由),就是以不解读文本为荣,纯粹是从理论到理论,可能也有它的成就,我也不想和他们争一日之短长。但请允许我把生命奉献给另一种风格的理论。在我这个课堂上,拒绝搞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我追求最大限度地解读经典文本的有效性。早在《聊斋志异》上,就有一篇故事说,不管猫的皮毛是什么颜色,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经过一个伟大政治发挥,救了我们国家,在这里,我想证明一下:只要能有效解读经典文本的就是最好的理论。
我所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为什么能感染人。问题又来了,什么叫感染力,什么叫做文学的感染力?伊格尔顿,甚至拒绝文学性概念,没有文学性,哪来感染力。他以英国文学史为例,自古以来文学是怎么回事,从内涵到外延就不断在变化。[2](P1~18) 照他这种理论类推起来,中国文学史,一开头的权威文本,周诰殷盘,是行政部门的布告、宣言,现在看来就不是文学。孔夫子和学生谈话的语录,是教育,庄子、老子的作品,是哲学;刘勰算是文学理论家了,可是《文心雕龙》把给皇帝的奏章都包括在内,根本不想分别文学与非文学;韩愈的《师说》,本来是议论文,可也堂堂正正地写在中国文学史里。
连研究的对象都不能确定,还谈什么理论?
再说,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就算人家认同了、肯定了文本的文学性、审美价值,可作品并不是终点,要给人看了才算是完成了。但人是不同的,读者在接受作品时,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把感情和智慧投入进去。读同样的作品,不同的读者的投入并不相同,评价就很纷纭,故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这种现象并不鲜见。陶渊明的诗,当年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就是个二品,可现在几乎公认是极品、神品。《三国演义》中的孔明的形象,世世代代受到读者的喜爱,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不好,智慧太超人了,像妖怪(“多智而近妖”)。更明显的是,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毛泽东则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四大家族的兴衰史。我当年读它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一点:大家族里,普遍存在着人的精神危机,接班人的危机。新诗闹腾了80年了,流派纷呈,博士、教授一大堆,在大学中文学科是“显学”,但到现在还有人不承认它的艺术价值。毛泽东当年甚至直言不讳,给两百大洋都不看新诗。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时候,舒婷、北岛在青年读者中风靡一时,我写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之欢呼,可有一个诗人贺敬之,觉得大事不好,组织对我的批判,就连艾青也不欣赏,还写了文章,说我们的“崛起”理论家,不是为了诗歌,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崛起”。
虽然对于作品的评价可能很纷纭,但不管多么纷纭,一千个哈姆雷特毕竟还是哈姆雷特,而不是李尔王。在理论上,毕竟文本的主体是“共同视域”。不管作家和读者的主体性有多么强大,多么纷纭,但读者所读的文本总是固定的,他的感觉、情感要受文本所提供的感觉、情感的经验和生动的形象的制约。再说,艺术价值虽然有变化,相比起来要缓慢得多。李白死了多少年了,社会生活的翻天覆地,不知几次了,可是人们对李白越来越欣赏,越来越着迷。艺术的欣赏,有跨越政治、经济的历史语境的特点,因此,马克思才说,古希腊文学不但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人类艺术“不可企及的规范”。那些经历了历史考验、获得了不同时代读者喜爱的作品,就成为真正的经典。
虽然文本是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对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感染,又证明了艺术价值是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特点的。
对艺术价值采取虚无主义的学派有一种共同作风,就是制造自己的精神优势,把你的嘴巴封住,把艺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化、不确定性偷换为在同一历史语境中的变幻,把不确定性绝对化,好像每秒钟都在变化,你根本抓不住;你刚刚抓住,它就变了。就是在同一历史语境中,研究艺术也是徒劳的。我在一个学术会上,听希利斯·米勒先生说,德里达宣称:小说要灭亡了。你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它,不是太傻气了吗?但这是一种诡辩,吓唬老百姓而已。第一,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按照波普尔的证伪说,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说小说要灭亡,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按照辩证法,按照解构主义,一切都在走向自身的反面,走向不存在。太阳要灭亡,地球要灭亡,人类也要灭亡,你德里达也要灭亡。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你德里达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当你的教授,发表演说。吊诡的是,去年德里达的生命灭亡了,他所预言的小说灭亡,目前还只能说遥遥无期。(众笑)当然,对一个故去的思想家,这样讲话,有失中国人的厚道。但是,这是事实,我不过是反映了事实。
在德里达们看来,一切都是绝对不确定的,是绝对相对的。表面上这是对一切理论的瓦解,可是,只要把他们的理论用来针对他们自己(这在辩论术上,叫做“自我关涉”),他们就不能不陷入悖论。按照他们的相对主义,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相对主义照理应该也是相对的。可他们却把相对性当作不受一切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的大前提,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相对主义是绝对的。这就是他们的悖论,这种悖论有着自我颠覆的威力。
不要让这种艺术的犬儒主义搅昏了我们的头。
和德里达不一样,直到我死亡,都要宣言,文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灭亡。除非确切地告知我,小说、诗歌、戏剧,在这一秒钟就要毁灭,马上就没命了,我才停止对艺术奥秘的探求。艺术比之其他文化历史现象,具有相对的绝对性,或通俗一点说,具有超越某种历史语境的稳定性。
学习理论,并不是为了玩弄概念,作文字游戏,最起码,它的目标,是为解读作品,揭示一般读者看不出来的艺术的奥秘。
比如,我们讲《西游记》,“大闹天宫”好在哪儿呢?好在它反映了农民、市民或一般的下层人民对现存秩序的反抗。这还没解释出“大闹天宫”为什么会那么艺术。孙悟空和二郎神打仗,施展变身术,变成老鹰,变成鱼,对这种变化,读者兴味比较一般。而到孙悟空变成一个庙,把尾巴变成旗杆竖在庙后面,读者就有兴味了。为什么这个尾巴变旗杆放在庙后,就比变成鱼、变成老鹰更生动、更有趣呢?我们的艺术理论到这儿就哑巴了。我觉得应该有人去解决。文学理论和流派,花样翻新,一茬又一茬,但没有一茬是有意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我就要从这个方面,知难而进,来试试看,我不怕被人家说是“老土”。(笑)“土”有什么不好?一切吃的都是从土里来的,《圣经》上说,连人都是从土里来的,最后还要回到土里去。《山海经》说,女娲造人用的也是黄土。人从土里来,不回到土里去,还想上天吗?(大笑)天上那么冷,零下多少度,又没有氧气,又没有冰激凌,又没有电视,我才不去呢。(大笑,鼓掌,喊叫)
许多学者写了许多学术论文来谈论文学,可其中有不少还是艺术的外行。这是因为他们对理论太迷信,迷信就是精神上的自甘贫弱。许多研究生、博士、教授,总是以为,只有懂得理论,才能享受到审美的阅读体验。事实上,恰恰相反,只有饱和的审美阅读体验才能给理论以生命。不能说明审美体验的理论,是病态的,迷信这样的理论是犬儒主义的。阅读的任务并不是为理论做例证,做附庸,而是以丰富的主观审美体验和抽象的理论做搏斗,在这方面,我们还真要有一点胡风先生的主观战斗精神。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可以解释为,审美的优势,只有审美体验有了优越,才能对理论进行同化、征服,甚至颠覆。
当代西方理论如果有一千条优点,但,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习惯于从形象外部研究形象。从概念到概念,以逻辑的演绎法为主。但是,这种演绎法,是有局限性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演绎法把结论包含在大前提中了。这是因为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普遍的,小前提是特殊的,才能对特殊得出结论。而普遍的、周延的大前提,却把一切特殊情况都涵盖在内了,故演绎法只能从已知到已知,不能从已知到未知。我想和它们从根本上唱一句反调,不是以演绎法为主,而是以归纳法为主,不从文学的外部关系入手,而从作品的内在构成去分析。打一个比方。比如,研究一盆水,你光是研究它的外部关系,说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地底下冒出来的、河里引进来的,这个只是外部关系,并没有提示出水的内在奥秘。要分析水的内在结构,就要说它是由二分氢、一分氧构成的,氢是可以自己燃烧的,氧是帮助燃烧的,合成水以后,它能灭火。我们就用类似的方法探究形象的结构。研究水并不需要把所有的水都弄到手,只要取其一滴,分子形态的,就够了。现在以贺知章的《咏柳》作为一个分子: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诗写出来有一千多年了,艺术生命仍然鲜活。它为什么好?怎么好?就是大学者,专门研究唐诗的,头发都白了,解读起来却很少沾边;有的权威人士,连门儿都摸不着。北京大学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咏柳〉赏析》。[3]
他说它好在:第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写的是一个“总体”印象。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地写柳丝很茂密。这就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设问。第四句“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回答,为什么这个叶子这么细呢?哦,原来是春风剪出来的。那么它的感染力在哪里呢?在这里:第一,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二,“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比喻“十分巧妙”。我读到这里,就不太满足。我凭直觉就感到这个比喻很精彩,这个不用你大教授说。我读你的文章,就是想了解这个比喻怎么巧妙,可是你只说“十分巧妙”,这不是糊弄我吗?(众笑)第三,他认为这首诗好在它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赞美了“创造性的劳动”。这一点,我比较怀疑。一个唐朝的贵族,他脑子里怎么会冒出什么“创造性的劳动”?读唐诗,难道也要想着劳动,还要有创造性?这是不是太累了?(众笑)这里,没有唐朝人的情感,也没有今天的读者的感受,这种感想是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中文系受过苏式机械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教育的傻学生,才可能有这样的解读。
为什么会这样傻呢?有美学根源。第一,美就是真。只要真实地反映对象,把柳树的特征写出来就很动人了。但这一点很可疑,柳树的特征要是一样的,不同的诗人写出的柳树不都是一样了吗?还有什么诗人的创造性呢?第二,这是一首抒情诗。抒情诗凭什么动人呢?凭感情,而且是有特点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这叫做审美情感。要写得好,就应该以诗人的情感的特点去同化柳树的特征,光有柳树的特征,是不会有诗意的。反映“柳树的特征”这样的阐释是无效的。第三,是不是要认识柳树的特征,并一定要有道德的教化作用。如果诗人为大自然美好而惊叹,仅仅是情感上得到陶冶,这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并不一定要依附于认识和教化价值。第四,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这就是方法,这位教授的研究,限于世俗形象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统一性。统一了,就真了;真了,就美了。其实,分析,就是要把文本中潜在的矛盾提示出来。
柳树的形象与生活中的柳树是不是真的完全一致呢?如果不一致怎么办?按照“美是生活”、美就是真的理论,不真的,应该是不美的,是不是?但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是以情动人,而不是以物的特征动人,它借助柳树表现感情。当一个人带着感情去看对象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很客观、很准确?不是有一句话吗?不要带情绪看人,带情绪看人,就爱之欲生,恶之欲死。情人眼里出西施,哪来那么多西施呢?癞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情人而是仇人呢?同样的对象,仇人眼里出妖魅。(众笑)带了感情去看对象,感觉、感受、体验与客观对象之间就要发生一种变异。
不动感情,是科学家的事,科学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身体的感觉,他宁愿相信仪表上的刻度,体温是多少,脉搏是多少,不能跟着感觉走,只有把感情排除掉,才能科学、准确、客观。文学和科学最起码的区别就在这里。诗以情动人,要表现对柳树的感情,但不能直接喊出来,必须通过对柳树的主观的、发生了变异的感觉。
如果诗人说柳树是一种到了春天就发芽的乔木,这很客观,很科学,但没有诗意;如果带上一点情感,说柳树真美,这也不成其为诗。他要通过主观感觉,还要让感觉带上一种假定和想象并发生变异才成。本来柳树就是黝黑的树干、粗糙的树皮、嫩绿的小叶子和细长的柳枝而已,他说不,柳树的树皮不是黑的,也不粗糙,他说柳树是碧绿的玉做的。第二句,他说柳叶是丝织品,飘飘拂拂的。柳树的枝条是不是玉的和丝的呢?明明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绝对真的、客观的,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呢?要表达感情。表达感情就要带上一点点想象,让它更美好一点,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没有想象,感情就很难表达,所以说,进入想象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的境界,相反,想象就是假定。进入假定的境界,想象自由了,感情就不难诗化了。
想象就是假定,假定了才可能寄托感情,而不是什么如实地反映生活。懂得想象是欣赏艺术的入门。
那位教授说这首诗的好处是它写出了柳树的特征。特征是什么呢?是柳丝很茂密。我觉得,不到位。写出柳丝的茂密,不是贺知章的成就所在。柳丝很茂密而叶子很细,很尖,这才是贺知章的发现。通常情况下,植物到了春天,树枝长得非常茂密的时候,叶子也相应肥大,叫枝繁叶茂,可柳树的特点恰恰相反。柳枝非常繁茂的时候,叶子却很细。这个特点让贺知章震惊了,诗人感到非常美。这种美,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是由于春风吹拂,温度、湿度提高了,是柳树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但诗人觉得这不过瘾,觉得不是这样的,它比自然美更美,应该是经过创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有目的地把它设计、创造出来的,比自然美更精致。这不是假的吗?按照美就是真的理论,这不是不真了、不是不美了吗?但这是一种假定,是一种想象,诗人美好的情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充分表现。这样惊人的美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而要从诗人的情感的美来解释。
为了表现这种情感之美,诗人的运用语言是非常有天才的。如果我问:这首诗,前两句把这个柳树写得很美,后两句进一步赞美它,哪两句更好呢?你们无疑会告诉我后两句更好。为什么呢?后两句更有想象力,感情更有独创性。把柳树的绿色变成玉,把柳树的枝条变成丝,这在唐朝诗人中是一般水平。今天的诗人也大都有这个水准。但“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语言就精妙绝伦了。那位著名教授说,把春风化成剪刀,比喻“十分巧妙”,我表示怀疑。春风原来是温暖的,是非常柔和的,不会有像剪刀的感觉。如果是冬天的北风——尤其是在长安——吹在脸上,刀割一样,那倒是可能。但诗人把它比作剪刀不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心理抵抗和怀疑,不觉得这是对艺术形象的破坏,相反,却给我们一种震惊,以诗人的锦心绣口把我们的美好感情调动起来。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从文艺心理学上的想象来阐释。
这样的形象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第一,形象是一种审美感觉,这种感觉可以随着感情而变异。但,这种变异又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联想机制的约束的。春风、柳叶和剪刀之间,反差非常巨大,从艺术上来说,这是有风险的,但,又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其底层还有一种机制,就是联想很自然,联想的渠道是相近的。因为春风吹过,柳叶非常尖,非常细,叶子的尖和剪刀的利之间,因为空间相近而自然地通过联想转换了。从柳叶尖、细转换为春风的利,就有自然的过渡,这叫相近联想,过渡就较自然。把春风比作剪刀是冒险,是想象和联想的相近,使它获得了胜利。
第二,从语言学上解释。
我刚才说过春风本来不是尖利的,但有人可能要说,这是二月春风啊,春寒料峭嘛。这一点可以承认。但,为什么一定尖利像剪刀呢?同样是刀,我们换一把行不行?菜刀,二月春风似菜刀。(众大笑,活跃)这就很滑稽,很打油嘛。这个矛盾要揪住不放,不能随便蒙混过去。这里有个学问到家不到家的问题。剪刀行,菜刀不行,不仅仅是心理联想作用,而是特殊的汉语的词语联想自动化。因为前面有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众答:裁。)对了,“裁”字和剪刀自动化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汉语的特点。如果是英语,不管是“裁”还是“剪”,都是一个字“cut”。 如果要强调有人工设计的意味,就要再来一个字“design”。这样运用语言,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叫作“陌生化”。通常的词语,因为重复太久了,其间的联想就自动化了,也就是没有感觉了。一定要打破这种自动化,让他陌生化一下,读者的感觉和情感才能被激活。但是,我要对俄国形式主义加上一点补充,陌生化又不能太随意,陌生化只有在自动化(如裁和剪之间的自动联想)的潜在支撑下,才能比较精彩。
你们可能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耳熟能详,但光是耳熟能详不算真本事,要能够用它来解读作品,哪怕就解读一首诗,也是真功夫。现在,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等等,你们都学了不少,但有几个人能用它们来解释这一首诗呢?这就是说,这一切都还没有学到手,还没有成为你们的能力和素养。
我们换一个观念,女性主义,或者文化批评,来试一试。
前面我提到的那位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提到,“碧玉妆成一树高”,碧玉,联想到“小家碧玉”。这本来是一条思维的线索,很可惜,他提了一下,以后,整篇文章,就把它丢掉了。应该把它抓住。因为,碧玉“妆”成的“妆”,暗示着女性的美,这是很有潜在量的。这是女性的装扮。装扮给谁看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男性的视觉,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意向,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欣赏眼光的?化妆当然是为了美,怎么才算美呢?玉,是贵重的,丝绦,丝织品,也是贵重的,以贵重为美,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是不是有一点贵族的眼光?这个女性的美,还归结到裁剪上去,就更明显了。把女性的美局限在化装、裁剪上,局限在女工上,是不是一种潜在的陈规呢?归根到底,在这首诗里,女性的美就是两点:第一,化妆;第二,裁剪。这都是贵族男性给女性规定的。
回过头来再看,那位教授说这首诗“歌颂了创造性的劳动”,是不是有点可笑,又有点可恨呢?这样的所谓的赏析,可以说是,典型的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
那个权威的教授,他只有一手,就是机械反映论和狭隘功利论。我们前面的分析,比他多了几手。我们的第一手,是审美价值论,第二手,文艺心理学,想象和联想论;第三手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话语陌生化理论,还加上我的补充和修正。是不是我就这么三下子呢?程咬金三斧头?不,我想,我应该比程咬金强一点。不信?我再露一手。用结构主义的一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的第三句,好像有点不一般。不知细叶谁裁出。谁不知呢?应该是诗人不知。可到了最后,诗人又告诉我们,是春风裁出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句法结构来看,全诗,基本上都是肯定的陈述句,但是这第三句,却是否定语气。这是偶然的吗?好像不是。在绝句中,第三句,改为否定句法,是常见的: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王翰《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杜甫《漫兴》: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杜甫《三绝句之一》: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
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杜甫《齐安郡后池绝句》: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杜牧《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白居易《重到城七绝句》:
年年老去欢情少,处处春来感事深。
时到仇家非爱酒,醉时心胜醒时心。
白居易《别草堂三绝句》:
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
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
王氏女《临化绝句》:
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
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
如此等等,举不胜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呢?到了第三句诗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改换了句法。从肯定的陈述句,变成了否定的语气(有时,是疑问语气,感叹语气,此处不详述)。这是因为,绝句每句七个字,四句都是如此,很容易造成单调刻板之感。而艺术形式是既要统一单纯,又要于统一单纯之中,丰富变化。故绝句的第三句,在语气上,做适当的改变,以求得语气转换的丰富。元人杨载在《诗法家数·绝句》中谈到诗的起承转合的“转”时说:“绝句之法,要……句绝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婉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4](P732) 统一中变化,单纯中丰富,是世界文学形式(乃至艺术)的共同规律。西方的十四行诗,在轻重抑扬交替上,是统一的;但,其中的句法,是变化多端的。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的绝句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绝句中的否定句式,还有一个功能,便于诗人从客观的观赏转入主观情感的抒发。
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把结构主义引进了,可是有几个人,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古典诗歌呢?没有。如今又跟着人家去喊不存在文学的新口号了。而另一方面呢,那些守旧的学者,仍然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唯物主义、狭隘功利主义的老一套去歪曲文本。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理论似乎更新很迅速,但,我们解读文本的水平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夹生的所谓理论窒息我们的审美阅读快感。
前卫的和守旧的理论家都轻视微观的文本分析,其结果,大学课堂上,中学课堂上,就产生了那么多的无效的、浪费的、愚弄人的所谓作品分析。连文本起码的内在矛盾都一无所知,连艺术在假定揭示潜在的心灵真实这样起码的艺术辩证法都不知道。再举一个例子。
《水浒传》里武松打虎,很经典。有一位先生很严肃地指出,武松打老虎,办法很危险,方法不科学。(笑)他说,《水浒传》上写,武松一只手按着老虎的头,大概左手吧,另外一只手就握起拳头来打老虎的脑袋,也许打了半个小时吧,老虎的鼻子就流血了,老虎给打死了。他说,这个方法不科学、不真实,因为老虎是猫科,猫科的特点是脊椎骨特别长。如果把头按下去,一般的动物,比如兔子,它的后脚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猫科的老虎,它的身量特别长,把它的头按下去,它的前脚无所作为——水浒传上写它只能刨出一个坑来,这是真实的。但它后面那两个脚干什么的?它不会闲着,肯定会拼老命,千方百计地翻过来,垂死挣扎,捣乱,去抓武松。在此情况下,武松别无选择,只能把另外一只手也按下去。一只手按头,一只手按屁股,其结果是僵持,就是这个样子。(众大笑)老虎以逸待劳,等你武松精疲力竭。最后是谁吃了谁呢?不言而喻。(众大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松打虎的方法是不科学的,骗不了有头脑的人。但是武松打虎却是一个经典文本,至今仍感染着我们。一般读者不会那么死心眼,去计较武松打虎方法的可行性、实用性问题,他们只是尽情体验武松打虎的丰富复杂的心情。这是一种享受,叫艺术享受。
艺术是一种必要的假定性。是假中之真。它和我们在假定上达到共识,就算武松把老虎给打死了,让我们来看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看到,这位武松先生自我感觉良好,一到景阳冈下的酒店,就自以为不是普通人,连喝酒都不受普通人的限制,一口气就喝了十八碗,又吃了好多牛肉,歪歪倒倒就往店外走,人家告诉他,这不行。怎么不行?有两点:第一,这酒是出门倒,透瓶香,三碗都过不了冈,如今你却喝了这么多。武松不买账,店家把官方的文书拿出来,他还是不信,并反咬人家一口,莫不是要赚我的店钱。后来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不相信群众”。(众笑)等到了冈子上,在一个败落山神庙前看到了县政府的布告,红头文件啊,(众笑)说是景阳冈有猛虎伤人,行路人等,须于巳午未三时结伴过冈。也就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大伙儿一起过冈。可当时是申时已过,快到酉时,也就是下午五六点钟了。这证明,真有老虎矣。武松这时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回去,好处是,生命不至于有危险,但有一条坏处,就是给人家笑话。《水浒传》写得明白:“须吃店家耻笑。”“须”是一定,吃是被,一定被人家嘲笑。你看这家伙,刚才是个小气鬼,现在变成了怕死鬼。(笑)武松受不了这个,就做了一个决策:继续前进。这样,武松就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上海人讲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众笑)走了一段,哎,没有老虎,加上酒又涌上来了,看见一块青石板,不妨小睡片刻。你看这个武松啊,又犯错误了,没有看见老虎,并不说明就真的没有老虎啊。这是唯心主义。说轻一点,麻痹大意。(众笑)还没有来得及睡下,一阵风来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出现在眼前。这时,武松几乎面临绝境,只剩下和老虎拼命一条路。人和老虎搏斗,有什么优势呢?没有。牙齿不如老虎利嘛,(众笑)指甲没有老虎的爪子尖嘛,连脸上的皮都不如老虎的厚。(众大笑,鼓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有一点比动物厉害,就是能制造工具。武松有什么工具?一条哨棒。这是金圣叹在评点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工具是什么?是手的延长。我打得到你,你够不着我。照理说,武松应该慎重运用这唯一可以克敌制胜的工具。可他用尽吃奶的力气举起哨棒,猛打下去,只听咔嚓一声,老虎没打着,却把松树枝打断了。松树枝断了,问题不大,只要哨棒在手,还可以继续打它个痛快。但是武松用力过猛,把哨棒给打断了。工具失去了长度,就没有手的延长的优越性了。这说明,武松在心理上是如何地惊惶失措。如果要算错误,这是第四个了。这下子,武松没有本钱了,横下一条心,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就用了那种不科学的办法,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说的“超常发挥”,(众大笑)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工夫,把老虎给收拾了。这无疑是一大历史的功勋,金圣叹说,武松“近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超人,至少在胆略和勇气上是如此。但是,这时超人武松变得实际了,他想,这老虎浑身是宝——加上那时又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众笑)——把它拖下山卖出一点银子来,至少可以作与老哥武老大的见面礼。可是怪事发生了,他把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居然拖不动了。这就表明,他超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但力量有限,而且胆子也有限。他这时想什么?还是趁早溜吧,(笑)如果再来一只老虎,可就危险了。他就一步步“挨下冈子去”了。哪知山脚下突然冒出两只老虎。这时,我们神勇的英雄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呢?《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武松的想法有点煞风景:“此番罢了。”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这下子完蛋了。(众大笑)一向自以为是不同寻常人的武松,是悲观到绝望了。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令读者关注的并不是武松打老虎的真实性、方法的可靠性,而是在打虎的过程中,这个超人的心理变化。他也会不相信群众,也会为面子所累,也会麻痹大意,也会惊惶失措,也会活老虎打死了而死老虎拖不动。再见到老虎,也会悲观绝望。这英雄的业绩是超人的,“近神”的;但他的心理活动过程完全是凡人的,金圣叹又说他是“近人”的。跟你我这样见了老虎就发抖的人差不多。(众大笑)
打老虎的假定性之所以是艺术,不是造谣,就因为揭示了一个真理:“近神”的、超人的神化的英雄,其实内心是“近人”的,和我们老百姓差不多。其实《水浒》中,还有一次写到打虎的,那就是李逵杀虎。李逵一家伙杀了四头老虎。但,在一般读者印象中,没有留下什么记忆。杀四头老虎不是更厉害吗?不。李逵在杀虎的过程中,只有一种情绪,就是为他妈妈报仇。你吃了我妈妈,我杀了你,不但杀你,而且把你儿子都杀光。这当然也是人的心理,但,这太简单了。比起武松那反反复复的又是人,又是神的众多层次,就显得单调,对读者内心深处处于遗忘状态的经验就没有多大召唤作用了,也就是说,感染力不够,文学性上不够档次了。
什么叫做文学性?这就是文学性。文学性就在二月春风似剪刀中的“剪刀”中,就在武松的多层次的心理变幻中。有什么神秘的呢?你征服了这个道理,作品就会动人;违背了,作品就逊色。文学性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争论不休呢?因为,他们没有本事分析出来。好像刁德一到了沙家浜,两眼一抹黑。许多理论家教授都把审美价值挂在口头上,但一到具体文本,不会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不出什么奥妙来。明明没有出息,但是,又不好意思承认。正好这时,来了一根救命稻草,洋大人说,根本没有文学性这回事,于是狂欢,歌声四起,山呼万岁。
(大笑,鼓掌)
在这样的狂欢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审美阅读本该具备的精神优势失落了。审美的战斗精神消解了。审美的情感升华遗忘了。这是理论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中,理论家舒舒服服地灭亡了,让我们来为他们白白活了一场而哀悼吧。但,我们不能仅仅为战友的阵亡而哀悼,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以审美阅读的优势精神和那些误人子弟的理论作殊死的搏斗。这样的历史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鼓掌)
收稿日期:2006—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