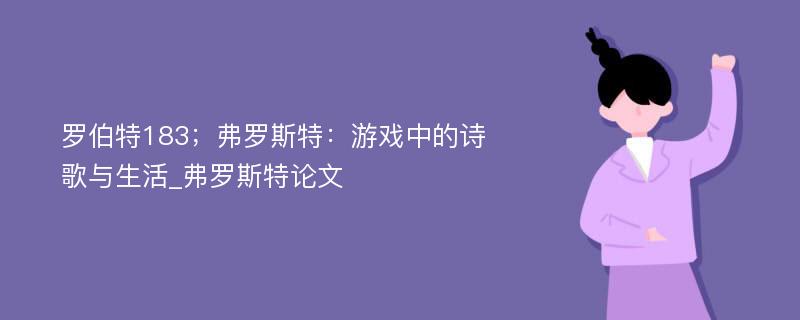
罗伯特#183;弗罗斯特:“游戏”中的诗歌与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斯论文,罗伯特论文,诗歌论文,人生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0)04-0009-05
在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中,拥有读者群最庞大、影响力最持久而且又最有争议的,当推罗伯特·弗罗斯特。弗氏既得到过鲜花与称颂,也遭到过攻讦与谩骂,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有名的两面神。一方面,他是“作品及和蔼形象感动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诗坛圣哲[1](P11),享有极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的创作水平和人格也受到过诋毁。马尔科姆·考利就曾在一篇评论中说到,美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从政治舞台扩散到了文学领域;文人们倡导所谓“积极、乐观、平和、‘纯民族’”的美国文学,并把诗作水平低下的弗罗斯特奉为他们的杰出代表;而弗罗斯特所获得的荣誉则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意味[1](P12)。弗罗斯特在自己指定的传记作家劳伦斯·汤普森的笔下更是变成了“披着人皮的魔鬼”[2](P12)。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虽然弗氏与艾略特一样成就斐然,但批评家们基本上把他视为保守的传统诗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弗氏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所做的独特贡献。
笔者认为,理解、研究弗氏的关键,是他自己极力推崇的“游戏”原则。在弗氏看来,诗歌是文学艺术范畴“游戏原则”最典型的代表。这个“游戏”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游戏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对立的双方。第二,游戏的策略类似暗喻,“以此指彼,以彼名唤此物,全在隐晦之乐”[3]。即,不论其自身有多么深刻的含义,都不能让人一下子琢磨透,而是必须给人以思考的余地,引出有关深刻或是肤浅的疑问。第三,游戏必须具有真实性。弗氏对彻底的游戏精神与假意的表演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讲,“我喜欢听人一辈子说,‘咱们来玩个什么游戏’。我不愿听人说,‘假装咱们在玩什么游戏’。要创作出精美的艺术,就必须用什么来游戏一番,比如诗歌中的词汇,艺术中的材料”[4](P32)。
笔者认为,弗氏用“游戏”原则创作出的不仅是精美而魅力恒久的诗歌,还有浸润了游戏精神的独特的生活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下四个问题的分析,说明“游戏”原则正是贯穿弗氏诗歌创作及其生存哲学的基本结构。
一、区域性——普遍性
以极具区域特征的人和物来指涉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是弗氏常见的游戏形式。总体说来,反映时代特点和风貌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面临的一个共同使命,但诗人们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以何种方式描述个人的认识和幽思。艾略特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城市,而弗氏则选择了远离城市喧嚣的新英格兰农村。这两位诗坛巨匠在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说明了诗人必须立足于一个自己熟知的小世界,必须确定一个属于自己且独具个性的观察现实的恰当视角。
在弗氏的游戏里,新英格兰成为折射困扰现代人的基本矛盾的独特空间。在弗氏的诗作中,田园风光、农活、讲方言的人确实占有相当的比重。从表面上看,新英格兰俨然成了弗氏的整个世界,成为他感兴趣的唯一空间。这一表面的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个有限的空间妨碍弗氏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也不能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声音不闻不问,更不能说明他的诗歌艺术缺乏完整性和普遍性。艾略特作为诗坛巨匠并不关心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生活,但没有谁认为他的艺术缺乏完整性。所以,问题不在于弗氏的区域特征是否与艾略特的完全一致,关键是,它是否真正折射了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弗氏从新英格兰的人、布满石块的山丘、黑暗的森林和冷沁的溪水中寻得最直接的物质对应,但也并未限于此、止于此。从新英格兰观察人生与单纯地反映新英格兰的生活是有区别的。弗氏不仅从新英格兰农村的山、水、人、物当中获得灵感,而且把这里当作了自己静观现代人两难境地的独特视解。
从这个区间产生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之物,并且“都是那巨大困境的缩影,都是那勇敢面对一切困难的意志的写照”[3]。但有趣的是,弗氏从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象征主义诗人。他不仅厌恶其中那种刻意追求的成分,而且认为象征主义会桎梏人的想象,从而扼杀一首诗的生命力[5]。他奇怪地把自己称为提喻诗人,因为在提喻中,局部可以指涉整体,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引出具有普遍性的意义[6]。例如,在《雪夜林边小憩》中,树林、农舍、白雪、马、冰、湖、佩铃、旅程等都是极普通的事物,但读者无法不因此生发出更多的遐想:个人意愿、外界的诱惑、社会的责任……在这里,普通而具体的事物负载了深刻而抽象的意义。所以,弗氏不仅成功地从一时一地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而且把一个个具体的地点扩展成更为宽广的天地,让这些有限的空间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弗氏曾宣称:“我包含对立面。我能涵盖众多的意义。我可以找到一段话来描述所发生的几乎是任何一件事情”[7],此说不谬。
二、传统主题——现代人的困境
用传统主题负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弗氏“游戏”原则的重要体现。在他的诗中,仍可见到一些传统的主题类型,如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但它们所传达的已不再是对于矛盾中某一方之偏好或成见。实际上,弗氏很少对事件的表面情况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他真正关心的,是本世纪的一些核心事实,即剥去了社会的、经济的表征后所暴露出的现代人疑惑、失落的痛苦感受。
例如,在常见的人—神关系的主题中,往往蕴含了弗氏对现代人矛盾的宗教思想的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超越无知、摆脱自身困境、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史。现代人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代科学却无法解答人们的全部疑惑。比如,它无法让人放弃对“上帝”或其他神灵的信仰,也无法说明,倘若上帝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冥冥之中操纵着人类命运的又是谁、又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把同色的蜘蛛带到那里,
然后在黑夜中把白飞蛾诱到那里?
有什么比黑暗的旨意更可怕?
假如旨意安心主宰这般细微的事情。
《旨意》一诗中白蛾与白蜘蛛的相遇,不仅是人类命运的客观写照,也真实地反映出人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势力面前的惶惑、不安与无奈。
此处,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中,人与自然不再是和谐的统一,而自然也不再是现代人精神慰藉的可靠力量。在《星星》这首诗中,星星代表了自然的眼睛。当人们仰望星空,寻求理解和同情的时候,星星起初似乎是要“聚拢……好像对我们的命运怀有仁慈之心”,但马上就变得视而不见:
然而既没有爱也没有恨,
那些星星像一些雪白的
密涅瓦塑像雪白的大理石眼睛
根本没有视觉的天赋。
自然是冷漠的,根本不在乎人的存在。它甚至可能变得异常残暴而危及人的存在,让人成为孤立无援的可怜虫。星星由对人类表示仁慈到“既没有爱也没有恨”的变化,说明现代人仍需清醒地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处境。自然界对人的存在是冷漠而可怕的,但现代人是否具有与之一决高下的勇气和能力呢?
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常见主题引出的,是现代人的人性特征与社会规范的巨大冲突。在《职责分明》一诗中,弗氏把现代社会刻划成一部炮制标准化产品的巨大机器。正如分工明确的蚂蚁一样,人必须依据苛刻的社会规范履行各自的义务。对社会分工的刻骨铭心的认识,导致了人的分化和隔离,使人沦为丧失了人类情感、只会机械动作的怪物。
在这种病态的社会里,“丧失了自己的人性,人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只蚂蚁。”[8]
可见,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存在常常是困难的。社会对个人施以控制,往往是对个性、创造力、自然生发的人类情感的无情剥夺,是社会价值对个人特征的极大压制。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呢?复杂的人际关系好比“……我们各长一只友爱与仇恨的手。/友爱之手把彼此紧紧相拉,/仇恨之手让我们苦苦争斗”。人类就是这样,生活在爱与恨、亲密与疏远、理解与隔阂的矛盾之中。《补墙》一诗也是这种矛盾心理的极好写照。读者首先听到了一个农夫的郑重声明:“有一股不喜欢墙的力量。”稍后又第二次听到类似的宣告:“有一股不喜欢墙的力量,/希望它垮掉。”尽管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修这堵墙,因为“他的全是松树,我的是苹果园”,但是,一墙之隔的邻居都关心修补界墙这一年一度的盛事。木讷的邻居更是抱住上辈的遗训不放:“篱笆牢,邻居好。”弗氏曾经说过,这首诗所讲的,就是最根本的人的悖论:“矛盾正是该诗的核心。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的悖论当中,存在于邻居和竞争对手当中,存在于人类的矛盾本性当中。”[9](P196)
弗氏这番话,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用诗歌关注现代人命运的重要声明。借助传统的诗歌主题,弗氏让他的读者认识到这样一个核心事实:人类生存具有沉重的悖论色彩。但是,人们大可不必因此产生悲观厌世之情,当然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盲目乐观,而应当勇敢面对困扰人生的一切悖论,认清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以理智、客观的态度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弗氏把人的悖论置于中心地位也正显示了自己作为现代诗人的高度敏感。
三、继承诗歌传统与发展现代风格
弗氏被认定为传统诗人,其部分原因是弗氏把创作风格带入游戏,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误解。除把新英格兰农村静逸的田园、树林以及农事劳作中的欢愉作为诗歌的主题外,他还沿用传统的诗艺,采用线性语言结构。他超脱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歌流派之外,对庞德、艾略特、威廉斯等现代派诗人所倡导的新诗运动缺乏明显的热情。
应当说,弗氏是在继承英语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风格。比如,在大量的自然诗中,弗氏显示了自己与以往的浪漫派诗人截然不同的自然观。浪漫主义赋予自然以人的情感,并把人与自然看作和谐的统一。弗氏则不然,从诸如上文提到的《星星》等诗中可以看到,弗氏把人的处境与自然视作两个相区别的层面。或许,浪漫主义的不足之处,正在于它实质上是在回避现实。显然,如果模糊人与自然的界限,人就无法通过考察自然的存在来反思自身的存在。
在游戏的遮掩下,弗氏小心翼翼、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自己的创新与发展。这种看似保守的中立思想和行为势必招致一些人对弗氏人格和文学立场的批评,但也确实是保护弗氏走出当时那个充满偏见的艺术环境的理想方法。“求新”是美国现代诗歌的主流。而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庞德和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的天下。他们强调诗歌自身的表现力,反对道德说教;主张改革英诗传统,代之以紧凑的肌理、词语反讽、多重组合、含蓄、象征和智性。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派也对这种诗学主张作了积极的回应。而弗氏则一贯认为诗歌应当“始于愉悦,终于智慧”[10],因此读者常能在其诗篇的末尾读到隽永的警句。所以在当时,他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新的诗歌流派作明确的评判,一边又反复强调自己能“以旧创新”[11],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求得发展。
这种“以旧创新”的典型例子,是弗氏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风格。他以清新自然、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语言入诗,从而把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传统推到极致。同时,尝试在诗文中准确而生动地使用真正的现代语言,创造性地提出了“句子—声音”(sentence-sounds)的概念,认为一个句子就是一种声音;它远比构成句子的单个词语所共同表达的含义更为深刻、更为丰富”[12](P193)。可见,弗氏十分看重声音在诗歌语言中的价值,并且试图在自己的诗歌中重构一种原初的声音。
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却在文学中丧失的,正是词语背后的句子—声音……试以在关闭的门两侧谈话的两个人为例,(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话音,但无法分辨他们所用的词语。即使这时词语不能传达意义,但声音却能,而且听者也能明白对话的含义。这是因为,每个意思都有一个特定的声音形象,换言之,每个意思的实在意义都对应了一个特定的声音,这个声音正是每个人出自本能所熟悉的……[13]
罗伯特·科恩曾提出,弗氏的“句子—声音”说与奥托·耶斯珀森在描述原始语言时所用的“句子—词语”、“声音聚结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2](P194)。不管怎么说,弗氏对原始的语言特征的认识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诗人在运用诗歌语言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弗氏主张“以旧创新”,全然没有那种抛弃英诗传统的激进,反而多了一分从容、自信与智者的风度,这也正是当时弗氏能立足于诗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游戏人生
其实,弗氏的游戏里没有任何玄妙、晦涩的内容,有的只是读者早已熟悉的东西。弗氏的高明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他把常见的视角、主题、表达方式等等带入这种游戏中,从而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极具弹性的思考空间。仔细想来,弗氏的生存方式也未必不是这种“游戏”原则的一个合理延伸。
例如,弗氏虽然生在新英格兰农村,但仍与城市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农村那种纯朴而宁静的生活,使他能充分感受到做百事通、多面手的快乐。而城市则让他对快节奏的生活、社会分工有了深刻的体会。他既是农民诗人,又是大学教授。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限制在农村或城市的唯一空间里,而是力图使自己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间保持平衡。同样,他可以做庞德等现代派诗人的朋友,但不愿以现代派自居,而是同他们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成为现代派的边缘诗人。
这种包含对立面的类比思维模式,显示出弗氏与艾略特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把现实世界看作是由不同生活层面构筑而成的一个整体。弗氏让我们看到了农村与城市、区域性与普遍性、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等关系的矛盾存在;艾略特则使我们认识了不同社会阶层、历史时期的对立。在这种类比思维模式当中,矛盾的双方没有强弱、高下之分;它们只是平行而且互为参照的不同生活层面。两位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弗氏能把这种基本思维结构成功地运用到个人的生活当中,从而表现出一个现代诗人彻底的诗性精神。
在这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游戏中,在这种诗性的生活模式中,弗氏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避免了表明立场和倾向时可能带来的尴尬,凸显了诗人保持客观中立、不走极端的心态。因此,弗氏游戏人生的突出特点,就是一种松散的约束,或者叫“中间道路”。每当弗氏面对生活中不同的存在空间,面对屈从还是独立的两难境地时,他总会表现出调和矛盾的高超技巧。
道理很简单。在现实的世界里,绝对的屈从或独立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弊端,其本身就是冒险。一个常见的基本事实是,要归属任何一个意义上的群体,个人就必须付出代价,要么放弃个人兴趣、爱好、自由,要么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完全离群索居的个人,不仅缺乏群体归属感,而且常被视为异类。
弗氏的游戏人生,并非视人生如儿戏,而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而作出的现实主义的选择。弗氏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曾说过,“有两种现实主义者”。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种现实主义者把满是脏泥的土豆拿给人看,以说明这是真实的土豆。另一种(包括他自己)则喜欢刷洗得干干净净的土豆。他认为,艺术就是要把生活刷洗、切削成形[9](P31)。可以说,弗氏的最终目标是要采取一种形式,并藉此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
正如弗氏用诗歌所反映的那样,客观世界既不是混乱不堪,也不是运行有序,而是介乎有序和无序之间,需要人类运用智力活动来加以认识。他还用这种辩证观来看待人类的命运,把绝望与希望、不幸与有幸、悲伤与快乐的矛盾存在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因此,他的艺术世界就像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既没有大喜大悲的极端,也没有盲目的乐观和悲观思想。在这里,他可以冷静地反思自身存在的命运,并且总能在看似不经意的游戏之中完成对自己深刻思想的传达。
弗氏身为现代诗人,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知之深则行之必至”。因而他以这种认识为准则,确立了自己极具游戏意味的生存模式。事实上,难以理喻的客观现实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诗性特征,而弗氏只不过是用了一种最为接近的游戏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个自相矛盾的客观现实的模仿。但他的模仿,绝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一种艺术的反思。他那独特的生存方式就足以说明现代人的困惑、不安和矛盾心理。弗氏把现代生活中的悖谬和难题客观地呈现出来,但绝不提供现成的答案。暴露矛盾、寓真理于平凡,反映了弗氏一贯的客观性。那种不带个人偏见的辩证思想,那种鲜活的大众语言,那种秘而不宣的睿智,不正体现了一种客观直陈的美学追求吗?弗氏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反映现代人的困境,恰好说明游戏过程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身陷“游戏”原则中的诗人与诸者,彼此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心智的愉悦。
结语
恰如威廉·普理查曾经说过的那样,“弗罗斯特用于说明诗歌的一个词是‘游戏’,因此他的行为与创作抑或都同这一见解有关”[2](P16)。客观现实的矛盾本质,对弗氏艺术思想的触动和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以自己的诗作和自身的存在方式对这种客观现实进行了寓真实于游戏、发人深省的模仿,而且对现代人的处境表现出真挚的关注。他从不同的角度诉说现代人心中的疑惑,并以游戏的方式说明,人们只有客观地看待各种矛盾,从容地面对一个远非完美的现实世界,才能走出自身的精神困境。弗氏的不凡之处在于,他能透过现代题材的现代化表征,看到现代社会的悖论本质。而且,他所依托的“游戏”原则中体现出的类比思维模式和含蓄的效果,正是现代诗歌的一个根本特征。莱昂耐尔·特利林曾用“可怕”一词形容弗氏这种奇特的现代性,认为可怕的感觉往往伴随新生事物的诞生而出现,是真正的现代诗歌的标志[14]。如果说风格通常体现的是一种基本的语言结构,那么,对弗氏而言,风格则是把这种基本结构彻底地运用在诗歌和诗性的生活模式中。在20世纪的美国诗坛上,能够像弗氏这样把生活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的诗人,可谓凤毛麟角。普理查曾经这样概括性地评价弗氏的文学生涯:“无论他做什么,也无论做得好与坏,他总能做得极富诗意”[2]。借用弗氏的诗句——“这些似花的水,这些似水的花”,似乎也应当这么描述诗人的诗歌和生存艺术:诗如生活,生活如诗。
收稿日期:1999-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