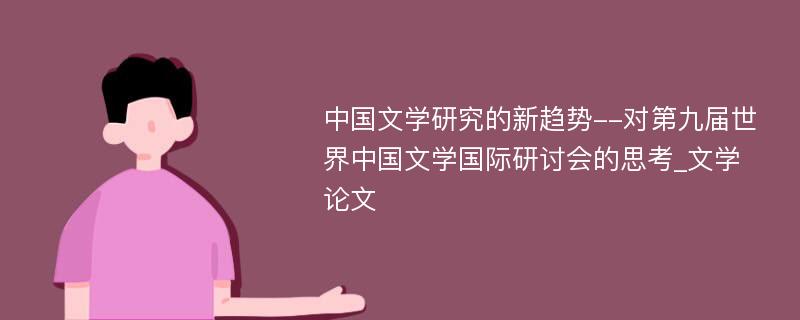
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关于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文论文,文学论文,第九届论文,新趋势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是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它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场戏,展露了新的研究趋向。
从1979年《当代》首开先例刊登台湾作家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风行当今大陆文坛;从1982年6 月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一届“台湾文学研讨会”,到1997年11月于北京召开“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华文文学创作区域覆盖面日益扩大的同时,华文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深化与拓展的态势。它不仅经历了研究队伍由小到大、由沿海到内地并渐趋遍地开花的外在形态变化,更重要的,这种研究发生了由单一到多向、由个体作家评论到整体文学面貌把握、由单纯的文本研读到深厚的文化意识观照的内在精神变化。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即是有力的明证。
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是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华文文学在其大本营——中国本土的集结,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在跨世纪之交背景上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围绕“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的总主题,会议分别以“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观察”、“汉语思维、地域推移与母体变奏”、“华文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华文文学的都市性与现代性”、“华文文学的文化学思考”、“华文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海外华文文学论谭”为题,深入探讨了华文文学的特征及发展前景。对于15年来的华文文学研究成就,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检阅和总结;对于走向21世纪的华文文学研究,它又具有一种前瞻的意义。跨世纪之交背景上颇具规模的研究力量的集结,显示出华文文学学科意识的确立与新的研究格局的形成。
有这样一些研究趋势值得人们注意。
其一,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观念已经成为共识。
华文文学作为世界上最大语种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十亿人口中使用华文的人占四分之一,而且遍布中国大陆之外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华文文学拥有广大的读者群。目前,60多个国家的1000多所高校开设了中文课程,许多国家的大学设有中文系。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从事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其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语种文学,皆难望其项背。当今海外有两千多位作家,近百个文学团体;在中国大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上各省市作协会员,则超过3万人。 与此同时,华文文学研究的日趋组织化和规模化,成为华文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就中国本土而言,从沿海到内地,从各地社科院到高等院校,纷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不断举行各种规模与形式的研讨活动。从全国第一届“台湾文学研讨会”,到后来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再至今天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仅就会议名称的变化, 也可以看出华文文学研究格局扩展的幅度。 不仅如此, 1986年,“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会议在德国召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教授与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教授,一同主编了《世界中文小说选》,在“大同世界”这个概念下把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放在一起,这种独创性标志了在“文化统一”宏观视野中的整合趋势。90年代以来,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还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内外学者目前正在酝酿成立“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台湾和香港地区先后举办了以“文学中国百年”与“香港文学五十年面面观”为题的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这表达了海内外学者渴望集合起来形成整体的共识。过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往往不研究中国大陆文学;而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学者,又往往忽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某一国华文文学的学者,甚至也不研究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这种区域分割、各自为战的情形,影响了华文文学整体的世界眼光的形成。有感于华文文学研究的整合趋势,与会者强调,用同一母语创作的华文文学既然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把握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放眼当今世界,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几大板块,即中国的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北美、南美和欧洲的华文文学。在这个总体格局中,大陆文学无疑是最大的板块,是华文文学同心圆的圆心。香港文学作为联系大陆与台湾、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最理想的交流中心,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愈来愈显示出它对于华文文学世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基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联系,同根同源又各具特色的华文文学几大板块之间互为影响,彼此参照,出现了新的创作景观。近年来大陆散文包括随笔、小品和杂文的重新兴旺,小小说创作的崛起,便与台港澳和东南亚有关创作的影响分不开。随着各民族文学交流进程的加快,不仅海内外华文文学将加速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和融合,而且华文文学与东西方各国非华文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不断加深。在世界逐渐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你走向我,我走向你,通过吸收、融合,变成新的自我,这是华文文学面向当今世界坚持民族性的开放姿态。鉴于此,如何在对各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做微观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加强对世界华文文学作为语种文学的整体研究和考察,特别是对不同板块的华文文学特色及互相影响做更多证同辨异的研究,乃至对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文学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成为当今华文文学研究势在必行的一种趋向。
其二,文化学的思考打开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回眸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工作,与会者深切地意识到,仅就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把文学研究同整个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使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深化。特别是随着世界文化西方中心说的解体,在未来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以华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再度兴起,将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现象,并给世界华文文学带来思想的活力和艺术的创意。由此看来,研究华文文学必须具有文化学的视野和跨文化的方法。如何以文化—文学的纽带,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从本质上讲是海外华人心系“双重家园”历程的结晶。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无法回避多种文化命题。这次研讨会上,特别引起与会者关注的,有如下内容:
(1)关于华文文学的“双重传统”。 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华文作家,一方面,作为“龙”的传人,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从思想感情到行为举止都受到民族文化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对故国家园的精神皈依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人生情结,“中国文学传统”成为华文作家创作的“灵根”。另一方面,海外华人赖以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又自有他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人情、文化模式和历史背景。海外华文作家在逐渐认同、吸纳居住国的生活经验和文学传统的时候,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借助中国人血脉中华族文化之灵根,融合所在国的“本土文学传统”,双重文化传统语境下的写作,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中华文化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新花果。离开了对“双重文化传统”的考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不同素质与特异色彩。
(2)关于文化冲突与变异过程中的华文文学定位问题。 华文文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与选择。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华民族文化与非中国文化的相遇,势必带来华文文学母题文化的保持与变奏。两种文化相遇,往往产生复杂的文化现象。正如金克木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两种文化共存有三种形式:一是平衡,二是压抑,三是归顺;两种文化不并存也是三种形式:一是混合,二是剔除,三是吸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语境。澳门作为一种鸡尾酒式的文化形态,葡国文化与华族文化相安无事,呈共存状态;而美国的华文文学,则是在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环境中生存。从60年代台湾作家白先勇、於梨华描写“无根的一代”的留学生文学,到近年来大陆作家小楂、严歌苓等人在跨文化背景上创作的“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皆可窥见身处边缘位置、饱经文化冲突的华文文本的写作意义。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化冲突与变异的过程中,还往往受到中心化与边缘化问题的困扰。对于处在华文文学中心地带的大陆文学而言,海外华文文学具有边缘的意义;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文学而言,以“少数民族”面貌而出现的华文文学又意味着一种边缘文学,这种情形构成它重要的边缘性。但它所涉及的不是文学优劣问题,而是地理文化视角上的差别,是所处的文化背景问题。中心与边缘是可以转化的,根据文化位置和影响而定。一方面,流寓海外的中国移民和华文作家,在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母题文化个性;在抵抗“边缘化”的过程中,融入本土的特色,产生影响日益深远、色彩纷呈的海外华文文学,并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调适、变化等提供了真实形象的文本。就此角度来看,边缘文学的文化传播与创造意义不可忽视。另一方面,过去研究界过于重视中心地带的华文文学,而忽略边缘地带的华文文学。随着90年代“中华文化圈”的提出,随着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照和研究的加强,这种情形会得到新的改变。
(3)关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文化身份认同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特征。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区》的精神,民族性和文化身份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实的需要在想象中不断地构成、丰富和重建。文化想象总是在对自我的想象、对“他者”的想象以及“他者”的想象不断构建。“实事上,‘华文文学’在习惯的使用上主要指‘海外华文文学’,它长期被悬置在与中国本土文学相分离的状态。……它们之间的分离状况,使得大陆文学自行其是,而华文文学则被流放于全球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顽强地去寻求文化的向心力,寻求文化身份的确证。”〔1 〕如果说,过去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怀乡”是作为一种文学母题来写,表现海外游子的家园情结;如今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怀乡”则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从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写,“家乡”的个人情感记忆也就放大为“家国”的集体文化记忆。
其三,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新景观。
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世界华文文学的言说者是大陆学者,而在历届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往往让大陆文学缺席,这就影响了华文文学几大板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次研讨会注重从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入手,传递丰富的创作信息,把握当今华文文学圈的总体特征。从与会者提及的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美华和澳华文学的发展态势来看,可以感知到不同板块的华文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风格异同以及创作的不平衡性。诸如民族文化母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延伸、补充和变奏,留学生文学题材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笔下的深化与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华文文学的都市性与现代性,以及不同性别背景下的女性文本的写作意义等等。
若以华文文学的都市形态而论,其中自有联系与比较的创作话题。都市化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必然趋向,正在不可抗拒地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都市意识所意味的正是现代人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在台港澳及东南亚一带,都市文学无疑构成当下的创作主流。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作为都市文化空间和文化品味产物的香港文学,认同于都市文化背景与个性,因而有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财经小说、框框文学这些颇带都市消费意义的大众文学的屡兴不衰。伴随台湾社会高度工商化的现实,都市文学早在80年代已经跃居台湾文学的主流地位。台湾的都市环保文学、都市工商文学、都市社会文学、都市心理文学,从都市生存环境到都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症结,从都市人的生存竞争到人性变异,都给予深刻的发掘与表现,诸如黄凡的《伤心城》、宋泽莱的《废墟台湾》、陈裕盛的《商战日记》、吴锦发的《消失的男性》等等。在东南亚一带的华文文学中,都市化写作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都市生活的多重价值决定了都市文学复杂的情感态度:它或表达了作家对都市感情上的排拒,或着重于都市弊端的理性批判,或体现了作家与都市文明情感和理智上的契合。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出现的由晚生代作家创作的都市小说,表明了与以往大陆都市题材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以迅速变化、色彩斑驳的当下都市生活为观照对象,写消费时代的欲望泛滥与都市化过程中的人性变异,表现出更多的表象化与欲望化倾向;他们竭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义无反顾地告别了过往的历史,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空间,表现出个人化写作的特点。从华文文学不同板块中发掘出来的都市化倾向,使得都市文学的整体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再以华文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来看,这次研讨会从女性写作的性别背景着眼,提出女性书写是一个比女性文学更宽泛的概念,它应该包括女性文学(带有性别特征的写作)、妇女文学(妇女写作与涉及妇女题材的宽泛视野,中性文学色彩)、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大陆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和澳门的妇女文学以及台湾的女性意识文学进行辨析。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来的鲜明大陆特征,表明了它与80年代张洁们女性写作的重要分野。一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与写作姿态的转变。出于对男权强大话语的恐惧,过去的女作家们竭力用“人”的概念逃避身为女人的性别特征;基于女性渴望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的反抗,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则通过女性主义者的自我宣称,进入一种“妇女写作”之境,于是有别于“公共话语”的女性“私语”写作突起,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成为典型的女性文本。二是关于女性躯体和性心理的描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进步带来女性解放,但男女平等的同时也几乎泯灭了男女差异,“文化大革命”将这种情形发展到极端,诸多的“铁姑娘”即是写照。到了社会不断开放、发展的90年代,女作家开始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正视和欣赏女性躯体,并把她视为承载女性灵魂、激扬女性写作的一种优势。与此同时,女作家们还努力摆脱“高喊女性解放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常常以性爱故事为载体,来解读女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揭示女性成长过程中深层的性心理与生命意识,因而她们笔下写到的异性恋、女同性恋和自恋现象,颇有些离经叛道、骇世惊俗的意味。
与这种锋芒犀利、色彩浓烈的女性主义文本不同,澳门的女性写作则显示出一种温和的态度。一则它不涉及女权主义,更多充满了温情色彩。澳门的妇孺、平民教育开展得比较早,她们获得思想解放早于内地妇女。女性虽享受人格独立,仍然重视传统责任;女性写作多为中产阶层的业余为之。这种生活有所保障、男女平等状态下的个人化写作不再以两性征战为主要观照对象,自然失却了激烈的言辞。林中英、林惠、周桐等人的作品,即便写到女性的切身问题,也往往是温情意识的观照,而非女性精神的投射。二则澳门女性文学充满“中介色彩”。女作家们多关注男性所关注的生活内容,而不只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她们希望做一个“中性人”:既有男性的气质、能力,以适应变幻多端的社会;又保持华族女性的传统美德,以珍视女性的原始美质。
对于台湾文坛而言,80年代以来虽有李昂、吕秀莲、李元贞们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更有廖辉英、袁琼琼、苏伟贞、朱秀娟等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写作。后者往往从台湾工商社会中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角色冲突等问题切入,来表现女性的自处和两性相处的矛盾与调适,揭示台湾妇女由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这其中虽然描写了两性之战的焦灼、困惑与艰苦,但最终目标不是一味的两性对抗,而是通过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唤起女性人生的自觉与自立,提高女性自处与两性相处的调适能力,创造“合理化的两性关系”。由此看来,不同地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写作,对于华文文学中女性书写时代的构成,有着多种角度的丰富、补充和参照意义。
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建立规范的学科意识与研究秩序已成为必然趋势。对于昨天而言,它无疑跃上一个新的层面;对于明天而言,则任重而道远。我们所期盼的,是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以新的姿态和更高的境界,步入世界民族文学之林。
注释:
〔1〕陈晓明:《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