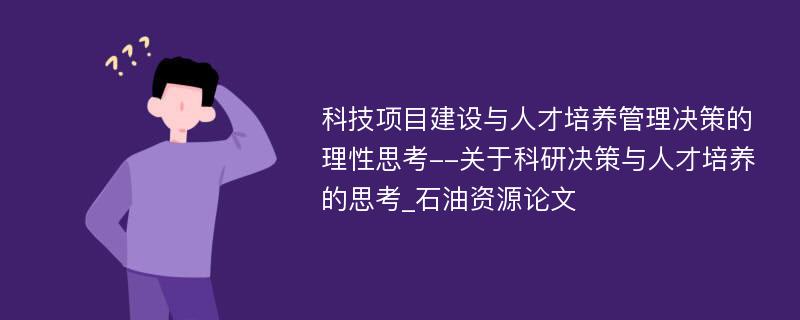
关于科技立项和人才培养管理决策的理性思考——Thoughts on Policy——Mak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Projects and Competent Personnel Training,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培养论文,理性论文,科技论文,Policy论文,Thought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前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决策,自有决策者的道理。但至少在某些国家级项目的上马和某些政策出台的决策过程中可能在考虑自然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以及我国的实际国情方面有不周的地方。下面列举两例,谈谈笔者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国家级科技项目立项
“九五”期间,关于天然气研究的千万元以上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至少有两项,分别由煤炭部和石油系统主管。最近,政府某机构又在组织专家论证,是否再上一个天然气方面的国家级项目。
我国的科研项目可能没有像楼堂馆所那样多的重复性建设问题。从天然气发展的角度和趋势来看,多上一两项这方面的科研项目本也需要,无可非议。可是科研经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很小。因此国家立项要从规律、国情、科学基础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从煤、油、气形成的理论来看,对某些上马的国家级油气研究项目的设置大有可商榷的地方。
早在1950年哈巴德(Hubbard)和鲁宾逊(Robinson )在对英格勒(Engler,1913)早期的石油形成机理略加修正后提出, 分解反应开始时气与沥青同时生成,其反应式如下所示:
干酪根→沥青+气→油+气+残余碳。
从前苏联天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提出油、气和煤同出于一源以来,到海相→陆相→煤成油理论的出现,反映了煤、油、气在某种程度上说确是密不可分的一家。当前石油地质研究中的化学动力学、有机质类型和模拟盆地热史研究方法,都源自克伦韦尔(Krevelen,1951)、 卡威尔(Karweii,1956)和洛巴金(Lopajin,1971 )的煤田地质学研究方法。60年代以来,煤岩学上普遍应用的许多研究方法,如显微组分、荧光分析等煤岩分析方法,逐渐修改成适合研究分散干酪根的方法后,才渐渐地证明了现今举世公认的干酪根生烃模式,使石油地质理论有了质的飞跃[1]。同样,石油地质研究的深入, 也扩展和促进了煤田地质学的发展。不同学科的渗透、交叉和联合,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这是一般的常识,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设立煤、油和气同时研究的大项目,既是经济效益的需要,也是自然规律的需要,人为地将其隔立起来分项目研究,既不经济,也难以达到更高水平。作为部和总公司一级决策的的项目,有其自身实际的需要,如设立煤层气开采研究项目等,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决策的有关这方面的项目,无非是想在更高层次之上上一新台阶,在理论上对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起作用,分立项目显然难以做到合而攻之,难以达到高水平。这些简单道理,本来是显而易见的。
在设立科研项目的决策上,我们何不看看和学学近期电视上播发的美国和欧盟各自在航空领域采取的联合行动。这既是趋势,也是实际的需要。我国的冰箱、彩电等工业产品形不成世界先进水平,除了与起步晚等其它众多原因有关外,恐怕与上述同一病源也不无关系。
从煤、油和气勘探和发现的实践来看,更应如此。 以新疆为例, 80年代以来,煤炭部投入找煤的勘探费用很可怜。因此,全国最近一次的煤炭资源预测所用的新材料,主要来自石油系统。从塔里木等盆地油气勘探的结果来看,其中很多喷油的钻井中也有气,两者并不是分而找之,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也大同小异,无根本区别。所以,作为国家级设立的项目,理应将这三者合而为一,设题研究。
就客观实际来说,容易找的能源,已经找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需要多学科配合和协作的难题。地矿部有多年丰富的前期勘探石油的经验,而石油系统有续后的丰富经验,煤炭系统也有自己几十年的风雨实践,几家的合作,将产生很大的合力。塔里木地块石油勘探发现的黄金时期,从内陆找出海相石油,就是地矿与石油两家合作的典范[2]。 作为国家级的立项决策者,应该充当“红娘”的角色,成为联合多家使其产生合力的媒介。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本应合而攻之,实却分而立之的设题局面?如何改变这一现象?深层次的探讨也许太复杂。但简单解决办法却有一个,这就是:但凡参加论证的专家既不应该也不能承担或涉及该项目的任何实际工作,也即建立专家论证回避制度。让参加论证项目的专家又负责搞此项目,显然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大原因之一。
二、“爱迪生”或“瓦尔德内尔”效应与跨世纪人才培养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培养高级人才和跨世纪人才的途径,如国家有“百千万”,各部、总公司又有“跨世纪人才”。这种形式是培养人才的最佳途径吗?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吗?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已从误区中走出来了,逐步采用就近入学的方针;选拔出国培养的方针也已经改变了,因为投入多而回报少,为此,我们交了不少的“学费”。难道在培养21世纪人才政策上还非要再交了“学费”才能有所长进吗?
从公认的人才标准来说,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可算是人才。综看获奖者,可又有几人能二次获奖?况且,他们的奖一般都是在获奖成果作出后多年才取得的。从一般的规律来看,大多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其一生有价值的创造性成果大概只有一次,只有极少数人能有二次或多次的创造。从世界范围来说,第一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孜孜不倦,在科学园地上辛勤耕耘,也就以相对论而闻名于世,流传千古。多产的当然也有,如爱迪生,一生发明不断。然而,后一种人才在所有的领域也只是凤毛鳞角。我们的国家需要大批人才,才有可能使21世纪真正成为中国的世纪。第一批获得几十万资助的人才,是否果真能超越他们曾有的成果而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取得进展者主要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学生或课题组中的其他成员?难道出了几部书稿,有了一批涉及非理科领域的文章就算有新创造吗?就算培养了21世纪的人才了吗?可能在第一批资助的人才中,确有许多已被造就成了帅才,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日理万机操劳群众的衣食住行,也能文理学科专著文章连连发表,但如何能保证在专业领域永远挂帅呢?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督促和要求那些曾创造辉煌业绩的人才和今日的帅才成为各学科领域的“伯乐”,发现和培养更多潜在的年青的人才。最近电视上和报纸上宣传的,冠以“东方科学之星”的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研究所所长陈竺的成长、表现是这方面的最好范例。老一辈为他当了“人梯”,他才44岁,在国际上成了名,他又为30出头的新人当了“人梯”。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里,新人不断涌现,许多年轻有为的学术带头人出现了,形成了一个在治疗白血病的国际前沿争创第一的群体。现代科学研究往往是学科交叉,需要大协作,需要团队精神,更需要思想极少束缚、敢想敢干的年轻人[3]。 只有不断涌现年轻人,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常盛不衰。我们要大力资助的应该是象陈竺这样的带头人,能带出在国际舞台有一席之地的一大批人才,而不应该只有出资让一两个个人成为21世纪的学术“领头羊”这一种方式。由于我国的国情所致,上述的跨世纪人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有许多走样,违背决策者初衷的地方。这将给占绝大多数无缘得到资助的科学工作者带来无可估量的负效应,也会使一大批有希望真正成为21世纪学术带头人的年轻一代受到不利影响。这决非危言耸听!北大方正集团总裁王选教授在电视上说得好:“看我的成就,就看20年后,经我培养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超过了我,有多少人可在这一领域的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据世界一般的人才成长规律,恐怕王教授的一番话,是很值得一些握有未来人才沉浮大权者们深思的。我们在已是人才的身上“挖潜”,还不如让他们慧眼识别如今还默默无闻,来日能一鸣惊人的未来可造就之才,这或许更现实也更有效益。但愿我国人才如雨后春笋,而不仅是林中孤竹。瑞典有“常青树”瓦尔德内尔,是瑞典的骄傲,同时也是瑞典的悲哀,因为他们没有像我国这样,乒坛人才辈出。我国能在世界数学、物理等奥林匹克赛上获奖,但不能就此而使我国成为科技发展的大国。仅造就少量的尖子人才,于泱泱大国的科技发展,不啻是杯水车薪。我们的方针应重点放在如今还默默无闻,将来能有机会腾空展翅的一大批未来的年轻人才身上。盼望21世纪的科技大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切莫要仅限于从我们所设想的“人才工程”中去产生人才。
由此想到近期出台的国家科学技术出版基金资助文件,文件中所资助的重点对象,恐怕大多数不是“扶贫”的对象,而是已在国家各种政策扶持下,在科技战线上“先富起来者”。他们大多不可能是实际意义上的在学术上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对象。在笔者看来,该资助的应该是众多的学术上富有创造性,但可能在21世纪世界科技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现今仍是默默无闻的小辈。我国有句老话:千里马常在而伯乐不常有。但愿在来年的文件上,能看到类似王选教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