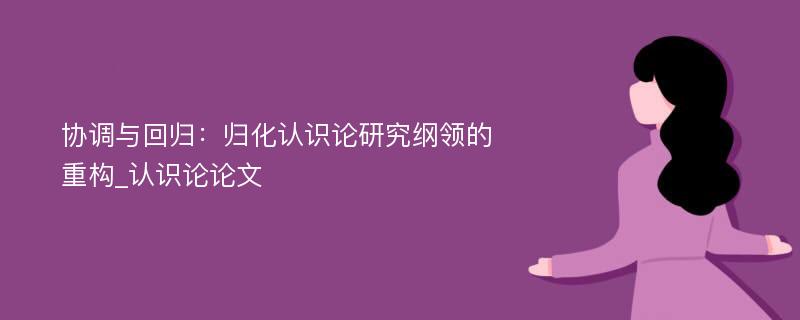
协同与回归:自然化认识论研究纲领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纲领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2—0009—04
自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于1969年提出自然化认识论问题以来,认识论问题再次成为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大的范围看,有关认识论研究纲领的重建主要有两条进路:首先是规范的进路,其次是描述的进路。目前两种研究传统出现了一种协同与回归的迹象。本文主要分析自然化认识论的转换命题,希望澄清与解决如下两个问题:首先,考察转换命题本身存在的困境与可能的解决出路;其次,自然化与规范化出现协同与回归的可能性条件。
1 自然化认识论的转换命题的终结与出路
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的出现,是继以奎因为代表的激进的替代命题失败后出现的一种温和改造认识论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原有的认识论框架内力图用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的成果来改造传统的认识论。转换命题的核心集中在对可靠性的高度关注上,而以戈德曼为代表的可靠论者,进而把可靠性的分析用在对不同认知群体的划分上,这样就出现了个体间论者(interpersonalist)和个体内在论者(intrapersonalist),而戈德曼对个体间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进而倡导个体内在论的主张。通过对知识产生过程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说,完全排除个体间论是不可能的,因为知识是公共的,它不是私人的,知识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由共同体决定知识的产生与确证是知识发展的一个不可少的步骤,当然我们也承认私人知识的存在,这是由于个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对此,威廉姆·阿斯顿(William Alston)曾指出:我甚至不能断定那些很少有明显错误的主题即被确证地相信的P是能够被成功地确证的信念。许多人确证地掌握许多信念,由于他们没有掌握一些理智或言辞上的技巧,他们不能确证那些信念。因此,事实上被确证不依赖于任何现行的或可能的确证活动。由此可知,确证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作用,具体的确证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对确证的阐释上,并不像有些转换命题哲学家所讨论的那样绕口。回忆一下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如何确证一个信念它涉及许多方面:首先要自己相信(个体内在论),然后向别人介绍,争取得到别人的支持与理解(个体间论),这两个过程中都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方法与标准,虽然两者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要确证一个信念,并最终使它成为知识,那么这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因此戈德曼简单地攻击一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对于阿斯顿的观点:即假如一个人为了确证地相信P,而又从不说明他确证地相信P的理由或证据,那么对于语境论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阿斯顿陷入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承认有无法说出理由的确证,因此不需要给出一个人的信念是被确证,又要求确证必须给出理由,这是不可能的。对于阿斯顿给出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我们认为也是不能成立的,他的例子是:小孩子和动物都能知道一些确定的事情,但是由此认为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断言给出理由是愚蠢的。即便有一些已经被确证的知识,但是它们不能通过诉诸给出或能够给出理由的活动来确证。对于这个例子,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动物和人是不同的种类,以此来类比是不恰当的,换言之两者根本没有可比较性,动物没有语言,无法形成有效的命题,而人则具有这种功能,动物的确知道许多有用的知识,但那是千百年进化的结果,动物是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而人则主动接近与建构这个世界,即便是孩子在儿童期也开始形成思维与推理能力,这点已经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力地证明了,而动物则没有体现出这种主动的学习与推理的能力;其次,卡尔·吉奈特(Carl Ginet)则认为:“即使对动物和小孩子应用确证概念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诉诸理由来追随确证概念通常也是不相关的。他更愿意把动物的和孩子的行为看作是相反的主张,即没有信念是知识除非它是被确证的。”[1] 作为个体间论者来说,他们不会采纳吉奈特的观点即所有的命题知识需要确证,并且只有在这种场合下确证才是必要的,确证总是主体给出理由的活动。总之,戈德曼的可靠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阿默德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戈德曼的可靠论失败了,可靠论作为一种确证理论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它既没有给喜欢个体内在论者的确证理论提供满意的说明,也没有对反驳个体间论者的观点给出满意的说明。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信念是如何产生对他们的知识状况是确证的还是没有确证的是没有关系的。”[2] 对于把可靠论作为确证的理论还有许多批评,大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种形式:①循环论的辩论;②模糊性辩论;③葛梯尔辩论;④实践标准的辩论;⑤可靠论蕴涵怀疑论的辩论;⑥建立可靠性方法的辩论等。由于个别的辩论已经有很多说明,本文将要就②、⑥的内容简要进行一些分析。
按照阿默德总结的看法,所谓的模糊性辩论是指:可靠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可靠的信念制造机制、方法和过程的概念是不清晰的。这种辩论很容易理解,因为这里涉及产生可靠信念的三种主要方式:机制、方法或过程,任意挑选一个都是很难给出没有歧义的界定。仅就方法而言,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人们坚信一个成熟的方法它趋向于产生的真信念比假的信念要多得多,这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也是归纳的一种表现,然而我们不能保证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这种方法不会产生一个不宜检测的假信念,虽然我们无法具体说出在哪一天会产生假信念,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时刻存在,这也是归纳论证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休谟早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必然性可以保证从过去的经验到将来的经验的过渡。我们敢于从已知的东西进入到未知的东西是习惯的结果。因此,以方法来求得信念的可靠性,显然基础是不牢的。对此戈德曼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建立可靠性方法的辩论,矛盾主要在于可靠论者把可靠性方法凌驾于科学之上或者独立于科学之外。问题在于可靠论者所依赖的方法真的可靠吗?大多可靠论者之所以如此强调可靠性的方法,是基于现代认知科学发展的成就,正如齐曼指出:“已经知道大多自然语言给颜色命名时依照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方案——这大概依照在人眼中的柱细胞与锥细胞,视网膜色素和神经感觉器官生理学机制的普遍性。很难相信,在许多不同的人的精神区域,相同的潜在关系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的表现,会完全是巧合:我们假设,他们必定用相同的方式感觉此类事物。”[3] 但是,由于人类既具有很大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差异,差异的存在,就已经打破了建立可靠性方法的可能性。
2 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的拓展与约束
关于可靠性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进路没有涉及,即把可靠性作为知识论的基础,这种进路是否可行呢?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哲学家Fred Dretske和D.M.Armstrong,对于德雷斯卡来说,以往的争论,即知识的确证主要地是一个给出理由的活动,坦率地说,这点对于人类的知识来说是不必要的。人类的知识所需要的只是可靠地产生的真信念,或者真信念是由适当的信息引起的。根据他的这种说法,必然得出:人类的知识不需要主体认知地掌握或觉察到信念是可靠地产生的,也不需要主体有能力去显示、或给出理由去证明信念是可靠地产生的,或经由适当的信息引起的。因此,德雷斯卡认为他的知识定义比传统的基于(JTB)知识定义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在处理葛梯尔反例时,他可以避免一系列的“诡计的包裹”(bag of trick),因为在葛梯尔的反例中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人确证地相信一个假信念。在德雷斯卡看来,假如一个真实的信念是由恰当的信息引起的,而且这个信息从不会是假的、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允许一个人确证地相信一个假命题。这样德雷斯卡就完全抛弃了来自个体内部的对信念的确证要求,他称自己的主张为外在主义(externalism)。对于确证他反问到:假如没有任何附加的益处,确证又有什么好的呢?正如他所说:“确证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假如它不影响一个人去相信的意愿,一个人自愿地去执行他所相信的,而不是信念的可靠性指导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确证还有什么可能的价值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发现了确证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看见(或知道)的事实不相关的原因。”[4] 这样,德雷斯卡就完全放弃了可靠性在确证中的作用,转而用可靠性来重构知识的定义,对于他的外在主义的观点也遭到了许多人的严厉批评,也许知识的可靠性理论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
对于德雷斯卡的强外在主义,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强调在德雷斯卡的观点上,加上内在论的限制,也就是说主体不仅必须要意识到、或者一定程度上认知地掌握什么是完全确证一个人的真信念,而且主体有时能够描述或展示什么是他所确证的信念,增加这些限制将取得很好的优势或者好的结果。但是,德雷斯卡却认为增加一个限制性的条件是不必要的,然而在他的论述中却存在一个严重的不一致,即一方面,为了表明他的断言是被确证的,确证对他来说又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否定增加内在论的限制性条件有什么好处?其实,这里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说人们知道他们实际知道的东西,在强限制性缺席的情况下,当我们问“你如何知道”时,他们不能给出任何理由这是合适的吗?显然,德雷斯卡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德雷斯卡的观点,阿默德指出至少有以下三点缺陷:“首先,这种建议的定义违反了我们通常直觉上关于什么是知识的含义,主体不能给出劝说性的理由来显示他知道信念P,因此,我们不能说也不愿意说,他知道P;其次,在内在论的限制性条件缺席的情况下,我们去发现谁知道的能力被严重的束缚;第三,德雷斯卡的极端问题事实上要求把给出理由作为既是知道也是相信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些内在论的形式是可以接受的。”[5]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发现:无论把可靠性作为确证基础的论证,还是把可靠性作为知识定义的基础都是存在严重理论困难的,换言之,单纯从内在论或外在论来考虑问题是行不通的,可靠性本身作为认识论转换命题的核心概念,自身就存在问题,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可靠性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可靠性源于主体自身的一种能力;其次,可靠性来自于一种方法和过程的保证。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则是外在的。因此简单地把可靠性单纯地从一个层面发展到极端,也就出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解决可靠论面临的困境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应该建立在分类与综合上,这也是转换命题可能的出路所在。
3 协同与回归:自然化认识论发展的可能之维
如果说转换命题是认识论自然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这个自然化的进程已经把认识论的发展道路引向了一个死胡同,应该不为过。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转换命题的核心概念:可靠性,最初来源是人的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带来的,自此,转换命题开始了由里往外的发展。客观地说这个研究进路已经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换言之完全的自然化无法完成认识论的使命,那么从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a reliable belief-making mechanism)往里追溯将是何种情况呢?这就涉及到元认识论的问题。关于认识的发生目前有两派理论:即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它是建构性;另一种则是历史悠久的先天论,这可以从当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中可以感觉到。1965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一书,其中提出的两组概念很能说明问题:“语言能力/语言表现,语言能力是人先天具有的独立能力,它通过学习某种或某些语言展现出来。”[6] 现在的问题是完全自然化已经证明无法完成认识论的使命,当代认知科学无法深入下去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回归传统的规范认识论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里的回归不是完全退回到传统的规范认识论范式,而是期望把自然化的进路与规范的研究进路进行协同,只有这样才能为重建认识论开辟新的研究范式。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J.A.福多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的认识机制,他提出了心理的模块理论(modularity)。他把人类认知过程从心理功能角度分为三类:“传感器、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输入信息流会依次接触到这些机制。这三类机制相互独立,但是却无法穷尽认知理论可能提出的各种心理机制类型。”[7] 在福多看来,输入系统是功能特异性的,这点很重要,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输入系统的功能是让信息进入到中枢加工器;输入系统通过对心理表征的编码来为中枢机制提供操作范围,它们是传感器的输出与中枢认知机制之间的中介。因此,他把输入系统看作是一种心理模块,这种模块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知的封装特性,有了这种封装特性,所以能够保持观察的客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输入系统的操作是强制性的。正如福多指出:“证明输入分析和背景之间的那种相互作用本身并不等同于证明前者的认知渗透性,你还需要表明自上而下的影响发生在输入系统的内部。就是说,你需要表明反馈信息不仅与输入加工的最终结果有相互作用,而且与输入加工中间水平有相互作用。”[8] 由于模块的范围特异性,这样认知渗透就发生在知觉辨认阶段,而很少能够在封装的模块内部发生作用。更为有趣的是,无意识总会伴随有某种封装性,一个无意识信念不能在有意识的推理中充当前提。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眼睛的眨眼、情急之中的脱口而出等等。在福多看来,目前的认知科学是关于输入系统的科学,信息封装无疑是这类系统的普遍特征。因为输入系统不与中枢加工系统等交换下信念信息(所谓的下信念是指说母语的人与其语言的语法之间的认知关系)。一般来说人类的输入系统有六个,分别是传统的感觉/知觉方式: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和语言。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寻找证据证明输入系统的范围特异性,只要有这方面的证据,就可以为先天论认知方式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众所周知,从实证主义开始到逻辑经验主义,这些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取消先验论的存在,由此才导致认识论的自然化过程逐渐升级的现实。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人类的认知过程是极其复杂的,目前的一些实验已经有力地证明这种范围特异性的存在。如福多曾引用哈斯金斯的实验证明:“只有受到相对限制的刺激类型才能控制对它进行加工的机制的开关,证实了输入分析器的范围特异性。”[9] 福多关于模块的范围特异性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福多与乔姆斯基同样坚信先天性的存在,这是无可置疑的。
1992年英国心理学家A.卡米洛夫、史密斯发表了《超越模块性》一书,试图继续深化认识的领域问题,她的立论基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福多的先天论的综合,史密斯指出:“皮亚杰主义和行为主义理论都不同意婴儿有任何先天结构或领域特殊性的知识。他们各自都只承认某些领域一般性的生物学上规定的过程;对于皮亚杰主义来说,是一组感觉反射和三个机能过程(同化、顺应和平衡);对行为主义来说,是遗传的生理感觉系统和一组复杂的联想规则。”[10] 因此,她提出了人类心理包括两类领域: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而她的领域特殊性相当于福多的模块,所不同的是福多的模块是封闭的,而她的领域特殊性则是开放的。她给出的证明领域特殊性的例子,如脑损伤病人,往往只丧失一种或几种功能,而不是丧失所有功能,就很能说明脑内领域特殊性的存在。再如一些白痴天才的案例,这些人脑的很多功能都处于有问题状态,而某一方面则具有非常好的功能,这就很能证明领域特殊性的存在。史密斯认为:“皮亚杰的观点和我这里的观点的主要区别是,我坚持认为存在某些引导后成的先天规定的领域特殊性的倾向。幼小婴儿在发展开始时所具有的要比皮亚杰所假定的多。”[11] 如果领域特殊性或者模块存在的情况下,如何阐释人类的认识?这可以称为元认识论问题,换言之,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史密斯给出的表征重达(RR,即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认识发展模型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简单地说,她认为表征重述是心理中的内隐信息以后变成心理的外显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先是在一个领域之内,然后有时在几个领域之间。它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动力之源,它同时受内源性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发展的RR模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水平I,表征的形式是对外在环境中的刺激进行分析和反应的程序。若干制约对在这个水平上形成的表征附加物发生作用,即“信念以程序的形式进行编码;程序似的编码按序列规定;新表征独立储存。”[12] 由此可以看出在表征水平I,所含的信息是内隐的,还没有办法被别的系统利用。其次是E1,水平E1的表征是水平I以程序方式编码的表征重新编码为一种新的压缩形式的结果。E1表征的特点是缩减的描述,它失去了以程序方式编码的信息的许多细节。我认为这可以看作逐步抽象化的表现。第三个阶段是E2/3阶段,在史密斯那里,只有超过了E1的各个水平上,意识的通达和言语报告才有可能。在E2水平上表征可通达于意识,但不能言语报告,只有E3才可能。在水平E3,知识重新编码为跨系统的代码,这种普遍形式被假设为与自然语言非常接近,很容易转化为稳定的、可交流的形式。对于RR模型,我认为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表征化阶段分为四级更合理,即需要E4的存在,换言之,E4代表了一种人工语言的表征,因为语言学家索绪尔已经对语言与言语进行过有意义的区分,如果没有人工语言的表征,人类知识的存储就无法完成,甚至在知识的传递中也将面临困难(波兰尼的难言知识与明言知识的区分,也间接证明了E4存在的必要);如果人类认识的表征达到E4阶段,才能形成有效的观察语句,并在这个基础上对观察语句进行真假判断,否则,将导致RR模型在婴幼儿阶段向成人认知方向的转化缺少了必要的联系环节;其次,由于存在先天的领域特殊性,那么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的判别问题,仍没有得到有力的说明,我认为人类先天的领域特殊性只能保证认知的框架与方向,而真正能够起到产生可靠信念的机制来自于在先天规范的引导下的不断试错过程,这点从对婴幼儿认识的发展的观察,可以证明。第三,认知的扩展机制,史密斯和福多的解释,明显存在问题,在这点上,皮亚杰的同化、顺应与平衡在解释上可能更有力。第四,模块或者领域特殊性的构想只能算一种科学假说,目前还没有神经解剖学的有力证实,正如菲奇(R.H.Fitch)与同事在1997年《神经科学年鉴》中指出:“经验证据表明,人类实际上不具备仅由言语激活的神经模块,数据的吻合表明,语言处理由神经生物学机制支持。”[13] 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能完全否定模块或者领域特殊性的存在,毕竟这里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现代的神经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能力发现这些组织的存在。更何况这些假说能够解释许多发现的事实呢?
4 结语
自然化认识论在转化命题的改造下的失败,又一次说明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坚固的壕沟,填平这道壕沟还有许多路要走,但这种理论进路的意义在于,通过现代的神经心理学、认知科学的进展,我们对人类的意识以及信念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研究也告诉我们,由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过程和方法产生的信念在某些时候对于一个人知道P是不必要的。正如约翰.波洛克指出的那样:“可靠性对确证不是必要条件,但是很有趣的是,缺少可靠性将使确证无效。”[14] 为了扭转认识论研究的误区,我们需要跳出单纯的自然化思路,使认识论的研究从描述向规范的回归与协同,将为认识论的研究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
收稿日期:2006—07—11
基金项目:本课题是山西大学郭贵春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的子课题:自然主义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