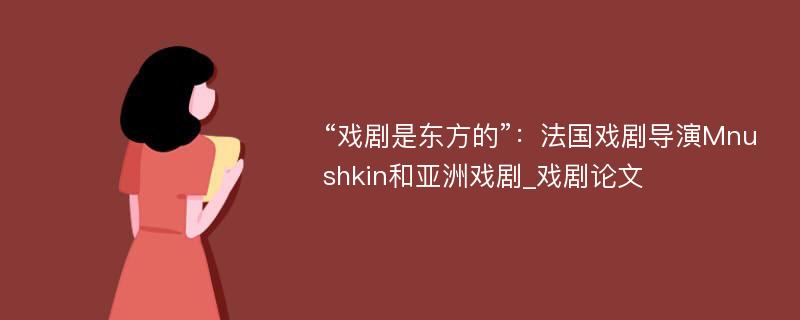
“戏剧是东方的”:法国戏剧导演姆努什金与亚洲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法国论文,亚洲论文,导演论文,姆努什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里娅娜·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 1939- )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乃至世界戏剧舞台上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导演之一,由她创建的太阳剧社(Thé?tre du Soleil)也已经成为60年代以来最活跃和影响最大的剧团之一。在四十多年的戏剧实践中,太阳剧社已经推出一系列产生了国际影响的演出。这些演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希腊悲剧的演出,吸收了日本、印度、中国和巴厘的戏剧传统,使这些演出成为20世纪西方互文化(intercultural)和跨文化(transcultural)戏剧的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姆努什金同安托南·阿尔托、梅耶荷德、布莱希特、格洛托夫斯基、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彼得·布鲁克等现代和当代导演一样,成为20世纪西方互文化和跨文化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
姆努什金对亚洲戏剧的认识和理解
姆努什金对亚洲戏剧的兴趣始于20世纪60年代,她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周边的国家,甚至到过包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从未到过中国大陆。1963年,姆努什金在日本东京一家小剧院首次观看了歌舞伎的演出。她看到一名演员用一个简单的鼓表演战斗场景,为此而感受到一生中最大的心灵震撼:“这个演员在剧场两个小时内教会了我所有的东西。他向我表明戏剧总是可能的,他可以说明一切事物。”1967年姆努什金在巴黎观看了印度卡拉曼达拉姆(Kerala Kalamandalam)剧团演出的卡塔卡利(Kathakali),后来她又在印度本地看过卡塔卡利演出。1989年姆努什金曾经邀请卡拉曼达拉姆剧团在太阳剧社演出用卡塔卡利改编的《李尔王》。她还在新加坡看过京剧表演[1]。在一次采访中,她谈到了中国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应邀在姆努什金自己创建的“演员传统研究协会”(Association de Recherche des Traditions de l'Acteur)上所做的示范表演。裴艳玲和郭景春的表演由姆努什金的助手之一索菲娅·莫斯科索(Sophie Moscoso)加以记录整理,并于1998年以书的形式发表[2]。
姆努什金对亚洲戏剧的兴趣是20世纪西方戏剧与东方戏剧整体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对亚洲戏剧的态度上,给姆努什金启发最大的是法国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阿尔托。阿尔托的戏剧理论不仅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先锋和实验戏剧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西方现代戏剧向东方戏剧借鉴开了先河,开创了西方现代戏剧中的“东方主义”的先例。姆努什金曾反复阅读阿尔托的理论,认为阿尔托所说的一切正是她所需要的[3]。她一再把阿尔托的名言“戏剧是东方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姆努什金看来,戏剧之所以是东方的,首先在于戏剧在西方已经枯竭。西方只产生了三种戏剧:古代戏剧,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意大利的艺术喜剧(即兴喜剧或假面喜剧),它事实上是来自东方的;还有现实主义戏剧,一种基于语言而不是形体的形式。像阿尔托一样,姆努什金在亚洲戏剧里看到的,是与西方现实主义和心理主义传统相对立的东西。她这样说:“对于我来说,戏剧的起源和我的源泉是亚洲的……我最近记得阿尔托说过:‘戏剧是东方的。’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戏剧所特有的东西是来自亚洲的,这就是演员创造的永久性的隐喻……我们西方人创立的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形式。那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创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与戏剧相关,只要一用到‘形式’这个词,就已经有一种亚洲感觉了。”[4]姆努什金认为,东方戏剧描绘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神圣的、与内在宇宙有关的世界”[5]。东方艺术的特点是演员要找到激情的症状,找到内在的疾病,那就是激情,它的色彩、它的矛盾,而这一点被西方一些人忘掉了,西方演员恰恰是在掩盖症状。在演出实践中,姆努什金经常教导演员“有必要做尸体解剖”[6],她把演员的职能比做解剖人体灵魂的外科医生[7]。在她看来,“亚洲演员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表现无法看得见的事物的真正符号。这就如同尸体解剖一样,你必须深入内心,找到灵魂疾病的症状,找到通过符号、通过象形文字来表达那种疾病的方法。那就是亚洲演员通过训练所要达到的……”[8]
姆努什金重视的是演员通过形体对灵魂所作的解剖和表现,重视的是形体运动的技能和形式,在这方面,姆努什金认为亚洲戏剧更是她效仿的楷模。在一次采访中,姆努什金表示演员应该有健美和可塑的形体,有节奏感,有音乐知识,也就是说不仅有理性文化,更要有“形体文化”。姆努什金直言不讳地承认:“亚洲戏剧一直就是我们的源泉。日本戏剧,能乐和歌舞伎,一直在丰富着我们的演出。它们允许演员发展一种极其严格的表演工具……我们之所以用亚洲戏剧的形式作为工作基础,是因为戏剧形式的起源就在亚洲。”[9]姆努什金宣称:“我的戏剧始祖是印度、日本和中国……他们发明了演员,他们发现了表演的艺术。”[10]
尽管姆努什金和太阳剧社高度重视亚洲戏剧传统,但在演出实践中,从未奢望掌握亚洲戏剧的科学体系和技术,从未照搬亚洲戏剧的形式和技巧。姆努什金高度赞扬亚洲的演员训练传统,认为西方人不懂得演员训练,但她同时否认太阳剧社的演员运用的是东方戏剧技巧。原因很简单:东方演员从六岁就开始训练,而太阳剧社没有这种能力。姆努什金所追寻的是一种亚洲戏剧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或者方法[11]。姆努什金在亚洲戏剧中看到的共同法则,并不是指这些戏剧长期形成的具体的、科学的表演技术和技巧,而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艺术精神和方法,即对形体的、隐喻的和形象化的艺术表现的重视。
姆努什金用亚洲戏剧形式重新发明莎士比亚
在太阳剧社迄今为止的全部演出里,最初全面体现亚洲戏剧影响的是姆努什金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姆努什金力图表现的是莎剧的历史性、莎剧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姆努什金说:“莎士比亚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距离我们如此遥远,就如同我们距离自己最深的心灵深处一样。”[12]在对莎士比亚进行历史主义的处理这一点上,姆努什金的方法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方法是相近的。在《理查二世》的演出里,为了再现莎士比亚描绘的英国中世纪时代,姆努什金转向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她写道:“不错,需要表现《理查二世》里的仪式和骑士世界的形象,对我来说,这样的形象在某些日本小说和电影里更加富有活力……日本告别中世纪比我们要晚得多,所以日本的中世纪也许是最接近我们的中世纪了。”[13]姆努什金还说过:“为何要选择亚洲风格的莎士比亚这样一种演出方法呢?亚洲戏剧,特别是日本戏剧的范例是不言而喻的,原因就是它的故事里有着出色的武士、贵族、王子和国王。”[14]
姆努什金指出:“在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戏剧时代,戏剧形式并不是很强的……我们在亚洲戏剧里寻找演出的基础,原因在于亚洲就是戏剧形式的发源地。在西方,除了希腊悲剧和艺术喜剧之外,根本没有出色的戏剧形式。”[15]从这个意义上说,姆努什金的莎剧演出里存在“亚洲戏剧的影响”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如同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一样,戏剧的“直接途径总是指向亚洲,因为在亚洲,音乐、舞蹈、神圣的艺术、戏剧,一切应有尽有”[16]。在一次采访中,姆努什金指出:“日本的戏剧形式是莎士比亚式的”:“当我到日本第一次观看了歌舞伎和能乐的演出,我当然一点也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总是感觉到,‘我似乎完全是在观看一场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就如同莎士比亚的服装一样适合于莎士比亚”[17]。
姆努什金对日本戏剧的借鉴,更多的是通过黑泽明的电影。黑泽明的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日本中世纪历史为题材和背景的,同时,他的电影在表现形式上深受日本戏剧的影响,有意识地借用能乐的程式化和形体化的表演艺术。总之,黑泽明的电影对姆努什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姆努什金一方面从黑泽明的电影里借鉴了日本戏剧艺术,特别是能乐的表演艺术,另一方面姆努什金从黑泽明的电影里形象地了解到日本中世纪的历史概貌,从而为她用“陌生化”的方法处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历史地和艺术地表现英国中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
姆努什金反对用现实主义的形式演出莎剧,认为莎剧的诗的文本与现实主义的演出形式和方法是格格不入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写的是仪式、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你真的认为亨利四世出现在公开仪式场合时,会像其他普通人一样行走吗?日本戏剧是惟一具有仪式的戏剧。东方演员用面具、符号、舞蹈、歌唱和其他一切形式表现他的内心活动……除此而外,戏剧是一种隐喻,莎士比亚是一位永恒的隐喻诗人。你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来表演他。”[18]当然,与许多现代导演对莎剧在文本上的自由处理不同,姆努什金坚持在文本上要忠实于莎士比亚,为此她亲自动手把莎剧翻译成法文,以尽量保存莎剧的诗的节奏和意象。为了表现莎剧里诗的隐喻和形象,避免现实主义的和散文化的演出方法,姆努什金认为亚洲戏剧是必由之路。
在《理查二世》的演出里,舞台设计完全是风格化的,整个舞台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的空间”,演员的表演具有歌舞伎或能乐的程式化和风格化的特色。演员跳跃着经由类似于歌舞伎“花道”的坡道进入空空的舞台。在整个演出中,演员的表演是在前台面对观众进行的,演员的台词是直接指向观众的,其中有演员像京剧演员那样用形体动作虚拟表演骑马作战的场景,像歌舞伎演员那样不时在台上跺脚,向空中跳跃,走圆场,以突出剧中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演出中有的演员戴面具,演员的浓重的风格化白色化妆与歌舞伎演员的化妆相似。演员的服装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紧身上衣、宽硬的轮状皱领和中世纪裙裤的混合,而演员的头饰和斗篷使人联想起日本风格的服装。音乐贯穿于整个演出中,乐师运用了许多来自亚洲国家的不同形式的乐器,使演出的东方情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第十二夜》的演出处理上,姆努什金从日本戏剧转向印度戏剧。她曾经说:“在《第十二夜》的演出里,我们是从婆罗多舞(Bharata Natyam)里找到灵感的。”[19]演出的服装设计和化妆仍然具有东方情调,演员的表演有时使人联想起卡塔卡利的舞蹈动作和姿势。但是,同《理查二世》里存在的歌舞伎和能乐表演因素一样,姆努什金并不着意在《第十二夜》里追求和再现完整地道的印度戏剧形式和风格,而更多的是在营造一种亚洲戏剧和文化的氛围。
姆努什金导演的莎剧上演后,批评家们很快就发现姆努什金借用了亚洲的戏剧形式,以为姆努什金是在用日本、印度或者中国的戏剧形式把莎士比亚加以“东方化”。姆努什金这种互文化戏剧实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一方面,由于姆努什金有意识地力图表现莎剧的历史性,由于她的实验更多是集中在戏剧艺术形式方面,没有能够对莎剧从当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作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姆努什金在演出里有侧重地杂糅了多种亚洲戏剧形式的因素,对熟悉亚洲戏剧形式的观众和批评家们来说,姆努什金的演出运用的并不是地道的亚洲形式,而具有明显的“东方主义”的味道。
我认为,运用亚洲戏剧形式演出莎剧不可能重新发现莎剧原本的演出形式和风格,而只是适应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现实主义、反心理主义的先锋派戏剧的需求,因此,莎剧和亚洲戏剧都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戏剧想象、利用和占有的对象。尽管姆努什金反对把莎士比亚当作我们的同时代人来处理,强调历史地处理莎剧,但是姆努什金的历史化和“陌生化”方法也无法为我们呼唤出那个在“环球”剧院挥戈作场的原本的莎士比亚。日本的中世纪历史毕竟不同于莎剧里描写的英国历史,想象的日本戏剧形式也只能为我们发明一个想象的莎士比亚。这样说丝毫不是在指责或者贬低姆努什金的莎剧演出,而是在强调说明:姆努什金处理莎剧的方法,不论它在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上与其他方法如何不同,也只能被看作是20世纪西方现代戏剧用来重新发明莎士比亚的众多方法之一。
姆努什金用亚洲戏剧形式重新解读古希腊悲剧
继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之后,姆努什金和太阳剧社于1991年上演了悲剧《阿特柔斯家族》(Les Atrides)。这个需要四天、十个小时的演出由四部古希腊悲剧组成,包括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和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一般认为,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作为西方戏剧乃至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作,表现了古希腊历史上中兴的父权制对没落的母权制的胜利以及进步的民主法治对落后野蛮的宗族复仇观念的胜利。姆努什金从激进的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她的演出对古希腊悲剧作了重新组合和解释,进而把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转变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希腊帝国的历史和政治悲剧。姆努什金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置于整个演出之首,提供了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历史根源和证据。
为了对古希腊悲剧的意识形态内涵作出新的解构,使观众摆脱西方对古希腊悲剧的正统解释,重新审视古希腊悲剧的意义,姆努什金在演出形式上采用了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的方法。姆努什金寻找的不是现代主义,比如运用现代服装,而是某种最接近古希腊悲剧、同时对现代观众来说最陌生的演出方法,包括对音乐、舞蹈和歌队的处理[20]。为此,她有意识地抛弃了西方几百年来演出古希腊悲剧的经典方法,在演出形式,特别是音乐、舞蹈和歌队方面,借鉴了亚洲戏剧,特别是印度戏剧的演出和表演形式,如卡塔卡利。姆努什金说过:“我并不想参考关于古希腊的历史文献,因为我害怕不知不觉地陷入那些关于希腊花瓶、外袍、服饰的陈词滥调中。我仍然相信在西方只有剧作法,在东方则有演员的艺术,而我缺了演员艺术是不行的,我将会毫无顾忌地利用它。”[21]姆努什金故意不用希腊面具,演员的化妆主要是受到印度最古老的梵剧舞蹈库提雅特姆(Kutiyattam)的启发。其次还有卡塔卡利、歌舞伎、能面的启发。剧组演员大多数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卡塔卡利的训练或以不同的方式领会到印度或其他东方戏剧舞蹈艺术。
与太阳剧社的其他演出一样,姆努什金拒绝在传统的剧场里演出希腊悲剧。《阿特柔斯家族》的演出场所同样是在太阳剧社的所在地,即巴黎郊区凡森地区(Vincennes)的卡都谢里(Cartoucherie)的一家废弃的军工厂。《阿特柔斯家族》演出的舞台是一个没有特定景设的空间。像卡塔卡利演出一样,场景的变化是由演员的表演来显示的。演员跳跃着跑步入场。整个演出贯穿着歌队的舞蹈,歌队由12个演员组成,其舞蹈在手势、形体和动作上有库提雅特姆以及卡塔卡利舞的影子。演员用朗诵式的风格直接对着观众说台词;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内心体验的心理现实主义不同,演员的表演动作更多是与外部形体、面具的表现形式和音乐伴奏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歌队用情感激烈、节奏鲜明的舞蹈对剧情和人物作出反应和评价,引导观众的情感反应和理智判断。古希腊悲剧的传统演出常用一种叫做“埃基克莱玛”(ekkyklema)的舞台工具(一个装有轮子、可以滚动的圆形或半圆形的平台),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把尸体从后台推倒前台。在《阿特柔斯家族》演出中,姆努什金只用一个简单的床垫来代替“埃基克力玛”。如阿伽门农和卡桑德拉、埃吉斯托斯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尸体都是放在床垫上,被拖上舞台的。应该指出,像太阳剧社的其他演出利用亚洲戏剧形式一样,在《阿特柔斯家族》里,姆努什金并不是企图照搬卡塔卡利的形体表演、服装、面具和音乐设计,而是为自己的演出吸取创作灵感。在一次采访中,姆努什金说:“在《阿特柔斯家族》里……卡塔卡利完全是想象的灵感来源。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对明晰、形式、细节精确的需求。”[22]
我认为,姆努什金的处理方法与她对希腊悲剧的重新解读是一致的。姆努什金借用亚洲戏剧形式对希腊悲剧的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处理,虽然可能无助于甚至有损于人们从熟悉的传统批评来理解希腊悲剧,但是它与姆努什金力图使观众从新的视野来重新理解和思考希腊悲剧的导演创作主旨,却无疑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注:此文为作者加工过的节选,详文请见原刊。
标签:戏剧论文; 莎士比亚论文; 艺术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第十二夜论文; 古希腊论文; 理查二世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