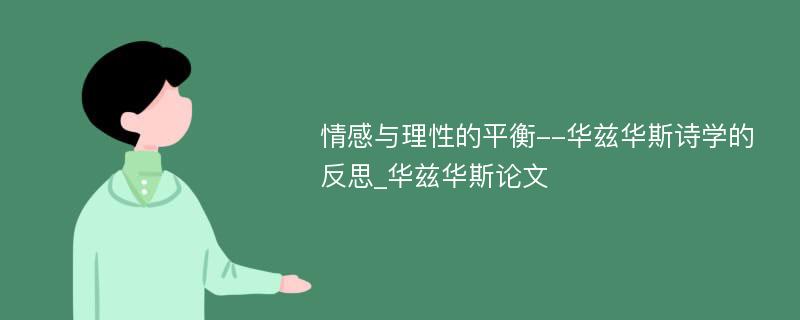
情与理的平衡——对华兹华斯诗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兹华斯诗学中有关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方面已得到了文论史的充分肯定,但是,他认为“一切好诗的共同点, 就是合情合理”(allgood poetry,namely good sense), 诗歌创作是“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沉思”,诗歌创作有理性的控制等,这一方面并未引起批评界的广泛注意。柯勒律治的诗学思想受谢林、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影响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其实柯勒律治的诗学思想中受华兹华斯诗歌理论的启示也不少,最典型的例证应该是华兹华斯的“沉思”和判断的理论的影响。柯勒律治认为诗人是理智与情感的稀有结合,认为莎士比亚的天才就在其判断力中;而华兹华斯,作为天才的另一例,即一种糅合哲理和情感的资质而受到称许。可惜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诗学思想“资质”的这种较完整的把握并未引起后代学人的注意,即使在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中,作者似乎为了特别强调浪漫主义批评传统中“灯”的地位,对华兹华斯的“沉思”一面着墨也不多。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也只强调华兹华斯诗论的过渡性质而忽略了其中的“合理”部分。倒是那些立志推倒传统的现代主义诗人,不仅在本质上继承了华兹华斯的革命与拒绝传统的精神,而且将华兹华斯不被19世纪所关注的一些具有现代性的主张发扬光大。
一、诗歌既是有意识的艺术又是自发性的艺术
看来,在诗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之间,似乎天然地存在着相互排斥、但又不得不纠缠在一起的力量。在文学史上,我们既能找到浑然天成的佳作,也能发现艺术使然的精品,只强调一个方面,难以说是全面的。因此,从文艺复兴开始,劳作与灵感的结合产生诗篇的观点即在英国出现,斯宾塞在《牧羊人日记》第10歌中的表述有一定的代表性:“诗不能由劳作和学问产生,却又以劳作和学习作为文饰;它通过某种‘热情’和神圣的灵感输入才智中。”(注:转引自卫姆塞特等《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第257页。)我们知道, 斯宾塞恰是华兹华斯最为崇拜的作家之一,我们很难确定华兹华斯有关诗歌是有意识的艺术这一观点是否直接承袭自斯宾塞,也许17至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诗论为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更直接的滋养成分。我们能在华兹华斯的“序言”中隐约照见本·琼生和约翰·德莱顿的不少观点。他要求诗人留心题材,并提醒诗人,他不是为自己而写作,而是为“人们”而写作。他说:
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已往一切情感的代表。(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华兹华斯正是这样, 将“思想”这一古典主义的关键命题作了奇妙的转换,使之成为“情感”的又一种形式,从而使诗歌的意识性与诗歌的自发性贯通起来,这种自发性就是智慧的运用和锤炼的技巧所给予的报偿。华兹华斯自己的诗歌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诗篇大多要进行长期辛勤的修改,这表明诗人的“情感”决不是不需要修改的。他甚至说:“我常常发现初次的表达是讨厌的,第二次用的词句和思想往往是最佳的,确乎如此。”(注:转引自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晚年时,他劝一位朋友:“作诗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 超过了人们准备相信的程度;绝对的成功取决于无数的细节。弥尔顿谈到‘不假思索的诗句源源而来’,但这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未可尽信。”(注:转引自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这并不是青年华兹华斯与老年华兹华斯的矛盾,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承认修改和技巧的重要性与凭借最初灵感的内心冲动和自然流溢是完全并行不悖的。因此,正像艾布拉姆斯所说:“他以表现说的力量,把诗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这一古老概念中的某些成分纳入了表现说的范围;正是因为表现说与众不同,才使得这些成份被谨小慎微地降到诗篇形成前后的暂时地位上。”(注:转引自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 )我认为在创作之前“意识”是对题材有目的的选择,对诗歌效果价值的期待;那么在创作过程中,“意识”就是华兹华斯的“沉思”与“平静中的回忆”,这也正是华兹华斯超越了同时代绝大部分浪漫主义诗人和理论家的突出之点。
华兹华斯“沉思”观点的提出是他三重反思的结果。首先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人类仅靠理性不能最后得救,还需要信仰,需要情感与爱;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只有情感与爱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沉思与理性。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中惟一亲历法国大革命的诗人,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激情、冲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暴力后果,成为促使华兹华斯重新反思人类的信仰、情感、理性、沉思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使华兹华斯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失去理性的时代是疯狂的时代,一个不会沉思的人就是不会进步的人。诗人与他的诗歌必须体现人类理性与沉思的勇气。
第二,华兹华斯“沉思”的提出还是他对英国社会现状反思的结果。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有两种强大的社会习俗引起了华兹华斯深深的忧虑。第一种是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拜金主义思想,刺激着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贪婪与欲望。第二种是日益发展的科学主义对人的心灵价值的漠视。欧洲文化中科学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自近代以来,英国的实证哲学与科学发展相互推波助澜,引起社会对文学作用的漠视。在华兹华斯看来,诗歌首先与科学一样是有关人类的知识,其次,诗歌是远比科学更高级与全面的知识。科学只能提供片段与零碎的知识,而诗歌则不同,“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诗歌的知识不仅比科学要完整、全面,更重要的是,诗歌在知识之外还关乎人的心灵,捍卫人的天性,“因为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管地域和气候的差别,不管语言和习俗的不同,不管法律和习惯的各异,不管事物会从人心里悄悄消逝,不管事物会遭到强暴的破坏,诗人总以热情和知识团结着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页。)华兹华斯并不排斥科学,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既需要热情也需要知识,既需要诗歌也需要科学。只有科学的社会,是人性的荒漠;只有科学的社会,人最终将蜕变为机器。
第三,华兹华斯诗学中的“沉思”源于他对英国文坛状况的反思。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新古典主义诗歌走向穷途末路,许多感伤的、内容贫乏的作品充斥文坛,对国外作品的翻译也充分迎合了当时的风气,不是感伤,就是暴力。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被抛弃了,华兹华斯痛心地指出,当时的文坛状况是,“已往作家的非常珍贵的作品(我指的几乎就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作者原注)已经被抛弃了,代替它们的是许多疯狂的小说,许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像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无价值的故事。”(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华兹华斯针对这一现状提出要珍惜传统,珍惜以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在笔者看来,这种传统包括传统诗学思想中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理性对情感的控制等观点。华兹华斯一方面高举反传统的情感论的大旗,另一方面又善于“沉思”传统诗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并不认为传统诗学中的以理抑情全无存在的必要,而是批判地吸收它的合理成分。
从华兹华斯的三重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毫无疑问,华兹华斯的情感观不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张扬自我、与新古典主义划清界线的重要标志,而且打破了摹仿说一统诗学的格局,开启了至今仍以形形色色的变形而存在着的表现说。当然,如果仅仅是以一种倾向遮盖另一种倾向,那决不是进步,充其量只是原地打转。经过三重反思之后的华兹华斯给情感与理性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合情合理(good sense)。(注:“good sense”多译为“良知”,sense一词本身就是情与理的结合、 本能的五官感受与后天辨别力的结合,我们知道华兹华斯是个讲究用词的诗人,他使用“good sense”是有其目的的。)
我们都对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对诗歌创作是有目的和价值的表达有很深的印象。华兹华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这种诗能使人们永久感觉趣味,而且从它的道德关系的性质和多样性来讲,也十分重要。”(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页。)华兹华斯对普遍人性的承认,对诗歌价值的强调,使得后来不少人都认为华兹华斯重返新古典主义。(注:参见《19世纪文学评论》第12卷,美国盖尔研究公司,1986年,第180-185页。)的确,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相比,华兹华斯强调了那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不愿提及、但却已成为他们部分血肉的文化积淀与艺术传统的某些新古典主义原则。但是细察华兹华斯的诗论与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不仅把新古典主义所强调的人类情感与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自我情感融合在一起,而且力图超越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局限,以求达到一种全新的审美情感境界。
二、“沉思”是协调情与理的中介
华兹华斯说,“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页。)。他承认诗歌具有超越个人的性质,能表达普遍的人性。但是,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是矛盾的,它们之间需要中介来协调,“沉思”(contem plate)就是这个中介。沉思消除了个人情感中与人类共同情感在伦理、道德上可能构成冲突的一面;沉思同时也将人类的共同情感具体地表现在诗人独特的心路历程上。这种普遍的人性情感颇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荣格把个人理解为人类自身全部积淀的成果。华兹华斯说:
只是一个的知识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天然的不能分离的祖先遗产;一个的知识是个人的个别的收获,我们很慢才得到,并且不是以平素的直接的同情把我们与我们的同胞联系起来。(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17页。)
这段话是批评界较少注意到的,笔者认为,它在表达华兹华斯力图超越浪漫主义的自我情感方面其实是很有深意的。华兹华斯意识到个体的生存与知识都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个个都生存在种种非典型的情境中,残酷的生存竞争把人分隔在不同的条条框框里,人的精神处于疲劳不堪、毫无自由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诗人必须寻找到能将诗人与读者或个人与个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华兹华斯看来“我们天然的不能分离的祖先遗产”正是一条能将人类联络起来的纽带。当然,华兹华斯与荣格不同。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在作家、艺术家的心中是一种异己的力量,集体无意识有时与作家的自我意识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华兹华斯看来,诗人与“我们天然的不能分离的祖先遗产”的关系并不总是那样紧张和不可调和。纵观华兹华斯的《序言》,我们发现,华兹华斯实际上对自己的许多概念并未作严格的区分和界定,在他的论述中,有几个概念是可以相互代替的,如“真理”、“自然”、“我们生存所必需的知识”、“我们天然的不能分离的祖先遗产”,这几个词句在文本中意义相近。华兹华斯认为,“人与自然根本互相适应,人的心灵能照映出自然中最美最有趣味的东西”,诗人“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17页。)由此,华兹华斯将诗人的自我情感叠加进集体的、祖先的遗产中去。
自然情感并不等于艺术情感,只有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才是他人所能接受的艺术情感。那么,自然情感要经过怎样的审美过滤呢?华兹华斯的回答是:沉思。自然情感向艺术情感过渡时,必须完成以下两个任务。第一,自然情感要经过“沉思”凝想,全神贯注地审视。这里的“沉思”,既有社会道德、文化积淀的参与,又始终充满情感。但由于有了道德、文化的介入,诗人逐渐从自然情感的状态中“平静”下来。在沉思的过程中,情与理之间达到了缓冲、平衡、制约。第二,自然情感必须经过对象化。无形的、流动的、氛围式的情感必须经过沉思这一中间环节而获得有形化、固定化和具象化。沉思即是化无形为有形的过程,它必然始终伴随着形象,而且,这种形象还与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思维取向与个性特征有关。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平静中的回忆”是沉思的基本状态。
“沉思”在此具有双重中介作用,它既是诗人个人情感与人类普遍情感的中介,也是自然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的中介。应该说,情与理的协调、平衡、融合是传统与现代诗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中外不少文学家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意识到艺术创作并不总是与灵感、激情同步的,雪莱就说:“当创作开始时,灵感已衰退了。”(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但是,灵感、 激情——平静——再度体验,此间的过渡一直是困扰作家与理论家的问题。华兹华斯提出了“沉思”这一中介,其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诗人的“沉思”中并非一味地“平静”,华兹华斯明确指出:“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2页。)诗人的沉思决不“平静”,因为诗的沉思本质上决不是思考,而是再度体验,它的对象不是理性观念而是情感,诗人沉思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情感。当然,这种情感与产生自然情感的物理时空有了距离,因而它就是回忆所涉的对象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平静消逝之后,再度出现在诗人心中的、与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就是被压抑在诗人心理深层的情感储备。这种情感储备既是人类普遍情感的积沉,又带有强烈的诗人个性色彩,而决不是私人化的情感。在华兹华斯的这句话中一共出现了三个“情感”(emotions),而这三个情感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诗人沉思这种情感”与“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中的两个“情感”,指的应该是诗人的自然情感,而逐渐在诗人心灵中再次产生的情感则不同,它指的应该是艺术情感。艺术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关系不仅是“相似”,更是一种“血缘”关系,华兹华斯选用的词“kindred ”本身就包含有这两种意思在内。也就是说,艺术情感来源于自然情感,但自然情感是艺术情感沉思的起点和基质,自然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的驱动力也完全源于诗人的心灵,转化的过程也是内心的一种体验。在华兹华斯看来,他强调“沉思”是同强调诗人的心灵、情感的作用并行不悖的。在1800年的《序言》中,华兹华斯进一步把诗人的这种“平静中的回忆”与“沉思”的能力作为诗人的重要标志。艺术沉思并不仅仅唤起情绪记忆,以及将情绪所携带的能量宣泄出来。艺术沉思作为全身心投入的对情感的再度体验,还必须将各种心理机能和知识储备调动起来,一同完成对情感的改造。华兹华斯一方面强调诗是情感的自然流溢,一方面又说:“我时常都是全神贯注地考察我的题材……这样做有利于一切好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页。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仔细梳理了浪漫主义诗学思想与欧洲以往各种性质不同的思想遗产的关系,真正体现出浪漫主义批评理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给浪漫主义下定义也一直是浪漫主义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参见亨利·雷马克《西欧浪漫主义:定义与范围》,载《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本处引文见《镜与灯》,第156页。)同时还强调“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注: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华兹华斯在此提出的是一个情与理如何平衡、制约与融合的问题。华兹华斯既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的以理抑情,又超越了浪漫主义的只讲情感,而力求使情与理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平衡、制约与融合。应该说情与理的深层融合是艺术沉思的最高旨趣。从对情感的回味、再度体验开始,伴随着全部知识储备和精神活动的投入,沉思的主体参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而从一己的情感体验升华为对人生宇宙、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的领悟。这样艺术沉思就超越了情感体验的层次而达到哲学认识的深度。
三、“沉思”是诗人情感对象化的中介
如果说自然情感经过艺术沉思而成为艺术情感是审美的一个转换,那么,将流动的、气氛式的情感通过一定的对象呈现出来,成为读者可以把握的诗情,就是沉思的第二项任务。在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中,情感的对象化就是使情与景结合的过程。
诗的基本单位是意象,而“意象是由情与景这两个原素构成的。情与景相契合而生意象”。(注: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第161页。)庞德认为, 意象是“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注:转引自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9页。)在诗歌创作中,情感的表现必须通过可以知觉的对象呈现出来,使情成形,在一定的意义上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够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认识的形式。”(注: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4页。)意象本身的生动性和具体性使它成了诗歌创作的最基本单位。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意象”(image)一词更多地暗示着内心的图景、内视的东西。这也正如华兹华斯所说的,对意象的把握与确定是艺术沉思的具体内容。
应该说,意象是艺术沉思形式化的最小单位,艺术沉思正是借助于审美意象而得到深化、明朗化的。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之一《我有过奇异的心血来潮》是他诗歌创作中少见的表达爱情的诗篇,作于1799年。当时华兹华斯已许久没有安妮特母女的消息,诗人对她们的思念之情一直缠绕于心。诗的第二节有两句诗:“晚间,在淡淡月光之下,我走向她那座茅舍。”在这里包含了两个意象:“月光”与淡淡月光之下的“茅舍”,诗人将思念之情与“月亮”、“茅舍”联系起来时,就使得思念、想望这种朦胧的、隐隐约约的情感体验具象化了。此时诗人的情感因获得了具体的形式而明朗化,而且借助这一形式在诗中的不断变化而使得诗人的感情进一步深化。我们将诗中有关“月亮”与“茅舍”的诗句列出:
晚间,在淡月光之下,
我走向她那座茅舍。
我目不转睛,向明月注视,
走过辽阔的平芜;
这时,月亮正徐徐坠落,
临近露西的屋顶。
我两眼始终牢牢望定
缓缓下坠的月轮。
只见那一轮明月,蓦地
沉落到茅屋后边。
什么怪念头,又痴又糊涂,
会溜进情人的头脑!
“天哪!”我向我自己惊呼,
“万一露西会死掉!”
月亮逐渐下沉的意象与茅舍逐渐靠近的意象预示着诗人就能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对象了,但是一个“怪念头”就使得诗歌的情绪直转而下,它加深并强化了诗人的审美体验,表达了诗人对安妮特母女的思念之深切,以及由思念而产生的忧虑和恐惧。
如果没有“月亮”与“茅舍”这两个感性的意象形式,华兹华斯对安妮特母女的思念就完全不是那么一种形式,要么永远只是诗人体验着的、只有私人性质的思念情绪,要么就以另外的景物为思念的感性形式。审美意象的感情形式在审美意象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感性形式,艺术沉思就只是一种极其朦胧的心理感受,它就不能成为人们自我观照的对象,不具有审美的意义。沉思在创作中是化无形为有形的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是与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思维取向与个性特征有关的。华兹华斯一直都把自然当作是自己毕生的朋友、导师和乳母,而且把童年当作是成年人重返自然的中介。自然与童年在华兹华斯的诗学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因而在华兹华斯的诗歌意象中,童年与自然是不断复重出现的两个最重要的意象,而且这两个意象有时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四、“沉思”观对20世纪诗学的影响
如果把华兹华斯的“合情合理”作为20世纪西方现代诗学的发展背景来考察,我们就能发现,他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诗学。艾略特的诗学是对浪漫主义的超越这一论点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从一般意义上讲,艾略特对浪漫主义的超越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经验代替情绪,以有意识的控制代替自发性的情感流溢;一是对诗的非个性化倾向的追求,以“自我的隐去”代替“自我的表现”与“自我的分裂”。从我们对华兹华斯情理观的分析中,可以说这两个方面也正是华兹华斯对浪漫主义诗学的超越所在。
艾略特将象征主义和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传统糅合起来,为诗与哲学的融合开辟了新的途径。他认为,诗应当“创造由理智成分和情绪成分组成的各种整体”,“诗给情绪以理智的认可,又把美感的认可给予思想。”(注:艾略特《诗与宣传》,周煦良译,载1936年7 月《新潮》第1期。)这些论点与华兹华斯的论述何其相似! 华兹华斯的由自然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的复杂过程,在艾略特这里被简化为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
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途径是发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发现构成那种特殊情感的一组客体、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样,一旦有了归源于感觉的经验的外部事实,情感便立即被唤起。(注:艾略特《哈姆莱特和他的问题》,转引自《西洋文学批评史》, 第614页。)
艾略特在反对浪漫主义诗学的自我表现时,从本质上继承了华兹华斯的精神,他说:“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寻求新情绪,而是要利用普通的情绪,将这些普通情绪锤炼成诗,以表达一种根本就不是实际的情绪所有的感情。诗人从未经验过的情绪也可以像那些他所熟悉的情绪一样为他服务。”(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胡经之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47页。)他还说:“诗并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胡经之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47页。)从艾略特论述的上下文看,所谓“普通的情绪”就是传统和传统所证明的人类普遍的情感,诗人的才能并不在于传达出自我经历的情感,而在于将自己从未经验过的情感——只要它属于人类普遍的情感——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经过了这种“自我的隐去”后,诗人的情感由“小我”而为“大我”,既克服了诗歌创作中的滥情主义,也克服了私人化倾向。
关于艾略特与华兹华斯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提及艾略特对华兹华斯的直接批判:
我们一定要相信,“情绪是在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是一种不精确的公式。因为诗歌既非情绪,又非回忆,也非(如果不曲解其意义的话)宁静。诗是很多很多经验的集中,由于这种集中而形成一件新东西,而对于经验丰富和活泼灵敏的人来说,这些经验也许根本就不算是经验;这是一种并非自觉地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所发生的集中。这些经验并不是“回忆出来”的,这些经验之所以终于在一种“宁静”的气氛中结合起来,只是由于它是被动地凑拢来的。自然,这并不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有许多地方还是需要自觉和深思熟虑的。(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胡经之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47页。)
经过对华兹华斯沉思理论的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艾略特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华兹华斯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华兹华斯“沉思”理论基本精神的接受。这种“批判”架式只不过反映了艾略特对华兹华斯的一种“影响的焦虑”。(注: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牛津,1973年)中认为,18世纪以后的大诗人们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之下,而当代英美诗人则生活在那些与弥尔顿作殊死搏斗后站稳了脚跟的强者诗人的阴影之中,这些强者诗人就包括华兹华斯。根据布鲁姆的观点,时至今日,诗歌的主题和技巧已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用尽,后来的诗人要想崭露头角,惟一的方式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的首创”。)
至此,我们可以对华兹华斯情感观中一些概念的梳理作一总结。在华兹华斯的诗学中,“合情合理”应是诗的最高标准。它既是对古希腊以来诗学思想中以理抑情思想的突破,又是对20世纪诸多诗学理论的预示,如后期象征主义的“自我隐去”、精神分析、原型理论、读者接受理论等。“情”是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的融合,并借助于语言文字而外显为艺术作品。“理”是社会道德、信仰与文化积淀在诗人身上的体现,“理”从诗人的选材、构思、对诗歌效果的期待到创作过程,都起着对“情”的“过滤”、干扰作用。在诗人的实践中,合理的未必合情,合情的也未必合理,这也正是古希腊以来诗学家有时张扬情感、有时又以理压情的原因。华兹华斯试图协调二者,这一协调的中介就是沉思。沉思使得个人情感消除了私人化的性质而与人类共同情感相融合;使得征兆式的情感化为艺术作品。沉思也使得伦理、道德、宗教都脱却了说教的外衣,而披上了情感的光环。沉思使情与理不分彼此、相辅相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华兹华斯关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中“自然”的含义,它决不是像地下的泉水般随时随地都在向外溢出,它是情与理的一种习惯性融合。我们应该充分注意的是,这种习惯性融合完全是诗人后天习得的结果,是不断地、有意识地强迫自我情感接受理性过滤的结果,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有了这种习惯以后,诗人就随意地服从它的引导成“自然”。华兹华斯的情理观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在情与理的平衡中,是以情为标准平衡理,还是以理为尺度平衡情?或是在不同的阶段各有偏重?也许这个问题不仅是华兹华斯情理观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世界诗学史上难以圆满解决的问题。
标签:华兹华斯论文; 诗歌论文;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论文; 近代文学批评史论文; 艺术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镜与灯论文; 艾略特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