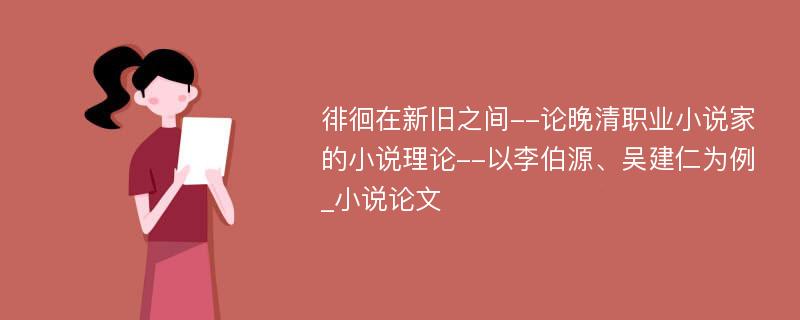
徘徊于新旧之间:论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小说理论——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家论文,理论论文,职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3)01-0107-05
一
晚清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写作开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家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这种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不仅以报刊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把报刊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
这些职业作家的身份与传统文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不再依赖于科举制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官方的束缚,自由地从事创作。尤其是他们的活动场所——报刊社和出版社——大部分设在租界,而在这些地方,清政府的控制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这无疑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不过,当时大部分作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小说在新的环境下该怎样变化,他们的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传统小说的模式中。尽管如此,新的创作环境和舆论环境以及发表园地还是为小说自身的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只要有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倡导,小说变革就势在必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梁启超抓住机会高倡“小说界革命”,为酝酿已久的晚清小说变革提供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依据。晚清小说家们蜂拥而起积极呼应,有的发表理论文章表示支持,有的通过具体创作来体现理论主张,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职业小说家,用大量的小说作品充分显示出“小说界革命”所取得的“实绩”。但是,在以往的关于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研究中,对职业小说家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理论上的诸多创见重视不够。本文力图对晚清职业作家在小说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总结。
晚清职业小说家的早期代表,应该包括《绣像小说》社的李伯元、欧阳巨源,《月月小说》社的吴趼人、周桂笙,以及刘鹗等人。他们大都是报刊或出版社编辑,同时又身兼作家;在思想上接受了某些西洋的新事物,可同时又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旧观念;在小说艺术上虽然汲取了域外小说的创作经验,但主要借鉴的是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手法。他们作为刚刚萌芽的职业作家群,既受到了文化市场规律的限制,同时又不能忘怀于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较充分地体现出晚清时期“新旧杂糅”的特征。
这类职业小说作家在小说理论建设上,略逊于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而在理论深度上,也不如后来的《小说林》派,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熟悉程度,无疑比梁启超及《小说林》派作家深入。他们的创作将“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引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扩展了小说的艺术手法的表现类型。
二
《新小说》杂志在日本创刊后,继之而起的,有《绣像小说》(半月刊)于1903年5月创刊,李伯元主编,至1906年4月,因李伯元逝世而停刊,共出版了72期。《绣像小说》专载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不像《新小说》杂志和后来《小说林》那样设有《小说丛话》和《评林》等专门刊载理论的栏目,因此与上述两大杂志相比,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建树不高。但《绣像小说》并非不涉及小说理论,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绣像小说》上的理论多采取传统小说批评的方式,即通过序跋、评点、札记等形式进行批评或阐发理论。若要细致的研究,则必须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点和序跋的分析来把握背后隐含的理论思考。
李伯元(1867-1906)是《绣像小说》的主编兼主要撰稿人,就《绣像小说》而言,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前,已经开始了小说创作活动。1896年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小报《指南报》,1897年又创办了《游戏报》,1901年创办《世界繁华报》。文人办文艺性和商业性小报,李伯元是领风气之先者。他曾在《论游戏报之本意》一文中写道:
《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贫矣,世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欢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是如是,是犹聚喑聋跛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海上为通商巨埠,骄奢繁盛,甲于五洲,势利之区,甫逃之薮,天生人众,懵懵懂懂,在睡梦中,而无有从旁为之大声疾呼者。……而且机制愈出而愈奇,心思日巧而杂拙,以及五方之所日处,九流之所日萃,诡伪变诈之事,无日无之。主人言论及此,窃窃以为隐忧,始有此《游戏报》之一举。或托之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1](P242)
说得虽然冠冕,但其实就是借“警世”为名,迎合市民的趣味。当时《游戏报》是“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文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掣,人则士农工商,强弱老幼,远人甫客,匪徒奸尻,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2](P450)就像丘菽园说的那样:“李伯元明经,骈文专家,又复兼长小品杂著,嬉笑怒骂,振聋发聩,得游戏之三昧……锦绣肝肠,珠玉咳唾,此才正非易易。”[2](P457)《世界繁华报》的内容和《游戏报》相类似,也是一种所谓“消闲”的小型报纸,内容约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时事嘻谈、谭丛、小说、论著诸类,对当日官场暴露、讽刺得很辛辣。所谓“讽林”,有如现在的《卷头言》,每天一首,印在报前,大都是讽刺、幽默作品。
这样的报纸一方面关注政治时局,另外又对社会人生抱一种无所谓的游戏态度。李伯元便多少具有这种对社会人生失望后的玩世心态。这种心态也许不够积极,但用之于小说创作可能别有所成,《世界繁华报》的“艺文志”和“小说”等栏目先后刊载过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吴趼人的《糊涂世界》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然而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李伯元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影响了他主编的小报和杂志的风格变化。
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得到中国小说界和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响应。一时鼓吹小说地位、探讨小说与社会关系、评析小说功能的理论文章纷纷问世。这种反响也充分体现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它先后刊登了《本馆印〈绣像小说〉缘起》(1903年5月、创刊号)和夏曾佑的《小说原理》(1903年6月25日、第3期)等著名文章,大力支持“小说界革命”运动,而且李伯元主编的《世界繁华报》上发表的茂苑惜秋生(欧阳巨源)《官场现形记叙》(1903)和忧患余生(何天言)的《官场现形记叙》等文章也对“小说界革命”表示赞同,他们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对“小说界革命”起了支持、普及的作用。
李伯元在主编《游戏报》时,强调的是游戏人生的态度,推崇玩世不恭的情感。但是在《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中,他的思想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该文中他阐述对小说的理解:“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注: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51-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篇文章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是否是李伯元本人,还有待考证。不过,李伯元当时任《绣像小说》的主编,《缘起》相当于发刊词,这类表明办刊宗旨和编辑原则的文章,应该和主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就把它作为李伯元的小说论文来讨论了。)正如袁进所分析的:“李伯元学着梁启超等人的语言在说话,‘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从这段话很难找到从前的李伯元的影子。由强调‘游戏’、‘玩世’,到提倡‘裨国利民’、‘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造成了小说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气。”[1](P247)
和这种对小说的理解相一致的,是李伯元的大量的社会小说的创作。作为社会小说的著名作家,除了《缘起》一文,他的小说理论大多只是散见于所作的小说的《序》《楔子》《评点》以及某些小说文本之中。黄霖指出:李伯元的小说观表现为:“他们对于丑恶现实的揭露,‘尝咨嗟太而言之,嬉笑怒骂而出之’(欧阳淦《海天鸿雪记》序),但在主观上并不倾向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深其辞,以进行直接而锐利的夹击,而是主张运用‘东方之谑谐,与淳于之滑稽’式的讽刺与幽默的手段,使作品呈‘含蓄酝酿’的艺术风貌,同时也存作者‘忠厚’宽恕之心。其创作实际是否达到了这一境界,那就又当别论了。”(注: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有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由此看来,李伯元的小说观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大略相近,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李伯元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影响。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李伯元与作为小说家的梁启超的创作取向却不一样,李伯元主要用力于社会小说,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政治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一篇)。单就艺术成就而言,李伯元的小说当然要超过梁启超。
三
1906年4月,李伯元去世,《绣像杂志》停刊。接着,1906年9月,吴趼人和周桂笙等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创刊,发行至1909年1月,共出版了24期。《月月小说》的性质与《绣像小说》大略一致,也没有专设小说理论专栏,但是,主编吴趼人和周桂笙等在《新小说》杂志的专栏《小说丛话》发表过文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小说理论的重要性,他们是小说理论家兼作家和翻译家,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就《月月小说》的主要理论而言,至关重要的人物还是吴趼人(1847-1910)。
无论在政治观或者小说观上,吴趼人与好友李伯元最相近,他们的经历和年岁也差不多,都是从办小报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吴趼人在1898年5月创办了《采风报》。对维新变法的赞成和以文学讽世教育的意识是这些小说家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基础。
吴趼人原先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并没有什么认识。在《〈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弁言》中,他就说过:“出言而不关于经济生命之学者,君子宁默:是故风云月露之词,壮夫当鄙为雕虫小技,吲稗官野史,徒以供人谈笑者哉。”这样的看法比较接近传统士大夫的观念,反不如李伯元有玩世倾向。这段话写于1898年夏季之前,那时候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尚未发表,就他的思想而言,当时很可能已经有维新改良的思想,但在“保教”方面与改良派完全不一样,他并不把小说当作承载自己思想的工具。以往的研究总是强调吴趼人的思想与改良派相近的一面,其实他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后期洋务派,十分关注于“保教”问题,这一思想形成后,就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小说成了“文学之最上乘”,他的态度也随之变化,把小说当作宣传思想的工具,认真写作小说,从《新小说》第8期开始同时连载历史小说《痛史》、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3篇小说,第13期又开始连载《九命奇冤》,这样每期上都有3篇或4篇作品,几乎占了杂志篇幅的一半,有时占了一半以上,成为《新小说》杂志的最主要作家,名声大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成了他小说观念的转折点。但是他内在的思想则没有什么变化。他在《小说丛话》的四则文字中指出:
吾自出里门后,虽未能遍游各处,然久居上海,于各地之风土人情,皆得而习闻之。吾之所闻,以淫风著者,十恒七八。惟吾粤几不知有“淫风”二字。偶有不贞者,则不复齿于人类。初不解吾粤何以独得此良风俗也,继思之,此亦小说家之伟功。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虽皆附会无稽之作,要其大旨,无一非陈忠孝节义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义仆代主受戮,孝女卖身代父赎罪等事,开卷皆是,无处蔑有,而又必得一极良之结局。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为之以良也。惜乎此等“木鱼书”,限于方言,不能远播耳。
他们两人在把小说作为宣传思想的工具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的思想内容则有天壤之别,梁启超主张“小说救国”,但是吴趼人则始终一贯停留在“保教”的水平上,最终提出“小说家之伟功”就在于“陈说忠孝节义”。
《月月小说序》则更清楚地表达出他的这种小说观:“小说能具此二大能力,则凡著小说者、译小说者,当如何其审慎耶!夫使读吾之小说者,记一善事焉,吾使之也;记一恶事焉,亦吾使之也。仰读吾小说者,得一善知识焉,得一恶知识焉,何莫非吾使之也。吾人于此道德沧丧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他指出写作小说的宗旨在于“吾人于此道德沦丧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从表面上看,这与梁启超所说“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一拍即合,然究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吴趼人的小说观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它们虽然在逻辑结构和对待小说的态度上有许多共通点,但其实质内涵正如上面所述,是判若两样的。吴趼人等普通知识分子不能像梁启超那样去影响国家大事。他们的小说观念(理想)和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困惑,而且是变革期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惑。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他们只能揭露时弊,力图纠正,这就是吴趼人和李伯元的社会小说观的内在限制。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限制,吴趼人强调小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态度甚至比梁启超还要激进。在《月月小说序》一文中,吴趼人在梁启超所提出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说的基础上,再加上两种功能,即“补足记忆力”和“易输入知识”之力。他从功利主义的认识出发,十分肯定和无限夸大了小说对社会的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文人,他与重视历史教育的士大夫传统有着不解之缘,骨子里天生有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自然重视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因此,吴趼人向读者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历史小说观“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
如果历史小说可以打动人心,那么在小说艺术上一定要有独特之处。吴趼人分析历史小说的艺术特点:“隐几假寐,闻窗外喁喁,窃听之,舆夫二人,对谈三国史事也。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盖小说家言,兴趣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1](P173)
他又在《两晋演义序》中讨论历史小说的宗旨和其教育上的意义:“旋得吾益友蒋子紫侪来函,勖我曰: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遗误阅者云云。”[1](P172-173)他既强调“发明正史事实”又不完全排斥“蹈虚附会”,要求真实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使读者在艺术欣赏中达到对历史较为全面的认识。他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尤为独特的是,吴趼人发展出一整套“写情”小说理论。吴趼人所说的“写情小说”,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写男女爱情的小说,而指写与生俱来的各类情感的小说,是写无一处用不着的情的小说,是写忠、孝、慈、义等伦理情感的小说,也即写广义的情,写人际关系间的情。那么,吴趼人所说的“写情小说”,与社会小说有什么不同?原来,按照他的理解,所谓“社会小说”,指的是暴露社会污浊的小说,而所谓“写情小说”,指的是表现社会生活中“未脱道德范围”的人际关系的小说。他在《说小说·杂说》中指出:“作小说令人喜易,令人悲难,令人笑易,令人哭难。吾前著《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出版后偶取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坠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能为其难,窃用自喜。然其中之言论理想,大都陈腐常谈,殊无新趣,连良用自叹。所喜全书虽是写情,犹未脱道德范围,或不致为大雅君子所唾弃耳。”
这种对“情”的特殊规范同时也成为他选择小说的标准:“历史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以入于道德之范围之内。即艳情小说一种,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后之投稿本社者,其注意之)。”[1](P170)
此外,吴趼人在小说批评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欣赏的评论文字。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全盘否定。侠人、定一等一些《小说丛话》里的评论家,则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解释古典小说。他反对这两股风气,在《说小说·杂说》中认为,“应当设身处地,为前人所思”,坚持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今动辄喜訾议古人者”,就像嘲笑自己“襁褓之无用”一样没有道理。“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牵引古人之理想,亦非是也。”这种主张和态度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四
李伯元和吴趼人等作为商业性小说杂志的主编和职业小说家,一方面他们对“小说界革命”表示出极大的欢迎和支持,因为小说地位的提高对职业小说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思想受到梁启超理论的影响,也在主编的小说杂志呼吁“改良”、“群治”等时髦口号,但并未像梁启超及其追随者那样走向极端,而是借着这些口号来扩大小说的影响,因此他们对“小说界革命”的支持主要不是体现在口头上和理论上,而是用创作实绩来显示“小说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作为作家,他们也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补充和修正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特别是在对待传统小说的态度上,他们表现得更成熟,也更有眼光。
另一方面,李伯元和吴趼人等与梁启超及其追随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身份各异,梁启超以政治家的身份倡导“小说界革命”,不需要考虑小说的商业性因素,而李伯元和吴趼人则直接承受着文学市场的压力。商业性因素的介入固然能使他们为了照顾读者的审美习惯,考虑杂志的发行量,在理论和创作上不趋极端,更多地保持了和传统小说艺术的有机联系,譬如对《儒林外史》的继承。但是市场的压力必然迫使他们迎合读者的趣味,“小说界革命”的冲击力也就在这种“迎合”中逐渐被消耗,因此,职业作家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保守”,实际上是由于文化商品规律所决定的。徘徊于新旧之间的他们,在小说理想和小说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矛盾,这也是文学步入商品时代共同面临的矛盾。
收稿日期:2002-09-12
标签:小说论文; 梁启超论文; 吴趼人论文; 李伯元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晚清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