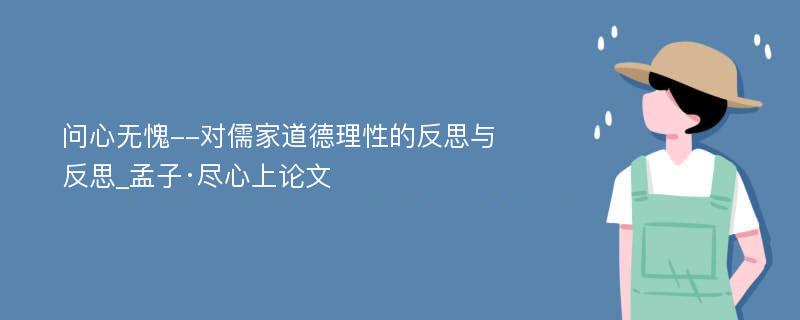
叩问良知的“不能”——关于儒家道德理性的反思与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良知论文,理性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孟子以来,儒家便有“良知良能”一说,到了北宋,张载又提出了“天德良知”说,由此开启了宋明理学中的良知学传统。到了王阳明,便专门以致良知为学。平时,他常常以“此知之外更无知”教戒门弟子;而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征思田的途中,他甚至还专门致书其儿子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王阳明全集·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充分表现了他对其良知之学的自居与自信。阳明之后,良知说风行天下,几乎取得了与天理同等的地位。直到今天,“天理良知”还仍然是国人口中常常出现的概念。
良知当然是道德理性的指谓,尤其是就道德理性在人之内在凝结而言的。在汉语的语境中,它往往起着做人之道德底线的作用。阳明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1](《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正是就良知对整个人伦世界的支撑作用而言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似乎总是强调良知的“能”,总是在高扬其正面的作用,却很少谈到良知的“不能”。其实,强调良知之“能”固然是对道德理性正面作用的阐扬;但叩问良知的“不能”却并不一定就是揭示道德理性的负面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良知的“能”往往体现在它的“不能”中,甚至也可以说,良知正是以“不能”作为其所有之“能”的前提基础的。
一、良知的提出及其所“能”
在历史上,良知首先是以“能”的方式提出的,因为这是良知得以提出的前提,所以我们也首先从其正面作用谈起。对于良知之“能”,孟子是这样表达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孟子·尽心上》)。
在这里,所谓良知良能首先都是指人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知能而言的,那么,这种先验的知能是否就是人的一种生而具有的本能呢?从孟子所举的“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来看,它似乎就是一种本能。但是,从其后面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来看,它显然又不是指人的生物本能,而是指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因为本能只能停留于躯体关怀和躯体需要的范围,并且是以“我”的需要来划界的,而要将这种近于本能的人伦之爱“达之天下”,就绝非生物本能所能奏效;就生物本能而言,也根本无法为自己提出这种超出“我”之需求的任务。由于孟子认为“此天之所与我者”[2](《孟子·告子上》) 又坚持“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它看起来接近于人的生物本能,实际上则是就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所以说,尽管这种道德理性近乎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但由于孟子要求“达之天下”,因而它实际上也只能是就人自觉的道德理性而言的。
张载的良知说则是这样提出的:
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
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3](《正蒙·诚明》)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天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3](《正蒙·大心》)。
在张载的这一论述中,由于德性所知(包括天德良知)主要区别于闻见小知,——后者极言其小(闻见之狭),所以前者也就主要是指其知之大而言的。但是,既然都属于知而又有大小之别,说明其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知”本身,而在于其知得以形成的不同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由于“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其基础自然在于人的五官,是五官“与物接”的产物;至于德性所知之所以能够“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尽性”的基础上的,是“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的产物。这样,如果说孟子的良知良能是人基于内在的道德理性而又作用于伦常日用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那么,张载的德性所知便同样是基于道德理性但又指向客观天道的天人合一之“大知”了。显然,从孟子到张载,良知之所知所能已经从人伦道德的领域拓展到客观天道的领域了。就其“能”而言,这自然是对其正面作用进一步高扬的表现。
到了王阳明,由于其一生险象丛生的从政经历,因而良知并不像张载那样因其所知之大与客观面向而得到弘扬,反而恰恰是因为其在现实人生各种是非关头的“一语之下,洞见全体”[1](《王阳明全集·刻文录叙说》) 的性质而得到精彩的发挥,因而也就得到了特殊的揭示:
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逆之患矣”。……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1](《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仅从这一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出,阳明的良知并不是像孟子那样对道德理性的当下推定,当然也不是对其思辨寻绎的产物,更不是像张载那样将其与见闻之知详细比勘的结果,而是在自己“存亡系于呼吸之际”的从政经历中对道德理性体究履践的结果。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感叹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1](《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从阳明良知说的这一提出过程可以看出,由于良知确实是他得之于其“百死千难”的从政经历,因而在其人生的运用中也就显得格外地得心应手。如“指南针”、“定盘星”以及“一语之下,洞见全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1](《王阳明全集·寄邹谦之三》) 等等,如果以人生为例,那也就真是所谓“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了。这就将良知之“能”高扬到“无不具足”的地步了。
但是,所有这些,毕竟都是从人生实践,尤其是从人生道德实践的角度展开的。如果我们要穷究良知之所“能”,那么它实际上也就主要是面对人生中各种是非、善恶的一种来自道德理性的当下断制或当下裁定。对于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的人生而言,良知确实是“无不具足”的,也确实具有“无不如意”的优点,但一当越出道德实践的范围,良知是否仍然“无不具足”呢?这就涉及良知所“不能”的问题了。实际上,也只有进到这一领域,才能真正进入到良知的核心部位。
其实,阳明生前就曾遇到过这样的疑问和追究。在与徐爱论学中,徐爱就曾这样追问阳明: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1](《王阳明全集·语录一》)
在这里,徐爱的追问就涉及良知之“不能”的问题,但阳明当时却通过良知的“头脑”地位及其“自然”的作用,将其贯注于温清定省等许多客观性的“节目时序”之中,从而使这些节目时序统统成为良知自我实现的“条件”。这样以来,在徐爱看来必须进行客观性讲求的知识性内容,就被阳明以“头脑”之“自然”的作用,完全收摄到致良知(心即理)之主体的实践工夫上来了。实际上,虽然阳明通过高扬良知的“头脑”地位,顺利地实现了这一贯通,但良知是否存在着“不能”的问题毕竟已经提出来了。
二、良知的“不能”
良知是否存在着“不能”?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回到儒学的源头,看看孔孟是否存在着“不能”的问题。因为良知既然是就道德理性在人的主体凝结而言,那么我们自然无法怀疑孔孟具有真正的良知;而孔孟所表现出的“不能”,自然也就体现着良知的“不能”。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所不能的事真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4](《论语·八佾》)。孔子无疑具有充沛的良知,但对“文献不足”的问题,良知也无可奈何,所以孔子只能承认自己“不能”。这说明,对于客观的知识性问题,即使拥有良知也无从措手,因为知识性的问题本身就不在良知的关涉范围;当然这同时也说明,良知本身也并不关心客观的知识性的问题,——良知只关心善恶的抉择与是非的裁断问题。所以,纯客观的知识性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良知的第一个“不能”。
除了知识性的问题,人生中的贫富、贵贱以及所谓遇与不遇等人生遭际问题,也不是良知所能决定的。比如孔子就曾感叹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4](《论语·述而》) 对于富贵、贫贱这样的人生遭际问题,良知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孔子才有“从吾所好”的抉择。这一抉择固然是由良知所发出,但这一抉择本身却恰恰表现了良知对富贵的“不能”。不仅如此,从个体人生的具体遭际到道之兴废这种人类时代性、历史性的命运,也都是良知所无法决定的,所以孔子又感叹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4](《论语·宪问》)。之所以要将道之兴废的问题上寄于“命”,正表现了良知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所以说,在客观的领域,从人生的具体遭际到道之兴废,都是良知所无法决定的。这可以说是良知最为根本的“不能”。
所以,到了孟子,就对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求”做出了明确的划分: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2](《孟子·尽心上》)
在孟子看来,人生中的追求无非是两种,这就是所谓“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由于“求在外者”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所以说是“求无益于得也”,——得与不得、遇与不遇并不取决于主体的良知及其主动的追求,而是取决于客观的际遇。这也就是说,对于一切客观外在的事物(包括人生中的遇与不遇),并不仅仅是主观的追求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对于人生来说,最好是“求在我者”。因为这种“求”,完全取决于自己;而“得”与“不得”,又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追求本身,所以只有这种“求”才是最有效的“求”。这样,孟子事实上也就通过一个“求在我者”,从而将良知之“能”及其作用全然收摄于主体人生之内在追求的范围了;而对所有的“求在外者”来说,由于其“求之有道”,“得”与“不得”又完全取决于客观的际遇(命运),因而实际上也就等于划在了良知所“不能”的范围。
那么,既然如此,张载何以又提出了完全有别于见闻小知的德性所知呢?而且在张载看来,由于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而德性所知的实现恰恰又“不明于见闻”,因而其必然是一种超越于见闻小知的大知;不仅如此,由于德性所知的特征是“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因而它不仅表现为其知之大,而且还是外向的,是对客观天道的大知。这样一来,原本已经被孟子收摄于主体人生道德实践范围的良知,就又被张载拓展到客观天道的领域了。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张载的德性所知不是良知、不属于道德理性的范围?其实,张载的德性所知不仅属于道德理性的范围,而且就是标准的良知,只不过这种道德良知被他专门用来认知天道,把握客观的天道本体而已。他说:“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天之声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属之,莫知其几万里之远也;天之不虞莫大于太虚,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极也。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3](《正蒙·大心》) 显然,在张载看来,如果只依赖耳目见闻,最后必然会陷于“不知”或“莫知”的地步;只有超越见闻并以“尽心”的方式直面天道,才能把握“天之不虞”的太虚。这也就是说,由于见闻之知只建立在耳目的基础上,而德性所知则建立在“尽心”的基础上,因而德性所知不仅比见闻之知知得更大、更远,而且也知得更为深刻、更为准确,这自然是对客观天道的整体把握了。
对于张载德性所知的这一规定,今人牟宗三将其诠释为“智的直觉”,意即人依靠道德理性可以对天道本体形成直觉性的领悟。(注:参见牟宗三著《智的直觉如何可能?》,载《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75页。)我们暂且不管人的道德理性是否拥有这样的穿透力,但张载将道德理性运用于客观外向的认知则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一直“以孔孟为法”[5](《宋史·张载传》) 的张载岂不正好与孟子背道而驰了吗?其实,这完全是佛教刺激的结果,针对佛教“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的唯识之学,张载当然要强调儒家道德理性对天道本体的认知能力,以“与之较是非,计得失”[3](《正蒙·乾称》)。所谓“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的天德良知以及依据德性所形成的对天道本体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德性所知,就都是这样提出的,也是其与佛老“奋一朝之辨”的表现。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才有后来朱子建立在“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基础上形成的对天道本体的“豁然贯通”之说[6](《四书集注·大学》)。实际上,这都是儒学在遇到外来文化挑战时对自家本有的道德理性认知能力高扬的表现,无论道德理性是否拥有这种能力,但其向自己素来所乏或“不能”的客观认知领域的主动拓展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两宋理学实际上正是以“能”的方式表明了自家原本的“不能”,而这种由“不能”向“能”的转化,正是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一个基本的区别。
到了阳明时代,由于理学家前仆后继的努力,来自佛教的理论压力已经基本上得到了缓解,在这种条件下,阳明反而通过对从认识向道德贯通的可能性之质疑,从而又将道德理性拉回到了伦常日用与道德实践的范围。这样,良知也就开始复归于其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领域本身,并从这一领域重新实现其对整个人生的归整与统摄。已如前述,由于阳明是从自己“百死千难”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出良知的,因而在他看来,“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1](《王阳明全集·语录二》) 这就是说,由于人生无非存在于体用两界,而良知恰恰贯通了这两界;既然人生不可能超出体用之外,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存在能够超出良知之外的内容了。具体来说,就是“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杂于见闻”[1](《王阳明全集·语录二》)。进一步看,“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1](《王阳明全集·语录二》)。这样,阳明就通过良知对体用两界的贯通与对人生日用及其见闻酬酢的充分渗透,从而实现了对整个人生的统摄。
不仅如此,由于良知本身既“不滞于见闻”又“不杂于见闻”,因而就这一点来说,自然也就不能排除见闻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也无法排除见闻独立自在的作用,因而见闻及其作用也就仍然可以存在于良知之外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阳明不得不再向人的五官——生物本能的领域拓展,以实现对人生全面而又彻底的占领。在《答南元善》一书中,阳明写道:“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这就是说,由于良知是做人的“头脑”,因而离开了良知的作用,人的耳就无所谓闻,目也就无所谓见,而人的心自然也就谈不到真正的思与觉矣。这显然是良知对人生全面贯通的表现,也无疑包含着对日用伦常的全面占领。
但这样以来,看起来阳明是处处高扬良知的渗透与统摄作用,是强调良知之“能”,实际上,当他处处强调良知之所“能”时,正好反衬且也表现着良知本身的“不能”。比如说,既然良知既“不滞于见闻”又“不杂于见闻”,那就正好说明良知是良知,见闻是见闻,但阳明却一定要通过内在的渗透,使良知全面地占领并彻底驾驭见闻,从而达到全面占领人生的目的。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一地步,那也就真正成了所谓离开良知,耳不能听,目不能见,心也就不能思与觉矣;但是,如果人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地步,还需要阳明如此提倡吗?所以,阳明的提倡与强调,正说明了良知事实上对人生有所“不能”;而阳明对这两大领域(见闻与知觉)的推进与渗透,也正好说明它事实上存在于良知的驾驭与统摄之外。所以,良知之所“能”的历史,实际上也正好是其所曾经“不能”的历史。
三、从“不能”到“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良知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能”,但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不能”。那么,它究竟在什么条件下“能”、又在什么条件下“不能”呢?其“能”与“不能”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而在其“能”与“不能”之间,是否存在可以转化、可以相互过渡的因素呢?凡此,都直接关涉到良知作用的发挥,因而也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看良知的“能”能够实现于什么条件下。已如前述,良知无疑是一种道德理性,是道德理性的主体(内在)化凝结与知能化表现,因此,凡是在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的领域,良知无疑具有善恶抉择与是非裁断的能力,对人而言,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而又必然的、要求主体善善恶恶、是是而非非的绝对命令。除此之外,越出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的范围,良知也就必然会陷于“不能”的地步,如孔子对“文献不足”的问题,对自己贫富、贵贱、遇与不遇以及道之兴废的命运问题,都属于“不能”的范围。在这里,不能说因为孔子拥有良知,就可以使自己由贫到富、由贱到贵以及由不遇转为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并不在良知的管辖范围,因而良知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凡是不在道德的管辖范围,良知也就必然会陷于“不能”的地步。
那么,这种“能”与“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由于良知是人的道德理性,属于主体性的范畴,因而凡是在人所能够涉足的领域,良知也都能够发挥其抉择与裁断的作用;反之,凡是客观自在亦即所谓纯客观的领域,良知都必然是无从措手且也无能为力的。比如王阳明对岩中的花树,就一定要将其收摄到“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并由此说明“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再比如对于天地鬼神万物,阳明也一定要将其收摄到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然后才能发挥良知的裁决作用:“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1](《王阳明全集·语录三》)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1](《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其实,这种“没有”并不是客观自在的“没有”,而是主体实践的“没有”,是价值与意义的“没有”;或者说,这种客观而“千古见在”的“有”,由于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对人来说,它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这说明,良知的权衡与决断只能存在并发挥作用于人生实践的范围,离开了主体的人,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既谈不到良知,也就无所谓其抉择与裁断的作用了。当然,反过来说,只要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范围,良知也就一定能发挥其抉择与决断作用,有时这种“能”甚至恰恰是以“不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论语·述而》),看起来这似乎只表现了良知的“不能”,其实这种“不能”正是良知之“能”的表现,是良知这种绝对命令迫使孔子不得不做出常人所无法做出的“不能”之抉择的,只不过这种抉择之“能”仅仅表现为“不能”而已。
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良知之“能”与“不能”的界限也就是相对的,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与范围的不断拓展而不断地变化。比如在孟子,良知良能就主要表现为“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但到了张载,良知就能够表现为“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从而可以把握“天之不虞”的太虚,而到了王阳明,离开了良知,人甚至不能见与闻、不能思与觉矣。这说明在孟子那里,良知仅仅作用于人伦日用的范围,到了张载,良知就成为对天道本体的一种认知,而再到阳明时,良知就成为人之见闻知觉包括各种生物本能活动的最高主宰了。固然,从现实存在的角度看,人的见闻知觉未必都有良知运行其间,离开了良知,人也未必就真的不能见与闻、不能思与觉,但从阳明的角度看,如果人能够时时处处都以良知之是为是,以良知之非为非,从而将良知完全内化为“自家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见与闻、思与觉,不也正是良知之见闻与知觉吗?而离开了良知这一“自家的标准”,人又将何见何闻、何思何觉呢?阳明的“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
到了现代,由于“德”、“赛”两“先生”的引进,又由于儒学对自身“不足”的进一步照察,因而良知之“能”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让我们看看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熊十力对良知之“能”的发挥:
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以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是良知之发用。何至有支离之患哉?良知无知无不知,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此格物也。皆良知之发用也。总之,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7](P668—669)
显然,在熊十力的这一现代诠释中,不仅“晨昏定省”这些传统的人伦日用,就是“革命”、“抵抗”乃至“入科学实验室”等一切现代人的活动,都全然成为“良知之发用”,自然也就成为“良知之妙用”(能)的表现了。而牟宗三关于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同样也是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拓展的表现。这说明,良知的作用范围、良知由“不能”向“能”的转化,完全是随着其主体对良知的体认度与认同度的逐步深入而不断拓展的,一旦人能够完全以良知之是非为是非,以良知之标准为“自家的标准”,那么,其人生必然会成为良知观照与统摄下的人生,其世界也将自然会成为良知良能的世界。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良知,看看它为什么会存在“不能”?已如前述,作为道德理性的内在凝结,良知始终是人的良知,也始终和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非人的世界——所谓纯客观的世界,因为完全脱离人的存在,因而也就是良知所首先“不能”的领域。作为“不能”,这可以说是良知最根本的“不能”;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没有”或“缺乏”的“不能”。因为良知既然是人的良知,它也就必然要以人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在没有良知的条件下追问良知之能,我们就必然会陷于像罗钦顺那样,因为追问“山河大地”、“草木金石”是否有良知的问题,从而根本否定良知的存在[8](《困知记·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崇一二》)。而那样一种追问,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将良知还原为天地万物之理了,这恰恰抹杀了良知之为良知的特征,因而也是从根本上对良知的取消。
那么,进到人伦世界以后,良知为什么仍然会存在“不能”呢?这是因为,作为一种道德理性,它在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的同时,本身也就防范了相反的可能,比如当孔子在感叹“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时,同时就不得不明确表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论语·里仁》) 再比如孟子,虽然不断地要求人们将爱亲敬兄之心“达之天下”,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明确表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2](《孟子·尽心上》)。显然,这种“不能”,正是良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违背自己道德本性的“不能”,与良知在纯客观领域的“根本不能”相比,这可以说是良知在现实世界自我实现过程中现实的“不能”。就是说,作为一种道德理性,良知不能容忍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意念等等;一旦陷入了这种“不能”——使“不能”成为“能”,良知事实上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实生活中所谓良知泯灭或泯灭良知,正是指此而言。所以,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说良知确有所“能”,那么,这种“能”也就只能建立在“不能”的基础上,并且是以“不能”作为其“能”之先决条件的;如果说良知之“能”确实揭示了我们人生的应然性目的性存在,那么,良知的“不能”则是以相反的方式确保着我们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合目的性。
除此之外,作为一种道德理想,良知的“不能”实际上又是其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保持张力的表现,也正表现着其对现实的一种理想性与超越性。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的“不能”。如果良知完全退化为现成的知觉或所谓“自然明觉”,如果现实社会的一切也均能成为良知之所“能”的世界,那么良知自然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理想性与超越性。历史上的泰州学派,正是通过将良知的自然化、明觉化,从而走上消解良知之路的。所以说,正是良知的“不能”,才确保着良知之为良知——道德理性与道德理想的标志;也正是这种“不能”,才支撑并观照着良知的发用流行之“能”,从而也支撑着我们应然的理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