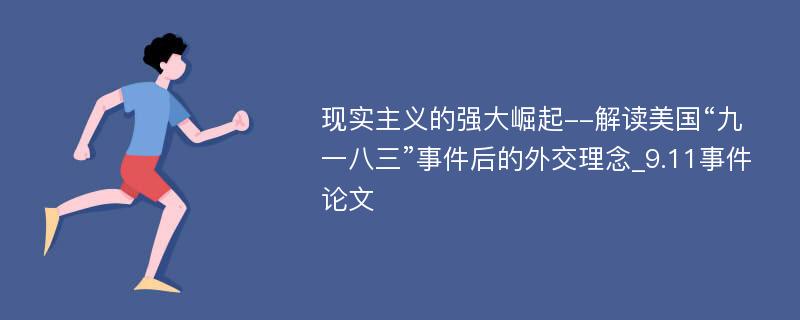
现实主义强劲抬头——“9#183;11事件”后美国朝野外交理念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野论文,美国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外交论文,强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后美国朝野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既可视为对于“9·11事件”后整个形势变化的新的认识,但也表现出“9·11事件”之前美国对于其外部世界认知的某种延续。
首先是对“9·11事件”对整个国际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究竟如何判断,就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预言,不光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称,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一切,这是媒体上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视之为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事件”之前的所有背景与积累。时下当红的一份国际研究杂志《国家利益》的主编亚当·伽芬寇则总结了当前的两种主要倾向。他认为,其一是“9·11事件”将把美国外交多年来的模糊与犹豫一扫而光,把美国从一个世纪以来集中于与欧洲法西斯和苏联为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与新对手较量。其二是“9·11事件”是无任何先例的变化,所以,将为未来留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因素。
“9·11事件”之后在美国外交界的这场讨论与争论,涉及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仅有关乎外交决策,而且事关理论。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强劲抬头。就笔者之所涉猎范围,我把这一流派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分别称之为是“乐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的现实主义”以及“历史现实主义”。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与其观点是否真正反映现实,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一派别与强调规范、道德、法律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理想主义流派”不同,“现实主义流派”强调的是实力,乃至强权的作用。
乐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之后一个月不到,由《国家利益》杂志发起,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名为“‘9·11事件’的影响”的研讨论。会上,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瑟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查尔斯·克劳瑟麦的观点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他直截了当地引用布什总统的话称:9月11日那天可视为是一个测量温度的计量器,我们将以其他人对“9·11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对美国关系的亲疏,以及来划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克劳瑟麦认为,这是因为,“9·11事件”反映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含意是指:恐怖主义力量取代法西斯和前苏联帝国成为美国外交原则的对抗者;虽然,美国独大的单边主义结构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但是恐怖主义激进力量对美国的打击使得美国“变弱了”;恐怖主义敌手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武器与进攻技术,借助狂热的宗教情绪,甚至依靠了对死亡的崇拜,使得挑战霸权出现了全新手段,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结构关系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克劳瑟麦还称: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中以美国为一方和以阿富汗塔利班势力为一方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不均衡关系”,虽然“美国正在变弱”,但是相对于被孤立、被封锁的塔利班而言,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剩余力量”。因此,克劳瑟麦提出,为使美国不再“变弱”,“当务之急是有赖于清醒的理智和成功的反应”。何谓“成功的反应”,克劳瑟麦认为,那就是要把在单边主义国际结构中独大的美国所“剩余的实力转化成为明确的政治后果”。
总之,克劳瑟麦以“显示力量”,“结盟”和“转化剩余实力”为核心范畴展示了他对“9·11事件”国际关系变化的理解。他在发言总结中称:“这样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比许多人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更加朝向经典的现实主义。”笔者所冠“乐观现实主义”之名即以克劳瑟麦的这种“自信”而来。
悲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后的美国对外关系讨论中,一方面传统类型的“现实主义者们”表现得信心十足,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情怀,笔者称之为“悲观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于去年1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认为,“9·11事件”之后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最无稽之谈,便是出现了“两大幻想”:其一,是以为由于当前美国急需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轻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作出历史性的选择,力争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一部分,尔后再变成为美国的盟友。与克劳瑟麦这样的“乐观现实主义者”相比,经验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热津斯基更倾向采用当今国际变局中种种现实的态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北约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启用“第五条款”,尽管俄罗斯率先,而后许多国家都支持美国反恐怖的行动,尽管伊斯兰国家会议谴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一致,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推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但是,他认为进一步观察之后便不得不对目前态势“表示很大的悲观”。用他的话来说,“团结合作是存在的,但是言辞多于行动。实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被改变。”
布热津斯基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当前反恐怖运动中的问题。
先看欧洲。布氏尖锐地指出:美欧传统合作中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部分——欧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当前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并不是以整个欧洲,而只是以个别国家的身份参与。甚至,近来欧洲不少国家还开始对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的强度与范围表示担忧。
至于俄罗斯,布氏坚持认为:普京是在观察美国是否真正愿为反恐怖联盟付出实际的代价,对俄罗斯而言,这包括北约东扩、ABM协议、外债的减免以及俄国内的车臣问题等各个领域。所以,布热津斯基表示“普京是想要进入西方与之为盟;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向美索要让步”还值得观察。他特别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国呼吁要与俄一起建立欧洲的强权,这样的强权实际上是在挤压美国。
布热津斯基指出:简而言之,在反恐怖的“团结合作”中(引号为布氏所加)甚至还找不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定义,而是各有各的说词。他说:“对印度人来说,恐怖主义威胁指的是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对俄罗斯人来说,指的是车臣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巴勒斯坦;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则是以色列;对美国人来说,当然不是伊斯兰教,但是在本·拉丹这个撒旦式的电视形象背后,究意又是谁呢?”所以,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布热津斯基担心以后的几个月将是对美国真正的考验,他尤其希望美国不要为试图稳定局势。而花上几年功夫纠缠在阿富汗事务之中。
历史现实主义
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夫威尔茨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1997年和2000年,沃氏曾先后发表两篇长文,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试图为当代美国对外战略指点迷津。鉴于他基于历史分析来铺陈他的现实主义理念,因此笔者把之归入“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类。
沃尔夫威尔茨的借古喻今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起因,是因为“既定秩序捍卫者”的“民主英国”遭到了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的德国的发难”。沃氏竟然以此比附当代的中美关系,直言中国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
此文既出,曾受到欧洲著名国际问题高等学府——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相兰欣博士针锋相对地回击。相博士的论文批驳了沃氏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误读:第一,当代中国根本不是当年德国;第二,当代现存秩序和当代现实的挑战者恰恰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第三,这位学者还运用史实在学术上证明上世纪初英德关系中的挑战者也恰恰就是英国,而并非德国。这场争论曾在欧美学术界引起震动。
其实,沃尔夫威尔茨关于冷战教训的总结也正好证明了他上述观点的谬误。他在上述两篇长文中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从上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美建交,一直到克林顿总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主张对华政策的强硬态度。非常明显,布什政府竞选期间及而后一度强调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加大对台湾军售力度等等,这与沃氏上述理念有直接的关系。至少,他试图挑战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既定秩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一个多月,沃尔夫威尔茨对《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则改变了调门。当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后果时,明确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军事就会越强大……军事上强大了并不意味着军事扩张。”“历史悲观主义者说,一百多年前,德国与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就是走的这条道路。我认为,历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但是经济增长也使和平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这位著名强硬派核心人物为何会改弦更张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反恐怖斗争“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加强”。
虽然,“现实主义流派”远不是美国对外关系指导性理念的全部,不过显然对当今美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性的影响。眼下无论“乐观的”、“悲观的”、还是所谓“历史的现实主义流派”之间的种种争论和改弦易辙,都体现出“9·11事件”之后美国朝野对于对外关系的一种新的解读与体认,虽然上述种种说法的含义与背景,还都有待观察,更谈不上会马上发生所谓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向,而且,美国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协议》非常明显是单边主义倾向增长的标志,但不容忽略的是,转型中的美国外交毕竟还有着另一些更为复杂的值得观察与思考的变化。
多年以来,特别是冷战以后,美国对外战略定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国际格局转换期,一个新兴的崛起中的大国必然会对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发起挑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之下,“寻找敌人”就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必然逻辑。试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人们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样的“敌我”逻辑,而去寻求新的和谐整体呢?“9·11事件”的血腥教训理应给人们提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