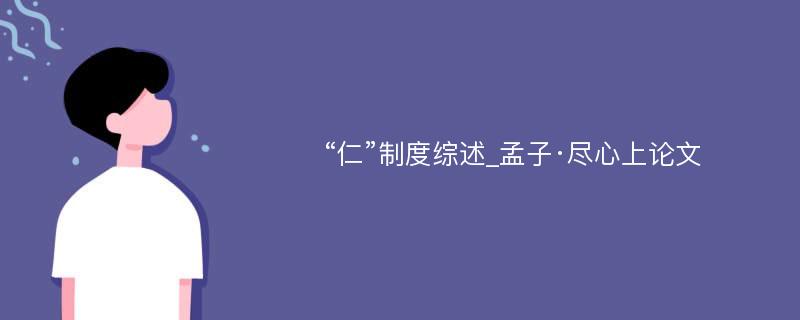
“仁学”体系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仁”是孔孟学说的核心概念,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所公认。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把“仁”提升为一种最高的价值原则,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予以丰富、发展,而建立了系统的“仁”学体系。他不仅为“仁”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更强调了“仁”在政治领域的意义,提出了“仁政”思想。
李幼蒸主张把“仁学和儒学分开来”,并认为“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①对于这一观点,笔者非敢苟同,但认为突显孔孟的“仁学”确实对儒家当代的转型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全球伦理基金会”的奠基者之一、德国著名宗教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在讲到儒家的宗教性时提出一个独特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宗教相互对话的语境下,把儒家的仁作为人类共同伦理的基础,难道没有考虑的价值吗?”②
可以认为,“仁”的概念至今仍然体现了儒学的真正本质。孔孟的“仁学”既包含心性之学也包含政治儒学。作为道德哲学的“仁学”不仅仅有伦理学暨政治学的内容,而且有宗教信仰的维度;不仅是价值体系,也是信仰体系。下面,笔者从“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仁的本质、君子论、性善论和天命观几个方面入手,简述“仁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揭示其相互间的逻辑联系。笔者确信,只有全面分析和同时发展仁学的这几个方面,才能使“仁”真正作为普世价值继续发展和发挥作用。
限于篇幅有限,笔者的分析以《论语》、《孟子》二书为主要材料。
二、“仁”升成为核心价值标志着先秦思想的飞跃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儒家思想以及“仁”作为核心价值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当时其他学派一样,儒家也是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和政治变动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对传统的规范制度,即礼发生危机的回答。孔子一生为恢复传统的礼治秩序而努力,试图建立一个“有道”的天下,其政治方案可以用“正名”来表述。子路问老师:“如果卫国的君主让您执政,您先做什么?”(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道:“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正名”的意思虽然是“纠正名分”(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但是,我们也可以把“正名”理解为“纠正现实社会中不符合价值规范的东西”。反过来也可以说,“社会现实要符合社会理想”、“实然的社会要符合应然的社会”。进一步说,应然的社会总是一种基于某种价值原则构想出来的理想社会,那么也可以说,“正名”就意味着使社会现实合乎某种价值原则。在孔子看来,“仁”就是这种价值原则。再者,孔子出于对当时社会上一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的不满,而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如果说“有其名而无其实”表示了传统礼治秩序的危机,那么,“正名”就是孔子为恢复传统礼治秩序而努力的表达。而“正名”的切入点就是“仁”。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他认为,“仁”是“礼”的根本;一个人没有仁心,所行礼仪也没有意义。龚建平说:“孔子对周礼的改造,其重要内容就是提出‘仁’这一概念,并以仁为基本精神来重新解释礼,赋予礼以新的内涵”;“仁是意义,礼是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的方式”;仁是“礼的内在根据”。③所以说,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正是在“仁”的概念中发现了“礼”的内在意义(sense)。
“仁”和“礼”的这种关系,正好与潘自勉对价值(或价值取向)与规范之间关系所做的解释相吻合。他说:“因为价值取向决定了规范中‘应当’的内容,价值成为规范存在的根据”④,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仁”是“礼”存在的根据。孔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危机的反思,在礼仪的背后发掘出了“仁”的精神、找到了“仁”这一道德价值内核,使礼仪不只是一种形式。
因为“仁”的价值是在对作为规范(习俗)的“礼”进行反思之后而产生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仁”的意义的发现是先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飞跃。德国汉学家罗哲海在其《轴心时代的中国伦理学——在向后习俗思想的突破这一视角下的重构》一书中,把心理学家科尔伯格(Kohlberg)关于“道德意识发展逻辑”的理论应用到对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分析中,详细解释了这种飞跃。依据他的分析,可以把“礼”定位于所谓的“习俗层次”,而把“仁”定位于发展水平高于“礼”的“后习俗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人们的行为取向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内在的“普世伦理原则”(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orientation)。⑤如果从个体道德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即是从被动的遵守规则向自觉按照价值规范行事的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我价值得以提高、主体意识得以凸现;同时,人作为人的责任感也会相应提高。
因此,对“礼”的反思和价值原则“仁”的发现,并不是对作为“习俗”的“礼”的否定,而是为“礼”找出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以便提高“礼”的有效性,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达到“仁”(价值)与“礼”(规范)的统一。用胡林英“道德内化过程”的话说,就是“他律和自律统一的过程”以及“德性形成的过程”。⑥
三、“仁”的伦理本质:爱人、忠、恕
“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而孔子的解释是多样的。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而当立志于仕途的学生子张问“仁”的含义时,孔子则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解释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仁学是“实践之学”,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不同,仁的实现形式(manifestation)自然也不同。比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在父慈子孝、兄良弟悌这四种具体社会关系中,我们能看到“仁”的伦理本质,那就是“爱人”和“相互性”(reciprocity)。不论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如何,“爱人”和“相互性”这两个本质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常所说的“尊老爱幼”就不完全符合“仁”的精神:过分地强调“尊老”,会让人忽视对长辈尊重时必须有爱心这一面;而片面地强调“爱幼”,又会使人过于溺爱儿童,却不尊重他们的人格,从而缺少“相互性”的一面。所以,在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时,应该补充以“爱老尊幼”的提法。
先讲“爱人”。“仁”表达了一种善心和善意:不论对方怎样,都善待之。当樊迟另一次问老师“仁”的含义时,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这有两层意义。其一、“仁”作为伦理情感,首先是指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孟子在解释人生而有之的“良能”时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但是,爱亲人只是爱人的基础:家庭是人生学习爱他人的第一个场所。所以,必须把“爱亲”推广到“泛爱众”才是真正实现了“爱人”。孟子的“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所以,“仁”作为爱的感情,既是天生的也是应该内化的感情需要。
“仁”另一个本质“相互性”,实际就是“忠恕”。孔子自己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在老师走后问曾参。曾参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以,冯友兰先生说:“行忠恕就是行仁。”⑦
关于“恕”的含义,学术界意见较统一,主要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译为“自己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做的事,也不要对别人做”。这句话,《论语》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孔子对其弟子冉雍讲的。我们知道,孔子认为冉雍非常适合做领导工作。当冉雍问老师什么是“仁”时,老师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二次是对子贡说的。子贡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老师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关于“忠”的含义,学术界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似乎出于对《论语》中的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一种观点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引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后解释道:“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和冯友兰等学者的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更强调冯友兰在解释“忠”时提到的“尽己”。他们大都援引朱熹“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句话。如张茂泽和郑雄把“忠”作为“尽己”之学,而把“恕”作为“推己”之学。与此相应,他们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推己”(恕)的两个方面,认为前者是“从正面说的”;后者是“从反面说的”。⑨
依笔者之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要是“恕”的含义,也预设了“忠”的含义。这种双重含义可以在皮伟兵的论述中看到:一方面,他引用冯友兰的观点,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分别解释为恕(推己及人)的“消极的方面”与“积极的方面”;另一方面,他却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视为孔子对“忠道”的解答,并解释道:“孔子的忠是修己,是对自己的要求,意思是要尽心竭力修炼好自己的德行。”⑩
无论如何,“忠”、“恕”与“爱人”三位一体,构成“仁”的本质。“尽己”为“忠”,但也包括“立己”和“己达”。“尽己”是“推己及人”的前提,而能否做到“尽己”,又必须通过“推己及人”(恕)表现出来。所以,“尽己”与“推己及人”是同一个过程,两者相互联系。而“爱人”又必须在“尽己”和“推己及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和不断得到验证。
当然,“恕”主要是指主体应把对方看成同类,更强调了人己关系的相互性,要求人们以己之心去度他人之心。所以,“恕”也更具有对他人的指向,比如对他人的同情心、宽恕和关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底线。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上》)。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恕”更高的要求,以“立己”和“己达”,即“尽己”为前提。
与“恕”相反,“忠”虽然也涉及人际关系,但更是针对主体本人所说。所以,对“忠”的分析也首先应从主体本人入手。孔子讲“忠”,主要是尽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端正对人对事的态度。换句话说,仅仅是表现于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还不能算是做到了行仁。只有这些外在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诚意,也就说做到了“尽己”,才算是“忠”,才谈得上是“仁”。
在孔子那里,“忠”与“诚”、“信”相近,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和践诺守信之意,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论语》中记录了“主忠信”(《论语·学而》、《论语·子罕》、《论语·颜渊》)、“言忠信”(《论语·卫灵公》)和“言思忠”(《论语·季氏》)等孔子的言论。这说明他把忠信作为说话办事的原则。孟子也把“忠信”视为和“仁义”以及“孝悌”同样重要的原则(《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告子上》、《孟子·尽心上》)。具体地说,就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要说心里话,而不是说对方想听的话;做事要尽心竭力地认真做,而不能只是敷衍了事或者是做给别人看。另外,“忠”本身包含了与人为善、教人行善。孔子对子贡讲交友之道时说:“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孟子也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
再进一步分析,“尽己”首先意味着“成己”。梁涛在分析郭店竹简里出现的、由“身”和“心”构成的“仁”的另一个字形时指出:“仁”表示“心中想着自己,思考着自己”,所以又有“成就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的意思。(11)笔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对“忠”的解释。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忠”与孔子所说的君子“修己”以及孟子所讲的君子“独善其身”和“诚心”之间的逻辑联系。“尽己”首先意味着“尽心”,保存和培养自己的善心(本心),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努力成为君子;不论别人怎么想和做什么,不论别人是否在场、是否观察自己,君子都会依仁行事。
因此,“忠”(尽己)首先应该理解为“诚心对自己”、“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自己的原则”、对自己问心无愧。孔子曾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也就是说,即使儒家说的“忠君”,也不是“盲目服从”的意思,而是说要有自己原则、服从高于君主个人的原则。
最后,从“仁”的整体意义来看,先秦儒家常以“人”释“仁”:如“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和“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种解释表明,在儒家思想中,“仁”被视为人的本质,即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孔子倡导“修己”(《论语·宪问》)、孟子倡导“修其身”(《孟子·尽心下》),这又表明,“仁”又被视为一种道德修养,一种人们应该通过道德内化而培养成的、自觉遵行的原则。孔汉思说得很好,“仁既是人本身所具备的,也是对人的要求:既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任务”,所以,“人应该真正成为人,也即成仁”(12)。
下面,笔者先讨论“仁”作为人的任务,即成为君子的问题,再讨论“仁”作为人的本质,即“性善论”的问题。
四、行“仁”的道德人格和政治主体:君子
“仁是最高的德,是不断企及的理想和目标。”(13)这句话非常恰当地解释了“仁”作为人的任务这个问题。与“仁”的“忠”和“恕”的本质相应,培养道德的过程包含“独善”和“兼济”两个方面,其最高理想当是“内圣外王”。当然,“圣人”(圣王)是理想追求的逻辑上的最高点;这一理想的提出是为了确立努力的方向和标杆,而它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子贡问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与“圣人”不同,成为“君子”却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比如,孔子认为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准则:“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换言之,君子是以圣人为最高理想、在现实中追求“仁”这一最高善、并在人生之中不断完善自己和帮助他人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精神高度的人。从“仁”与“君子”的逻辑关系上看,仁学“不仅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内容的表述,而且是一种合格实践者养成学”;因为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士”代表着这种具有“个人伦理选择意志”的“合格实践者”,所以仁学又“是君子学(狷)和士学(狂)”。(14)
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君子是内化了规范、并有道德自律能力的人。这种观点在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能看到。其开篇为:“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五行皆形于内而时习之,谓之君[子]。”(15)
最后,如果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又说明,君子的人格不仅包含独立的意志,也包含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
当然,“君子”不仅是对那些在求“圣”的道路上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的描写,也是对这一类人的要求。当子路问老师,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时,孔子回答:“修己以敬。”子路又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回答:“修己以安人。”子路还是不甘心,继续问道:“如斯而已乎?”孔子这才回答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
孔孟的这两段话,不仅讲了君子修身的阶梯,也说明“圣人”和“君子”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也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这种对“圣人”和“君子”的双重理解,又与“伦理政治”这个中国制度和思想的特点相对应。在“伦理政治”的模式中,政治和伦理是统一的,伦理规定政治目标,政治是为了实现伦理目标。从仁与君子道德培养的关系来看,可以说,仁是君子行为的本源(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出发点,仁意味着善心,作为目的,仁意味着“安人”、“安百姓”。
余英时说得好:“由于‘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16)当然,行“仁道”既是对君子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像君子一样为政。换言之,安人、安百姓实质上还是表达了一种“治人”的统治关系。
这种伦理政治模式中的统治关系可以用孔子的“德治”思想概括。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的两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之以德”表述了通过教化培养人们的道德心的主张。而“为政以德”,则表达了执政者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品德,凭借“道德感化力”治理。
这样,“德治”的思想又包含了强调榜样的作用和力量。《论语·颜渊》中讲了这件事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孔子不仅表达了他对“政治”的理解,以伦理价值及其正确性来规定政治目标,也强调了具有君子道德风范的执政者所能起到的模范作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执政就是使人们端正行为;你自己带头端正行为,谁还敢不端正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他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出发,试图说服当时的执政者实行“仁政”和“王道”(《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讲‘仁’,更多的是强调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君以‘仁爱之心’来施政”,所以,孟子的“仁政”说是对孔子的“仁”学的继承、深化和发展。我们知道,孟子对学生公孙丑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也给梁惠王、滕文公阐述行“仁政”的办法(《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滕文公上》)。总结夏、商和西周的历史后,孟子得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和“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的结论。这里的“以德行仁”就是通常所说的“王道”,即不通过强权,而是通过道德教化让老百姓心里服从,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下面,我们探讨“德治”、“仁政”和“王道”的人性论基础,也就是“仁”作为人的本质的问题。
五、“仁”的人性论基础:性善论
人性论是对人的本质属性所作的深层次的探讨,因此,它本来就是“仁”的学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孟子以其“性善”论为孔子“仁”的思想建立了基础。
从现有文献来看,孔子谈到人性主要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句话。李亚彬解释为“人有相近的本性”,而“后天的环境习染使人的道德水准相去甚远”。他认为,“孔子在试图寻找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内在关联。”(17)当然,孔子的弟子不仅继续深入地探索了“仁”等道德价值与人性的关系,也继承和发展了人类道德“来源于天”的思想。《中庸》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头就是证明。在从郭店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中也能看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仁,性之方也”和“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这类观点。孟子的贡献则在于他对“人性善”的论证,并以此发展了“仁学”。
因为孟子将人的生理欲望追求、道德追求区分开来,所以,孟子所言“人性”,实际上指的是天赋予人、只有人所具有、并表现于“道德追求”的“内在追求”。因此,人天生有善性,就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他也说:“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所以,所谓“人性”,就是指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君子能保持和发展而小人却会失去的东西,也即人的道德意识的萌芽,孟子称为“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或者“本心”(《孟子·告子上》)。另外,孟子将仁的根源与根据直指人心。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孟子所说的“心”实际上指的是内在于主体的“道德本心”,而且也能看到,他试图给人们培养和发展这种“道德本心”、并由此而成为能“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的君子指出一条道德自律的道路。
总之,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在他那里,性在心中,心性为一。“心”是天之所与我者,“性”是人所固有的本质。不过,孟子论述的更多的还是人“心”。首先,“心”有双重的作用:它既是思维的器官、具有理性的功能,也是产生情感的器官。关于前一种功能,《孟子》中有个例子。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他:“为什么同样是人,有些人是君子,有些人则是小人?”孟子回答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心”的“思”这个功能,对道德意识产生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二,人的善心、善性来源于天。
关于“心”的后一种功能,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咋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孟子不仅以人们能观察到的现象直证人性本善的论点,也具体说出了能发展出“仁、义、礼、智”这四种人类基本道德意识的萌芽。他接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不言而喻,道德本心就是道德的萌芽。
从上句也可以看出,孟子把道德意识本身(仁、义、礼、智)和道德意识的萌芽(仁、义、礼、智之端)明确区分开来。所以,他说“仁、义、礼、智”,有时也指道德意识萌芽。比如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意思是,道德意识萌芽既然是天所给与的,也就是人所内在的,而不是来自于别人和社会。
当然,生活中不是人人都会成为有道德意识的君子。但是,这与孟子所谈的“性善”并不矛盾。如果某人没能产生和发展出道德意识,按孟子的观点,那只是说明他心中本来存在的道德意识萌芽没能得到发展;或者是因为这个人被孟子所说的“人爵”(《孟子·告子上》),如官爵、地位等不是天赋予人的外物所迷惑,或者因为这个人过于追求生理欲望,即孟子所说的“小体”(《孟子·告子上》)。孟子在批判告子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因此,道德意识培养的关键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省去体验和发扬光大人内在的道德意识的萌芽,做到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求则得之”也即君子成长之路。换句话说,“人性善”并不是说人人都会自动成为有德性之人。人有善端,只是人能产生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而成为君子的必要前提,而不是足够的条件。相反,只有后天的努力才能使人最终成为君子。孟子提出“人性善”和保存“本心”的观点,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培养道德意识和情感不难,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谓“为仁不难”;另一方面,它使人为什么能产生和发展“仁”等道德意识的问题得到了理论解释,从而为“仁学”的继续发展建立了基础。这样,“人性论”和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君子论”就有了逻辑关系。
最后需提及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仁政”和“王道”的思想紧密相连,或者说,孟子提出“性善”论,也是要为他的政治理想提供理论基础。笔者以上曾引孟子的这句话,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实际上,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后面是“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句话。在这里,孟子讲的是“仁政”。而他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梁惠王上》),则是他为了说服当时的君主施行“仁政”和“王道”的最好例子。
六、“仁”的内在超越来源:天命
上面提到,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意识来源于天。在《孟子》中,我们还能找到更具体的例句。孟子说:“夫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这两句话很清楚地表明了“仁”这个核心价值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天命”之间的逻辑联系。
把“天”视为人类社会道德的来源,一方面,能为伦理道德的存在和维护提供一种高于人类本身的东西作为最终依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伦理道德存在和维护的论证已经进入了信仰的领域。李幼蒸说:“信仰的产生导致人生方向的确立,这正是宗教的特有效力所在。仁学正因为同样具有产生人生信仰的力量而具备了宗教这一方面的职能。”当然,因为“仁学是学而后信,而其学又是经验本性的”,所以,“现代仁学君子学是通过不断丰富个人知识来达成信仰目标的。”(18)这样,核心道德“仁”、道德的来源“天命”和道德之人“君子”之间逻辑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天命”观一开始就与人的道德问题紧密相连。我们知道,“天命”观产生于西周初。为了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提出了包括“敬德保民”在内的“天命”思想。一方面,他们宣扬,周代商统治天下是因为文王、武王以其“敬德保民”的政策得到了“天命”;另一方面,他们也告诫自己,只有继续推行“敬德保民”的政策,才能保有“天命”,从而保有自己打下的江山。按照这种观点,天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赏善惩恶的意志:谁有德,就奖励谁,就把统治天下的大命赋予谁,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相反,如果在位的君主失德,作为惩罚,天就会收回其统治天下的大命。所以,在位的统治者必须“敬德配天”。
虽然儒家所持的政治立场与统治者本身不尽相同,但他们继续发展了“天命”思想。他们相信,天不仅有意志、有道德标准、能主宰人类的命运,同时也相信,天为道德本体、即道德的来源。所以,一方面,他们对天持有敬畏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并相信能通过自己努力去认知和接近天,达到内在超越的“天人合德”。比如,孔子称赞古代圣君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里,天不仅被看成是高于人间任何人和事物、只有圣君才能效法的至高神,也间接表达了天本身就是人间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准则。正因为君子认识到了“唯天为大”的道理,所以他们才有“畏天命”(《论语·季氏》)的态度。另一方面,与“知天命”(《论语·为政》)的过程和境界相应,他们也产生和怀有受命于天而救世的信念。当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险时,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论语·子罕》)而当他在宋地受宋国司马桓魋的威胁时,又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样的信念度过困境。
对天主宰人事以及君子受天命的信仰,不仅能使君子富有为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而奔波的责任感,也能使他们对人世间的事情和个人的成功抱某种超然的态度。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命”,即我们以下将要说到的“修身待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孔子“畏天命”和“知天命”的思想得到了孟子的发展。如上所述,孟子的“性善”论中也包含了人的道德来源于天的信仰。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而这个“心”则是天赋于人的“道德本心”,比如能发展为“仁”的“恻隐之心”和能发展为“义”的“羞恶之心”。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既然天是道德本体,它又把道德意识的萌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个善端)赋予人,那么,我们培养道德意识、成为“君子”的“修身”过程,也可以看成是对“道德本心”,同时也是对天作为“道德本体”的认知过程。因此,孟子的“心性”论和他的“天命”论是紧密相连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句话完整表达了他的思想。
先谈“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我们可以解释为:通过自省充分扩充善良的本心,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为善。懂得了人的本性为善,也就懂得了天为道德本体。这一句描述了“认知天意”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言行,保持与人为善的态度、自觉做善事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善性源于天的道德,人做善事本是天意。
第二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表示了对天的态度:既然人的善性源于天的道德,那么,作为天之下民的人就应该不辜负天的期望,通过保存道德本心和培养天赋予人的善性来回报天。换个角度说,人要活得心安,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就得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反过来说,只有坚定不移地修身养性,同时顺从天的安派,才能活得心安,才能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第三句“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的含义。
当然,这种态度是以“畏天”的态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要在追求“知天”的过程中时时意识到自己在天面前永远是渺小的、人的行动范围受制于“天”、决定于“命”。这种意识不仅不会阻碍反而能激励君子不懈地努力。一句话,君子要在时时“畏天”的意识下,不断地努力修身(尽心知性)和“知天”。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孟子的建议是“思诚”,即不断地“诚心”。《中庸》里有这样的句子:“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从“诚”的意思“真”、“信”出发,我们可以说,“诚”是“天之道”的基本属性和根本规律,表示“天”是完美无缺的道德本根。而人所要做的就是追求这个“至真”、“至信”。“思诚”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去体会和接近这个“至真”、“至信”。何晓明认为,“孟子以‘诚’为天的根本规律,而人则通过追求‘诚’——真心真意的充实、完善天赋予人的仁、义、礼、智的善端——而达到‘诚’的境界,以与天道合一。”(19)
孟子接着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诚”是与信仰相连的。既然“诚”是天道,而“与天合德”的“圣人”象征着“思诚”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目标,那么“思诚”,就不仅仅意味着君子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地追求对天道的认知,也意味着君子不断地培养和增强人的道德来源于天的这个信仰。“知天”和对“天命”的信仰是同一发展过程。可惜,这种对“天命”的信仰长期以来被冠以神学的观点而受到批判。所以,我们当前要恢复儒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最关键的工作之一就是重新恢复这种“天主宰人”和“人的道德来源于天”的信仰在仁学、同时也是在儒学中的地位。一句话,重建仁学的信仰体系。没有信仰因素的仁学是不成熟和不完整的仁学,也违背了孔子、孟子的思想。
七、小结
仁学是集伦理、政治、哲学和宗教信仰为一体的综合学说。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致力于制度规范的重建以及对人的价值反思的过程之中,是由于“礼坏乐崩”、“天下无道”而产生的“忧患之学”。仁学不仅包括“爱人”的最高原则、至善的目的以及“忠恕”之行仁(爱人)方法,不仅包括培养独立道德人格以及以推行“仁政”为目的的君子之学和“内圣外王”之学,也包含涉及人的道德价值基础和来源的“性善说”和“天命观”。
换言之,作为“终极关怀”之学的仁学,有其宗教信仰的维度和超验性,不仅是对“人性善”和对“天命”信仰,同时也是对“仁”本身,“仁”作为人的本质和任务的信仰。仁学既是价值体系,也是以“天理良心”为内容的信仰体系。没有信仰这个维度,就不是完整的仁学;如果忽视了“天命”信仰这个维度,也就不可能培养人的敬畏心,仁学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牢固的基础。
“任何社会行动都具有某种意义,或者说都具有超出直接生活需要的某种意义追求”,“人的价值存在必然要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理想追求。”笔者认为,“仁”仍然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sense)的核心价值,是一种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想。如果当代中国社会的“失范”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人的价值秩序……失去了统一的信仰支撑”,(20)那么,重新反思“仁”和发展“仁学”,就是中国人重建自己的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唯一选择。
注释:
①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页。
②孔汉思、秦家懿(Küng,Hans;Ching,Julia):Christentum und Weltreligionen:Chinesische Religionen.Auflage,München,Zürich:Piper,2000年,第140页。
③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1、119、167页。当然,龚建平声明,他说的“意义”“不是从解释学的角度得来,而是儒家思想固有之义”,“‘意义’即‘意’之适宜或适宜之‘意’”。参阅第61页。
④潘自勉:《论价值规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他把“礼”定义为“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等规范体系”,第20页。
⑤罗哲海(Roetz,Heiner):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zeit.Eine Rekonstruktion unter dem Aspekt des Durchbruchs zu postkonventionellem Denken.Frankfurt a.M.:Suhrkamp,1992年,第51、52、200页。
⑥胡林英:《道德内化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50、51页。
⑨参阅张茂泽、郑雄《孔孟学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⑩皮伟兵:《“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和”视域中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9、131页。
(11)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64页。
(12)孔汉思、秦家懿(Küng,Hans;Ching,Julia):Christentum und Weltreligionen:Chinesische Religionen,第140页。
(13)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71页。
(14)参阅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第201页。
(15)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17)李亚彬:《道德哲学之维——孟子荀子人性论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18)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第207、9页。
(19)何晓明:《亚圣思辨录——《孟子》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20)潘自勉:《论价值规范》,第3、1、2页。
标签:孟子·尽心上论文; 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的名言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