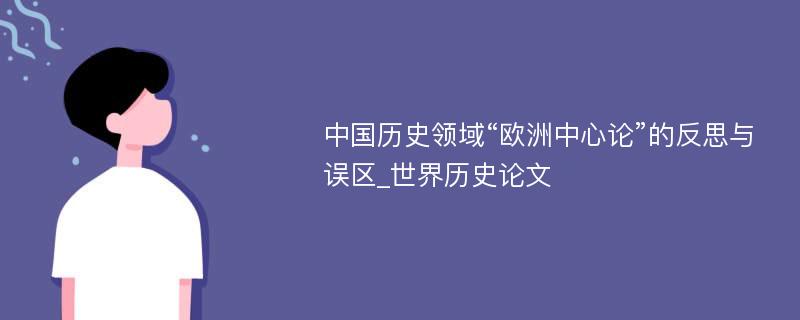
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及其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欧洲论文,误区论文,国内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12-05
自从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诞生以来,反对“欧洲中心论”(或曰“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便成为我国世界史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并提出要对之有所超越。可以说,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极大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但是,诚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1](p.47),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欧洲中心论”在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影响及其反思,近年来一些学者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①。笔者试图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史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各种看法的回顾与梳理,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雷海宗、周谷城等老一辈学者便举起了反“欧洲中心论”的旗帜。雷海宗1954年撰文指出,“地理大发现”一词中“‘发现’一词乃纯粹欧洲立场的名词”,建议改称“新航路的开辟”[2](p.34)。1961年周谷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批判“欧洲中心论”,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3]。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也没有忘记反“欧洲中心论”,如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世界史》明确提出要“破‘欧洲中心论’,恢复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本来面目”[4](p.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吴于廑先生便是代表。他提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架构,力图以此摆脱世界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论”影响[5]。近年来,随着全球史兴起和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随之深入。综合目前我国世界史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认识来看,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对我国世界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第一个层面主要关注世界通史的内容比例,认为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著作中西方所占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史为主轴的历史。周谷城指出:“我写世界通史之前,曾翻阅了许多著作,发现其中有一共通之点,都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谓之古典世界。古典世界之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作法便是欧洲中心论。”[6](p.3)这种现象在世界近现代史编撰中更为明显。有学者曾做过认真统计,并以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为例,指出“该编上下两卷6章24节共910页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余79%基本上都是有关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其中“58%的篇幅给了欧洲,只有4%涉及中国”。因此认为,这反映该著作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7](p.94)。
第二个层面的关注点在于世界史研究中的社会发展标准,认为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所确立的标准为圭臬”[8](p.43)。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经常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9](p.Ⅷ),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第三个层面的反思则从世界史研究中一些概念工具入手,认为我们现在用以表述世界史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源于西方经验,而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叙述非西方的历史,也是“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都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遍论、进步论之上,反映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元叙述。不仅西方学者用诸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等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8](p.43),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也被非西方世界广泛接受,我们的历史研究同样无法摆脱。马克垚先生评价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我们历史科学使用的概念、范畴、模式、理论、规律,都可以说是出自西欧的。”[10](p.21)
二、“欧洲中心论”反思中的认识误区
以上三个层面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及其影响问题的认识。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些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该将世界通史类著作中欧洲部分所占比重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
“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与欧洲(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强势地位密不可分,但对西方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对此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近年来,不少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马世力先生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确实曾经在西欧或欧洲,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承认世界近代史中心曾在西欧或欧洲同“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用否认历史发展有中心的作法去反驳‘欧洲中心论’,也不能用否认欧洲在近代曾经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或把其它什么地区说成是中心,甚至否认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历史进步性的方法去批判‘欧洲中心论’”[11](pp.55~58)。李义中也认为强调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与“欧洲中心论”两者之间只是形式上相似,而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从真正历史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考察欧洲或西方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影响及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完全站在非历史、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利用历史(学)以宣扬种族、文化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然而许多人往往只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外在形式或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相似而无视其本质区别并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12](p.108),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
在正确认识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再来看通史类著作中世界各个地区所占比例问题,就会有更加理性的看法。世界史当然不是各个地区或国家历史的累加,更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每部通史著作都代表了作者对世界过往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必然会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体系”。不论是五种社会形态观、整体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都代表了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但不论哪种体系,求真应该是唯一的原则。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弗兰克等,他们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有了不同的认识,并取得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笔者认为,即使这样,这些学者也只是把欧洲领先的时间向后推迟了,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对欧洲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都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多种体系构建历史,但任何一部求真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忽视欧洲的重要地位。相应地,在内容比例上,欧洲的内容也必然会在这一时段占据较多比重。以工业革命为例,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一事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偶然性,并强调英国的好运气,但对偶然性的解释应该无损于对其重要性的强调,不能因为其发生有偶然性因素,就对其最早发生在英国的意义及其影响加以贬低。如果一部通史著作对工业革命的发生只是略有提及并轻描淡写,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不应该的,也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特定时期对西方作用的强调和论述并不必然就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不能因为通史类著作中西方在某部分占了较多比重就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当然,对西方过于强调和突出也是不合适的,削减其他地区的内容而时时处处突出西方的特殊性,甚或认为其他地区没有历史不值得记载的做法才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反对。至于西方部分在通史著作中究竟占多大比例才合适,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应该看到,新近出版的通史著作在处理各地区所占比例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马克垚先生的《世界文明史》为例,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农业文明时代”总计376页中,关于欧洲的内容有129页,所占比例为34%;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7页,占66%。在“工业文明的兴起”部分双方比例发生了变化,共计557页中关于欧洲北美的内容有315页,占57%,关于亚非拉的内容242页,占43%。笔者认为,在近现代史部分发生的这一变化较好地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趋势,也充分显现出我国世界史学者对于通史类著作中不同地区所占比例问题的新的思考。
(二)源于西方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欧洲中心论”也应有所区别
“欧洲中心论”固然是近代以来欧洲(西方)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影响。但我们在看到“欧洲中心论”狭隘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欧洲(西方)思想的全部。在博大精深的欧洲(西方)思想文化的诸多体系和流派中,除了“欧洲中心论”狭隘思想之外,还有众多非常有价值、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尽管源于西方并植根于西方历史和经验之上,但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确切的真理性,因而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有着根本区别。如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的思想理论,但却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其许多理论和概念被世界各地人们广泛使用,并与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样,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现代化等概念尽管也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用来表述历史发展和进行研究,这些概念与“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垚先生谈到:“西方的理论有其真理性,可是只是从西方出发来看世界的,所以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所一再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10](p.21)我们应该明确区分源于欧洲(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欧洲中心论”。
以“现代化”为例。罗荣渠先生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变动;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用高效率途径赶上先进工业国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过程[13](pp.16~17)。众所周知,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是率先在西欧完成的,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可谓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其理论也源于西方。但这并不能成为妨碍我们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来表述历史和进行研究的理由,也不能因其来源于西方而将其视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它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一系列改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所涵盖的内容及其方向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仍然是无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普通中国人也许并不明白理论上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但‘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向往;在今天,现代化仍旧是国家的目标,是民族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14](p.54)。当然,现代化并非西化。世界现代化既有共性,又由于各个地区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其特殊性。“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14](p.55)我们所建立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这一概念源于西方经验,但其与“欧洲中心论”却没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民主、自由、文明等概念和范畴也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是源于西方的理论成果,但这些概念同样有其进步性和普世性,是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15]这些范畴及其理论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将其使用在对历史的表述中并不必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对此必须加以区分和明确。事实上,中华文明一直具有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佛教最早源于印度,但异域文化的出身并不影响它与我国本土文化的水乳交融,而它对我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化、民主等概念源于西方,就简单地认为凡使用这些词汇来对历史进程进行表述就一定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而应该予以具体鉴别和区分。
由上可见,我们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如果对上述问题不加区别,便有可能陷入反“欧洲中心论”的认识误区,从而导致反“欧洲中心论”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只有克服这些认识误区,才能更好地处理通史类著作中各地区所占比例问题,也才能辨明源于西方的一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区别,从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三、对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思考
反对“欧洲中心论”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有通过这种“破”与“立”,我国的世界史体系和理论建设才有可能真正走出“欧洲中心论”的阴影。在这方面,吴于廑先生的探索具有启迪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完全照搬苏联的世界史体系,而这种体系将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都按五种社会形态编列起来的做法,从根本上说仍是以欧洲为标准的,也即有学者评论的“欧洲中心意识依然存在”[16](p.122)。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和探讨,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和思想,吴于廑是其中的代表。吴先生提出了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整体史观”,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中主流的史学思想。有学者认为,“整体史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克服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既科学地吸收了全球史观等西方新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潮的合理成分,又摈弃了它们所固有的片面性”,因此“是目前较为科学的世界史观,‘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也是较为科学的世界史体系”[17](p.203)。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吴齐本仍存在缺陷,并未完全摆脱作者想要避免的“欧洲中心”倾向[7](p.94);但其所做的诸多有益探索不容抹煞,“整体史观”代表了我国学者在学科体系上对超越“欧洲中心论”问题的思考,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要真正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绝非易事,还需要国内外学者不懈努力。尽管前路艰难,但史学工作者仍须加倍努力。因为,“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而这种探讨正是世界史这门“学科存在的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18](p.187)。马克垚先生认为,要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需要“让各个国家、各种背景、各种文化传统的史学家,都来参加这一工作。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与此同时,“按照自己的认识”去研究历史,并不等同于要对源于西方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完全漠视,而另起炉灶,而是应该“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去“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10](p.22)。刘新成先生也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18](p.187)。由此可见,要真正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一方面需要摆脱在历史研究和实践中以西方为模板的倾向,加强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本国文明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各种已有理论成果,包括西方史学理论成果为己所用,以逐渐接近共识。惟其如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才能避免陷入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误区,真正做到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世界史研究不断发展。
注释:
①参见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载《历史研究》2006年3期;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载《世界历史》2005年3期;马世力“也谈‘欧洲中心论’”,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5期;刘新成为杰里·本特利等著《简明新全球史》所做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载《历史研究》2011年6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