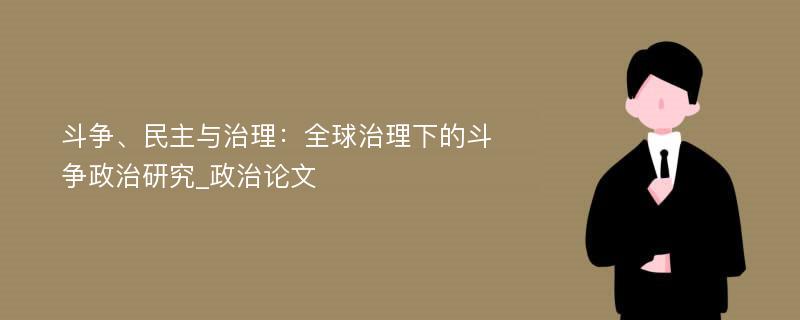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政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4-20。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4-0021-07
一、问题的提出:抗争政治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的浪潮就一直此起彼伏,社会运动理论也随之兴起和发展。这些理论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社会抗议、抗争乃至冲突进行解释和预测,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理论流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北美的资源动员及政治过程理论。①尽管这两个流派的侧重点和优缺点有所不同,但可以说,这预示着来自底层社会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日渐形成、发展并受到学界的重视。②印度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计划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正在颠覆传统政治学的观点,在以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为主的印度底层社会研究群体看来,“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v s.公民社会架构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反倒提供了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她/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这两者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③
综合以上学界的观点,抗争政治在国内政治中的意义主要在于两个层次:在微观上,个人、集体抗争是维护和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后武器”,是公民人权得以保证的最后砝码;④在宏观上,抗议性政治对被抗争的国家体制乃至社会结构都有一定的影响。抗议性政治的集大成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通过对法、英两国革命道路的重新解释,认为介于暴力革命和议会政治之外的第三个空间——抗争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对民主化的推动是积极的。因此,相对于主流政治体制,蒂利长期研究的抗争政治也就是与“去民主化势力”的斗争,对民主化贡献巨大,欧洲过去两百年的民主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抗争政治的历史。⑤
在社会运动的另一层空间——国际和全球社会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网络化趋势,把许多原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变成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并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全球范围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蔓延开来。这就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全球社会运动,即在国际层面发起的非制度化的各种国际集体行动,旨在影响各国和全球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顺其自然地,国内抗争政治及其功能是否可以延伸到国际乃至全球层面?那些解释国内抗争政治的理论是否同样可以应用到全球社会运动当中?全球社会运动是否能被界定为抗争政治?抗争政治对当下全球治理有何理论和实际意义?上述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要探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抗争的场域:从国家走向全球
抗争政治的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及内外表现形式,集中体现在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社会转型带来的全球社会运动;这使得个人、团体和国家在风险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机制很难面面俱到地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国内和国际社会中的抗争便应运而生,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
2.1 全球化及全球风险社会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因特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强。国内的新社会运动从科技、环境、经济等领域转向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公民为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向国家与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等抗争性群体行为。全球化使得抗议和流血事件跨国界发生,这都必然对当今国际社会本身及其治理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当今人类正处于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之中。⑥必须看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风险,如大规模失业的风险、贫富分化加剧的风险、社会冲突的风险、制度变迁的风险、生态风险,以及经济增长过程被制造出来的风险、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和抽象科学研究的不充分性所引致的风险等等。⑦因此,斯科特·拉什(Soctt Lash)认为,不仅从自然风险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而且从社会结构面临风险的意义上看,从个人主义消涨的意义上看,从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⑧特别是世界性议题,如生态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全球经济危机、和平问题、人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围绕这些问题及其所带来的种种风险而兴起的全球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社区发展运动、反战运动等等。运动的主体,诸如单个公民、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国家在维持国际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方面都进行了不同于以往常规政治的举措,并取得一定功效。
2.2 全球转型、全球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转型
1944年,波兰尼(Karl Polanyi)出版了他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正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该书的新版前言中所说,“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大转型”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正如波兰尼指出的,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⑨世界经济在过去的岁月里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一味追求GDP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可以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构成了当今全球社会运动的两个方面,也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而且,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社会掀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与60年代末兴起的新社会运动颇为相似。反全球化运动是新社会运动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的一种体现,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新社会运动理论以新的内容。⑩伴随这些理论反思的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从实践上去抗争和维护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全球治理是以政府的作用和国家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的疆界模糊不清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就很容易被视为最强大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政府或联邦主义。正如赫尔德和麦克格鲁(Held & McGrew)所说,最强大国家倡导全球治理总是以它们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作为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制在原则上缺乏独立的权力,其作用主要是为了促进最居支配地位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利益。(11)可见,政府间或政府间联盟的全球治理仍然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这种国际社会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所覆盖的只能是国际社会很小部分的领域,甚至只是覆盖着最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间联盟的利益领域,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领域处于“无政府的治理”之下。这就意味着,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国家行为体相互之间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根本不能独立地实现全球的“善治”。全球治理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只有多层次的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全球的“善治”,特别是包括各种跨国行为者共同作用来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2)
因此,在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边缘发挥全球治理作用的则是以非政府组织或非政府联盟的全球公民社会系统,各种形式的全球社会运动也应该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13)特别是随着全球社会问题的日益繁杂,诸如在国际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地震、海啸等具有突发性、全球性等特点的问题上,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在应对时显得相对迟缓,而非制度化的全球社会运动却能够有效地进行补充。在这种情形下,全球社会运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
三、全球抗争、民主与治理:抗争的功能与局限
抗争政治是对抗争走向全球的概括,在内容上包含着对现有国际治理机制(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等)、环境、人权、战争等广泛领域的抗争;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围绕单一议题以及人类永恒发展的诸多全球社会运动,包括全球化运动以及反全球化运动两个层面。全球抗争政治与当下的以国际机制为核心的常规全球政治具有一些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从国内层次上的抗争政治特征可见一斑。“对抗性政治”这一概念是主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理论家们最新的提法:“对抗性政治指的是权利声称者与其抗争对手之间发生的一幕幕公开的和集体性的互动活动,在这一类互动活动中,(1)至少会涉及到某个政府行动主体,它或者作为权利声称者出现,或者作为权利声称的目标对象出现,或者作为第三方出现;(2)一旦该权利声言得以实现,将至少影响到其中某一方的利益。”(14)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它扩展了社会运动的研究范围,把诸如民族主义、革命、罢工浪潮和民主化进程之类的政治现象也包括进来;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突破了制度化政治行动和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界限,只强调该类政治行动的冲突性质。(15)
从上述关于国内抗争政治的界定和意义可以看出,国际抗争与国内抗争在理论价值上具有相似之处。全球抗争中的抗争者更多的是国际底层社会中的个人和组织,如普通公民、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等,呈现出与被抗争者相比较弱势的地位。它们诉诸非制度化,非常规的,带有一定对抗、冲突色彩的政治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对其所关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施加影响。作为一种新政治形态,相对于正式政治,如当今全球政治中的制度主义政治,其新意在于以非正式的、草根的行动主体及非制度化行动,在良性对抗、冲突、抗争中实现正式制度和组织不能达到的绩效。这些都体现在抗争对全球民主、全球治理的正面效应:全球社会运动为个人提供了影响国际政治的参与机会;促使国内政治决策国际化,进而影响国际政治事务;大多数全球社会运动都倡导国际道义,追求全球正义,这对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还增大了国际间信息流量,打破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信息“储蓄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强国因垄断信息而垄断国际权力。(16)国外学者已经考察了与国际抗争新型表达方式相关的各种问题,并分析了国家对非政府行为体——它们反对当前的世界秩序,并宣称要提出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方式的替代方案——的兴起做出的应答。针对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一些更为醒目的抗争运动,如在西雅图、布拉格和热那亚举行的示威……世界社会论坛先后在阿莱格雷港和孟买举行了四次大会,这些学者重新审视了政府和国际机构、尤其是欧盟所采取的主要法律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了把国际冲突“裁判化”的策略,有些新式诉讼人想使用这些策略,把有争议的主张交与第三方裁定者(如法院、仲裁者、人道主义机构等等)处理,从而使它们获得合法性和能见性。(17)
作为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非正式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跨国活动领域,其基本的组成要素是国际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它们同样是抗争的主体之一,对于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研究全球治理的著名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鲁所说:“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很显然,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的活动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但是,它们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区域性的政治组织被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含义之外,那么,全球治理的形式和动力将得不到恰当的理解。”(18)此外,詹姆斯·N·罗西瑙也指出全球治理的单位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至少有部分描述世界政治的相关术语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政策协调网、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19)特别是面对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全球问题时,上述行动者能发挥正式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不能尽善的功能。所以全球治理委员会主张:“在全球层次上,治理基本上是指政府间关系,但现在我们必须理解,它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多边合作和全球资本市场。”(20)
当然,以抗争为核心的全球社会运动引发的抗争政治也有其自身的功能局限,这是由当前抗争的特点决定的,即非预测性、非理性、非正常性、非组织性等特点。具体讲,非预测性是指社会运动可能在任何地方爆发,并不分具体的地点。因此,全球社会运动在国际制度环境中仅仅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整合功能并没有强制性,完全是靠呼吁、行动来扩大影响,借以“唤醒”各种行为体的“道德良知”,使之自觉遵守全球共赢的国际准则、担当“国际道义”,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协调发展;它缺乏必要的资源,因而使它们对政府或政府间组织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全球社会运动的目标具有全球性,但这些目标很可能与其所在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发生冲突。(21)
归根到底,这些抗争者与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行为者都有社会运动与抗争的需求。这些社会运动与抗争已然成为民主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社会运动与国家、政党、国际组织之间相互渗透,在国内与国际层面都引起传统政治行为者,如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的关注,在具体议题与政策上有了“被治理者的政治”。学者通过对美国公民权运动、新左翼、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墨西哥人争取民主的斗争等社会运动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社会运动与国家、政党等常规政治行为体具有内在的紧密关系,可以说,社会运动与常规政治是相互交叠和渗透的。因为这代表着政治活动本质的发展: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运动基于相同的基本原则——普通公民的政治意见是值得咨询的。这集中体现在社会抗议和常规政治参与是互补的:首先,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制度化政治活动是高度间歇性的过程,集中在选举期间;而社会抗议和结社活动则可以不受季节和年份限制持续进行。第二,绝大多数传统政治参与活动仅仅允许相当粗泛的选项表达——对于具有相当广泛主张的某个候选人或政党,是赞成还是反对;社会抗议和结社活动却可以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赋予活动以特异性。第三,抗议活动和社团活动提供了纯化和强化选举结果的新方法。第四,不仅政党,而且社会运动也能够影响公共选举的结果。总而言之,没有理由认为社会抗议活动和传统政治活动应该是替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当社会团体能够运用后者的时候就会放弃前者。(22)因此,作为跨越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藩篱的社会运动与抗争正是在国家、政党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关注普通政治参与者,尤其是底层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超越传统正式政治的范畴,从而益于多元社会的民主与善治。
四、结语
抗争政治,无论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全球政治层面都初露端倪,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这有益于在目的论和方法论层面开发抗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一方面,在给抗争的“定性”上,抗争政治不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而是与常规政治相对应的政治形态。按照蒂利的解释,非抗争政治——比如布坎南和杜洛克强调的财政、税收与民主的关联、政治参与和政治公开、利益表达与政治组织活动等等——仍然构成政治活动的主体,但是民主化却主要发生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上,也就是公民与代理人之间的三个互动部门:公共政治、类别不平等、和信任网络。这三个部门同时也是抗争政治的三个战场,共同促进着民主化。民主化因此可被概括为公民与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威权之间的关系变化、抗争政治的结果,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公共政治制度化的维度,需要以社会不平等的削除程度和在今天以社会资本来称呼的信任网络来衡量。这一视角既适用于审视现实社会的民主现状,比如“9·11”之后美国民主的退步或者东欧“后共”国家不同的民主进程,也适用于重新看待法国和英国民主道路的差异和意义。(23)
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抗争政治已由暴力革命向社会运动转变,这体现在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兴起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这种抗争方式的转变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24)而且,在很多国家里,选举民主制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在民主化的浪潮中,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任何国家在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集体抗议行动,特别是在威权主义国家,这些集体行动正是威权崩溃的主要动力,具有独特的抗争过程与机制。(25)这些国别、地区以及比较研究的理论与事实已经证明:在全球民主化的示范效应下,无论是单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与抗争促使常规政治的行为者不得不重视这股力量,协调、整合社会运动与政党、国家、地区组织、国际社会之间的博弈关系,发挥社会运动与抗争对民主与治理的正功能。这种运动中的力量对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治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值得去探求应对抗争、开发抗争良性功能的新思路,发挥国际机制、国家、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实现民主与善治。
然而,全球社会运动,即使在西方,也仍然是政治的边缘,它的功能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是国际制度环境中的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全球治理中的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层次,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它自身还具有前文所述的非预测性、非理性、非正常性和非组织性的特点,这一切都决定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全球化的确导致了权力的转移,但并没有使权力转移到所有的全球社会运动的手中,而只是与所在国,尤其是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利益一致的全球社会运动,才可能获得民族国家的支持,从而能够发挥一定的全球整合功能。但是,这一类的全球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意识”早已成为某些强权国家的意识了,这类全球社会运动所反映的只是某些强大国家推行世界主义的“全球国家”的工具。(26)而绝大多数的全球社会运动都因直接挑战民族国家权威而事实上成为仅仅是在政治框架之外的全球性的“草根运动”。这是目前全球抗争政治的实然状态,抗争政治在全球层面上推动民主与善治有待于国家及国际权力体制的逐步民主化。
总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使民主与治理运转起来的一个特定要素便是社会运动。作为非制度化政治的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与制度化的传统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交互关系,如若忽视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刻地理解制度化政治。国家、政党、社会运动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共同作用于抗争政治之中,在国际社会、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形成更加和谐的关系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可以扮演重要而积极的角色,并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
注释:
①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裴宜理,阎小骏:“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于建嵘,斯科特:“底层政治与社会稳定”,《南方周末》,2008年1月24日。
③[印]帕萨·查特杰著,田立年译:《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孟宪平:“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人权诉求”,《社会主义论丛》,2007年第2期。
⑤[美]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等译:《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⑦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6页。
⑧[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⑨[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⑩刘颖:“反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
(11)[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陈志刚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2)D.Hel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
(13)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全球治理的转型”,《国际论坛》,2006年第11期。
(14)[美]麦克亚当,塔罗,蒂利著,李义中等译:《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5)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16)同①。
(17)[巴西]罗尔·恩瑞克·洛何,卡罗斯·R.S.米兰尼,卡罗斯·施密特·阿图利:“国际抗争的表达和民主控制机制”,《国际政治》,2006年第3期。
(18)[英]戴维·赫尔德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9)[美]詹姆斯·N.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马丁·休伊森等编:《走向全球治理理论》,纽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20)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之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1)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全球治理的转型”,《国际论坛》,2006年第11期。
(22)[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章延杰译:《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ⅩⅩⅡ-ⅩⅩⅢ。
(23)吴强:“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英民主道路的解读”,《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2月7日。
(24)李文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5)谢岳著:《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曹荣湘等译:《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标签:政治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