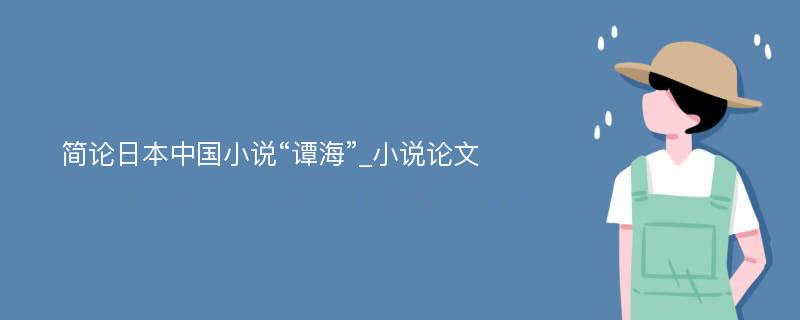
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日本论文,小说论文,谭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汉文字圈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影响,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用汉文写就的文言小说,我们今天称之为“域外汉文小说”。这些作品既是该地区和国家文学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因为是用汉文写成,和我国汉文学和汉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部分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汉文学的传播和影响,了解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民族风格,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文学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仅就日本汉文小说《谭海》作一个案的解剖和分析。
一
《谭海》,亦作《谈海》,日本依田百川著。作者生于天保四年(1833年),卒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为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汉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出生地在江户八丁掘佐仓藩藩邸,父贞刚是佐仓的藩士,食禄高达二百石,母名千重,娘家姓斋藤。小名幸造、信造,最初字百川,后以此为本名,号柳荫、学海。他初于佐仓藩藩校学文习武,以后因立志成为书法家而寄居筑地的牧野天岭书塾求学,又因不满于塾生的见识低下,不久进入滕森天山的书塾。其时正值嘉永五年,他年满二十,同门的友人有川田甕江、岸田吟香等,特别是甕江,成为他终身的密友。安政五年,被任为佐仓藩的中小姓,才干得到赏识,因到藩校温古馆服务,历任木付、郡代官、藩邸留守居役等。庆应四年,于鸟羽、伏见战役之际奔走于国事,如为救前将军庆喜赴京请愿等。明治维新后,任佐仓藩大参事,被公认为尽力于藩政,结束废藩置县的扫尾工作后,他辞职回到佐仓。明治五年,任东京会议所书记官,始正式踏上仕途,并一度在《邮便报知新闻》社工作。明治八年,出任太政官,在修史局任职。明治十四年,任文部省权少书记官,致力于制定小学音乐教材。明治十八年,官至文部省少书记官,随后退出仕途,专注于戏剧、小说创作。
《谭海》即为其官宦时AI写作作的小说,明治十七年凤文馆首次出版。此前,明治十一年,依田百川与依藤博文及当时的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等,发起改良歌舞伎剧,主张历史剧需基于严密的考证,并对当时演出的《松荣千代田神德》提供了建议和指导,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歌舞伎界的最初尝试。明治十九年,依田百川参加了演剧改良会,决意将脱离宦海后的余生贡献于演剧改良运动。他与川尻宝岑合作的《吉野拾遗名歌誉》(明治二十一年一月凤文馆)、《文觉上人劝进帐》(明治二十一年九月金港堂),其对史实的重视和高雅的风格,为日本近代历史剧的形成规定了基本框架。明治二十二年以后,他主要向壮士剧社提供剧本,由其上演的剧目有:《拾遗后日连枝楠》(明治二十四年八月上演)、《政党美谈淑女の操》(明治二十四年九月上演)等。其间除剧作之外,还创作有《侠美人》(明治二十四年金港堂)等小说。由于其激进的演剧改良主张,每每招来墨守成规的演剧界的白眼,在剧坛陷于孤立状态。明治三十年以后,因健康每况愈下,对演剧改良的热情减弱,常在家作诗自娱。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祝寿活动之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其藏于无穷会的四十四册日记,是反映明治时代文坛历史的珍贵资料。(注:关于作者依田百川的生平资料,本文参阅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进《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7年本卷三第492—493页。)
关于依田百川之性格爱好,其好友川田甕江在《谭海·叙》中曾叙及“百川读书五行并下,能文雄辩,骂经生迂儒,不抵半文钱。其谈艺苑盛衰,闾巷风俗,旁及院本杂剧、妇女妆饰、衣履钿钗、玩好之细,由俗入雅,溯委讨源,凿凿可听。”(注:川田甕江:《谈海录》,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2页。 )此外伊势矢土胜之的《后序》中也谓“先生当今通儒,以能文鸣”,“曾参藩政,职掌兵农,奋激淬励,欲一洗旧弊,顾与俗吏龃龉,不能展其才”,“亡几,迁文部书记官,又不得逞其所长。”(注:伊势矢土胜之:《谭海·后序》,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二末第1页。)可见是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 着意改革旧弊,但仕途不甚得意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经生迂儒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所交往的,也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歌舞伎界演员团十郎、菊五郎、角藤定宪、川上音二郎等,也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和汉学家,如为《谭海》作序的终生好友川田甕江,为明治时代文章三大家之一(注:关于川田甕江的材料,参见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近《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也为《谭海》作序并写评的另一位好友菊池三溪,与依田百川、信夫恕轩并列,被称为明治时代充分发挥了小说趣味的别具特色的汉学家。(注:关于菊池三溪的材料,参见日本近代文学馆小田切近《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
《谭海》首次出版为明治十七年(1884)凤文馆本,该本版式宽松,天地阔大,字体秀丽,刻工精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但该本仅有两卷,卷二终后即为辱知生伊势矢土胜之所撰《后序》,再后就是版权页,看来不是残本,而是当时只出了两卷。明治二十五年,博文馆购买了业已倒闭的凤文馆镂版,又出版了此书,也是卷二终后为辱知生伊势矢土胜之所撰《后序》,再后即为“明治二十五”版权页。但后面又有两卷,卷三之前另有一序文,为鸿斋石川英所撰,序文中讲到“斯书一出,彼(此指书中所写“逸人奇士”)湮没不彰者,得传名于后世,亦应扬眉于九泉之下矣。今又著二编,愈见言谈之多,腹笥之大,顾世之湮没不彰者,皆将藉君之彩笔而不朽于世。”(注:鸿斋石川英:《谭海·叙》,日本1893年博文馆本,卷三第5页。 )其卷四终后又有一版权页,写明为“明治二十六年”博文馆本。可见三、四两卷为后编和后出。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该本版式、天地、字体和印工都明显不如凤文馆本,博文馆主人在识语中云:“本书曩日凤文馆刻而公于世,然尔后同馆闭锁,而本书亦随不多行于世,令人憾焉。仍今兹本馆买其镂版,而谋读者之便,改为活字小册印行焉。”(注:博文馆主人:《谭海·识语》,日本1893年博文馆本,卷一第3页。 )当年此书由凤文馆刊行时,一时“远近传观,洛阳纸贵”(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2页。),而八年之后, 博文馆再度印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二
《谭海》所记,皆为“畸人寒士,才女名妓,一言一行,一技一能,可喜可悲,可笑可泣之事”,这在日本也是所谓“正史不载,大人不语”(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2页。)的内容。但本书作者不仅平时注意采撷近世奇人逸事,而且常常访问调查,亲质其人,随得随录,裒然成册,先出两卷,又续两编,最终完成了《谭海》四卷。
综观全书,确如序中所说,《谭海》所记大致为两类人:一类为畸人寒士,一类为才女名妓。前者如《芭蕉》、《其角》、《太田南亩》、《小知》、《俳优团十》等,记当时被视为鄙俗的俳歌与民歌作者的经历;《近松门左》、《其硕》、《西鹤》、《鬼贯》、《京传》、《马琴》、《三马》、《一九》、《种彦》诸篇,记同被歧视的小说家的逸事;《祥蕊子》、《僧兆溪》、《光悦》、《风外》、《心学》、《志道轩》等篇,记高僧逸士的故事;其他《巨杯》、《丰年糁》、《侠客晓雨》、《女盗》、《骗盗》、《吉田空昙》、《吉田雨冈》、《田中丘隅》、《卖酒郎》、《镊工》、《熊本廉士》、《宛丘》、《卖菜翁》、《孝丐》、《侠盗忠二》、《老仆清吉》、《二丐》、《车夫喜右》、《奇士甘死》、《画师》、《哑丐》等篇,则记述了士、农、工、商、隶、侠、盗、丐等各行各业中畸人寒士的所言所行。后者如《妙海尼》、《正传尼》、《妙喜尼》,记女尼之奇节;《名妓濑川》、《奇妓首信》、《侠妓小柳》、《贞妓》,记风尘女子之慧眼英骨;《译莺君》、《小君》、《小万》,记诸才女之多才与多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很显然,《谭海》所记,已经由“王公相将”的“盛世伟业”向市井人物的“一言一行,一技一能”(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页。)转移, 这种文学表现对象的重心下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当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在进行着一场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新的价值观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因此重下层畸人寒士、轻传统王公将相便成为时代使然。当时正如依田百川在《谭海》卷一《名妓濑川》中所形容的:“幕府之盛,人材辈出,上自执政大臣、文武百僚,下至巧艺伎术、巨商良贾、俳优倡伎,莫不有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焉。”(注:本文所引《谭海》原文,均引自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兹后不再出注。)《谭海》所记,正是“巧艺伎术、巨商良贾、俳优倡伎”中“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其实不只是依田氏,其他小说家也莫不如此,如菊池三溪,其所著《本朝虞初新志》,也是以记述市井人物为其特色;其他如《谭海》中叙及的诸多小说家,也都烙有大致相同的时代印记。
当然,重要的还不在于写了谁,而在于通过对这些市井人物的描写,表现了新的市民阶级的思想趣味和价值观念,并由此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例如不分贵贱,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进而发家致富,这是《谭海》多次出现的主题。卷一《丰年糁》,写一个“掷金如土,负债山积”的富家子弟,穷到了“赤身孑立,乞食道路”的地步,有一天突然自我振奋曰:“吾犹有身在,岂无衣饭!”最后终以沿街卖糁(一种米饭团)而“买宅居货,俨然绅商”;卷二《志道轩》,写一位“放浪江湖,饥渴殆死”的僧人,也是有一天游浅草寺见香客如市,忽然仰天大笑说:“予舌尚在,穷饿自取焉,非天也。”于是“凭几说书”,名声“遍于一都”;卷二《卖菜翁》,写一自幼失去双亲者,“日鬻菜蔬为业”,所得钱除供一日饭之外,余皆买书,后做了授书先生,仍“蓝缕百结,担菜出售,毫无耻色”,学生请求他“勿事贱业”,他回答说:“予藉以此活,犹不胜乞贷为富乎?”像这样依靠自己的身体、舌头和双手自食其力,不以卖糁、说书和卖菜为“贱业”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治维新时代市民阶级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即使写的是一些官吏,也重在描写他们的“精练吏务”和“富国济民之术”,如卷二《吉田雨冈》,写雨冈善动脑筋,为民架桥浅草川,架成后“课人桥税二文钱”,借助这笔收费支付造桥费,“不费官库一钱,公私便之”;同卷《田中丘隅》,写丘隅初为驿长,置“义田”,赈救困穷,后又“治荒川有功”,“从庶人擢至民牧者”,并通过亲身经历,教育百姓神鬼妖巫不可信;同卷《那珂宗助》,写宗助精通水利,受命浚一河道,他“开角力场于水上”,募村民子弟争来角力,乃命制浚通河道需要的藤索竹笼,胜者赏布一匹,工费减半,而工效倍之;诸如此类,都强调官吏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诸如建立税制、破除迷信,激励竞争等公私两便、事半功倍的方法来为地方和百姓造福,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治时代的务实精神和效益原则。
除去表现新的价值观念和务实精神外,《谭海》中有相当的篇幅,旨在表现市人一种类似我国魏晋风度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风貌表现各异,但在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张扬个性的意义。《谭海》所写的诸俳歌者和小说家,如芭蕉的“飘逸绝尘”,其角的“啸傲自若”,太田南亩的“滑稽诙谑”,小知的“不失童心”,京传的“中夜”“狂呼”,马琴的“不与世俯仰”,一九的“率性任性”,都可视作是这种精神的外化表现。其中突出者如京传,常常“中夜跃起,挑灯疾书。或绕屋狂呼,或仰天大笑;或列食器于前,任手啖食;或不上厕,溺器与书册同陈。家人惊以为狂发”;又如一九,室中“书籍杂陈,笔砚并列,杯盘枕衾,纵横狼藉,不馀寸隙”,一天“夏晓早起,残月如昼,步到日本桥下,游兴遽动,单身上程,游京师浪兴三月馀而还”;还有小知,火灾起时,众人忙乱不迭,他却“箕踞松下,抽笔批俳句百韵,绝如不知火者”,凡此种种,颇有点我国《世说新语》中人物与猪共食、雪夜访戴、临火不乱的气概。
当然不只是俳歌者和小说家,其他人物也有狂放不羁者,如志道轩本是僧人,却慨然曰:“戒律者,桎梏耳。声色酒肉,岂足溺我?且将脱桎梏,为大快活人矣。”乃鬻袈裟佛经,以买酒肉,数日而尽。放浪江湖,饥渴殆死,人皆笑为狂。后虽找到了“凭几说书”这条生路,但得钱数百,即饮酒啖肉,不留一文,并在自己画像上题诗曰:“谈史谈军数十春,大悲阁下得名新。曾夫木叩床头日,白眼总看世上人。”不仅公然以阮籍自居,而且其挣脱“桎梏”为“大快活人”的言语行为,确有着张扬个性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内核。
此外,《谭海》中还有相当部分,意在表彰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无疑是封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着糟粕的成分,但本书在描写上却颇有特色和可取之处。
和本书整个描写对象的中心下移相吻分,本书表彰忠、孝、节、义的部分,被表彰者也多为底层百姓和市井人物。如《小出氏仆》、《虾夷三孝子二贞妇》、《横滨贞妇》、《长门二孝子》、《孝丐》、《孝义复仇》诸篇中所写及的义仆、孝女和贞妇,都是一些下层百姓;再有一些写见义勇为的篇章,如《义兄弟》、《侠妓小柳》、《侠客晓雨》等,其中人物也是妓女侠客一流;还有一些写重义轻财的篇章,如《熊本廉士》、《义斋》、《三组街与三》等,所写的也都是一些“职卑秩贱”的医生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物虽读书不多,但朴实好义,其言其行令人感动。熊本廉士捡得黄金三十两,千方百计找到失主,失主又复赠一磁碗,殊不知磁碗是一古物,值百金,于是又复往还其金,两人为此相让争辩不止。义斋作为医生,“见贫而病者,为给药不求谢仪,且以薪米赈之,或授以本钱,令营业”,而麻田侯要他长期侍奉看病,并“谕以厚俸”,他先是称病,既而又装死,最后逃之夭夭。像这类美德,实已逸出了封建道德的范畴,而具有一种新的品格内涵。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还把传统美德和“情”沟通起来,赋予了传统美德以新的理解。如《泽莺君》篇末议论说:“余尝谓厚于情者,莫过忠臣孝子焉。不惮艰难,不避死生,非厚于情者不能也。”《小君》一篇篇首又说:“尝谓笃于忠孝者,其情必挚;励于节义者,其思必深。何则?笃至人伦者,出乎情而合乎道,盖不知其然而然尔。”这就是说,重于感情的人,才会是忠臣孝子,才能具有忠、孝、节、义等人伦美德,因为人的这些美德都是出于内心感情,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这样就把传统美德从“道”的教条返回到“情”的本原,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具有新的时代色彩的。
三
《谭海》作为一部用汉文写就的文言小说,继承和借鉴了我国传统笔记体小说的格局和手法。书中各篇一般都采用史传写法,先交代所写对象的姓名籍贯、家庭身世、性格嗜好(当然也间有议论开头的);然后进入具体描写,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展示人物的性格风采;最后多用议论作结,有时采用“野史氏曰”的形式。这些都和由我国史传文学发轫而来的笔记小说相仿佛。
在具体艺术风格上,本书体现的是一种“据实结撰”的特点。作者无论是写畸人寒士,抑或才女名妓,都把人物的身世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有时还写明访问调查了何处何人,给人的印象是决非杜撰而有。叙述人物事迹时,也文笔平实,有根有据,真实可信,决无架空凭虚之谈。作者所遵循的,是汉魏和清代《四库》编纂者所倡导的小说概念,在风格上更接近《阅微草堂笔记》而与《聊斋志异》相异趣。作者好友多爱把此书与《聊斋志异》等书做比较,指出:“近世所传《聊斋志异》、《夜谈随录》、《如是我闻》、《子不语》诸书,率皆鄙猥荒诞,徒乱耳目,而吾友依田君百川著《谭海》,颇有异其撰者。盖彼架空,此据实;彼外名教,此寓劝戒;彼主谐谑,此广见闻。”(注:川田甕江:《谭海·叙》,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1页。 )“盖拟诸西人所著《如是我闻》、《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等诸书,别出一家手眼者。但彼率说鬼狐,是以多架空冯虚之谈;是则据实结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备修史之料,可以为作文之标准也。”(注:菊池三溪:《谭海·序》,日本1884年凤文馆本,卷首第3页。 )虽然这些序文的褒贬未必恰当,但所总结的《谭海》“据实结撰”的特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四库》编纂者提倡的小说应“寓劝戒,广见闻”,反对“诬漫失真, 妖妄荧听者”(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2页。),本书正是这一主张的赞同者和实践者。
但也正是由于本书作者恪守的是“据实结撰”的原则,因而又使小说缺少像唐传奇那样翻空造奇、委婉曲折的风致,缺少像《聊斋志异》那样虚拟幻设、奇特瑰丽的艺术魅力,在文学性方面不免要稍逊一筹。只是由于作者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文功底,因而本书在艺术上仍有诸多可取之处。
作者驾驭汉文字的能力很强,他交代有序,叙事有方,不仅叙述语言简洁生动,人物对话也颇能传神。在情节提取和结构安排上,他善于抓住典型事件,剪裁得当,不枝不蔓,而且注意布设关眼和伏线,以使前后照应。有不少地方,描写不乏生动之笔,文学性颇不弱。
如《名妓濑川》,写一个叫文字的善时曲者,想以数十金求一夕欢,濑川笑许之。于是这家伙“鲜衣美带,故自修饰,夜抵松楼”:
濑川盛装而出,光艳四射。酒三行,濑川曰:“闻大夫善歌,请为妾度一曲。”文字大喜,歌喉宛转,尽其绝伎。曲罢,濑川顾侍婢曰:“取彼物来。”至则白金千锭也。濑川笑曰:“聊以劳大夫。”一揖而入。文字嗒然失色去。
这里,寥寥数十字,有色:“盛装而出,光艳四射”,有声:“取彼物来”、“聊以劳大夫”,有形:“顾侍婢”、“一揖而入”,从而把一个气度不凡的名妓形象勾画得如见如闻,而那位善度时曲者从“歌喉宛转”到“嗒然失色”,其表情变化也颇富戏剧性。
又如《侠客晓雨》,写一个住秽多坊的无赖熊八,自恃力大势众,凶横跋扈。侠客晓雨欲收拾他,一次中元节遇到了机会:
晓雨与客饮中街蔫屋,红粉满座,弦歌竞兴。熊率徒过其前,晓雨见之,遽掩鼻曰:“臭来,臭来!”熊怒,目光如炬,抚刀曰:“何臭气?”一座失惊,弦声忽止。晓雨自若笑曰:“殆是秽多臭气。”熊益怒,欲斩之。刀未脱室,晓雨蹶起,左手遏其腕,右手执所穿木屐,一击踣之,骑其背,双拳乱击。徒皆瞠视无敢近者。熊负痛而逃,晓雨反坐复饮。
这段文字,不仅两个主要人物“声态并作”,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晓雨的“掩鼻”、“自若”、“蹶起”、“以屐相击”、“双拳乱击”,熊八的“目光如炬”、“抚刀”及“负痛而逃”,都可谓是绘声绘色的传神之笔;而且周围环境气氛的渲染也非常出色:从“红粉满座,弦歌竞兴”到“一座失惊,弦声忽止”,气氛的紧张令观众屏住了呼吸;晓雨痛打熊八之时,众徒“皆瞠视无敢近者”,也从侧面衬托了晓雨的神威;一场激战之后,晓雨若无其事地“反坐复饮”;凡此等等,都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如果把这段描写诉诸于视觉形象,当更觉精彩生动。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侠盗忠二》一篇,此篇写一盗而侠者忠二,骁勇狠暴,远近畏之如虎,后因病被缚之床,磔杀于大度关前:
其槛车至大度,动止自若,不异平时。行刑前夕,谓吏曰:“大度有加部氏善酿,请饮一碗。”饮毕而寝,鼾声如雷。将就刑,又劝一碗,曰:“饮此酒,死此土,亦一快事!”更使饮一碗,笑不受,曰:“临刑而醉,吾岂畏死者耶?”两腋贯枪者凡十四,即绝。
先后三次请酒或劝酒,忠二所言虽不同,但都凸现了一个侠盗的豪气和胆量;三层层层递进,令观者如见如闻,正如评语在此所点明的:“临终从容,写得如生。”
综上所述,《谭海》在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张扬个性和传统美德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依田百川作为一位明治维新时代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必然会烙有时代的印记。
和依田百川遥相呼应,我国同时代的小说家当首推王韬。王韬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也是一位文言小说家。无独有偶,他的《淞隐漫录》自序于光绪十年,《淞隐琐话》自序于光绪十三年,和依田百川《谭海》刊行时间(明治十七年,我国光绪十年)正好差不多同时。王韬是一位游历过英、法、俄诸国的文人,并办过报纸,主持过书院,是一位受过西化熏陶、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的小说虽为效法《聊斋志异》之作,“然所记载,则已孤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 它们也是作者“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注:王韬:《淞隐漫录·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在这一点上, 和《谭海》应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两国推行维新的结果不同),文体不同(《谭海》为笔记体,《淞隐漫录》等为传奇体),作者不同(毕竟一为日本人,一为中国人),他们同是用汉文写成的小说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无意比较它们之间的高下优劣,但在论及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相应历史时期时,引入域外汉文小说作为参照坐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