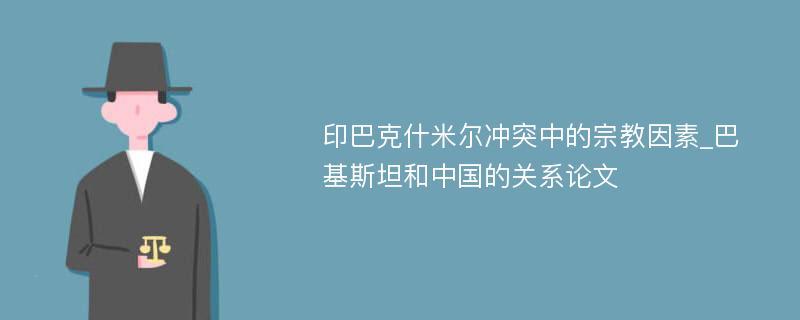
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的宗教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什米尔论文,印巴论文,冲突论文,宗教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4-0065-08
一、宗教是引起冲突的重要因素
南亚地区冲突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领土、资源、语言、种姓、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殖民征服、军事侵略及大国干预等。这些因素既有外来的,比如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分而治之”策略导致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教派冲突;也有内在的,比如印巴分治之初,两国都有因语言问题引发的各种群众运动和冲突。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源和动力。南亚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产生冲突之根源,而在这个宗教渗透力和影响力都极为强大的地区,宗教是引发冲突的最为突出的因素。
克什米尔冲突是南亚地区最激烈和最持久的冲突,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60年来,印巴两国因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三次战争和一次准战争(即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虽然国际社会曾干预过,印巴两国也就此举行过多轮谈判,但目前仍无和平迹象,而且克什米尔实控线两侧的渗透和反渗透、恐怖和反恐怖活动持续不断,暴力袭击不断发生,双方军队的所谓擦枪走火更是习以为常。
克什米尔冲突的难解,不仅因为它是领土的争夺、军事的较量和政治意志的比拼,更涉及深层的宗教问题。宗教矛盾对冲突的形成及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这种矛盾既有其历史根源,也与印巴两国的内部政治状况有关。
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殖民者在撤离次大陆前以宗教为基础分治印巴的结果。1846年,英国殖民者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卖给印度教徒古拉布·辛格(Gulab Singh)后,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的矛盾冲突开始加剧。1947年殖民者撤离前通过的《蒙巴顿方案》及《印度独立法》则使印穆双方形成对抗局面。两者原则上接受穆斯林联盟的“两个民族”理论①,同意将英属印度分为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自治领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自治领,并指出克什米尔等500多个土邦有权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自治领,或成为独立国家。② 其中克什米尔是最大的土邦,其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印度在争夺克什米尔时动手早,成功地争取到信仰印度教的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协定》。由于当时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占77%,因而巴基斯坦拒绝接受大君的选择,坚持宗教分治原则,并要求按照朱纳格土邦的先例② 由克什米尔人民公决其未来。双方冲突由此产生,并很快发展成两个新生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3/5的土地和3/4的人口,其余部分由巴基斯坦控制。
自此,由印巴的争夺所导致的克什米尔冲突开始加剧,而宗教矛盾则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政治失败激化了宗教矛盾。虽然印度在法律上给予了克什米尔特殊的自治地位,但新德里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一直不放心。特别是在印巴对抗的背景下,印度始终忧虑难消,因而不断加强对克什米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第一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在政治上开始逐步削弱克什米尔的自治权,以加速其与印度联邦的政治整合,在军事上,则大量抽调非本地、非穆斯林的军队进驻克什米尔,甚至以其取代本地警察维持治安。进驻克什米尔的军队包括中央警察后备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边界安全部队(Border Security Force)、印藏边界警察(Indo- Tibetan Border Police)及国家步枪队(Rashtriya Rifles)等,他们多来自印度东北及旁遮普地区,有着丰富的边界游击战和反恐经验。但印度的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阶段性的失误。第一阶段是1953—1975年,以首次关押谢赫·阿布杜拉开始,到1975年最后释放为止。在这一时期,印度一方面长期囚禁有独立倾向的谢赫,另一方面逐步削弱克什米尔的自治权,试图使其成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从1984年解散法鲁克·阿布杜拉政府开始,到1996年结束“总统治理”为止。印度联邦政府为完全控制克什米尔,用尽政治手段,国大党还越俎代庖,长期垄断克什米尔在联邦人民院的6个议席,完全中断了克什米尔的民主程序。这种做法激起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民众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扶持亲信、国大党插手选举是印度教徒在对穆斯林搞直接统治,因而走上了武装反抗甚至独立的道路。
此外,印度联邦政府对克什米尔的经济发展始终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当地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指标,如生产总值、木材和手工艺品出口、人均收入等都呈急剧下降趋势,同时失业率大幅上升。大量穆斯林青年或从世俗学校转向宗教学校,或从课堂走向街头,成为反印的主力。
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宗教政党和机构则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他们在动员、组织和领导穆斯林的反抗运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伊斯兰复兴浪潮影响下,克什米尔涌现了一批新的伊斯兰宗教政党,包括自由阵线(Mahaz- e- Azadi)、伊斯兰学联(Islamic Students' League)及伊斯兰研究会(Islamic Study Circle)等。这些组织一度集中在“穆斯林联合阵线”(Muslim United Front)麾下,并积极参加了1987年的议会选举。选举败北,其领导人和活跃分子多遭逮捕。政治上遭受挫折后,他们开始利用清真寺动员群众。一时间,克什米尔的清真寺成了反印堡垒,宣礼楼里传出的是成千上万人要“自由”的呐喊。1988年后,武装反抗运动开始成为主流,“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则成为反抗运动的新的领导者,他们利用伊斯兰教广泛号召和动员民众。他们对印度教徒、政治领导、军情人员、办公大楼、军营、警察局、公共汽车等目标发起恐怖袭击。1989年,该组织绑架了内务部长穆夫迪·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女儿,从而导致了联邦政府在克什米尔的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1990年3月,该组织在一苏非圣地举行30万人的集体宣誓,要为“自决”战斗到底。1993年后,“各党自由会议”(All Party Hurriyat Conference)成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民意的新代表,该组织与巴基斯坦在举行全民公决这点上立场一致。它旗下的二三十个成员中,既有谋求独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也包括亲巴的克什米尔伊斯兰促进会和穆斯林会议,还包括圣战者党(Hizbul Mujahideen)等武装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得他们的斗争策略也较灵活,既搞武装斗争也搞政治斗争,既打也谈。从2000年起,该组织几次主动停火,与联邦政府举行会谈,但都因在接纳巴基斯坦为第三方、允许该组织访问巴基斯坦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欢而散或无果而终。
其次,宗教改变了克什米尔地区冲突的特点。印巴间的三次战争使巴基斯坦认识到,武力不能改变现状。1971年第三次战争后,克什米尔问题陷入僵局,1998年印巴的核试验更是加剧了这种状态。在弱势和僵局的态势下,巴基斯坦开始利用印控克什米尔的混乱,从“政治、道义和外交”上支持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解放”事业。印度和美英等国认为,巴基斯坦为改变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开始改用伊斯兰“圣战”武器,巴三军情报局为“圣战士”提供大量武器弹药、金钱物资,巴的宗教学校成为培养“圣战士”的摇篮,巴控克什米尔则成了对恐怖分子进行“岗前培训”的基地。④
在这种局面背后,宗教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因为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坚持克什米尔地位未定、应进行全民公决的法理基础。同样出于宗教感情,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宗教组织均将克什米尔冲突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冲突,无论国内问题有多大、矛盾有多深,他们都全力支持政府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进入印控克什米尔的有很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将印度视为敌人也多是出于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此外,不同时代民间所称的民兵、志愿者、游击队、渗透者、武装分子或“圣战士”的共同身份其实也都是穆斯林。1995年后,外来的泛伊斯兰主义“圣战”组织和“圣战士”开始大量进入克什米尔,这使克什米尔冲突带上了更多的非本地化色彩乃至宗教色彩。从总体来看,这些“圣战士”中既有克什米尔本地人,也有来自巴控克什米尔、阿富汗、阿拉伯、中亚和苏丹的“外国人”。按照印度反叛司令部收集的数据,1999年的前8个月,印军击毙的617个游击队员中,167个是“外国人”,占27%。2000年的前8个月,击毙的游击队员总数为941,其中有261个“外国人”,占28%。⑤
同时,正是这种宗教因素使得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开始不断向外扩散影响,从而导致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虔诚军”(Lashkar-e- Toiba)和“穆罕默德军”(Jaish- e- Mohammad)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圣战”组织,其成员沿着740公里实控线及印度与查谟西南和巴基斯坦的200公里边境线不断向印渗透。他们起初在印控克什米尔活动,后又渗透至新德里、孟买等城市和地区,进而制造自杀性爆炸恐怖案或挑起大规模的教派冲突。2001年12月,这两个组织袭击印度联邦议会大厦,引起印巴百万大军在实控线两侧紧张对峙一年多。虽然美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宣布其为极端和恐怖组织⑥,但其网络却难以铲除。2002年2月,“虔诚军”涉嫌插手印度古吉拉特邦导致800多人死亡的印穆教派大屠杀;2006年,“虔诚军”在孟买制造连环爆炸案,导致近20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并几乎使印巴和平进程中断。
西方有观点认为,克什米尔冲突的不断发展是亚洲伊斯兰化的结果,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泛伊斯兰运动改变了克什米尔冲突的特点。目前的局面是,克什米尔冲突在怀有极端宗教立场的穆斯林的眼里已成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而印度则将自己的镇压和报复行动视为反恐斗争。
二、宗教差异使冲突难以化解
克什米尔被称作亚洲的“心脏”,因为它正处在中亚、南亚、西亚和东亚的连接点上。这一地理位置也使其在历史上经历各种宗教和文化的融合或碰撞,并呈现出今天的高度碎化的状态。
(一)宗教认同差异导致矛盾。印控克什米尔由三个宗教特点鲜明的地区组成,即克什米尔河谷、查谟和拉达克。其中克什米尔河谷面积最小但人口最多,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拉达克面积最大但人口最少,佛教徒占简单多数;查谟则印穆人口相均。
虽然印巴都宣称对整个克什米尔拥有主权,但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并不抱希望,巴基斯坦也不试图领有穆斯林不占多数的拉达克和查谟,而克什米尔河谷则成为印巴冲突的焦点。克什米尔河谷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超过90%,什叶派约占5%,印度教徒不到5%。在近代,印度教大君曾视该地区的居民为“被征服地区的外国人”。⑦ 1947年10月,身为穆斯林的谢赫·阿布杜拉开始任克什米尔临时政府的总理,与哈里·辛格大君相反,他主要关心的是克什米尔河谷地区居民的利益,并将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他对查谟和拉达克地区并不关心,甚至表示即使这些地区要独立他也不反对,结果引起了这些地区居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谢赫下台,但他建立的政党国民大会党一直是克什米尔的执政党,该党的选民基础是克什米尔河谷的穆斯林,政策也自然向此倾斜。在查谟印度教徒的强烈要求下,印度联邦政府开始不断干预该地区事务,而河谷地区的穆斯林则将这种干预视为印度教徒的统治,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在这里驻扎了近40万军队和准军事化武装。由于这些士兵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印军与巴基斯坦渗透人员和恐怖分子的斗争也变成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较量,导致这一地区的宗教关系也极为紧张,血腥冲突频发。就在这一时期,由于穆斯林极端分子曾提出要扫清克什米尔河谷的印度教徒,使得近十万的印度教婆罗门被迫逃离该地,而成为斯里那加或新德里的难民。
查谟地区曾是印度教大君的统治中心,印度教徒占人口总数的60%,但这些印度教徒与克什米尔河谷的婆罗门在人种和种姓上均差别较大,其政治目标也不尽相同。虽然穆斯林人口在查谟不是多数,但在该地区的6个县中,穆斯林占多数的有3个。这3个县的穆斯林也各不相同,多达(Doda)县的穆斯林占57%,与克什米尔河谷穆斯林一样讲克什米尔语,两者政治诉求也一致,但县境内的穆斯林只在有些地方占多数,比如在该县的三个主要城镇中,多达镇穆斯林占多数,巴德尔瓦(Bhaderwah)镇印度教徒占多数,而基希特瓦尔(Kishtwar)镇则是印穆人口各占一半。另两个县拉朱里(Rajouri)和蓬奇(Pooch)的穆斯林属于古贾尔人(Gujjars)和拉其普特人(Rajputs),与巴控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旁遮普的穆斯林共性较多。查谟是宗教对抗比较激烈的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印度教右翼组织在该地区都较为活跃。1947年印巴分治时,这里曾爆发大规模的宗教仇杀。
拉达克地区最初佛教徒占优势,但穆斯林人口在该地增长很快,现在两者人数大体相当。该地有两个县,列城县佛教徒居多,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卡吉尔县穆斯林占95%,他们属什叶派主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但在人种上属于波罗的海人。佛教寺庙据有该县的大量土地,什叶派穆斯林则控制当地经济,并垄断了列城和西藏的贸易。当地的佛教领导人对克什米尔河谷地区并没有认同感,而是希望与印度教查谟合并成一个邦或一起成为旁遮普邦的一部分。
巴控克什米尔由北部地区和“自由克什米尔”两部分组成。北方地区包括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洪扎。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在人种上则属于西藏人。洪扎的穆斯林属于伊斯玛仪派。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对该地区采取的是逐步整合的策略,齐亚·哈克执政时期(1977—1988)巴政府曾强化这一策略,结果导致什叶派开始反抗逊尼派的“统治”。巴基斯坦除派军队镇压外,也借助教派力量的帮助,来自西部边境省和阿富汗的帕坦部落民在军方授意下进入吉尔吉特地区,屠杀并驱赶什叶派穆斯林,同时外地移民在政府鼓励下纷纷进入该地定居。到2001年1月,克什米尔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人口比例已从原来的1∶4提升到了3∶4。这些“外地人”往往成了进入印控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武装主力。
自由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讲旁遮普语,在法律上享有“独立”地位,持有巴基斯坦护照而不是身份证,它有自己的立法会(LEGISLATIVE)和国家委员会(STATE COUNCIL)。但巴基斯坦政府对该地的管理和控制是非常严密的,如国家委员会的14个成员中一半由巴基斯坦总统任命,而巴总统本人则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巴联邦政府的克什米尔事务部则涉足当地日常事务的管理。巴基斯坦的各政党对该地区也均有渗透,除人民党在此设有支部外,其他党派也都在该地有代理组织,比如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在该地的代理组织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All Jammu and Kashmir Muslim Conference)。
(二)政治对宗教的利用使冲突加剧。克什米尔的政治是教派政治。政党往往从宗教组织蜕变而来,或是某宗教组织的政治翼,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或保护宗教信众的利益。虽有政党在创建伊始曾自称为世俗政党,但后来也逐渐教派化。
国大党因标榜世俗政治,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几次选举中,曾成功地吸引了很多穆斯林。在克什米尔其选民库主要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查谟,为了迎合当地的印度教徒,国大党也往往会利用教派问题。以1983年议会选举为例,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甚至利用将抑制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威胁来争取印度教徒的选票,结果引发了选前、选中和选后的教派暴力。这次选举中国大党在克什米尔河谷一票未收,而获得了查谟地区3/4的席位,充分显示出克什米尔的政治教派化倾向。
上世纪7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阿富汗“圣战”组织抗苏的胜利使克什米尔穆斯林信心大涨,并意识到了伊斯兰武装的力量。谢赫1982年去世后,没有谁能控制克什米尔河谷的伊斯兰武装化势头。上世纪80年代,印度教教派主义复兴浪潮波及克什米尔。“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将自己视为南亚正宗,进行反伊斯兰教宣传。“国民志愿团”领导人曾宣称,“伊斯兰教是世界的更大威胁”。⑧ 印度教政党印度人民党也积极利用克什米尔冲突。该党前身人民同盟1951年就卷入克什米尔教派冲突和教派政治,其政治行动口号是,给克什米尔自治地位,让它将像巴基斯坦一样独立。1980年,该组织变更为印度人民党后,不仅在全印炒作克什米尔题材,而且在国大党的资助下,插手克什米尔政治。1990年,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通过印度媒体警告巴基斯坦说,“如果要克什米尔400万穆斯林,那就要做好消化全印1.2亿穆斯林的准备。”⑨ 1991年12月中旬到次年1月下旬,印度人民党组织了一个半月的“统一大篷车”(EKTA YATRA)游行活动,从印度最南端康尼雅库马里到克什米尔首府斯里那加,一路宣扬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威胁,煽动教派对立。1993年7月起,印度人民党甚至公开征召退伍印度教军人组成民兵,保护查谟地区的印度教徒免受穆斯林游击队的袭击。1998年,印度人民党成为联邦执政党后,对克什米尔武装分子的镇压更为残酷,克什米尔穆斯林甚至将此视为纯宗教性的报复。
(三)宗教分裂导致民意分裂。克什米尔的民众分为独立、维持现状、亲印和亲巴四派。这种分化使他们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极难达成共识。
1.独立派。与次大陆其他地区相比,克什米尔有其独特性。首先是地形地貌。克什米尔崇山峻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次大陆则以平原和丘陵为主。其次是历史发展进程。印度历史上分多合少,而克什米尔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隶属于印度的中央政权。在同意加入印度联邦后的最初10年里,克什米尔保留有自己的宪法,其元首称“总统”,行政首领称“总理”(印度其他邦的行政首领称“首席部长”)。克什米尔这种独特的地理历史背景导致了“克什米尔特性”(Kashmiriyat)和克什米尔民族主义的产生。“克什米尔特性”是超越宗教、语言和政治倾向的克什米尔人的共同文化特征,是14世纪伊斯兰苏非派和印度教结合的产物。而克什米尔地方民族主义则体现在他们对平原地区的中央政府没有认同感,因而希望独立。这种独立意识和离心倾向在精英和大众阶层都存在。
当印巴轰轰烈烈闹分治时,克什米尔大君哈里·辛格则采取躲避和拖延战术,1947年8月到10月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虽然后来大君在压力下加入了印度,但克什米尔的独立运动却从未停止。由于哈里·辛格反感尼赫鲁,当时的印度政府转而扶植谢赫·阿布杜拉,后者虽曾公开宣誓效忠印度,暗地里却希望独立。1953年至1975年,印度政府长期限制谢赫·阿布杜拉的人身自由,同时不断加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1955年,支持谢赫的克什米尔精英成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全民公决阵线”(Jammu and Kashmir Plebiscite Front),主张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克什米尔是否并入印度。
这种谋求独立的情绪在克什米尔从未消失,苏联解体和中亚5个独立共和国的出现则使克什米尔独立势力看到了自由的希望,一时间涌现了数十个独立运动组织,其中以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为代表。1993年后成为克什米尔新民意代表的各党自由会议除赛义德·阿里·沙·吉拉尼(Syed Ali Shah Geelani)派外,其他派别都倾向独立。1998年新成立的民主自由党(Democratic Freedom Party)则明确宣布最终目标是独立。
谋求克什米尔独立的除穆斯林外,还有印度教徒。查谟印度教徒主张独立,建立一个以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为中心的纯粹印度教徒国家。但这派主张不是主流,也难成气候。
2.维持现状派。该派代表谢赫·阿布杜拉之子法鲁克·阿布杜拉的一段话代表了这一派的基本立场:“让巴基斯坦人永远占有巴控克什米尔,让我们和平地生活在这里(作者按:指印控克什米尔)”。⑩ 这一派的民众基础雄厚。由于长年的冲突和斗争,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没有哪个家庭不是暴力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没有哪个村庄和城镇能幸免于难,穆斯林则是暴力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维持现状派不满于战争和流血使得他们与停火线另一侧要“解放”他们的穆斯林在观念和利益上存在较大分歧。不过,这种分歧不是矛盾,而是相互隔膜、陌生和不合作。1963年,印控克什米尔因供奉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胡子突然失踪引发了长时间的骚乱,1965年,巴基斯坦支持的“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uncil)乘机宣布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Of Jammu And Kashmir),希望打开革命形势,但结果令人失望。克什米尔穆斯林非但不将巴基斯坦游击队视为“解放者”,反而看成破坏者,认为印巴冲突搅乱了他们争取权利的斗争。当巴基斯坦武装人员向毛拉们求助时,绝大多数毛拉都不愿意帮忙。当巴基斯坦武装人员请求避难时,许多穆斯林家庭都感到恐惧,生怕被“秋后算账”。上世纪90年代,“虔诚军”等极端组织曾要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妇女出门戴面纱,使得当地穆斯林极为反感这些改变他们生活的“外来者”。
3.亲印派。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徒、佛教徒和锡克教徒属于这一派。谢赫·阿布杜拉执政期间(1947—1953),曾在克什米尔实行彻底的土改,将查谟印度教地主及拉达克佛教寺院的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农民,实际上是穆斯林。亲印派认为自己的利益在穆斯林精英组成的克什米尔政府领导下得不到保障,只有新德里才是自身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因此要求废除宪法第370条,即废除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而将查谟和克什米尔改造成一个普通邦。
4.亲巴派。情感上,印控克什米尔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亲巴派,这是由宗教认同决定的。即使主张独立的穆斯林往往也会在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间摇摆不定,并在某些时期表现出亲巴倾向。谢赫·阿布杜拉是典型例子。谢赫·阿布杜拉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民主和世俗政体,但他自己是穆斯林,他的群众基础是穆斯林,他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司令部都建在伊斯兰教圣地。他的穆斯林身份使他在情感上倾向巴基斯坦,他第一次入狱就是因为接近亲巴的美国政治家。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独立派往往将与巴基斯坦的合作视为谋求独立的前提,因而也会在某个阶段成为亲巴派。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是主张武装独立的,但它最初几年与巴基斯坦有关机构和组织往来密切,常将武装人员送到巴基斯坦境内营地培训。自称代表克什米尔民意的“各党自由会议”与巴基斯坦关系也相当密切,二者不仅在搞全民公决这点上有共同点,而且遇有重大政治事件都相互通报。
三、宗教因素对克什米尔和平进程的影响
与中印热心推动边界问题谈判相反,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谈判长期陷入停滞,已成死结。其难点就在于除领土因素外,还有宗教因素。由于宗教涉及民众情感,因而比领土争端更为复杂。
(一)宗教宿怨难以消除。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本是同根、同族、同宗、同文化的同胞。14世纪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建立统治前,当地居民主要信仰印度教和佛教。14世纪后,伊斯兰教开始占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苏非派进行的,但暴力强迫改宗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斯坎德尔(SIKANDER,1389—1413)苏丹就曾强迫印度教徒或其他信众信仰伊斯兰教,并摧毁多处印度教圣迹,使宗教矛盾开始出现。而矛盾的加深则是在近代。1846年印度教大君统治克什米尔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地位发生倒置,印度教成了统治者和有产者的宗教,伊斯兰教则成为被统治者和无产者的信仰,这也体现在法律法规上。比如,印度教徒崇敬母牛,而穆斯林喜食牛肉,但1920年前的克什米尔法律规定,屠杀母牛者判死刑。这条法律后来有所松动,但刑期最低时也是七年。(11) 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也常演化成宗教矛盾。如,1865年政府军枪击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穆斯林披肩工人,结果引发了印穆冲突,导致无数伤亡。
印穆宗教仇恨的难以消除充分表现在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上,这场论战持续了近500年,倒寺和护寺的斗争也持续了近500年。巴基斯坦政府声援印度穆斯林,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则卷入其中。1992年,印度因寺庙之争引发全国性大屠杀时,巴基斯坦穆斯林也对境内的印度教徒进行报复。2005年7月,8名穆斯林武装分子冲进阿约提亚寺庙,用汽车炸弹炸开安全防护墙并与警方激烈交火,差点引起印度境内的教派屠杀。而克什米尔对巴基斯坦穆斯林而言,是旧怨加新仇,他们不会让步,也不会袖手旁观。
(二)意识形态对决异常激烈。克什米尔现已成为印度世俗主义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对决的舞台。按照“两个民族”理论,穆斯林居多数的克什米尔应全部纳入巴基斯坦版图,而不是印度。巴基斯坦坚持克什米尔是自己的“静脉”,没有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领土和意识形态就不完整。虽在国力和军事实力上居下风,但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不惜代价争取克什米尔。用穆沙拉夫总统的话来说,为克什米尔事业奋斗是他的“天职”。(12) 巴基斯坦还利用印度对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严厉镇压试图向国际社会说明,在印度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穆斯林是不可能与印度教徒和平共存的,从而证明“两个民族”理论的合理性。
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世俗主义的国大党将其作为展示其世俗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窗口,宗教政党印度人民党将其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但他们都坚决反对“两个民族”理论,坚持穆斯林是印度民族的一部分,主张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占有是合法的、不能谈判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印度要解决的不是“克什米尔问题”(Problem of Kashmir),而是“克什米尔内部问题”(Problem in Kashmir),即军事上加大打击跨境恐怖主义的力度,政治上理顺中央和克什米尔的关系、恢复民主选举,经济和社会上加大投入,国际上挫败巴基斯坦和国际人权组织对其违反人权的指控,将克什米尔问题宣传为由巴基斯坦支持的“侵略”和自己的反侵略问题。
近年来,印度改变过去的僵化立场,其领导人几次主动启动和平进程,也将克什米尔问题列为印巴谈判内容,但真正的谈判从未进行过。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执行两个“任何”的政策:不接受任何重新划分国际边界的提议,不接受任何以宗教为基础试图进一步分化印度的提议。(13) 巴基斯坦一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也开始显示弹性,放弃了将联合国决议作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唯一方案的立场。2004年10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甚至提出将克什米尔划为七个区的想法。该提议的主要内容是,将实控线两侧的克什米尔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划为七个非军事化的管理区,让其逐步独立,或实现印巴联合控制下的共管,或实现联合国授权下的共管。印度方面认为这个提议与联合国决议一样,都是以宗教为基础分裂克什米尔的想法,因而置之不理。巴基斯坦只好重提全民公决。
(三)印巴战略调整使冲突长期化。按照印度和西方的说法,第三次印巴战争后,被断掉一“臂”(指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帮助东巴成立孟加拉国)后的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力量对比中更处弱势,被迫采取新策略:以穆斯林武装分子牵制印度正规军,以非常规战争和代理人战争消耗印度国力(14),而印度在克什米尔治理不善引起的混乱则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机会。为应对这种变化,印度一方面继续保持在克什米尔的驻军数量,另一方面加强部队的反恐和防渗透能力。2004年印度发布新的战争令,将小规模边境渗透引发的低烈度冲突作为今后要应付的主要作战样式之一,并且提出低烈度作战的政治目标是“冲突管理”而不是“冲突解决”。(15) 印巴改变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正面消耗,转入了低成本的游击战、迂回战和持久战,克什米尔冲突将长期化。
收稿日期:2008-01-18
注释:
① “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的立国理论,指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应以此为基础建立两个民族国家。它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83年首次提出,后经伊克巴尔和真纳发展、集成。
② 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③ 朱纳格土邦居民80%为印度教徒,但其王公是穆斯林。王公1947年8月宣布加入巴基斯坦,印度自治领政府否认其宣布,提出要实行全民公决,并派兵进入接管政权。1948年2月,印度政府不顾巴基斯坦指责,在该地区搞全民公决,结果绝大多数居民同意加入印度自治领。
④ Christophe Jaffrelot ed.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Anthem Press,p.127.
⑤ Sumantra Bose,Kashmir,Roots of Conflict,Paths to Pe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1.
⑥ 2001年,美国宣布这两个组织为恐怖组织。2002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宣布其为极端组织。2002年3月,印度宣布其为恐怖组织。
⑦ Iffat Malik,Kashmir,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Dispu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9.
⑧ Robert G.Wirsing,India,Pakistan and the Kashmir Dispute :On Regiona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St.Martin' s Press,New York,1998,p.165.
⑨ Iffat Malik,Kashmir,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Dispu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1.
⑩ Sudhir Jocob George ed.Intra and Inter- State Conflicts in South Asia,New Delhi:South Asian Publishers,2001,p.225.
(11) Sumantra Bose,Kashmir,Roots of Conflict,Paths to Pe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8.
(12) Christophe Jaffrelot ed.A History of Pakistan and Its Origins,Anthem Press,p.273.
(13) Ashutosh Misra,“The Problem of Kashmir and the Problem in Kashmir:Divergence Demands Convergence”, Strategic Analysis,Jan-Mar 2005,p.36.
(14) Monique Mekenkamp,Paul Van Tongeren eds.Searching For Peace in Central and Sonth Asia: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Peacebuilding Activities,Boulder,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p.297.
(15) 曹永胜、王京地:“强调控制规模,印度发布新战争条令”,《环球时报》,2004年12月1日,第10版。
标签: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印巴战争论文; 印巴冲突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巴基斯坦经济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穆斯林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印度教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武装论文; 印控克什米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