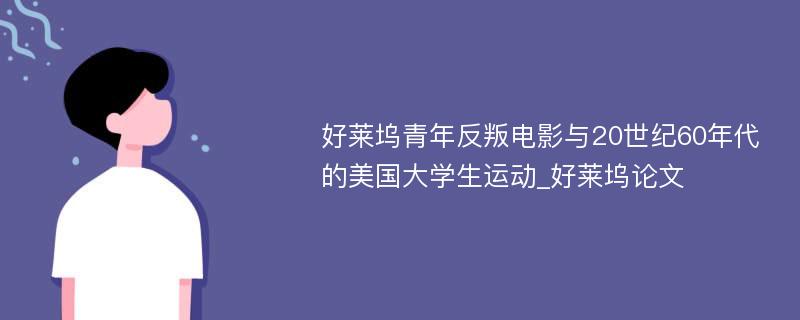
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与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美国论文,青年论文,大学生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反映或解读它们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比现实的事件稍晚一点而已”(Lev,Peter,2000:1)。作为美国社会青年化的标识,六十年代①美国大学生运动及其相随的激进政治与反文化现象,也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六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形成了一个电影亚类型——青年反叛电影(teenpics),这一类型片开启了好莱坞电影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这类电影因其在解读、建构和解构青年新伦理与学生激进政治方面的作用,对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电影与社会运动的结合,这是六十年代美国(也是西欧)社会运动史、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电影对青年学生的反叛伦理、学生运动中的历史事件是怎样解读的?电影与学生反叛的关系如何?电影制作和宣传对大学生运动的退潮有何关系?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大众媒介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生运动的特征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大众媒介的控制作用这一问题上,成果比较丰富。不过,就六十年代美国电影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而言,研究较少。少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电影与反文化”这一问题上,如陈淘的《美国青春片中性的政治学》(陈淘,2000年),李轶君的《迷茫与反叛之旅——读解〈毕业生〉》(李轶君,2005),许海龙的《弗洛伊德的“孩子”与毁灭的“成人”——好莱坞的“反文化电影”》(许海龙,2007年)等论文。本文作者试图考察六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与大学生运动的互动关系,并把重点放在电影对大学生运动的双重作用这一研究上,以期对大学生运动衰微的原因作出一些合理解读。
一、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出现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战后规模庞大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陆续成年,但这一现象并未为好莱坞重视,青年没有成为电影叙述的主题。直到1967年及前后,它才表现出对青年文化与大学生激进政治的浓厚兴趣,开始推崇青年伦理和同情学生激进政治。这种变化,是由以下一系列内外因素综合促成的。
从内部因素来看,好莱坞陷入生存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影业格局变化,是促使其走向新好莱坞的主要动因。
20世纪60年代,与美国丰裕社会的繁荣和兴盛相悖的是,好莱坞影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总结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电视的普及和电视节目的推广,促进了娱乐的家庭化,抢夺了大量电影观众。1959年每周观看电影的人数大约有8700万,而到了196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500万(Foreman,Carl,1973:699-706)。根据1967年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研究,除30岁以下的青年人之外,其他年龄层的电影观众人数正在急剧减少(Bodroghkozy,Aniko,2002:38-58)。这使得好莱坞电影的上座率急剧下降,票房收入直线下挫。仅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联美公司就损失了8500万美元收入,米高梅公司损失了7200万美元,21世纪—福克斯公司损失了6500万美元,而哥伦比亚公司陷入破产边缘(Bodroghkozy,Aniko,2002:38-58)。海外市场本来占票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这时受欧洲新浪潮电影的冲击,境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好莱坞的海外市场份额直线下降,已经只能依靠吸引本国观众来盈利了(Foreman,Carl,1973:699-706)。
二是海外片的持续引进对美国国内电影市场构成了严重冲击。60年代好莱坞仍然沿袭了旧好莱坞的制作方法和风格,如摄影棚制作方法、故事性的叙述风格等。而此时,在欧洲,以法国电影界为首,新浪潮电影取得巨大成功。它以非叙事的风格、自然景的拍摄方法、大胆的个性表演,赢得美国青年人的喜爱。海外片持续流入美国市场,“戈达尔、特吕弗以及安东尼奥尼的革新,已征服了新一代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以及艺术殿堂之观众”(杰·马斯特,1992:225-251),这进一步压缩了好莱坞电影的生存空间。
好莱坞影业的萧条,促使其内部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50、60年代,联美公司先后落入辛迪加集团和花旗银行之手。1966年,派拉蒙公司成了海湾和西方石油公司的一部分;1967年,环球公司被美国音乐公司收购;华纳兄弟公司被七艺公司合并,两年后又归于华纳通讯公司旗下;1969年,米高梅被超美集团并购。八大制片公司只剩下了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和迪斯尼3家暂能独立运作,至此,好莱坞历史上的大制片厂制度逐渐消亡。
好莱坞出现的新格局对实验性电影的制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新的不熟悉电影事务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商业资本家掌控好莱坞,使得美国电影业进一步商业化。“60年代晚期电影公司不再有兴趣制作电影,他们只控制着整个流程最后的营销环节”(Quart,Leonard,2002:73-74),这种新的分工体系给主张实验性新电影观念的青年导演提供了足够的创作自由。这种格局的变化对好莱坞的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社会的青年化、学生运动与反文化运动显示的青年力量的增长以及深受青年反文化影响的被称之为“电影小子”的青年导演逐渐主导好莱坞,是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出现的强大外在动力。
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快速进入青年化的时期。到1964年,二战后出生的庞大的婴儿潮群体②中最年长一批已经成人,此后,步入青年的人口数量逐年急剧增长。到1967年,美国人口的52%是年龄低于25岁的青年人。悄然进入青年时期的婴儿潮一代,对美国人口结构的冲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是因为人口达7600万的婴儿潮一代直到1982年才能全部进入青年时代。青年数量的增长,也给电影业带来了新的潜在的观众群。事实上,在60年代,青少年群体是电影观众中唯一数量在上升的群体。根据1967年美国电影协会的统计,好莱坞48%的票房收入来自16-24岁的青少年观众(转引自Bodroghkozy,Aniko,2002:38-58)。创造符合青年口味的文化产品,挖掘最具潜力的青少年观众,是好莱坞弥补中产阶级成年观众流失的最好办法。
美国人对社会青年化的趋势虽有所预见,但社会对汹涌而来的青年潮,其安置和接纳仍无法调适到位,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青年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因冷战局势的恶化、美国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向普及化、越南战争的升级等特殊氛围而进一步突出,最终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新左派运动、大学生运动与反文化运动。
1962-1964年,大学生运动属于改良性的社会运动,它以建立一个替代性的参与式民主社会为奋斗目标,提倡青年学生应明晰自身群体及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学生运动初期实施的校外“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并未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1964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自由言论运动”,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大学生运动开始受到关注,青年力量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965-1966年,美军在东南亚大举增兵并征召大学生入伍,引发大学生强烈不满,大学生运动进入到以反战、反征兵为重心的高涨阶段。与此同时,反主流文化、反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反文化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与学生运动形成合流,共同组成那一时期一道特殊的政治文化风景。这样,在美国历史上,青年人首次占据了社会最显著、最强有力位置,青年现象成为美国人不能忽视的“存在”。紧跟美国政治文化的变化节奏,尝试与青年政治对接,对青年的文化与政治运动做出某种回应,续写新的美国梦以赢得青年观众,这符合好莱坞的生存之道。
真正推动经典好莱坞向新好莱坞过渡是一批被称之为“电影小子”的青年导演。好莱坞格局的变化为青年导演创造了展示才华的最佳机遇。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丹尼斯·霍珀、迈克·尼科尔斯、阿瑟·佩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约翰·卡萨维斯特、萨姆·佩金帕、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科西斯、维廉·弗里特金等人,组成了美国电影界的文化左派,主导整个影坛。与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师徒培养方式不同,这些青年导演大多属于第一代接受过正规电影专业教育、学院出身的导演。他们懂得电影产业运作的规则,懂得娱乐与价值的结合模式,熟悉好莱坞的商业化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大学和学院,与同龄人有着同样的运动体验,分享着相似的价值理念。他们希望能迎合青年学生对关联性电影③的要求,创作出属于青年一代的电影。这些都使得青年导演们能够沿袭和借鉴欧日电影经验,大胆地创新和实践新电影。正是这些导演,使好莱坞与青少年观众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市场策略和制片方式的转变引发了青少年内容的电影的流行,也造就了左右当今电影工业的年轻观众群。”(Noherty,T.1995:14-15)
二、走进青年世界与运动的扩容(1967)
关注国内社会之关切,瞄准市场的新动向,改进电影理念和技术,这是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走出泥潭的唯一途径。到1966年,青年文化与学生激进政治是美国电影业不可忽视的存在,迎合青年学生的风尚和喜好成为好莱坞的共识。
创作青年喜欢的电影这一任务,落在了新好莱坞的导演们身上。在建构学生激进政治和反文化上,新导演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要将反文化的、学生政治反叛的因素注入到电影制作中去,迎合青年学生对创作“关联性”电影的要求。迈克·尼科尔斯的作品是为了探索“被好莱坞利用得太糟糕并且损毁的主题——青年”(Bapis,Elaine M.2008:43-45)。《逍遥骑士》的导演丹尼斯·霍珀表示,“当我们在拍摄这部片子时,我们已能感觉到整个国家在熊熊燃烧,包括黑人、嬉皮士、大学生。我的意思是说我把这种感觉融入到影片的每个符号中去”(彼得·比斯金,2008:67-68)。而彼特·方达(Peter Fonda,《逍遥骑士》主演、编剧)则强调,“1968年,我们有自己的音乐、艺术、语言和服装,但是没有自己的电影”(Lev,Peter,2000:5-6)。
1967年下半年,《邦尼和克莱德》和《毕业生》先后发行,标志着经典好莱坞完成了向新好莱坞的过渡,青年叙事与青年反叛类型成为了衔接这一过渡的内容与形式。好莱坞进入了与青年政治与文化亲密接触的时期,这势必对大学生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影片《邦尼和克莱德》(阿瑟·佩恩导演,作品还有《爱丽丝的餐厅》)被称为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获得了第40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奖。它是一部根据大危机时期美国两个银行抢劫犯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整个故事虽然发生在30年代,但很明显的与1960年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相一致,反英雄、反主流价值、反秩序的主题在电影中有着清晰的呈现。影片中,两个强盗邦尼和克莱德被塑造成有血有肉、有正义感、有尊严的形象,而相反,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警察,却被塑造成了无能、奸诈的群体。连最后的结局,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那么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死于对同伴父亲的信任。在影片中,强盗充当了无情冷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审判者,他们的反叛行为在普通美国人那里是有口皆碑的。邦尼和克莱德是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反叛者,也是无辜的牺牲品。阿瑟·佩恩颠覆了强盗的传统定义,同时也为六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反叛行为的合理性写下了很好的注释,“个人反抗社会、反常规和享乐主义的生活风格强化冲突,直接反抗社会不公正和禁锢个性自由的暴力获得了正当性”(游飞、蔡卫,2002:307-308)。
麦克·尼科尔斯的《毕业生》真实地反映了六十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本杰明是加州伯克利分校的高材生,在面对人生目标时总是茫然和孤独。“担心我的未来”,“我希望它与众不同”,“我只是有点不适应”,等等言辞,表现了大学生们普遍的迷茫心态。而父辈所代表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却显得庸俗、虚伪与糜烂,不再有道德说教的功能(鲁宾逊太太与本杰明的不伦关系即可说明)。其主题歌《寂静之声》很好地表现了青年人与父辈之间无法跨越的代沟,“我的话如雨滴般落下,在寂静的围墙中回响”,“他们交谈无需言语,他们领悟无需倾听”。本杰明最后挣脱了父辈们的控制,以逃婚的反叛方式,重获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毕业生》揭露了父辈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虚伪,宣扬了自由的、纯真的青年人的爱情。它真实地反映了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是一曲六十年代青年大学生新伦理和新价值的颂歌。
1967年两部青年反叛电影的发行,在美国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好莱坞电影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史上,《邦尼和克莱德》和《毕业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的问世,对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和反文化运动而言,无疑是一剂催化剂。早在1965年,学生运动就开始为新闻媒体所关注。其后一年,作为最早举起反战旗帜的学生运动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SDS)成为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作为另一种媒介形式,电影的介入,其亦真亦幻的青年叙事,以及对青年反体制、反文化的隐喻或明示的支持,将运动的理念进一步地推广开来,使运动进一步进入了公共视野,扩大了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它促进了大学生运动的扩容。与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强、观点模糊、不连续的文字或视频报道相比,电影文本的青年反叛叙事在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更强烈而持久。电影文本为反文化反体制活动正名,让更多的原本疏离激进政治和反文化的青年学生加入到运动中来,或者成为运动的同情者。在好莱坞《邦尼和克莱德》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托德·吉特林,2007:147-148)。《毕业生》在曼哈顿放映时,众多青少年冒着严寒,排队等候观看这部为他们制作的电影。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高年级学生米瑞安·韦兹(Miriam Weiss)曾谈到看《毕业生》的感受,“我为之笑,为之流泪”,“我把他(本杰明)看作是同感兄,他对未来、对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的困惑,我也如此”(Man,Glenn,1994:34-36)。麦克·尼科尔斯在后来谈到《毕业生》的结局时承认,即使五年后,反叛者和父母一样,融入主流,观众也一样会被刺痛而产生愤怒,因为他们分享着与本杰明一样的体验(Man,Glenn,1994:48-49)。一位受访者回忆,尼科尔斯的电影是“我们这一代紧抱着的影片,把它看作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预言”(Bapis,Elaine M.2008:59-60)。媒介的正名,越战的未决,都促进了学生运动的扩容。1967年开始,是SDS成员急剧膨胀的时期。1967年6月,成员约为3万人,一年后,最保守估计也有4万。到1969年,成员已经达到了10万,在组织外围的学生规模更为可观。1970年春夏之交的骚乱中,参加者达430万,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60%。
其二,它对运动的新走向起了重要的作用。1967年下半年,一向以示威抗议为主的相对温和的学生运动,开始转向暴力抵抗。10月,在向五角大楼进军过程中,学生与军警发生了搏斗。1968年前五个月,就发生了多起校园被炸事件。学生运动走向激进和暴力,虽然牵涉到多重原因,电影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在《邦尼与克莱德》中,暴力是作为一种美学来欣赏的。影片中杀人越轨的行为并不可耻,因为它首先是反体制的,是为反体制而采取的极端手段。一位名为杰拉尔德·朗的气象员就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弗朗茨·法农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一样的英雄。阿比·霍夫曼称,“美国早已把它的魔球遗失在了边疆,自那时起已不再有无所不能的神话,我们独自在影院看《邦尼和克莱德》时猎获了它。”(转引自吕庆广,2005:243-244)1968年及以后的影片,暴力与革命叙事更为直接,它无疑助推了学生运动的新转向。
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的尝试促进了学生运动扩容与激进化,不过,学生运动与反文化也对新好莱坞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运动参与者逐渐形成的观影生活习惯,将使新好莱坞的青年叙事进一步地延伸,也鼓舞好莱坞继续行走在青年路线上,追逐着青年人的时尚,与青年为伍,最终使好莱坞一度成为六十年代青年人自己的媒介形式。
两部影片的发行,使美国电影上座率出现自二战以来的首次上升,青少年成了最大的观影群。至此,好莱坞历史上的复兴开始了,经典好莱坞时代开始迅速转向了新好莱坞时代。好莱坞对青年文化和伦理的阐释,虽然浅陋,但是却抓住了青年人的心理,即好莱坞是同情青年反叛的,它正记录自己这一代正在创造着的历史。观看电影,对青年学生而言,就如观看荧幕上的另一个自我,给人“一种正在掌控大学、国家或者世界的行动主义感觉”(Bapis,Elaine M.2008:33-34)。也正因为如此,看电影逐渐成了青年反叛者的生活习惯,“这是100年电影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段,看电影,思考电影和谈论电影已成为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的热情所在,大家钟爱的不只是演员们,还有电影本身。”④好莱坞通过青年反叛电影,通过对冷漠的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攻击,成功地俘获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造就了一个18-25岁观影群。
青年反叛电影尝试的成功,国内票房收入大增,青年观众数量的稳定增长,进一步鼓励新好莱坞导演坚守青年路线,追逐青年时尚。随着运动在1968年之后逐步走向激进化和暴力化,导演们的创作也变得更为大胆、更为激进。为了赢得更多青年、大学生观众,1968年之后,导演们直接将现实的激进政治场景搬上了荧幕。从1967年开始之后的几年里,无论作为影视创作者、影评家还是作为观众,青年人都在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电影业。著名编剧家莫里斯·拉波特(Maurice Rapf)就曾感叹,电影成了青年的媒介,而青年人热爱着电影(Bapis,Elaine M.,2008:26-27)。
三、建构青年激进政治、文化伦理与运动的发展(1968-1971)
进入1968年,全美及西欧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游行、示威、占领校园及街垒战等等场景,在欧美各地先后上演。上半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而在其他西欧国家,1848年革命的场景似乎重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暴动以及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骚乱是这一时期运动的典型事件。这些运动再次见证了青年力量,引发了欧美电影制作理念的进一步变革,青年反叛类型电影得到更深入地发展。五月风暴之后,欧美拍摄的电影于1969年集中推出,这使1969年成为欧美电影与青年文化全面接触的一年,“无论是电影风格、还是电影内容,或是观众,欧美电影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Lev,Peter,2000:16-17)。在戛纳电影节上,英国的学生反叛电影《如果……》(1968年)获得金棕榈奖,美国的《逍遥骑士》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午夜牛仔》获得了最佳美术贡献奖。《爱丽丝的餐厅》(Alice's Restaurant)和《媒体的冷漠》(Media Cool)也获得了许多好评。同年,好莱坞还发行了《雨族》(the Rain People)、《野帮伙》(the Wild Bunch)、《最后的夏天》(Last Summer)、《鲍勃、卡罗、托德和艾丽丝》(Bob & Carol & Ted & Alice)以及《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等一系列反文化影片。影评家彼得·列夫(Peter Lev)评论道,“如果说好莱坞与大学生激进政治相遇的话,那么正是在1969-1970年间,伴随着《逍遥骑士》、《爱丽丝的餐厅》等影片的发行,好莱坞才公开地宣扬反战激进主义和青年文化”(Lev,Peter,2000:60-61)。
1969年的青年反叛电影中,丹尼斯·霍珀导演的《逍遥骑士》,“以充分的叙述自由”,“表现了六十年代青年无政府文化的能量”(Lev,Peter,2000:2-6),成为六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一部反文化影片。它讲述了两个长头发的摩托车手——嬉皮士青年比利和华特的自由与冒险之旅。两人从墨西哥贩卖可卡因,在洛杉矶销售,然后一路驶向新奥尔良。摇滚、毒品、麻醉剂、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在路上感到舒适的内容,异化和疏离是两人始终无法拭去的感受。与主流社会的一次次接触让他们一次次遭到野蛮的攻击和伤害:餐馆拒绝服务,参加节日游行被捕,警察偷袭,无端遭到当地居民恐吓与射杀。最终,两人在路上的青春与生命被保守的乡下人毁灭。
在影片中,避世、逍遥自在的两个嬉皮士,是美国社会的无数嬉皮士青年的代表,他们反美国、反体制文化、无所顾忌的自由,既宣扬了反文化的伦理,又激发了青年们实践异托邦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导演霍珀就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彼得·比斯金,2008:67-68)。
20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电影大都只表现青年内心的异化感、反文化的行为,或者边缘人物的暴力,激进政治电影还很少见。《毕业生》虽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场景,但对发生于两年前的“自由言论运动”保持缄默。1970-1971年,受反文化电影成功发行的鼓舞,也为回应如火如荼的学生反战运动,1970年至1971年,好莱坞新导演们开始直接书写和叙述激进政治。
1970年春,好莱坞各大影片公司集中推出了多部反映学生激进政治的电影,如《激进分子》(The Activist)、《青春火花》(Getting Straight)、《草莓宣言》(The Strawberry Statement)、《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扎布里斯基海角》(Zabriskie Point)等。
在此类作品中,《草莓宣言》和《扎布里斯基海角》最具代表性。《草莓宣言》是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詹姆斯·西蒙·丘嫩(James Simon Kunen)的自传改编的一部电影。它以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事件为背景,主人公西蒙是对校园政治不感兴趣的普通学生,卷入了哥大正在进行的静坐抗议、占领校园大楼的活动。西蒙不是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在与警察的对峙中,在目睹警察对学生的暴行之后,变成了一个激进政治分子。
影片对大学生政治的同情,对警察破坏大学自治、镇压学生的谴责,都是非常明晰的。为了揭露镇压行径,导演甚至用20分钟的时间来展现警察对躲避在体育馆内示威者的施暴过程。戴维·皮里(David Pirie)在《每月电影公告》上作了这样的评论,“即使三年前,也没有人能够预想到像《草莓宣言》这样的影片会在米高梅公司的旗帜下出现。这部电影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左派(反体制、反政策、反战等等)的基本观点是正当的,才会去探讨哥伦比亚运动中一个大学生的内心世界”(Pirie,David,1970:142-142)。
《扎布里斯基海角》由意大利新浪潮代表人物安东尼奥尼导演。它讲述的是一位革命忠诚度不明确的大学生马克的故事。在校园冲突中,他枪杀了一名警察,偷了一架飞机,飞往亚利桑那沙漠。在那里,他遇见了年轻的达利娅,一个不关心政治、正在赶往公司老板隐居地的兼职秘书。两人相爱、同居,然后分道扬镳,马克在归还飞机时被杀,而达利娅继续自己的行程。得知马克已死,达利娅眼前出现了老板的房屋被烧毁的幻觉。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同样给青年观众一种思想导向,即政治上不够激进的青年在形势所迫下也会变得激进。达利娅的幻觉告诉人们她的信念变化,“幻觉是一个诅咒,它预言她将献身于暴力的生活”(Yacowar,Maurice,1972:197-207)。
出于对变幻无常的青年观众市场的担心,这些在1969-1970年初拍摄的影片,于1970年春季抢先集中发行。不久,受“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和尼克松宣布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影响,美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学骚乱,六十年代大学生运动达到最巅峰的阶段。好莱坞青年反叛电影关于大学生激进政治和革命的预言似乎得到了应验。不过,这些电影在票房上却出乎意料的遭受重挫。除了明星埃利奥特·古尔德(Elliott Gould)加盟的《青春火花》取得较好的票房收入外,其他无一成功(Farber,Stephen,1970:24-33)。尤其以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扎布里斯基海角》为甚,这部电影广受批评它的制作成本为700万美元,而收入仅为90万美元,被称为是“现代电影史上最突出的灾难之一”。⑤
1971年,好莱坞工业继续发行了《比利·杰克》(Billy Jack)等少量暴力革命系列电影。它们在情节和拍摄手法上并无多大的超越,《比利·杰克》的故事与《扎布里斯基海角》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其他的也只不过延续了激进政治电影的制作风格,票房收入无一取得成功。此后,激进学生政治电影退出了新好莱坞导演的视线。
1968-1971年,新好莱坞继续追逐青年时尚、取悦青年观众,对大学生激进政治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运动的进程及理念施加了重要的影响。
其一,这一时期的青年反叛电影无一不宣传“反美主义”,宣扬反体制、反文化的正当性。在这些电影中,无论是精神上的反叛,还是行为上的大逆不道,都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安东尼奥尼在影片发行时就明确表示,“我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怀疑”(Golden,Jeffrey s.,1970)。影片极力刻画“警察与强盗”、“父与子”、“保守者与革命者”以及“他们与我们”的对立,并且为每一对关系的后者正名。而反文化的符号,毒品、摇滚乐、长发、性自由等被看作是个人摆脱社会异化、寻求精神自由的武器。
为反体制、反文化正名自然为青年尤其是学生的反叛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也鼓舞了青年学生进一步参与政治革命和文化反叛。1968-1970年,学生运动与反文化运动同时达到了顶峰。1974年,当政治革命偃旗息鼓之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则继续在社会青年、中产阶级以致整个主流社会中扩散开来。
其二,这一时期的电影很多都带有“实录”或“纪实”的性质。一些电影为纪录性影片,如《媒体的冷漠》、《伍德斯托克》(1970)、《激进分子》。《媒体的冷漠》直接由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示威者参与拍摄、制作而成。在《激进分子》中,导演也用了伯克利分校的马克·史密斯等激进学生,“作为电影真实性的证据”(Bodroghkozy,Aniko,2002:38-58)。在《伍德斯托克》中,导演米歇尔·沃德利(Michael Wadleigh)力图以记录片的形式再现1969年反文化运动的最重要集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盛况。它虽然没有当事者直接参与,对音乐节所传递的讯息理解也有所扭曲,但是仍然反映了部分的现实,学生运动的地下报纸《自由新闻》(Free Press)就曾评论,“作为一个文本,它能够在重申反文化青年关于不同社会秩序的观点中起到作用”(转引自Bodroghkozy,Aniko,2002:38-58)。
也有一些电影采用现实文本,如《草莓宣言》。它是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骚乱的参与者詹姆斯·西蒙·丘嫩写的回忆录改编而成的电影。以一位运动新同情者的底层视角来刻画学生运动以及政府镇压对其心理和行动上的影响,记录一位普通的自由主义者皈依激进政治的历程。
此外,一些电影还将故事发生的场景设定在作为学生运动或反文化的标志性地带,如《毕业生》中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最活跃的大学之一;《草莓宣言》发生的现场在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骚乱最严重的大学;《媒体的冷漠》发生在1968年广为人知的学生示威所在地芝加哥。一些电影制作者还直接前往大学、群居村、先锋文化中心格林尼治村进行实地拍摄。他们或者直接记录激进学生和反文化的生活,或者以之作为叙事背景。SDS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卡尔·奥格尔斯比就曾提到,1969-1970年间,在其隐居的群居村里,就有电影制片人前来拍摄学生政治革命题材的影片(理伯卡·E·卡拉奇,2001:351-352)。
“实录”或“纪实”电影,直接将普通激进学生的政治体验、学生运动中一些重要的事件搬上荧幕。在故事的叙述中,它们价值上倾向于肯定青年反叛的合理性(通常会设置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来警示暴力革命与反文化所要承担的代价和牺牲,但电影中大部分叙事与之无关),这会给学生运动、反文化的参与者和观望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由独立影片制作人自行创作,但由大影片公司冠名发行的电影,自然会给青年观众造成整个好莱坞认同他们的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印象,更坚定了其反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纪实电影,通常被看作为对某种历史真实的记录的。当自身体验过的真实或者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的行为被作为历史在记录时,婴儿潮一代创造历史的感觉在荧幕提供的真实中得以实现。无疑,这增加了青年反叛的勇气和力量,将对参与者的持续卷入、旁观者变身参与者等提供很大程度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刺激。
其三,好莱坞电影极力宣扬暴力,把学生激进政治等同于暴力的反抗,刻意突出学生运动与体制的对抗。
在这些影片中,既有作为美国体制化身的警察、国民自卫队对镇压运动施加的暴力,也有青年的暴力反抗,还有保守美国人对反叛青年随意施加的暴力。早在《邦尼和克莱德》中,两个强盗被警察射杀的场面竟被设计成死亡的芭蕾舞风格,创造了美化暴力的范式。在《逍遥骑士》中,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嬉皮士被保守的乡村人无端地枪杀,激化了青年与社会的对抗情绪。在《草莓宣言》中,长达20分钟的警察对示威学生的施暴情景,带来的不外乎是反叛学生对暴力反抗行为合法性的进一步认可。
这类电影对暴力的极力刻画和渲染,势必对大学生运动的进程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首先,影片中隐喻着暴力反抗的合法性,推动着学生运动迈向暴力和极端暴力的方向。亚特兰大地下报纸——《大斑鸟》(Great Speckled Bird)的一位评论者在观看《草莓宣言》后写下影评,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的运动宣言书,“看完后我变得疯狂了……相当的疯狂。其他很多人都如此。我们不仅仅同意某人对我们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我们的思想也转变了”(转引自Bodroghkozy,Aniko,2002:38-58)。社会学学者奈杰尔·扬(Nigel Young)也指出,一些以新左派、大学生运动为主题的电影,展现的只是与其经历完全不一致的象征符号和形象。它们弱化了运动,也强化了运动的革命姿态,助长了运动内部存在的趋势,即脱离分析、经验的趋势(Nigel,Young,1977:346-347)。
1967年美国大学生运动,即在电影、新闻媒体等大众媒介对其暴力的形象定制的影响下,开始偏离和平的轨道。休伦港宣言所倡导的参与式民主制以及非暴力斗争方式被新一代运动领导集体抛弃。这一年,SDS领导人提出了“学生阶级论”,提升了学生的政治要求。1968年,SDS会议决定支持黑人权力,希望通过支持黑人暴力解放,来诱导美国革命。同时,SDS对城市游击战、红卫兵运动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将之付诸实践。到1969年,从SDS中分离出来的气象员组织,已经沦为一个暴力恐怖组织,在大学、政府部门、军事研究中心等地实施了数百起爆炸。前学生运动领导人托德·吉特林就对电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许多电影都将有关暴力的内容进行了浪漫而又粗卑的处理——断章取义的暴力、美化的暴力、令镜头耽溺的暴力和无须理由的暴力。这些电影既是这种新情绪的象征,又是它的催化剂”(托德·吉特林,2007:145-147)。
其次,新好莱坞对学生激进政治和暴力革命的煽动,对反体制行为的隐性或明喻的支持,日益让观众不安,使其对学生运动题材的电影以及运动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1970年全国大学骚乱前推出的电影系列,更加剧了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慌,遭到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学生和大量来自其他年龄层观众的谴责。《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当大学生被枪杀,各大学正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之时,电影业的不人道的笨蛋却突然推出了《青春火花》,一部以充满暴力的大学为主题,热情高昂的小伙子们摧毁大学,以及人们在被包围的大学里扭打的电影”(Farber,Stephen,1970:24-33)。影评家莫里斯·雅各沃尔(Maurice Yacowar)在观看《扎布里斯基海角》时曾被坐在后面的成年男性的反应震惊了。在影片中出现黑人学生被杀的情形时,这位男子说“就应该这样”;当马克在归还飞机时被杀,他说“太好了”(Yacowar,Maurice,1972:197-207)。新好莱坞对学生激进政治、反文化的迎合与建构,在短暂地推动学生运动和反文化的价值延展之后,又因其建构的暴力形象而对学生运动声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使运动迅速地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合法性随之丧失。
其三,新好莱坞电影在发行过程中,通常会利用学生运动和反文化的宣传工具——地下媒体和大学报纸做宣传,以吸引学生观众。《伍德斯托克》发行时,影片公司和影院特地在《洛杉矶自由新闻》(Los Angeles Free Press)、《万花筒》(Kaleidoscope)等有名的地下媒体刊登广告。一些导演还特意接受地下媒体的采访,表达对学生运动与反文化的支持。《草莓宣言》的导演斯图亚特·哈格曼(Stu-art Hagman)和编剧伊斯雷尔·霍洛维茨(Israel Horovitz)就曾接受了《洛杉矶自由新闻》记者的专访。霍洛维茨表示,这部电影是为了触动400万观众的心,激发青少年的集体感,“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那些已经信奉激进政治的人们。电影假定参与运动的人早已形成了集体意识。它保护的是那些同西蒙一样、必须了解社会不公正准则的人们”(Bodroghkozy,Aniko,2002:38-58)。通过地下媒体的广告宣传和地下记者对电影的评介,新好莱坞电影在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制作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运动的参与者们假定为“圈内人”。1969年哈佛罢课事件中,一位新生说,现在的商业电影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为同一个理由占领建筑物,而过去进大学就是追求异性(Vertov,Dziga,1970:1-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好莱坞已经与青年文化、激进政治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反文化与激进政治被好莱坞制作成了文化消费品,成为这一时期好莱坞追崇的时尚。好莱坞反叛电影的引导,促使更多的学生走上了政治或文化反叛之路。但是电影对运动内涵和理念的曲解,对暴力革命的宣扬,对运动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成为流行的时尚,对学生运动的损害也将是致命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最终演化为一幕过程与结局均受新好莱坞随意框定的戏剧。而一旦运动话语过时,好莱坞很快就会调整方向,寻找新的时尚。即便它还关注尚在进程中的运动,也只对其进行解构和批判。
当然,在电影与青年文化政治结成的密切联系中,好莱坞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青年文化政治走向的影响。
反叛青年群体本身的政治文化价值的变动与审美情趣的变化会影响好莱坞电影的受关注度,这无疑给电影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潜在风险。六十年代美国的大学生运动,除了深受媒介的影响之外,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其缺乏持续的动力。作为一场志在革新社会的运动,这场运动却在指导思想的多元与急速切换、行动无序以及多次组织分裂中渐失元气。从自由主义的《休伦港宣言》到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急速转变,运动从未真正出现过统一的指导思想,反叛学生也未在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选择中达成共识。竞争多元的思想,使运动的主题也急速地切换。从民权运动的同盟者、大学的改造者到反征兵反战再到暴力革命者,学生运动主题的变幻无常,使得好莱坞青年叙事的主题也处于急速变化之中。如果说,好莱坞最初的反文化作品还能激起大多数青年的兴趣的话,到了1970年左右,它的激进政治作品要在大多数青年中获得认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比较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运动发展到激进暴力阶段,追随的反叛学生已经越来越少了。1969年,全国性的运动组织SDS解体,而主张依靠工人阶级的进步劳工党逐渐放弃了大学,而信奉黑人革命的所谓“革命的青年运动”已经逐渐走向了恐怖的暴力革命之路,均失去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由此看来,1970年还沉迷在激进政治的好莱坞,事实上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它可能会失去那些已经或正在疏离激进政治的大量学生观众。追逐运动的时尚,同样给好莱坞的文艺复兴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对于激进暴力政治中的反叛者,电影的取悦能否奏效,电影能否成为他们中意的宣传媒介,这也是一个未知的难题。电影与青年之外的观众的对话,在这种情境之下也会变得异常困难。1970年电影的青年叙事,多重困境已经显现了出来。在电影界,这些担心其实早已存在,这是1970年激进政治电影集中推出的关键原因。但是,1970年这些电影的惨败,却是新好莱坞实验者始料不及的。
四、解构建构与运动的衰微(1970-)
1970年新好莱坞推出的以校园革命和青年反叛为主题的电影,虽然切中了学生运动的脉搏,成为春夏全国大学生骚乱的预演,但是几乎全部归于失败。这种结局,看似不合情理,实则在情理之中。
第一,激进政治电影在大学骚乱前后推出,情境与现实的相似性,加深了人们对动荡社会的恐慌。在国家经历动荡不安的十年后,许多美国人已经对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显出了厌倦,渴望安宁。1967年以来喧嚣的、血腥的、程式化的荧幕,遭到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学生和其他年龄层观众的抵制,他们渴望观看到有安全感的电影。
激进政治电影在好莱坞内部、影院业主协会中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些人担心政策是否允许,销售总监们则担心反体制的主题将对开拓海外市场不利。一些公司老板对电影不得不取悦傲慢的、自以为是的青年的状况非常不满(Bodroghkozy,Aniko,2002:38-58)。
出于对票房收入、公众抵制的担心,1970年电影发行时,制片人和导演都有意弱化影片的反叛主题。《草莓宣言》的制片人就声明,这不是关于大学革命而是关于成长的影片,关于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骚乱时期如何渡过认同危机的影片。《青春火花》的导演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也有相似的言论(Bodroghkozy,Aniko,2002:38-58)。制作者们都力图使人相信影片是遵守“安全叙事法则”的,虽有暴力,却是无害的。
为了吸引观众前来观看,影片公司在广告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草莓宣言》被设计成长头发的男主角双膝跪地,保护着一位尖叫的女孩,旁边是骚乱的图景,而画面顶端写着:“他们的梦想是上大学”。《扎布里斯基海角》的广告则是沙漠中男女主角裸体相拥的画面,希望突出青年人的性问题以淡化反叛色彩。
不过,虽然制作者们将电影强拉入一个安全的叙事空间里,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原本的真实意图是无法更改的,因而这些影片遭到广泛的抵制。
第二,好莱坞电影对学生运动叙述的不真实性,引起了激进媒体和大学生的反感。虽然新好莱坞对学生运动、反文化投怀送抱,但仍遭到不少激进学生的非议。激进分子希望这类电影能记录六十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真实状况,电影导演能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
《青春火花》、《草莓宣言》都因其纪实电影的“非纪实性”遭到学生运动的喉舌——地下媒体和大学报纸的攻击。《凤凰》杂志指责《草莓宣言》的导演哈格曼没有对革命、暴力或青年人表明态度,电影只是为了娱乐。而指责《青春火花》从头到尾都只是抗议,不是社会改革的主题。激进学生甚至在各地阻挠《伍德斯托克》的上映(转引自Bodroghkozy,Aniko,2002:38-58)。哈佛大学《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也发表了多个评论员的文章,对《草莓宣言》、《革命者》、《青春火花》等电影进行了批评。有人评论,影片“没有阐释青年文化、校园抗议或者各种各样人们称之的‘革命’”(Vertov,Dziga,1970)。也有人批评影片“把革命简缩成几丝战栗、恐惧、英勇和笑声,目的在使观众在情绪上得到满足”(Crawford,Jim,1970)。
第三,激进政治类电影直接将激进学生的经历搬上荧幕,抹煞了艺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鉴赏性大为下降。这些电影将大学生运动的细节简单地加以改造,就搬上了荧幕。现实政治的简单重演,且电影本身对政治观念的挖掘又不够深入,使其情节失去了悬念、失去了鉴赏性。
总的来说,1970年的革命电影在价值审视、获取商业利润、激进者的期望以及作品的娱乐与艺术性等问题之间,始终难以取得平衡,也无法取得平衡,从而酿就了惨败的结局。
1970年及其后,激进政治与革命为主题的电影逐渐归于沉寂。影片公司及新导演们开始调整创作战略,新的方向主要表现为怀旧与反思。1971年2月,美国娱乐媒体《综艺》指出,“思乡病已经在电影及其它艺术作品中突然出现”(转引自Bodroghkozy,Aniko,2002:38-58)。
好莱坞制作了一系列怀旧类型的电影,如1970年的《爱情故事》、1973年的《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1975年的《龙虎少年队》(Cooley Higll)等电影。这其中,《爱的故事》和《美国风情画》是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两部电影。
《爱情故事》被影评家称为是“复兴时期好莱坞转向保守与传统的先行者”(Bapis,Elaine M.2008:175-176)。它讲述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各类社会运动、越南战争之前)哈佛大学学生奥利弗和詹妮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关于大学生活的影片,与同年发行的其他青年政治电影风格完全不同,它将叙述的时间拉回到50年代末期。在这个时代,哈佛的校园宁静而有诗意,哈佛的学子们勤奋苦读,哈佛的爱情故事既浪漫又感人。纯真的过去给人们带来了怀旧的情感和诱惑,影片让人远离了现实中大学校园的骚乱,与1970年的现实隔离开来。这部电影既是对遥远的50年代的追忆,也在动荡的1970年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这部由派拉蒙公司推出的试探性影片,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创造了巨额的票房收入,成为1970年最受欢迎的两部影片之一。一位评论家认为影片的成功,“不能归功于作家对人物的刻画和塑造,而可能归功于这部小说的梗概,它允许普通的读者去幻想浪漫场景”(Berk,Philip R.1972:52-54)。
1973年上映的《美国风情画》(乔治·卢卡斯导演)轰动整个影坛,是1970年代美国怀旧电影运动的又一经典范例。故事发生在1962年,即总统被刺、越战以及反文化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祥和的小镇。导演将视角集中在四个即将开始新的人生历程的高中毕业生身上,叙述了他们参加晚会的那一夜的奇妙经历:恋爱、摇滚乐和疾驰的跑车,成年人缺席的、欢乐平等的青年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存在方式。成长终须选择,也终有选择。疯狂的夜晚过后,四个青年人重新回归主流生活,或进入大学读书,或工作。同《爱情故事》一样,《美国风情画》也是“一场没有伤痛的记忆”,是为“逃避1970年代早期暴力的社会冲突类电影的策略”(Lev,Peter,2000,Preface)。
反思类电影大致与怀旧电影同时出现,但到1974年前后,怀旧类影片逐渐减少,而反思型电影却大行其道。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危机、水门事件等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扫除了青年人一贯的乐观情绪,加重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保守氛围,也促使美国社会开始对六十年代进行反思。“1974-1976年间,当水门事件、石油危机而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消失之时,‘六十年代的死亡’成为美国电影的突出主题”(Lev,Peter,2000:61-62)。
1970年,电影《乔》(Joe)被认为是较早的一部反思电影。它讲述的是嬉皮士女青年梅丽莎·康普顿的父亲比利枪杀了她的男友,并在憎恨嬉皮士、黑人、同性恋者的工人乔的加盟之后,血洗格林尼治村嬉皮士公社并误杀女儿的故事。在影片中,父与子、主流文化与反文化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作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代表,比利和乔的行为表明“沉默的大多数”的愤怒和反击。
在《乔》中,“诺曼·韦克斯勒(Norman Wexler)的小说很明显的意图,是通过提供青年人被害、中年人的残忍报复以及嬉皮士生活方式的荒淫实验等场景,让观众们自己决定站在代际冲突的哪一边”(Andrews,Nigel,1971:75-76)。但是,这部发行于1970年那个特殊年份的电影,意想不到地被保守观众和持温和观点的观众视为知音,“迎合了保守观众对嬉皮士、黑人、毒品交易的畏惧心理,也迎合了温和观众反对堕落和无序的心理”(Lev,Peter,2000:24-25)。
《乔》的成功,促成了一系列反思类电影的出台。新好莱坞先后推出了《唐人街》(Chinatown,1974)、《纳什维尔》(Nashville,1975)、《香波》(Shampoo,1975)和《飞越疯人院》等影片。⑥这些影片无一不在描述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失落,无一不对六十年代的精神价值提出质疑。电影的这一新方向,伴随着美国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日益保守,使得新好莱坞逐渐回到体制内运作。
反观1970年及其后新好莱坞的电影,其对学生运动退潮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1970年之后好莱坞青年电影制作已经迅速远离了“激进政治、暴力和革命”的叙述主题,青年叙事已经发生了逆转。
在新的电影叙事中,新好莱坞开始为观众打造“安全的叙事空间”,同时也开始走向皈依主流价值观的路途,“制片人无助地去取悦观众,却都被票房收入的微小数字困惑了,现在,他们开始期望制作安全的娱乐产品,制作道德纯正的电影了”(Farber,Stephen,1970-1971:24-33)。
《爱情故事》、《美国风情画》等影片,将视角拉回到混乱的六十年代之前,在静谧、祥和的空间里展开叙述。这中间,青年有叛逆行为,但它只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是离经叛道。在《乔》中,暴力的使用被看作是“沉默的大多数”保护他们的自由、恢复美国和平与安宁必要的手段。
新好莱坞电影推动学生运动走向暴力、并将学生运动框定为暴力政治之后,又迅速转移了对该运动的关注,转向完全相反的“安全叙事”导向。这一突然的转向,对已经与之形成依赖的学生运动及参与者的打击无疑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作为“暴力叙事”的学生激进政治,已经成为过时的时尚。由于远离了普通青年的视界,通过电影等媒介的宣传效应来征募新会员已经变得不可行了。对于老成员来说,当电影等媒介不再记录他们的历史时,创造历史的激情也会随之消散。1970年秋季之后,从SDS分离出来的各类组织,已经失去了凝聚力,面临人员严重流失的困境。大一新生只关注学业成绩,对政治兴趣降低,无法征募新成员,而很多激进者退出大学,步入主流社会。
另一方面,“安全叙事”实质上是对新好莱坞前一时期盲目追逐青年时尚的否定,也是对现实学生激进政治的合法性的否定。这样,新好莱坞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反意识形态化,既压缩了运动的扩展空间,又造成了运动合法性的消失,使学生运动的衰落与新好莱坞的转向相伴而行。1971年前后,美国人发现作为革命基地的大学已经恢复了平静。
其次,怀旧型与反思型两种类型的电影,都对运动的价值和理念进行了或明示或隐喻的批评,推动了大学生的价值观转向。
怀旧类电影回避了1960年代的各种冲突,以更早时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作为叙事的起点,精心描绘青年人浪漫的年华、纯真的情感与成长的烦恼,这与混乱的六十年代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对许多人来说,50年代象征着幸福和单纯的黄金时代——一个未受骚乱、种族暴力、越战、水门事件和暗杀扰乱的时代。人们已经对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创伤感到麻木了,他们期待一个更安宁、更幸福的时期”(Hurup,Elsebeth,1996:136-139)。新好莱坞的导演敏锐地捕捉到了电影观众对“暴力叙事”的反感,走上迎合美国人新观感之路。
毫无疑问地,规避现实,尤其是完全与现实相反的叙事本身,就是对运动价值和观念的回避和批评。好莱坞警示那些运动的坚持者,暴力的手段、颠覆的行为是不受欢迎的,也是新好莱坞已经主动抛弃的时尚。同时,它也向不曾参与运动的新生代传递讯息,应该平静地享受生活。在《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非常个人化,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政治事件都与之无关。而《美国风情画》再次强化了好莱坞对学生运动的新态度,即疏离和训诫。疏离,即远离对好莱坞商业有害的激进化的反叛风格。训诫,即以怀旧的叙事,浪漫情节的铺排,教育和启示尚迷离在运动中的人们,回归主流社会才是前途。
反思型电影对运动的价值和理念的批评则更直接、更明确。在《乔》中,以往被视为前卫、新社会生活象征的嬉皮士生活方式,被正统秩序的恢复者乔和比利视为堕落的、腐朽的、不能原谅的。电影《纳什维尔》中,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无我”和“利他”。嬉皮士、摇滚歌手等都声称热爱政治,而实际关心的只是利益。青年的自私与短视,使“观者在反文化的视域中不能找到与主流文化不同的那种舒适感”(Lev,Peter,2000:65-66)。
两类电影都对青年价值观的转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60年代,支撑学生热情参与运动的是从休伦港宣言中延伸出来的新价值观——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1970年之后,这种新价值观逐渐脱离了国家、社会导向,走向了自我主义,它考虑的是“我”而非“我们”。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整个70年代被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等社会学家称为“自恋”的十年——自恋、自私、个人意识而非政治意识的时期。在自恋主义的价值观下,运动的平息也在情理之中了。
好莱坞回归安全叙事与体制内叙事的原则,在推动学生运动的平息和对反文化的深层反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无论在反思型还是怀旧型电影中,青年人仍占据荧幕的中心位置。热情澎湃的60年代青年是被批判者,50年代传统青年是新宠,无论如何,好莱坞仍然选择与青年有关的叙事,作为其转型的基础。青年人不离经叛道的反叛仍被支持,如《美国风情画》中青年的欢乐追逐,《爱情故事》中男主人公对资本家父亲的反感等等。可以说,在新好莱坞时期,运动给电影烙上的“青年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在好莱坞其后十几年的发展中,创作青年人喜爱的电影、争取青年观众仍是其最重要的发展策略,而怎样满足而非追随青年的文化价值需求,如何在变动的社会中寻找到非青年观众的价值与审美标准,使电影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需要,成为好莱坞发展的新思路。
五、结语
在美国青年力量占据强有力地位的六十年代,好莱坞与大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一度结缘。这种紧密联系给好莱坞和大学生运动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走进青年世界,使好莱坞从行业危机中走出,进入新好莱坞时期,重新焕发生机。而过度追随变动无序的学生运动,特别是深陷激进政治及暴力革命叙事,却使好莱坞一度面临极大的风险。在遭受惨败之后,好莱坞走向体制内叙事,但是运动为其烙上的“青年印记”仍是无法消除的。
对于大学生运动来说,好莱坞电影对于建构和解构运动的合法性、青年新伦理价值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好莱坞以青年文化、学生政治为电影创作主题,这对美国大学生运动的快速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电影对运动的追随,也造成了运动泛化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同时,电影把运动简单地等同于“暴力反抗”、“与体制的对抗”,使运动限于特定的形象定制之中,存在于“暴力叙事的空间”之内。这对运动日后的发展极为不利。
1970年及其后,电影制作重新回归“安全叙事”、远离激进政治和暴力革命。好莱坞通过怀旧和反思类电影,对原来所追捧的青年价值进行批判,将美国大学生激进政治及反文化置于质疑和诋毁氛围之中。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的退潮。
注释:
①The Sixties在西方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历史内涵的词汇,它代表一个特定的时代。从时间上来看,它以5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兴起为起点,以70年代初黄金时代终结、各种社会运动衰退为标志,时间跨越三个年代,不再是通常意义的年代界限。国内学者具体表述不一,有的翻译为60年代,有的则为20世纪60年代。笔者认为,用“六十年代”这个表述更为妥当,因为它不仅能够突出特殊的年代涵义,还能与通常意义的年代表述相区别。
②亦称“生育高峰一代”,指出生于1946-1964年的一代,数量约7600万。
③六十年代,学生激进分子对大学的知识与教育的非关联性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他们所要求的关联性主要是,一是个人内心体验相关,二是社会现实相关,能疏解社会问题。激进学生对电影的要求也相似,一家大学报纸称,“电影如果不能使观众参与其中,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失败了”(参见Bapis,Elaine M.2008:32)。
④苏珊·桑塔格语,转引自彼得·比斯金著:《逍遥骑士,愤怒的公牛——新好莱坞的内幕》,引言第7页。
⑤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ld/Zabriskie-Point-(film)。
⑥对学生激进政治、新左派运动和反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这类电影,源源不断,一直持续到80年代前中期,如1977年的Between the Lines,1979年的The Return of the Secaucus Seven,1983年的The Big Chill等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