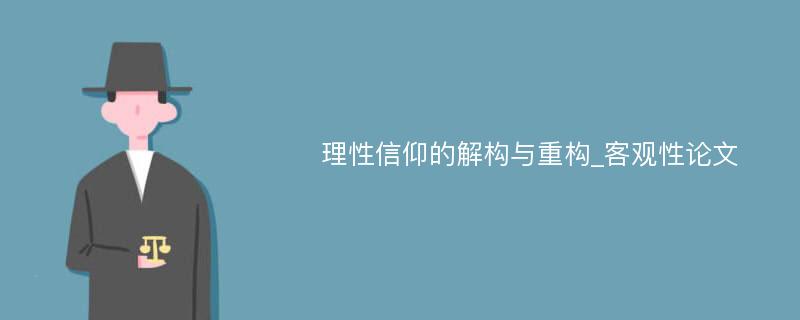
理性信念的解构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念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类理智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和发展,才露出了文明之光。人类有高于其他动物的智慧灵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被无知的黑暗所遮蔽。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有文字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文字的出现为人类积累知识和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然而,文字的出现,理性能力的提高,文化信念的内化,并不是只伴随着真理、智慧、正义和宽容精神的传播,有时,人类恰恰借助于新的能力去从事前所未有的恶。动物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同类做牺牲,去敬拜神灵。可是,许多有了宗教文明的早期人类,为了博得神灵的欢心,把自己的同类像牲口一样宰杀,把他们的首级或心脏当作祭品。实际上,我们不必为阿兹特克人的野蛮感到过于震惊,当前世界上存在的种族灭绝与仇杀行为,其野蛮性与古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20世纪末,某些自诩“文明世界的领袖”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理念的正确,为了自由的战略利益,而用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攻击别的主权国家,屠杀其他民族的平民。由此可见,人类理智能力的提高与人类文明自身的和谐发展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它们时常处于矛盾关系之中。
人类理性的发展或理智能力的提高,在为人们带来便利和福祉时,也往往给原有的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因此,从老子开始,人们就时常思考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卢梭甚至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人类道德的堕落。老子云:“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注:《老子·章三》。)卢梭则说:“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加任何东西”,反而“败坏我们的风尚”,“玷污了我们趣味的纯洁性”(注: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5页。)。老子和卢梭等人所代表的观点,是对只看到理智进步积极面的朴素观点的反动,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他们迫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但是,与对理智发展的朴素肯定论一样,老子和卢梭等人都没有认识到,人类理性发展同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样,都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
二
作为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首先,人类的理性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在现实中,理性都是单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情景中处理具体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人类思维和行为特征,整体的人类社会并没有进行任何理性思考,理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通过具体个人的大脑和感性活动呈现出来的。因此,一方面,任何理性思维过程和理性知识都只能是具体的并且带有特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化的产物,理性活动及其产物——知识——都有突破特殊情景和特殊形式的要求。合乎理性的思维和合乎理智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共识为基础并通过舍弃纷纭多样的特殊性而趋向普遍性。
其次,在存在的结构上,理性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一方面,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特征,人类理智连同理性知识都必须反映和适应客观世界。在此,人类理性有客观的性质,它与狂想与臆测不同。另一方面,作为人们把握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手段,理性采取的是某种主观的形式。因此,理性必然带有主观的成分。理性的客观性必须通过其主观性才能逐渐呈现出来,因为人类知识的客观性有赖于历史上人们的想象力和大胆的探索。
再次,人类理性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时,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活动中展现出的思维和行为特征。因此,它既有为自己的需要或意图而规定的一面,又有受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的限制并由这些规律所规定的一面。前者是理性的价值规定的方面,后者是理性的逻辑规定的方面。逻辑规定决定着理性活动和知识在观念体系上是否连贯,观念是否能够恰当地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定却支配着人们理智活动的方向和动力。这两种规定常常保持着某种张力。
又次,人类理性本来是对非理性的超越,正是人类的有意识的活动终结了自然的无意识的发展。正因如此,理性与非理性也就没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人类理性以自然界的漫长演化为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类理智和理性知识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理性的发展决不意味着非理性(意志、潜意识、直观、热情、冲动、想象力,等等)功能的减退,相反,理性时刻离不开非理性功能的支撑,有时理智持久的劳作能够培养出更稳定、更可靠的非理性功能来,譬如,科学家的直观能力就绝非一般人所能比。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设想,在人的精神结构中,理性功能与非理性功能也许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的面而已。
最后,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所表现出的思维和行为特征,理性的基础就在社会历史之中,因而它必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但是理性在形式上却超越现有事物和当前范围的限制,试图使事物按照人的愿望朝“应当”的方向发展,因此理性又天然地具有理想性。一方面,在其起源或生成方式上,理性都是特定历史境遇的产物,都是针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事物提出的某种工作思路。但是,另一方面,就其形态而言,理性是对事物的合理化理解和普遍性解释,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举理性的“火把”去探索黑暗的无知区域,因此在“形式上”理性必然具有超历史和超现实的特点。这就是说,理性作为历史和现实的“儿女”,也就以希望的形式代表历史和现实的未来。
三
理性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理性由事实规定和由价值需要规定的对立统一,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理性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理想性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人类理智能力的发展和理性信念的确立必须走一条不断自我摧毁和自我重构的道路。
人类的任何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在最终的意义上都只能是特殊的东西,但它们在形式上都表现为普遍性的东西。既然理性是对人类历史和现实活动的合理化把握,那么它就必然趋向于超越现实特殊性所设立的限制,使其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普遍性。实际上,理性内容的特殊性和形式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正好构成理性发展的逻辑动力。理性是对特殊性和有限性的不断超越,所以它应当是不断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改变自身和丰富自身的;但是,理性知识一旦建立起来,就要求相对的稳定性,要求形式复杂的特殊性适应自己的“普遍”形式。因此,在本性上说,理性就是既要求稳定又要求变动的。如果只注意理性的普遍性,看不到现存理性形式的暂时性,那么理性就会逐渐蜕变为僵死的观念形式,并且因为不能把握和综合新的材料而对实际生活失去指导意义;如果只关注理性的特殊性,看不到理性追求合理化进程所伴随的超越性,那么理性就会转变成为狭隘的见解或意见。由此可见,在关注理性的特殊性和暂时性时,我们就要不断地拆解、解构和摧毁它,以适应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在考虑理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时,我们就必须随时构造它的形式,以使它有一个能够呈现的存在形态。
人的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如果不能反映或适应客观世界及其规律,那它们只能算是纯粹的主观臆测和梦呓。但是,如果把任何暂时的理性形态都视为客观的,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理性活动和理性知识自身存在的主观性因素。我们的理智能力和知识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它们也不会成为完全的客观性,更变不成客观事物本身。既然主观性是理性活动和理性知识的“客观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考虑它们的主观性,才算尊重了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的“客观性”。既然主观性是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的存在要素,因此,如果忽视它们的主观性,那就造成了双重的主观性。实际上,理性起源和内容的客观性与理性存在形式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什么坏事,这种矛盾也是理性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从根源上说,没有主观意识就根本没有人类理智活动,那也就根本谈不上理性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的主观活动(想象、直观、潜意识,等等)恰好是推动理智积极理解和把握客观世界的动力和形式。没有牛顿的执着热情就不可能有万有引力的发现,没有凯库勒(August Kekule)丰富的想象力就不可能有苯分子结构的发现。再说,任何认识活动都有观念形态的因素起作用,因此所有理智活动都有主观的创造性成分羼杂其中。正因如此,列宁才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页。)显然,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客观现实”。这种现实也促使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构已有的理性形式,以通过进一步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反映、理解和表述更多的客观内容,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接近于客观真理。如果我们停留在当前的有限的客观性上,认为我们当前的理性知识就已经是客观真理,那么我们反而会放弃更多的客观性,走向主观性甚至主观主义,因为不仅客观世界在运动发展,而且人类理智能力和认识能力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认识只能是无限地接近于客观现实,但永远达不到绝对的客观性,现存理性方法和知识只有一部分客观真理的成分;部分的客观真理不是客观真理的全部,也不是客观真理的全过程。如果我们只相信我们的主观性,那么我们当然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并因此而失去了进一步探索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也就是丧失了我们的主观性。我们必须不断地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解构我们现存的理性形式,并重建新的理性形式,才能推动我们的理性认识不断深入。
理性活动既受理智形式和逻辑规律的规定,也受人们的价值取向的规定。这两种规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同样是推动理智活动和理性认识不断深入的动力。一方面,客观的逻辑规定未必完全服从人们的所有需要,为了使它们为人们的价值目标服务,人们不得不对客观逻辑进行创造性操作。比如,水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泛滥的洪水却是致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水利设施控制洪水。另一方面,人们的需要一旦固定为价值目标,往往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取向,这种取向常常忽视周围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本身的逻辑规定。比如,在近代初期,当理性认识能力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守旧势力仍然维持旧的价值观(宗教的和封建的),从而与理性自身的逻辑发生尖锐的矛盾,理性的纯理智或逻辑的层面逐渐获得胜利,以致到现在人们又在担心完全摆脱了价值理念制约的理智主义。从历史上看,理性活动的纯理智层面和价值取向层面经常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当人们从旧的价值目标转向新的价值目标时,需要对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提出新的要求,对其进行新的操作;当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的逻辑已经揭示我们的某些需要不合理时,我们就应当对我们的价值目标进行某些修正。勿庸讳言,当前全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需要,修正我们的价值目标;同时,我们也要使我们的理智活动和理性知识的客观逻辑,重新纳入到我们的长远目标之中,为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服务,不能使工具理性失去价值理性的约束。
在人的行为活动和精神活动之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同样是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动力,并且促使理性不断自我解构和自我重建。在人类理智发展的童年,幼稚的理性首先把自己的根基和功能几乎全部归功于神灵。当人类理性逐渐成熟起来时,它开始怀疑神灵的作用了,人们开始探讨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自主性问题。这种怀疑和探索就汇成理性启蒙的运动。在启蒙精神的推动下,近代理性主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与自然科学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使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面貌大为改观。但是,理性主义却变得片面化了,它愈来愈仇视非理性,排斥非理性(如情感、意志、幻想,等等),看不到非理性因素与理性之间相互补充的一面,结果是不能全面地审视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非理性主义趁机抓住这个问题,力图取代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动摇人们的理性信念。这种情境就为我们提出了重建理性信念的任务。然而,如果在近代初期我们是因为理性得不到应有的地位而构建理性信念的话,那么,人类到了20世纪末,我们却要为了把非理性因素整合进人的存在结构中而重建理性信念。如果我们不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解释非理性因素和功能,并且给予它们一定地位,那么非理性主义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泛滥。法轮功事件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需要更为重视的是,理性的理想性与历史性及现实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促使人们必须不断随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变化而重建我们的理性形式。我们知道,理性有从理想出发而设定的一面。然而,虽然理想是对现实的观念性超越,但是观念本身有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一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想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超越。正因理想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理想才不是纯粹的空想,才是可以实现的展望。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运动都是人类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可是,理想一旦实现就不再成其为理想,我们必须提出新的理想。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实活动的改变,我们必须不断重建我们的理性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