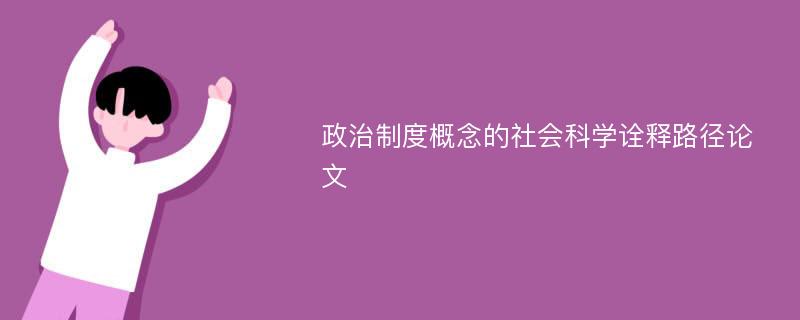
·政治发展研究·
政治制度概念的社会科学诠释路径
[法]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
(欧洲大学研究院 政治与社会科学系,佛罗伦萨)
马雪松,王 慧编译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制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相比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制度内涵的重视,政治学较少对制度概念进行清晰阐释,更缺乏对制度化概念的系统研究。基于多学科比较视野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学聚焦制度的规则向度,社会学关注制度的组织及程序向度,政治学则认为制度关乎整个共同体的维系和演化。政治学语境下的制度概念具体表现为组织,其对程序和规则发挥必要的支持功能。政治学比其他学科要重视制度化研究,不仅强调制度的内部因素,而且主张制度化经由建设性环节才得以实现。政治学应当将更多制度外部的支持性因素纳入制度化分析,同时以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视角探讨制度及制度化概念,这也为揭示社会科学不同分析路径之间的关键差异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键词: 制度;制度化;政治制度;概念界定;政治科学;社会科学
一、引 言
在政治学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制度作为推进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始终被视为政治研究的枢纽和要津。由于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激烈冲击,政治学的制度研究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间日渐衰落。20世纪80年代,马奇(James March)与欧森(Johan Olsen)在新制度主义浪潮中重申制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制度研究自那时起步入复苏,由理性选择理论所孕育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是备受瞩目。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度研究的式微境遇实际上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政党、议会及政府一类的制度不仅仍是单一国家及比较政治研究的典型分析框架,而且在当时蔚成风气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模型中,展现中性色彩的结构概念其实与制度概念并无实质区别。
政治学的制度研究再度复兴,但致力于“清晰阐释”制度概念的工作却极其罕见。政治学者看似不太介意制度概念的模糊性,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则对阐释制度的确切含义富于热忱。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制度的定义往往更加丰富,社会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制度的经典定义,认为制度是“社会结构要求人们按照脚本饰演角色时,规定其合理预期行为的深层模式”[1]。半个世纪后,斯科特(W. Richard Scott)对制度作了更为详尽的界定,主张“制度包括认知性、规范性和规制性的结构与活动,并为社会行动赋予稳定性和意义性”[2]33。这两种观点当然不是确定无疑和详尽无遗的,举例而言,斯科特虽然重视“认知性、规范性和规制性”的结构维度,却忽略了制度的活动(activities)层面。如果将上述社会学定义应用于政治学领域,制度概念必然会牵涉更多内容且引发更大争议。
(4)浓厚绿色金融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由于绿色发展项目普遍存在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长、收益不确定、风险高等特点,影响了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政府应加大绿色金融的宣传力度,树立并推行节约、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绿色信贷理念,重视金融机构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企业、社会群众参与到绿色金融中来,使金融机构和社会团体资金更多的投向绿色环保产业。
白酒感官品评方法参考GB/T 33404—2016《白酒感官品评导则》、GB/T 33405—2016《白酒感官品评术语》。
政治学语境下的制度概念有待澄清,“二战”后颇为流行的“制度化”术语也充斥不少疑义。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制度化宽泛地界定为“组织及程序获得价值与稳定的过程”,认为制度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四种特征。这一定义促使人们细致考察制度的演进过程,但又因为仅涉及“程序”却对“活动”只字未提而略显狭隘。亨廷顿关注制度化得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但被他忽视的时间因素同样是重要的自变量,而且预示了制度必将走向式微[3]12-14。制度不会仅凭自身而发挥某项功能,其效力大小既取决于行动者如何运用制度的内在特点,还取决于社会这类外部因素对制度的反应;至少在政治领域,制度的强劲程度同外界的支持性因素表里相依。制度化研究需要与制度概念研究携手共进,后者犹如一把钥匙,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为何以及如何被设计出来以妥善解决相关难题。学者目前对上述重要问题的思考不免失于粗浅,系统审视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政治学比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更关注制度化问题,亨廷顿对此投入心力尤多,他认为制度是“获得价值和稳定的组织与程序”,人们可据此推断制度化具有随时间而演进的特征。制度并不是从其确立那一刻起就自动获得“价值与稳定”,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1962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论文为上述观点提供了经验层面的佐证,他以详尽的资料表明众议院选区在美国共和制发展过程中竞争力愈益提升[17]。六年以后,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制度化需要时间进程提供的纵深背景。
二、多学科比较视野下的制度概念
制度研究在政治学中长期存在非问题导向的特征,表现为政治学者很少关注政治制度的构成要素。行为主义革命发端前的政治制度分析多在经验层面上进行,大学设立的“政治制度系”相比于政治哲学研究更重视政治现实研究。“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制度这一术语较少出现在学术著作的索引当中,如芬纳(Samuel Finer)的《统治史》,在这部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鸿篇巨制中,索引甚至不见制度一词。萨托利(Giovani Sartori)在1980年出版了《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解析》,虽然他志在廓清社会科学的关键概念,但制度在书末索引乃至全书上下都付之阙如。凭此猜测,萨托利或许认为制度概念无须加以界定。
制度与制度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在基本概念和内在逻辑上密切关联,但也存在引人深思的诸多问题: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安排”究竟是水到渠成或一蹴而就地成为制度,还是时过境迁后再成为制度?是否存在制度化的周期?制度化周期内的某些安排是否比其他安排具有更多或更少的制度色彩?制度化周期内同样的安排是否随时间的不同而展示出更多或更少的制度色彩?
行为主义对待制度的消极态度广为人知,这种态度与其说是一种“印象不佳”的倾向,倒不如说是一种“理应如此”的立场。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在1953年出版,该书索引中有不少词汇与制度相关,虽然书中在讨论白芝浩(Walter Bagehot)与布赖斯(James Bryce)时对制度概念不着一墨,但仍有理由确信伊斯顿认为白芝浩与布赖斯谈及的政治实体就是制度。行为主义虽未否定制度的作用,但由于阿尔蒙德把内涵更为广泛的结构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人们不得不审视制度和结构之间可能的差异。这或许表明,制度概念引发争议的根源,恰恰在于制度含义未经充分清理便仓促容纳了新的要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未有人前瞻性地提出罗斯坦(Bo Rothstein)发表于1996年的观点:“无论政治学者讲述何种故事,它都必然与制度相关;政治学的一项核心议题是,现实生活不过是制度随时空变化而呈现的各式变体”[7]134-135。劳森(Kay Lawson)在1985年出版的《人类政体》中首次清晰触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制度作为一套结构,以明确界定的规则履行既定的重要功能,并运用这些规则对人际关系进行调节”[8]。
马奇与欧森于1989年出版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为上述争议打上新制度主义的烙印,1984年他们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则是该书观点的雏形。这本著作影响深远,可是他们对制度的阐释即使不算惜字如金,也因言辞过于简略而造成理解上的晦涩不明。马奇与欧森的开卷语犹如阿尔蒙德与科尔曼十年前观点的回声,“诸如此类”这样的字眼再次取代了概念界定:“就大多数当代政治理论而言,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等传统政治制度,与企业一类的传统经济制度同命相连,正在从显赫位置上落寞退场”[9]。该书第一章旨在分析“政治生活的制度视角”,并提出“本书余下章节将探讨政治领域的制度,尤其关注行政制度如何为政治生活赋予秩序并影响变迁”[10]。然而,马奇与欧森同此前学者如出一辙,既没有给出制度的定义,更未将制度同其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要素进行区分。
至于收获,则是一位梦幻般的女子出现在了画家的生活当中,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埃莉诺·希达尔。罗塞蒂惊异于她天使般的容貌与冰清玉洁的气质,将其视作自己的比阿特丽丝,并将她陆续幻化成众多浸沐在中世纪圣洁光辉下的女性。罗塞蒂的奇特在于其从身到心都沉浸在了艺术中,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将生活和梦幻彼此分开,故而他对希达尔倾注的爱也异常奇特:他将心中的“利兹”(罗塞蒂对希达尔的昵称)完全地理想化了,圣灵化了。而这位恋人的顺从也使她像极了皮革马利翁雕刻的加拉太。如此,他们的爱情竟罩上了一层超世俗的、唯灵的色彩。这两件事情共同催化,遂使罗塞蒂的画风一意朝着现实的反方向前行,终于彻底走进了神秘的诗性境界。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度界定才被列入研究议程,古丁(Robert Goodin)率先关注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制度的角色。兰恩(Erik Lane)与厄森(Svante Ersson)在2000年出版了《新制度政治学——偏好与后果》,以政治学者的身份对制度概念进行全面界定。值得考虑的是,兰恩与厄森在1999年出版《西欧政治与社会》第四版时还恪守略显陈旧的立场,虽然指出“本书关注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种形式和根源,并考察其产生的政治后果,据此勾勒出全书内容的逻辑轮廓”[11],但两位作者无意对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予以界定。相隔仅一年,《新制度政治学》摒弃了马奇与欧森式的非问题导向的纲要风格,而是用整章篇幅讨论“什么是制度”并提出“制度的模糊性”,在将社会学制度主义描述为整体性制度研究路径的同时,还探讨其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野。这显示了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但兰恩与厄森似乎没有让制度概念与政治学语境产生“共振”[12]。本文认为,只有对多个学科在制度议题上的不同见解作出全面考察,特别是说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制度为何有别于经济学与社会学,才能理解这种“共振”。
古丁1996年编著的《制度设计理论》,或许是探究各式制度主义类属问题的先声。“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有悠久的制度主义传统,并在近期复苏中展示出若干新的变化,新制度主义在各自学科背景下呈递出不同的含义”。通过审视各具特色的制度范畴,古丁认为 “制度概念通过学科内部及学科之间广泛的多样性才得以建构,学术传统在概念界定中呈现不同倾向,概念界定则按某种方式‘内在于’各自实践”。对制度含义及运作方式作出“外在”说明之后,古丁接受了亨廷顿对制度关键特征的概括,同样相信“社会制度无非是稳定、有价值且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13]2-21。
政治生活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旦工会、雇主或非政府组织之类的“社会组织”试图把自身观点强加于非雇员身上,这种差异便体现出来。当“外部支持者”一类因素影响组织的维系时,人们可能不会继续遵守组织规则,制度化也难以水到渠成般地顺势就位。因此,制度化经由建造环节才可实现。这也解释了制度化为何是政治学分析的重要概念,但是政治学者在重视制度化概念的同时,却从未系统探讨制度化的基础及动力问题。
仅从制度内部问题这一视角看待制度化的学者,并非只有亨廷顿一人。近三十年,古丁及其合作者在《制度设计理论》中同样以内部视角进行审视,提出制度变迁的意外方式、演化方式与设计方式。就第三种情况而言,能动者可以针对政策、机制和体系开发出多种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恰好对应制度为克服“去制度化”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古丁揭示了制度不再履行相应功能时便会出现“去制度化”,但没有深入思考以往履行相应功能的制度何以不再如此。
不同学科在制度问题上的歧异见解是否应加以弥合,当前各方仍然各执一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三个学科缺少聚焦点,因此制度概念的界定难以形成共识。正如古丁所言,经济学致力于克服个体选择这一难题,所以尤为重视规则要素。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体既是理性能动者,也在经济生活中作出机械式反应,因而除非有规则决定个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否则不能期望个体实现自身目标。制度不能停留于规则层面,集体安排对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同样至关紧要。在给《民主思想百科全书》撰写的“制度设计”词条中,奥菲(Claus Offe)指出“构成制度的规则和行为惯例不仅在实际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而且要得到第三方的认可、验证和期许;对某些更为重要的制度来说,精巧复杂的规范理论、组织章程与鲜活创意与之相伴相生”[15]。此外,社会分析应聚焦个体选择活动以及个体所属集团施加的压力,斯科特在此意义上同时强调组织与程序的关键作用。
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使政治学的制度概念有别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可否认,作为决策制定过程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存在相似之处,但政治中的决策制定发生在共同体或“系统”之间,无论共同体成员是否参与决策、作出决定或表示同意,政治决策都同他们休戚相关。基于这一原因,伊斯顿在《政治体系》中阐明政治必须是“权威性”的决策过程[16],并由此得出两点重要推论。其一,政治生活的选择活动很少由个体作出,一些人尽管可以像放弃自身协会成员资格那样退出所属共同体,可是退出国家生活则无比困难的。其二,许多政治问题涉及未参与决策过程的人,但传统经济学甚至大部分社会学者对此缺少关注。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不仅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之间划下畛域,而且有利于人们理解制度的含义。不无遗憾的是,虽然罗斯坦区分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但他并未进一步作出详实说明[7]144-149。
三、制度与政治:以组织与组织中的程序为例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大致理解,为何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界定制度时,总是强调组织而非程序或规则。就政治生活而言,规则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虽是制度过程的一部分,但当政治规则与政治程序加之于没有参与决策过程的大规模人群时,它们只能通过组织发挥作用。如此一来,规则和程序要想获得承认,就必须被自身“权威”已获认可的组织赋予其合法性。就经济生活而言,权威力量的加持也十分必要,因此经济学者宣称国家必须强制实施经济领域所要求的规则,但他们又不时以某种优越心态和冷漠姿态对待政治,仿佛“政治只是做其分内之事”。诺思显得更为宽宏大度,他注意到“政治规则通常以适当方式催生经济规则,不过两者的因果关系却是双向的”[14]48。政治规则与社会规则的关系与之类似,但也常有例外。社会组织的规模通常较小而且看起来运行自如,只要不发生严重冲突便不会寻求国家权威的介入。只有政治领域才会诉诸持续而普遍的权威,组织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无论规则与程序多么重要,都必须得到组织的庇护与扶持。因此,在政治学语境下,制度主要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既包括政治色彩彻头彻尾的立法机关或政党组织,还包括政治色彩并不贯彻始终的其他团体。行为主义将政治过程中的社会实体引入政治学视野并无过错,但这些实体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是兼具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特性,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同样如此。
可以看出,制度的定义不能一概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因为它可能为了迎合众人口味而简化得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在政治学语境下探寻制度的定义,必须瞄准能作出权威性决策的一类实体,它们所处的位置使其通过程序与规则而能够采取实际措施,这些程序与规则也正是组织的“左膀右臂”。在政治学语境下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唯有如此才可能解决政治制度的主要难题。这个难题就是,长久以来制度都被视为清晰可辨的,但在涉及组织以及组织决策的表达方式问题时仍存在不确定性。
四、制度化及其在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早在行为主义崭露头角以前,政治研究就已超越政治制度研究的传统风格,尤其是当政治集团理论扩展至社会领域之际,许多学者以温和的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治制度的见解。例如,杜鲁门(David Truman)在1962年出版的《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中指出,“制度含义的模糊性令人难以准确判定哪些集团可被看作制度”[4]。还有学者以不算直截了当和审慎周密的方式,质疑集团一类的实体是否如同党派或议会那样也属于制度。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1960年合作完成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依据利益表达功能而将政治集团划分为制度化利益集团、群聚式集团、非群聚式集团与失范化集团。不过,阿尔蒙德与科尔曼无意于界定制度化利益集团,而是止步于“考虑发生在议会、行政机构、军队、官僚、教会等诸如此类组织中的现象”,并用寥寥数语指出“为了不再被制度一词引入正式规范分析的歧途,本书主张使用结构这一概念”[5]。时隔数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Bingham Powell)在196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再度轻描淡写地提出,“现代政治体系存在不少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正式性及制度性通道”,并认为党派、议会、官僚与内阁亦在此列[6]。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前述议题,致力于更好地界定制度概念并揭示制度要素,进而阐释制度化得以强化或弱化的方式。循此思路,第二、第三部分主要探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聚讼不已的一项难题,即制度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组织范畴与程序范畴提供容身之所;第四、第五部分的分析焦点是制度化,旨在考察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制度化存在哪些显著差异。
政治学不仅对制度性质的看法有别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且在制度化问题上同样持有独到的见解,但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经济学和社会学认为,相关安排可以即刻成为制度。重视制度变迁的诺思也未曾提到制度化,但他认为“制度的渐进变迁”以缓慢累积的方式发生,“而非一种不连续的形式”[14]6。相比特定经济案例中的“规则”如何获得“价值和稳定”,诺思更关心产权如何在不同社会中的转变。引申来看,在阐释制度及其作用时,许多经济学者如同诺思一般并不关切制度如何发展,而更在意新规则如何取代旧规则。
考虑到经济学者只将制度视为规则,那么他们否认这些规则的实现路径是“演化式”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社会学者如果也持这种观点则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同时关注组织和规则,所以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几乎只能是“演化式”的。斯科特将制度化术语置于自己著作的索引当中,但他对时间作用的理解迥异于政治学者,更未能为其赋予重要地位。斯科特借鉴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观点,提出“相比那些目标分散且技术薄弱的组织,精确界定或技术成熟的组织更少受制于制度化的影响”[2]19。此后,他又觉察到组织正式目标与真实目标的差异,以及权力所发挥的作用。斯科特还受到斯廷施凯姆(Arthur Stinchcombe)的启发,赞同制度是“权势者推行某些价值或利益结构”的副产品,强调“手握权柄者如能把持权力,这些价值和利益便得到保护”。通过引证朱克尔(Lynne Zucker)的实验研究,斯科特指出制度化可被操纵,它不是随时间推移而自动获致的某种结果,而是制度在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呈现的一种状态,这些条件或多或少可被随意安插布置[2]83。
斯科特所审视的社会组织事例明显无法适用于政治领域,这是因为他只关心组织成员的境况,而不去留意组织对其他人员可能施加的影响。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分析思路有其合理性,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或企业的研究,无须顾及组织以外的决策活动。就组织内部的行动者而言,制度化的组织要求受雇者必须遵守规则,循规蹈矩的好处不仅在于规避可能的惩罚,还体现在规则的制度化可以让人们有章可循并同气相求。
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大省,以叶菜类生产为主,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本省蔬菜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50%左右,其生长周期短,复种指数高[1]。广东省热带、亚热带的气候特点为农作物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光、热及水资源,因此在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该地区的叶菜田通常连作,1年内种植多茬[2]。
《钴鉧潭西小丘记》被收录于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之一。通常的教学只关注到作者通过“贺小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却往往忽视了文章本身的“美”。本文单纯从审美的角度来透析文本。
五、“外部”因素在政治制度的制度化中的作用
《制度设计理论》收录了奥菲执笔的“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设计”,这篇文章清晰表明“整个政体”(the polity at large)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奥菲在以“挑战、崩溃与求生反应”为题的一节中提出,“制度可能在回应如下三种挑战时发生崩溃:其一,制度无法成功灌输那些影响成员忠诚度的规范与偏好;其二,制度在满足相关需求及承载相关功能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替代因素的出现而被打破;其三,制度在履行其应尽职能时出现明显失败”[13]31-33。以上情形都是制度的内部问题,但制度的外部因素在这三种挑战中均可构成重要诱因,比如此前依赖制度或信任政府的人们,由于某些原因对制度及其代理人失去信心。奥菲所说的第一种情形是基于制度及其代理人视角的分析,他并没有认真考虑整个政体中的成员是否对制度有所不满或不再满意的情况。
从宏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把握制度的多重面相,特别是倾听经济学与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可行建议,对政治制度概念的界定十分必要。若将三个学科放置在水平维度,可以发现经济学与政治学分据两端,社会学居于其间。斯科特认为制度同时包含组织与活动,这也表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中间立场。包括劳森、兰恩与厄森在内的政治学者也指出,政治学长期以来主张制度首先是组织。经济学则专门强调制度的程序内涵,如诺思(Douglas 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作了这样的界定:“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讲是人为设计出来并用以塑造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条件。”[14]3不难发现,诺思在描述制度时没有提及任何组织。
政治学者对制度化的重视程度远胜于经济学者与社会学者,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可以与对制度的热情等量齐观,但对制度化过程的起源和形式还缺少全盘审视。亨廷顿业已关注制度化发展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相关原因,但其仅侧重“内部”,因而与社会学取向大同小异。亨廷顿认为时间因素对制度化过程中的四个关键特性的成熟定型至为关键,不过他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呈现该过程的。换言之,时间本身应被视为制度化的一项“原因”,但不能简单认定“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越久,制度化水平就越高”。政权的衰颓和倾覆表明,制度化的进程非但不是线性的,而且还可能是可逆的。亨廷顿自己就曾指出,“组织如果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便会陷入危机,在此形势下要么承担新的功能,要么只能苟延残喘或行将就木”[3]13-15。亨廷顿过于关注更具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性的制度,这一点类似斯科特对帕森斯功能主义观点的批评,“帕森斯认为相互联系的人们的行动被导入共同规范标准与价值模式时,行动系统就被‘制度化’了”[2]12。帕森斯与亨廷顿不曾阐述制度同社会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但不可否认这是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方面,因为功能主义者必然相信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对整个政治体系发挥影响。
Poly(S)-TPBO螺旋构型能稳定存在于各种有机溶剂中,比如:二氯甲烷、四氢呋喃、乙酸乙酯、二甲基亚砜(DMSO)、甲苯和苯等.
这种状况无疑是矛盾的。支持性因素(support)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哲学与经验研究的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从组织和程序两个方面考察制度时,却很少把支持性因素与政治制度的创设、维系及消亡相联系。政治学者不会否认某些支持性因素有益于政权维系,也能够接受这些支持性因素本身的起伏波动,但他们没有把这一见解注入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过程分析,更没有扩展到政治制度分析。
2.2 两组患者疼痛情况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在政治制度的制度化及“去制度化”过程中,肯定外部因素并非强调它比内部因素更加重要。实际上,政治制度以及一些兼具政治属性的社会制度有其特殊性,这类制度的决策领域往往逾越自身边界,受到决策影响的人们会在政治领导者允许的范围内施加影响。于是,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权力、政治文化和环境,支持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在临床上,冠心病患者容易发生充血性心力衰竭,而冠心病合并心衰后,患者的心肌会发生缺血、坏死等一系列的恶性改变,会导致心功能严重下降[1]。目前心肌能量代谢相关药物对冠心病心衰合并糖尿病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该研究选取了曲美他嗪来治疗冠心病心衰糖尿病患者,并选取该院在2016年1月—2018年1月期间收治的140例冠心病心衰合并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曲美他嗪在治疗冠心病心衰合并糖尿病的临床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由于支持性因素不存在失灵的问题,而只是在政治制度的语境下发挥作用,所以制度化也相应地在政治语境下具有某种特殊性。关注支持性因素使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分析更具现实感,但也使政治语境下的制度定义更加复杂,因为人们对“政治制度一旦脱离其依赖的支持性因素依然能够独立存在”持怀疑态度。换言之,如果某个政治组织或政治程序不能得到支持或仅得到微弱支持,就很难将其视作常规制度。一方面,或许有学者认为,将政治制度的存续与其可能获得的支持联系起来未免脱离实际,因为制度是以“稳定、有价值且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为特征的组织或程序。支持性因素明显与这些特征毫无关联,而且制度性组织或程序的实质内容并不取决于它们得到的支持性因素。此外,由于支持性因素在来源和发挥影响上十分复杂,当这些因素达不到一定临界值时,是否意味着相关组织或程序无法成为制度。人们针对以上难题更可能简单认为,判定组织或程序能否成为制度的主要标准仅仅是“稳定的、有价值的及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还有貌似合理的观点提出,行政部门、代议机关、政治党派、甚至宪法在支持者屈指可数、并借助强力才得以维持的情况下仍然作为制度而存在。平心而论,这些对象在摇摇欲坠之际很难称之为制度,对制度与制度化加以区分更有助于分析此类问题。处于瓦解边缘的政治体系也将到达“去制度化”的终点,此时的政府顶多算是一个徒具其表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者在分析组织或程序时常常从内心深处认为制度概念太过复杂,这也是他们青睐制度化概念的重要缘故。
为得到连贯一致的制度概念,研究者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各门学科在制度定义方面分歧颇多,与其基于社会科学整体视角阐释制度,不如更为务实地让这些学科各自作出探索。毫无疑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在界定制度时,往往指涉截然不同的现实对象。经济学倾向于简化制度的内涵并从同质化角度进行分析。政治学面对行政部门、代议机关、政治党派这类宏大制度时,既不会忽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也不会把制度抽象为同质化的相关安排。社会学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并左右逢源,其立场取决于研究对象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大量实体,还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少量实体。更为棘手的是,制度特征的差异性与制度化过程的多样性直接相关。因此,在纷繁头绪下对制度与制度化形成完整认识会异常艰难。但是从积极角度来看,学者当前所面临的各类难题也反映出制度分析正在取得进展。制度与制度化研究作为一个有待求解的谜题,不仅表明人们在理解社会生活时存在巨大鸿沟,还为揭示社会科学不同分析路径的关键差异提供重要线索。
本文原题为About Institutions Mainly, but not Exclusively Political,选自R. A. W. 罗德斯(R. A. W. Rhodes)、萨拉·宾德(Sarah A. Binder)与波特·罗克曼(Bert A. Rockman)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参考文献:
[1] PARSONS T,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Free Press,1954,p.239.
[2]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 London:Sage,1995.
[3] HUNTINGTON S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4] TRUMAN D B,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 New York:Knopf,1962,p.26.
[5] ALMOND G A,COLEMAN J 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4-33.
[6] ALMOND G A, Powell G B, Comparative Politics ,Boston:Little Brown,1966,pp.84-85.
[7] GOODIN R E,KLINGEMANN H D,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 LAWSON K, The Human Polity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5,p.29.
[9] MARCH J G, OLSEN J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8,No.3,1984,pp.734-749.
[10] MARCH J G, OLSEN J P,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Free Press,1989,p.16.
[11] LANE J E, ERSSON 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Los Angeles:Sage,1999,p.14.
[12] LANE J E,ERSSON S,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London:Routledge,2000,pp.23-37.
[13] GOODIN R E,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4]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BARRY P B, FOWERAKER J, 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Routledge, 2001,p.363.
[16] EASTON D,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Knopf, 1953,pp.135-141.
[17] POLSPY N W,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No.1,1968,pp.144-168.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8-005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12&ZD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源流与方法变革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课题“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理论源流与方法凝练”。
作者简介: 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1929年生,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荣休教授。
译者简介: 马雪松,1982年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慧,1991年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巩村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