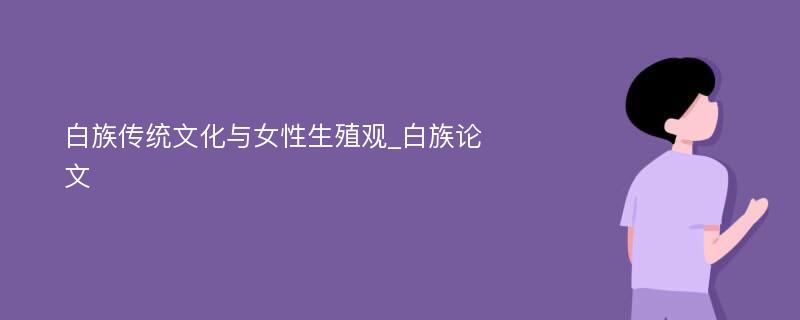
白族传统文化与妇女生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文化与论文,妇女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生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对此十分重视。白族也如此,尤其是白族的传统文化,如地理环境、血缘宗族观念、宗教信仰、恋爱婚姻、家庭与妇女生育观念等关系中,精华与糟粕共处,优劣并存。本文意在通过这些与人口再生产有关联、与妇女地位和作用相联系、与妇女生育观念密不可分的传统文化的分析,取其精去其粕,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
关键词 传统文化 生育观 人口 关联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创造模式,它既是人类活动的成果,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造就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文化模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均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并一代代相传,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生育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各民族对此都十分重视。于是在生育观上,各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观念。白族也不例外,尤其是白族的传统文化,对白族妇女的生育观影响很大。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本文在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探讨白族传统文化共同特征,如地理环境、血缘宗族、宗教信仰、恋爱婚姻、家庭意识中体现的生育观念。
一、地理环境与妇女生育观
白族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现有人口195万多人,云南有134万,男性为67.7万,女性63.3万,主要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中民家约占总人数的95%,那马占3.5%,勒墨占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加之自然气候差异,居住在怒江和澜沧江边的勒墨、那马人,从事刀耕火种同时逐渐开始农耕,险恶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生态直接影响和威胁着妇女的生育与健康,造成这里地广人稀。而在洱海区域坝子中的民家,农耕方式已形成,这里的生态环境相对有利于妇女的生育和健康,但又形成人口密集状态。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致使不同地域中的白族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风俗习惯也有所不同,从而在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上也有差导。然而,白族聚居的云南各地,山峦起伏,江河密布,交通不便,把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同一支系不同地域分割开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白族得以保持着完整的民族特征,使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传承和沿袭,这正是人们追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以人畜耕作,广种薄收,靠天祈雨的低下生产力,沿袭着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自我固守的传统文化中,迫使人们只能靠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种的繁衍来加速人口的发展。于是,人们渴望增丁添口,崇尚大家庭,来满足亲子感情和自我成就感,以保证自我的生存和整个民族的壮大。这就从根本上刺激了生育的运行机制,也就必然制约和影响着妇女的生育观念。据调查人们普遍持有“人多势众”的思想,造成居住在不同地域里现60岁以上的妇女,普遍生育5~7胎以上,有的多达10胎以上,无节制地生,直到不会生为止。在生育过程中又无卫生和健康条件的保障。据调查资料载,1951年以前,由于旧法接生,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当时土改卫生工作队共调查50931次孕产者,其中流产者占7%,早产占2.4%,难产占2.8%,足月产占87.8%。在38203次分娩中,自产自接者占76.3%,旧产婆接生的占14.2%,新法接生仅占9.5%,产后感染(产褥热)占12.85%,产后流血者占13.26%。在出生婴儿6726人中,婴儿死亡率高达40.2%[1]。那时,在险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根本谈不上调节和控制生育,也没有让妇女安全通过妊娠、分娩、母婴健康、不感染疾病等措施。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白族地区历史上曾流行的“血吸虫病”,曾危害妇女的生育健康;还有“麻风病”,在民间曾一度认为是不治之症,因而发生过枪杀或活埋患者的事件;洱海区域的山区或半山区,由于生活用水低碘引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及克汀病,民间称为“大脖子病”,严重地影响妇女的生育;还有宾川、漾濞、祥云、鹤庆等地温泉水氟含量超标而引起的“地氟病”;又由于白族饮食习惯中喜吃“生皮”的习俗引起的“旋毛虫病”等地方病流行,严重地威胁和影响着妇女生育健康。促成当时高生育文化成为一种必然,使生育观从根源上带有顺其自然的惯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的改善,新法接生的普及,以前那种危害妇女的疾病得到控制,孕产妇死亡率1988年下降到5.63/万[2]。自然生态影响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1984年经考核检查,达到中央规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麻风病目前基本消灭;地方性甲状腺肿及克汀病已达到国家颁布的基本控制标准;地氟病经过改水降氟工程(即引泉水入村、打深井)得到控制;“旋毛虫病”的根治涉及到移风易俗和长期宣传才能彻底根治。所以自然环境仍然直接间接地影响妇女身心健康。这与白族血缘宗族观念分不开。
二、血缘宗族观念与妇女生育观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白族社会仍然存在父系家庭公社和封建宗法大家庭。如勒墨人和那马人的父系家庭公社,都以血缘纽带维系家庭公社的基础。泸水县洛本卓乡的勒墨人大约有近百个父系家庭公社,分属虎、鸡、木、菜四个氏族[3],分布在不同村寨,每个村寨居住着一至三个父系氏族,也有一个父系家族分居于相邻几个村寨,每个家庭公社包括同一家族的七八户至数十户一夫一妻制父系小家庭[4]。每个氏族有自己的氏族长、公共土地和墓地,有互帮互助的权利与义务,生产中有共耕关系,有共同祭祀活动和血族复仇义务。而在洱海区域的宗法大家庭中,除去包括四、五代成员的大家庭外,多数分解为一个宗族有许多小家庭。在喜洲、周城等村镇,有的宗族达上百家。每个宗族均有自己的田产,家族公共墓地;并以宗族的共同血缘为纽带,建有宗法祖宗祠堂。如喜洲16村每一个同宗同姓都有宗祠,遍布在各街巷和村落。在喜洲街北栅外就有白语称之为“董格次叹”、“鸭格次叹”、“尹格次叹”。“格”白语意即宗族。此外,还有同姓不同宗的祠堂,如喜洲城北村就有“上加次叹”、“西加次叹”,家族中由辈分高的年长男性任族长,个别也要世袭族长现象。族长权力大,主持家族内生产生活、祭祀祖先,参加庙会活动以及处理纠纷。白族普遍还有宗谱和家谱。据史料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张氏国史》流行于南诏大理国[5]。到宋元以来,高氏及杨、赵、李、董等名家贵族都修过家谱[6]。于是,时至今天不同地域中的白族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族谱、家谱及聚族而居的特点。有的一个村寨往往就是一个大家族,有的则是血亲关系的几个家族,即以家庭、宗族血缘关系而聚居。剑川县的下沐邑村有杨、张、颜和王四大姓,其中以杨、张两姓为主[7]。形成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从遵循“一切服从氏族组织利益”发展到“维护家族内共同利益”的民族传统意识,并靠血缘宗族社会组织来加以保证,以修宗庙、祭祖宗、续家谱来增强宗族观念。
白族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封建的宗法制度,而宗法制的核心又是家长制和夫权制,并以嫡系长子继承制为其特征的父系传承;加之白族传统农耕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多子多孙,几代同堂被认为是农耕社会幸福的标志;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冤家械斗”、实力竞争;在村落中享有地位的特征也是人多,人多势众,家族阵容就庞大,而这一切都归之于妇女的生育。于是与氏族社会的遗风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生育观被延续下来,为了血缘宗族的兴旺,强烈地刺激着白族妇女的生育,越穷越生,且要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子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继承者首先是儿子;有女无子的可以招赘女婿,叫做‘讨实子’,无儿无女也可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但都必须取得家族的同意;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的继承权。”[8]生育就是为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家族中容不得不生男孩的妇女,更不容不会生育的妇女,她们使家族“断子绝孙”,那是家族的奇耻大辱,以“养个母鸡不会下蛋”来讥讽不育妇女,妇女被当成性和生育工具,在家族中无地位。故白族民间流行有“妇女无喉咙,说话不算数”。[9]“母鸡做不得三牲”等。在宗族观念束缚下,妇女必须遵循宗法社会宗族家法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过了门的媳妇不仅要承担全家人衣食住行,更主要的是为家族生儿育女,使自己的一切服从于宗族的利益。在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事实上还维系了白族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村落家族的作用与功能。家族不仅是生产联合体,且家族人多势众观念更加强烈,要求妇女多生,生男孩,使得淡化了几十年家族制得以复活,给优生优育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带来一定困难。这又与白族妇女血缘宗族观念联系在一起。
三、宗教信仰与妇女生育观
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殊的宗教信仰。本主为汉语意译白语名,过去地方志书里多称为“土主”,民间称之为“老公尼”、“阿太尼”,总称“本任尼”,即始祖之意,具有鲜明的祖先崇拜的特征。这种由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祖先崇拜,强化着妇女生育的传宗接代、繁衍子孙的观念,同时还维系着白族社会血缘宗族关系。在白族信仰中,本主就是本社区的主宰神,它管天,使风调雨顺;管地,使五谷丰登;管畜,使六畜兴旺;管人,使人丁昌盛,阖境清吉。因此人们相信本主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无论有什么困难只要祈求本主,都可以得到解决。白族妇女结婚,要到本主庙祭祀,祈求本主保佑送子,又如妇女生育,家人也要到本主庙去敬香,请求本主庇佑,减轻疼痛,顺利生产;就连小孩出生、满月、周岁、生病等,也要到本主庙去祭祀,祈求本主保佑平安吉利。在她们的观念里,子嗣繁衍关系到宗族兴衰;家族的存续、民族的发展与壮大,都寄托在子嗣的延续上。而子嗣的繁衍又与妇女的生育健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白族的信仰中,祈子嗣和保佑母婴健康的观念很强烈。于是在每座本主庙中,除主神本主外,还有配神“送子娘娘”、“九天卫房圣母”等,专司送子嗣。今天白族妇女观念中仍存在祈求本主保佑宗族兴旺、子孙昌盛、儿孙健康成长,民族延绵的意识。正如大理满江村本主庙的一副对联所说:“体天地之好生大生广生生不已;保子孙于彝世十世百世世不穷。”[10]反映出人们于本主崇拜中的生育观和多子多福的精神依托。
白族信仰的本主神,近似于希腊神话中的神,却又比希腊神话更具有人情味,并且来历不同。他们之中有“自然之神本主”,如云雾、太阳、月亮、石头、树桩、鱼螺等;有“龙本主”,如大黑龙、小黄龙、龙母等;有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本主,如杜朝选、段赤诚、孟优等;有南诏大理国的帝王将相本主,如细奴罗、蒙世隆、赵善政、段宗傍、郑回等;有征战南诏的唐朝将领,如李密父子;还有戍边屯垦的明朝将领傅友德、沐英等,还有为民所敬仰的节烈、贞女的女性本主,如阿南、柏洁夫人等。这些本主都有神话故事伴随,形成丰富多彩的白族本主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又世代相传,长期在庄严的祭祀中朗诵,从而体现本主信仰中的观念,由此也就深入人心,形成牢固而有力的白族民族传统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长期支配着白族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其中还有充分体现白族生育欲望的生殖崇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石雕女阴——“阿央白”即生殖器崇拜,它与许多庄严的神像并列,受人膜拜。每年农历7月27日至8月1日,洱海区域的青年男女汇集于此对歌,寻找情侣,并对“阿央白”进行跪拜,祈求爱情美满,婚姻幸福。平日,已婚妇女来此跪拜祈求子嗣;已生育的妇女则求多生,生男孩;有孕的妇女则拿生香油在石雕女阴上擦抹,认为擦后即可生儿子,并祈求生产时顺利,减轻疼痛。白族先民们把生育力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重视妇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女阴的生殖能力,也就自然表现出对女性生殖器崇拜,表现出人们关心种族繁衍、尊重和维护生命力,对人口增殖的强烈生殖意识。
与生育现象联系起来产生的祖先崇拜,鱼螺也成为白族先民的崇拜物,并把鱼作为“始祖母”的象征,已不仅仅是对女阴的崇拜了,其生殖意义与血亲关系紧密相连。“鱼作为一个氏族群的‘根’经代代相传,几经流传仍深深植根于洱海先民的意识中。”[11]今天洱海区域白族社会生活,仍与鱼有密切联系,无论宗教信仰的祭祀,还是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都与鱼联系在一起。大理喜洲河矣城本主庙,供奉的“洱河灵帝”,就是直接把鱼神尊像供奉于本主庙中,让人们祭祀。祭品也少不了鱼;婚宴餐桌上也离不开鱼;就连新媳妇过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上街买鱼,以示自己的生养能力;丧葬中也以鱼为殉葬品,认为鱼有复生的能力,而借其复生能力促成人之再生。就连妇女的服装上也处处可见鱼崇拜的痕迹,如少女戴鱼尾帽;妇女上衣、袖口、衣襟上缀着象征鱼鳞、鱼人的银白色泡子;围腰、裤脚边、鞋上绣有鱼纹图案。可见人们对鱼的崇拜,将鱼与生殖相连,把鱼作为女阴象征,其中又包含了生殖、血亲、种族意识。
洱海区域的白族还盛行一些与人口增殖,特别是与妇女生育相关的活动,如一年一度“绕三灵”盛会,青年男女以此为寻找对象的好时机;已婚不育妇女可以择偶“野合”,祈求得子。此外,为祈求子孙兴旺,白族民间还流行“修路”、“架桥”活动。通过宗教信仰和各种活动,以求神灵保佑儿孙满堂,赠子荫宗,这也就是白族在长期的宗教信仰中形成的生育观念,并一直左右着妇女的生育行为。现在则成为阻碍优生优育、节制生育,影响妇女健康的文化基础之一。
四、恋爱婚姻与妇女生育观
白族传统文化中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通常人们恋爱自由,但婚姻不能自主。女孩长到13~15岁,就必须履行人生礼仪“穿耳洞”,穿过耳洞象征着少女可以恋爱了,在民族节日上对歌,唱白族调,寻找情侣。农闲时夜晚男女青年三五成群在村落里幽会,约会地点称之为“花南”,白语曰“南毫”,直到50年代末村寨里还保留着“南毫”,供青年男女在一起娱乐。而在勒墨和那马人中,女孩长到13~14岁就离开父母的大火塘到小屋居住,这种小屋类似“南毫”,男女青年在一起弹口弦、吹树叶、对情歌,相互倾吐爱慕之情。因此不会唱调子的姑娘难寻如意君郎,不会对歌的小伙也难找到聪慧能干的姑娘。所以白族生来爱唱歌,自古也就有依歌择偶的传统。故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12]
可是,白族少女即使是自由恋爱,最终仍须经过传统的婚俗程序方可成婚。通常青年男女钟情后,征得家长同意,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到女方说亲,讨求女孩生辰八字,经占卜求吉,如若双方辰相抵触,这门亲就不能成。民间常言:“一山不容二虎”,意即两个属虎的人不能相配;“龙虎相斗”,属龙的人不能找属虎的人成亲;“羊落虎口”,就是属羊的女孩不能找属虎的男子,否则会相克。除当事者“八字”不相冲犯外,也不能与家人相顶撞才能婚配。依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有些地方还流行过“指腹婚”、“娃娃亲”、“买卖婚姻”等,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生育与健康。
白族婚姻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1949年前,极个别有过一夫多妻。同姓同宗不婚外,与其他民族亦可通婚,但仍以在本民族内通婚为主。盛行姑舅姨表婚,即首先在表亲中选择配偶,俗话说“表姊表妹表上床”。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财产不外流,亲上加亲。这一习俗至今还流行,笔者在洱海区域许多村寨作调查,发现有的村寨中有弱智、痴呆、哑儿,究其根源,几乎都是近亲婚配的结果。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白族联姻范围越来越小,方圆很少超过几十公里,大多就在几里内。调查证明,在本村落内联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尤其为保留一份土地,即将自己的份额土地带到婆家,出现了同村恋、村内转的封闭式婚姻,使得本来就乡里乡亲又亲上加亲,不仅加重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更严重地影响妇女的生育观念和人口素质。
白族婚俗中还保留着反映母系制特点的从妻居制,即招婿入赘婚。这种婚姻形式分别为:有女无子,为女儿招婿;有的则是女儿大儿子小才招婿;有的虽有儿子,但为增加劳力而招婿;还有的则是父母与女儿关系好,而不愿女儿出嫁才招婿。无论那一种方式的招婿入赘婚,都是从妻居,并在缔结婚姻时,请中证人立约,阐明双方权利与义务,有女无子招赘婚,入赘男子要改名换姓,有权继承女方家的财产。入赘婚双方所生子女,规定长子姓母姓,为母亲家继承人;次子姓父姓,有权返回父亲的本家,这便是白族社会中“长子入祠,次子归宗”的传统。而无论那一种方式的入赘从妻居婚,均可使紧张的婆媳关系变成母女关系,能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保障妇女的地位与权益,有利于妇女的生育健康和反映妇女的意愿。
历史上白族社会中还流行过“抢婚”习俗。抢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发生在未婚青年男女中,男女相爱,可女方家不同意,男方家只有通过抢的方式才能成亲。另一种方式则发生在已婚妇女(多半是寡妇)中,男方通过媒人与寡妇公婆或本人说定,男方趁其外出参加庙会或赶集时将其抢回成婚。通常寡妇不能再嫁,而通过抢的方式促成寡妇再婚,免去寡妇活守寡,有利于妇女身心健康。
如今白族青年男女大多数都能自由恋爱,自主婚姻,选择如意伴侣,建立幸福家庭。但在边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的乡村,传统婚恋习俗仍在制约、左右妇女,姑舅姨表婚没有彻底根除,买卖婚姻时有发生,一些乡村早婚现象严重,早婚必然带来早育,早育使妇女过早地担任生育重担;有的为要男孩而造成多生,甚至还出现高龄孕妇,严重地威胁影响妇女生育健康。这里蕴含着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
五、家庭对妇女生育观的影响
白族家庭基本上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这种小家庭包括祖父母和未嫁娶的儿女,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幼子一般与父母同住。在怒江的勒墨人和兰坪的那马人中,三四代同堂的家庭不多。可在洱海区域的剑川、鹤庆、大理等地,几代同堂家庭居多,这与白族传统崇尚四代同堂大家庭的观念分不开。直到80年代初,笔者在周城镇和其他乡村调查时,人口最多一户有24人,10人以上户数也不少,7至8人者居多,村里的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居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如今白族家庭人口最多者6~7人,且数量较少,大家庭逐渐解体,走向父母和子女的核心家庭,4~5口人居多,核心家庭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生育观。
过去许多人认为,白族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很低,是男人的附属品,丈夫负责掌管处理家庭中一切事务。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因而在实际生活中权力较大,往往由妇女当家,母亲胸前的钥匙串便是家庭财产和权力的象征。加之白族传统对后代子嗣的重视,于是在家庭内对妇女生育都很重视,盼望人丁兴旺,把添丁生口视为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和喜事,随之便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生育习俗和观念。
此外,白族男女成立家庭后,通常不退婚或离婚。媳妇过了门,生为男家的人,死为男方家的鬼。丈夫去逝也得活守寡扶持子女,开门立户沿袭香火。这种家庭文化一直桎梏着白族妇女身心健康,故在白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贞节牌坊,随时可听到节妇、烈女的故事。据清《鹤庆州志》载,元明清以来,仅鹤庆就有“节妇”552人,“烈女”40人,“孝女”14人,“贞女”24人。人们好过歹过凑合着过,不容离婚和寡妇再嫁,否则会受到舆论抨击。同时白族社会也曾遗留过没有子嗣的家庭,丈夫可以纳妾和寡妇“转房”的习俗。通常妇女久婚不育,或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丈夫可再娶,避免绝嗣断代,这便是从前造成一夫多妻的原因。寡妇“转房”又称“叔就嫂”,即兄死其弟或堂弟娶兄妻,俗话说“弟娶兄妻天下有;兄纳弟媳天下丑”,这种习俗在那马人和洱海区域流行。但在丽江九河的白族和勒墨人中则流行弟亡,兄可纳弟媳,而兄死,其弟不能纳寡嫂,据说这是“长兄当父,长嫂为母”之故。可无论那种方式,过去妇女均无权提出离婚的要求,正如俗话说:“男人不给一张纸,女人只有等到死。”丈夫则有权随时休妻,洱海东岸海东和挖色地区夫妻不和,丈夫只要写封“休书”给妻子,便算离婚。碧江勒墨人的离婚更简单,丈夫只要打一木刻给妻子或调解人保管,就算离了婚。
可见在婚姻家庭中,为生殖繁衍,妇女在家庭中被重视;生育得到关怀和照顾,也有一套完整的生育健康保护方式;而在夫妻关系上,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妇女仍处于被动地位,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主动权。故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白族家庭一般较稳定。随着社会发展,婚姻法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推广,传统影响、制约妇女生育的习俗和观念在改善,有利于妇女健康的生育观念和幸福家庭风尚正在兴起。
以上对白族传统文化共同特征,地理环境、宗族观念、宗教信仰、恋爱婚姻、家庭与妇女生育观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探讨,其中精华与糟粕同在,优良与粗劣并存,先进与落后共处。意在通过这些与人口再生产有关联、与妇女地位与作用相联系、与妇女生育观念密不可分的传统文化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注入新时代的内容加以传承,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本民族的、现代的妇女生育健康观念,真正提高民族人口质量。
注释:
[1][2]《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八,科技志、教育志、卫生志,第377~378页。
[3]云南编写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3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修世华:《论怒江勒墨人的父系家庭公社》,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2页。
[5]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南诏图传》部分5~6题记。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出版。
[6]张锡禄:《南诏与白族文化》第2页,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第5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白族简史》第2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云南编写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92页。
[10]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第6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蒋印莲:《生殖文化在洱海地区的遗留》,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22页。
[12]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