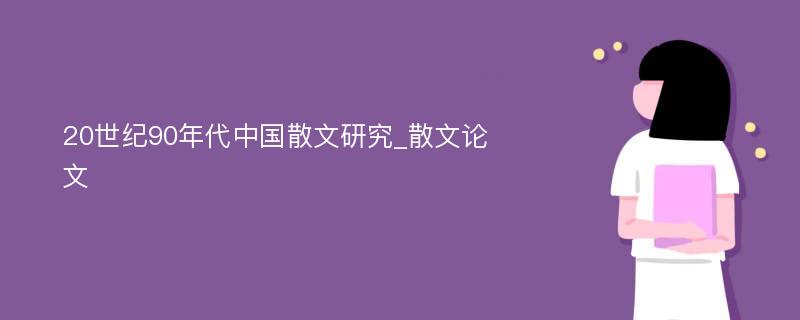
九十年代中国散文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0)01-0033-37
一
90年代是散文繁花盛开、争奇斗妍的年代,是散文题材广博、多元发展的年代,是散文更强调主体意识,更注重美学价值的年代。有人将90年代的散文形象地描述为“太阳对着散文微笑”;“一颗被冷落在文学深宫里的明珠,如今被大众捧在蓝天白云之下,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它熠熠闪着动人的光芒——这颗明珠就是散文。”[1]有人认为20 世纪的散文创作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30年代,第二次便是90年代[2 ]。如果放在当代文学史上考察,90年代散文又是继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高潮。这样的描述和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90年代的散文创作之所以形成高潮,有其深层的原因:
一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90年代,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繁荣,人民生活多姿多彩;政治气候清明,社会环境宽松,极左思潮逐渐失去市场,人们的精神世界获得极大自由。
二是作家思想方面的原因。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作家们那种冲破束缚、拨乱反正、大悲大喜的亢奋激昂已成历史,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的那种时来运转、进入盛世、喜迎朝阳的欢呼礼赞也渐趋平寂,到了90年代,作家们能更从容、更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体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而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层次去描摹风云的变幻、时代前进的足音,去抒写作家细致的生活感受及审美体验。
三是艺术观念方面的原因。80年代初对杨朔、秦牧等散文大家的批判过后,作家们更清醒地看待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更认真地吸取其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因此胸怀更为宽阔,技法日臻完美。与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散文亦是经历了“现代派”、“先锋派”的喧闹激进之后,复又转入平稳、扎实的发展轨道,能更冷静、更从容地体验生活,反映生活。
总之,90年代的散文更加贴近生活,靠近民间,关注人生,更具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加强调表现主体意识,袒露内心世界,热切呼唤“艺术散文”、“精神化散文”,于是90年代的散文便呈现出既扎实,又精彩、多元的发展态势。有人概括1997年散文创作的总体特点是:“叙事性、抒情性、议论性等多种体式齐头并进,各显其能;以小见大、平中见奇、寓浓于淡等各种艺术技法也表现得纯熟自如,各显异彩。”[3]如果用以描述90年代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看来亦应是适合的。
如果说,70年代末的散文是刚刚冲破岩层、喷出地表的山泉,80年代初的散文是泉瀑涌动、交汇奔泻的溪涧,那么90年代的散文便是兼容并蓄、浩浩荡荡的大河,貌似平平稳稳,却又广博深邃、大气磅礴。
二
90年代的散文,有相当一部分以透析历史文化,观照社会现实,关注人类命运为其主要内容。这类散文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在描述咏叹历史风云、文化事件的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袒露作家的博大胸怀,抒写作家的审美体验,发射作家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力量,因而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类内涵深厚,大气磅礴的“大散文”,已成了90年代散文园地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这类散文的部分作者是阅历丰富,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教授,故其作品又可称为“学者散文”。余秋雨、季羡林、林非、萧乾、雷达、宗璞、杨绛、谢冕、张中行、黄秋耘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有的联想引申,纵横捭阖,由康熙的文治武功到慈禧的斑斑劣迹,概括了清王朝由兴盛到没落的过程,令人荡气回肠,嗟叹不已(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有的以阅尽沧桑的慧眼、洞察中外的心智、潇洒诙谐的笔触,勾勒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追忆“文革十年”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非人境遇及人性摧残,写尽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心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季羡林《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有的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暴虐专横,泯灭良知,阐述中外艺术创作的共同规律,追寻自然、浑成、真知、意蕴无穷的“艺术的极致”(林非《从乾陵到茂陵》);有的追溯北大百年的辉煌业绩、优秀传统,描摹一代代文化巨擘的神采气韵,展现象征民族精神的北大灵魂,抒写对北大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澎湃激情(谢冕《一百年的青春》、卞毓方《煌煌上痒》)。
20世纪末,人类的生存空间日益恶化,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类受到了自然空前严厉的惩罚。不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怀着对人类命运的忧虑,极度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很自然地便成了90年代散文的一项突出内容。这类题材的散文显然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突出,成就都更大。李存葆的《鲸殇》,王英琦的《愿地球无恙》均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的力作。多年来,确实难以见到这样大气磅礴、充满力度的作品了。《鲸殇》传递了一种愤慨和悲怆,不愧是“从鲸反观人类处境和人类未来的大作品”,洋溢着一种“神的拯救情怀”,被称为“人类的神话”[4]。 《愿地球无恙》则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织,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广大背景下,极目环球苍生,心系世界凉热,既有忧患、焦虑、悲观、绝望,又有思辨、探寻、期盼、祝愿,真正称得上是“心鹜四极,视通万里”。“愿地球无恙”发出了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作家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艺术家的深深敬意,创作了一批缅怀颂扬的散文,其间也不乏佳作。经过一两个年代的时间淘洗、积淀,经过作家的冷静思考、长期酝酿,时至90年代,写这类题材便显得更为得心应手,情深意切。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梁衡。与七八十年代同类题材的散文相比,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大无大有周恩来》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构思,着力揭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重视人物的神韵风采。如《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在“文革”当中被监视管制于江西新建县期间所住过的一座小院和走过的一条小路,作者拜谒这座小院,轻踏这条小路,不由得触景生情,想象当年邓小平在这里生活、劳动的情景,揣摹邓小平忍辱负重,思考党、国家和人民命运,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心境,包含了对伟人落难的深刻理解,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故能撼人魂魄,引人共鸣。
三
90年代散文创作的另一道风景线是大批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加入散文创作行列,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专攻散文的作家比例似乎越来越少,而兼治散文的“双栖作家”、“多栖作家”明显越来越多。
小说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专长介入散文,有如天外飞石投入平静水潭,很快便打破了散文创作的常态和定势,给散文肌体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劲活力。他们将小说的情节和场景、人物和故事,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带进散文艺术天地,使散文的艺术空间得以装饰和延伸,审美情趣得以弥补和拓展。他们惊喜地发现散文更便于直接倾诉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更便于随意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悟,散文天地竟是如此高廓宽广,他们以小说家的姿态娓娓写来,将社会万象、生活百态采撷进散文花篮,让小说和散文“联姻”,确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汪曾祺、李国文、高晓声、王蒙、刘心武、冯骥才、贾平凹、张承志、李存葆、韩静霆、铁凝、张抗抗、史铁生、张伟、陈忠实、何士光、梁晓声、韩少功、邓刚等都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散文佳作。
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对地坛景物情调的描写,对草木虫鸟、气候物景的感知,有如诗人般细致;对宇宙万象、日月轮转、生死命运、人生意义的思考,有如哲人般深刻悠远,而对母亲、长年坚持来园子散步的一对老人、爱唱歌的小伙子、女工程师、长跑家、弱智小姑娘和她的哥哥等人物的刻画,则又分明显示了小说家的才华。韩静霆的《梵高和青藤》描述梵高和青藤道士徐渭的思想性格和绘画艺术,人生经历和凄惨命运,表达作家对两位伟大画家的深刻理解和由衷敬仰,其间对梵高疯狂地割下自己的耳朵、徐渭以三棱巨锥扎入自己耳道,拿锤子击自己肾囊的描写,确实是“满眼血色”,作家凭借丰富的想象再现了那悲壮、惨痛的细节,凸现了两位画家的鲜明个性,令人震惊、惋惜、悲伤,充分显示了小说家的特长与功力。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所忆念的昆明雨季的仙人掌、菌子、杨梅、缅桂花、小酒店,无不使读者也像作家那样“想念昆明的雨”,作品虽没有直接描写人物形象,但作家自身的思绪性情、审美情趣都像缅桂花那样,挂满雨珠,馥郁诱人。作品写的是40年前昆明雨季的情味,这和他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画家、戏剧家的散文也异常活跃,独具特色,具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牛汉、曾卓、绿原、雁翼、忆明珠、流沙河、李耕、叶延滨、周涛、舒婷、傅天琳等涉足散文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其中有的诗人涉足散文之后,对散文的兴趣已超过了诗歌,有的已很少写或干脆不写诗了,如流沙河、周涛。流沙河戏称自己是“江郎才尽,很少写诗”了,周涛则被誉为是“站在诗的肩膀上”摘取散文硕果的散文家。此外,画家吴冠中、韩美林、黄永玉,戏剧家魏明伦也写了不少散文名篇。
诗人以其独特的诗心慧眼、激情敏感去捕捉散文题材,营构散文篇什,抒写自我性灵,因而其作品极富诗意情味,似有一股股薰风暖流萦绕浸润读者心灵。他们的散文,在揭示人情人性,吟咏亲情爱情方面尤为突出。如雁翼的《隔壁两个女囚徒》在监狱的特定环境真实描写两个女囚徒的性意识及性饥渴及其求生欲望,表现“我”的自省自责,赤裹“我”的灵魂,同时褒扬了人与人之间难得的信任、坦率、平等,毫无掩盖地袒露了人的本性本能。周涛《守望峡谷》对怒江峡谷半山腰傈僳族村寨的思蜜纽和胡蜜花母女俩的天生丽质、聪颖可爱却又一贫如洗、默默忍受蒙昧落后的摆布倾注了满腔的怜惜与同情,由此引出了对“有关人类生存的哲学命题”的深刻思考。绿原的《二十一世纪的随想》则是对20世纪的回顾和21世纪的展望,其间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对社会世道的深刻洞察,既有诗人的热情宣泄,又有哲人的冷静思辨,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广博胸怀与超前意识。
画家吴冠中的《柳暗花明》、黄永玉的《此序与画无关》、韩美林的《谁下地狱》所写的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对人生真谛的探求,则深深烙上了画家的印痕,如不是杰出的画家,又焉能写出如此随意挥洒且具真知灼见的散文?
四
90年代散文创作的又一突出特点是新生代的创作异常活跃,影响越来越大,其作品令人刮目相看。90年代初期和中期,好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一批新生代散文家的散文集和合集,如《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九千只火鸟——新生代散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60 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散文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就是较有代表性的几部合集。90年代后期,一些散文刊物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使新生代散文在社会上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如《散文天地》编发了新生代散文专号(1997年第6期)、 《散文选刊》编发了新生代散文特辑(1998年第2期、第3期),均对新生代散文的繁荣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综观新生代散文家的超越意识及创作实绩,他们确实成了90年代散文创作的生力军。
新生代亦称晚生代,是指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和70年代初,90年代产生影响的一批散文家。他们大多数有大学本科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文化素养较好,创作起点较高。祝勇、原野、老愚、于君、止庵、摩罗、冯秋子、苇岸、叶依、南妮、彭程、瘦谷、王开林、戴露、潘向黎、邓浩、洪烛、周晓枫、田晓菲等就是他们当中的突出代表。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意义的跨世纪散文家,21世纪前半叶的散文舞台将逐渐由他们替代一批老散文家而成为主角。
在散文观念方面,新生代散文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独抒性灵,表达真我,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与思考。他们认为散文应该是“活性的、音乐性的、解放性的”(周晓枫),应该“表达真我”,抒写“人性生命的体验与思考”(邓浩),“反思、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摩罗),展现“作者的灵性和内心力量”(冯秋子);认为散文的独特魅力“在于作者心灵的彻底敞开,不加矫饰,展示一个本真‘我’”(彭程)。
(二)呼唤崇高,追求大气,青睐大气磅礴的扛鼎之作。他们认为渗透于散文当中的应该是“高尚的力量与精神品格”,“能够擦拭读者的心灵门窗”(于君);他们呼唤“真正大器的散文”,认为它们应该具有“某种深厚博大的气质”(于君);还有人极力推崇“大气”,推崇“大散文”,认为“大散文什么都能承载,历史的、现实的,林林总总,不片面不单一”,还形象地喻之为“散文界若没有几篇大气磅礴的扛鼎之作,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海军一样”(洪烛)。
(三)挣脱束缚,不拘一格,主张散文形式要多样、多元。他们认为散文“首先是个广泛的概念,介乎诗与没有文学性的学术论文之间”,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随笔和有文学色彩的论文都是散文,“四者在散文里并不分主次”(止庵);认为“不同的作者尽可以顺应和发挥各自的喜好特长,或抒情感怀,或摹写世象人心,或作哲思理趣的探寻”(彭程);有的甚至提出“新文化散文”的概念,认为当代散文创作中与文化接壤的部分即可理解为“新文化散文”(洪烛);有的对当前散文界的守旧偏狭、门户之见表示不满,认为“规矩太多”,“很有点势利眼”,“散文的生机因此而大受伤害”(摩罗)。[5]
新生代散文家牢牢把握了散文的本质特征,崇尚高雅的格调和磅礴的气势。他们并没有在散文的概念方面过多纠缠,争论什么才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而认为但凡能表达真我,挥洒自如的,都算好散文。由此可见,新生代的散文观要比“旧生代”开放、广泛、宽容。他们不太理会有关散文概念之争,只管潇潇洒洒、自由自在地“独抒性灵,表达真我”,源源不断地奉献出闪耀着智慧和思想灵光的篇章。这正是新生代的可爱之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世纪散文的曙光。
新生代散文家的创作实践,令人信服地印证了他们的散文观念、艺术见解及审美情趣。其中较为突出的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承载丰富,内涵深厚,较为大气的“新文化散文”。这类作品,几乎涵盖了历史、现实、文学、艺术、哲学、宗教、自然、人生诸多方面的内容,在写法上,既有抒情般的韵味神采,又有学术论文般的评述思辨,正如他们所说的“介乎诗与学术论文之间”。如摩罗的《耻辱与耻辱意识》、止庵的《谈温柔》、彭程的《错位》、洪烛的《城市备忘录》等。这些作品,拓展了散文的外延,丰富了散文的形式,具备强有力的文化思想,凸现了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二)审视自我生存状态,抒写个人生命体验的人生感悟散文。虽然前一类散文也具备这些因素,但这类散文体现得更直接,更集中,更鲜明。如王开林的《终结》所写的便是关于生和死、关于生命形态与生命意义的思考,好些句子简直成了具有深刻哲理的格言。冯秋子的《婴儿诞生》有沉重苦涩,有神圣崇高,有喜悦欣慰,更多的是道义和责任,显然这也是“生与死的体验”的永恒的话题。潘向黎的《收藏时光》以自己所珍藏的挂历为载体,写出了时光的飞逝,生命小径的多变,生命之花的易凋,视角独特,抒情深切,读之使人生出无限慨叹。
(三)叙述方式灵活多变,大胆创新。他们敢于突破一切散文套式,不讲究起承转合,而是根据不同题材及其思想情绪而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无拘无束,随意挥洒。有的隐而不露,不动声色,以宁静的心态和朴实的语言娓娓而谈,叙述大地上的一个个小故事、一个个小生灵,从中透露作者的审美情趣及仁爱胸怀,如王开林的《大地上的事情》。有的思绪活脱,清纯自然,以浸透情感的笔写活了一个个生活画面,有如一首首精美的散文诗,如于君的《斑驳的德富芦花》。有的极目骋怀,如幻如梦,任凭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在作品中随意流淌,如瘦谷的《树的记忆》。
总之,新生代散文不受传统束缚,富有创新精神,厌恶浮夸、藻饰、滥情,崇尚自然、淡远、意在言外,讲究表达到位,追求角度刁怪,赞赏幽默机智,为散文创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经验。
五
90年代,在散文理论方面的探讨、争鸣亦是十分活跃。例如关于散文本质的研究、“大散文”口号的提出、“艺术散文”旗帜的高扬,对“小女人散文”的褒贬等,都在散文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其中关于“大散文”和“艺术散文”的讨论影响尤为深远。
“大散文”的概念最先是由贾平凹于1992年在《美文》的《发刊词》中提出。贾平凹不满目前的散文状态,深感当前流行的散文概念“范围是越来越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于是提出“大散文”的口号,主张“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同时他又强调散文必须抒写作家的真情实感,认为“真情实感在,文章兴,浮艳虚假,文章衰”,他不遗余力地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6]。
之后,刘锡庆、蔡渝嘉于1996年在《当代艺术散文集粹·跋》中进一步张扬“艺术散文”的旗帜并批驳了“大散文”的主张。刘、蔡认为“大散文”的主张是“对‘现代散文’(文学四体之一)的一种倒退”,其最大弊患是“使散文的‘范畴’无从界定,使它继续成为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驳杂纷乱文体的一个个‘收容所’和‘大杂脍’,”,“再这样‘大散文’地纠缠下去,散文必死无疑”[7]。
应该说,刘、蔡提出的对“人”和“人性”认识的五个表现层面(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艺术散文”的三个审美特征(自我性、内向性、裸视性)的论述是抓准了散文的本质的。他们认为散文“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史、心灵史,是作者生命展开的形式”,“充满着对‘人’生存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是创作主体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栖息地”。强调散文作者应该把艺术观照的镜头对准自己的心灵世界。
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不应该排斥、拒绝“大散文”,指责“大散文”把散文引上死路。尽管“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的提法不够准确、严密,但“大散文”论者所强调的散文要“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这些观点与“艺术散文”论者所提出的散文应该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史、心灵史”的主张应该说是殊途同归的。
20世纪的车轮即将悄悄隐去,21世纪的钟声即将轰然敲响。20世纪散文到了90年代巍然耸起形成高峰已凝成历史,21世纪散文的春天必将繁花竞放,灿烂如霞。那一座座新高峰正向我们逶迄迤而来。
收稿日期:1999-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