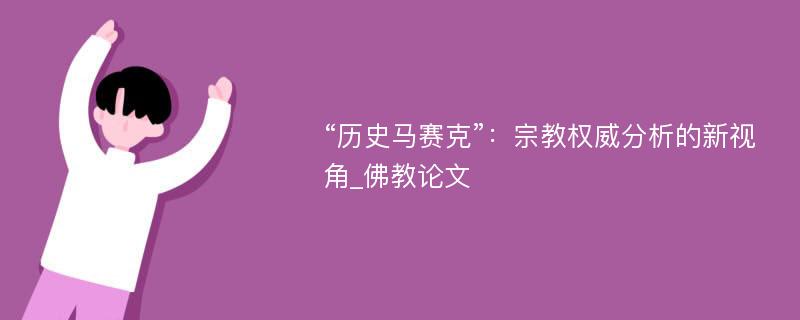
“历史镶嵌”:宗教权威分析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权威论文,新视角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7)03-0021-05
一、研究缘起:中国宗教的镶嵌特征
镶嵌视角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杨庆堃(C.K.Yang)最早提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这一概念,形容一种自身并不独立存在的宗教,它的仪式、教义和神职人员,均已和其他的世俗制度(如家族、政治)混杂在一起,世俗的历史文化、制度或仪式镶嵌并影响着宗教[1]。他指出在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宗教,可以视为一个弱组织性的僧侣集团与弱组织性的会众[2]。混合宗教没有独立的僧侣集团与信徒,这是由混合的世俗制度镶嵌而造成的,这样的混合宗教在社会组织中还不具备独立的结构重要性。顾忠华认为佛教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通过镶嵌机制而使之代代相传下来,人们一直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想象着自己与自然、超自然的关系,所有的佛教沟通都是以社群的集体意义作为前提,个人再怎么特殊的“神秘经验”,一旦成为社会沟通的对象便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关联[3],佛教组织无法摆脱社会制度、组织和规范等历史文化传统体系的镶嵌而单独运作。因此,这构成了宗教和社会历史文化镶嵌分析的双重焦点和取向。宗教绝对不是孤零零地悬在人们的脑海中,就像宗教不会纯粹出自人类的幻觉一样,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社会学不就是研究宗教、社会和历史文化如何彼此镶嵌的一门学科吗?
二、“历史镶嵌”: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选择“历史镶嵌”作为宗教权威研究的分析工具,首先是基于理论上的考虑:第一、镶嵌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领域,而将其用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非常少见。镶嵌分析可以为宗教权威提供新的研究途径,为我们更充分认识宗教权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第二、影响宗教权威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通过镶嵌视角可以将非宗教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来。镶嵌视角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宗教以外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视,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关注那些隐藏于历史文化结构之中的镶嵌关系。依照涂尔干(Durkhein)的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凡是处在可透过沟通来相互传达的“神秘经验”都属于一种集体(collective)现象和社会事实,即使具有“超自然”和“反经验”的特质,却始终不能真正地“超”于“社会”之外,而是镶嵌于其中。在宗教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传统宗教只会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中逐渐消逝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出现,宗教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脉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外,贝格尔、卢克曼与帕森斯探讨宗教私人化时,背后都涉及宗教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4],这些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宗教权威产生的内在原因。
其次,将“历史镶嵌”作为宗教权威分析的理论视角,还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第一,“历史镶嵌”视角视宗教为历史文化的产物,对“神”是一种“存而不论”的研究态度,宗教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是理解社会历史文化的必需工具。宗教研究的目的不只是在宗教本身,更重要的是透过宗教了解群众心理,了解社会历史文化,从而更好地把握宗教组织形态与社会动向。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应着重宗教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二者之间的镶嵌问题,而不是局限在宗教内部,因此要求观察宗教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去探究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第三,对宗教进行“去神秘化”的分析,尽量不涉及宗教的神秘经验或奇迹。把宗教表现出来的具体可观察的行为、可化为言语的述说都当作一般社会行为来分析,不强调其超感或超能的部分。神秘经验、奇迹或神话不会无中生有,必有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子,以之为线索,追究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第四,注意集体的宗教现象,而较少讨论个人的灵异感受或神秘经验,追究出其反映的大历史文化背景[5]。第五,“历史镶嵌”视角同时也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不但提倡横向的区域比较研究,而且也提倡纵向的历史比较。蔡彦仁指出,宗教现象学容易犯忽略历史承传、流变与宗教的比较的关系[6]。因此,应主张分析和比较宗教在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的源起及发展,分析其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7]。不同的宗教现象通过进行历史比较,来为宗教建立系统性(systematic)和一致性(coherent)的解释。
三、概念界定:“历史镶嵌”与宗教权威
所谓“历史镶嵌”(historical embeddedness),就是指社会历史文化禁止、限制或允许宗教徒及组织的行为逻辑和运行机制,为其提供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假设、正式规范系统或价值系统,指导与引领宗教徒的行为模式,使其分享共同的信念、价值、行为假设与互动角色,具有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因此,“历史镶嵌”是以传统和文化型态的形式呈现的。基于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往往发展出性质相异的宗教[8]。在每一宗教组织内,由于宗教行为是发生在历史文化背景或脉络中,因此,社会文化历史控制正在进行的宗教行为及过程。“历史镶嵌”强调宗教徒及组织与非宗教机构特别是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镶嵌关系,主张置于复杂的历史文化脉络下进行考量,体现其对历史文化的依赖性。
什么是宗教权威?以佛教为例,就是指佛教组织代表的神圣性或权威性程度如何,僧人是否被人们视为佛祖的侍者、服务人或代表,他们是否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组织的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如何?具体来说,宗教权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僧侣与住持等承担了专家权威的角色,他们都是专家,是对俗人作为宗教服务之有训练的仆人,在所有宗教中,执事人员均具有这方面的专家权威[9],并被期待为能代表佛陀与世俗进行沟通祈福的中介,从而满足社区成员的心理需求。其次,宗教权威是否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陈重成认为宗教权威与韦伯所说的科层化权威有很大的区别,宗教仪式的领袖权威不是来自官方的任命,而是源自传统文化价值的规范,以及个人魅力形象的建立[10]。换句话说,宗教团体之领导人物的克里斯玛魅力,在宗教的认同形式中是左右信徒选择信仰时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再次,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宗教领导人的非正式权力的建立(the making of informal power)与认可(recognition)均以宗教神圣性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宗教文化赋予宗教领导人地方社会中的“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村落中的宗教领袖的非正式权力型态都是“反馈型权力”。此外,佛教组织是否能借助佛教的威信,对社区情感、信仰和经济等方面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最后,佛教组织宗教权威是否由禁律隔离开并受保护,是否与世俗事务保持一定距离。
四、中国佛教:“历史镶嵌”中的宗教权威
从传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佛教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组织,它并没有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而是镶嵌于世俗社会中。余光弘认为寺庙是传统汉文化的“基象征”(key symbol)[11]。或者说,传统的历史文化镶嵌于佛教发展过程中。
首先,传统儒家文化的镶嵌使得中国佛教的发展具备了鲜明的特质。中国化的佛教组织的社会行动必然与社会历史文化相呼应,其行动方式与儒教伦理有着高度关联性。在传统社会中,儒教发展出一套地方性社会结构所接受的伦理。采用或是妥协儒家伦理价值,佛教才能向外传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受理性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不重视宗教,凡事从现实主义出发,注重客观实际,仅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只是对宇宙存在、祖先存在和神灵存在有一种信仰。其次,世俗权力的镶嵌也使得传统佛教组织具有弥散性特征。中国虽然存在着宗教,但是其形式与西方相差悬殊,它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也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属于典型的弥散性的组织特征,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杨庆堃为代表。他指出中国的宗教不是由于缺乏中心组织而退处社会从属地位,就是由于儒家政府非宗教性的控制与压迫而居弱势,没有一个宗教团体能够成功地与中国官僚政治抗衡[2]。再次,由于“大传统”的存在,使得佛教不得不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佛教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小传统”,依附于儒家“大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整体性的泛图腾体系(totemic system),而这个图腾体系又可区分为官方的或正式的“大传统”(great traditon),以及民间的或非正式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等两大体系。佛教文化是乡土社会中的一般民众的俗文化,与农民的文化和习俗密切相关,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而“大传统”是以传统社会上层阶级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取向的精英文化。“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存在着合作与一致的关系,在传统上,宗教与理性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从的运作关系,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中某些成份存在。在佛教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儒家与佛教彼此互相融合,与儒教有着高度关联性[12]。最后,宗教与道德的分离,形成了儒家与宗教之间的合作,但在某些时候二者也会存在相当尖锐的矛盾。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正统思想,因而无可避免地与如此遍在的宗教现象组成一种运作关系,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一套纯粹理性主义原则的体系。儒家反对佛教的理论一直都认为佛教割断亲属关系,逃避生产工作,这样会危及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组织、亲属系统与经济秩序的基础。
杨庆堃从组织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历史上中国宗教弱宗教权威的情况[2],首先,传统社会结构的镶嵌决定了宗教组织的弱宗教权威性。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组织中占据支配地位,宗教的影响深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但是由于中国宗教在组织上不能强固,其很难真正镶嵌于日常的权力结构之中。由此,在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中,儒家与宗教是形成一种主从关系,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国的混合宗教与特化宗教的组织特性。其次,中国宗教不是制度化宗教,而是混合宗教(除了中国的佛教具有混合宗教的特征外,最具混合特征的就是民间宗教了,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如此。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宗教信仰的形态是以混合宗教为主,也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因此大部分的信仰者在宗教的认同态度上通常是一种不明确的模糊态度[13]),或称为普化宗教与扩散宗教。混合宗教本身并未拥有独立的组织与人员,由于社会制度及其世俗权力的镶嵌而处于其控制之下。中国境内除去为数甚少的基督教与回教,其他重要的特化宗教都没有发展出有组织的僧侣集团及在信徒间有组织的教育或教区。寺庙间偶尔有地方性的联结,但它们没有超出地方性的教阶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并且在基本上仍维持每个寺庙的独立地位,佛教的高僧并不能领导全国境内的僧人或寺庙。正是由于中国宗教缺少独立的中央组织的僧侣集团与有组织的会众,使它无法真正镶嵌于社会组织的一般架构并占据任何重要的地位,从而使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与政治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再次,宗教在组织上的薄弱,使它深受中国社会制度镶嵌的影响并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配角,这是长期以来儒家与宗教合作的特性。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组织的薄弱,宗教在历史上将不会一直安于从属地位。佛教虽然是制度性的宗教,但是也具备了普化宗教所缺乏的独自存在。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由于古代佛教缺乏层级组织,所以不能产生对于理性教义学的一致关怀[14]。因此,佛教自南北朝入华至清代,由于国家权力的镶嵌和控制,从未发展出佛教自身的全国性宗教组织[15],由于佛教这种组织上的弱点,使其难以镶嵌在上层社会结构中,不得不处于从属地位,不能成为社会结构的支配性因素,佛教的这种组织特点也决定了其弱宗教权威。与佛教的这种组织涣散性和弱宗教权威相比,基督教则属于一种典型的建制性宗教,也是许多学者将它归结为基督教最为成功的地方。有一些研究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讨论基督教如何从无组织性、弱组织性走向强组织性,进而达到加强宗教权威的过程。如虞伯乐对台湾基督教聚会所的研究,他将“召会”的宗教活动内容分成“工作”、“教会”两个部份,透过组织发展过程的讨论,说明二者间关系的改变如何呈现了组织的科层倾向[16]。同时,基督教组织科层化也是建立在其组织文化的基础上,其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包含认同于组织所信奉的核心价值与信念相当高,更反映出成员对组织的向心力与忠诚度等文化面向上呈现出相当高与一致程度的组织文化[17],这不但加强了其组织性,而且也增强了组织的宗教权威。
在历史上,僧人依赖和借助世俗权威维持自身的发展。封建王权向寺庙御赐封号,使之成为代表正统思想意识的象征。社区关系和社区网络镶嵌在佛教领域中,尤其是社区精英或宗族势力的镶嵌,使得寺庙组织的生存、发展及运行都依赖于其保护。陈重成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以庙宇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基本上都是由村落中的士绅阶层所组成[10],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虽然普遍存在着宗教活动,但却缺乏社会组织形式的宗教,因此也没有产生固定的宗教团体,各种性质的宗教活动和民间寺庙的基本组织结构都是由于宗族组织及村落权力结构的镶嵌而纠缠不清,并成为宗族共同体的主要构成部分[18]也就是说,作为非宗教人士的地方精英镶嵌宗教并起支配作用,僧侣阶层则从之。
封建王权利用权力强制镶嵌寺庙管理,是出自游离于信仰系统之外的功利目的,是为其政治统治神性服务,根据政治目的,封建王权可以利用权力镶嵌对寺庙施加惩罚,甚至镇压宗教权威,民众也是功利性祈福消灾的心理。因此,中国宗教从来都不具有纯粹的超越性信念,世俗性的功利主义镶嵌其中。宗教组织是在国家政治和封建王权权力镶嵌和支持下而存在的,其在历史上的兴衰与封建政权的态度紧密相连。谢和耐指出,他们从自己的政策而给予佛教的支持和为寻求削弱佛教势力而进行的镇压便突出了佛教的弱势地位[19]。杨庆堃(C.K.Yang)也认为中国宗教组织薄弱的原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权力强制镶嵌与控制,几乎在每一个主要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宗教团体与世俗权力的竞争与冲突,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不清,世俗镶嵌并控制神圣领域。中国世俗权力强制镶嵌于宗教领域,并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控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重要时期曾有某个特化宗教不依靠世俗权威的镶嵌来提供庇护与支持,从而自己发展出一处坚强的结构地位。宗教能获得真正的权威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的宗教获得了社会的属性,从而成为社会历史力量的代表者。由于宗教组织在社区历史上没有取得支配性力量,在世俗权威的镶嵌和控制下,其不得不依赖于世俗权威,使之具备弱宗教权威的特质。
五、小结:“历史镶嵌”及其再思考
在历史上,佛教组织虽然也有神学和祭祀等宗教神圣性仪式,但由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强势镶嵌,并没有脱离社区世俗系统,其自身无法独立发挥作用,只能依托社区的宗族势力或世俗权威才能发挥其功能。佛教的宗教权威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与世俗权威平等的地位(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世俗权威也曾借助宗教权威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也曾大力提倡过佛教,如韦伯在研究中国宗教时,认为中国的皇帝就像是最高层的僧侣,如同父亲在家庭里,于血缘基础上反而进一步拥有了宗教资源,以确保其世俗权力的正当性[20],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工具性利用关系。由于儒教与佛教、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对立,佛教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宗教权威难以真正镶嵌世俗领域并占支配地位,反而是世俗权威镶嵌并控制宗教领域。不像中世纪西欧,曾经存在着神权高于皇权,宗教权威高于世俗权威的现象。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世俗权威的强力镶嵌,宗教权威不得不依附于世俗权威,其需要在世俗权威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古代的僧侣虽无自发的全国性组织,但国家为方便管理僧侣,却设有僧官制度,亦即将僧人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内,朝廷倡行封赠之风[21])。可以说,“弱宗教,强政府”或“强社会,弱宗教”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特点。其次,社区精英或家族势力的镶嵌,也使得寺庙组织具备了弱宗教权威的特征。在社区的历史上,宗教权威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要素,它的形成、积累和运作都深深镶嵌于社区网络中,只有依托于这种社区网络,宗教权威才能够正常运转,才能发挥正常功能。离开了社区网络,其宗教权威就会迅速下降甚至消失。最后,寺庙组织在社会基层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相对较低,其不能独立于基层网络之外,也不能成为社区秩序的支撑和控制力量,对社区影响的功能有限,寻求地方势力和世俗权威的保护的行为取向在历史上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不仅历史镶嵌与中国宗教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西方也同样如此。西方学界有很多探讨宗教如何受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变迁的影响,尤以韦伯“除魅化”理论相当具有代表性。韦伯认为一部西方近代史其实就是一个理性化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所带来的不但是一个不断除魅化的世界,并且也造成了“意义的丧失”,而在过去,意义的给予却是宗教对人来说的最重要功能[22],这也导致了宗教权威的降低。
宗教历史虽然一经发生便走向历史的后台,但其内在张力却持续存在,并可能在后继的历史路径中被重写和强化,也就是说宗教组织行为不可避免镶嵌于传统中。佛教的宗教权威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外,信徒集体行为背后的宗教历史文化基础仍然非常重要的[23]。过去的宗教行为对现在和将来的宗教行为产生影响,形成独特过程及机制,历史和传统所塑造的宗教行为具有一种“惯性”,为现实宗教生活行为制造出一种依赖结构,历史和文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决定着现在或将来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