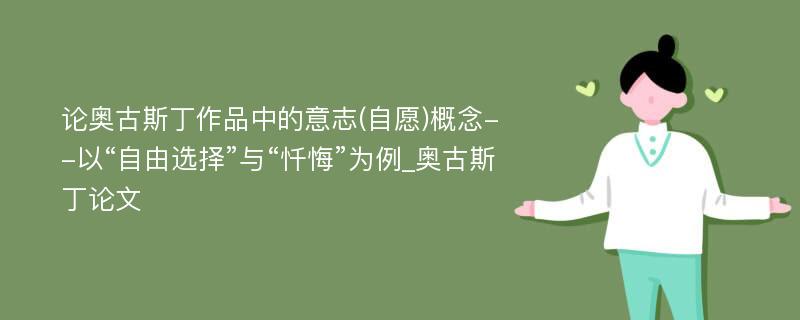
试论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意愿(voluntas)概念——以《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忏悔录论文,为例论文,意愿论文,自由选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3.1 文献表示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5)03-0112-13
导论:意愿概念的发明
“意愿”这一术语在近世特别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对道德行为的解析中作用显赫。 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者很自然地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谁首先发现了意愿?现代研究者通常 认为意愿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中不占显要地位,奥古斯丁才是“第一 位意愿哲学家”[2](PP.85-110);[3](P123)。然而在近年关于意愿概念的发明的讨论 中,不少古代哲学研究的学者坚持认为,尽管希腊哲学中不包含现代的意愿概念,但他 们的行为理论已经涵盖了近世哲学归于意愿主题的领域。诸多奥古斯丁之前的哲人被推 举为意愿的发现者,包括柏拉图[4](PP.146-152),亚里士多德[5](PP.453-473),斯多 亚派的克里斯普斯和波塞东尼乌斯,柏拉图派的盖仑[6](PP.107-145),伊壁鸠鲁和卢 克莱修[7](PP.353-362),斯多亚派的塞涅卡[8](PP.17-35)和埃比克泰特[9](PP.234-2 59)。
然而,在意愿概念的历史演进中,重要的不仅是谁首先发明了这一概念,而是我们为 什么需要或者至少是曾经需要这一概念。后者在当代英美心灵哲学对意愿概念合理性的 抨击中尤显紧迫。Gilbert Ryle在《心的概念》一书中强调,意愿概念纯属人为虚构,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意愿来描述和分析道德行为[10](P62)。首先,奠基于意愿概念的灵 魂三重构成学说(思想/感觉/意愿)并没有经验根基;其次,我们不能够见证他者的意愿 活动(volitions),我们也不能裁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评判是否以其意愿活动为根基; 此外,用意愿概念解释人的自愿行为(voluntary actions),我们总要追问意愿活动自 身是否自愿行为,这就隐含了无穷倒退的危险;而且,灵魂三重构成论只是一种解释心 灵观念的“准机械论”主张(a para-mechanical theory):意愿活动的学说乃“机械身 体中的幽灵”这一神话不可避免的延伸,二元论者需要意愿概念来联结身体和心灵。简 而言之,意愿这一技术化概念奠基于对心灵和身体的机械化读解之上,毫无实际意义和 价值可言[10](PP.61-80)。
当我们潜入意愿观念形成的历史迷宫时,我们必须面对Ryle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我们 不仅必须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演进以及谁在其发展历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要阐明 为何这样的对意愿的解释是理解道德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对我们更加重要的是和意愿观 念紧密关联的对人的生存的深刻洞见。本文将试图论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旨趣引领 着奥古斯丁赋予意愿概念以显赫地位,以此解释人对恶行的责任。奥古斯丁坚持意愿作 为独立的心灵能力(faculty)乃是我们外在行为自愿性(voluntariness)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观点使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明显地区别于其古希腊和罗马的先行者。而且,在意愿 概念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发展了对人的自由的深刻理解,由此而来对人的生存不同于希 腊罗马理智论(intellectualism)的观照。通过对奥古斯丁在《论自由选择》和《忏悔 录》二书中意愿理论的重构,我将指出奥古斯丁对意愿的现象描述和深入分析将供给我 们足够的材料以回应Ryle的尖锐抨击。
首先,对本文选材的一点简要说明。《论自由选择》是奥古斯丁最重要的哲学论著之 一,通常被视为其哲学摆脱希腊罗马和摩尼教二元论影响的转折点[11](P114)。该文聚 焦于意愿的自由选择,详尽地阐释了意愿和恶的起源的内在联系。在其著名的自传《忏 悔录》中,奥古斯丁生动地描绘了恶的起源问题如何使其最终转向基督信仰。它特别提 供了对意愿相互交战这一现象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诠释,这最为突出地彰显了奥古斯丁 意愿理论的原创性。正如阿伦特所论,在奥古斯丁的意愿哲学中,《论自由选择》最具 论证性,而《忏悔录》则富于现象描述[2](P93)。当然,奥古斯丁对意愿观念的反思贯 穿其一生,尤其是在《三一论》,《上帝之城》和晚年批驳裴拉基派的著作中,但革命 性的转变已经出现在这两部相对早期的著作中。以上构成本文选题的基础。
在检视奥古斯丁对意愿的原创理解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澄清意愿概念在希腊罗马哲学 中的发展,这构成了奥古斯丁思想不可脱离的历史语境。
一、希腊罗马哲学中的意愿观念(存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3对hekousion和proairesis的分析
2.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与自由意愿问题
3.塞涅卡论善意(bona voluntas)和高尚行为,voluntas和激情的起源
4.埃比克泰德的proaihesis
二、《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中意愿概念(voluntas)的语境(存目)
1.《论自由选择》概述
2.恶的起源问题和奥古斯丁的最终皈依(《忏悔录》卷1至卷8)
3.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神学语境:恶的起源和意愿的发明。
三、作为心灵独立能力的意愿
1.意愿作为心灵独立能力的提出
上述两部作品相关论证和叙述的概述清晰地显示出奥古斯丁的意愿概念的神学背景。 奥古斯丁极度敏感于恶的现实性和强大力量,对信仰的执着驱使着他不断地去反思恶的 现实对作为至善的上帝的威胁。神正论的问题贯穿奥古斯丁对意愿和自由选择的反思。 在此需要突出的是,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的神学关注引导着他去发现独立于欲望和理智 之外的另一种灵魂能力:人的意愿。
如上所述,奥古斯丁对自由选择的反思开始于将恶区分为罪和惩戒。如William
Babcock极富洞见地指出,这一区分使奥古斯丁得以重思恶的起源问题:“在这一新形 式中,问题不再是和谐宇宙中恶的在场,而是有关道德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一方是 犯罪的人,一方是正义的上帝。”[12](P236)对奥古斯丁来说,如果罪行不是出于意愿 ,那对它的惩戒就绝无正义可言[1](Ⅰ,1,1)(注:本文中奥古斯丁著作引文按照卷、章 、段落的顺序标注。因条件所限,引文未能参考现有中文译本,概由作者参照相应的英 文译本从拉丁文译出。具体版本见参考文献。)。在《忏悔录》卷2对幼年盗梨罪过的反 思中,奥古斯丁同样强调正是自己对恶行快感的扭曲的迷恋决定了这一行为的自愿性因 而成为可归罪的。奥古斯丁将形而上学的恶的问题转化为生存论的罪的问题,同时突出 道德行为的自愿性特质,然而,这些恶行如何本质上归属我们而被称为自愿的,这驱使 着奥古斯丁给出一个生存论的和道德心理学的解释。与之相应的是,希腊罗马哲学家总 是把恶设想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他们极力将恶行的根源追溯到无知,从而使人或者至 少是智者作为理性动物能够免于其咎。恶对奥古斯丁来说首先是我们生存的有机构成。 人作为罪者必须为其自愿的过犯负责。
因此,恶的自愿性带给奥古斯丁这样一个问题:灵魂的何种能力(faculty)乃是恶的源 泉?一方面,奥古斯丁不可能接受感性或者身体欲求作为恶的原因,因为它们不可规避 地或者说必然地降临在我们身上。同时,这些自然能力由上帝所创造,我们在归罪它们 的同时也就否认了上帝的全能和至善;另一方面,恶的起源不可能是理智。因为理智或 者正确理性(recta ratio)乃是尘世中最高的善,它自身不可能被误用。“无人用正确 理性为恶”[1](Ⅱ,18,50),这就意味着必然存在着不同于欲求和理智的另一种灵魂能 力,人们因对它的误用而被归罪。这一能力确保了人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中选择和成为其 自身的自由。只有在这一自由的基础之上,人才成为了他所选择的恶行的主体,亦即罪 者。这一能力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被明确地命名为voluntas。当然,意愿的独立性在此 只是作为他对恶的神学反思的未加论证的必要假设,我们还需要通过澄清其著作中意愿 和欲望,意愿和理智之间的内在关系重构其哲学论证。
2.意愿和欲望
奥古斯丁强调意愿是恶行的唯一源泉。然而,在《论自由选择》中,贪欲(libido)或 可谴责的欲望也被建议为恶的原因。在《忏悔录》中,依照圣经传统,奥古斯丁也强调 大部分恶行起源于三重贪欲:亦即对统治权的贪欲,眼睛的贪欲和肉体的贪欲[13](Ⅲ,8,16)。恶的起源在此被还原为欲望而不是意愿。同时,奥古斯丁强调当我们有对正直 和崇高生活的欲望,我们也就有正当生活的善的意愿。善的意愿同样与可称颂的欲望亲 密相关[1](Ⅰ,12,25)。
我们确实很难区分意愿和欲望在我们行动前道德抉择中的功用。首先,这一问题事关 我们行事前的心灵状态(affectus animi),特别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动机。然而,我们的 欲求或者意向都是内在的,外在于我们的他者并无可能进入我们的灵魂加以察看。他者 可见的只是作为我们内在心理过程的结果性表现,亦即公开行为。这一行为完全可能不 忠实于我们的灵魂而扭曲了心灵动机向他者的呈现。奥古斯丁同样敏感这一困难:“常 常公开表现的行为是一样,做它的人的心灵状态(animus)又是一样,或者那转折的关键 时刻不为人知。”[13](Ⅲ,9,17)
只从外在的公开行为的视角出发,确实不易判定什么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特别在我们的行为的冲动如此强烈而相应的行为接踵而至时,没有任何时间的空隙可供 我们反思。就我们外在行为的本性而言,它起源于即时的冲动还是灵魂屈从于较低的欲 望的结果,并不会造成本质性的差别。或许将它归咎于欲望或者冲动更加简单明了,如 同当代英美的行为理论所倾向的那样。因为当贪欲如此强大,我们不加犹豫地就将其付 诸行动,这一贪欲看起来更像我们道德决断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场合中,强制性的 欲望驱使着我们为它的实现效力。人的行为和欲望的紧密衔接几乎没有给意愿留下任何 空间来表达它对我们的冲动的态度。至少,在公开行为的层面,我们经验不到意愿作为 心灵独立力量的功用。经验性的直觉使我们把外在行为直接地不加中介地和欲望的强力 和迫切性联系起来。这正是Gilbert Ryle强烈地反对把意愿作为独立能力或者引入意愿 行为(volitions)的主要原因。Ryle指出意愿作为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的联结点的存在 毫无经验根基,一个人永远不能见证他人的意愿。Ryle因此认为我们毫无必要用这样一 个隐蔽的意愿去描述公开的道德行为。他更进一步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未提及意 愿性和意愿这一能力[10](PP.61-80,esp.64)。基于Ryle的这一论述,在阐释奥古斯丁 的意愿概念以回应Ryle的驳斥之前,我将对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卷3中对行为起源 的著名论述作一简要评述,这将帮助我们澄清引入意愿概念的必要性。
亚里士多德很清楚营养能力,感觉或是思辨理智都不是行为的原因。相反,行为是由 欲望所决定的(kata ten epithumian),特别是对不节制的人而言。然而,节制的人尽 管感受到了欲望的冲动,却不按欲望所提示的行事,反而服从于理智的判断。亚里士多 德由此得出结论:实践理智和欲望乃是行为的动因[14](Ⅲ,9432b14-433a14)。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止步于此,他观察到理智并不能离开欲求而引发运动。理智的 行为可以追溯到理性的欲求(boulesis),它同样是欲望。很显然,欲望才是行为最终的 单一原因[14](Ⅲ,10,433a22-433b1)。然而,这一强势论断必然面临这样的难题:在亚 里士多德对节制和不节制的分析中,非理性的欲望对立于理性的欲求。什么因素决定了 一个欲望比它的对立面更强?(注:亚里士多德只是提及了这一困难,并且强调从数量上 说行为原因存在多元性,而从根源上说行为原因则是单一的(《论灵魂》Ⅲ,10,433b1 0)。他并未进一步讨论如何解决不同行为原因的相互冲突。)如果这只是由欲望自身的 强度和紧迫性所决定的,如亚里士多德所暗示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并不能对由欲 望所主导的行为主动地有所贡献。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欲望能力如同感知能力一样 ,总是由某个可欲望的对象所唤起并指向这一对象[14](Ⅲ,7)。因此欲望的出现以及它 的强度都完全依赖于这一外在的对象因而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没有力量去召唤某 一欲望的出现也不能根除心灵中呈现的某一欲望。因此我们的心灵就成为不同欲望的战 场,而我们则不过是这些强有力的自然倾向的玩偶。人的行为主体性和自主性无法扎根 于亚里士多德以欲望为行为唯一动因的论断。当我们将这一心理分析推及道德行为领域 时,这一理论的严重后果更为明显:如果一切行为从根源上说来自不依赖于我们的自然 欲望,我们就无需对我们在欲望冲动下无可避免的行为负责。因为所有在这一情形下的 行为都是违愿的相应地也是可宽恕的。
我们由此回到奥古斯丁对意愿和欲望的关系的阐释。他非常清楚对公开行为的心理解 释的困难,他也熟悉欲望特别是诸如性冲动这样的非理性欲望的强迫力。然而从一开始 ,奥古斯丁就拒绝接受欲望或者冲动作为我们决意行为时的决定性因素。在《论自由选 择》中,在暗示了libido或者cupiditas作为恶行的统治性因素之后,奥古斯丁随即指 出这一解释并非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有说服力。因为当一个奴隶出于不在恐惧中生活的欲 望而谋杀了他的主人时,奴隶的欲望自身无疑是善的。如果欲望在此作为谋杀行为的唯 一动因,去惩戒这一明显邪恶的行为在道德动机上就毫无根据可言。同时,上述亚里士 多德的解释也使得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在其根源上无法区分,因为对不在恐惧中生活的 欲望既可以出自善人,也可以出自恶人。这显然是奥古斯丁难以接受的后果,它驱使着 奥古斯丁转向灵魂的其他能力来区分善恶行为:“然而差别在此:善人如此追求它(案 :指不在恐惧中生活),他们使自己的爱远离那些在拥有时总有失去危险的事物。而恶 人,则竭力铲除一切障碍以便他们能够安全地享用这些事物,由此过上充满邪恶与罪恶 的生活,这或许更应被称作死亡。”[1](Ⅰ,4,10)
在此重要的是面对同一欲望的不同态度。而奥古斯丁强调:“除了心灵自身的意愿和 它的自由选择,没有什么能使心灵与贪欲携手。”[1](Ⅰ,11,21)正是意愿的错误态度 或者选择使得自然而中立的欲望成为可责备的。相应地,奥古斯丁强调所有人都欲求或 者选择(velle et optare)幸福生活,但并非所有人都意愿正当地或者高尚地生活。“ 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欲求是一件事,通过善的或者恶的意愿而应得某物是另一回事。”[1 ](Ⅰ,14,30)对奥古斯丁来说,光有对幸福生活的正确欲求是不够的,只有借助善的意 愿和对这一欲求的正确对待,人才可能获得其应有的幸福。
很清楚,在奥古斯丁看来,不是欲望自身而是我们对这一自然倾向的同意或者异议决 定了我们行为的道德特性。奥古斯丁论证道,不论我们的欲望多么强大而具有压迫性, 我们总是可以对这些倾向和冲动说“是”或者“不”,因为我们总是有能力不按我们即 时的冲动或者反应行事。正是意愿的认同或者决定表达了我们对由欲望所触发的行为的 贡献,也就是由欲望而来的行为中的道德主体性。只有在这一内在的自主的认同行为的 基础上,相应的公开行为才可以被称为我们的行为。因为“如果我接受或者拒绝可选择 的对象的意愿不是我的意愿,我再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称为我自己的”[1](Ⅲ,1,1)。 在此,选择的对象正是欲望的冲动或者暗示,而意愿的接受或者弃绝则使我们的行为成 为我们自愿的举动,我们也因此而必须为相应的公开行为负责。
在上述论证中,欲望和意愿的区别首先可以通过对象的不同来确定。欲望由外在对象 唤起并且朝向这一对象,欲望朝向“那些我们可能违愿地失去的东西”(quas potest
quisquie invitus amittere)[1](Ⅰ,4,10)。与之相对立的是,意愿的对象只是意愿行 为自身。拥有一个善的意愿只需要去意愿它[1](Ⅰ,12,26)。相应地,欲望的出现和满 足总是超出我们的控制,而没有什么比意愿更在其自身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欲望自 发地无可规避地出现,而意愿则自主地自愿地表达着自身。因此,我们才常常被称作欲 望的奴隶,而意愿则使我们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
人的举止的道德特性要求意愿这一能力及其选择独立于欲望而成为我们道德行为的决 定性心理因素。诚然,我们并不能直接通达欲望和意向的内在世界,如Ryle所坚持的那 样,我们也没有对意愿存在的直接见证。然而,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责任提供了我们线索 去反观抉择时刻的心理过程。
前述对意愿和欲望的分析中,欲望这一能力被假定为完全不由我们控制的自发冲动, 这暗示了意愿对欲望的认同或否弃发生于欲望之后而且显得全然孤立于欲望。根据这一 观点,欲望或者激情的整个形成过程就被认定为我们被动地违愿地承受着的过程。由此 ,欲望也就和道德责任全然无关。如此我们就难以理解奥古斯丁为何谈论“可责难的欲 望”,“僵死灵魂的激情”。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欲望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通过 对欲望或者激情本性的细致考察,来捍卫意愿能力作为自愿性和道德责任的唯一根其这 一论断。
在第1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强调激情同样可以被给予颂扬或者责难。 然而,他没有给我们对非理性欲望的道德责任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15](1111a25-1111b 3)(注:参本文第1章第1节。)。塞涅卡以愤怒为例细致地分析了激情的起源。他强调尽 管最初的具有推动性的印象是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的,但是愤怒这一激情绝非不包含 意愿行为的纯粹冲动。当然,在塞涅卡的哲学中,意愿意指理性的认同,它跟随并且服 从于理性的判断[16](P2,4,1-2)(注:参本文第1章第3节。)。奥古斯丁对激情的理解深 受塞涅卡影响(注: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情感和激情进行了更加广泛深入地讨 论,相关论述可参加该书第9卷和第14卷。本文将讨论集中在这两部相对完成较早的著 作。),但他最终突破了理智论的传统,强调正是意愿对最初冲动的认同或者否弃决定 了欲望和激情成为可责备的。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宣称,“败坏的意愿的后果就 是贪欲(libido)”。对奥古斯丁来说,在此发生作用的不是理智推理的错误,而是一意 孤行的意愿的认同,它的选择独立于欲望和理智的暗示或者建议。
在对登山宝训的评述中,奥古斯丁更加形象明确地描述了欲望的形成:首先是自然的 不顾意愿的某种暗示(suggestio),这等同于塞涅卡的最初冲动;随后这一暗示给与我 们强烈的快乐(delectatio)。最后我们赞同(consentio)这一快乐[18](P12,34-35)。在 这一过程中,尽管激情最初状态中的自发的反应不依赖于我们,在激情完成之前,我们 总是能自由地接受或者拒绝这一自然的暗示。
这一欲望解释的要点在于:接受或者弃绝的决断甚至在欲望在我们的心灵中成形前就 已经发生了。这就意味着现实化的欲望(并非最初的自然冲动)已经包含了意愿的赞同。 不可驾驭的激情自身就是可责备的,即使它没有最终触发相应的行动。奥古斯丁强调, 那想要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却没有机会去做的人并不比那实际做了的人罪过更少。这一对 未能实现的邪恶意向的道德洞察充分显明了,即使是对欲望自身的意识就已经包含了可 责备的意愿的认同,因为在我们的意愿自愿地使这一欲望成为现实行为之前,他已经赞 同了激情最初的暗示。在奥古斯丁的眼中,我们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激情的撞击,因为 自然冲动的暗示的现实化需要意愿的赞同,后者无疑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内的(注:当然 ,奥古斯丁也很明确意愿在自然冲动的强大暗示之前的软弱。他强调人生而在无知和困 苦中。然而,这最初的处境并不能取消人通过意愿的认同而实现的自由选择。这一论断 将在后文对奥古斯丁自由观的讨论中得到印证。)。
由此我们可以为奥古斯丁在这两部著作中有关意愿和欲望关系的论述作一小结:第一 ,意愿能力独立于欲望的强迫力。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地见证心灵的这一内在力量,但人 类公开行为的道德属性揭示了意愿运作的独立性。第二,意愿能够在最终决定行为之前 反观并且评估自然冲动的暗示。第三,意愿作为道德主体的认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主动 特性。并非欲求,而是意愿才是我们公开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最后,甚至欲望自身,当 他被我们的心灵所确认时,它已经包含了意愿的赞同。因此,意愿能力并不孤立于自然 冲动,它和我们自发的反应交互作用:意愿面对着自然冲动的强迫力并且使它现实化为 朝向外在对象的激情,我们没有纯粹自然化的欲望,在我们心灵中呈现的总已经被意愿 所认同。
3.意愿与理智
现在我们转向意愿和另一灵魂能力理智的关系,奥古斯丁对其皈依基督信仰的现象学 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二者相互作用的生动样本。在《忏悔录》卷8中,奥古斯丁承认柏 拉图派的思想已经帮助他逐步了解上帝的非物质本性和绝对的善。他不再是空虚的人, 对上帝毫无所知[13](Ⅷ,1,2)。正如《忏悔录》的法文评注者所强调的,朝向上帝的“ 理智的皈依”(la conversion intellectuelle)已经发生在《忏悔录》卷7中他对上帝的柏拉图式的解读中[19](PP.82-84;P139)。这一理智的皈依使奥古斯丁更加确信上帝的存在及其精神性本性。然而,这一理性知识的确定性却不足以使奥古斯丁全心地热爱并分享上帝[13](Ⅶ,20,26)。他引述福音书来描述他的迟疑不决:“我已经发现了美丽的珍珠。要买他我必须卖掉所有的一切,因此我犹豫了。”(注:《马太福音》13:46,引自《忏悔录》Ⅷ,1,2。)对奥古斯丁来说,这一迟疑并非理智做出错误判断的失误,而是意愿在面对已为理智所知的正确号令之前的软弱。在此,我们见证了意愿这一能力的运作独立于理智的能力及其理性判断。理智的判断使奥古斯丁确认上帝作为非物质真理的本性,然而,意愿却对这一有说服力的论证说“No”,甚至试图把它从心灵中清除掉[13](Ⅷ,7,16)。在这一迟疑中,意愿的意向和理智的命令相对抗。尽管理智有能力发号司令,但却不足以决定人的行为,因为意愿可以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注:在后文对奥古斯丁有关意愿自身间的冲突的评述中,我们将证明意愿本质上自由地免于一切强迫力,即使是理智的命令。)。对奥古斯丁来说,人的行为唯一必要的条件是拥有全心的意愿:“那唯一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不仅要走向彼处而是确实地到达彼处,正是要有去走的意愿,并且这一意愿是如此地强大而绝对(fortiter et integre),而不是那些半心半意的意愿(semisaucia voluntas)时而扭向这边,时而另一边,在部分上升和部分坠落中挣扎。”[13](Ⅷ,8,19)
在《忏悔录》卷8中奥古斯丁详尽地描述了两个不完全的意愿交战的现象以及它神秘的 解决。奥古斯丁对基督信仰的最终认同也相应地被称为道德心理的皈依或者是“意愿的 皈依”[20](P47);[21](P8)。在奥古斯丁自身的皈依体验中,理智的运动只是为意愿 的决定性转变铺平了道路。理智的活动固然可以供给心灵相关的观念和判断,但对这些 观念和判断的认同或者弃绝,它却不是理智而是意愿的事务。
在奥古斯丁对其生命中最紧要时刻的心理分析中,显然理智能力不足以决定意愿的取 向,也不能独立于意愿的认同而决定他的行为。这一和斯多亚传统截然对立的论点,同 样可以在《论自由选择》中得到确认,尽管某些论者认为这篇作品带有强烈的斯多亚派 印记[8](P31);[22](PP.49-68)。在奥古斯丁对人类始祖堕落前的初始状态的分析中, 他强调人类始祖接受了理解号令的能力,但却不能服从它。在此,奥古斯丁明确地区分 了理性和智慧(ratio et sophia):“理性的(也就是说能思考)是一回事,而智慧的却 是另一回事。借助理性,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号令,服从信仰的首要责任,由此他能够履 行它所被命令的事务。正如理性的本性在于理解号令,去服从这一号令乃是智慧的本性 。无论那理解号令的心灵能力的本性是什么,实行他们的乃是意愿。”[1](Ⅲ,24,72)
对奥古斯丁来说,理性,或者理智能力不足以使号令现实化,在原罪中,亚当能够理 解来自上帝的号令,但他却未能将其付诸行动,这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智慧,也就是说他 还没有去服从它的正确意愿。理性知识的真理并不能确保意愿的正确。因为理性能力只 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却不能确保我们如此去做就能够达到幸福生活。从另一 个角度看,意愿的同意或者异议总是独立于对号令的认知。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亚当 总是能自由地接受或者拒绝律令,而只要他意愿,他就拥有去服从律令的能力。因此, 亚当要为他自愿的选择导致丧失了服从律令的能力而被责难。奥古斯丁强调通往或者离 弃智慧的行为总是包含了意愿的决断[1](Ⅲ,24,73)。正是意愿能力赋予我们去正当地 幸福地生活的智慧。
当然,没有理智对神圣律令的理解,去服从这些律令的正义行为也无从谈起。奥古斯 丁从未否认这点。然而,在上述伦理语境中,更重要的显然是运行于决断时刻的我们的 实践智慧,而不是思辨理性,后者以理性判断的形式结束并且等待着意愿的赞同。因为 ,我们不能够靠着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及其实现条件而变得幸福。对此世的人而言, 更重要的是实际地获得幸福。只有实践智慧能够使我们下定决心去现实化与幸福相关的 欲望和判断。
奥古斯丁强调在决断的时刻,意愿总是有能力不按理性慎思(deliberation,
proairesis)所要求的行事。这一观点可以从他自己的皈依经验中导出,而在《论自由 选择》中,奥古斯丁则给出更加形而上学的论证。在该书卷1和卷3中,奥古斯丁强调, 心灵不可能成为贪欲的奴隶,除非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他给出了如下的论证:首先, 低于我们心灵的,比如说身体,它能力应当更弱不能够征服理性的心灵。其次,如果另 一个心灵像要强迫我们去做恶,这一邪恶的心灵自身已经在恶的混乱中变得比那受强迫 的无辜的心灵要虚弱。最后,那高于我们理性心灵的必然是无比地正义和有序,它比心 灵更强但他不会强迫心灵服侍贪欲,因为这显然是邪恶的不义的行为[1](Ⅰ,10,20-1,1 1,23;Ⅲ,1,2)。
奥古斯丁的论证奠基于如下形而上学假定:存在者有着客观的秩序而且价值内在于世 界之中,因为世间的一切必然要最大限度地被秩序化。奥古斯丁将这一秩序命名为“永 恒律法”(aeterna lex)。同时,他将这一存在和善的等级秩序发展成为能力的等级秩 序。“因为如果弱者能够号令强者,这个世界的秩序就不是最卓越的。”[1](Ⅰ,10,20 ;[21](P76)能力在此乃是回应善的能力,因此更好的或者说更善的必然更有力量。这一 形而上学或者存在论的假定确保了心灵的转向贪欲并不受到任何外在的胁迫。我们可以 将这一能力秩序原则推广到内在的心理过程,以此捍卫意愿的独立性。在心灵自身内部 ,理智或者正确的理性,它从不可能被误用,无疑是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心灵能力,因 此它也不会强迫意愿为恶。另一方面,贪欲或者欲望依照永恒律法乃是在心灵的控制下 ,由此欲望也没有能力强迫意愿去对抗自身。最后,邪恶的意愿要比无辜的意愿虚弱, 前者显然不能强迫后者向更低的贪欲屈服。甚至意愿自身也不能够强迫一个意愿去为恶 (注:后文对奥古斯丁意愿冲突论的讨论将应证这一论断。)。按这一逻辑,我们就能证 明在恶行中,意愿的运作独立于外在和内在的胁迫。
以上是奥古斯丁在传统的等级秩序的形而上学中捍卫意愿独立性的努力。这一努力在 对恶的意愿的解释中尤为得心应手,它的产生显然独立于理智的判断。但在对朝向幸福 的善的意愿中,这一形而上学解释将面对极大的困难。在这一情形下,当理智强迫着我 们的意愿朝向永恒的善时,理智自身仍然保持其善的本性,这大概也是希腊罗马理智论 者使善的意愿(bona voluntas)屈从于正确理性(recta ratio)的根由。由此,奥古斯丁 有关意愿和理智关系的观点还必须在对善的意愿的分析中更深入地展开。
在《论自由选择》有关善的意愿和幸福的论证中,奥古斯丁提供了对意愿能力和理智 能力关系的更为生存论的解释。首先,奥古斯丁坚持幸福乃是人的属己的同时也是首要 的善,然而这一至善只需要保持对永恒的善的善的意愿就可以实现[22](PP.61-63)。凭 借善的意愿,我们就能够过上值得赞颂的有德性的生活。按照奥古斯丁的解释,这一生 活就等同于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所热爱的不会在违背意愿地情况下被夺走。他强调, 幸福的人必然是对其自身善的意愿的爱者[1](Ⅰ,13,28)。然而,意愿能力完全依赖于 我们自身:要拥有善的意愿只需要去意愿它。意愿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意愿自身[1](Ⅰ ,13,27)。意愿本质上的属己性将幸福的抽象观念转化为人的生存状态。“正是依赖意 愿我们应得并且过上受颂扬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依着意愿我们应得并且过上耻辱的不 幸生活。”[1](Ⅰ,13,28)奥古斯丁将这一观点推进到这样一个层次,没有任何正义的 行为可以在排除意愿的自由选择下实现。这也正是上帝将意愿能力赐予人的缘由[1](Ⅱ ,18,47)。只有最为个人化的意愿行为使我们的心灵适合永恒的律法规则和德性的要求 ,我们也因此而被称为我们的德性的主人。
由此我们回到意愿和理智这一论题。正如奥古斯丁指出的,理智的对象乃是真理,它 向一切人开放并为一切人共同拥有,绝非任何人的私有财产[1](Ⅱ,14,37-38)。不同心 灵的理智活动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并且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同一对象。我们理智行 为的方式本质上由它共同的对象所决定。因此,在幸福这一案例中,对某一对象本性的 理性知识并不能将这一最个人化的善带给我们,因为有关真理的知识作为共有物向所有 人开放,它并不能确保我们个人对它的认同。如果知识强迫着意愿朝向它的对象,也就 是朝向共有的永恒的真理,意愿的自愿性和个人化的特性就会被完全毁坏。这就必然意 味着即使在理性的迫使下朝向永恒的善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善,它却绝不是 我自己的善。在这一情景下,我的决断不再是意愿自由的认同,也就不再是“我”选择 使自己的心灵适合永恒的善。我们不能从这一强迫的行为中获得颂扬,即使它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由此结论,在善的意愿中,意愿这一自由能力的发生效用同样独立并且面于 理智的强迫。
上述分析很容易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奥古斯丁认为voluntas这一心灵能力远远高 过其它,而成为呈现在一切事件中的原初性力量。或者更直白地说,相对于希腊罗马的 理智论传统,奥古斯丁的voluntas更应当被称为唯愿论的(voluntaristic)[8](P18)。 然而奥古斯丁自由哲学的重要评述者Mary T.Clark坚持认为奥古斯丁是被不恰当地称为 唯意愿论者,因为他从未将现实世界还原为意愿,也没有使人的意愿对立于理智或者是 高于理智。前面的分析着重强调了意愿的独立性,在此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意愿和理智的 内在联系。
对奥古斯丁来说,理性或者理解力乃是人最卓越的能力,它使人和野兽区别开来[1]( Ⅰ,7,16;Ⅱ,6,13-14)。相应地,这一能力必然在我们的行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于动物 本能的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性行为必然包含了理智的活动。奥古斯丁也强调 当我们渴望幸福生活时,我们的心灵总已有了幸福的某种意象。“因为我们一无所知的 ,我们不会爱它。”[13](Ⅹ,20,29)或者更明确地,“如果我们不是对它有确定的知识 ,我们就不会意愿坚决地欲求它”[13](Ⅹ,21,31)。意愿的决定,特别是与幸福生活紧 密相连的善的意愿总是伴随着对我们目的的理性知识。在《论自由选择》中,奥古斯丁 将恶的意愿描述为和世界秩序相对立的对尘世之物的错误的爱,而善的意愿则是服从永 恒律法合于秩序的正确的爱。当我们拥有这一善的意愿时,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永恒律法 。对奥古斯丁来说,人的意愿并非全能无上的,我们只有接受或者拒绝我们所“见”的 能力。然而我们的意愿能力无力决定什么能被我们的理智所见[1](Ⅲ,25,74)。
意愿并不孤立于理智,而是和它交互作用,正如意愿和欲望的关系。首先,没有意愿 提供认知的动机,我们的理智行为就没有可能。意愿使我们的心灵能够专注于知识的对 象。另一方面,没有必需的观念和对行为目的的慎思,意愿就是盲目的,也很难同自然 反应相区分,因为自然冲动的暗示在此将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对象。最后,最终决断的 权力本质上归属意愿能力,因为意愿总保留着不按理性建议行事的能力。更进一步,正 是意愿的这一自由认同将我们的行为内化为我们作为特定个体的行为。因此,意愿在我 们的抉择中乃是本质的和决定性的,而对世界秩序的理性知识特别是对爱的对象的知识 同样也是我们的自愿行为所必需的。完全无知的情形下的行为不能够被称为自愿的或者 是我们的行为。同时,善的意愿总是和理智的号令相一致的。
由此,我们论证了意愿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中的独立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尽管意愿的功 用和其他心理能力亲密连接,意愿的独立性也引入了对自由的全新的独到的理解,这也 使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迥然相异于其他古代哲学家。
四、意愿与自由
在对希腊罗马哲学中意愿概念发展的重构中,我们已经看到意愿的本质同自由观念内 在相关。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中,“voluntas”,“proairesis”等与意愿 相关的核心观念都被认为是确保人的心灵免遭外物搅扰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正如埃比克 泰德所强调的,“如果你意愿,你就是自由的”[23](Ⅰ,17,28)。意愿(proairesis)使 人免除了奴役和屈从[23](Ⅱ,10,1)。奥古斯丁对意愿观念内涵的阐释延续并且深化了 这一哲学传统。
对奥古斯丁来说,道德责任,意愿的独立性和自由这些观念相互紧密关联:人必须为 他自由地自愿地所作的一切担当责任,因为只有自愿的行为才能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行为 。然而,只有当行为者拥有去做不同于他实际所作的自由时,他的行为才可以被称为是 自愿的。在奥古斯丁看来,这一选择其他可能性的自由或者能力只存在于独立的意愿之 中。这一观点明确地表现在奥古斯丁在《论自由选择》卷3对自然的(naturalis)和自愿 的(voluntatis)区分之中[1](Ⅲ,1,1)。奥古斯丁引入了精神朝向当受责难的贪欲的运 动和石子自由下落的运动的类比来阐释自由意愿所引起的灵魂运动为何当受责难。它们 的相似性在于其动因并不来自外在的力量而在于运动的物体自身。然而石子没有能力去 抑制它的下落运动,而只要精神意愿,他就有能力或者自由在另一个方向运动。因此, 石子的运动是自然的,而精神的运动则是自愿的[1](Ⅲ,1,1)。显然,能选择另一个可 能方向的自由在此被视为自愿行为的本质特性。奥古斯丁强调这一选择的自由由意愿的 独立性所确保,因为意愿既不能被强迫性的自然冲动也不能被有说服力的推理所胁迫。 因此,行为的可责难性或者道德责任可以追溯到意愿的自由选择。
1.选择的自由
正如De libero arbitrio这一标题所示,整篇对话都聚焦于意愿的自由选择(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以及它和恶的问题的本质联系(注:在该书的手抄稿中,卷1通 常带有“Unde malum”(恶由何而来?)这一标题。Cf.De libero arbitrio.Ed.W.M.
Green.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an XXIX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Pars Ⅱ,2,p.207.)。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同样坚持意愿的自由选择是我们做错事和承 受上帝的裁决的原因[13](Ⅶ,3,5)。奥古斯丁用liberum arbitrium或者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来表达人在不同的行为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1](Ⅰ,11,23; Ⅰ,16,34;Ⅱ,1,3)。他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够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呈现在我们之前,但 我们拥有去接受或者拒绝我们所认知的行为方式的能力。欲望和理智将那些有吸引力的 行为目地呈现给我们,而意愿能力则在不同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并最终决定我们的行为 。O'Connell在其对《论自由选择》卷3的重述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分析:“liberum
arbitrium这一术语暗示了奥古斯丁首先将其设想为自由判断……选择的主体被召到前 来在吸引和反吸引(attraction and counter-attraction)之间进行判断;依据这一判 断的结果,意愿被激发着去追逐那被认为是更有吸引力更能导向幸福的善。”[24](P61 )(注:Robert J.O'Connell,The Origin of the Soul in St.Augustine's Later
Work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7,p.61.)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判断或者决断(arbitrium)并不是理性过程的结果,因为意愿的决 断固然常常诉诸理智的能力,但其本质上是独断的(arbitrary)。在上一章的分析中, 我们已经强调了意愿的判断或者决定的独立性,尽管它受到欲望的暗示和理智的判断的 强烈影响。“arbitrium”这一术语更相关的是意愿的自由认同或者倾向性,而不是暗 含着理性思量的心灵的判断或者认定。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作为道德责任根基的意愿的自 由行为。正如奥古斯丁在有关理性和智慧的讨论之后所总结的:“尽管意愿是被那可见 的驱向行动,而人们无力决定他们能看见或者触摸到什么,但他们确实有能力接受或者 拒绝。因此我们应当认为精神受到较高的或者较低的感知的影响。而这一理性实体从这 两类(感知)中选择(sumat)它所意愿的,根据这一选择(ex merio sumendi)它遭遇不幸 或者获取祝福。”[1](Ⅲ,25,74)(注:着重号由引者所加。)
奥古斯丁在此肯定了意愿能力总是有能力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意向中进行选择(注:参《 忏悔录》Ⅷ,10,23中对同一灵魂的同一时刻的不同意向的讨论。)。对于意愿的选择 ,有两点至为关键:首先,它应当自愿地自由地出现,无视任何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强迫 力量;其次,它是我们自己选取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有能力去选择那不同于实际 实现的另一种可能性。
这一自由选择的观念已经暗含在奥古斯丁对意愿独立性的论证中。首先,人的意愿的 决断免遭任何外在力量的搅扰。在奥古斯丁有关人的自由的讨论的神学语境中,外在的 强力首要地表现为上帝的救助和魔鬼的诱惑。奥古斯丁强调魔鬼并不是用强力压迫人, 而是通过游说的方法攫获人的灵魂[1](Ⅲ,10,31)。人的罪过在于它以自己的意愿屈从 于来自外界的邪恶诱惑。正是人的意愿的自愿认同使得人应当为他接受魔鬼的引诱而遭 受惩戒。如果这一罪过不是自由的而是被魔鬼的力量所胁迫,罪过的出现就无可避免, 恶人也就失去了对他自己行为的主导而无需为之负责,这对奥古斯丁无疑是难以设想的 。与之相反,奥古斯丁强调在这样的诱惑下人仍然有能力寻求上帝的救助,人只要意愿 转向上帝他就可以拒斥诱惑[1](Ⅲ,20,56)。因此,对魔鬼诱惑的认同乃是人的意愿的 自愿决定。而魔鬼的诱惑力不足以取消人的自由选择和人在恶行中的主体性。这一神学 论断同样可以在奥古斯丁对能力等级秩序的形而上学理解中得到应证。完全剥离了善的 魔鬼,显然要低于由上帝创造并且能在上帝的救助下获得救赎的人类。魔鬼没有力量去 强使人的心灵作恶,正如身体或者贪欲无力强迫人的心灵成为贪欲的奴隶。
然而,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中,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自由的关系要更为复杂,特别是 他晚年作品中对恩典的不可抵御性的强调。本文将把讨论限制在这两部相对较早的著作 中。
在《忏悔录》卷9中,奥古斯丁强调:“没有人能在违背意愿的情形下行为正当,即使 它所作的是善事。”[13](Ⅸ,12,19)因此,当上帝扶助他的母亲克服了对酒的贪恋时,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前陈述道:“然而你不是根据你利用他们所成就的而奖励他们,而是 根据他们自己所意愿的(quod ipsi voluerunt)。”[13](Ⅸ,8,15)对奥古斯丁来说,我 们的有德性的行为依赖于上帝的恩典,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的出现同样也伴随着意愿 的认同。上帝并不强迫我们违背意愿地朝向正当行为,否则这些行为就不能被称为义人 自己的行为而受颂扬。这在奥古斯丁对上帝的预知和人在罪孽中的自由的协调性的论证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奥古斯丁的对谈者Evodius指出上帝的预知必然使意愿的自由 选择成为不可能:“既然他知道人要犯罪,这罪就必然犯下,因为上帝预知了它将要发 生。当无从避免的必然性存在时,如何能有自由意愿呢?”[1](Ⅲ,2,4)
奥古斯丁首先强调无人能够违其意愿地获得幸福这一观点,这意味着当上帝预知我们 的幸福时,我们的幸福并不是在没有意愿认同的情形下必然地降临。因此上帝对我们的 幸福的预知也包含了对我们意愿幸福的预知:“因此,尽管上帝预知我们在未来将要如 此意愿,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是在自愿地意愿。”[1](Ⅲ,3,7)更进一步,当上帝预知 我们的意愿时,这意愿必然如同上帝所预知的那样,因为上帝的预知绝不可能会错误。 然而,一个意愿如果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它绝不是意愿,这就意味着意愿只有在我们自 由地意愿时才会呈现在我们的心灵中。由此可以推知上帝的预知并没有取消我们行为时 意愿的自由,而是更加确认了这一命题:我们的意愿是自由的并且在我们的能力之内, 否则上帝起初的预知就是错误的[1](Ⅲ,3,8)。依据同一推理,尽管上帝的恩典将至福 带给人类,但它并未夺取人的心灵意愿的自由。否则,我们就会违背意愿地幸福,这显 然是荒谬的。由此可以明确上帝的恩典并不是否认人的选择自由的外在强力(注:上帝 的恩典也可能成为心灵甚至意愿中的内在力量。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强调上帝是最 为内在的并且无可比拟的贴近我们的心灵。在这一内在意义上上帝的恩典可以决定或者 准备我们的意愿,当然,在这一情形中捍卫人的自由是另一个不同于外在强力下的自由 的问题。)。
上述叙述中,我们看到外力并不能破坏人的选择自由,同时,意愿同样独立于其他内 在的心灵力量,这在上一章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尽管自然的冲动极富强迫力,理性 的判断很有说服力,意愿总是有能力作出不同于欲望和理智建议的决断。现在,我们将 进一步阐明意愿的运行是如此地独立而且自足,以至于甚至一个意愿都不能命令另一个 意愿。
在《忏悔录》卷8对于奥古斯丁意愿的皈依的叙述中,他注意到意愿的这一荒谬的特性 :当心灵(animus)命令身体时,命令即刻被服从。例如,当心灵命令手挪动时,这整个 过程是如此地轻易以至于人们很难将命令和它的执行区分开来。但当心灵命令它自身时 ,它却遭到了抵抗[13](Ⅷ,9,21)。意愿的这一荒谬性确切地表达了奥古斯丁彼时的困 境:他已有服侍上帝的全新意愿,并且命令自己的心灵去全心地如此意愿。然而,他旧 有的倾向肉欲的意愿和这新的意愿相冲突,这褫夺了他的灵魂执行上述命令的注意力[1 3](Ⅷ,5,10)。我们看到意愿给它自身命令,但这一命令并不能强使意愿按照他所命令 的方式运行。在意愿给出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奥古斯丁仍然在最后的皈依之前犹豫不决 。他对自己的犹豫和意愿的这一荒谬性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命令的力量在于意愿的力 量,而命令不被服从的程度也在于意愿的不投入程度。因为是意愿在召唤这一意愿的存 在,他所命令的不是别的意愿而是它自身。因此那召唤的意愿是不完全的,它所召唤的 也就不会发生。而如果它是完全的,它就无需召唤这一意愿的存在了,因为它已经存在 了。”[13](Ⅷ,9,21)
对奥古斯丁来说,他皈依上帝的意愿是不完全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还伴随着旧 有意愿的抵抗,或如阿伦特所言,他的反意愿(counter-will)的抵抗[2](P95)。这一半 心半意的意愿不能以强力迫使奥古斯丁的心灵放弃他已养成的习惯而全心地意愿新的生 命。奥古斯丁对此的解释奠基于意愿的本性和其强度之上。它从对奥古斯丁个人经验的 反思上升到对意愿本性的一般性探讨。根据这一解释,这一意愿对自己的命令必然是不 会被执行的,无论这一意愿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或者这一命令毫无必要,或者命令 着的意愿因为它内在的缺陷而无力执行自己的命令。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 意愿不能以强力召唤自己的存在也不能根除已经确立的意愿。而且,意愿自身也无力使 半心半意的意愿变得完整。
上述意愿的荒谬性显明了我们不能够以命令(imperium)的方式用强力统治我们自己的 意愿。意愿本质上是自愿的和个人化的。意愿的自由决断,它独立于一切内在的外在的 强力,忠实地呈现了我们在世的生存状态。我们如何意愿显示了我们在此世如何存在。 意愿是我们生存最惟妙惟肖的肖像。如奥古斯丁所说,当我们意愿或者不意愿某物,我 非常确信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在意愿或者不意愿[13](Ⅶ,3,5)。因此奥古斯丁强调意愿 的对峙实际上反映了自我的分裂:“那意愿服从的自我和不意愿的自我乃是同一自我。 它就是我。我既不是完全地意愿也不是完全不意愿。因此我和我自己相对立,我和我自 己相分离。”[13](Ⅷ,10,22)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意愿乃是人格的根基,它明确地揭示了我们公开行为中的内 在状态。另一方面,意愿是如此地个人化或者人格化,只有“我”才能够“决定”意愿 的倾向和强度。当然,此处的“我”不能够被还原为任何分离的心灵能力:欲望,意愿 或是理智。作为意愿根基的我乃是每一个个体行为者的整个生存。而且,这一“我”也 不能象主人号令他的奴隶那样决定意愿。意愿从不能被强迫去做对抗自身的事情。我的 命令只能以自愿的方式被意愿服从。我在这一意义上能够决定意愿的意向和强度:意愿 这一现象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生存处境。因此,甚至“我”也不能被称为意愿的原因,意 愿是如此地自由以至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作为它的原因而不破坏它的自由本性。正因为这 点,当Evodius追问意愿自身的原因时,奥古斯丁强调:“那么,除了意愿自身什么可 以是意愿的原因呢?它或者是意愿自身,那么就不可能追溯到意愿的根源。而如果它不 是意愿,那也就没有罪了。或者意愿是罪的第一原因,或者就根本没有第一原因。”[1 ](Ⅲ,17,49)
在奥古斯丁看来,当我们试图寻求恶的意愿的原因时,我们就是在以一种不合宜的方 式研究我们的行为,它使我们免除了对自己罪责的承担。他强调恶的意愿就是恶的终极 原因,我们不应该为这全然自由和自愿的行为再寻找原因。
意愿依赖于我们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的决断或者选择又展示了我们是谁。意愿不受任 何强迫地在我们的心灵中自发自愿地呈现。这就是我们能够对意愿的根源所说的一切。 如阿伦特所建议的,“意愿是这样一个事实,它在其极度偶然的现实性中不能够用因果 性术语加以解释。”[2](P91)意愿的选择就是我们个人的抉择。意愿是我们的公开行为 的本质动因,但它自身却不在因果链条之中。很显然,意愿的这一偶然事实并不包含
Gilbert Ryle所批评的无穷倒退的困难。
前述的论证无疑强调了人的自由的否定性层面,亦即免于强迫的自由。然而,奥古斯 丁对自由的理解的特出之处还在于他对人在不同的行为模式间进行选择的能力的强调。 我们是自由的,这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意愿不同于我们实际选择的另一种可能,而不仅 仅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心灵不受外物的侵扰。
奥古斯丁一方面强调,人在很多行为中,去行为的意愿并不等同于相应的能力[13](Ⅷ ,4,6;Ⅷ,8,20)。在《论自由选择》卷3中,奥古斯丁指出人生而在无知和困苦中,我们 的力量因原罪的影响而受限制。人的自由也相应地受到限制[1](Ⅲ,20,56)。但另一方 面,灵魂又接受了判断的自然能力(naturale iudicium),通过它灵魂倾向智慧而不是 迷误,倾向平和而不是困苦(注:这一自然的判断能力(naturale iudicium)能使人自由 地行正义,或者自由地服从永恒旅法,然而自由选择或者自由决断(liberum arbitrium )却是某种独断的无视判断对象的行为。奥古斯丁强调人在堕落之后,因为这一自然判 断能力的损毁,不能够通过意愿自由地选择他所应当去做的。然而,在无知中的人仍然 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或是自愿地做出决断的能力。因此,自然的判断力更相关的是行 善的自由,而liberum arbitrium则更接近选择的自由。这在下一节的分析中将得到证 明。)。依赖这一自然能力,人能够判断和自由地选择他所愿意去做的。判断或者选择 的对象总是向意愿能力开放,而意愿也有能力根据自身的意向作出决断。因此,当奥古 斯丁从负面论述意愿的独立性时,它也从正面强调了我们选择的自由。而且,这一意愿 的个人化选择突显了我们的生存处境。相应地,我们也应当通过奠基于意愿自由选择基 础上的行为去实现我们未加确定的向未来开放的自我生存。对奥古斯丁来说,他的理想 不再是斯多亚派的智者,后者在获得智慧的同时一劳永逸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性本性,随 后所作的不过是保持这一确定本性不受身体,激情或者其他外力的侵扰。对奥古斯丁来 说,人只有在保持其意愿朝向永恒真理时他才是智慧的。如果人自由地选择背离绝对的 善,智者也会成为当受惩戒的罪者。
在此,意愿的选择看来是漠视善恶的价值中立行为。特别是在《论自由选择》中,奥 古斯丁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有能力拥有或者放弃善的意愿[1](Ⅰ,12,26;Ⅰ,16,34)。相应 地我们也似乎有完全的自由去意愿永恒的善和转瞬即逝的善。意愿的自由被描述为双向 的对其对象保持中立的能力。然而,同样在《论自由选择》中,奥古斯丁指出意愿能力 被赐予人类,是为了人能因此按他的意愿的自由选择正当地生活。选择的自由是为了善 的目的,而不是某种漠然的自由:“如果任何人用自由意愿去犯罪,它将遭受神圣的惩 戒。如果自由意愿被赐予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人能够正义地生活,而且也使人可能犯罪的 话,那么这一惩戒就是不公正的。”[1](Ⅱ,1,3)
对于相信意愿是作为来自上帝赠礼的奥古斯丁,漠然的(indifferent)或者说中立的意 愿的自由是不可忍受的。这将我们引向奥古斯丁自由观的另一个层面。
2.行正当的自由
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奥古斯丁对自由意愿(libera voluntas)的理解比自由选择(
liberum arbitrium)要宽。Gilson在他对奥古斯丁的恩典和自由观的分析中将自由(
libertas)同自由选择区分开来:“圣奥古斯丁想要知道的不是对上帝的爱是否在我们 的自由选择范围之内,而是它是否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去做我们所选择的行为的能力要 比自由选择意味着更多,它就是自由(liberty,libertas)。在圣奥古斯丁那里,并不存 在恩典和自由选择的问题,但存在恩典和自由的问题。”(注:Etienne Gilson,p.157.also cf.p.323 n.85,Gilson在此详尽地解释了奥古斯丁有关自由的术语用法。)
Gilson强调liberum arbitrium暗示了作恶的可能性,而libertas则意味着意愿借着恩 典在善中被确认。他坚持认为只有libertas确保了我们在对上帝的爱之中的真正自由。 相应地,这一自由的缺席就是罪,自由的对立面。同时,Gilson将自由选择等同于意愿 ,而认为自由则是另一回事。
Gilson的论证在Mary T.Clark对奥古斯丁自由哲学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她同 样认为奥古斯丁区分了人的自由的两个层面:自由选择或者自由意愿的能力和那使人达 到作为人的真正目的而使人成为其所应当是的自由[26](P45)。然而,Clark更敏感自由 选择和自由之间的联系。她强调在奥古斯丁的早期对话中,自由乃是自由意愿的实现而 不是对它的否定。自由来自上帝这一事实也确保了它不会毁坏同样是由上帝赐予的天生 的自由(选择的自由)[26](P68)。
近年的研究中,Wetzel也注意到了自由意愿和免于束缚的自由(freedom from
constraints,liberum arbitrium)的区别。他批评道,尽管当代两位重要的评述者John M.Rist和Gerald O'Daly都意识到了这一区别,但没能考虑到对善的回应同样是自由的 一种形式,亦即自由意愿,它不能被还原为漠然的自由或者是免于束缚的自由。而这一 点也使得奥古斯丁的自由意愿观念对这些学者而言变得不可理解[21](PP.219-222)。
Wetzel强调将意愿作为独立于欲望的选择能力的理论使一切行为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不 可理解,因为如果这一理论正确的话,那么没有任何行为可以借着它的动机就被充分理 解。根据Wetzel的观点,区别于理性和欲望的意愿能力,以及它独立于善的推动性力量 的运作都不过是裴拉基派的虚构[21](P11)。
在Gilson和Wetzel对奥古斯丁自由观的重构中,对善的回应的真正自由和漠然的自由 之间的差异被强调,二者甚至被视为对意愿及其自由的相互对立的解释。在他们眼中, 对奥古斯丁意愿和自由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去做我们所应当作的自由,而不是在不同可能 性间漠然选择的自由。在下文中,我将追随Clark对这两种自由间内在联系的洞见,强 调他们本质上都归属意愿能力而在奥古斯丁的意愿观中统一起来。
上面的章节中,已经明确确立了选择的自由乃是道德责任不可或缺的根基,在此我们 转向意愿现象的另一个特性:我们总是意愿那我们认为是善的东西,特别是幸福。上一 节中我们强调意愿的选择完全免于任何强迫,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然而,意愿的这一 双向力量并不能保证我们总是意愿那实际上对我们有益的善。因为在决断的时刻被意愿 独断地判定为善的很可能被证明为实际上我们并不愿意承受的恶。如奥古斯丁所强调的 ,没有人意愿不幸,但对某些可谴责的对象的选择却可能导致不幸,尽管在选择的时刻 他并不期待出现这样的不幸处境[1](Ⅰ,14,30)。这意味着那被我们意愿的自由判断为 有吸引力的目的很可能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夺去,特别是当我们的意愿自愿地将我们 的心灵转向可谴责的贪欲时。用奥古斯丁的例子,一个为了能够不在恐惧中生活的奴隶 杀死了他的主人,当他为他的恶行遭受惩罚时他必然要失望。在此,自由选择的能力使 得我们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失去了通过意愿去获取幸福的能力。如我们在上节结尾时提到 的,奥古斯丁坚持认为意愿是为了人类能够正当地和幸福地生活而被赐予人类的[1](Ⅱ ,1,3;Ⅱ,18,47),但意愿的自由选择却可能使这一结果变得不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比 自由选择更多的东西来确保意愿这一能力能够将我们引向幸福生活,它不仅在我们看来 是善,而且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善。当我们真正取得这样的幸福时,我们所拥有的 也不可能违背意愿地被夺走。这是意愿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意愿能够实 现它的善而没有任何能够强迫它背离实际的善。只要我们意愿,我们就能够成为我们所 应当成为的,不受一切侵扰,甚至不受我们自由选择不可预期的结果的侵扰。正如
Clark所指出的:“人的自由的主要特性正是它所带来的幸福。”[26](P52)简而言之, 选择的自由同时向善和恶开放,但是只有善的意愿或者行正当的自由才能带给我们幸福 。
进而言之,意愿的自由选择也可能给它自身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论自由选择》卷3 中,奥古斯丁强调亚当的自由选择使他遭受了无知和困苦作为对他没能意愿他所应当做 的惩戒[1](Ⅲ,18,52)。这一惩戒显然限制了选择的自由,因为当我们不能知道什么是 正当的,也无力去执行那正当的命令时,只有那不正当的可以成为我们选择的对象。在 这样的情形下,另一种可能的行为模式就始终潜藏在黑暗之中,我们也因此不情愿地承 受着我们自由选择的后果。在对两个意愿征战的现象的分析中,奥古斯丁生动地描述道 :“我为这样的自由叹息,但我不是被别人强加的铁链束缚而是被我自己选择的铁链束 缚着。这个敌人牢牢控制着我的意愿,为我制造锁链并将我囚禁。败坏的意愿的后果就 是激情。在奴从于激情时,习惯就形成了,习惯不遭遇抵抗,它就成了必然性。”[13] (Ⅷ,5,10)
败坏的意愿逐渐将习惯的枷锁套在奥古斯丁头上,这一肉体的习惯成为了对奥古斯丁 意愿的强迫性力量,尽管它最初起源于意愿自己的认同。由于这一习惯而来的必然性, 奥古斯丁不能够坚决地选择全心皈依上帝。在此,意愿的自由选择甚至毁坏了他在意愿 时作出选择的能力。
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恶的意愿无可避免地给我们的意愿能力带来损毁:它使我们远 离幸福而成为习惯的奴隶。当我们将自己的心灵通过恶的意愿交付贪欲时,我们就成为 贪欲的奴隶而不再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这种情形下,我们只是被动地不情愿地行为, 我们的意愿不再是自愿的,而我们的选择也不再是自由的。恶的意愿破坏了意愿能力的 自愿性和自由。与之相反,善的意愿使我们的心灵朝向永恒的善,而只要我们意愿,这 一意向就不能被强力夺走。去正当行事的善的意愿保证了我们选择我们所应当成为的自 由。善的意愿使我们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因为当我们意愿正当地崇高地生活时,没有 人甚至上帝会去夺走我们对自己行为的主宰。由此可以推知意愿的能力是非对称的。也 就是说,只有善的意愿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意愿,因为只有善的意愿才确保了我们在道德 行为中的完全自由。由于意愿的非对称性,选择的自由不足以确保意愿能力的运行,我 们还需要行正当的自由或者成为真正自我的自由来确保幸福的稳固根基。然而,这一行 正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意愿的自由选择的取消,而是它的实现和完善。只有当我们有了 正当行为的意愿,我们的选择才不会像在恶的意愿的情形中受到过往选择结果的影响。 当善的意愿出现在我们的心灵中时,我们总是能够自由地选择善的或是恶的生活。另一 方面,行正当的自由又不能缺少选择的自由。否则我们以善的意愿所行的就不能称为有 德性的行为,因为善的意愿如果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就没有为这一心灵的倾向贡 献什么[1](Ⅲ,25,74)。而且,善的意愿如果不是来自意愿能力的选择,它就甚至不能 被称为意愿。因为它无需我们做出任何贡献就产生,我们也不能从这样的“意愿”中实 现幸福。
综上所述,奥古斯丁对意愿自由的理解要比选择自由丰富,但他并未取消人的选择自 由,只有借着这一自由人才能够意愿不同于他实际所做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行正当的 自由来确保我们所选择的确实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另一方面,选择的自由是我们颂扬和 谴责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只有当意愿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才能颂扬或是责难这 一意愿及其相随的行为。
结论:通向对人的生存新的理解
通过对希腊罗马哲学中意愿观念发展的回溯和对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和意愿基础上的 自由观的详尽讨论,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古斯丁或许不是意愿这一术语的发明者 ,但他对意愿概念作为心灵独立力量和公开行为的决定性心理因素的原创性理解,他对 建立在意愿独立性基础上的选择自由的充分强调都使他的意愿理论在观念史中卓尔不群 。这些洞见不仅帮助奥古斯丁克服了恶行责任的难题,而且引入了对人在世界中的生存 的新的理解。根据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人不再被等同于其本质有理智活动所决定的理 性动物。对奥古斯丁来说,人的生存是不能由理智能力限定并且还原到理智行为的。正 相反,人必须通过意愿的自由选择实现他自己的本性,它向未来敞开并且只能在死亡中 才能最终完成。人的意愿不受任何强迫和限定因而也是最为个人化的。意愿及其选择使 我作为意愿者明确地区别于其他行为者。一个行为只有在他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时,它才 能被称为我的行为。意愿是我们人格的根基。在奥古斯丁的眼中,人首先是本质上独立 并且因为他的意愿而不能被他者取代的独特个体。这一对个体性的强调使奥古斯丁有关 人性的教诲特立于其他古代哲学家,正如阿伦特所评述的:“正是人的个体性的特性解 释了奥古斯丁的名言,亦即他之前没有任何人,也就是没有人能够被称为‘个人’(
person);而这一个体性在意愿中显示它自身。”[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