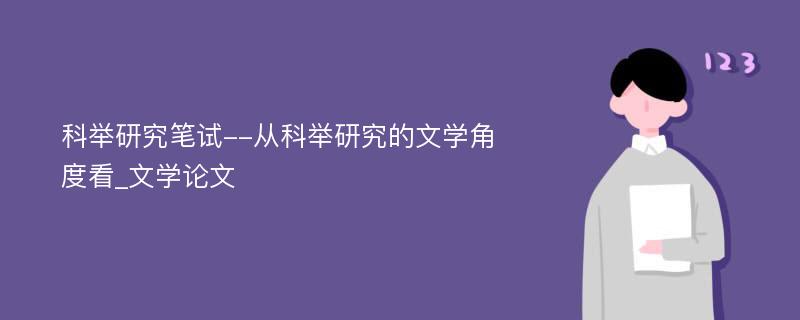
“科举学”笔谈——科举学的文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笔谈论文,视角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学视角考察科举学,可以看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中国古代考试诗文、文学体裁和题材,还是文人挥之不去的科第情结,都说明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
先谈考试诗文。从正统文学的角度看,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宋散文的生辉,及“考试文学”——八股文、策论的兴盛。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是以首场诗、赋最重要。为此,许多人认为: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爽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土,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惟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北宋庆历改革中,针对诗赋考试的声病、对偶,文章写作流于形式和内容空洞的倾向提出批评,《宋会要·选举》中道:“旧制以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式,一字偶犯,便遭降等。知识才学之士临文拘忌,府就规检,美辞善意,郁而不伸。”庆历四年(1044年)科举改革,以用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决定高下,自然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写作“古文”逐渐取得了优势。庆历新政虽旋即失败,但对文风改革之效却十分显著。宋代仁宗朝后期的皇祐年间,古文已盛行于世,到嘉祐年间,写作“古文”,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风气了。为此苏轼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1]北宋古文家欧阳修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了古文中艰涩的倾向,而导之以平实优美的文风,他还提拔了一批富有文学才华的古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等。嘉祐以后,由中唐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历经二百年的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所谓“唐宋八大家”,除韩柳外,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祐年间。此后,继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遂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庆历改革,进士首场试策之举,使得宋代散文生辉。
明清之际,八股文成为最重要的考试文体。八股文是介于韵文、散文之间的文体,它汲取了以前一切文体形式,其中唐诗也是其滥觞之一。秦锡淳《试帖笺林》言:“唐人以诗取士,变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谓之试帖。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然后结以收之。六韵者多,八韵亦间有之,其首尾即起结也,中四韵即八比也。试文之八比始此。”[2]唐人试诗结联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时文之“大结”有启发意义,试律结以干请诵圣等套式,也与八股文大结有类似之处。它形成于王安石的经义取士,直至明代朱元璋洪武改制,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最后定型。八股文成为明清科考最重要的文体,是经术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此外,自汉代创立的策论,被科举制所沿用,历经唐宋元明清,该文体形式成为一种特殊的“考试文学”,而殿试状元策又被称作“官人文学”。[3]试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灾异、地理、民族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主要是测试应考者的德、才、学、识以及应付现实“时务”的能力与技巧。状元策既是一种特殊的策文,又是“最好的”策文,它们的文学性,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仍然是很强的。首先,作为文学的重要因素的“真实性”,在状元策中可以得到保证,同时,它们大抵可以满足文学对于现实性和充实性的要求,故读起来往往言之有物,内蕴丰富。其次,作者通常注意在状元策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胸怀、风采和精神等。这些正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这个“人物”便是“状元”。许多状元策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读来不禁令人感奋,而且令人对其作者心怀向慕。如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元化;清代的钮福保、孙家鼐、张謇等策文均如此。从文学的角度看,“官人文学”所给以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逊色,也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纵看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再看科举制与文学体裁和题材的关系。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科举制的兴盛,使得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地出现。我以为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广泛而有意义的,还在于其对诗文、笔记、传奇、戏剧、话本小说体裁和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的历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产生了科举人生的方方面面,诸如:及第落第、场屋省试、投文干谒、慈恩题名、曲江游宴等等,其中既有登第后的激越、落第失意的悲哀、奔波赴举的艰辛、干谒求人的愁苦、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又有及第后的风流秦楼楚馆的欢悦。大凡士子科举生活的诸方面,均呈现在他们的诗文里。
由于正史在记载科举制度上受到体例的制约,使我们无法窥探科举制度的全貌,而我们却可以在私人的笔记中看到科举制的方方面面。如:五代有王定保的《唐摭言》就对唐代科举制有一个全景式的描述,是我们研究科举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如洪迈的《容斋四笔》、《容斋续笔》,方勺的《泊宅编》,释文莹《玉壶清话》,王泳《燕翼诒谋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射采伯《密斋笔记》,王谠《唐语林》,《隋唐嘉话》,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焦竑《玉堂丛语》,王士禛《池北偶谈》等等,不一而足。私人笔记既表达了作者对科举的态度,又对科举制度研究起了补缺的作用。笔记中大量的有关科场的琐闻轶事,给我们展示了科举社会的另一面。
“科举婚姻”似乎成为科举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其中“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事。《开宝元年遗事》载:“长安有平康里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进士及第为平生最大一件快事,总得找个人说说,而勾栏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妓女便是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的情韵,与士子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同时,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又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一种审美的态度,发抒情感,品味生活,并进而去寻觅爱情。二者一拍即合,于是便产生了“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的传奇小说,便是这种体裁的滥觞。这两部传奇的面世广标志着“进士与妓女”母题创作已趋成熟。此后许多故事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这一母体的创作。
唐代进士放榜之后的曲江大宴就有达官显贵前来观看新科进士,为自己家挑选东床快婿之传统。因此一些寒门书生一朝发迹变泰,很可能引起婚姻关系的变化,于是以科举及第后“负心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便应运而生。通常是穷书生金榜高中之后,抛弃了结发妻子,“背亲弃妇”,负心男子的形象多出于文学体裁中。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为这类作品的发轫,该作写张生出游,在普救寺与寄寓此寺的崔莺莺相遇,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终在西厢私会。后张生赴考,莺莺竟遭遗弃。到宋代就有如:《张协状元》、《蔡伯喈》(又称《赵五娘》或《琵琶记》)、《王魁》等一批描写负心汉的作品面世。《张协状元》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有中国戏剧古化石之称。这个剧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负心弃妻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古代戏曲中最早的负心男子的形象。
“科举婚姻”作品中还有一类为:穷书生科场高中与某千金结为百年之好,《聊斋志异》、《三言》中许多篇章为此种描写。才子佳人小说随着科举的套路化而套路化。鲁迅先生为此总结:“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墙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存‘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定为限),实际上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就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变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4]
进京赶考是士子人生的一部分,赶考路上的各种机遇艳遇,便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窦娥冤》中的窦娥到蔡家当童养媳,起因就是为了还债及为她父亲换取进京赶考的川资。《西厢记》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赶考的大道,中了状元,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干脆以魂魄随同书生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千古绝唱,不正是赶考书生人生机遇的写照!《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中因赶考引出的爱情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最后,谈谈文人挥不去的科第情结。科举对文人来说就是人生。自从科举降临在这个浩浩世间,就与士林阶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士子的心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科第情结。在士子的视野里“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在士子的心目中,科场得第最令人魂牵梦绕,如痴如醉。从此在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悲喜喜、惨惨烈烈的剧目。科第情结,怎是一个“爱”,抑或一个“恨”字所能表达出的?个中的滋味,只有久困场屋的士子才能品味得出来。
45岁的唐代诗人孟郊在《再下第》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下第心情:“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其失落伤感之情溢满字里行间。次年,当孟郊进士及第,兴奋之余挥毫而就《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其神采飞扬、喜形于色的情态。一朝登科便觉天地为宽、山川生辉。事实上,无论是下第诗还是登科诗,所表达的都是文人的心声。晚唐诗人杜荀鹤在科场奋斗了30年,终年闭门苦读,以至“发白老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闲居即事》),应举遭挫,痴心不改,“公道算来终达去,更从今日望明年”(《长安春感》),直至46岁才登科。
宋代的词人柳永考试落第后,玩世不恭地写下了《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柳,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面对科场落第,他以“偶失龙头望”自诩,以孤傲之情发泄了“明代暂遗贤”的牢骚,完全不同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的自怨自艾、怨而不怒之态。《鹤冲天》似乎是他的一篇人生宣言书,向上流社会宣告从此要向“科举——入仕”的人生轨迹告别,去追求那“偎红依柳”、“浅酌低唱”的生活。事实上,他却忘不了对朱紫显达的渴慕。这首词给他的仕途经历带来了很大的挫折。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记载:仁宗皇帝听说了他的《鹤冲天》后很不高兴,于是在柳永又去考进士时,仁宗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他又一次经受落第的打击,因而谑称自己为:“奉旨填词柳三变。”[5]但是在柳永的心目中却始终没有为“科名”二字平静过,他常常在醉梦中惊醒,痛感马齿徒增,老大无成。他在《戚氏》一词中伤感道:“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他为无名无禄而伤感,科场不顺而懊悔。最终他还是投入科场“彀中”。
明清时期小说家除汤显祖是进士出身外,其他小说家均无进士“学位”。蒲松龄屡试不第,到晚年72岁才援例成了贡生;吴承恩、冯梦龙均科场失意,仅补了个贡生。虽然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科第的机遇,但巨大的失落感和严重的自我压抑迫使他们去寻求心理补偿,以自由为本质的文学作品便成为获得补偿的有效途径,他们往往在文学作品中借笔下的男主角成就功名来寄托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20多篇“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如《贾奉雉》、《考弊司》、《席方平》、《三生》、《司文郎》、《叶生》、《王子安》等。从《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既有“爱”或者说向往的一面,又有“憎”或者说无奈的一面,事实上在蒲松龄那里,对科举的爱恨交加,正体现了士林阶层对科举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儒林外史》揭露了科场中人格扭曲的众生相,从周进的“口吐鲜血”到范进“痰迷心窍”的病理报告中,揭示了科举时代的悲剧。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高鹗的笔下第一百一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中描写,脱了红尘的贾宝玉还中了乡试第七名,贾兰中了乡试第一百三十名,贾家中兴有望。最后由甄士隐预测,贾家“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为小说的结语。这部蜚声中外文坛的名著,仍未跳出传统小说尽投“彀中”的套路。正是这种科第情结凝聚出一篇篇色彩斑斓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