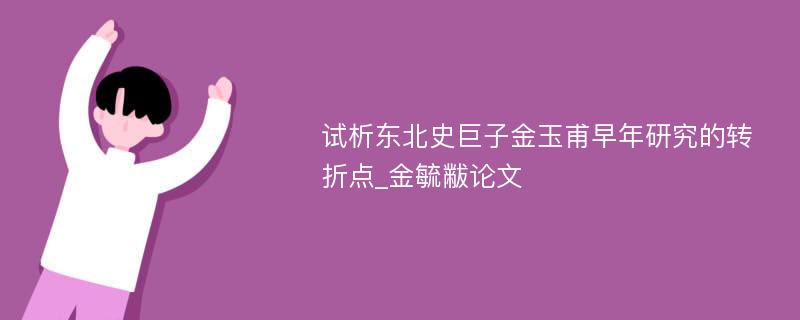
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早年治学转折点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擘论文,探析论文,转折点论文,早年论文,金毓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9)06-0094-03
近代著名文史大家金毓黻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学成后返回东北,历任多个行政职务。自1922年起“基于忧乡之心”,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成为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金毓黻的治学历程,研究者多以其自撰《千华山馆书目录序》中所言“迨癸亥(1923年)讫今,则致力于乙部”[1]6,推定金毓黻先生在三十七岁以后,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笔者经过仔细研读他四十年书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发现早在金先生矢志进行东北史研究之前,在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下旬至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初,他来过当时的黑龙江省,任省教育厅科长。在仕宦生涯转折、由奉至黑龙江的时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此时,这位史学大家确立了自己“此后从研究史学入手”的方向。因此,本文对金毓黻早年在黑龙江省的仕宦、读书生活及相应心态等进行梳理解读,以使关注东北史的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国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一、离奉北行的原因
金毓黻先生1916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返回东北,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后升任议会秘书长。1920年,先生时年三十三岁,任奉天省议会秘书长,正是仕宦生涯之始,刚刚升任,可谓青年才俊。那么他为何在正是一路升迁之时,从奉天辗转远赴黑龙江,任一省的教育厅科长呢?在金毓黻先生四十年撰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中,其心路历程、治学经过历历在目,是研究这位学者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认真检读,将其北行原因陈述如下。
金毓黻年轻时性情急躁,心浮气盛,他意识到这一个性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余作日记前后十年有余,积至十余册,偶一覆视,无一页不有脱误,性躁气浮,难与入道,宜乎学业之不犹人也!”[2]17而且自己身体的疾病也与急躁的性情密切相关,《静晤室日记》五月十九日记道:“余之咳疾,两月未愈……尝求其致疾之原因,一由于事繁,一由于性躁……性躁则不能容物,不能容物则有时不应怒而怒,怒久则疾生矣。”[3]37怎样彻底根除浮躁之病是年轻的金毓黻一直反思的问题。他在民国九年三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八字,则涵养天趣,泛应曲当,而无患于昏惰矣。”[2]6外界烦恼喧嚣之“动”既然不可尽去,就只有在内心中求“静”,“程子曰:‘主静之宜,譬之置烛静室,风不吹,烛亦不灭,人善养生则长寿,亦用此理。’”人如果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3]33,才会在修身之途上日益精进。他之所以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静晤室”,自言“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1]22,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虽然有此意向,但是人在官场,百事扰心,金先生每每感叹身不由己,“倦于酬酢”[3]45。纵观他早年日记,即便身为一省议会秘书,金毓黻也没有丝毫官僚气和市侩气,每日所记多是读书心得和悟道体会,心志所向,仍为谆谆学者之风。但是耽于官场冗务,时日既久,除了心境难静之外,金先生还深有“日月不居,年事渐长,自省所业,百无一成。每一思及,盖不胜薄冰深渊之惧也”[4]62。谨就《静晤室日记》前四卷粗略捡拾,因公务繁杂无暇潜心读书治学之语频频可见,“公务稍冗,未多看书”[4]76,“公冗,无暇读书”[4]83,“忙碌竟日,未习一字,未读一文”[5]115。在这样的生活中,金毓黻深感压抑:“以自由之身心,受无形之桎梏,此人生之大不快事也。”[5]115“数日内疲于酬酢,百事未治,心君不宁”[4]76,“长此以往,何能成就!”[4]94
就在这样的心态之中,金毓黻逐渐萌生了罢此职位、另谋去就的想法。他想另觅一处杂务不多、相对自由的差职,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潜心于治学。恰逢此时,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孙钟午向金毓黻发出召唤,邀他去黑龙江就职。此前孙钟午也供职奉天,于民国九年八月十一日升任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孙钟午的邀请促使金毓黻下定了决心。他在民国九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语云:‘需者事之贼也。’又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需而不断,世间一切事皆不能成。丈夫做事,唯有一刀两断而已。”[5]110后来遂“摒弃一切”,“北行之计已决”[5]143。金先生即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赴黑龙江任职。他自述当时心态说:“此次应召,欣然就道,发于本愿,非有人迫之使然。”[5]43因深感在奉天议会工作的四年中,“最后一年,则意兴萧索……暮气滋矣”。如果再不断然弃旧向新,恐怕人生难有进步,所以“欲假易地迁职,以作我朝气”[6]144。
二、治史之向的确定
在黑龙江生活之初,金毓黻内心极为矛盾。他时常感到“心中俶扰不自安”。[6]149“心君扰扰,踧踖不安”[6]154,究其原因,“私欲塞胸故也”[6]149。这个“私欲”,就是汲汲于仕宦之心。回顾此前,他在奉天省议会已有相当不错之政绩,此次来黑龙江教育厅任一科长,决定是否正确?一天在镜中看到自己“面色枯黄,殊不如在奉之日”,不由得产生“远来何为耶?此理不能自喻”[6]156的感叹。对自己的这种状态,金毓黻深感忧虑,并且时常自省,告诫自己“惟有确守朱贤之说,壹志绝欲”,才有可能“拨雾见天,而心君有泰然一日也”[6]154。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毓黻原来的“心绪纷扰”[6]134之态逐渐趋于安宁淡定。心志一定,“陶陶之乐,油然生矣”,残留的私欲就此去除,也不再受官冗纷扰,“今昔之情,何其殊耶!”[6]162
自此以后,金毓黻认识到,自己应该继续走这条从政为辅、治学为主的道路,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摇摆不定了。他在民国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祁向不定,而心好动……今日思读书,明日忽讲交际,泛泛若不系之舟,浮水之萍,心无定见、行无定向……以致今日学问无成……自今日起,应……勿动于浮说,勿劫于外诱,笃志力学,始终弗懈。期以十年……或能有所树立。”“自古哲人名儒,所以能自成其学者,不外数事:一曰用心专一,二严立课程,三砥砺品节。凡人有所不为,始能有为,即是用心专一。”[6]164此时,金先生经过对以往生活和治学的反思,诫告自己今后当笃志专一于用心治学,并且自忖以此前基础,当以十年为期,或可成就。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笃志力学”的具体方向究竟是何志何学。十二月二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刻所拟读之书,厥为史传、地志、政典……学以致用为归,否则文似韩、欧,诗如李、杜,亦奚以为?”“此后所业,即用是为职志,不止于浅尝……持此不懈,期以十年,或庶几得偿宿愿乎?”[6]167至十二月三日,金先生明确写道:“余此后既从研究史学入手。”并且决定此后对于自己也感兴趣的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问,“略知其大凡即可矣,不必过事详求也”[6]167。应该说这是金先生确定此后治史道路之始。一旦确立了今后的人生走向,免去应酬、潜心读书;又适应了在黑龙江的饮食生活,心灵自由、体适安畅,金毓黻真切体会到“为学必先曰求放心……身可受桎梏,而心不可受桎梏”[6]162。“杂念去而心君宁,俗累少而真乐出。脱去缚羁,还我自由,无思无虑,独往独来”[8]184的境界。此后虽然多次有朋友劝说他再回奉天参加议会选举,他自己也明白“若不来江,在理在势于参议院定占一席”,但是“已决计不为”。即便家君一再来函促作参议,不愿他在黑龙江久留,金毓黻也决意不为。他认为,家人朋友之议,出乎关心,但只有自己才明了“妄念既去,便觉心中莹然,最为快活”[8]的感受。他人之不解金毓黻宁肯选择清闲职事读书治学,以为自讨苦吃,金毓黻也毫不在意。“他人之所谓苦,正余所谓乐,既乐事此,何苦去之?”“夫亦从吾心之所安而已!”[9]
三、为学视野的展开
金先生青年时即已具备优秀的从政素质,在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半年后,他又随长官赴吉林,自此来往于沈阳、齐齐哈尔、吉林、长春之间,直到1931年升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一直未脱仕宦生涯,但是其心志并无意于此。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四处考察、广为搜求,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镌》。公余之暇,博稽古书典籍,整理研究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并有所著述。正像他后来自述这段经历时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划,故学间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1]3
金毓黻先生在齐齐哈尔的这段仕宦读书生活,也正是上述思想的反映。从《静晤室日记》中看,那段时间的确冗务不多,可以有一定的身心自由读书治学。他在十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公务稍简,拟以两月之功专治古文辞及诗。”[6]150按照自己的设想,金先生在齐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史学名著。其研究阅读的文学著作有:洁珊先生的《诵诗随笔》、《抱润轩文集》、《文选》、《儒林外史》、《白华阁诗集》、《宋诗钞》。史学著作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论》、《欧洲政治思想史》。语言著作有《实用国语文法》,学术札记类著作有《越缦堂日记》,游记类著作有梁启超《欧洲心影录》、侯保三《南阳旅行记》等。
在诸多书籍之中,金先生致力最勤,耕读不辍,日有札记者当属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其中收录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七百余篇,为历来治文史者必读必备之书。在研读过程中,金毓黻细致体味、研精覃思,多所心得。他对古文的喜爱由来已久。“自戊申(1908年)讫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1]6。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期间,即勤于文学修习,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后来金毓黻先生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因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与他早年的古文功夫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收集《史记》和“苏诗”的妙言佳语辑录成集,以备写作之用。《静晤室日记》中有大量的诗、文、记、联等文学之作,均用语工整、意境深远。与此相关,学诗写诗、以诗会友,也是他在齐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至十四日,与挚友查安荪、黎雍共同倡议,连作八集诗钟会,以不同字嵌入诗中作联,其乐陶陶。在研读诗书之余,金先生还沉心书法,日记中多有提到自己在悬腕、运笔、铺豪、临帖等方面的体会、切磋、进展。
除了研读各类著作,金先生还经常翻阅载有新动态新思想的报章杂志,主要有《新青年》、《建设》、《大学月刊》、《时事旬刊》、《新潮》、《东方杂志》、《民铎》、《小说月报》、《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等。
在这一阶段,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西方哲学理论东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金先生及时关注了学术界的新动态,在以往研读古史的基础上,对史学方法有了更多的思考,并接触、接受、辨析了一些国内新史学、西方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观点新方法,治学视野为之展开。如他谈到梁启超和胡适时说:“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6]160评价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6]160。谈到胡适论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时,认为其右汉而左宋,自己与其见解不同[6]166。
这一时期随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1919年4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邀请,来华访问讲演。前后在上海、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1920年7月离开中国。杜威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金毓黻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四日日记中提及杜威的“新历史的研究”及陶孟和的相关阐释,认为这种观点是历史学的“新旧之分”,高度评价杜、陶二氏所发之言“足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6]168。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也于1920年9月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做了多次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金毓黻先生在日记中也谈及了罗素在北京女师的演说[7]216。由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国内对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增多。金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柏氏将于1923年来华讲演的消息[7]218。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1919年5月的《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金先生也非常关注,他谈到李大钊论“唯物史观”一词,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观点:“人类之生活为社会全部之生活。往昔历史专详政治,此为社会一部之生活,故为新史学家所不取也。”敏锐地指出“此为唯物史观之胜义”[7]219,可谓切中肯檠。
虽然综观其一生,金先生仍是走理、文、小、史四途,以传统史学之路立身治学的学者,但是从他早年的札记中即可看到,先生丝毫没有固执己见、胸襟狭隘,而是海纳百川,终成其大家风范。
收稿日期:2009-09-15
标签:金毓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