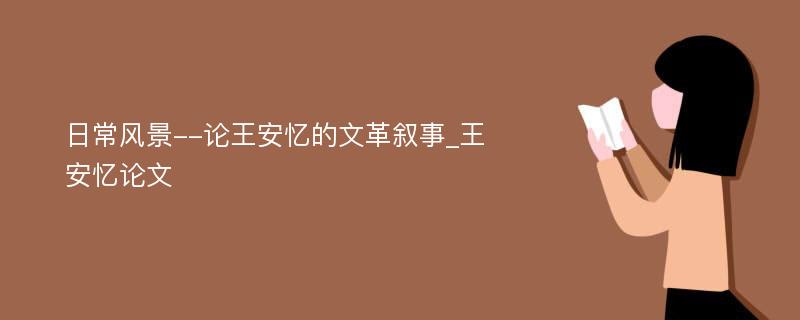
日常的风景——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日常论文,风景论文,王安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墙:红的;人:蓝的,灰的,草绿的;裤腿:男,七寸,女,六寸;名字:凡爱文的均改为要武;世界:成了个清一色的世界;读书的,教训教书的;教书的,听训;做工的,写大字报;写字的,做工;有钱的,抄个精光;没钱也能周游世界;十字架,老佛爷,一概砸烂,家家供起忠字台;世界,成了个颠三倒四的世界。
这是王安忆在《六九届初中生》中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形象概括。作为一名六九届的初中生,一个从一九八○年开始小说创作并且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优秀作家,“文革”的历史、插队的经历、知青的感受不可能不进入她的创作视野,也不可能不影响她的文学表达。她笔下的故事有些发生在那个年代,比如《“文革”轶事》、《流逝》;有些穿越了那个年代,比如《叔叔的故事》、《长恨歌》;有些却是那个年代的引子或尾声,比如《好婆和李同志》、《冷土》。无论“文革”怎样出场,那些在我们惯常的定义中充满血腥、暴力、荒谬、非理性、悲愤和惨烈的浓重色块,在王安忆的娓娓讲述中被稀释成了忧伤而琐细的日常景致。那街头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斑斑血迹融进了亭子间每日的小菜泡饭,也融进了江淮流域农家日常的洗衣烧锅。王安忆对那个年代日常景致的悉心描述凸现了日常生活超越时代的恒常性,凸现了日常生活对人的重新确立和重新肯定,也凸现了王安忆“文革”叙述的独特价值。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都不是时代风云里风口浪尖上的英雄,面对世事的无常,命运的多变,他们无法主动地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没有理想,有了理想也不可能实现,生活中的大事儿都做不了主,只好将所有的心思和智慧都投入吃穿用度和衣食住行。在谈到上海的市民精神时,王安忆说:“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① 其实,正是这“一日一日的生计”,这“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有着恒久的韧性和耐力,它蕴含了生活的快乐和忧伤,包容了人生的安稳与飞扬,支撑着人们度过许多危难的时刻。
王安忆是将生活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家。她在《长恨歌》中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细致而饱满的描述,足以让读者领略“文革”前上海弄堂里的旖旎风光。在五十年代,纵然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时代风尚,但精致、细腻、讲究的日常生活仍有它存在的空间。王琦瑶和严师母在穿衣、化妆和发型上比拼着,这两个艳丽的女人那“翠绿色的短夹袄”、“舍味呢的西装裤”、“织锦缎镶滚边的短夹袄”、“浅灰色的薄呢西裤”、旗袍和秋大衣,衬托着胭脂、香粉、口红和指甲油,混合着理发店里洗发水、头油和烘烤头发的焦煳味,成了这条曲折深长、狭窄逼仄的平安里中最亮丽的风景。一周两次的下午茶,糕饼点心、汤圆糖水、乌梅汤莲子粥,寂寥的日子被这热闹的下午茶点燃。天冷了,屋子里安上了炉子,王琦瑶们在炉子上烤鱼干、烤山芋、烤年糕、涮羊肉、下面条、包蛋饺,吃着聊着,午饭茶点晚饭连成一片。谁能想到,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大事儿,火炉边的小天地却是这么地良辰美景。
生活在流淌,“文革”开始了。在这个衣服的颜色、款式乃至裤脚的尺寸都有具体规定的扭曲的日子里,追求精致而优雅的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无必要,甚至还是危险的,但王安忆仍将上海人的衣食住行作为她观察和描述的对象。她曾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像得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② 王安忆也正是通过观察这种规范制度下小小的花样翻新,确立了她对“文革”叙述的独特视角。
一九六六年,雯雯上初中。然而,这场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滚滚向前的革命却越来越与她无关。因为“世界不关心她,她也就无须关心这世界了”,“她只关心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自己:自己的头发,衣着,举手投足的姿态,给旁人的印象,以及自己的痛苦和欢乐”③。一个小小的语录包,她斜背、直背、把带子放到各种长度,为了背着好看;不同颜色质地的衣服,她会佩上不同样式材料的毛主席像章;头发不够长,却成天想方设法、花时耗力地把它们编成辫子,还不断地变换着辫子上玻璃丝的颜色;她想要一件绿军装,这不单是小姑娘对时尚的向往,而且只有绿军装“才有权利享受一点腰身”。雯雯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又害怕被别人注意,自己跟自己别扭着,对自己的关注有时甚至是一种苛刻。然而这却是每个青春期的少女都会经历的心理过程,乱糟糟的年代因此也成了她成长的背景和影子。
衣装发型既是装扮给别人看的,也是一种自我的感觉。王琦瑶做了头发,便有了做人的兴趣;雯雯按照自己的理想折腾自己,自我感觉也陡然地良好起来;欧阳端丽喜欢好衣服,穿着不合身、不合意的衣服会难受、会不自在。严师母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它是做人的“面子”,“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而“吃是做人的里子”,“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虽然在严师母看来里子不如面子重要,因为“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④ 但是在没法儿讲究也不能讲究,只有今天不想明天的年代里,里子的实惠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面子那“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毕竟,那实实在在的口腹之乐让人觉得踏实温暖。
欧阳端丽对生活的重新认识便是从买菜开始的。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更早顶着冷风去排号头,买到心仪的肋条的兴奋、不管不顾畅快地吃顿“红烧肉烧蛋”的英勇、排到买鱼号头的踏实都将一个含蓄优雅的少奶奶变成了平常人家的主妇。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她开始变卖东西,随后又在家里帮别人带孩子,去工场间里缠线圈,她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为她确立的生活方式被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击得粉碎,她终于认识到: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这些东西“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得更好。手段和目的就是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⑤。革命改变了她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却改变不了她日日都须应付而且马虎不得的一日三餐,也正是这些调动起她的智慧和精明、勇气和耐力,支撑起了她“做人的兴趣和精神”。
然而,仅仅从吃饭穿衣来揭示那个特殊年代日常生活的恒常性并不足够,王安忆进一步将她的观察和思考深入下去,那便是——房子。有了栖身之地,吃饭穿衣才有了根基,平庸琐碎才有了着落。《鸠雀一战》中小妹阿姨的生活目标便是要一间房子,她将自己所有的心力和精明都投入其中。生活有了目标,做人便打起了精神。她在张家做过三十年保姆,每个星期日都去跟张家儿子周旋,想要回自己住过的那个小房间;为防万一,她又撺掇五十七号阿姨占了闸北小叔叔的那间房,甚至亲自动手。不管“文革”是否发生,小妹阿姨都需要一间房子安身立命,“文革”带来的世事变迁只是给了她一线要房子的希望,而房子终于成为泡影多少跟她自己的性格和做人相关。
借用严师母对穿衣吃饭与做人的比喻,我们或许可以说,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里子”,它把人推进私人空间,是“做人做给自己看”,满足的是人的物质要求,而世故人情则是日常生活的“面子”,因为举手投足都要与旁人发生关系,所以它把人推向公共领域,是“让人信服和器重”,实现的是人的精神渴望。人的日常交往把个体编织进了人群,多种社会关系和三餐一宿一起构成了人们每日必须认真面对,专心应付的日常生活。
在许多“文革”叙述中,这场浩劫对人最大的摧残正是体现在人际关系上,父子夫妻划清了界限,朋友反目成了敌人,那最可信赖的人往往又是落井下石的人……然而,在王安忆笔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伤害和算计、理解同情和互助是恒常存在的,它们并不因“文革”的到来而有过多的改变。“文革”开始了,被启发教育的保姆给东家贴大字报,小妹阿姨嘴里却不说东家的“不”字,她想的是贴了大字报以后还怎么跟东家相处。屋外红旗漫卷,却与好姆妈和谢伯伯毫无关系,他们的夫妻反目是因为收养来的妮妮打乱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样式(《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文革”时期是“我”的“忧伤”年代,“我”为妈妈仅有的一张电影票给了姐姐而忧伤、为妈妈继续在看电影这件事上的不公平而忧伤、为妈妈不让“我”自作主张留小辫而忧伤、为姐姐在班主任面前揭我的短而忧伤、为老师训斥“我”而忧伤……而“我”的忧伤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忧伤的年代》)。学校停课了,几个成份不好的中学生除了等待别无选择。在无事可做的等待中,路小红感慨着与继母客气中透着疏远的关系,极力在记忆中搜寻母亲的影子;丁少君对邻家小妹有着身体的冲动,心里却想着路小红;丁少君和陈志浩彼此心里有过节儿,但他们都喜欢路小红,还商量着三个人组成一个集体户。少男少女细密而单纯的心思在这平静的等待中弥漫开来(《大刘庄》)。
《“文革”轶事》可以说是王安忆将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铺排得最为饱满丰富的文本。那乱世间男女进进退退迂回曲折的试探,百无聊赖无事生非的调情,充满怨恨与复仇快感的背叛,惩罚别人更重创自己的负气都被作家细腻的心理描述演绎得淋漓尽致。“青工”赵志国与资本家女儿张思叶的婚姻在上海人眼中是那种乱世中的珠联璧合,谁都没吃亏,也都让对方占了便宜。当赵志国走进这个今非昔比,只剩下女流之辈的张家时,寂寥萧条的亭子间突然显出了生气。王安忆似乎有意将这一男三女放进一个封闭的狭窄空间里,来探讨两性关系的多种可能性。赵志国娶了姐姐,爱上了妹妹,跟嫂嫂也知根知底地体恤着。姐姐下了农场,剩下的三个人内心里惊涛骇浪,表面上却平静如水,不愿把话说穿,又暗中都较着劲。妹妹到底年轻,承受不了爱情的煎熬,赌气插队去了吉林,嫂嫂因没有占到大房子捅破了姐夫小姨之间的窗户纸,使原本含蓄的遮遮掩掩的情感历险突然摆在众人面前,结果,姐姐受不了丈夫爱妹妹,丈夫受不了被背叛被看穿,两个同道人一起落荒而逃离开了上海。姐姐很爱赵志国,爱得很“忘我”,照顾着赵志国脆弱的自尊心,常常为了迁就对方而忍气吞声;赵志国明白她的心思,可怜他却并不爱她。妹妹也很爱赵志国,但爱着爱着就变成了爱自己,她沉浸在自编自演的感伤剧里,决意去吉林插队是她这出感伤剧中最荡气回肠的一笔,她想借此永远地惩罚赵志国,也让嫂嫂觉得内疚,无奈观众们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遂演员的心意,她悲壮的谢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嫂嫂最了解赵志国,他们有着相同的阅历,又深谙男女之间的游戏规则,感情归感情,游戏是游戏,但破坏了规则就得受罚。“文革”在这样一个充满心智较量的故事里蜕成了淡淡的底色,插队落户也似乎简化成了主人公暂时回避矛盾的一种策略;在这样的叙述中,如果“文革”退场,故事依然成立。
当“一千里外的北京,正进行着一场江山属于谁的斗争。一千里外的上海,整好了装,等着发枪了”⑥ 时,那远离大都市的乡村县城仍然延续着几千年的世故人情。
大刘庄的姊妹们在艰辛质朴的生存环境中磨出了善良达观的性情。没钱打扮,却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用草木灰滤过的水把头发抹得又滑又亮,用麦秸编戒指金灿灿地戴满手指,搜肠刮肚地盘算着一件与众不同的布料,粮食吃紧的时候也能偷偷地让出些口粮救别人的急。婚姻大事从来都是父母做主,守着女儿家的本分和尊贵,但若是遇到男方退婚这种伤害脸面的大事,却有着自己的固执和坚守。当姊妹们成了媳妇,担负起一家老小的穿衣吃饭时,她们便开始邋邋遢遢、粗声大气,还斤斤计较、爱占便宜,生活的艰辛和男人的驱策让她们变得泼辣粗鲁不自爱。就像庄稼不断地播种,不断地收割,一茬一茬的小女孩长成了姊妹,一茬一茬的姊妹长成了媳妇,生儿育女,生生不息,她们最远也就去过县城,革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些人突然就变成了右派。乡间的温暖多情、平和善良却能包容这些来农村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人。黄医师总是回蚌埠探亲,探亲总是超假,大刘庄的干部社员从来都只是同情他而不是指责他;张医师夫妻恩爱,家教严谨,社员们对她总是怀有尊敬,夫妻俩的亲昵举止也被保守的社员照单全收;于医师的丈夫是那种懒惰傲慢性格乖戾的右派,庄上的干部很难喜欢或者同情他,但他也没受到太坏的对待;马医师问诊的时候死了,四乡八邻的农人们老远举着幡旗哭号着送他,人们都记着他的好。至于知青们,七十年代初已经有部分人招工到了县城,留在农村的知青也涣散了精神,成天往县城跑,他们不会认同农村,也与县城格格不入,但不论是已经进城了的“精刮”,贪小便宜的“文化革命”先驱、言辞光芒四射的“哲学奇才”、嬉皮士式的体育生,还是那帮热衷文学高谈哲学,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在县城里四处游荡的过客也都被冷漠粗粝的县城所接纳。于是,在王安忆的“文革”叙述中,我们看到,不论是乡间的温暖多情还是县城的冷漠粗粝,它们都能容纳、消化甚至支撑着这些外来的因素,正是它们的兼容并蓄得以让这些曾经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心情开始乡村县城的隐居生活,而那些例行的训话、学习、劳动改造只是关于革命的一个肤浅表情。
“文革”是一段非常态的时期,王安忆叙述的却是这“非常态”中的“常态”,她专注于笔下的小人物们如何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专心应对日日恒常的衣食住行、世故人情,默然地任大时代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正如王安忆在《隐居的时代》中所言:“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⑦ 其实,也正是这些“暗藏的意愿”滋养着恒常的日常生活,也正是对这些日常生活的书写显示出王安忆“文革”叙述的特质。
列菲伏尔在讨论人的异化与社会革命时指出:“以往模式的革命只重视宏观世界的革命,即重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而忽视了微观世界的革命,即忽视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忽视了个人的解放。”在他看来,要消除对人的异化,实现人的根本解放就必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和改造,进行文化革命⑧。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不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进行政治或经济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着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人们的生活习惯、习俗礼仪、交往原则、情感模式以及生活理想随着一次次的革命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
“文革”可以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改造得最为彻底的一场革命,这在“文革”时期的叙述和“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叙述中鲜明地呈现出来。在“文革”时期的主流叙述中,主人公都被高涨的革命热情充斥着,穿衣吃饭的家常生活完全被排斥在叙述之外;每个人都是革命的人,彼此的关系以阶级划分,没有朋友,没有爱人甚至没有兄弟姐妹,有的只是同志和敌人,是是非非的世故人情被简化了。在这样的叙述中,人们有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思维,一样的理想,复杂的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简化为单一的纯粹的革命目标。而由于“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深重影响,在“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文革”的叙述都是当代小说的重要内容。这些故事大多通过展示普通善良的人们在“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让作品或者成为“文革”的历史见证,或者直接表达对“文革”的控诉,或者借此梳理和探讨“文革”发生的思想根源。在这些内容情节大致相同的“文革”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场灾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重大变化,最突出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冷漠、仇恨、残酷、荒谬和非理性代替了原本存在的复杂而暧昧的情感联系。
然而,虽然现代革命始终对日常生活持有批判和改造的态度,日常生活也不断地在革命的过程中变换着脸面,但日常生活本身也有其恒定性。赫勒在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指出,日常活动的特性是那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有某些凝固于每一具体道德习惯领域之中的基本的和一般的规范,舍此,则日常生活在事实上将不可能进行”⑨。事实上,正是这些“每一天都发生”的日常活动和凝固的规范是人们安身立命、立身行事的载体。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自我得以确认。
王安忆的“文革”叙述并没有回避革命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但她更为关注的却是日常生活在这些重大变化中仍然坚守着的东西。比如“每一天都发生”的三餐一宿和人们对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争取和奋斗;比如人们对美和时尚的追求,像上海街头的“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和姊妹们手指上的麦秸戒指;比如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细密思绪和乡村沉淀了几千年的温良淳厚。从王安忆对这些恒常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扭曲的时代中的没有被扭曲的人,一个经历了“颠三倒四”的时代还能形神不散的人。而这或许正是王安忆“文革”叙述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见《王安忆说》,第24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②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见《王安忆说》,第241页。
③王安忆:《69届初中生》,第1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④王安忆:《长恨歌》,第18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⑤王安忆:《流逝》,收入《王安忆自选集·海上繁华梦》,第4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⑥王安忆:《小鲍庄》,收入《王安忆自选集·海上繁华梦》,第273页。
⑦王安忆:《隐居的时代》,收入《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隐居的时代》,第39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⑧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第3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⑨赫勒论日常生活,见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