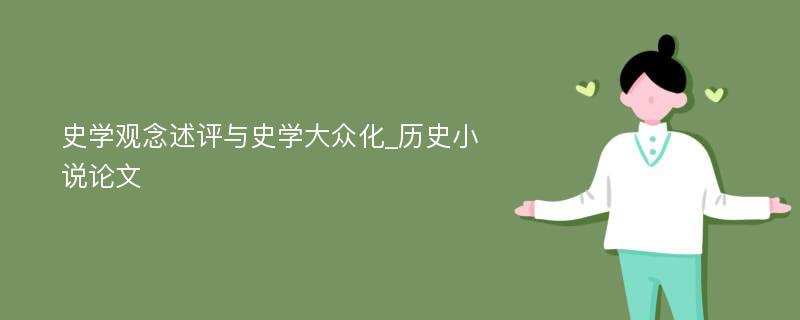
史学观念的检讨与史学普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1)01-0084-07
近20年来,我国史学界关注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史学如何适应迅疾变化的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走上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之路。史学中人为此纷纷献出锦囊妙计或开出良方猛药,从而形成较多的讨论热点,其中之一,就是史学普及问题。(注:史学普及,即史学作品更广泛地和更好地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认可与起正面导向作用的一种史学活动。)“史学的普及工作,实是有关整个民族的历史教育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9页。)那么,史学普及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总的情况并不理解,史学中人对此漠然者有之,茫然者有之,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亦多。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用更为宽广的视野来检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史学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碍史学的普及。
史学观念是史学界普遍存在的认识史学问题而得的思想成果。它对史学实践活动有直接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思想总是走在行动的前面。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影响史学普及的观念作必要的审视和澄清,促使发生变化,史学普及要么是“雾里看花”,要么是“水中捞月”,难以实现。本文拟从“史学作品的类型”、“史学社会功能”和“文化市场”三个方面与“史学普及”的关系略加论说,以期引起更多的学人来关心此事。
一、史学作品的类型与史学普及
史学作品的类型,指的是以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形成的种类。史学作品的分类标准是多样的,并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与明确其范围。如近代以来,按修史主体的不同有分为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的,依思想内容的主要差异有分为神学史书和世俗史书的(主要指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史学),其他如按人物、事件和时间顺序等所作的分类,不一而足。近年来,史学中人以史学作品内容的深浅、表述形式的严肃与活泼、语言使用的难易程度等的不同,区别为“正规史学”与“通俗史学”。(注: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见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有的以史学作品追求的价值差别,提出“研究型”与“通俗型”的类别。(注:黄留珠:《时代呼唤通俗史学》,《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6期。)也有以作用对象的不同,指出史学应分为“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⑤(注: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或者“雅的历史科学”与“俗化的历史作品”。(注:杨东铭、陈文滨:《透视历史世俗化现象》,《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在具体界定通俗作品时,有的学者还把“画象”、“画册”以至“鼓词”和“评书”等都包罗进去,不可谓不广。但以上分类(可称为二分法)有一不足之处,即对历史人物传记和其他一些带有兼容或交叉性质的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付之阙如。而历史传记、历史小说等作品从过去与今天的情况看,无疑可以划入史学作品范围,并且还是史学普及的一支生力军。(注: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第四章第四节《通俗史学的发展与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编撰》,可为证。)如果让这类作品在今天还游离于史学作品之外,史学普及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认为将史学作品分为史著、历史传记和历史题材作品三类(以下简称为“三分法”),更符合史学作品的现状,更有利于史学普及。为什么呢?
首先,是历史学综合性特征使然。历史学以其能全方位地和立体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多彩内容见长,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史学作品具有多样化特点。如历史传记、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等就是体现当代人对历史诠释、沉思、期盼,表明爱憎好恶的重要形式。一些好的此类作品在反映过去的社会内容和风貌等方面,在读者观者可接受方面极具细节的、情感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拒于史学大门之外。其次,二分法容易在史学作品具体分类时陷入“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两难境地,使一些作品流离失所。我们都知道,社会生活中“亦彼亦此”现象大量存在,断难一刀斩之,一些史学作品亦然。如张亚新著《曹操大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版),有558千字,五编,二十七章。全书不但全面记述了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还用专章分别叙说了其世界观、性格作风、文学才能、家庭和身后褒贬等。在书末,作者设附录四:生平大事年表、主要地名简释、主要职官简释和主要参考文献。另如一些记实作品——真正的——也多类似于此。它们是“正规的”、“精英的”还是“通俗的”、“大众的”呢?一定要加区分,恐怕最终还是不明不白,不了了之。三分法有助于我们摆脱困境。再次,史学界对当前涌现出的大量历史传记、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少有问津,它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如将它们纳入史学作品中(其实很难说分离出去过),从历史和史学角度有针对性地去加以剖析和评说,使它们有所发扬、有所放弃、有所改进、有所创新,对史学普及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以下我们就来简单地叙说一下三分法的具体情况。
史著。主要指以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为代表,并由此而生成的各种著作形式。它可以分为资料型、学术型和知识型;或者分为“用章节进行系统叙述的教材”,“篇幅较小,不征引原始资料的通俗读物”和“引经据典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页。)今天,不少学者所讲的“史学普及”在很大程度上还囿于“通俗读物”范围中,应该说,跳出此圈,海更阔,天更宽。
历史传记。指的是记载历史人物事迹的一种文字形式。关于传记的本质属性,在我国学术界有历史属性说、文史分离说、文史结合说和文学属性说,四种意见相持不下。(注: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8页。)传记本质属性的不确定,不仅给这一类图书在分类方面带来不便,而且还使史学界和文学界对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传记“似管非管”。史学界侧重其主要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性原则,对其艺术性则因学力、习惯等的限制往往一笔带过。文学界偏重其艺术性,对历史真实性等基本要求则轻描淡写。各自不同的评论重心引出两点麻烦:一是一些本应更为耐读的历史传记,却因僵化的套路、刻板的形式和呆滞的语言等原因,给读者留下不少不应有的遗憾。二是有少数不分是非、缺乏社会责任心和历史正义感的作者以“翻案”和“平反昭雪”为幌子,给一些早已有历史定论的暴君、恶人和丑类涂脂抹粉,以妆扮后的新形象接二连三地招摇过市。当然,这与部分文人信仰失落、金钱法力无边相关,但史学与文学中人也难脱干系,尤其是史学界对这种历史大是大非问题多是低调处理,没有鸣鼓而攻之,就意味着容忍与默认。“伪历史”和“假历史”从根本上误导读者,使那些缺乏科学历史知识的人由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甚至怀疑一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说,坚持历史传记的历史属性说或文史结合说,从史学思想和史学普及实践两方面讲都是必要的。
历史题材作品。指的是以文学艺术形式和手法来表现历史内容的作品。这是一个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的各种作品的泛称,包括有历史小说、历史记实作品、历史剧、以历史为内容的影视作品,等等。我们将历史题材作品作为史学作品的一个类型,并非“多管闲事”。理由有二:一是一部上乘作品理应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但在历史题材作品难求“两全其美”的无奈之中,内容当重于形式。既然此类作品以历史为内容,不妨将其纳入史学作品中。二是因当前此类作品所存在的十分突出的庸俗化倾向使然。这种庸俗化倾向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总是与误解、曲解,甚至编造历史内容相联系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庸俗化形式有二:一是非历史、假历史现象突出。一些历史题材作品(历史传记也有)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放弃历史客观性原则,在历史之外显功夫,过分地夸张和猎奇,主观地去揣测人物的心态,专注个人生活细节的奇闻艳事,等等,确实不敢让人恭维。如历史上集大功大过于一身的专制皇帝秦始皇,在影视形象上,要么是一位情场失意而内心极度痛苦的可怜虫,要么就是一位不理朝政而云游天下的剑客(不少时候还是蒙面的);铮铮铁汉荆轲被演绎成一位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殉情者,梁山伯、祝英台、唐伯虎等人的剑术与飞檐走壁功夫十分了得;中共地下党的市委主要领导人公然自投罗网,去换回在国民党狱中的妻子。类似于此的天方夜谭与客观历史实际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状况的经常出现,让人一言难尽。“他们企图证明英雄并不真的那么英勇,坏人也并不真的那么坏”。(注: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3页。)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文化常识而出现的语言、场景等错误,让人啼笑皆非。时光倒流,西汉人大嚼明中叶以后才传入中国的白薯,唐朝小李白极其超前地高声朗诵宋人所写《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孔子的父亲被尊称为“老爷”。孟姜女被叫作“孟小姐”之类,不一而足。更有将“留发不留头”的太平军将士的“长发”剃去,使之个个秃着脑门、梳长辫,从基本形象上抹去了他们与清王朝誓不两立的界限。看样子,对这种庸俗化倾向依靠零星的、就事论事的批评已难以奏效,将其纳入史学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尖锐批评,才能以正视听。史学界应该让一些此类题材作品的作者、编剧、导演和演员明白,历史题材作品绝不是靠随手翻读几则历史资料,弄点小聪明就能取得成功的。“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注: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不然,那种用自以为是的态度或凭感觉去写历史、演历史,又不说出点中听理由的事将一再出现。由此下去,史学普及将很快走向自己的反面——远离历史,远离大众,冲天而去。
史学作品类型由二分变为三分,首先,可以更充分和更完整地体现历史学综合反映社会历史面貌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其次,有利于扩大史学作品范围,使一些漫无所归的作品适得其所。再次,自觉认同历史传记和历史题材作品的历史属性,将其纳入史学范围,有利于建立起更广泛的史学评论机制,“扶正祛邪”,推动史学普及更健康地持续发展。可以说:“三分”史学作品是史学能否普及以及怎样普及的关键和先决条件之一,以下两个问题能够展开并得出结论也是以此为基本前提条件的。
二、史学社会功能与史学普及
近年来,史学界对史学社会功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对解决史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应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史学普及扫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但是,就二者关系而言,以下三点仍值得一提。
第一,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社会功能与单个作品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是协调的,不能“以全代偏”,前者尤应向具体化和多元化方向转变。
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社会功能是一种理论层面上对史学的社会作用进行的高度概括。它抽象出诸如史学所具有的揭示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的功能、认识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等,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覆盖各种史学作品;并且,这类功能对史学实践活动所起指导作用的时间特长,甚至是无限的。正是这种“广泛覆盖”和“长久性”,使我们在评说具体史学作品时,容易用整体功能的一般性说法去代替具体分析,甚至将一般性功能的各项内容综合起来作为评判某一作品的尺度。这种“求全”的偏颇,使一些社会功能相对单一的作品,如“史话”、“传记”和“历史小说”等难以得到中肯的评说。由此,“求全”价值取向驱使作者向它看齐,从而使不少作品好像是“克隆”出来的,至少在精神上。
我们认为,凡史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社会作用,与史学社会功能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整体功能保证史学作品的正确方向,并需要在具体史学作品中转化为具体和特殊功能才能对读者观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我们只重前者,往往只有“伤其十指”的效果;只有融前者于后者之中,才能真正做到“断其一指”,有所收获。
第二,用“变通”的观点来区别对待史学作品不同类型所呈现出的功能差异。
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和史学的发展,史著,尤其是其中的通史、断代史等,功能由单一转而全面,由简单趋于复杂。中国古代史书的主旨讲劝善惩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近代史书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都无法与现代史著所具功能的全面性相比较。与此相反,史学普及作品往往只突出部分的功能。如传统戏剧很“重要的文化功能还在于教会人们区别善恶的道德标准”。(注: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又如在“二十年代初期,小学教师讲历史,三国部分就是按照《三国演义》讲的”。(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3页。)前者强调建立“道德标准”,后者在正规的历史教科书出现后,自动失去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只有对史学作品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其功能或增生或剥离诸情况,才不至于“扬此抑彼”或“抑此扬彼”,才能对史学作品的多种类型少持一分成见,多发现一分可取;从而以平和与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们、接受它们。
第三,史学“消闲功能”应当得到承认。
所谓史学消闲功能,即人们有意识地通过史学作品来愉快地度过闲暇时间。一般来讲,这一活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它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二是它使一般人能感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如了解过去和怀旧等。三是它容易为人体验和理解。(注:黄琳斌:《论史学的消闲功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史学消闲功能是怎样通过史学成果体现出来的呢?又应怎样有分寸地去把握它呢?
作为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坚持史学作品类型的三分法,就能比较好地寻出与消闲功能相对应的合适载体。一般来讲,在诸如历史理论、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形式,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一些历史专题研究等著作形式,与消闲功能联结就很难,这也包括一些研究性质的历史人物“评传”。如《史记》、《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书中文情并茂的上乘之作,但读之以消闲者恐不多见。而在一般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等作品中,消闲色彩就较浓重。因为此类作品的作者可运用多种方式去叙说、描绘所记人物所处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时代背景、所具有的一波三折的经历、与三教九流人物的交往、特定时期又极具地域文化特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等,十分容易引人入胜。至于历史题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消闲色彩十分突出,以至于有时就连历史最基本的教化功能也只有淡淡的痕迹,甚至掩而不露,给人们留下非常广阔的思想空间。这大约算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佳作了。
就后一问题而言,当然不能因某一类或某部作品中消闲功能突出而排斥、否定和拒绝其他史学功能。如只重“消闲”,势必降低史学作品的水准,失去历史所特有的韵味,流于形式上的热热闹闹,到头来却空空如也。至于那种别有用心地去搜罗历史上的一些轶闻艳事,用不雅的文字、图画或镜头等去迎合和满足一些人的不正当的感官需求的做法,最不可取,是对史学普及的极大为害。因为它使读者观者认为历史毫无可取之处,一团糟。这是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的。因此,史学消闲功能绝不是任意所为,还是要以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科学地解释历史来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只是这个“益”有多有少,有显有隐,有直接有间接而已。总之,不能忘记“寓教于乐”是起码的要求。
三、文化市场与史学普及
今天,文化市场(注:文化市场,即精神文化产品发生社会作用的场所。)对史学有直接影响,历史选题的多样化,从政治经济拓展到文化领域,从社会精英转向一般民众、家庭婚姻等;鼓励“史话”、青少年历史画本等的创作;提倡改革文风,强调史书文采等,都标志着史学正在向文化市场靠拢。近20年来涌现出大量的历史传记和历史题材作品,更是文化市场直接催生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股以“实用”标准认定事物价值的社会思潮。史学的“实用性”颇受怀疑,史学也由以前处于学术中心向学术边缘转变,由热趋冷。出现“史学危机”一说,从而也引发了“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讨论导致了重大的史学转机:即史学必须面向社会、面向文化市场,不能再呆在象牙塔中,成为众多学人的共识。当然要做到真正的“面向”,尤其需要有意识地去努力探索和积极实践。在此,特提出三点浅见,以期引玉。
首先,建立坚守并拓展文化传统市场、争取中间市场、开发新市场的观点。
坚守传统市场,即史学面向那些目的明确、目标坚定、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以史著为主的研究成果,以传授准确的系统的见解深刻的历史知识、提高整体史学水平为宗旨。在此范围内,孤独的历史思想结晶,排比分析材料的历史考据成果等仍应有突出的地位。除坚守外,还需拓展,即史学充分地利用学科优势,自觉地走进社会,赢得社会的认同。“在国外,7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产生了一个公共历史学分支,他们以历史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宗旨,走出学院,去政府机关、企业公司、公共机构、历史文化遗址等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的在联邦、州、地方的政府机关做决策分析,有的在企业公司里整理档案、撰写企业史,帮助企业做政策研究,还有的参加文化资源的开发、管理和保护。”(注: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思考和借鉴的。
争取中间市场,指的是史学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历史传记、历史小说等的评论和创作。中国古代史学家中多有“传记”高手,近现代也不乏名家名作。而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创作者多与史学界不相干,尤其是后者。历史传记和历史小说等又是当前许多人通过轻松的方式接受历史知识和观点的重要选择之一,可以说影响大,穿透力强。但是,不少史学工作者连“评论”都觉得有失身份,又何谓“创作”呢?这其实是专业知识的一种极大浪费。史学界在中间市场无足轻重的状况亟需改变。
开发新市场,即史学工作者大胆地去涉足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等的评论、创作与拍摄,以有助于生产出更多地把历史美与艺术美更好结合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从本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史学大家郭沫若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历史剧。此类成功范例早已成空谷足音,不禁使人生出丝丝苦涩。
其次,史学作品走向文化市场,不应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
我们认为史学作品应随社会时代的进步潮流,并为之摇旗呐喊,而不是随金钱之波而逐流,要有益于人而不是相反。如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所吸引的观众数量十分惊人,忠于原著也值得称道。影片《红樱桃》以一则发生在一个中国女孩身上的故事,让观众去沉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永远无法抹平的精神创伤。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国藩》等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那里口碑不错。无庸讳言,类似于此,既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不是太多。相反,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作者和书商,抓住在社会转型期中一些人因失去信仰和缺乏理性,产生出追求赤裸裸的原始本能的人格缺陷,大肆造作。经他们之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帝王、皇后和军阀武夫等的荒淫无耻、宦官的性变态等都闪亮登场,并且不吝笔墨,着力渲染。为满足一些做着发财空想梦的人,豪商巨贾“传”又纷纷出笼,其中有的“传主”与经商无关,被强行拉入。在传中,作者绘声绘色地去描述豪商巨贾如何玩弄“钱变权,权变钱”的官商勾结的鬼把戏、行贿受贿的伎俩,等等。长此下去,史学普及只能说“道路曲折”,不能说“前途光明”。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读者对史著的接受及其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很多学者比较容易认同历史传记、历史题材作品是史学普及的形式,但却认为史著的“普及”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偏差呢?一是认为史著的学术性与“普及性”只有对立,没有统一。在强调所谓“学术性”的思想偏颇影响下,一些史学成果在理论上的尖深玄虚,使人如堕云中;部头之巨大,使人不敢正眼相望;语言之枯燥艰涩,使人难以卒读;等等。这种成果欠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对读者的关注,只好“养成深闺”中,成为“明日黄花”。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将学术性与“普及”、与读者割裂的思维偏向的结果。二是对历史学的全过程认识模糊,不少研究者只重视自己的撰述过程,忽视社会和读者接受的过程。其实著作的完成只是全过程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将读者纳入考虑范围,史学工作者在思维方式、写作习惯等方面都需作出较大的适应性调整。18世纪英国杰出的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说:他要使他的著作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摆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采用通俗的方式,不用一个注释,将本来像一团乱丝和枯燥无味的问题,如阴阳五行、封禅、神仙说、灾异说、受命改制,谶纬等,像讲故事一样一个一个有条不紊地讲出来,而且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如胜,娓娓动听。这是在长期潜心研究和高超的语言能力基础上产生的上品。可以说,只有对读者的重视,才会出现既有学术品位又有可读性的史著;只有相当数量的史著得到普及,史学普及才是完整的;只有完整的史学普及,史学才算是与社会时代同步。
综上所述,“三分”史学作品类型既是史学作品现状的反映,更在史学普及问题上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史学社会功能与具体作品的特殊功能之间的关系,史学消闲功能等都有赖三分法而成立;文化三市场说、关注读者更是与三分类型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反过来看,后边两大部分的论说又使史学作品“三分”更具合理性。可以说,以上所讲史学观念的调整与转变,将使史学普及更具活力;从长远看,史学普及的情况将影响到我国史学在下一世纪的合理定位、存在方式和总体格局。
收稿日期:2000-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