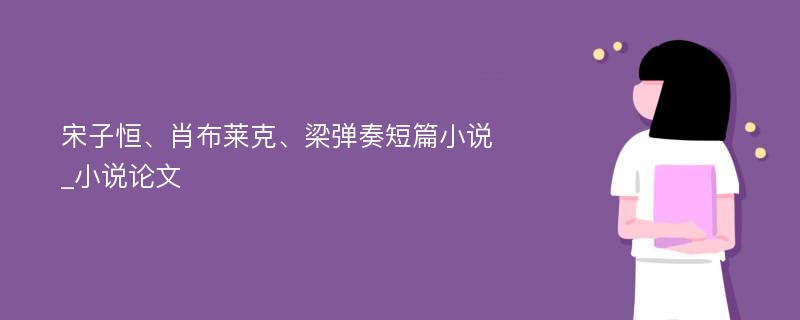
宋子衡、小黑、梁放短篇小说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试论论文,宋子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华文学发展至今近80年,其中以小说最为丰收。
50年代开始,就有马来西亚年轻学子留学台湾,其中有不少人在台湾创作。70年代开始,潘雨桐、李永平、张贵兴、商晚筠等留台生的小说创作受到台湾文坛广泛注意,作品在台湾结集出版。80年代马华作家开始与东南亚各国及港台地区进行多次文学交流,加上90年代大马政府全面解除人民访华限制以后,不少的小说作家有机会在中国台湾及大陆出版个人小说集,使马华文学能够更广泛地介绍到各国去。
本文要介绍的是三位杰出的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小黑和梁放。他们三人多次获得小说奖,功力很受本地文坛肯定,而又未曾在国外出版过小说集。
宋子衡
宋子衡,原名黄光佑,祖籍广东惠来,1939年出生于北马。五年级即缀学,60年代开始创作。
宋子衡被公认为马华文坛中,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得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他在1972年出版的《宋子衡短篇》及1987年出版的《冷场》两本小说集里收录的29篇小说,主题几乎是一贯的,即在求人性完善的本质,在怀疑中寻求肯定人的位置、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尊严等等。
宋子衡喜欢在小说中为人物安排一些困境和危机,并描述不同人物在不同遭遇中的各种反应。这些反应,不论是理智的或是愚蠢的,都说明人正本能地在挣扎着活下去。他尤其喜欢探讨人在面对问题时所作出的“荒谬行为”,以此来表现人生境况的荒谬性。小说中呈现的荒谬,既是一种事实,也是某些人对这种事实的清醒的意识。作者借此来说明荒谬其实是人的生存条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乐天庐夜宴》中,作者描述一个由中国赤手空拳南来的涂乐天,以40年的血汗来追求一生中的一个大目标,即“用整百万元建筑一间最豪华堂皇的红毛楼”。这幢建立在山上的楼阁“乐天庐”,终于在主角70岁时落成。主角在70岁大寿当晚举办了一个盛大庆典宴会,为他的生日,也为“乐天庐”的落成。这一天,“两个庆典融合成了一种深重的意义”,“他知道,今晚是他生命趋入饱和点的时刻”。一向穿“黄斜纹道地唐装,习惯展露胸膛”的主角,破例穿上西装大衣,“尽管怎样的不舒服,不习惯,他也乐意承受,只为配合这个宴会的隆重性。在望着工人们为晚宴而忙碌时,他竟然有动手帮忙的冲动,因为那些动的影子根本就是他自己”。
从跳板到人力车,从人力车到小杂货摊,40年后的今天,他已是一个实业家,一幢豪华洋房的主人。他的心情极度开朗极度兴奋,因为这一天是他充满生命光彩的日子,他已达到用一生来追求的目标——寻找理想中的完美。这令他的生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就在他那生命辉煌的书页正等待着宾客们来赞赏、来领略时,他突然感到一切都很空洞,“这不只限于空洞的,而是整个生命的感觉”。先前的满足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焦急与不安,那是令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反常心理。作者在主角与得力助手俞国锦的对话中,透露了主角的这种心理:
“锦兄,你看那窗上的雕龙怎样?我看它象缺乏了生气。”
“我觉得它很美,它不是已成为龙了吗?还要求什么?”
显然地,主角非常抗拒心中那种空洞的感觉。空洞表示不满足,有缺憾,然而主角却不认同会有什么缺憾,在这一个生命价值可以获得肯定的时刻。在描写主角的微妙心理状况时,作者运用富有张力、无比饱满的意象,利用事物或场景构成象征意义,达到了意外之意的效果。较为特出的是“声音”的描写,他以声音来象征主角的安全感。向来对吵杂声很厌烦的主角,此刻却渴望更多更吵的声响,因此“他让宾客围着乐天庐,让更多更吵杂的声音由山坡下逐渐涌向乐天庐,仿佛这些声音能够衬托自己的生命。”接着,吵杂声越来越强了,有宾客歌功颂德:
乐天伯,乐天庐真了不起,百闻不如一见,不亲眼看到还难教人相信呢
!天兄,乐天庐真的是一种成就。天伯,乐天庐花去多少钱呢。乐天兄……
还有筷子、酒杯、盅碗的碰击声。当场面越来越热闹、喧嚷声越来越强时,涂乐天心中的空洞就能够被补得越多,心中的安全感就会越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肯定就越多。
等到四小时的宴会结束,喧嚷声完全停止时,主角发觉他必须面对一个不能逃避的新的事实:“一个生命能抵御着种种艰难,必然是为了一个目标的牵引,一层一层地跨跃过去。”而他已爬到这儿了,会不会就是止境,他开始感到混淆和矛盾起来。他仍想停留在那四个小时内,然而“收拾杯碟的人一个不小心,掉下一只酒杯,那尖锐的碎裂声使他震醒过来”,使他不得不从生命的顶点中跌下,然后陷入难以忍受的空虚中。主角没有想到,他穷尽一生所有的活力去追求理想中的完美,追求到以后,完美反而成了一种困境,一种不完美。或许他可以继续追求另一个目标,然而他终必有他的局限性。在这儿,荒谬被作者表现为一种人们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生存之间的割裂或矛盾,以致主角想把乐天庐毁掉,因为“乐天庐仿佛不停地在扩大、在增高,而他却不断地在缩小、在缩小……”。完美成了缺憾,得着成了失去,寻获生命意义成了失去生命意义……这一切,不是作者消极之举,而是对人类无止尽的欲望之感叹及对人类的不知足颇有反抗意味的承认。
小黑
小黑,原名陈奇杰,祖籍广东潮阳,生于1951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及教育系,目前为一中学行政人员。出版过小说集《黑》(1979)、《前夕》(1990)、《悠悠河水》(1992)、《白水黑山》(1993)及多本散文、杂文集。小黑的小说内容都立意在反映生活与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注重取材的社会意义。傅承得曾指出:“小黑的率真耿直和满腔热血,使他对社会上的种种光怪陆离而别人又习以为常的现象不满……一个作家应有的真诚和勇气,我在他身上找到了。”[①]在其小说作品中,他常以民族本位为依凭观照现实,批判一切有损民族尊严的社会现象、变态人物与灵魂。小说不仅具有剖析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刻性,也充满创新意识,显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
在1987年10月27日,马来西亚发生了大逮捕事件,既“茅草行动”。在这事件之前,大马出现极端种族言论,使各族间的关系因经济、文化、政治及教育的困扰而呈现出不稳的现象。一些种族极端分子发表的煽动文字,以及某些政治领袖把华人称为“外来移民”的言论,令华社愤愤不平。接着华文小学的风波,令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忧,于是引发了“天后宫事件”——数以千计的华裔,不分党派集在天后宫作出抗议。不久后,马来极端分子也召集了一个大集会作出抗议,令种族情绪一时非常紧张,担心1969年的5.13历史事件会重演。而后,政府就展开大逮捕行动,令人震惊不已。小黑的《十·廿七的文学纪实与其他》,通篇采用一则虚构故事,再串连几篇不同作家先后发表在报章上的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摘选,追述了86年大选前的不安稳情况,一直到大逮捕过后的余荡,构成一部表现形式新颖的文学作品。
在摘录文学作品及评论文章的同时,小黑也以报导式的手法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写出来,再以纵横交错的叙述观点把实际的文字报导与虚构的小说故事组合起来。作者的意图并不仅于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小说透露了他对种族极端主义政客刻意玩弄种族间的敏感话题而造成两极分化现象日渐尖锐的不满。
此外,小黑也借此作品来探讨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态度。他曾说:“优秀作家必须有良知、勇气、还有爱。他爱家,也爱国。因此在跟着社会一起成长的同时,审视、纠正、批判社会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了。”[②]文中摘录了诗人方昂、何乃健、傅承得的诗作,唐林的评论文章及小黑本身的一首颠倒诗、小说及社会评论,让读者看到文艺工作者在面对“外患”时的一股力量与勇气,否定了“大马华裔作家自我恐惧,不敢面对事实”的言论,并道出了在我国特殊政治环境下,作家的反应“必须无愧于面对自己的民族外,更应该对其他民族公正,无私”。而我国对本地华文报刊的文章一向也用严谨的态度去审查,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谨慎,绝不能写出偏激、敏感、情绪化的文字。
《十》这篇小说就是一个佳例。乡青小说推荐奖总评陈雪风对这篇小说作出以下的评语:“……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与发生的各种事件,即使是敏感与尖锐的,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不能轻易去碰的事件,只要作者多动脑筋,发挥巧妙的构思,采用适当的形式,都可以撷取来作题材,写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③]
如果《十》的主题是探讨华社面对外患的困境,《前夕》则道出华社内忧的主因[④]。在《前夕》里,小黑剖析了华社的病情,揭露了华社低沉的一面。文章如唐林在《沉痛的挽歌——读〈前夕〉有感》里指出的“它犹如华社沉沦一面的送葬曲,一首叫人感到沉痛的挽歌。”[⑤]小说中整个家庭里的几个成员(父亲,大、二、三哥,叙述者(妹妹))以及大专生小固,事实上,就是整个华社的缩影。作者通过这个家庭不同人物的政治意识探讨了华社与政治的关系,文中透露了华社充满投机取巧、争权夺利的政客,只晓得趋炎附势、盲从愚昧的小人物,有政治理想的却因各持不同观念而无法团结及合作的政治工作者,以及受过高等教育却没有政治意识的年轻一代,从而揭露出华社问题的症结,并表现出作者对华社的担忧。
在《白水黑山》里,作者的野心就更大了。这是一篇中篇历史小说,其时间跨度差不多从日军于1941年占领马来亚,一直到80年代为止。小说通过几个人物的沧桑史,描绘出马来西亚近50年来政治、社会的演变,其重点放在描绘抗日时期一群热血青年从事游击队的抗日行动,而后来走出森林后的生活面貌,那是发人深省、充满正面经验及反面教训的一段历史。此外,他也从人事的沧桑变迁中,刻划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对人性作出了探讨。小说无论是内容、主题思想、或其表现手法,都是由作者精心策划及思考提炼出来的,尤其是表现手法,具有创新的特色。
小说内容丰富,作者要探讨的事物很多,其中一项是通过几个人物探讨时代变迁中变与不变的人性。白猴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在英国殖民地时代他是英殖政府的爪牙,与洋人同声同气剥削同胞;在日治时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在动荡不安的乱世里过得风风光光。几十年来,无论政局怎样改变,他仍以其“见风转舵”的生活方式过得很风光。在不同时代里,在社会不断变迁下,白猴的“随机应变”使他一直过着有钱有势的生活,作者对这种“变中的不变”性格作出了嘲讽与无奈的感叹。
与他成为对比的是陈立安。年轻时他跟着游击队领袖杨武出生入死,受他的影响极深。走出森林后的陈立安把杨武当成偶像,把感情寄托在黑山,陷溺在过去的“辉煌岁月”中,一直对自己不能在森林里与杨武共患难而耿耿于怀。固执的陈立安不愿意调整自己适应一变再变的时代与社会,以不变来表现他对理想与信念的坚持,因此一直过得很不快乐。直到有一天,他以为早已经“壮烈牺牲”的杨武出现了,他发现心中的英雄已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得不再是当年热血满腔、执着追求理想的积极分子,而成了为世俗应酬忙得乐不思蜀的俗人了。杨武的“变,是适应环境的基本求生法”,粉碎了陈立安的信念,以致后来他终于离开当初他留下的黑土镇,跟儿子到他乡去安享晚年。陈立安从不变到变,是作者对处在新时代新政治气候下、不肯改变一些狭窄观念的华裔作出的感慨。
无可否认,小黑的小说作品强调了民族的反省及唤起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嘲讽、理智的凝视代替感情的反拨,冷静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发抒。他以这样的方式解析他周遭的事物,使问题意识显得更为鲜明,容量也较为辽阔。
梁放
梁放,本名梁光明,祖籍广东新会,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劳越砂拉卓镇。他在华文小学接受6年教育、在英校念中学后,负芨英伦,现职土木工程师。他在1980年开始创作小说及散文。
梁放所生长的乡土、环境,以及他的体验与思索,引导他走向小说创作。在《烟雨砂隆》及《玛拉阿妲》两本小说集中,收录了他创造的一系列阐释砂劳越风土人情的小说。
在《龙吐珠》里,他描写早期从唐山南来的华裔与伊班族女子的故事,反映了早期砂州特殊的社会状况与民族关系。作者通过一个从唐山南来的华裔与一个伊班族女子结合所生下的儿子古达之叙述观点,来揭示一个家庭悲剧。古达的父亲(阿爸)以过客的心态在砂州落脚生存,托人找来一个16岁的原始居民伊班族女子“印代”(伊班语,母亲之意),表面是要为他打理家务,事实上是要一个能为他长期提供服务而自己却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女人。印代对阿爸产生感情,对他死心塌地,甘心地留在他身边任他摆布,默默承受阿爸无情的对待,并为他生下儿子。阿爸不肯承认这个他坚持要打掉的骨肉:“怎么会有你这孩子的,黑黢黢的,拉子种!”他一向就处处显得比印代与古达优越,吃饭时一个人在桌子上开饭,母子两人则坐在桌子脚边的草席上吃。此外,阿爸的眼中根本没有母子两人的存在,他一心一意想回去唐山,因为“那儿才是家”,“那边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与儿子”。这边的私生子与原不关紧要娶来为了陪宿的女子则是“拖累他,害他多了两张吃饭的口,妨碍他提早蓄足钱回去的扫把星”。
马华文学中,描写从中国过番到马来西亚的华裔之沧桑遭遇的内容并不少见,然而一般故事发展都是主角在南洋落地生根,建立新的家庭,然后在良心的谴责之下,尽其能力去补偿隔海另一岸的发妻与孩子。梁放的这一篇小说则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原因是选择具特殊社会背景的砂州为故事背景令他有更大的发挥。砂州土著伊班人的低微社会地位及其善良、逆来顺受、忍耐力强的民族性格令印代成为阿爸“回唐山”意识与行为的牺牲品,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性,而另一个牺牲品古达,从小因身上有一半母亲伊班族血统而受到歧视、长大后耻为“拉子”、憎恨自己的身份而不愿意认娘的作法,更为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力与感染力。
《锌片屋顶上的月光》与《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有着相同的主题,即揭露砂州陷入紧急状态时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些悲惨事件。在《锌》一文中,叙述者回到自己的故乡母校执教时,忆起了当年的老师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通过现实与回忆穿插的方式,作者从刘老师及秦老师的际遇,揭示了马共组织渗透民间而造成的不幸事件。《一》则通过主角探访已故姐姐、姐夫遗下的孤儿,带出当年马共活动带给人民不幸、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的故事。小说探讨了深受其害而支离破碎的家庭三代成员,在恐怖及悲惨的经历过后,如何适应及调整自己以面对现实。小说虽没对砂州风情民俗作具体的描绘,乡土色彩并不强,然而它们就像是砂州的历史片段,令人看了对那恐怖的日子感叹不已。
在《烟雨砂隆》及《温达》里,作者则描写了都市人走进原始居民的土地,从都市人的眼来看这片土地的人与事。在《烟雨砂隆》里,小说中的几个工程师从繁华热闹的吉隆坡来到砂州小镇“坟”工作。他们都是“摆脱不了人类物质文明”的人。小说通过一宗在砂隆河发生的覆舟死亡意外事件,含蓄地表现出朴实平淡的乡下生活给人的不同感觉。对文中的叙述者,这片土地“尽是看不断云与树,走不尽的是诗意盎然的羊肠小路”,而对意外事件中的死者而言,乡下生活是苦闷寂寞的,以致他冒险乘船到土族的长屋里去找女人解闷,却不幸在汹涌的河流中丧命。
《温达》则是通过叙述者因公事重新踏上阔别了10年的砂州美丽的小山城鲁巴安,与伊班族友人温达重逢叙旧,带出了他们相识且建立了深厚友谊的经过。10年前叙述者以工程师身份到小山城来进行一项现代化工程,以自己是“改造这一片旷野森林的一份子,以期日后向西方文明看齐”的优越感来到该地,雇用了温达当团队随身助手。纯良的温达身上有着浓厚的被落后观念所囿的历史积淀,但仍有不少道德精神的闪光,勤劳质朴的民族品格溢露至深,民族文化的津液仍在他的血脉里流淌。这使叙述者从一开始对他的轻视、能力的怀疑及戒备转变为一股浓厚又微妙的感情。最后,现代化工程结束了,叙述者在临走之前由衷的对温达道谢,而这道谢“指向还不止因为温达曾拯救过我”。在这儿,作者巧妙地安排了“道谢”来暗示叙述者从原本的“施者”身份转变成“受者”的身份。当初以欲改革这片土地的优越姿态出现,而最后自己却转变成被这片土地改造的人(价值观之改变),这一切隐隐约约地蕴藏着象征意义,说明这块土地上,时常传统与革新、容纳与排斥冲突,而溅起浪花,久而久之又复归于沉寂。而把所有对立的矛盾予于统合的,便是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与挚爱。
以上几篇小说,虽然各有不同的内容、故事与技巧,然而予于连缀,就巧妙地反映出砂劳越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特色与时代精神,以及每一阶段的讯息。无论从人物性格的刻划到环境氛围的营造,从风情习俗的描绘到语言的运用,显示出作者真诚地反映了他所熟知的社会与生活现实。
注释:
①傅承得:《愤怒的小黑》,《南洋商报》,1986年12月10日。
②张曦娜:《作家·爱·良知——专访小黑》,小黑《悠悠河水》,(艺青,1992),162页。
③陈雪风:《赶路,是不分昼夜的》(《十》这部小说获得1990乡青小说推荐奖,此文乃乡青小说推荐奖总评),小黑《悠悠河水》,160页。
④何乃健在文章《传达给年轻一代的薪火》中指出华族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困境,基本上有二,其一是外患,其二是内忧。外患的根源,是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内忧的主因是华社的一些劣根性造成。
⑤唐林,《沉痛的挽歌》,小黑《前夕》,(十方,1990),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