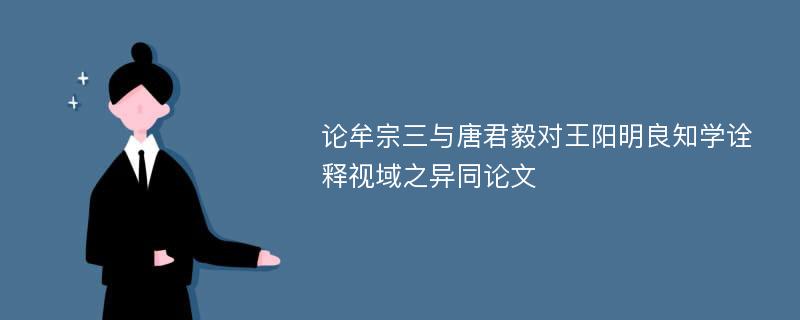
论牟宗三与唐君毅 对王阳明良知学诠释视域之异同
李 玮 皓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在牟宗三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于现当代有两个诠释向度:一是成就了知识逻辑等之“执的存有论”向度;二是从形上学方面以道德实体之呈现落实而贞定天地万物之在其自己之“无执的存有论”向度。唐君毅则立基于“良知”为吾人生命之意义之根本之诠释视域下,提供吾人论述王阳明良知学如何建立现代人文世界一条可供参照之道。两者立说皆建立于王阳明文本之充分把握上,而正面肯定王阳明良知学之意义价值。然两人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理解仍有其差异之处。总结两人诠释视域差异之处可就三点说明:“思辨分解”与“辩证体验”、“逆觉体证”与“性情感通”、“宋明三系说”与“朱陆之通邮”。
关键词: 牟宗三;唐君毅;王阳明;良知
在宋明理学之研究上,阳明学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具有丰硕之成果。而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为当代港台学界研究王阳明良知学之大家,当代研究宋明理学之学者所申论之议题,多半承接或面对牟先生与唐先生两人之诠释视域而加以发挥。牟先生通过康德自律伦理学,重新诠释并肯定王阳明良知说之义理,足以作为吾人之先验道德主体之自觉,彰显吾人之所以为人之尊严与价值;反之,唐先生则透过“道德自我”与“生命存在”为核心并加以辩证,强调道德主体感通于生活世界中,且挺立自我之生命,进而拥有道德之生活。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皆正面肯定并深化王阳明良知学对于吾人生命之意义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以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小语种。小语种是指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如法语、德语、越南语等语言,“一带一路”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人员以及当地人才共同努力,因而使我国产生了小语种人才荒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小语种课程,其教学模式也面临转型,企业对小语种人才培养也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目前两岸中文学界对于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二人个别针对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研究不胜枚举。而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诠释视域之比较,主要着重在朱熹义理上。如乐爱国先生的《牟宗三、唐君毅对朱陆异同的不同阐释与学术冲突》指出,牟先生“认为朱陆异同在于:朱熹把道体性体看作只是理,而陆九渊看作只是心;朱熹为‘性即理’,并非等同于陆九渊‘心即理’”。唐先生则认为“朱陆异同在于工夫论上同时两者又可以相互贯通”[1](P66)。陈振昆先生的《牟宗三与唐君毅对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对比诠释》则从价值意识、方法论与诠释系统三个基础性的差异上开展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的对比诠释,而得出牟先生本于孟学的“本心之义道”,与唐先生本于易学之“仁心之生道”来诠释朱熹义理中之丰富意涵及其体用、动静关系[2](P196)。吾人可从上述文章中看出身为当代新儒家之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对于朱熹义理之诠释有异有同。然吾人要在此进一步追问的是:相对于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对于朱熹义理之关注,少有学者将牟宗三先生之诠释视域与唐君毅先生之诠释视域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互相对比,进而展开论述。其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视域是否亦存在着异同?
基于上述之讨论,就学术思想史之角度而言,探究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二人对王阳明良知学之对比诠释,乃为吾人值得正视与省思之现代新儒学议题之一。职是此故,本文以《王阳明全集》与牟先生、唐先生之著作,作为主要征引书目,另随文征引当代学者之讨论,以论述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之义蕴,并探究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旨趣。
一 牟宗三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视域
牟宗三先生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主要见于《王阳明致良知教》与《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两部著作之中,《王阳明致良知教》之旨趣主在诠释王阳明致良知之义蕴。然20年后,牟先生认为此书可作废[3](P215)。而可废之缘由可就两个层面而论:其一是当时牟先生对于王阳明与朱熹、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刘蕺山等宋明儒者之间之关系,理解之程度尚未成熟。其二是王阳明之义理乃是其自身经由百死千难后有所体悟;而吾人亦可从《王阳明全集》中之诸多语录见王阳明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易传》等经典提出其之理解与诠释,是以吾人能够透过文献与经典来理解王阳明,是更为体贴于王阳明之良知学中。职是此故,牟先生认为,其独立诠释王阳明之义理虽不致有误,然若要将王阳明义理体悟透彻,最好不要单独讲。
同时,吾人从上述两书中均可见《致知疑难》一文,然吾人要在此进一步追问的是,牟先生在《致知疑难》一文中欲处理之问题为何?首先,牟先生即以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4](P6-7)作为其“随文领义”论述之起点而言:
阳明在此所谓“物”是吾日常生活所牵连之种种行为也,实即具体之种种生活相也。既是生活相或生活行为,自必系于吾之心意。吾之每一生活,每一行为,吾自必对之负全部责任。吾既对之负全责,自必统于吾之心意。[3](P245)
牟先生深识高见之诠释开拓吾人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视域。然亦有些问题仍待讨论,曾昭旭先生即言:
牟先生指出,王阳明所言之意之所在之“物”,不应仅仅被理解为纯心理之意向;所谓“意之所在”乃指吾之心意系在于种种行为或种种生活相。此亦体现王阳明所谓“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4](P3)。是以“事亲”“事君”“仁民爱物”亦或是吾人平日之视听言动之感觉与语言行为等等生活世界中日用人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皆包含着吾人生活之意愿、态度、责任,且包含与吾人生活中产生联结之对象。
复次,牟先生进一步以“桌子、椅子”之喻,以诠释“知识”与“良知”之关联[3](P245-247)。吾人之良知虽能断制行为者之行为,却无法断制眼前之物之何所是。牟先生先区分所谓“物中之理”与“德性之理”。认识物中之理之心和认识德性之理之心乃非同。认识物中之理之心为“了别心”;认识德性之理之心为“良知”。物中之理有其质,不同于德性之理。即如天体运行有其必然之规则,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吾人每个临事之当下之自我之自由意志所做出之自我决断与对自我之行为负责。依王阳明心外无物之旨趣,吾人生活中之所有洒扫应对进退皆与吾心必然产生联结。是以牟先生将王阳明所言之“物”“心外无物”等相关义理归于“乾坤知能”形而上之命题,并将桌子、椅子等客观之事物归于知识理论之问题。总而言之,牟先生认为吾人应将此两者加以区分,对良知本体与道德行为之反省以建立“道德形上学”;通过对知识行为之反省以建立“知识论”。所以,牟先生言:“在致良知中,此‘致’字不单表示吾人作此行为之修养工夫之一套,……且亦表示须有知识之一套以补充之。此知识之一套,非良知天理所可给,须知之于外物而待学。因此,每一行为实是行为宇宙与知识宇宙两者之融一。”[3](P250)职是此故,可见牟先生尝试以曲折之诠释方式将知识理论之问题收摄在王阳明致良知之义理下。
牟先生进而以“行为宇宙”与“知识宇宙”来诠释儒家如何参赞天地之化育[3](P249-250)以先区分所谓“行为宇宙”与“知识宇宙”。牟先生所言之“行为宇宙”亦可称“良知系统”,即为王阳明所言之事亲、事君、仁民爱物、视听言动之“物”。此宇宙之旨趣即如王阳明所言:“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4](P244)由此可知牟先生依王阳明之意,强调吾人之良知天理之实体乃人生宇宙之大本。在形上之良知天理中,本无心物二分;然良知本体不容己,是以须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中,通过吾人之道德实践致良知之义蕴。
再次,牟先生所言之“知识宇宙”亦可称“知识系统”,此宇宙之旨趣即在:“吾人一方获得对象之知识,而成功知识之系统,一方对此‘知识行为’加以反省而明白如何成知,此就是知识论。在此步反省中,知识方法、逻辑、数学、纯几何,乃至一切知识条件,皆有安顿。”[3](P256)析言之,牟先生欲将知识宇宙收摄在良知之下,在致良知之行为历程中,既蕴含抉择致良知之道德心,亦包括认知事物之了别心。此诚如王阳明所言:“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4](P81)总之,牟先生从王阳明良知学之视域来看吾人一切追求知识之活动,皆为良知之间接表现。
牟先生在良知系统、知识系统这两个系统中,并非为“双向融入”,而仅是“单向融入”。即良知系统能够融入知识系统,牟先生提出之解释为“良知之自我坎陷”,良知决定坎陷它自己转化为了别心。就此了别心而言,心与物为对,心与理亦分二。吾人能通过了别心,以成就知识之系统。其缘由在于吾人良知之自决自定。致良知亦即致天理。良知自我呈现,自我体悟良知进而致良知。此时吾人良知与天理之关系乃直通。无内外、心物二分。然就了别心而言,心物二分,知识理论并非由良知直接提供,乃是通过辨物析理方能获得。了别心不能直接体悟本体,唯有复归于良知,通过良知方能体悟本体。此时吾人了别心与本体之关系乃曲成。
然在此吾人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牟先生亦提到,知识系统是“非良知所能断制”,由此可见,知识系统似乎难以收摄入于良知之下,然牟先生又尝试诠释知识系统摄入良知系统之进路,是以造成牟先生在论述知识系统收摄良知系统之理论困难。对此,牟先生则是強调:“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从物使能知物,知物使能宰物。”[3](P251-252)牟先生认为,吾人之良知本体亦可经由坎陷自己转为了别心从物知物进而宰物,而蔡仁厚先生曾将牟先生致良知之行为历程分为五步:(1)良知天心决定成就——应当之行为。(2)在致良知之“致”中,良知决定坎陷它自己以转化为了别心。(3)了别心在与物为对中发动知识行为以成就知识系统。——对此知识行为加以反省,即成为知识论。(4)融摄知识宇宙而会归于行为宇宙,使知识统属于良知。——反省一切行为而知其皆统属于良知之天理,即成功道德形上学。(5)良知恢复其不与物为对之天心天理之本性,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各得其成。——这最后一步即形上之直贯,表示致良知教之圆满完成[5](P67-68)。总而言之,在牟先生之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于现当代有两个诠释向度:一是成就了知识逻辑等之“执的存有论”向度;二是从形上学方面以道德实体之呈现落实而贞定天地万物之在其自己之“无执的存有论”向度。职是此故,牟先生将王阳明良知学之视域彻底发挥,吾人之良知呈现必须在吾人之生活中透过道德实践展开,此展开之过程必须有一客观之历程,以涵摄知识,生活世界中之吾人道德与知识亦不相离。
二 唐君毅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视域
林先生所言乃是针对在牟先生之诠释下,其高举道德本心,过于强调超越之“良知呈现”之境界,将自我主观之良知呈现视为客观标准之格局教条而教导他人,并落实在生活世界中作一普遍之行为判准,而导致无视道德情境权宜性之可能,此易构成吾人彼此间之违隔不通。
如是,吾人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阳明看来,作为创生天地万物之良知,与吾人之间是如何之关系?原来王阳明所谓吾人良知灵明所呈现之一气流通,使天地万物本具之意义,皆透过吾人心中之一点良知灵明而获得彰显,吾人之心进而方可超越与天地万物之限制[4](P141)。唐先生即补充道:“心之被‘限制’所限制,亦其自己所决定,因为心之活动之本质即超越向上。”[9](P125)是以王阳明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吉凶灾祥、万物之存在之朗现与吾人之良知连结合一,真实实践良知全体之大用。
诚然,王阳明在此并非否定外在客观事物之存在。其主观地肯定吾人与天地万物以吾人之良知感通之重要性,藉由吾人对于自我内在良知之肯定,并以吾身实践之,进而通向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唐先生即补充道:“当你的心体会了生命世界、物质世界之精神的意义时,你的心开始笼罩着宇宙之全境了。你将真觉整个的宇宙如全呈现于你心灵之镜。物质、生命、精神,在你的心中同时存在。但是当你发现这三个东西,同呈于你整个的心灵时,你将进一步发现,这三个东西,原是互相渗透的。……宇宙之一切存在,原来是一互相渗透,互相转变配合之一和谐之全体!当你真能体会全宇宙之互相和谐时,你将发现宇宙本身之美,宇宙是一复杂中之统一。你有如是之思想时,你心中的宇宙之各部,自己互相贯通了!”[10](P158-159)在此仁心感通之无限过程中,吾人之良知即为宇宙天地之中心,而宇宙天地即获得生生之机。
王阳明以为吾人之心体是至善之良知本体,然吾人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良知本体为至善,那么,吾人时常感受到之“恶”或私欲,是从何处来呢?吾人可从王阳明以除去园中花间草之譬向其门人薛侃阐述至善之良知本体与生活世界中善恶之别[4](P33)。王阳明阐述生活世界中“善恶”与“好恶”之别,花与草皆为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之物,然之所以名为花,之所以名为草,乃因吾人判别而有花与草之名之别。然对于花与草之自身而言,此名之别乃是因吾人由躯壳上起之私念私意、动于气而外加之。是故,因吾人外加之名,亦即皆随此名而伴随着对外物好恶贵贱之主观评价。花与草之善与不善,甚至天地万物皆并无意义价值上之善恶之别,乃因吾人之良知本体之好恶判断而有此之分。是以吾人必须要做到不随自我之躯壳起念而不动于气。王阳明在此并非要吾人不去作价值判断,而是在价值判断之当下,必须“循良知天理之流行”而不着意,进一步做到不滞不留,一以贯通。王阳明虽肯定吾人天生本具良知本体是以皆可成圣,而有“满街皆圣人”之主张。然若吾人不时刻加以对自身躯壳所起之意下工夫,则一念陷溺,唐先生指出:“人种之罪恶可以齐天,可用一切善为工具,以畅遂其恶,然而其产生之最原始之一点,只是一念之陷溺,由此陷溺而成无尽之贪欲?……人之可以由一念陷溺而成无尽之贪欲,只因为人精神之本质,是要求无限。人精神所要求的无限,本是超越现实对象之无限,然而他一念陷溺于现实的对象,便好似谓现实对象所拘絷,他便互会去要求现实对象之无限,这是人类无尽贪欲的泉源。人所接触现实对象,本是有限,只有精神之自觉才是无穷无际,人陷溺于现实的对象时,他失去了他自觉中的无穷无际之感,于是想在现实的对象中,获得此无穷无际之感,于是人才有了无尽之贪欲。”[6](P156)恶即伴随而生,亦即偏离了儒家义理之正道,丧失了吾人生命之意义价值。
(1)Th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level among primary students isvery low.
唐先生肯定吾人若在每个遭遇困难之当下皆能一念自反:“不陷溺之念即是天理流行,依乎天机而动。……诚然,我们要常常自觉有不陷溺之心境,非最高的人格不能。但是当下的不陷溺的心境,则是一念自反,即能具备的。因为我们才觉有陷溺,知病便是药,我们的心便已不限溺。我们觉有陷溺而拔出,即不陷溺。这是我们当下可以求得的。我们亦可说,我们之不陷溺的心,原即我们之从事一切现实活动的心之‘本体’。我们只怕不自反;才自反,它便在。而一念之超拔,即通于一切的善。”[6](P168)
参照国标GB/T 21562—2008《轨道交通 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17]以及AQ 8001—2007《安全评价通则》的要求[1],总结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安全风险预评价方法步骤如下:
所谓致知格物者,……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4](P51)
(1) 由潮流的双向流动带来的继电保护配置整定问题。传统的配电网是单向电源网络,主要使用三段式电流保护;当配电网中分布式电源较少时,仍可使用电流保护;但当分布式电源达到一定规模(穿透率较高)时,分布式电源严重影响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和灵敏性;但如果使用面向双侧电源的差动保护,又会增加配电网投资。因此,分布式电源引起的继电保护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7]。
依王阳明义理系统而言,其探究的是当吾人生命遇到困境之时,该如何去复求心物合一。良知本心即为吾人心之本体,亦为天理,即为至善之存有,此为本体论;“致”即为充分推致与恢复,此为工夫论;致良知即是本体亦为工夫,而王阳明实以“致良知”之工夫收摄“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之义理将其打并归一工夫。唐先生则补充言:“真能知此良知本体之好善而恶不善者,则良知本体之至善,即已呈于前,而不善则渐自销化于无形。故此知本体之自身,亦为工夫。……致良知,实即良知本体之自己流行为工夫或用。”[11](P345)当吾人之良知呈现之时,其要求实践之范围即为无限,而天地万物皆在吾人之良知感通之下,因仁心而及物润物,进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职是此故,吾人须致自我之良知于万事万物之中,以求一切皆得其正,此为推致扩充良知之义,在推致之过程中,亦即是恢复吾人之自我之良知本心,推致与恢复,其义一也。唐先生则指出:“阳明之言致良知,则又正是重此天理人欲之辨。阳明之言良知之是是非非,即初表现于其存天理、去人欲之事之中。”[12](P295)又言:“阳明之致良知,则由人之知其所己知者,以开出。人由知其所不知,乃日趋于广大;人之知其所己知,则所以日进于高明。广大所以切物,高明所以切己;广大者方以智,高明者圆而神。”[11](P349)综上所述,王阳明之返求自我之良知能真切而体贴地扣紧道德自我之生命而使吾人得以安身立命。黄振华先生指出:“当唐先生发现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道德境界的时候,他即发现中国哲学的伟大价值,他发现中国哲学在道德理想的创建上有极高的成就。”[13](P510)在唐先生立基于“良知”为吾人生命之意义价值之根本之诠释视域下,提供吾人论述王阳明良知学如何建立现代人文世界一条可供参照之道。
三 牟宗三与唐君毅诠释视域之理论基础之差异
上文对比论述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两者立说皆建立于王阳明文本之充分把握上,而正面肯定并深化王阳明良知学之意义价值。然而,两人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理解仍有其差异之处。
1.“思辨分解”与“辩证体验”
牟宗三先生以康德哲学诠释中国哲学,然其本身从未建立一套有系统之哲学诠释学。而牟先生谈论吾人面对中国哲学文献之态度时对于诠释之理解提出基本之旨趣,即诠释须依着文本之客观条件,否则易流于无根任意而毫无客观性可言。当吾人在反复思辨之后,文本之主要义理自然呈现,即依此作出理解分析,厘清其间之疑问[14](P9)。对此,李明辉先生补充道:“牟先生……所说的‘文献途径’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般所谓的‘历史考证的途径’或‘考证的途径’。……建立在‘文字训解’与‘义理诠释’底循环关系上。”[15](P190)换言之,牟先生透过“文字训解”和“义理诠释”交互融摄之历程,方逐渐形成明确之概念,再将明确之概念加以融会贯通终成完整之哲学系统。
现代人崇尚自然,追求绿色和食品安全,平台将鲜果的种植、采摘、包装、运输等各环节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在平台上进行展示,可以让消费者吃到放心的鲜果产品。
牟先生厘订“良知”的性质,剀切说明良知是一无声无臭的本体又是一活活泼泼的呈现,而不是一言说系统中的默认。然而对如何涵养这良知善性,属于工夫修养一边的讨论指点,牟先生却极少说到。后学如果径直承继牟先生的说法而事实上不作致良知的工夫,单依牟先生的学统,是无法检查得到的。[16](P135)
由曾先生之见解可看出牟先生极富思辨性,有着明确之问题意识以及独到之学术创见,然在讨论实践面向时却略显不足。王阳明曾言其致良知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4](P1747)。王阳明良知学之旨趣并非只是在书本中专研学问,而是必须将所学之义理,落实于生活中,如此若真面对困境时,才能临危不乱。此亦是“知行合一”之体现。
反之,“超越的反省”乃为唐君毅先生所认知一切义理研究方法之核心:
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应该在具体的情境中去强化训练,让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接受教育。因此学校要定期设计、组织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把对小学生的习惯培养融入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如,可以以信念、责任、合作、感恩、诚信等专题教育为内容,定期开展主题班会、征文比赛、专题演讲等系列活动,开展小学生课堂行为习惯达标、养成教育签名以及“好习惯伴我行”等系列活动,组织每月一次的学生才艺展示,每学期一次的田径运动会,每学年一次的感恩教育等活动,举行课间舞、拔河比赛、校园十佳歌手评选等活动。这样把养成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个环节,真正做到“真实情景中的德育教育”。
所谓超越的反省法,即对于我们之所言说,所有之认识,所知之存在,所知之价值,皆不加以执着,而超越之;以期翻至其后面、上面、前面,或下面,看其所必可以有之最相切近之另一面之言说、认识、存在、或价值之一种反省。[17](P205)
国内外针对电动汽车充电站设施选址研究的文献较多,主要集中于对选址评价、布局规划、定容优化策略等方面。文献[3]建立了基于空间聚类和多层次模糊评估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模型。文献[4]研究了直觉模糊环境下社区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决策优化。文献[5-6]分别考虑削峰填谷和计及碳排放,构建了电动汽车充电站多目标选址定容规划模型。此外,文献[7-8]提出基于云重心理论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规划评估方法,将定量和定性指标进行处理并建立了云模型。上述研究虽对电动汽车充电站构建了不同的选址模型,但未涉及具体应用场景研究,前期也缺少对充电站选址合理性的综合评价分析。
同时,唐先生在其晚年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所自创之纵观、横观、顺观三观配合体、相、用三境,以及正、反、合所撑开之心灵九境说,将道德意识归于第六境,并将“天德流行境”安排至最高之第九境:
一是各工程项目部领用工程材料时,均以工程管理部填列的大料单为依据,在特别情况发生时,存在超出限额部分未及时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二是工程管理部的大料单以设计管理部的设计图纸为依据编制,领料单一出,就将材料悉数领出,存在未用材料存于企业仓库或散于工地现场的情况,不利于施工企业采购资金的安排和材料存放安全;三是单个工程完工后办理退料时,工程项目部往往将尚未用完的的散件直接退回,未能按照节约原则在下一个工程中进行充分利用,存在不愿领用可改造使用的散件而领用整件再分割使用的情况.
此儒家之思想,要在对于人当下之生命存在,与其当前存在之世界之原始的正面之价值意义,有一真实肯定,即顺此真实肯定,以立教成德,化除人之生命存在中之限制与封闭,而销除一切执障与罪恶所自起之根,亦销化人之种种烦恼苦痛之原。[18](P158)
唐先生所言即是肯定全幅人生,于人生之一切活动中体验吾人身为人之意义价值。而唐先生亦承继了王阳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4](P1066)之旨趣,视吾人内在之良知本体而感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通主客、天人、物我,以超主客并契合天德同流行。
在牟先生诠释视域下,王阳明所言之良知有其精辟体贴之处。其肯定吾人自觉地相应道德本性,并作出道德实践,且肯认一个超越之道德实体,作为其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之依据。然此亦引发了一些讨论。林安梧先生指出:
在牟先生之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可溯源于先秦之孟子。王阳明所谓:“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4](P95)牟先生即诠释道:“‘真诚恻怛’便就是他的本体。‘他的本体’意即他的自体,他的当体自己,他的最内在的自性本性。”[3](P218)是以王阳明所言之良知即是具自发性与呈现性,且具有天理之道德内容,并非外在于心之对象,而是内在本具于吾人之中。
该架构的超宽带接收机具有宽带、高灵敏度、高截获概率、高相噪设计、很好抗干扰能力等优越电性能,与传统信道化接收机相比,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特点,与射频数字化接收机相比具有侦收频段宽等特点[5]。因此,该超宽带射频接收机架构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宽带频谱监测系统的要求。
牟先生将王阳明之工夫论旨并同入天道之活动,自吾人道德本心与他人及天地万物真切之互动中,愈能见其自正之自我,见其真实之本性,活在当下随时体现天道之生生不息,亦在此朗现不已之当下,吾人即能自觉地逆觉体证与天德同流行[3](P223)。是以牟先生言:“即朗照并朗现物之在其自己,亦反照其自身而朗现其自身。”[14](P42)此由内而外足以呈现,贯通本体、工夫、境界与现象之成德之教,牟先生称此为“道德的形上学”。
王阳明言:
2.“逆觉体证”与“性情感通”
当代新儒学在牟先生的系统下,太强调“良知”做为“本体”,而这个良知本体直接上溯“道体”,在这个体系下强调良知本身能够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能够因此展开一个道德实践的动力。……因为这个主体主义跟本质主义的倾向太强了。[19](P337)
唐君毅先生道德哲学之基石,即承继着阳明学开展,此亦为吾人道德自我之根源。唐先生曾言:“道德的问题,永远是人格内部的问题;道德生活,永远是内在的生活;道德的命令,永远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道德生活,即自觉的支配自己之生活。”[6](P25-26)又言:“实践人道之始,并不待远求,并不待对人性有穷尽之研究与分析,而唯待人之就此日常失活中,人之异于禽兽知性之自然表现处,而加以自觉,以知其所以为人,此即实践人道之开始。”[7](P550)吾人一切之道德实践皆为自律自发,而吾人实践道德之过程乃发乎其内而行之于外,不能有丝毫外来之因素;所有之他律被动、不自然之行为皆无法归入道德之下。王阳明以“良知”作为其义理系统最高本体之规范。而天地万物皆是由良知所创生变化而出,王阳明所谓“生天生地”[4](P119),乃为强调“良知本体”之自然流行,而“无对”即是指出此良知本体即是在这流行发用之过程中,能无所不在,进而圆满无缺、无少亏欠。唐先生亦指出:“我的心之本体,即他人之心之本体。因为我的心之本体,它既是至善,它表现为我之道德心理,命令现实的我,超越他自己,而视人如己,即表示它原是现实的人与我之共同的心之本体。”[6](P109)依王阳明之义理而言,无相无形之良知妙用流行并创生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中之天地万物,良知既超越于一切万物之上,却又流行于一切万物之中。唐先生则指出:“良知之不可为善恶之概念所判断之一对象,而只为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之超越的主体。……良知不自有其善,及良知之由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而成为一切被判断为善者‘源’。”[8](P459)换言之,即是以吾人之良知即为天地万物之灵明。
反之,唐先生之诠释视域中,其出吾人生命通过“感通”与“升降”流行于九种境界之中,其依据即在于“依此性情,人形成一理想时,此理想即先实现于此性情之内,而亦求通过其身体行为,以表现于外,而实现此理想于其周遭之世界”[18](P488),并以“性情感通”作为诠释之原则。唐先生将“性”字作“心”与“生”字解,并将人性合作“心灵”与“生命”为一整体[20](P144-145);换言之,唐先生不似牟先生将良知当作吾人之最高之意义价值,而是包含了生命与心灵两个部分。当吾人由性情为起点真诚恻怛而发,具体展现吾人之心与其他人物间相互感通之实情实感,进而呈现出吾人本身生命心灵中之最原初之真性情,此良知仁心之感通亦为最原初之“仁”的展现。唐先生称之为“成己成物之仁心”[20](P146)。
唐先生以为吾人之道德主体,唯有透过“正”“反”“合”之超越的反省辩证方得以确立。而吾人亦能透过“超越的反省”将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中之种种现象(俗情毁誉之超越、人生之艰难与哀乐、死生之说与幽冥之际、人生之虚妄与真实、人生之颠倒与复位)透过不断地超越辩证反省,不断地自觉之心灵体验,翻转至种种现象。如此具体落实在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出入于诸家义理中斟酌权衡彼此分际之活动。
同时,唐先生重视的是良知感通在当下生活之境遇而有不同之应对方式:
吾人之生命存在与心灵,必须先面对此当下之境,而开朗,以依性生情,而见此境如对我有所命。此中性情所向在境,此境亦向在性情,亦如有所命;而情境相召,性命相乎,以和为一相应之和,整一之全,此即一原始之太和、太一。境来为命,情往为性。知命而性承之,为坤道,立命而性以尽,为乾道。乾坤保合而为太极,则一一生活之事之生起,皆无极而太极。[18](P280)
唐先生指出,在良知感通之动态过程中,自是由当下生活之境遇而始。吾人良知为本,以良知之发动感通而蕴含情与意,良知本自感应所动之性情,依性情而尽命之所令而行。而所谓原始太和、太一,乃就吾人之心灵最原初之感通而呈现之无限价值。就唐先生之诠释意义而言,王阳明良知学乃是就生活中不同之情境,以性情为内容,以感通为动力而开展。王阳明亦有言:“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4](P109)是以在唐先生之诠释下,良知即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具体落实在交互主体之整体性之中。
3.“宋明三系说”与“朱陆之通邮”
牟先生提出“三系说”,其主要内容分为:
五峰蕺山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特提出“以心着性”义以明心性所以为一之实以及一本圆教所以为圆之实。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
象山阳明系:以《论》《孟》为主,摄《易》《庸》。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于工夫亦重视“逆觉体证”。
伊川朱子系:此系以《大学》为主,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于《中庸》《易传》所讲之道体性体,为“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此大体是“顺取之路”。[21](P49)
牟先生之“三系说”,将王阳明定位于陆王一系。而“陆、王系又可与五峰、戢山系列合为一个系统为正宗,伊川朱子系则为别宗”[22](P415)。就牟先生之分类方法可知,其强调“以心着性”“逆觉体证”由道德实践反求诸己之中,以印证天道之内在于吾人之心之旨趣。牟先生“尊陆王”“抑程朱”之分系在港台学界中影响力尤巨。然对牟先生之说提出质疑者,亦皆不乏其人,如刘述先先生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为宋明理学的共识,并据此反对牟宗三先生认为程朱之横摄系统,不能讲天道性命相通贯之主张[23](PIV)。总而言之,在牟先生之诠释下,其“三系说”不仅宗于陆象山与王阳明“心即理”说之心学,且强调“心”具有普遍且超越之意义。
反之,唐先生之诠释视域中,其重视的是各家思想间如何进行会通:
依吾平日之见,尝以为凡哲人之所见异者,皆由哲学义理之世界,原有千门万户,可容人各自出入;然既出入其间,周旋进退,还当相遇;则千门万户,亦应有其通。……论此宋明儒学中哲学义理之流行,亦当观其义理流行之方向,如何分开而齐出,又如何聚合而相交会;不先存增益减损之见,以于同观异,于异见同,方得其通。[12](P9)
唐先生即说道其体悟所有之义理固有千差万别,然实为一整体之历史中开展之,是以就此发展历程而言,于此发展历程其中之义理亦必有其可疏解之处,即此发展历程之整体性所在。是故个别义理间之差异,亦仅是对此之整体性之不同见解。是以唐先生以为中国诸贤义理之间实有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之可能。
职是此故,唐先生对于阳明学承继之见解,亦以此“会通”为进路展开:
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父母给予我大力支持,利用假期,千方百计地为我联系美术教师和摄影老师进行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美术作品《把青春献给新团场》入选农垦美术展览。我在临近高中毕业时,父亲把购置日立牌电视机的钱,托人在上海买了国产经典海鸥4A 120相机送给我。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架相机,在当时同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1年年底,由于我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对摄影技术有些了解,被选中在兵团团场从事宣传工作,我开始接触新闻摄影。
阳明之学又实由朱子所论之问题、与义理而转出。其归宗义之近象山,乃自大处言之,此固不可疑。……若其精义所存,则与朱子之别在毫厘间,而皆可说由朱子之义转近一层而得。[12](P206)
可见在唐先生之诠释下,王阳明义理对于朱熹、陆象山均有所承继,其认为王阳明良知学之精义乃由面对朱熹思想之问题所转进而来,始于朱子而归宗于陆,而唐先生之目的在于袪除后儒将陆王一系与程朱一系对立相非难之态度。王阳明亦曾言:“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3](P233)由此亦可看出,从王阳明之立场而言,如何通透圆融地会通朱陆义理,在同异之间共同迈向成圣成贤之道,此方为王阳明良知学之大旨。
四 结语
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两者立说皆建立于王阳明文本之充分把握上,而正面肯定王阳明良知学之意义价值。然而,两人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之诠释理解仍有其差异之处。而总结两人诠释视域差异之处可就三点说明:“思辨分解”与“辩证体验”、“逆觉体证”与“性情感通”、“宋明三系说”与“朱陆之通邮”。
推荐理由:“回弹力”是人们在面对困扰、挫败和威胁时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芬兰焦点解决大师本·富尔曼用真实故事和积极心理学,写作了《回弹力》。在书中,他梳理了人类智慧的多种生命资源,比如人与人的关系、对意义的追寻、有意识地选择改变视角等,从而能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自身的生命资源找到走出困境的契机。
曾昭旭先生曾经公允地提出牟先生与唐先生二人之于当代新儒学之意义:
新儒家何以为新?与新儒家何以为儒?前者是指对西方文化之冲击有何响应之道?后者是指此回应是仅止于思辨理论学术之回应?抑更能回到生活世界作实践的回应,藉回归生命人性之根源(即所谓“道”)以解决生命与文化因失本而造成之困局?……牟学重在表述当代新儒学之何以为新,唐学则重在表述当代新儒学之何以为儒。[24](P1)
诚然,一完整之诠释活动必须通过细腻之分析,否则诠释即成空洞。然所有精确分析之学术活动成果,亦应当涉入生活世界中以见其道德之意义。据此亦可见牟先生与唐先生诠释视域下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互补性之旨趣。
Up until now, many attempts have been conducted for the high output power of the GaSb based SDLs23. At present, the maximum CW output power of GaSb based SDLs emission at different wavelength has been listed in Fig. 3.
综上所述,牟先生与唐先生之研究贡献对于王阳明良知学于现代社会之发展有着极大帮助。吾人可就牟先生诠释视域下,能在纷乱错杂之事象中,通过分析与判定,而使王阳明良知学之概念更为清晰;而在唐先生之诠释视域下,王阳明良知学能回到生活世界作实践之回应,调节存在于吾人生命与文化之种种矛盾、对立与冲突之负面效应。挺立自我文化中永恒之体与当代之用,进而开展传统儒学与当代社会对话之可能,以承继王阳明良知学之文化生命能自强不息。
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众筹模式支持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对于破解科技创业融资难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苏州六大代表性众创空间中的54家科技型创业企业和301位众筹投资者的调查,分析科技型创业企业众筹融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政产学研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进一步发挥众筹模式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支持作用的对策建议,助力打造“双创”升级版。创业融资活跃程度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作为曾经的“苏南模式”发源地和今天的“创业名城”,苏州的“先行先试”对全国范围内科技众筹创业的实现路径也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乐爱国.牟宗三、唐君毅对朱陆异同的不同阐释与学术冲突[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2]陈振昆.牟宗三与唐君毅对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对比诠释[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6(6).
[3]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1.
[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蔡仁厚.王阳明哲学[M].台北:三民书局,2009.
[6]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7]唐君毅.哲学概论:下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
[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
[9]唐君毅.心物与人生[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10]唐君毅.人生之体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
[1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
[1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
[13]黄振华.唐君毅先生与现在中国[G]//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4]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4.
[15]李明辉.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诠释中之方法论问题[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6(3).
[16]曾昭旭.在说与不说之间——中国义理学之思维与实践[M].台北:汉光文化,1992.
[17]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
[18]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
[19]林安梧.牟宗三前后: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史论[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1.
[20]唐君毅.中国文化与精神价值[M].台北:正中书局,1993.
[2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M].台北:正中书局,2012.
[2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23]刘述先.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
[24]曾昭旭.为新子学定性定位[J].鹅湖,2018(4).
On the Difference of Mou Zongsan and Tang Junyi ’s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Conscience
LI Wei-hao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Shandong Universt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Mou Zongsan,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has two interpretation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one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knowledge logic and so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theory of existentialism” to the degree,one is from the form of schoo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ntities and chastity of all things in their own “No practice of existentialism” to the degree.Based on “conscience” as the funda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our life,Tang Junyi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ow Yangming’s conscience establish a modern humanistic world.Both of them are based on the full grasp of Wang Yangming’s text,and positivly affirmed of the meaning value of Yangming’s conscience.However,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ers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Summari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erso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eld of view,it can be explained in three points: “Speculative decomposition” and “dialectical Experience”,“inverse consciousness” and “ emotion pass”,“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Zhu’s Mail”.
Key words :Mou Zongsan;Tang Junyi;Wang Yangming;conscience
收稿日期: 2019-05-06
作者简介: 李玮皓(1988-),男,台湾新北人,助理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宋明理学、清代哲学、新儒家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9)05-0047-09
(责任编辑王能昌 )
标签:牟宗三论文; 唐君毅论文; 王阳明论文; 良知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