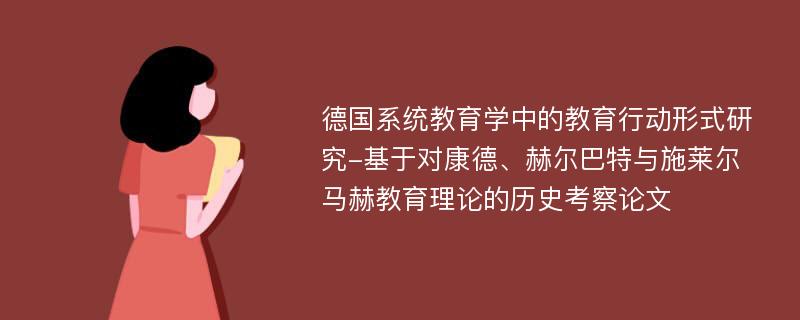
教育研究
德国系统教育学中的教育行动形式研究
——基于对康德、赫尔巴特与施莱尔马赫教育理论的历史考察
林 凌
摘 要: 如果说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大革命性成果体现为分化出了三分的教育行动形式,即儿童管理、教学和教育支持,那么,为这种三分的教育行动形式奠基的正是康德、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的教育与教化理论。教育行动着眼于对个体的不确定的可塑性和主体性的承认,因而也有着明确的作用界限。教育行动强调未成年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并最终指向对其社会参与能力的培养。三种教育行动形式各司其职,不可偏废,它们既延续着自启蒙以降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也呼应着当下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关键词: 康德;赫尔巴特;施莱尔马赫;教育行动形式;判断力;行动能力
从德国普通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教育的关切在于对日常经验和人际交往进行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拓展,并由此形成人的判断能力和参与能力,并且教育应当在所有学科中对这三方面能力进行培养。[注] 彭韬、[德]本纳:《现代教育自身逻辑的问题史反思》,《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第92页。 现代社会的这种教育关切与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将人的理性和尊严推到至高地位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直接体现这种教育关切的是康德、赫尔巴特与施莱尔马赫等人所区分的教育过程所应当包含的三类教育行动形式。虽然三人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却体现着共同的教育愿景:教育的使命在于使未成年人能够自主地选择未来的生活方式和进行职业规划,在与他人的自由交往中使自身的人格与尊严能够得到承认。根据德国当代教育学家底特利希·本纳(D. Benner)的观点,古代社会建立在“适应”和“指导”基础上的二分的管理实践转变为近代三维化的教育行动,意味着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行动的革命,标志着古代社会形态中的教育学和市民社会形态中的教育学之分界。[注] [德]本纳:《普通教育学》,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6页。关于近代以来三分的教育行动形式的概览可参见:彭正梅:《德国教育学概观:从启蒙运动到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7页。亦可参见:Rektor, O. Die Dreiteilung in der Erziehungslehre Schleiermachers und in der Pädagogik Herbarts. Evangelisches Schulblatt, 1897, 47(3): 93-112.
一、教育行动形式分化的历史语境
教育行动理论的形成和教育行动形式的分化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能力的大发现和个人价值的提升密切相关。由于人的“可完善性”或“可塑性”得到强调,进而,一种新的通过教育来帮助未成年人形成自身的确定性和使命(Bestimmung)的历史经验也随之产生。[注] D. Benner: Allgemeine Pädagogik, 8. Auflage.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Juventa, 2015.德语Bestimmung兼有“确定性、规定性”和“任务、使命”两层意思,人的使命也就是人的理性的自我规定性。 关于“人的使命”的话题在近代德国有着悠久的讨论历史。1748年约翰·施巴尔丁(Johann Joachim Spalding)出版了《对人的使命的观察》(Betrachtungen über Bestimmung des Mensch)(后更名为《人的使命》)一书,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的使命的大讨论,参与者包括门德尔松、康德、费希特、席勒、施莱尔马赫等,这场大讨论最后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而结束,即在一个庞大的关于秩序的哲学和神学体系瓦解之后,我们只能在一种碎裂的意义上去探讨人的规定性或使命。[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Die Bildung pädagogischer Urteils- und Handlungskompetenz als Aufgabe des Pädagogikunterrichts im öffentlichen Schulsystem. In: R. Bolle & J. Schulzenmeister(Ed.): Die pädagogische Perspektive. Baltmannsweiler: Schneider Verlag Hohengehren, 2014, S.79-80. 在古代城邦社会,教育行动旨在管理未成年人以使之适应既有的城邦秩序。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教育思想开启了现代教育学的进程,一种基于主体的理性能力和独立思考基础之上的培养人的判断力和行动能力的教育诉求日益凸显。成长中的一代被视为有学习能力且具有自我能动性的理性存在者,无论就其个人发展还是就其社会交往而言,他们都应当自己去形成自己的确定性,也即是说,未成年人要能够摆脱父母一辈的社会等级或所从事的职业的束缚,通过接受新的教育来发展自身的思考、判断和行动能力,以寻找和确定自己的未来使命,并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因而,与未成年人的这种“未被规定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正是年长的一代(教育者)对成长中的一代(受教育者)的“可塑性”和“教育需求”的承认。[注] H.-E. Tenorth: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züge ihrer neuzeitlichen Entwicklung. Weinheim und München: Juventa Verlag, 2010, S.110-111. 即,承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已按照其父母的社会等级而被预先规定,他们应当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确定性;同时承认,未成年人之所以能够寻获在未来的确定性,正是因为教育使他们具备了相应的能力。
上述“可塑性”和“教育需求”又进一步涉及到,未成年人作为具有思考、判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参与到教育行动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对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加以承认并使之变得可能的基本的教育行动形式。[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Die Bildung pädagogischer Urteils- und Handlungskompetenz als Aufgabe des Pädagogikunterrichts im öffentlichen Schulsystem. In: R. Bolle & J. Schulzenmeister (Ed.): Die pädagogische Perspektive. Baltmannsweiler: Schneider Verlag Hohengehren, 2014, S.77-98. 更确切地说,教育行动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对人的主动性的激发”[注] 来自费希特的提法,或译为“要求实现自由的自我能动性”。详见:[德]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基础的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文集(第2卷)》,梁志学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5页。该观点亦见于施莱尔马赫的作品: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In: M. Winkler & J. Brachmann (Ed.): Texte zur Pädagogik (Ban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0, S.21, S.31. 。它所要达到的状态接近于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强调的“成熟状态”(Mündigkeit),即一种个体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仍旧能够运用自己的知性能力的状态。在该文中,康德将启蒙表述为人走出一种“由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这种状态的产生并非在于理性能力的缺乏,而仅仅在于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注]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在《康德论教育》中,这种启蒙的要求被转化为一种“让儿童学习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的教育诉求,旨在强调对未成年的判断能力和与之相应的行动能力的培养。新人文主义者(例如洪堡)和对教育做出系统思考的教育学家(例如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均将此作为教育行动的基本关切。
既然现代教育不能再强制性地去塑造和规定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而应当通过激发未成年人的主动性,使之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并支持未成年人逐渐向自我负责的行动方式过渡,那么,教育行动也必须注意自身的影响范围或作用界限。三种教育行动形式既要各司其职,也要避免相互的僭越。首先,对儿童所进行的管理应是一种不带任何积极目的的消极的管理措施,它的实施仅仅是为了防止儿童不明智的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其次,教学应当是一种具有教化作用的教育性的教学。教学活动不仅要包含师生间的教育性的互动,也应当包含一种主体在学习过程中所建立的人与世界之间的教化性的互动。从本质上讲,学生并不是从教师那里获得学习,而是借助于教师的帮助在某个事物或某项任务上进行学习,因而真正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学生获得教化的过程。[注] D. Benner: Erziehung und Bildung! Zur Konzeptualisierung eines erziehenden Unterrichts, der bildet. Zeitschrift der Pädagogik, 2015, 61(4), S.481-496. 而教化过程的开启正是教师的教学行动的边界。最后,为未成年人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做好准备,需要培养他们的公民品格和一种自我负责的行动方式,由此,一种支持性的教育行动形式也就必不可少。总而言之,教育行动的终点就在于当儿童达到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自己、自己指导和约束自己的时候。[注] 这里所提到的有关教育行动的界限的观点来自本纳(Dietrich Benner)教授于2017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关于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讲座,特此说明。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开启了对康德、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的教育理论和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行动形式的历史考察,以期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当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在康德那里,教育行动的核心任务在于“均衡和合乎目的地发展人的一切自然禀赋”[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其关键则在于促进儿童的独立思考,并通过野性的克服、技能的获得和社会交往规范的训练、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人类社会逐渐臻于道德化的时代。在赫尔巴特那里,儿童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三种教育行动所要实现的是作为教育的“整个目的”的道德,而教育行动所遵循的乃是教育发展的自身逻辑。在施莱尔马赫那里,保护、管制和支持三种教育行动形式所体现的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个体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彰显了“教育学的尊严”[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9. 。由康德、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所确定下来的现代教育的三分的教育行动形式是德国“作为科学的教育学”兴起和发展之路上的重要基石。
二、康德:以“让儿童学习思考”为核心的训诫、培养、文明化与道德化
一旦儿童产生了那种“能下决断的真正意志”,真正的教育也就开始了,这涉及两方面的任务:培养青少年儿童的明智和性格。前者涉及对未成年人的兴趣进行多方面地拓展,这是“教育性教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后者涉及通过道德来增强性格,也即增强“意志的前后一致性与坚定性”[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从而能够使未成年人能够过渡到一种自我教育的阶段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明智的意愿来行动,这是“训育”所要完成的任务。
康德最著名的道德学说是他的“绝对命令”。黑格尔批评这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同语反复”[注]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0页。 ,但对于理解康德的教育思想而言,“绝对命令”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体现在它对每个个人和他人人格的承认与尊重。这是康德在绝对命令的变式中所强调的:“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做手段。”[注]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与此相关的教育学命题是:“怎样才能把使儿童服从法则的强制同使其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或者说,“如何在实施强制时培养出自由来?”[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因为教育中的强制是必须的,但教育的使命却在于指导学生良好地运用其自身的自由。康德认为,每一个未成年人从童年开始都应当得到自由。这就意味着,每一位儿童在获得自身自由的同时还应当学习对他人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并要明白限制的目的正在于为使其能够运用自由。在康德看来,要实现教育的这一任务,关键就在让儿童学习思考。教育应当成为一种旨在让儿童学习思考、判断和自由地行动的教育艺术(或技艺)。基于此,康德设定了四种教育行动形式或行动维度,并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任务而展开,即儿童的独立思考。
康德将现代教育的四种行动形式确定为:训诫(Disziplinierung)、培养(Kultivierung)、文明化(Zivilisierung)和道德化(Moralisierung)。训诫,指的是抑制人身上的动物性,以免对人造成损害,与其它三种形式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教育行动形式。培养,指的是造就人的技能,但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技能培训,而是使学习者掌握一种可用于指导各类具体运用的一般性技能。文明化,是指为使学生能够顺利地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而做的准备,包括风度、礼貌和机智等的培养,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而能顺利地与他人交往,并使他人能为自己实现终极目的而服务所应当具备的。文明化的过程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互动方式,但在文明性的教育传承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并非是教师所进行的形式上的指导,而是参与到教育过程中的人员所开展的用以培养教育者的习惯和使之社会化的活动。[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S.128. 所谓道德化,康德指的是人要获得那种“必然是为每个人所认同的目的,同时也是能够作为任何人的目的的那种目的”[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这是教育行动所要实现的高级阶段。康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已实现了训诫、文化和文明化,但还远非道德化的时代。[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由此,一种和人的理性能力紧密结合的道德要求就成为近代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的核心关注。到了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席的继任者赫尔巴特那里,这种道德化的任务被理解为了儿童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的目标。[注] D. Benner: Allgemeine Pädagogik, 8. Auflage, S.228. 用赫尔巴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道德是教育的“整个目的”(ganzer Zweck)。赫尔巴特重新确立了教育学与伦理学、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教育行动形式被纳入了一种教育发展的自身逻辑之中。
对于这四种教育行动形式,康德并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先后加以排列的。虽然道德化是最晚出现的,但人们却应当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确切地说,道德教化应当渗透在每一种教育行动形式之中,其余三种行动形式则通过完善儿童的理性能力而为道德化的实现奠定基础。康德将儿童行动中的道德的自我规定性作为一种自由活动(自由意志的自律)来加以思考,教育和教化过程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学习思考,对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法则进行思考。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康德的教育行动形式旨在让儿童学习思考,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养未成年人的道德能力和参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培养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或权威的指导下也能独立地使用理性的能力、勇气和决心。康德对这四种教育行动形式的规划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意识进行的,即将教育学发展为一门“判断性的”“科学”[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
压力注浆孔的布置就是超前探水孔的布置位置,根据该掘进段实际情况,如渗涌水量较大,可在适当位置增加注浆孔的数量,以确保防治水效果。
三、赫尔巴特:由“道德”目的引出的管理、教学与训育
康德的伦理学通常被视为是纯粹义务论的代表,“自由意志的自律”的命题也有着同义反复的危险。但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仍旧是赫尔巴特发展其自身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这不仅体现在赫尔巴特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使命的认识上与康德一脉相承,还尤其体现在他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自律”的命题发展为一个以“内心自由”这个实践理念为基点的道德判断体系。这里首先涉及道德的两个现实性条件:明智和(对明智进行服从的)意志;其次涉及教育行动所肩负的将这两者加以实现并进行联结的任务,这也就是他的“由教育目的引出的普通教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在“普通教育学”中,赫尔巴特确定了教育的自身逻辑,明确了人类活动的实践领域和学校教育所应当培养的六大兴趣领域,形成了一个有体系的旨在培养青少年儿童的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普通教育学方案。[注] 林凌、彭韬:《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7年第7期。
道德是教育的“整个目的”。一方面,赫尔巴特认同“绝对命令”中所包含的对每个个人作为其自身目的的承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康德那条唯一的、高度抽象的“绝对命令”事实上是脱离于具体的实践情境中的行为目的和道德判断的,因为道德应当是一桩桩具体的“事件”,应当是“自然现象”(Naturbegebenheit)[注] J. F. Herbart: Über die ästhetische Darstellung der Welt als das Hauptgeschäft der Erziehung. In: W. Asmus (Ed.):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Pädagogische Schriften (Band 1). Düsseldorf und München: Verlag Helmut Küpper Vormals Georg Bondi, 1964, S.107. ,德行应当是道德判断的结果,而在形成道德判断之前首先要对意志关系形成一种无强制也无须加以证明的审美判断。更进一步的是,赫尔巴特不再将道德仅仅作为最高的和唯一的任务,而是在伦理学和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为人的道德的形成增加了一个教育行动的维度。[注] D. Benner: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Systematische Pädagogik (Band 2): Interpretationen.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Verlag, 1997, S.22.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是最高的、自身即目的的善,而教育是相对低级的、为实现最高目的而作为工具的善。[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页。 这种目的论的等级观念是前现代的,它既是等级社会的产物,也是帮助等级社会将等级性合法化的工具。赫尔巴特的立场很明确,他的“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不但是针对一切人和所有社会公民的、无性别差异、无身份等级差异的“普通的”教育学,也是“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进而形成独立的思想,从而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的教育学。因而,赫尔巴特势必要对这种自身不包含其他目的的、作为最高目的的目的进行扬弃,取而代之以道德作为人和教育的“整个目的”的理念。与之相配套的,是从这个教育目的中所引出的三种教育行动形式:儿童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
对儿童进行管理旨在通过教育的强制手段克服儿童的烈性与欲望,从而保障儿童能够从自身的烈性和欲望之间逐渐形成其“能下决断的真正意志”[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因为只有当儿童的意志能够下判断时,才有可能形成审美判断和明智,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形成道德判断和德行。赫尔巴特关于儿童管理的教育措施可联系到康德所提出的“在实施强制时培养出自由”的思考。康德肯定了强制措施在教育行动中的合法性,但并未对教育强制的界限予以说明。赫尔巴特则进一步提出,教育的强制措施只有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是合法的:其一,“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或者说,仅仅只是为了预防儿童的不明智的行为;其二,只有“在儿童表现出具有真正意志的迹象之前,其烈性的克服是可以通过强制来实现的”。[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页。 严格说来,管理措施还不是真正的教育行动,它只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准备,它所关心的只是儿童的当下,教学和训育则是为了儿童的未来、为了儿童的教化。因而,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向下一个教育实践维度过渡,当儿童能够进行自我管理时,这种教育行动也就变得不再必要。
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康德曾在1776/1777年的冬季学期、1780年的夏季学期、1783/1784的冬季学期和1786/1787年的冬季学期分别开展了关于教育学的讲座。《康德论教育》(Kant über Pädagogik)一书并非由康德本人撰定,是他的学生弗里德利希·提奥多·林克(Friedrich Theodor Rink)在康德去世前一年(1803年)根据康德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而成。教育学也并非康德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构成,有关教育学的讲座乃是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应当时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而开展,旨在对当时普鲁士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方法层面上的改善有所助益。[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2011, S.123. 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从《康德论教育》中找到诸多与康德批判哲学相对应的思想,而且,关于教育的学说,康德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实用的而非先验哲学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所确定的几种教育行动形式上,尤其体现在“培养”和“文明化”这两种形式上。前者造就技能,后者使人具有社会适应能力。
管制措施适用于较年长的未成年人,旨在抵抗在学生体内自己发展出来的与教育的目的违背的东西。[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86. 教育管制的作用范围在于:只要未成年人对恶的(或坏的)东西进行模仿的意愿一直存在,那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恶的(或坏的)主动性就应该加以抑制。[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S.227. 它包括两种形式:身体方面的管制和道德或理智方面的管制。施莱尔马赫强调,没有哪一种教育管制可以对身体和精神作出严格的区分,所有的管制都会涉及这两方面,只不过不同的管制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在道德或精神管制方面,他主张一种“羞耻心的激发”,这种管制措施可以对单个的意志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并由此而对思想态度施加间接的影响;在身体管制方面,他则主张一种“身体上的强制力”,一旦青少年儿童的思想态度能够控制意志活动,身体方面的管制就必须停止。[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101-103.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管制措施的运用可能导致的危险,即虽然未成年人向外表现出的意志活动得到了改变,但内心态度却未曾改变。[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S.228. ——而能够对未成年人内在的态度或思想施加影响的,只有教育的支持。若要向教育支持过渡,则还需要涉及到另一种管制措施,也就是他在1820/1821教育学讲座中所讨论的训育(Zucht)。在施莱尔马赫这里,训育旨在改变学生的“自我关系”,使学生心中反对教育的潜在因素能够服从于一个更高者,而于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未成年人的自由感和自我认识,因为只有有能力达到自由的存在者,才有能力认识自身行动中成问题的和不被允许的成分。[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344. 正是通过训育,从保护和管制向教育支持的过渡才得以可能。保护和管制都是对支持的教育行动的必要补充。
试验材料取自漳州市引种的大花序桉优良单株,选择连续晴天2 d以上且枝条无露水时(一般在上午9∶00—10∶00左右)进行取样,剪取正处生长季节、当年生、幼嫩部分、无病虫害、芽体饱满、生长健壮的枝梢。保鲜带回实验室。
站在历史的高地上怀古伤今还有如《湘川吊舜》:“伊予生好古,吊舜苍梧间。……九疑云动影,旷野竹成斑。”[5]立于南部湘川湖上,抒发其前不见古人的惆怅,今又无来者的伤感。他还站在北部边关,叹雄奇荒凉的景象,如其《易水怀古》:“落日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5]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眼中所见昔日胜极一时的景象,今日的萧条,与诗人内心的苦闷相互照应,沿途的景象所呈现的便不再是单纯的景象,写胜地的被弃,也是写诗人的被弃,便不得不发出强烈的怀古叹今之愁。
在管理、教学和训育三者中,赫尔巴特认为只有后两者才是“真正的教育”。管理只立足于儿童的当下,教学和训育才关注儿童的未来。教学过程包含的是教育者、学习者和事物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管理和训育则只涉及师生间的互动。教学和训育都建基于一种“审美的必然性”[注] J. F. Herbart: Über die ästhetische Darstellung der Welt als das Hauptgeschäft der Erziehung, S.111. ,也即一种实践中的判断力的“审美的原因性”[注] D. Benner: Die Pädagogik Herbarts, S.67-77. 。在前一方面,赫尔巴特将“对世界的审美展示”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旨在拓展青少年儿童的经验与交往的兴趣和形成青少年儿童的“思想范围”;在后一方面,赫尔巴特也认为“只有从道德观的美学威力出发,才可能……把真正的道德化为性格”[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训育的最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帮助教学,使教学得以影响一个业已独立的人在今后的性格形成。如果说康德的道德教化阶段仅仅在于使人获得一种“信念”(Gesinnung),在于使未成年人能够获得一种能使其坚信和秉持的判断依据,那么,赫尔巴特不仅在实践哲学和伦理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论作为教育主要任务的对世界的审美展示》和《普通教育学》延续了康德试图将教育学推向科学化发展的愿景,他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确定了“教育的自身逻辑”和“教育行动的自身逻辑”[注] 彭韬、[德]本纳:《现代教育自身逻辑的问题史反思》,《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D. Benner: Allgemeine Pädagogik. 8. Aufl.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Juventa, 2015. ,并推动了“作为科学的教育学”的发展。这一推动对于德国科学教育学的发展无疑是里程碑式的。
四、施莱尔马赫:“代际实践”中的保护、管制与支持
德国神学家、教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也曾在当时的柏林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时间分别为1813/1814冬季学期、1820/1821冬季学期和1826年夏季学期,其中以1826年教育学讲座的笔记最为完整。但是,施莱尔马赫讲座内容的出版是在他去世15年后。他作为教育理论家的身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重视,“对施莱尔马赫教育学的惊人发现”与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注] O. F. Bollnow: Einige Bemerkungen zu Schleiermachers Pädagogik.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1986(5), S.719-741.
为了加强航海类学生的毕业实习保障,学校应该严格审核学生实习企业的资质,选择实力雄厚、发展前景好、员工福利待遇高的航海企业进行合作,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权益教育培训,可以邀请航运企业专家到校,给学生讲解相关的劳动保护知识,或者通过宣传橱窗、印刷宣传册等,引导学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丰富学生的权益保护知识,同时调整学生的实习心态,使学生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施莱尔马赫的教育行动理论强调教育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并将教育行动视为年长一辈与年轻一辈间的代际实践活动。他认为,教育行动既对个人的发展负有责任,也对社会发展负有责任,因而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个人特质,并使未成年人准备好参与人类的“全体共同活动”(Mitgesamttätigkeit)[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15. 。教育行动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他称之为教育的“普遍方向”,即教育和教化要使成长着的一代有能力为成熟、独立地参与共同的多元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教育行动所要实现的第二个目标他称之为教育的“个人方向”,因为教育的普遍任务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个性和特点被教育所倡导的共性所遮蔽,因此教育行动要对每个青少年儿童的个体性和个人特质予以承认,并通过教育措施加以支持和推进。为落实这两方面的教育任务,支持未成年人的独立性的发展,施莱尔马赫确定了三种教育行动形式:保护(Behüten)、管制(Gegenwirkung)和支持(Unterstützung)。三者缺一不可,并以教育的支持为重点。
总体而言,在施莱尔马赫那里,他更为强调的是教育作为一种代际实践活动的属性,教育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年长一辈的人不再能确知年轻一辈未来所将面临的境况。虽然必要的保护和管制措施不可或缺,但训育(作为一种向教育支持过渡的形式)和支持更为重要,尤其是教育的支持。因为未成年人在教育行动的支持下最终要发展出的是一种自我负责的状态,并进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也就是康德谈论启蒙所提出的:要走出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成熟状态”正是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教育的终点。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儿童观是一种“小大人”观,“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考虑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到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注] [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那么无疑,近代教育行动形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儿童视为儿童,并由此确定下儿童管理(康德的“训诫”、赫尔巴特的“儿童管理”和施莱尔马赫的“保护”与“管制”)在给予儿童自由和抑制儿童的烈性之间所应当保持的张力和界限。这对我们当下的儿童管理工作中如何把握“可为”和“不可为”提供了参考。
教育性教学旨在将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提升到科学与艺术的层次上,将他们的人际交往经验提升到社会的和宗教的同情的层次上,从而在兴趣的多方面性的拓展中培养起他们的均衡的判断能力和明智。教育性教学同时关注各类兴趣:经验的兴趣、思辨的兴趣和审美的兴趣;同情的兴趣、社会的兴趣和宗教的兴趣。前三种兴趣属于“认识序列”,后三种属于“同情序列”。认识序列中的学习过程和同情序列中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教学而得到紧密结合。教学过程呈现为一个在“专心”和“审思”间进行相互转化的分阶段的过程,教育者展示和阐明学习对象,学习者不仅获得对学习对象的判断能力,还同时拓展了将所学到的内容运用到教学情境之外的兴趣。[注] D. Benner: Die Pädagogik Herbarts. Weinheim & München: Juventa Verlag, 1993, S.115-113. 通过这种教育行动,未成年人既扩展了自身的经验模式,即同时具有日常的、科学的和艺术的经验模式,又在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三类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中获得了锻炼。这种通过教学完成的多方面兴趣的拓展,能够培养起未成年人的“思想范围”,促使其形成明智(Einsicht,又译为“识见”、“洞见”)并按照自身的明智有道德地行动,过渡到一种自我负责的行动状态上。
支持的教育行动是施莱尔马赫教育行动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它所要影响的是未成年人的思想态度(Gesinnung,又译为“信念”)和技能(Fertigkeit)的形成。技能的形成只能是方法性的和技术性的,包括读、写、算、画的技能,也包括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的自由对话中的辩论的技能。[注] D. Benner & F. Brüggen: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S.229. 思想态度的形成则只能受到自由的生活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认为,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108. ,每个个体本身都带有主动性,而且生活本身就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因而教育行动对思想态度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在他看来,教育的管制只能用于防止那些不利于个人特质发展的因素,个人特质的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的支持。但就教育的普遍方面而言,或者说,在一种旨在走向公共生活而对人进行的教育中,应以管制措施为主。
无论采用哪一种仿真策略,都可以从以下3方面设计仿真模型:(1)设计总控程序;(2)设计基本模型单元的处理程序;(3)编写公共子程序。
五、教育行动形式分化的历史启鉴与现实意蕴
上文的论述和分析试图结构性地呈现康德、赫尔巴特与施莱尔马赫各自的教育基本思想和与之相应的教育行动方案,阐明他们对于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意义和重要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希望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自然的教育和实践的教育而使他们“学习思考”,“学习衡量自己的力量,学习认识他人的权利及对自己行为的限制”[注] [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使未成年人逐渐成长为能够在公共领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成年者。赫尔巴特通过教育目的引出的管理、教学和训育旨在培养具有多方面兴趣和能自我负责的未成年人,借助于教学和一种支持性的、咨询性的教育行动而将他们引导到公共生活中去。施莱尔马赫的教育行动更是明确地要在个体和社会的辩证关系中培养起“全体共同活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康德、赫尔巴特还是施莱尔马赫,他们所探讨的教育行动均指向如下的教育愿景:“保障各领域独特的基础知识、推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各领域独特的判断能力以及培养一种超越知识和判断的各领域独特的参与能力或行为设计能力。”[注] D. Benner: Drei Arten von Kausalität in Erziehungs- und Bildungsprozessen.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2018(1), S.107-120.
三位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愿景既反映了启蒙时代对人的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要求,也同样启迪着我们对当下教育实践的思考。本研究最后要讨论的正是近代三分的教育行动形式为当下的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启示。
合理有效的施肥对小麦的生长至关重要。小麦对大量元素的吸收,随着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生长状况而变化。产量要求越高,吸收养分的总量也随之增多。一般栽培条件下,每形成100kg的小麦籽粒,需从土壤中吸收氮素3kg左右,五氧化二磷1-1.5kg,氧化钾2-4kg,氮、磷、钾的比例约为 3∶1∶3。
(一)儿童管理中的“可为”与“不可为”
教育的保护措施适用于儿童的早期阶段,旨在使青少年儿童远离那些干扰教育的因素,从而使支持活动能够不受阻碍地发挥它的作用。[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73. 但是,保护措施并不能使未成年人完全免于有害的影响,而且也不进行知识的传授,不能促使学生去反对那些与共同生活的理念相违背的东西,因而学生如果仅仅是被保护,那他将得不到磨练,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或者拥有意志力,也就不可能带着自身力量走进社会的共同生活。[注] F. Schleiermacher: Grundzüge der Erziehungskunst (Vorlesungen 1826), S. 74-75.
欧瑞康(Oerlikon)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集团,致力于通过专业研发的材料、设备和表面技术,帮助客户提升产品性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欧瑞康集团旗下有表面处理、化学纤维两大事业板块。其中表面处理事业板块包括欧瑞康巴尔查斯, 欧瑞康美科和欧瑞康增材制造。欧瑞康美科通过一系列独特的表面技术、设备、材料、服务、专业机加工服务和部件,提供使客户受益的表面增强服务。
儿童管理的“可为”之处在于对儿童的烈性和危险行为进行制止,以防止他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这是教育行动在承认与尊重儿童的个体生命、自然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范围内的使命。而儿童管理的“不可为”则意味着,家长和教师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在这个范围内必须是消极的,也就是说,管理仅仅旨在克服儿童的野性,以保护儿童自己设定目的的能力(自由意志),使儿童的“能下决断的真正的意志”或判断力得到发展。教育者切不可过早地在儿童心中种下极具规范性的“教条”,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儿童今后无法摆脱对权威的依赖,以至于在没有教育者的帮助之后就无法进行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无法做出独立的判断,无法采取独立的行动。正如卢梭所言,“他(儿童——笔者注)所知道的东西,不是由于你的告诉而是由于他自己的理解。不要教他这样那样的学问,而要由他自己去发现那些学问。你一旦在他心中用权威代替了理智,他就不再运用他的理智了,他将为别人的见解所左右。”[注] [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7页。 此外,在班级管理中,教师要善于运用班级的法规或“公约”来制约和平衡儿童间的自由和权利,这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契约精神和儿童的品格,从而为培养他们的公民品格和能够顺利地、有教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做好准备。儿童管理所要遵守的“可为”与“不可为”是教学和德育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性工作。
(二)“教育性教学”中教学与育人的辩证统一
在近代的教育行动形式中,一种将教学和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十分显眼,这要归功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性教学”理论。较之于康德的“培养”“文明化”“道德化”过程,以及施莱尔马赫的“支持的教育”(包括思想态度的形成和技能的形成),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更具理论优势。虽然前两者均将未成年人思想态度和道德的形成也贯穿于其它教育行动形式的开展过程中,但却存在重德育而轻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的现象,换言之,他们的学说具有更为强势的伦理学导向,轻视了教学本身所要实现的自身目的。而赫尔巴特,如前所述,他构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乃是教育学自身的独特属性,也即本纳所说的“教育的自身逻辑”。因而,在赫尔巴特那里,每一种教育行动形式都有着其自己的行动逻辑,其中每种行动逻辑又都是现代教育自身逻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能偏废。
训育措施是一种指导性的和支持性的教育行动形式,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的意志的前后一贯性和坚定性,也即通过道德来增强未成年人的性格。弄清楚了意志如何做决断,也就能弄清性格的形成。“行动是性格的原则”[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因而训育(或者说性格塑造)与教学不同,它本质上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一个过程,它所希望实现的是学生要超越等级性的道德的界限而在相互交往中承认各自的人格,它要求学生要按照以均衡的多方面兴趣为前提的明智来行动,他们所要服从的应当是自身的明智的意愿而非外部的权威[注] D. Benner: Die Pädagogik Herbarts, S.119. 。这就是赫尔巴特所希望实现的“有道德的人自己命令自己”[注] J. F. Herbart: Über die ästhetische Darstellung der Welt als das Hauptgeschäft der Erziehung, S.108. 的状态,也是康德所希望实现的未成年人的一种教育上的“成熟状态”。正是在道德学说方面,赫尔巴特既是一位康德主义者,又以一种实在论的、心理学化的方式来分析人的性格形成和对康德做出批判。他将性格视为意志中的那种“坚定性”的成分,它突显于一个人“决意要什么”和“决意不要什么”间的比较。[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这一比较的过程,对于主体而言就是其对自身的意志进行判断并服从于自己的判断结果的过程。
所以,赫尔巴特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有效地整合了学校的教学育人工作,但这决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而是相互渗透,并以人的教化(育人)为根本落脚点。德国教学论的经典之作《教学论基础》曾这样来评价这一贡献:赫尔巴特使“教学论有史以来首次提出了教育学问题和任务,为未来指明了方向,为现代教育指出了问题所在”[注] [德]F.W.克罗恩:《教学论基础》,李其龙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
河南自贸区自建成以来对河南省贸易企业提供诸多优惠政策,河南省国税局除落实既定税收优惠政策之余借鉴已经试点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的税收政策,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继续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就我国当下教育和教学的现实任务而言,“教育性教学”为我们指明了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教学和育人如何能够辩证地相统一并最终落脚到育人上来。在这一点上,赫尔巴特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他将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的“自我启蒙”的理念转化为了一种教育与教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集中体现在他所强调的“兴趣的多方面性”的拓展和“思想范围”的培养上。
其一,拓展兴趣的多方面性。“兴趣”概念是赫尔巴特教学论思想的论述起点。他对兴趣概念做了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如何使之与教学相结合的详细分析。赫尔巴特的论述旨在阐明兴趣多方面性的发展机制,让教育者从中意识到开展教育和教学的最佳契机。例如,他既阐明了学生如何在“明了”“联想”“系统”与“方法”的阶段上拓展兴趣,又对应地指出了教师应当如何开展“指明”“连接”“教导”与“给予哲学的观点”的教学过程。虽然人的学习从本质上来讲是学习者自身在学习对象上所开展的过程,也即是一个自我教化或自我启蒙的过程,但这个教化过程需要借助于教育者的帮助与支持才得以开启,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教师的教育行动决定了学生是否能真正地开启学习过程以及是否是符合学生的学习意向和兴趣而开启的。更为重要的是,兴趣还关联着人的精神生活,它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源泉”,因而,当教育者将学习者的兴趣视为教育和教学的手段的同时,赫尔巴特提醒教育者,兴趣更是教育和教学的目的:“学习应当为从中产生兴趣服务。学习将会过去,而兴趣应在整个一生中保持下来。”[注] 转引自:[德]赫尔曼·诺尔:《不朽的赫尔巴特》,见《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但兴趣多方面性的拓展不仅是教育的关切,也还是道德的关切,它直接地连接着实践哲学中“完善”这一理念的实现,而“完善”的实现是道德在人身上实现出来的必要环节[注] Herbart, J. F. Allgemein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In: G. Hartenstein(Ed.):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s Sämtliche Werke: Schriften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Bd. 8), Leipzig: Verlag von Leopold Voss, 1851, S.39. 。就此,德国精神科学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尔曼·诺尔(Hermann Nohl)曾盛赞赫尔巴特的兴趣论是“真正哥白尼式的对于教育学说的拨乱反正”[注] [德]赫尔曼·诺尔:《不朽的赫尔巴特》,见《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对我们而言,赫尔巴特的这种兴趣保养论将知识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锻炼与实践相结合,将教学与育人辩证统一,并将最终的落脚点放在了育人上,无疑是对当下如何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启示。学校教学中的知识不仅在作为手段的兴趣中得到顺利传授,而且在作为目的的兴趣中获得活力和长远意义。这种真正活起来的知识不仅具有工具性的实用价值,也具有人格性的道德价值。
其二,培养学生的思想范围。与多方面兴趣的拓展和自我教化或自我启蒙紧密相关的是,在教学与育人的实施过程中,学习者要形成他的“思想范围”。按照赫尔巴特的说法,思想范围的形成甚至是“对教育者来说就是一切,因为从思维中将产生感受,而从感受中又会产生行动的原则与方式”[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所以,思想范围的培养是教学与育人相结合的另一个体现。它一方面涵盖了学习者通过知识学习过程所获得的一切判断、批判性的观点、动机、标准和行动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涵盖了“对自我和事实负责的、理由充足的行为的条件和可能”,因而也是“人格的道德中心”[注] [德]F.W.克罗恩:《教学论基础》,李其龙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教育者利用思想范围的连锁反应就可以联想出自己应当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支持,使学生的知识学习和心灵成长过程相互补充、相互衔接。同样地,教育者也要机敏地把握培养学生思想范围的发展契机,“在正确的时间传授给学生正确的知识要素,让他们产生新的有益的思想联系,从而得以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围’”[注] [德]希尔伯特·迈尔:《课堂教学方法(理论篇)》,尤岚岚、余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 。这是教育者教学育人“取之不竭的材料”[注] [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李其龙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
思想范围的建设和多方面兴趣的拓展是教育性教学的任务的一体两面。教学所培养的那种平衡的多方面兴趣就是思想范围的支柱,而思想范围不仅是明智判断的质料来源,也是形成个人道德性格的基础。因而“立德树人”的根基就在于这种培养平衡的多方面兴趣的思想范围建设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的的教学过程也绝不是与德育没有实质性关系的单纯的智育工作,它是德育工作的构成性环节。
(三)教学育人的落脚点在于成就“自由的行动者”
无论是赫尔巴特还是康德和施莱尔马赫,他们均将未成年人在教育上所要达到的“成熟状态”视为教育行动的终点。“成熟状态”这一概念本是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所界定的人的启蒙状态,指的是人具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使命”大讨论时代的思想结晶,也由此成为启蒙教育家设计教育行动形式的核心关切。教育上的成熟状态乃指未成年人可以过渡到一种自我教育的状态上。这种自我教育超越了纯粹的知识和文化的学习,而指向在社会情境中的对已掌握的知识、礼仪、社会规范等进行实践的能力。对这样一种能力的培养也同样是当代教育的核心关切。从本质上来说,学生逐渐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乃是在教育者的支持和帮助之下通过社会活动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是管理和具有教化作用的教育性教学所为之奠基的教育行动的最后环节。
在这最后一环上,教育行动的任务就在于为学生的自我教育创设条件并提供支持,教育者的角色也相应地转变为咨询者。这种教育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所有的教育影响都能转化为今后学习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行动方式,成为自由的行动者。但这一教育行动形态的落实有两个前提:其一,学习者在童年的时候不能被教师的操纵型的管理行为所压制;其二,教学过程的开展应杜绝知识的被动灌输,而以培养人的反思的判断力为目标,坚持教学和育人过程的辩证统一。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一种支持性的教育行动才能将学生引导到一种自我负责的行动状态上去,也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一种“知行合一”的品格才可能真正形成。对这样一种支持型的教育行动形式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索在对学习者进行管理和教学育人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处理学科知识、关键技能和必备品格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培养合格的公民奠定基础。总而言之,三种教育行动应当各司其职,不可相互取代。
“成功了!”壶天晓长舒一口气,和镜心羽衣拍手庆贺,他们两人合力开通了丁达的实时影像池,这是在能量共享状态下才能搭建的感应中枢节点——对于单体能量不足的两个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三者便能实时收到远在天上、地下各个战区的伙伴的影像状态并自由地沟通。像能同时看到多重世界似的,丁达这次真正眼前一亮,他的小情绪一扫而光,瞬间变得欣喜若狂。他一直未能解锁的新技能,竟然被向导室中的两位向导悄悄地解开了,他甚至开始有些感激他们。
德国教育学家赫尔维希·布兰卡茨(Herwig Blankertz)曾将18世纪的启蒙教育学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总结为如下要点:教育是可以由人掌控的;教育要深入真实生活,生活也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教育科学的萌芽就在于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解析出教育的自身结构,从而形成可精确描述的教和学的方法;教育应将儿童视为儿童,而不仅仅是小成人;等等。[注] H. Blankertz: Die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r Gegenwart, 10. Aufl., Wetzlar: Büchse der Pandora Verlags, 2011, S.28-30. 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赫尔巴特和施莱尔马赫的教育学思想和他们关于教育行动形式的方案正是启蒙教育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的时代也已过去两百多年,但近代德国系统教育学中的教育行动形式及其试图实现的精神却始终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着。
Educational Action Forms in German Systematic Pedagogy :A Study Based on Educational Theories of Immanuel Kant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and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LIN Li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China)
Abstract : One of the most revolutionary achievements of modern educational theory i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orms of educational action, namely, child management,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support. The educational and enlightenment theories of Immanuel Kant,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and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se types of educational actio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action focus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ndefinite plastic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refore also has a definite limit of their functio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action emphasi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judge and act, and ultimately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children. The three forms of educational action each has its own duties and cannot be neglected. They continue the humanistic and rational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also echo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 Immanuel Kant;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Forms of Educational Action; Judgment; Action
中图分类号: G40-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 2019) 03-0149-11
收稿日期: 2019-01-18
作者简介: 林凌,女,浙江诸暨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后。(浙江 金华 321004)
(责任编辑:子聿)
标签:康德论文; 赫尔巴特论文; 施莱尔马赫论文; 教育行动形式论文; 判断力论文; 行动能力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