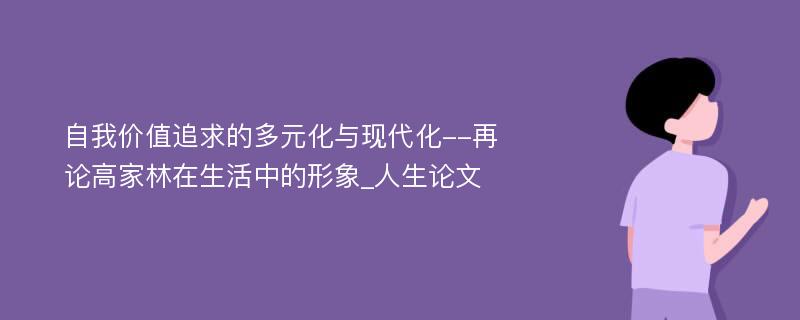
自我价值追求的多元性与现代性——重评《人生》中高加林的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现代性论文,自我价值论文,形象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1)01-111-3
近年来出版的许多种文学史教材中,对路遥的《人生》有种种赞美的评价。有的称赞小说“以写实的笔法描写了一位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青年追求新的人生道路的曲折历程”,“以主人公命运的坎坷和追求的执着动人”;[1]有的批评高加林,认为“他的行为动机中包含着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蔑视,他的奋斗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2]陈思和先生主编的教材虽然指出了作者在描写高加林形象时超越了早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但他仍然认为在高加林身上,“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意义终于被他误解”。[3]这些文学史评价的关键词几乎都定格在农村青年的“人生追求”、“人生意义”,而对这种人生追求、人生意义的描述则是突出它的曲折性和个人主义特性。这种观点其实包含着一种价值的评判,也就是说它们否定了高加林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的阶段性选择,肯定的是高加林在人生追求不断失败后的自我反思和“浪子回头”式的终极结局。对这样一种文学史评价,我们认为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在《人生》的结尾,经历了情感沧桑的高加林大声说,“真正爱的人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这一表白否定了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相恋,而把爱的真谛赋予在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情感关系上。但是,难道只有高加林和刘巧珍之间的感情才是爱情的真实反映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相互爱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一种高尚的情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感情恰恰不是真正的爱情。
让我们来看小说文本:“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哩?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你喝水!”“是剩下十一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从这些对刘巧珍的描述来看,刘巧珍是个漂亮的姑娘,她朴素而简单,但朴素和简单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单调。我们可以想像不识字的刘巧珍和通讯员高加林之间的精神沟通有多么困难,巧珍只会和他唠叨庄里的水井修好了,老母猪又下了几个崽子,再说些什么呢?巧珍自己也不知道了。确实,她除过这些事,还再能说些什么!巧珍和加林从精神上是完全不“门当户对”的,世界观不一样,生活理想不一样,加林想方设法要再次回到城市,巧珍却无法离开农村,安于农村生活。这种思想上的距离甚至裂缝,不可能为他们的感情建立起“爱”的基础。
小说中对“和巧珍恋爱中的加林”的描述,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感情不是爱情。即便当初他们在一起,也是他遭受打击极度需要人安慰的结果。就如书中描写的,“高加林听着巧珍这样的话,心里感到很亲切。他现在需要人安慰。他于是很想和她拉拉家常话了”。加林此时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期,他暂时忘记了国际时政,避开了文学。他只想抓住巧珍这根救命稻草,好好歇息。所以说农民刘巧珍和农村知识分子高加林之间的感情从一开始“爱”的成分就不多,因为爱情应该是心心相印,并不只是简单的相濡以沫。
相反,小说文本是这样描述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的:“在学校时,亚萍是班长,他是学习干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俩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又都爱好文学,互相都很尊重。”“他们性格中共同的东西很多,话也能说到一块。”“加林小心翼翼,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和亚萍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这些交代式的描写可以充分的显示出黄亚萍和高加林之间的感情,自学生时代起就有了心心相印的“爱”的基础。他们可以一起聊文学,国际政治或者其他,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互尊重,相处愉快。所以说,加林和亚萍之间的爱情才是现代性爱的代表,其内涵乃是男女双方处于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证自身价值的共享双赢状态。黄亚萍所构造的情爱,是在她与高加林相互付出中,不断获取新的情感体验,达到新的理解层次,并且双方都保持不依附于对方的姿态,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那么,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情感呢?我们认为这种情感本质上是一种“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认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时期受压抑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对受创经验的回忆是创作的契机。路遥很早就离开亲生母亲,这种残酷的情感剥夺给其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深深地尘封于情感记忆之中。加上后来路遥的情感路的艰辛,使得作家这种精神向往变得更加强烈但又无从发泄。他开始写作时,从小时候开始郁积的心理愿望会投射到作品中,不自觉地利用情感转移的方式,通过刘巧珍所具有的情爱行为,表现出对母爱的向往,难免混淆了爱情和母爱。文本中有很多地方体现,首先,在加林教师下岗、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巧珍大胆向他表达爱意。她的爱纯粹,她爱的是高加林,而不是高加林的身份和地位,即使加林只是个落魄的农民,她也愿意爱他。然后,高加林回乡后一直愁眉苦脸,巧珍主动提出要加林到城里工作,暗示为了他的前途自己被抛弃也没关系。接着,在加林真正把她抛弃之后,还哽咽着说:“加林哥,你别再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最后,当加林重新回到土地时,她不仅拉住想要给高加林制造难堪的妹妹,还央求高明楼,让加林再去教书。这就是母亲对待孩子般,无私单纯至死不变的爱,无论孩子是穷是富,无论孩子对自己伤害多深。但这种母爱似的爱情绝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两性之爱,对于生性冲动、富于追求力的高加林来说,享受这样的母爱式的女性之爱,也未必是人生的幸福。
《人生》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它的意义最突出的就在于它为出走的乡村青年设计了一个回归乡土的现实结局,在价值判断上确立了对回乡种田的肯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路遥精心设计了一些情节或细节,层层递进,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强烈又固执的“土地情结”。首先,路遥从土地这个具体的物象入手,指出土地可以给人止血,有治愈功能。小说是这样写的:“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人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话都是敢对你说哩!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可见,黄土止血原是一个象征性的功能,它治愈的不仅是肉体,而且是心灵。其次,路遥把土地抽象化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人在外界受到伤害,总是可以回到土地得到一种安慰。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皈依,认为人的根永远在土地,人一旦离开了土地就没有办法生存,并且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人的身体和心灵最终都要回到土地,完成作为人的一种循环。像巧珍这样的乡下女子,她有着最自然的纯朴和可爱,她可以没有爱情,但是她不能离开黄土地。像加林这样一心想离开土地的热血青年,也只是城市的一个过客。
第三,作品强烈偏向紧紧扎根于土地的人,他让那些辛勤劳作在土地上的人们都具有“土地”一般的品质。作品是这样描写巧珍的:“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的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写巧珍就像关中的肥沃土地一样,不待耕耘,自有深蕴。又如:“是这样的,我昨晚还听巧玲说,公社可能还要叫咱们学校增加一个教师。加林回来一下子又习惯不了地里的劳动,我想看能不能叫他再教书。”这是写巧珍像土地一样宽容厚道。确实,巧珍朴实而又内心丰富,付出而不求回报,胸怀宽大。她不愧是扎根土地的劳动者,就像土地一样,表面上朴实无华,却是千千万万人得以生存的根系,从不向人们索取和要求,却给人带来丰富的收获。
土地情结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的一种精神原型,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之作用是双面的,它能给民族的成员个体以牢固的根基感,安全感,同时也会化作一种堕力,阻碍民族成员个体对外在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安土重迁,不思进取。所以,《人生》中强烈的土地情结固然加深了人物塑造的文化底蕴,但是这种土地情结一旦进入文明的价值评判体系,它所产生的作用就值得评论家警惕。我们认为,路遥的土地情结深层流露出的是对城市文明的排斥心理,而绝对维护农业文明的根基和发展。所以在小说的后半段,他不惜花大手笔来夸张描写黄亚萍和高加林的物质生活的奢靡,对他们的爱情进行一种讽刺,以高加林再一次回到土地的失败告终。(后来改编成电影的《人生》截去了具有浓郁的小资情调的这一段,也可能是导演对于路遥这一思想的不赞同)。当然我们要为以巧珍为代表的女子感叹,被她们的善良纯洁的精神所感染。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如果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永远生活在山村,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耘,那么他们的人格如何健全,这个社会又如何进步?像高加林这样,向往城市、闯荡城市,征服城市,恰恰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土地和粮食,但同样需要都市文明,我们必须肯定社会上的分工有所不同,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生活在农村或城市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大家生活和工作方式有所不同。
追求是高加林形象的精神特质,也是高加林性格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具体显现,对高加林的追求的价值判定,就决定了对高加林这一典型性格的价值认定和意义赋予。所以如何认识和评判高加林的追求,就成了领悟这部小说和感知这一艺术形象的关键。
高加林在小说中的追求是通过两条线索表现出来的,一条是对真正爱情的追求,沿着这一线索,小说展开的是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关系。从小说描写的情节看,选择刘巧珍,就是选择包容奉献,选择黄亚萍,则是选择志趣相投。现代意义上的两性之爱,本来应该是两个独立个体建立在志趣相投基础上的情感,但小说以加林亲口承认和巧珍之间的爱情,否认跟亚萍之间的爱情,最后回到土地,悔恨不已而结束,并且在作品后半段,加强巧珍善良的戏份,浮夸加林和亚萍物质生活的奢靡以及亚萍的刁钻任性。这一结局安排,否定了高加林对现代意义爱情的追求,也贬抑了爱情意义的现代维度。在这里我们对作者的立场应该反思两点:第一,作者对刘巧珍的赞美骨子里是对儒家文化传统中“夫为妻纲”观点的认同。他花大量笔墨来赞同女子付出爱情,不求回报,隐忍吞声。但爱情不只是一方一味地付出,而应该是相互付出,共同收获。而不是以女子依托男子的形式存在,如果女子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经营一份感情,这也不能看作是爱情一定会持久的必然条件。第二,作者对高加林“始乱终弃”行为的谴责,实际上是对个人恋爱自由原则的背叛。路遥在作品中,让高加林最终梦想破灭回到农村,这是对加林的一种惩罚,其潜在的话语即批判加林抛弃巧珍这一行为。但我们事实上不应该批判高加林,苏霍姆林斯基说:“只要是人,第一个念头总是要找一个共命运的伴侣,这种心怀是生命的表现。”高加林只是遇到了一个精神上可以和自己结合的姑娘,而放弃了之前的感情。这只能说是人情感上的一种重新选择,是有生命迹象的表征,不能把其放到道德的高度上进行指责。如果我们要批评高加林,只能说他与巧珍确定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他不应该在自己的低谷时期草率的接受了巧珍的感情。恋爱自由,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国民争来的个体权利,时值80年代,我们没有理由倒退到封建社会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枕头抱着走的无爱婚姻形式。
另一条线索是对事业、对城市生活的追求。高加林的事业发展总的来说跌宕起伏,经历了下岗归乡—返城工作—再归故乡三个阶段。他高考失败之后回乡里担任教师,高明楼耍手段把他从民办教师中除名,加林回乡当农民。他拼命压制对于这种靠关系说话的愤恨,自己也凭借“关系”返城当上通讯干事,最后又由于被人告发而被取消了公职,再次回到农村。我们认为,路遥让高加林梦想破灭再次返回农村,是想借此进一步说明追求在城市立足的高加林们的失败的必然性。作品的结局无疑是对于高加林们追求的一种全面的否定。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高加林的追求是没有错的,仅仅应该批判的是他追求的方式。应该说,高加林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农村先进青年的代表,在他身上既显示了现当代上进青年身上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同时又体现着这一代农村先进青年在急剧变化动荡的改革生活中心智的不成熟。他是农耕文明发展当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有着原本落后的根源,但是,他又显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精神上,但又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人”,因为他重于发展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而很少想到要顾全大局。所以,高加林们有着视野开阔,想人之不敢想,做人之不敢做,努力拼搏向上的精神。同时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他为追求名利,不顾原则,更多地将自己坚定执着的追求理解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但是,他作为一个涉世不深,人生观世界观还在不断形成当中的青年,这种人生局限性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现代城市生活不断发展的时代,一个上进的农村青年被农村中的“上等人”排挤,被城市人侮辱,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梦想却遭陷害,自我追求和社会权力的滥用形成了强烈冲突。这种转型时代中出现的现象,恰恰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