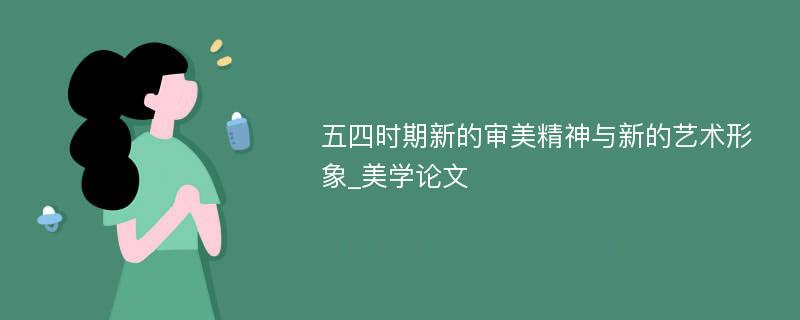
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形象论文,精神论文,新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1-0087-08
一
恩格斯谈到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时曾指出:新思想、新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1]五四时期,中国新的美学精神的确立和新艺术形象的诞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是缘于经济的发展[2],而明清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思想文化的渐变则是其应运而生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形成了古典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文化。从孔夫子到王国维,时间的跨度上达2000多年,但他们的思想方法的本质和创造的精神文化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作为站在统治集团立场上的士大夫为这种统治更完善、更有效而服务的。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被迫开放口岸,听凭西方列强的殖民资本在沿海建立了桥头堡。中国数千年的泱泱文化屈服于强盗的船坚炮利,同时也使一部分清醒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像魏源、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是呼吸到海外文明的新鲜空气,从而写出自己的不朽著作。因此,从1840年至五四时期被学术界划为一段情况独特的“近代”。“近代”真的能独立成“段”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虽然由于殖民资本的侵入,在社会性质上,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殖民资本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来说比例是很小的,同时由于殖民资本是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人的屈辱一起登陆的,它在中国主流社会和广大民众中不被欢迎是毫无疑问的,衍生于殖民资本的工商经济的思想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在中国具有广泛被接受的话语权。另一方面,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有所变化,从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社会实质的变化远没有名称的变化那样大。中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封建统治集团手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P25)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P85)所以,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实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少许变化的延续,是“古代”社会、“古典”文化稍有变化的延伸。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到五四时期还要大张旗鼓地反封建了。当然,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不容否定的,如振兴民族资本的洋务运动、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读书人的变法呼吁等等,但这些实践和理论的进步只是推动了社会的“量”变,而远没达到“质”变。中国社会完成从“古代”到“现代”的蜕变,是在五四时期。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质变。
在社会性质的描述中,“五四时期”并不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日子。而应该指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从量变最后达到质变的一段重要时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上的话语权必然体现为文化上的话语权,以《新青年》(先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为主导推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产物。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首当其冲。其实,文学思想的转变就是指导语言的艺术作品的美学思想的转变,“文学革命”就是指导文学的美学思想的革命。以此为导线,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主导文化的改变。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主导,使中国社会名副其实地进入到了崭新的时代。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是毋庸置疑的。
另有一种探索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起点是王国维和梁启超。这种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海禁的开通,中国士大夫较多接触了西方文明,在思想中产生了一种现代意识,黄遵宪、魏源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到晚清,这种现代意识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那里达到高潮。但他们仍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封建皇权的膜拜态度。他们在政体上向往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推翻皇权。在政策调整上,希望的是依靠皇帝力量进行从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革命。虽然带有浓厚的现代资本主义色彩,但他们的改良、维新是建立在与封建政权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为这个政权的巩固而服务的,所以,尽管带有现代思想的因素,但总体上却不能被归入现代思想系统。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罗筱绍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分析极为准确和深刻[4],尤其鞭辟入里的是,它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民主和民族的革命”。要实现民主就要反封建,要民族独立就要反帝。而反帝反封建正是五四运动的主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本质体现。这是戊戌维新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等没有达到的层次。中国美学精神、中国文艺思想及中国艺术形象的“现代性”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是一致的。因此,把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发端人物是不科学、不符合事实的。
总之,中国社会、中国美学精神和文艺形象的现代性发端是五四时期,这是中国的社会实践、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和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决不能人为地提前或推后。
二
中国五四时期形成的新美学精神是什么呢?这种美学精神以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大众化为特征,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为目标,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以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正视悲剧、追求客观真实为突破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5],其实质是倡导用新的美学精神来取代旧的美学精神。
如果说中国古典美学更多地与伦理学相联系,更多地考虑“善”与“不善”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美学则更多地与科学相联系,更多地考虑“真”与“不真”的问题。相对来说,伦理学涉及更多的社会性主观评价。在统治阶级的思想为统治的思想的古代社会,“善”与“不善”往往凭统治集团的准则来评判,缺少现实的依据和客观规律的标准。科学则完全按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对象,尽可能排斥评判的人为因素,使“真”与“不真”的判断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客观规律的依据。因此,强调文艺创作和审美中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传统、反封建的特色。
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胡适与“保守派”张厚载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组有关戏剧改良的文章。张厚载认为传统戏曲不可偏废,因为它有3大优点:意会化、标准化、程式化。中国旧戏的这些所谓优点遭到了胡适猛烈的抨击。胡适反对这些古典美学原则,就在于这些美学原则与客观真实性是不相一致的,按照这些美学原则创作的文艺作品必然是虚假而不可信的。
文艺作品当然可以表现虚假的情景和形象,但这种具体写作上的虚拟必须与总体本质上的真实相一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真实”,而是依照客观规律的发展性和科学的理想性所设定的“真实”。因此,这种艺术真实实际是一种“善”。“真”是客观规律性,“善”是实践意志的主观理想。按理说,作为实践意志的主观理想的“善”如果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与客观规律性——“真”——是不会发生冲突的,即“真”与“善”是统一的。这种“真”与“善”用感性形态体现出来,就是“美”。所以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6]他所说的“美的规律”,既包含着客观规律性,也包含着实践意志的主观理想性。
然而,“真”与“善”如果形成了冲突,孰是孰非呢?毫无疑问,“真”是正确的,只有“善”才会是错误的。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真”是“善”的标杆。有了“真”,才可能有“善”,有“美”。失去了“真”,“善”和“美”“皮之不存,毛亦焉附”,所以,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真”是第一层面的东西,“善”和“美”是第二层面的东西。胡适强调文艺作品要体现“真”,抨击旧戏的虚假,说到底,是用现代美学观点、现代思想文化向古代美学观点,古代思想文化的开火。这与他懂不懂旧戏、懂不懂京剧是无关的。
与胡适一样,五四新文化的闯将鲁迅也对虚假的“善”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的名作《狂人日记》就是驳斥这种“善”的最好的形象写照。他愤怒地指出:不改变对虚伪的“善”的追求,“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8](P241);不改变对虚伪的“善”的追求,中国的国民性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而虚伪的“善”的替代物应是亦诚的“真”。他不止一次地号召青年:“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在他看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9]鲁迅在此所说的“真”,不仅指文艺思想的“真”——描写的真实和真实地描写,更具有美学精神和实践意义上的涵义——强调对客观规律性的追求,反对虚伪地粉饰现实。
总之,扬“真”抑“善”在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过程中,起着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与扬“真”抑“善”相一致,五四新美学精神极其重视悲剧的本质和作用。胡适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圆满的团圆……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真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胡适、鲁迅对悲剧的重视,正反映着中国现代美学强调正视现实、敢于揭示真实的精神原则。他们所说的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与古已有之作为文艺体裁的悲剧并不是一回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抨击封建旧文化不敢描写悲剧,并不是说明文化中没有悲剧体裁,而是抨击旧文化的悲剧美学范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只是一种“瞒”和“骗”的悲剧,一种假悲剧,其实质就是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承认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艰难,没有通过自己努力去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缺少敢于奋斗、敢于胜利的豪情壮志和博大胸怀。五四新文化带来了美学精神的更新。现代美学精神对悲剧范畴深刻认识、充分重视、积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正是新文化不同于旧文化并超过旧文化的反映。
在这些新美学精神指导下创作出来艺术形象,当然是绝不同予以往的旧形象的。这种不同不是个别艺术形象在创作上的突破,而体现为新文化中的所有艺术形象都以与旧艺术形象本质不同的新面貌出现于精神文明的舞台。它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来到。
三
在新美学精神的指导下,现代艺术形象有哪些新特点呢?这些新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扬典型化,摒弃类型化
类型化是古代美学精神的重要特征。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塑造原则统治了西方数千年[7]。直至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罗仍在重申:“你教演员们说话万不能随随便便;使青年像个老者,使老者像个青年。”[10]换句话说,青年只能是青年的样子,老者必须是老者的模式。西方文艺创作中的这种类型化准则直到18世纪现代美学形态的崛起才被改变。而类型化准则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则更长。类型化准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大量的文艺实践。如唐代自居易的《长恨歌》所塑造的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形象,就是情痴情种的类型。为了塑造这对类型,作者不顾杨玉环曾为寿王妃而被唐明皇抢去的事实,不顾杨玉环因与李隆基吵架而数次被逐出皇宫的事实,尽善尽美地编造了一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恩爱夫妻。这样的艺术形象,与其说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不如说表现了作者主观世界的“善”——对男女爱情的理想模式的憧憬。这样的艺术形象是很难深刻展示大千世界的本质的。中国的小说也是塑造类型性人物的主要园地,像《三国演义》,其中的人物简直成了各种类型的代名词:诸葛亮是智慧的类型,刘备是仁慈的类型,张飞是粗暴的类型,关羽是义气的类型,曹操则是奸雄的类型。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除了他们所代表的类型,反映不出任何辩证的复杂性,因而,体现他们性质的,更多的是现象的量的堆积,而不是本质的深入挖掘。在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自然很难显示出社会的本质方面或客观的规律性。中国戏曲塑造类型人物则另有一绝,那就是让角色戴上面具。如让扮演关羽的演员戴着红脸的面具演出,以代表正义、忠勇、义气;让扮演曹操的演员戴着白脸的面具演出,以代表奸诈、阴险、狠毒。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完全被规定在面具所代表的类型中,既很少发展,更不允许转变。并且一种艺术形象一旦被定为某种类型往往很难再予以改变;即使硬要改变也常常会被先入为主的类型印象所否定。
现代工商社会显现着人类至今社会形态中的最复杂的情状,与此相应,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大幅度提高,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了。这就是五四时期及以后产生大量现代典型性艺术形象的基础。就典型性形象来说,最早、最深刻地创造出经典作品的是鲁迅。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类型性形象的现代典型性人物形象。阿Q是浙江农村未庄的一个贫穷雇工,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甚至别人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平常靠给别人打短工为生,也常受到地主和其他人的欺负,只能靠“我过去比你们阔多了”的口头禅来的安慰自己。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很难给它归类的:说他是农民的类型,可他身上有许多流氓无产者的狡诈和无赖。说他是流氓无产者的类型,可他身上又有许多农民的质朴和勤劳。说他是好人,可他也恃强凌弱、为了生存而做梁上君子。说他是坏人,可他又是被剥剥、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中的一员,甚至最后含冤被杀。阿Q能够被归入哪一种类型呢?没有一种简单的类型是与他相符的。阿Q就是单独的“这一个”。按照黑格尔对现代文艺中典型形象的分析和思格斯对典型人物的解释,典型形象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不属于任何类型,这种人物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并且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他才有丰富的意义,才揭示出社会的本质性和所含意蕴的全部复杂性。
阿Q是独特的典型人物,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似乎浑身充满着矛盾和复杂性,但这个人物产生于辛亥革命后的浙江农村未庄好像一切又是顺理成章的:贫苦和愚昧、勤劳和狡诈、质朴和无赖、向往革命和不许革命……一切的一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上都是可能存在的。而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用如椽大笔,通过艺术形象,把这一切都揭示了出来。这是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卓越贡献。
典型性艺术形象的创作是困难的。人物形象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可以包含无限丰富复杂的内涵。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这个人物必须在文艺家为他提供的环境里“必然地”具有这样那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换句话说,他的丰富复杂性是由于他的环境使他不得不丰富复杂的。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是具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代成熟的文艺家,才能创作出这样的艺术形象。但是,现代优秀的文艺家决不止步于这样的艺术形象创作,他往往以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思想文化制高点作为创作具体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基准,使典型形象不仅反映社会本质,而且是最深刻地反映社会本质。如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样的艺术形象。文艺史上许多大师的作品至今难以逾越,不是后人再也写不出类似大师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了,而是大师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所处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之巅是如此的接近,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成为真正不朽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后人的思想高度再没有达到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之巅如此接近的程度,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当然也达不到如大师的艺术形象这般经典。
不过,无论如何,艺术形象的创造摒弃类型化、追求典型化,开创了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显示着文艺美学领域中古典美学形态的逐渐淡出,现代美学精神的日益崛起。
(二)高扬平民化,反对贵族化
艺术形象是平民化的还是贵族化的,不是由被描绘的题材决定的,而是由文艺家的审美体验(它体现着时代的美学精神)所决定的。在古代,经济结构决定了它是一个等级观念森严的社会,文艺作品的形象也处处反映出它的面貌。古代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无论他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塑造他们的准则,或描写他们的写法,全部都是以统治阶级的,即贵族化的视点出发的。像古典名著《水浒传》虽然描写的是绿林聚义反抗官府的事,照理应该是以平民的视点而不是贵族的视点来塑造形象,可是事实上却相反,是用贵族的视点而不是平民的视点来创造艺术形象。《水浒传》中只有英雄是被大肆歌颂的,而其他人即使不是坏蛋也往往成为英雄行动的牺牲品或垫脚石。如黑旋风李逵,常常“抢起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逵这种滥杀百姓的行为,不但不被谴责,还隐隐予以赞扬。这样的视点就是贵族化的视点。再如武松报仇鸳鸯楼的故事。张都监受别人买通,要害武松性命。武松脱身后回来报仇。武松假如只把张都监和几个陷害他的人杀了,那是很正常的。可他却大开杀戒,滥杀无辜,这样的滥杀无辜在《水浒》里竟被作为英雄行为来写,这不是贵族化的视点是什么?又如潘巧云与和尚私通,杨雄知晓后将潘巧云骗到荒山,对她“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再“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且不说私通是不是罪当处死,即使罪当处死也不应如此地虐杀!《水浒》中对杨雄和作他帮手的石秀都以英雄好汉视之,津津乐道地描绘这场虐杀(旁边还有另一个偷看这场虐杀的好汉鼓上蚤时迁)。这种视点绝不是平民的,而是贵族的;是封建统治阶级视平民如草芥的观点在文艺家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反映,不管这个人物形象是贵族的英雄还是平民的豪杰。这种贵族化的艺术倾向在五四时期以后被摒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民化的塑造艺术形象的视点。
五四时期,率先用平民化视点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的是鲁迅。鲁迅的《故事新编》可以说是把英雄人物平民化的典范。如《奔月》,写嫦娥因吃羿射来的乌鸦、麻雀做的炸酱面吃厌了,偷吃了道士送给羿的金丹,于是飞升到月亮上去了。这个故事把神话中能射日的羿和月中的嫦娥完全平民化了,给嫦娥的奔月描绘了一个可信的理由。写的是神仙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喜怒哀乐,都是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情节,读了使欣赏者既感到十分亲切,又觉得合情合理。
在这里,神话传说中的丰功传绩完全被现实化了,本来高高在上的英雄人物完全被平民化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大禹在欣赏者心目中的地位,反而由于写得现实化、平民化,更显得可感可信可敬可亲了。这就是现代美学精神里平民意识的魅力。鲁迅《故事新编》中其他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也大抵具有这种平民化的魅力。这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在文艺领域的体现。
五四时期美学精神的平民化视点的另一个实现点,是将传统中始终被认为很崇高的事情作了很现实的、很基础的探查,揭示出生活的真实面目。如对爱情,古代文艺作品中常常赋予其崇高的地位。追求自由爱情的人物,无论他们的行为按社会标准来看是多么的出格和荒唐,始终被描写成可爱或悲壮的艺术形象。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主人公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被渲染得如此的惊天动地,被完全而充分地肯定和赞扬,而不顾李隆基晚年沉溺于声色之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事实;也不顾杨玉环仗着好色的李隆基的宠信,与几个姐妹一起出入皇宫,过着极其奢侈靡烂、荒淫无耻的生活的事实;似乎只要有爱情,一切都是美好的。殊不知李、杨的所谓爱情是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李隆基凭借拥有的权势财富可以把自己看中的女人夺过来,杨玉环为了分享皇帝的权势财富可以高高兴兴地从太子妃成为皇帝的宠妾。这样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被赞美,就在于作家只着眼于爱情的崇高,而不审视其现实基础的缘故。
《西厢记》对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形象的描绘,亦与《长恨歌》如出一辙。《西厢记》写游学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与进香的贵族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红娘作筏,私订终生,最后状元及第,终成眷属。这种爱情的基础是什么?无非是郎才女貌。相对而言,世界上能中状元的男人很少,貌如天仙的女人也不多,难道他们就不能有爱情?与此相反,真正完全建筑在郎才女貌基础上的爱情倒是十分脆弱的,男人有江郎才尽的时候,女人有年老色衰的归宿,难道到此时他们曾有的爱情也非得消失不可?所以这种艺术形象纯粹是贵族化的不顾现实的产物。其他作品如《牡丹亭》等也与之差不离。这种视点在五四时期才得以纠正。
五四时期有许多描绘爱情故事的文艺作品,但其描绘的视点都已平民化了,即都从现实的基础角度来塑造爱情故事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艺术形象虽然好像有些平淡,却更真实可信。如鲁迅的《伤逝》,写一对青年夫妻涓生和子君的故事。涓生和子君为了自由恋爱,双双走出家门结合到一起。他们曾经为爱情所激动,期盼小家庭的生活能展开他们人生的精彩一幕。然而,生活却是非常现实的。俩人成家后开销骤增,涓生的薪水渐显不足。更要命的是,涓生后来失去了工作,靠写稿谋生根本不可能,经济的拮据使小家庭中产生了矛盾。子君得了病,无线治,最后不得不回到娘家,并郁郁而终。同样是爱情故事,鲁迅没有因爱情的崇高而使之脱离现实基础,而是从现实基础入手去探索爱情存在的可能与否。这样的爱情故事及其主人公自然更具真实性和可信性。在鲁迅的小说里,爱情也是崇高的,是人类的美好的情感之一,但这种爱情绝不是可以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的,也不是高于一切社会活动的,而要以社会中人的眼光来审视和衡量。这样的视觉,就是与古代爱情作品的贵族化视点完全不同的平民化视点。正是这种平民化视点塑造的艺术形象才感人至深,使欣赏者读之难忘。如果说,在《红楼梦》的时代,由于特殊的经历而使曹雪芹以平民化的视点描绘了宝黛的爱情故事,还属于另类;那么,在五四时期以后,对爱情故事的平民化视点的描绘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美学精神了。除了鲁迅的小说外,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显示着现代美学精神总体上取代古代美学精神的时代的到来。
(三)强调科学化,摒弃神秘化
古代美学精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化。尤其是英雄人物,仿佛总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或技艺是常人不可企及的,甚至加上一些特殊的外表或降生背景,以突显他的神秘性和不同凡响。如《三国演义》写刘备的外貌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写张飞的外貌是“豹头环眼,燕领虎须,声如巨雷,势如奔马”。写关羽的外貌是“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这些奇异的外貌在小说中都被赋予了褒义,并暗示他们必将有不凡的遭际。特别是刘备,他的外貌最奇,最后达到的地位也最高。其实,两耳真能垂肩那就像猪耳朵了。两手真能过膝那就像大猩猩,怎算正常?但是,这样塑造人物是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特点,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又如《说岳全传》,将赵匡胤说成是霹雳大仙转世,岳飞说成是大鹏鸟转世,而与岳飞有纠葛的对头个个是他在仙界仇家。这样塑造出来,艺术形象带着强烈的宿命性和神秘性。尽管小说里的杜撰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实际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化成因果报应。这样的艺术形象的感染力自然不会大到哪里去。
这种塑造艺术形象的神秘化倾向源远流长,即使在清代,受工商经济特殊环境的影响产生了像《红楼梦》那样带有现代美学意味的文艺作品,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神秘化倾向仍未见消退,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出生时口里就含着一块玉。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转世,发誓要把一生的眼泪还给神瑛侍者。至于薛宝钗等金陵十二钗及贾府里略有头脸的姑娘,几乎无一不是在仙界登有名录的。小说里的现实故事被说成是仙界因缘的宿命演绎,并常常在情节的关键处仙凡两界,来一番相互印证。如此塑造形象的方式,还是古代文艺思想中神秘化倾向的体现。这种神秘化倾向,反映着古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不足,也反映着古人对复杂的社会情状所作的主观臆断,说到底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方法处于落后阶段的反映。
五四时期以后,形象塑造上的神秘化倾向几乎一扫而光,科学地、现实地描绘艺术形象成了文艺作品不约而同的选择。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是一个落魄文人的形象,作者的笔触带着可怜可叹的情感,却很客观,没有丝毫神秘的色彩。对于人物形象的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内涵,鲁迅写来更是栩栩如生:《祝福》里的祥林嫂第一次守寡到鲁镇帮佣,“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到第二次守寡再到鲁镇帮佣时,“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到最后,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对祥林嫂形象的变化,鲁迅没有从任何宿命的、神秘的因素上予以解释,而是从她的人生遭际上予以揭示:第一次守寡时祥林嫂想自食其力,故出来帮佣。第二次守寡时,不仅她的第二个丈夫得伤寒死了,而且儿子也给狼叼走了,心灵受到了重大的创伤。祥林嫂最后的样子是由于受封建思想伤害,精神崩溃,被雇主赶出来,流落街头而造成的。鲁迅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对一个妇女的迫害,并对这个艺术形象的发展变化予以科学的解释。这种深刻性和真实性是任何神秘化的古代形象所达不到的。
不仅是鲁迅,五四以后的优秀文艺家们实际都把科学化的准则作为自己塑造艺术形象的尺度:创造自己熟悉的形象,对这形象的形成和发展给予符合客观规律的解释,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真实。叶圣陶在谈他怎样写小说时说道:“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员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劝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口才。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我有几篇小说,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就是这样产生的。”[12]巴金谈《家》的创作时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13]从这些著名作家所谈的创作体会中可以看到,他们写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他们亲身感受的事情凝聚而成的,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现实生活典型化的结果。因而,他们作品里的艺术形象没有神秘化的成份,而只有经过科学酝酿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为什么古代作家创作的形象往往带有神秘化倾向而现代作家创作的形象没有神秘化倾向呢?抽象地说是古代作家按照古代的美学精神,而现代作家按照现代的美学精神。具体地说,则是古代作家塑造形象常常从观念出发,而现代作家塑造形象大多从生活出发。出发点不同,塑造出的艺术形象的特点也就不同的。这种创作出发点的转变也是在五四时期完成的。
总之,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是中国文艺美学精神从古代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的转折点。受此影响,形成了现代艺术形象典型化、平民化和科学化的特点。
收稿日期:2003-11-20
标签:美学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长恨歌论文; 鲁迅论文; 爱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