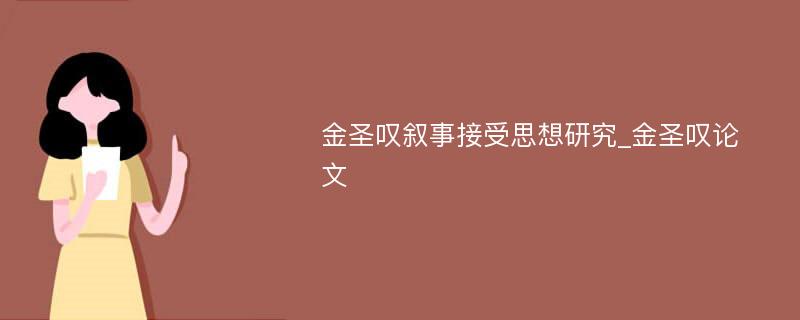
金圣叹叙事接受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金圣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10)04—138-04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小说评点家。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包含着大量的叙事思想,这些叙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两部作品的评点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观照金圣叹的叙事思想,我们发现,在他的叙事思想中有许多与接受美学类似的地方,虽然作为17世纪的中国批评家,他的叙事接受思想不可能与接受美学完全合拍,也不可能这样“现代”,但其中却有着许多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内容。金圣叹的叙事接受思想可以从文学批评的目的,叙事接受的性质、内涵、条件,和如何进行叙事接受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大的范围来说,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接受,一种专业化的文学接受。批评家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金圣叹从三个方面对文学批评的目的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首先,文学批评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人的活动的一种方式。金圣叹受佛教宇宙观的影响,认为自上次浩劫以来,已经几万万年。而这几万万年间,多少生命,“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他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其生也偶然,其在也短暂。但金圣叹并不认为人应该消极无为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①生命既已存在,就要想法度过,金圣叹将之称为消遣,虽然从终极意义上说,所谓消遣也无意义,因为生命终究还是逝去,但即使这样,人还是要选择自己的消遣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而金圣叹给自己的选择的消遣方式就是著书立说,进行文学批评。“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②这样,金圣叹实际上将文学批评作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活动形式做了肯定,从而也就肯定了文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金圣叹的人生观虽有一定的消极与游戏的成分,然而,在意识到生命的偶然性与不可逆性的同时又强调人的作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抗争。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了金圣叹人生观中积极的一面。
其次,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接受、继承与发扬光大。“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已也。”“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古人以十倍于我之才识,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古人已逝,“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这样,古人的创作和古人创作的妙处就有可能湮没无闻,需要有人“批之刻之”,将其阐发出来。这一方面是对古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对古人创作的发扬与光大。金圣叹将之称为“恸哭古人”。③
自然,对于金圣叹所说的“古人”,我们不能胶柱鼓瑟地理解。“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与我同时者自然就是今人了。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一圣叹外书》里,金圣叹谈到了古人,也谈到了后人,却没有涉及今人,似乎他的批评与今人无关。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理解。金圣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涉及古人与后人两个维度,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批评与今人无关。在《水浒》第58回的总评中,他写道:“吾因叹文章生于吾一日之心,而求传于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夺。当斯之际,文章又不能言,改窜一唯所命,如俗本《水浒》者,真可为之流涕呜咽者也。”④作者的构思读者难以知晓,作品又不能自诉,因此,就需要批评家发挥作用。这里,金圣叹虽然还是从古人、后人的角度立论,但很明显,这段论述也包括与自己同时的作者。因此,宽泛地说,金圣叹所说的古人和古人的创作,实际上是包括了同时代人和同时代人的创作的。
第三,文学批评是对读者接受的一种启发与指引。“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⑤作者已逝,无法向读者解说自己的作品,作品不能自言,而读者又不一定能够正确地阅读作品。因此,就需要批评家居间其中,解说作品,启迪读者。金圣叹将这看作是自己也即批评家的一种责任,是对读者的一种回报。他从自己思念古人出发,联想到后之读者也必然思念自己,那么,批评家以什么来回报后之读者的深情呢?“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⑥进行评点,以对读者进行启迪、指引。金圣叹将这称为“留赠后人”。自然,对他所谓的“后人”也应作宽泛的理解,是包含了今人在内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恸哭古人”与“留赠后人”之间,金圣叹更重视的是后者。因为“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唯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无亲。若夫后之人虽不见我,而大思我,……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⑦往者之不谏,来者犹可追。以往的作者已逝,作品已存,无法再做改变,批评家能做的,就是启迪后之读者。批评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读古人,而是引导后人。由此可见,金圣叹是把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读者身上的。这与接受美学的重视读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就叙事接受的性质而言,金圣叹认为,叙事接受是种再创造。
作者已逝,作品不言,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阅读文学作品,阅读的结果肯定因人而异。金圣叹对此有清醒的理解。在批判《西厢记》是淫书的说法时,他写道:“《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⑧读者由于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思想观点等的不同,阅读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这与后来鲁迅所说的: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⑨,是一样的意思。但不知鲁迅是否受到金圣叹的启发。
更进一步,金圣叹并不认为在这种种的阅读理解中,有一种理解就是绝对正确,人人都需遵守的。他一再重申,他的评点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观点。“夫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西厢》所写之人之事,不管有无,古人都没有告诉金圣叹,而“我又无从排气御神,上追至于千百年之前,问诸古人。然则今日提笔而曲曲所写,盖皆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西厢记》便如此写。”⑩这些论述,有几层意思值得注意:第一,文学接受是一种独立的活动,它独立于作者的创作活动之外,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不一定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读者阅读《西厢记》的过程也是自我创造的过程。第三,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要受到自身条件与素养的限制,每个读者的理解,都要受到其前理解的影响。第四,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都是有道理的,不能轻易否定。第五,即使是阅读经过批评家解读的作品,读者仍会产生自己不同的看法,不会完全跟着批评家走。金圣叹的这些思想接触到文学接受中接受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问题,肯定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很有超前的因素。它早已超过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给予批评家的那点自由,直指接受美学的核心观念。只有金圣叹这样对文学活动有深刻了解与深入思考的非体制文人,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那些体制中的儒生,知识再渊博,也很难提出这种想法,因为这其中实际隐含着对有着最高标准的封建大一统思想的否定。
对于叙事文本的内涵,金圣叹持文本多重性的观点。文学作品具有多重性,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不是新鲜的命题。古代学者早就提出了“文无达诂”的思想,但金圣叹是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提出文本的多重性的,这就给这一古老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他认为:“《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不是《会真记》文字。”“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11)这里,他至少区分了四种不同的文本,一是《西厢记》所依据的唐传奇《会真记》的文本,二是《西厢记》本身的文本,三是金圣叹自己所评点的《西厢记》文本,四是“天下万世才子”也即其他读者阅读所产生的《西厢记》文本。而其他读者阅读《西厢记》所产生的文本与金圣叹评点所产生的文本是不一样的,由此推论,这些读者之间的文本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无数的《西厢记》,不同的读者有自己不同的《西厢记》。它们虽然是在阅读王实甫所创作的《西厢记》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又与王创《西厢记》不同。“文章又不能言”,文学作品无法自己说明自己,读者也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自己的阅读结果。王创《西厢记》作为既定文本,并不能告诉读者它表达了什么思想,塑造了什么形象,用了什么艺术手法,这些只能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领会。在读者的不同理解中,王创《西厢记》也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这里,金圣叹实际上接触到了作为接受美学核心思想之一的潜在文本与现实文本的问题。
叙事接受需要一定的条件,金圣叹主要从接受的环境与心态两个方面探讨,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是一件郑重的事,要有良好的环境与心绪。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他指出:“《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并坐读之者,叹其解脱无方也。”(12)读《西厢记》如此,读其他的古典名著也是如此。总之,阅读文学作品,应该创造良好的环境与心绪,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作品中去,把握作品的精髓。对于金圣叹的这一观点,应该辩证地分析。一方面,文学阅读是种高智力的活动,需要全神贯注,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作品内部,把握其微妙之处。因此,从实质来说,金圣叹要求阅读文学作品取一种郑重的态度,保持一种适宜的环境与心绪,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金圣叹的一些具体要求的确有理想化的成分,一般读者很难达到,因此又不宜胶柱鼓瑟,生搬硬套。
对于普通读者,叙事接受的相关理论固然重要,但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对于叙事作品阅读的具体指导与建议。金圣叹对此十分重视,在评点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第一,是阅读叙事作品应注意的方法与原则。金圣叹强调,“读稗史亦有法”(13),不得因其是小说而轻之。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思想。首先,是接受者接受文学作品时应取的态度。金圣叹认为,对于阅读对象,应该尊敬、郑重。“读《西厢记》,便可告人曰:读《西厢记》。旧时见人讳之曰‘看闲书’,此大过也。”“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酹地赏作者,此大过也。”“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自赏,此大过也。”(14)阅读文学作品,应取庄重、感激、认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阅读对象的价值,具有极大的诚心,极其专心致志,从而达到阅读的目的。如果把文学作品看作闲书,取随便翻翻或者无聊时消遣的态度,很难对文学作品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其次,对于阅读对象应该全面把握,不仅要知道它在说什么,而且要知道它怎么说。“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而今人对于书中的妙处,往往“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对于这种阅读方式,金圣叹是深为惋惜甚至深恶痛绝的。他希望读者阅读时不仅要关心故事、情节,更要注意人物、艺术、思想,注意文学作品“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15)只有把握了这些叙事上的妙处,才算真正读懂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说什么”是一回事,“怎么说”是另一回事。金圣叹十分重视怎么说。比如《西厢记》写了男女情爱,道学家们以此说它是淫书,金圣叹大不以为然。“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自身耶?一部书,有如许丽丽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丽丽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如何公行,如何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16)总之,不要总是眼盯在《西厢》写了情爱上面,更要看它是怎么写的,这才是会读书、真读书的人。值得指出的是,强调“怎么说”,正是当代叙事学的核心观念之一,金圣叹的叙事观念,的确有一定的超前性。再次,他提出,阅读叙事作品要“一气读之”与“精切读之”相结合。“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叙事作品,尤其是优秀的叙事作品,内涵丰富、艺术精湛,不是一次阅读就能把握的,必须从不同角度反复阅读,既要从总体上把握其故事构架、人物关系、情节线索,又要从细微处把握其艺术技巧、形象塑造、思想表达的细处与妙处,这就需要整体把握与反复吟咏相结合。金圣叹认为,反复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把握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而且可以把握阅读的方法,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眼光,另去读出别部奇书。”(17)因此,反复阅读看似花了时间,其实是节省了时间。复次,金圣叹认为,阅读叙事作品需要多思。读者阅读时只有勤于思考,才能了解作品的妙处,了解作者的构思。同时,也只有多思,才能全面地把握阅读对象。
第二,是对《水浒传》《西厢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行具体的提示,以指导读者阅读,帮助读者理解。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作者的构思与作品的总体结构进行分析。在评点《水浒》与《西厢》时,金圣叹十分注意对作者构思与作品整体结构的分析,因为只有把握了作者构思与作品的整体结构,进一步理解作品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不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的“腰斩”《水浒》,将《西厢记》第五卷排除在王本《西厢》的整体结构之外,都是源于他对《水浒》《西厢》总体结构的认识。在评点的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对作品结构和作者构思的提示。如在《水浒传》第70回的总评中,他指出,“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在第70回夹评中,他又反复指出,“文字既毕,例有结束,此回固一部七十篇之结束也。一部七十篇,则非一番结束之所得了,故特重重叠叠而结束之,今第一重结束。”“第二重结束。”“第三重结束。”“第四重结束。”“一百八人姓名,凡写四番,而后以一句总收之,笔力奇绝。”“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以诗起,以诗结,极大章法”(18)在结尾一回对文章结构反复说明,以使读者对《水浒》的结构有一清醒的认识。
二是对读者阅读的重点与方向进行提示。叙事作品特别是大型叙事作品往往内容丰富,艺术手法多样,一般读者在阅读时,有时难以把握重点,找不到欣赏的途径,从而对理解与欣赏作品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需要专业批评家发挥作用。金圣叹在评点《水浒》和《西厢》时很注意这一点,经常进行有关的提示与启发。如在《水浒》第30回总评,金圣叹告诉读者,“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后面则用三四百文字一一分析这些“闲处、细处、严处、大处、别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第18回写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投奔梁山,王伦怕影响自己的地位,不想收留。吴用试图用言语挑动林冲,让他火拼王伦。正好这时林冲前来探望。金圣叹提醒读者道:“此写吴用文中,亦将林冲夹杂而写。读者须分作两分眼色,一半去看吴用,一半去看林冲,乃双得之也。”(19)这些评语言简意赅,对于提起读者阅读时的注意,却有着很好的作用。
三是对两部作品内容与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特点与妙处。如《西厢记》第一卷第一章,张珙登场,借助黄河,抒发了一番自己的雄心壮志。金评写道:“张生之志,张生得而言之;张生之品,张生不得自言之也。张生不得自言,则将谁代之言,而法又决不得不言,于是顺便反借黄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隐隐岳岳之无数奇事。呜呼!真奇文大文也。”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但这一见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仅仅将张生写成偷香窃玉之徒,张崔的恋情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张未见崔之前,将其胸怀抱负表露出来。作者借黄河让张生倾吐胸臆,正是文章的巧妙之处。但读者由于艺术修养等方面的原因,容易忽视。金圣叹将其指点出来,从而使读者欣赏其中的妙处。
自然,在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指导的时候,金圣叹也存在不够精严的地方,有些地方难免掺进了他个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甚至偏见。如他对宋江的贬斥,对某些情节、事件、字词的过度阐释,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喜说“过头话”的习惯,等等,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的来说,金圣叹对《水浒》《西厢》的阅读建议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总体上看是站得住脚的。它们与金圣叹关于文学批评的目的,叙事接受的性质、内涵、条件等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金圣叹叙事接受思想的主体内容。
注释:
①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3、4页。
②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116页。
③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3、5、3页。
④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504页。
⑤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⑥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7、8页。
⑦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7、8页。
⑧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1页。
⑨鲁迅:《〈绛花洞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
⑩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8、49、18页。
(11)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8页。
(12)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8页。
(13)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116页。
(14)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9页。
(15)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16)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8页,第11页。
(17)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18页,第12~13页。
(18)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598页,第602页,第603、604页。
(19)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第261、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