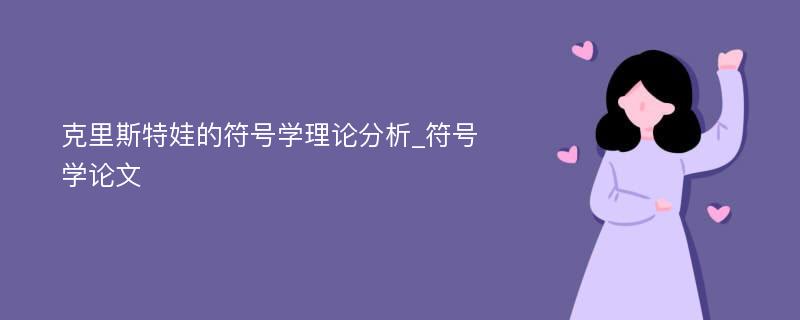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斯特论文,克里论文,符号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是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当代法 国著名的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自1966年她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后,就投入到符号学 的研究之中,旋即成为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先人物,先后发表了《符号学:解析符号学 研究》(1969),《语言——未知物:语言学导论》(1969),《小说文本,转换式言语结 构的符号学方法》(1970),《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等重要著作,提出了符号学的科 学问题和解析符号学方法,探讨了符号学的性质、任务及意指实践论,并把文学文本作 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从而阐明了符号的转换论、文本的生产性等主要思想。克里斯特瓦 博采众长,又富有创新。索绪尔、乔姆斯基、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既为她所“ 窃取”,又为她所批评,因而她的符号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哲理性以及批判意识 。
一、理论的渊源
“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种意义相同的称谓:Semiotics和Semiology,分别来自于美 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 sure)。如果作学科的溯源,早在古希腊学者那里就可找到关于符号的论述。亚里斯多 德在《解释篇》谈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问题,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 是口语的符号。虽然亚里斯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所谈的语言符号的性质与现代人的观点相 去甚远,但他们对符号的关注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
符号学作为科学研究的面目出现是在皮尔士和索绪尔的时代。克里斯特瓦指出,“他 们两人几乎同时强调符号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并勾勒其理论框架”。(注:Julia Kri steva,Language the Unknown:An Initiation Into Linguistics,translated by Anne M.Menken,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296,P.296,P.297,P.297.)皮 尔士的贡献在于他给符号概念下了确切的定义,对符号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和描述。他写 道:“逻辑学在一般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的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 ”(注:Julia Kristeva,Language the Unknown:An Initiation Into Linguistics,tr anslated by Anne M.Menken,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296,P.296 ,P.297,P.297.)进而提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因而符号理论也是关于 意识和经验的理论。而且,他区别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像”(icon)符号,与其所代表 者相似(例如一个人的照片);“标志”(index)符号,与代表物有某种联系(如烟与火相 联系);“象征”(symbol)符号,仅仅任意地或约定俗成地与其所指物相联系。符号学 从事这样的以及形形色色其他形式的分类。
克里斯特瓦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之上的,它包括三个部分 ,即隐含说话主体的语用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关系的语义学,描述符号之间形式关 系的句法学。(注:Julia Kristeva,Language the Unknown:An Initiation Into Ling uistics,translated by Anne M.Menken,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 .296,P.296,P.297,P.297.)皮尔士对符号的基本理论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但是第一个对 语言符号作出详尽、科学的现代定义的人是索绪尔,他更关注自然语言。
索绪尔比皮尔士早大约三年(1894年)提出符号学的概念。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 明确写道,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 意义。要发现语言的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 他认为,语言比任何东西都更适宜于了解符号问题的性质。基于这一认识,索绪尔考虑 过多种符号系统(文字、象征仪式、军用信号等)研究的可行性,进而试图建构符号学这 门科学:“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 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 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 的一部分。”(注:Julia Kristeva,Language the Unknown:An Initiation Into Ling uistics,translated by Anne M.Menken,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 .296,P.296,P.297,P.297.)索绪尔对符号学的探讨,几乎只限于此,但对后来的研究所 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他在语言发展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语言 差异原则、类比和演化、粘合、语言波浪的传播等重要概念,对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影 响极大;他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定义,虽然是针对语言符号做出的,却启示了所有的 现代符号学家。
索绪尔把语言研究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但不少符号学家自此得出另一结论,认为 语言是基本的,其他意指系统(signifying systems)都在语言基础上模塑而成。罗兰· 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明确指出:“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 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这样一来,目前在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与文体学中围绕 意指概念所做的研究就呈现出统一性。”(注: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页。)由此,巴特提出了符号学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并开始了语言学与符号学两个学科真正分家的历史。
克里斯特瓦像巴特一样十分重视符号学从语言领域向非语言的广阔社会、文化领域的 扩展。她说:“符号学所发现的是……支配任何社会实践的规律,或者如人们所喜欢的 ,影响任何社会实践的主要强制力在于,它是有指示能力,即它是象语言那样表述的” 。(注:Julia Kristera,“The System and the Speaking Subject”,The Kristeva R 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7,P.27.)任何言 语行为都包含了通过手势、姿式、服饰、社会背景等这样的“语言”来完成信息传达, 甚至还利用语言的实际含义来达到多种目的。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既然社会实践被视为 “象语言一样结构”的意指系统,那么任何实践都可以作为与自然语言相关的“第二模 型”来加以科学研究。“正是在这具体领域,今天的符号学才正式形成”。(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P.79,P.75-76,P.78,P.74)
符号学的普遍化和应用化过程,同时也是其理论基础深化的过程。符号学虽因现代语 言学和语义学的发展而成熟,但正因如此,它与哲学史上古典符号学思想的关系也引起 进一步的关注。由于现代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古典哲学前提有内在的联系,符号学理 论的基础问题就立即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之中。克里斯特瓦对符号学的地位特别重 视,并指出:“……符号学已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方法。它今日渗入一切社会科学 ,渗入与意指方式有关的一切科学话语或理论(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认识论、历史、 文学批评、美学)中,并位于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其中相互斗争的场所内。符号学取代了 古典哲学,成为科学时代的科学理论。”(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45页,第644页,第646页,第654页。)
克里斯特瓦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意指实践这两个方面来探讨符号学的理论思想,提出 了符号学不仅是一种语言学理论,而且是“一种批评的科学”的著名论断,论析了它与 其他科学的关系,并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双重知识空间,认为它 是一种颠覆传统秩序的政治批评实践。无疑,这与她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的解构立场是密 不可分的。
二、批评的科学
克里斯特瓦刚到法国不久,就开始思考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1969年 她发表了《符号学:批评的科学/科学的批评》这一篇重要文章,着重探讨了两个方面 的问题:作为批评科学的符号学以及作为马克思、弗洛伊德与符号学之间重要关系的生 产概念。这就是说,克里斯特瓦认为符号学是一门具有批评意识的科学理论,它吸收了 语言学、现代数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融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 关注文本的生产和文学的意指实践。她的符号学理论既不同于皮尔士、索绪尔以静态语 言分析为主导的符号学思想,也有别于德里达关于“能指”与“所指”的消解观念,她 所构想的符号学,也就是她独具特色的“符义分析”(semanalysis),是一种容纳了多 种学科知识,且运用于社会文化与文艺批评的理论方法。
在克里斯特瓦看来,当代符号学运动最有生命力的表现是所谓符号的意指性实践(sign ifying practice),即研究文化中各符号系统的能指方式。前苏联符号学成果给了她深 刻的印象和影响。这除了因为苏联符号学家侧重文化符号系统的分析实践外,也因为他 们企图广泛运用信息论的科学术语来作为符号学实践的理论工具。她认为“塔图学派符 号学家为了建立第二模型系统应用了符号逻辑、数学概念和信息论概论”。(注:李幼 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45页,第644页,第646 页,第654页。)因此,她相信作为科学时代之科学理论的符号学具有科学的特征。这就 是:第一,符号学与其他科学,特别与它从其借取模型的语言学、数学和逻辑学具有特 殊关系;第二,引进了新的词汇和破坏了现存的词汇。
“任何科学思想的更新都是通过术语的更新。每一种新的科学都包含这种科学术语的 革新。”(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P.79,P.75-76,P.78,P.74)基于这一 认识,克里斯特瓦指出当今符号学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话语视为短暂的现象,因而拒 绝传统人文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术语,却借用其他精确科学的词汇,并以为这些新的词汇 或术语具有符号学研究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另一层意义。对她来说,马克思经济学的创 新之处是把社会看作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用工作方式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双重形式中 的“生产”概念取代了“超自然的创造力”这一概念,而且马克思使用了大量新的术语 ,诸如“剩余价值”、“上层建筑”、“重商主义者”、“生产力”,并给予它们新的 意义。
克里斯特瓦一方面抽象地赋予当代符号学以“科学性”特征,另一方面却使符号学学 科具有十分含混的性质,它承担了数学和自然科学无法承担的“自我批判”任务。这是 因为“符号学利用语言学、数学、逻辑模型,并将它们用于意指实践。这种结合既是理 论现象也是科学现象,因此根本上是意识形态现象,它使所谓‘人文的’科学话语的精 确性和‘纯粹性’非神秘化。它颠覆科学方法与之有关的精确性前提,被颠覆的前提均 在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和数学中。”(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itic 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P.7 9,P.75-76,P.78,P.74)把作为意指实践的符号学称作意识形态现象,也就指出了它的双 重性格:科学分析工具和此工具的科学前提的可疑性。于是符号学既构成了其“对象” (即符号学实践活动内容),又构成了其“工具”(作为模式和分类方法),而分析工具本 身又成为分析对象。这样,与自然科学不同,“符号学只能作为一种符号学批评起作用 ,它通向一种非符号学对象:通向意识形态。”(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45页,第644页,第646页,第654页。)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观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与她作为“新马 克思主义”推崇者的立场有关。在她看来,马克思是实行符号学批评功能的第一人,因 为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思想的断绝是通过大量政治与经济的意指实践分析进行的。政治、 经济批评构成了“古典”符号学的基型(prototype)。这样,符号学可以说是继承了马 克思开创的批评传统。
由于这种双重性格,符号学在意识形态史和知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同时,符号学话 语的兴旺标志了“我们的文明正在经受文化的瓦解过程”,符号学特性说明了资产阶级 (‘良心的’)言语在其种种变体(从神秘美学到实证科学主义,从‘自由’新闻业到有 限‘介入’论)中“伪装拙劣的敌对性”。(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iti 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P.79,P.75-76,P.78,P.74)在趋向“毁灭”的资产阶级文化中,“科学”也难免噩运,符 号学意识到科学“消亡”的趋向,因而设法使科学的知识复苏,即揭发科学话语中的“ 虚幻性”和“敌对性”。于是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功能的符号学可比之“俄国革命 ”,也可视作“一种科学意识形态论”。(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itic 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P.7 9,P.75-76,P.78,P.74)而且,克里斯特瓦认为符号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功能是积极的,它 “既非相对主义也非认识论怀疑论”,却能破坏其中“科学呈现为自身封闭圈”的传统 思想,同时还揭示“科学如何在一种意识形态中产生。”这种符号学理论的突出特点在 于使科学通过符号学检讨而获得自我意识,从而破坏传统的哲学基础。由此可见,克里 斯特瓦试图使符号学的自我批评活动和对科学理论前提的批评分析,与对传统思想整体 的“革命性”批判结合起来。正是在此目的上,她的理论既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 er)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与德里达的西方思想史批评发生了联系。同时,她反复强调 她的理论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一致。因为符号学思想史与“资产阶级意识”缠结在一起, 符号学应该采取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增强自 我批判意识。
然而,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思想比马克思理论走得更远,“因为后者不能对(社会价值 、商品与货币的流通等)产品以外的生产进行分析,尽管使用价值理论勾画了一种不同 的分析模式,即对生产的内部性给予关注。”(注:Julia Kristeva,“Semiotics:A Cr 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The Kristeva Reader,P.75,P.80 ,P.79,P.75-76,P.78,P.74)托里·莫娃认为这一点还未被马克思完全掌握,直到弗洛伊 德把梦作为“工作”或“过程”来加以分析时,这种有关无意识的生产理论才得以产生 。由于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理论模式, 能够揭示意指对象的变异性,“即欲望成为语言、交流或产品之前所起作用的另一场景 (the other scene)”,于是兼具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的主体就成为意义产生和解读 的中心,主体在此不仅是结构,也是过程和实践。
三、解析符号学——意指实践论
“解析符号学”是克里斯特瓦在符号学的大范围下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它以意指系 统的成义过程(significance)为主要对象,关注说话主体的身份构成,强调语言的异质 性(heterogeneous)和物质性(material)层面以及文本的多层表意实践。事实上,它是 一种针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分析性。对此,克里斯特瓦 明确说道:“关于符号的这种解析理论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来以主体与符号为内容的 符号学运作基础,重新确定符号学的方案。解析符号学—符义解析——绝不满足于笛卡 尔式的或知性行为式的对封闭体的描述……它视表意实践为多元实践。”(注:史忠义 :《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3页,第125页,第127 页。)
解析符号学法反对把文本作为静态的符号系统来研究,它视文本为一种超语言(transl iguistic)的程序,一种动态的生产过程,认为文本不是语法的或非语法的句子的静态 结合物,不是简单的纯语言现象,而是在语言中被激发产生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复 杂的实践活动。而且,文本的构造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学客体或美学客体,它与其历史、 文化、社会变化紧密相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体”(ideologeme)通常贯穿于文本之 中。克里斯特瓦发现由史诗向小说文本的发展是基于象征表意体向符号表意体的转换。 她对这一转化的本质及其成因的阐述为我们理解诗性符号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 。
一、由象征到符号的转换
中世纪欧洲是典型的符号学时代,即“一切因素都相对于‘超越性所指’(上帝)的统 一支配下的另一因素而意指;一切都是似真性的(verisimilitude),因为在一个独立系 统下均可以符号学方式推出。”(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年,第645页,第644页,第646页,第654页。)。十三至十四世纪的欧洲是 以符号的思想代替象征的思想,以史诗向小说发展的转型时期。在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 现象之前,克里斯特瓦区别了象征与符号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差异。她借用索绪尔的话说 ,“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 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而符号却不“佯装承担象征层面这一微弱的意指关系”,能指与 所指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化、历史上的约定俗成,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于是,“作为 现代思想的基本表意体和小说话语的根本要素”,符号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指涉单一独 特的实体,远离其超验基础,但引发相关意象或概念;它的意义是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 的产物;它蕴含着转换原则,新的结构不断生成和转换。(注:Julia Kristeva,“From Symbol to Sign”,The Kristeva Reader,P.72,P.69,P.68。)
十三世纪以前,象征表意体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之中。它指涉一种不可知、 不可代表的宇宙超验现象和人类普遍本质,象征与指称物是单一的联系,其间的二维空 间是分离、不可交流的。象征体系中的文学类型往往是神话、史诗与民间故事,所有的 文本组织形式是封闭的、同质的和静止的,对立的事物呈现出分裂、不相融的二元特性 ,诸如高贵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勇敢与胆怯。在以象征表意体为基础的文本中,亚里 斯多德的三段论显而易见,人物的独特性也受到了限制,往往代表二元对立中的一项。 例如《小红帽》中的“小红帽”是善的象征,“大灰狼”则是恶的化身。这种二元对立 论反映了在一个固定的空间而不是时间之内的故事叙述的静态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单 一性。
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象征受到符号的挑战。随之,象征的神圣性被符号的含糊性/ 双重性(ambivalence)所代替,意指单位不再指称对象所隐含的宏大思想。符号以开放 性、异质性和动态性为特征,具有不分离(nondisjunction)原则和双重矛盾性。对立品 质、否定性因素通常在同一人物身上显现,譬如被嘲笑的君王、战败的勇士,不忠的妻 子、邪恶的教士。实际上,符号的表意体允许指涉“存在”现象的复杂性。
在从象征向符号转换的话语中,唯名论(nominalism)起了决定性作用。唯名论者与亚 里斯多德的信徒及古典神学思想相反,否认共相的存在,并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抨击象征 语言的思想,抽掉其超验的理想支柱,摧毁其贯时的内容,而代之以共时方向的符号的 多样性。贯时的无限性(向往神)被共时的无限性,即事物与个性行为的多样性、客观世 界的无限性所取代。而且,“唯名主义以符号的拼合来构造现实,并以小说的‘无意识 ’哲学及其创造性来建构艺术这一独立范畴”。(注:Julia Kristeva,“From Symbol to Sign”,The Kristeva Reader,P.72,P.69,P.68。)
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期,小说作为一种符号实践的叙述文体开始出现。法国第一 位小说家安托万·德·拉萨勒(Antoine de La Sale,约1385-1460)的《让·德·圣勒 特》继承了唯名论的话语类型,作品一开始通过贵妇之口介绍了“共相”,它们象征着 基督教世界的各种美德,诸如忠诚、希望、贞洁、忍耐、正义、毅力和谨慎;然后作者 笔锋一转,质疑并驳斥了这种理性的真实性,并以现实的合理性取代了种种“共相”的 合理性。作者的直觉与神秘主义者所鼓吹的超验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拉萨勒小说中 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直觉,是表意手段的一种运作类型,作为运作核心,完成了由神到人 的转化。克里斯特瓦还对拉萨勒的第一部作品《拉·萨勒德》中的希彼尔(Sibyl)王后 的形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位欧洲神话中的可怕的女祭司,到十五世纪以各种不同的形 象出现于文学、艺术之中。事实上,“Sibyl一词已脱离了象征的超验性,而享用符号 的‘任意性’,”它是“话语无限可能性之产物”。(注:Julia Kristeva,“From Sym bol to Sign”,The Kristeva Reader,P.72,P.69,P.68。)
从象征到符号的转化中,狂欢节话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反规律的话语,表 现出一种反象征性、双重性和兼容性的特点。狂欢节话语摈弃了史诗故事中“讲叙者— —讲述内容——受述者”的这种传统的口头交际模式,建立起一种既呈直线型,又呈体 积型、决裂型的交际空间,也就是一种既传达意义信息,又作为表意实践、兼具场景和 生命活力的双重多义的话语空间。于是每个参与者同时扮演着作者、演员和听众、讲述 者、信息和受述者、规律和反规律等多重角色。人物的角色不断转化,面具成了保证转 换机制联结双方的特殊媒介。它是交替的标志,是对同一性的拒绝。这种以相异性为特 点,否定真实身份的面具成为符号、文字产生作用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典型,也成为动摇 象征的重要标志之一。小说采用了面具空间的双重形象、对话式组织和施动者转换等手 法。而且,狂欢节话语往往体现出一种表意游戏的形式,艰涩的语言、重复的语音、无 因果关系的言语杂乱地拼凑在一起。克里斯特瓦认为早期的小说试图把这些表意游戏引 入叙事脉络而加以理性化。拉伯雷(Rabelais)是第一个作这种尝试的小说家。他的作品 里不乏艰涩词语、言语拼凑、简单罗列等现象,小说中的叙述性复句因为重复而背离了 原来的语义,仅仅成为小说文本转换中空洞的表意手段和修辞手段。他的作品可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卡夫卡等深受狂欢节话语影响而创作出的小说相媲美。
通过对史诗向小说转化的这一意指实践的分析,克里斯特瓦指出表意手段与语义对称 的二分法属于象征观念,而符号观念的文本突出语言的物质性与异质性,突出表意手段 的转换和变化过程。在转换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不断生成。
二、文本的转换
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文本是由话语、叙事和两者关系构成的整体,话语、叙事构成相 对独立、又可区分为若干层面的意义层次。克里斯特瓦指出这种静态的研究方法不能揭 示文本的成义过程以及内在的生成规律。她强调文本的生产性或生产过程的机制,提出 文本不是一个语言学现象,不是言语汇集中出现的那种平淡无奇的意义结构,而是意义 结构生产本身,“是记录在印刷文本这一语言‘现象’,这一现象文本上的生产过程。 ”(注: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第125页,第127页。)她心目中的文本是一个生动的、具有活力的实体。
强调文本动态性的克里斯特瓦,将文本分为二个层面:现象文本(phenotext)和生殖文 本(genotext)。前者指存在于具体语句结构中的语言现象,常见的音位、语义描写和结 构的分析适用于这类文本,但它与语句而不是文本主体(表述)发生关系。生殖文本则“ 规定了表达主体的构成所特有的逻辑的运算,是现象型文本结构化的场所,是意义生产 之场”。(注:转引自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外国文学研究》 ,1989年1期,第17页。)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现象文本为文本的表层,即被意指的文 本结构,生殖文本为文本的深层,即意指过程的生产性。事实上,她的文本二分法与乔 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既相关又分离。
生成语法理论的优点在于把语言形态的描述从静态的结构,转化为动态的结构,视言 语行为为生成过程,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语言观念以及所有表意体系的方法。无疑,克里 斯特瓦接受了生成语法理论的影响,她的现象文本和生殖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与生成语法 中的表层结构——“语言行为”(performance)和深层结构——“语言能力”(competen ce)是相对应的。但是,她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中看不到任何一种成分类型向另一 种成分类型,一种逻辑类型向另一种逻辑类型的过渡。实际上,所谓的生成语法,并不 生成任何东西,只提出一种生存原则,假设出一个深层结构,作为表层结构的原型。她 心目中的“生殖文本”是语言运作的一个抽象层面,绝不反映语句的结构,是先于并超 越语句结构的语义生产过程。这种成义运行过程发生在语言之中,却不能浓缩为所谓正 常交际活动中的表层话语。生殖文本并非为现象文本生殖现存的语句,而是成义过程中 不同阶段的表意手段。由变化中的表意手段构成的序列可能是现象文本的一个词、一个 语句、一段言语、一个无意识结构等。生殖文本是不断异化、处于无限变化过程中的复 数的表意手段,现象文本中已经格式化的表意手段只是无限表意手段中偶然采撷的一个 。(注:史忠义:《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第125页,第127页。)这种复数特征超越了现有格式和深层结构的二分法,也超越了现 象文本中表意手段的单一性。因此,“转换”是生殖文本的鲜明特征,是文本生命力的 源泉。
克里斯特瓦的意指实践论是与她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批评方向一致的,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色彩,她坦然称其为唯物主义的意指理论。与此同时,它与结构主义,甚至解 构主义思潮相关,强调文本意义的解读是一种无限演变的过程。她所解读的大量现代派 文学作品均为其解析符号学方法之实践。
克里斯特瓦在《诗歌语言革命》一书中(1974)对诗歌文本作了更深入的研究,认为文 学文本并非是一般文本的子系统或偏离正常规范的文本群,而是具有“无穷代码”的文 本。文学文本是基于能指的无限运动,它由能指不断产生、活动、再重组,并不断扩散 。这一意义无限观念明显地来自德里达的理论,但又辅以她喜爱的数学元语言加以说明 。作为能指生产构成项的不再是索绪尔的符号,而是德里达的“字符”(gramme)。她视 其为一种代数性的超组合段单元,甚至以聚合论和符号逻辑进行说明。诗的意指生产即 为一种多重联系网。如同所指总是逃逸的、延迟的一样,主体的最终构成也是生殖文本 作用不断延搁的结果,它们导致了现象文本中种种不确定的意义效果。这样,如同德里 达的解构论,克里斯特瓦的解析符号学,开放了文本所隐含的无限可能性。然而,他们 两人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德里达基于“书写不能在主体的范畴下思考”之认识,对结构 和文本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从而解构文本形式的统一性、结构与意义的完整性。克里斯 特瓦虽否定文本的封闭性和静态性,却关注语言性质的说话主体,并以论述表意手段的 发展性和变化性,突出了文本意义生成中的生命活力。这与解构主义者的怀疑论是大异 其趣的。因此,托里·莫娃等批评家把她看作“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是不无道理的。
四、结语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与她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作为法国左翼思想家和 “先锋派”批评家,她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巴特文化意义批 评等理论思想,另一方面吸收了现代语言学、数理逻辑、俄国形式主义、格雷马斯叙事 学等批评方法。她的理论所包含的知识容量和概念常使人头晕目眩,科学的客观外衣和 解释性的主观意见往往任意混合。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多重知识的融合、多种理论的交 错使克里斯特瓦成为当代法国最出色的符号学理论家之一。
在符号学领域,她的主要贡献在于超越了索绪尔的静态结构主义模式,而转向动态的 文本研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这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并把它用于文化与文本的批 评实践。而且,她对符号学的科学性论述及理论探讨,使符号学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科学 领域中一种具有双重批评功能的重要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