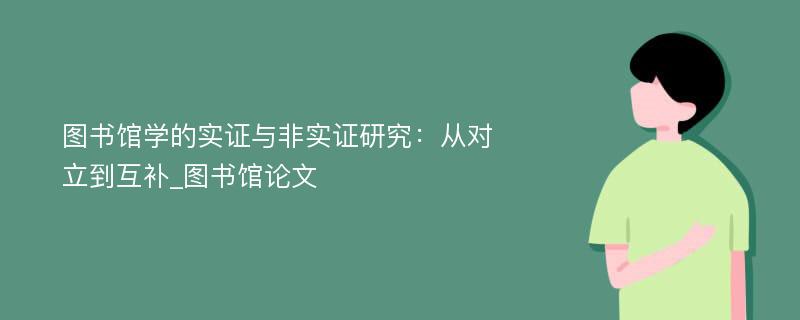
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与非实证:从对立走向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对立论文,与非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缺失实证研究。于是,“弘扬实证研究”的呼声骤然响起,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陡然增多。与此同时,人们对非实证研究的责难和不屑之声也不绝于耳。那么,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应该互补共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崇尚实证:中国图书馆学的新潮流
实证研究原是自然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经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倡导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它“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追求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客观化、精细化和准确化的目标。具体而言,实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验、调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描述研究对象的现状、探究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实证研究方法根植于实证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须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
在图书馆学领域,成立于1928年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曾在20世纪30~50年代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由此,实证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长盛不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缺失实证研究的传统,而经验总结和思辨研究方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不过,历史的时钟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缺失实证研究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并从事实证研究,现已呈现出一股“实证研究热”。据统计,2000-2010年间,国内图书馆学界发表实证研究论文109篇,而且从2008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中实证研究类课题数量大幅增多[2]。这表明,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广泛认同。
认同并推广实证研究方法,这本无可厚非。尤其是以实践性、应用性为显著特征的图书馆学,在其研究中提倡和贯穿实证精神,广泛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其科学性与规范性,所以实证研究方法应该得到提倡和弘扬。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些提倡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人在提倡实证研究的同时贬斥非实证研究方法,言语中渗透出只有依靠实证研究方法才能改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落后局面的“实证至上论”倾向。如有人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长期处于“感悟性研究”状态,认为“当今图书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往往带有非常明显或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普遍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大多数文章,仅限于空泛的议论……整体流于低水平重复和徘徊的状态”,动辄“发宣言、展共识、谈精神、说理念……一厢情愿地时尚空谈”,图书馆学“日渐成为自拉自唱的‘自恋’之学”[3-4];我国图书馆学长期无法“融入学术主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实证研究,因此只有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才能“提升图书馆学在现代学术之林的地位”[1];未经“选题—检索—研究—结果”这一研究程序所产生的所谓“成果”都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伪果”[5]。与此同时,一些人把提升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希望寄托于实证研究,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当今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切实发展我们的事业,掌握真实的情况,了解准确的消息,除规范化的实证研究之外,别无他途”[3]。
实证方法倡导者们的上述言论,至少传递出三方面的意义:一是“过去时光的惨淡”,即以往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大都属于“空泛议论”,即使是曾经产生过“热门效应”的图书馆宣言、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理念等研究,也都属于“感悟性研究”,缺乏理性、缺乏客观性,更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致使图书馆学长期不能融入学术主流,学科地位低下;二是“告别过去,迎接新救主”,即告别过去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范式,而去迎接实证研究这一新救主,亦即迎接“一个全面系统地开展实证研究的新时代”[5],因为实证研究能够反映“真实的现实,是有实证数据支撑的,是可靠的,是能够使大家知其所以然的”[3],因而能够为当今的图书馆学研究摆脱“学术困境”指明方法路径;三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的“全面回归”,亦即主张用客观、公正、中立的职业价值观和严格按规范程序进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建立实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这也就意味着实证主义认识论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结束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崇尚实证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崇尚实证,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新潮流,这意味着非实证研究将逐渐丧失昔日的辉煌而走向边缘化。面对这种过度推崇实证方法的潮流,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反思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2 图书馆学研究过度推崇实证方法的弊端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研究方法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端:容易导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容易导致以形式合理性代替实质合理性的偏颇;容易产生以科学思维排斥人文思维的单向思维模式。
2.1 容易导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
简单地说,实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经验实证,二是逻辑实证。经验实证主要根据观察或调查到的事实来证明某种假设,目前国内图书馆学界的大部分实证研究就属于经验实证范畴。逻辑实证则借用语义逻辑或数学逻辑来证明某种原理或假设,国内叶鹰先生的“抽象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研究就属于逻辑实证范畴。
实证方法的应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所研究的问题应具有因果规律性,即具有因果一致性的内在联系;二是研究方法与规则是统一的,即研究必须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具有严格因果关系且可以进行逻辑归纳的事实判断领域。因此,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那些具有因果关系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用实证方法去客观描述。但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问题就不宜或无法用实证方法进行准确论证,因为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具有严格的因果规律性,不宜或无法用统一的规则来强行论证。如图书馆立法的目的问题、提供平等服务的合理性问题、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合理性证明问题、为弱势群体提供特别服务的合理性证明问题、图书馆制度(包括宏观与微观制度)的合理性证明问题、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对图书馆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就不宜或无法完全用实证方法去客观、准确地论证。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弱点。这个弱点主要表现在它无法解决价值选择问题,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无法避开价值选择问题的。文德尔班指出,“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界的齐一性,目的是要形成具有客观普遍性的事实判断和定律,社会科学则以价值为对象”[6]。显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以实证方法鄙视或排挤非实证方法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认识和做法必然造成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事实上,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法彻底做到“价值无涉”,对此普特南(Hilary Putnam)指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至少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7]也就是说,以“价值无涉”为指导思想的实证研究,难免以客观、真实的名义强行驱逐价值,致使所谓的“事实”变成了无灵魂的“事实”。
2.2 容易导致以形式合理性代替实质合理性的偏颇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始终面临两类理性的二元对立,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这种对立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式合理性以事物的可计算性、效率作为“合理”的标准,而实质合理性则以维护人类社会的道德、公平、和谐等正义价值作为“合理”的最终标准。技术理性以形式逻辑或数学逻辑作为它的方法论基础。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被量化或形式化;有关人类理想、人的本质等形上问题被驱逐出科学殿堂之外,只追求所谓的“真”,而“善”、“美”等主观判断的东西被界定为“意见”而非“知识”。于是,技术理性压制价值理性,整个社会都被技术理性的逻辑所控制,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由此形成。
实证研究方法因其以形式逻辑或数学逻辑作为它的方法论基础,所以它的应用也难免产生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不一致性问题,尤其难免出现以形式合理性代替实质合理性的问题。其表现如下:
第一,以“非完全事实”代替“完全事实”。推崇实证研究方法的人认为,实证研究能够反映“真实的现实,是有实证数据支撑的,是可靠的,是能够使大家知其所以然的”。其实,实证研究所反映的现实不一定是“真实”,其结论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例如,对图书馆员快乐指数的实证研究,其论据来源于调查统计数据,并最后以加总平均的方法得出结论(指数),这里必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调查来的统计数据反映的是真实情况(完全事实)吗?不一定,因为被调查者(图书馆员)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满意或不满意及其程度的判断,是含有价值意向的判断,而且每个人所填写的数据不一定是自身感受的真实表示,甚至可能在某种“暗示”或“误判”的影响下作出“虚假表示”,这说明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调查统计数据不一定反映完全“真实”的情况,而只能反映“非完全事实”。对此,实证论者可能提出这样的反驳:个别被调查对象的“虚假表示”可通过加总平均方法“忽略掉”。殊不知,加总平均所忽略掉的是客观存在的差异性。这种只反映整体性、同一性而忽略差异性的实证研究,难免陷入“多数暴政”的逻辑陷阱,摆脱不掉以“非完全事实”代替“完全事实”的逻辑尴尬,因而其结论也不能完全保证“可靠”。
第二,以形式逻辑代替其他逻辑。实证研究擅长的是用数学公式或图表方式形式化地表示现象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叶鹰先生把图书馆的“轴心”要素概括为“资源—知识—服务”[8],并构建了图书馆函数:L=L(l,i)[9]。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作这种形式化处理是有必要的,因为它能把复杂的图书馆现象概括为三个变量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使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认识达到抽象的高度。但是,图书馆学研究不能仅限于此,因为建立图书馆函数只是遵循形式逻辑的研究,而图书馆发展中的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则需要作非形式逻辑研究,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如何定位图书馆发展战略问题、如何通过立法保障图书馆经费问题等,就不是形式逻辑研究所能阐述清楚的。也就是说,形式逻辑研究有其适用范围,不能无限扩大其应用范围,即不能以形式逻辑研究代替其他逻辑研究。
2.3 容易产生以科学思维排斥人文思维的单向思维模式
众所周知,科学思维和人文思维是有区别的,两类思维各有各的价值用途。人文思维的逻辑相对于科学思维的逻辑而言,具有非必然性、非形式性、象征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特点,它不以真值条件为依据,它的主导推理类型是类比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或归纳推理。“人文思维逻辑也就是研究人们怎样理解、反思和诠释(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思维方法与逻辑机制。……它的‘定义’不可能是实指定义或本质定义,而是语用定义或语境定义,它的判断是价值判断”[10]。图书馆学研究需要科学思维,以达到一定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效果,但科学思维并非适合于一切图书馆现象的描述,有些图书馆现象可能更适合用人文思维来阐述。如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克劳福德和戈曼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提出“图书馆学新五律”)、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等论著,其思想内容主要用人文思维来阐述而未用科学思维进行确然性证明,但仍然具有普遍的说服力和广泛的认同性。过度推崇实证研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排斥人文思维的单向思维模式,致使图书馆学理论缺乏应有的人文向度。针对这种过度推崇科学思维的倾向性,巴特勒曾批评道:“科学的真是太过头了。”谢拉也曾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近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11]。
3 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的互补:未来的应然走向
学术研究应该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实证研究方法也不例外。这表明,实证研究方法和非实证研究方法之间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互相鄙视、互相排斥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也应该走向互补,尽早避免过度推崇实证方法从而排斥非实证方法的偏颇。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从方法一元走向方法多元,从方法专制走向方法民主。
3.1 从方法一元走向方法多元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只能在特定的适用范围内有效。这表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其实都是“特殊方法”,而不具有无限普遍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应该遵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规则。从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而言,不同的知识类型应该选择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国哲学家舍勒(M.Scheler)曾把人类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统治—事功型知识、本质—教养型知识和获救型知识[12]。统治—事功型知识即为实证的经验理性知识,本质—教养型知识即为形而上学知识,获救型知识即为精神性个体行动知识。无论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统治—事功型知识的论证,而很难适用于本质—教养型知识和获救型知识的论证。就拿获救型知识而言,它“没有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真与假的问题,只有个体性的有效的有无意义的区分”,它“涉及个体的福乐、悲苦、希望、安慰,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有非个体性的客观一致性”[12]253,因此获救型知识很难用实证方法加以论证。借鉴舍勒的知识划分方法,我们也可以对图书馆学知识结构进行划分。图书馆学知识通常被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大类。据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简单判断:实证方法主要适用于应用图书馆学研究,而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则更适合应用非实证方法,因为理论图书馆学知识大都涉及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问题。笔者在此想强调的一点是:理论图书馆学知识并非只涉及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新内容的探索,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还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或使命——理论批判,亦即对图书馆事业实践中的非合理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这种揭露和批判一般以人文思维和价值判断方式进行,其中需要主观见解的陈述与个性的张扬,因而不宜用以客观和中立为特征的实证方法论证。这就表明,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非实证方法也大有其用武之地,其应用也应该得到与应用实证方法一样的重视和尊重。
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研究,知识类型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过度推崇某一种研究方法的“方法一元论”,必然严重束缚思想的开拓性与创造性。从方法一元走向方法多元,是活跃学术思想、开拓学术思维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该提倡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同时并举的“方法多元论”,那种死守实证方法一隅而不顾其他方法的“方法一元论”只能落得“特殊性以普遍性自居”的尴尬。
3.2 从方法专制走向方法民主
用一种研究方法鄙视或排斥另一种研究方法,显然是方法专制的表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方法的认识和做法,就具有一定的方法专制倾向。如有的人认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加强严谨、规范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才能提升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5],这种“孤注一掷”式的过高指望实证研究的效力的观点,难免踏入以实证方法排斥非实证方法的方法专制轨道。方法专制必将导致以下两方面的弊端:
第一,缺失方法民主。允许和提倡多种研究方法的和谐共存,就是方法民主的表现,而方法民主又是学术民主的重要表现。以一种研究方法鄙视或排斥另一种研究方法的方法专制,实质上是以自己的意志否定他人意志的狭隘欲望的表现。其实,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之间决不存在高低贵贱或孰优孰劣之分,每一个研究者个体既有使用实证方法的自由权利,也有不使用实证方法的自由权利。那些未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不能只是因为未使用实证方法而受到鄙视或否定。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而言,实证方法无法突破工具理性的限度,因而难以阐明涉及价值理性的问题,而我们知道,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恰恰存在着许多需要用价值理性思考的问题。图书馆学研究中可使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只是研究者依据所阐述的知识类型和研究目的而有待选择的工具。所以,研究方法之间只存在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而不存在天然的孰优孰劣问题。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方法而鄙视非实证方法,正是人为地强行区分孰优孰劣的非民主表现。
第二,缺失批判意识。崇尚实证方法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研究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殊不知,在追求客观性与准确性的过程中往往难免丢失一些可能更为重要的东西,其表现如缺失价值理性、缺失批判意识等。本文只谈缺失批判意识的问题。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观察、抽象得到的事实才是纯正、科学的事实。这种“唯事实论”,其实只看到了现象逻辑而未看到现象背后隐藏的更“真实”的逻辑。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看到了这种更“真实”的逻辑。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实证逻辑以尊重事实的名义为统治逻辑辩护,其“思维的逻辑依然是统治的逻辑”[13],因为实证研究所依据的“形式逻辑所蕴涵的形式化、抽象化和数学化的倾向,它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生活所采取的中性的态度,它对抽象的思想秩序和法则的维护,它对现实矛盾性的排除,都使它缺少对实在本身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14]。马尔库塞称现代社会中缺失批判和否定意识的人为“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那么,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研究是否容易导致缺失批判意识的弊端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图书馆学实证论者们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证据是基础,证据决定着研究,这就是实证研究的关键”[5]。意思是说,证据就是事实,证据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然而,证据不等于事实,更不等于真实,因为证据是通过观察现状得来的,而“观察渗透着理论”,“现状充满着假象”,所以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结论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正因为实证研究以证据为“马首是瞻”,极易陷入“现实就是合理”的逻辑误区,“缺少对实在本身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图书馆学实证论者们贬斥非实证研究,其思想方法难免掉入“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的逻辑陷阱,其结果必然难免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意识的缺失。
笔者作出上述论证的意图在于: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上,方法一元和方法专制都不可取,应该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导下,使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之间实现互补相安的共存共荣局面。
4 结语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图书馆学界的人们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恨不得让实证研究“一统天下”时,自然难免遭遇反对的声音。如已经有人指出,“缺乏理论的实证研究,对数据的描述多,对规律的总结少,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证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及总结上,而未能对变量尤其是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有力的解释;对事实的叙述多,对事物的抽象少,我们的实证研究对事物的解释也往往采用的是用现实描述现实的形式,而不对研究事物进行认识层面的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实证研究不能深入研究对象的抽象层面,总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热衷于描述事物表面的联系,没有解释力和预测力”[15]。无论这种反对理由是否成立,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遵循:无论反对者的观点可否接受,都要给反对者以说话的权利。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说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吧,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自己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