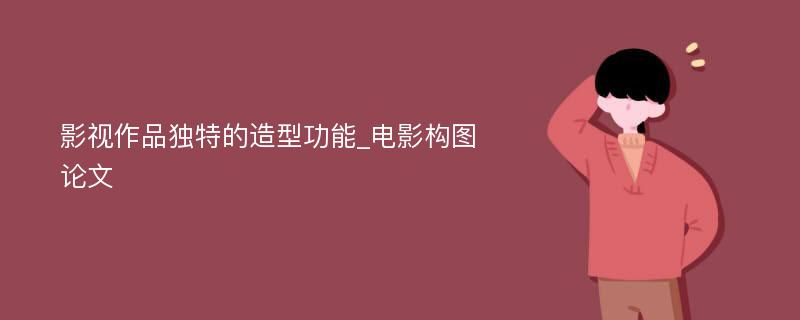
影视作品的独特造型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作品论文,独特论文,造型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视艺术也许不是最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但却是最先进和最接近自然生活形态的。因此,构成生活原生态的声、光、画面就成为影视作品最本质和最重要的造型元素。但在电视剧作中,对语言的重视往往超过了对声、光、画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影视作品中声、光、画的造型功能作一探讨,以提高影视制作的水平。
音响(音乐)的造型功能
有一种理论认为,影视屏幕是一个三维空间结构,首先是由一系列分镜头构成的图像空间;其次是观众感受空间;第三便是由声音拓展的潜在空间。这个潜在的空间有时可以通向一个隐蔽而实则具有巨大扩展力和可能性的情节空间(或曰心理空间)。如经典名片《公民凯恩》的片头,报界大王凯恩躺在病床上,喃喃地说了句“玫瑰花蕾”便死去了。这里便由声音提供和暗示了一个“情节空间”的存在,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这个“第三空间”运行,它似乎是通往另一个更加隐秘的心理时空的门户,使观众始终面对一座巨大的心理迷宫,一座不可捉摸也无法接近的卡夫卡式城堡。可以说,由声音造成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扩展了观众的“心理景深”,扩大了银(屏)幕的空间涵义,是影视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及表现手段。
声音,主要包括对白、音响和音乐。音响主要由影视作品中的物音、乐音、人声、噪音等构成。它是通过音频传播出来的电子化的声音,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声音,因此它与生活呈现相似的状态,又不同于真实的生活,如中高频噪音可以采用音乐中的十二音技巧,用乐队高音乐器演奏,利用人耳最敏感的频段制造出极强的听觉刺激,但从听觉感受上还是乐音,而不是毫无美感的彻底的噪音。音响的运用是使电视剧最接近人的自然生活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音乐是最富旋律美和节奏感的声音。人们常常说,当语言不够用时,便产生了画,当画不够用时,便产生了音乐。音乐是流动的画,是无字的诗,它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语言,它可以使情感发生蝴蝶的触须一般微妙而纤美的颤动,可以像爬山虎一样细细密密地爬满心灵的篱墙,它既能“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地暗示出一切,也能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气势对澎湃的激情予以完美的展现。音乐的适当应用,是填补动作及语言的空白,创造完整叙事时空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音响及音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剧情及剧中环境作背景音响(音乐),充当无形的“道具”,创造真实的时空效果。如电影《邻居》中,影片一开始,便利用音响效果制造了一个真实的空间环境——收音机中的广播员正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走廊中,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炒菜声、锤钉声以及嘈杂的人声合成了一部真实的、多声部的生活交响乐,无论“旋律”、“节奏”、“配器”,全都因地制宜,尽善尽美,创造出一个充满了“生活感”的时空环境。再如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和巧珍坐德顺爷的马车进城,开始的气氛是轻松活跃的,笑语声,清脆鞭响,马蹄轻快的“得得”声,合成了一支优美谐谑的小步舞曲,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后来,德顺爷讲了一个虽经时间磨洗、仍留有淡淡伤感的真实爱情故事,年轻人沉默了,心中有根隐密的弦被轻轻触动,一曲悠扬而情深意长的民歌“走西口”不失时机地溜了进来,马蹄儿的得得声似乎变得空幻轻灵,把人们带进了一条绵长的时间隧道。在时空的那一端,一样有着风花雪月,离合悲欢,而在时空的这一边,谁知道等待着年轻人的又是什么呢?那少不知愁、如小孩儿额头一般光洁的“爱情”上,第一次被镌刻了一道浅浅的皱纹。再后来,高加林和巧珍分手了,载着巧珍的马车,独自行在寂寞的山路上,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孤独、清脆的马蹄声,以一种单调而冷酷的节奏,拖着巧珍远离了爱情和幸福……《人生》中几处音响的运用,不仅仅是环境的“道具”之一,渲染出逼真的时空效果,也是主人公充满了爱或忧伤的心声的外化及物化,不但符合人物心理及身份,而且符合人物所处的具体地理环境,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其二,打破时空障碍,创造深远的意境。法国影片《长别离》中的音乐运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主人公的丈夫在战争中失踪了,战后,她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并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于是请他到她的小酒吧做客,想方设法唤起他的记忆。她在留声机上放了《费加罗的婚礼》,唱机优雅缓慢地旋转起来,音乐带着对旧日时光的无限留恋倾泻而出。女主人公似乎希望能通过留声机唤回和留住曾有过的日子——对于逝去幸福的追忆和对于将来幸福的渴望通过音乐交叉在“现实”这一有着无限可能性和爆发力的“点”上,使得小小的银幕空间融富丽的音乐、灰黯寒酸的现实、模糊神秘的未来于一体,深邃悠长,使影片产生了如梦如歌的艺术效果。
音响的运用也可造成同样的效果,在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齐导演的影片《末代皇帝》结尾中老年溥仪来到故宫,面对着大殿宝座,感慨万千,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位老人身上发生了断裂和转折,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他心中的感受呢——几乎没有。溥仪在殿中徘徊,似乎在等待,又似乎在寻觅。忽然,他在幻觉中听到了蛐蛐的叫声,果然,他在宝座下发现了童年在此嬉游时丢掉了的蛐蛐。人虫相对,溥仪终于释然:几十年了,他不过一直在寻找童年时丢掉的蛐蛐,他得到了它,一生也就过完了。人在历史面前不过是只虫,而一只虫在人的眼里也就是一部历史。蛐蛐的叫声把溥仪拉回到童年,而溥仪又从这几千年不变的叫声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近似的永恒”,感觉到对所有人都同样残忍同样善良同样公平的永恒,终于能够以一种形而上的眼光反观作为历史缩印本的自身,反观历史。在他即将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也即失去未来的时候,找到他一生都在苦苦寻觅而总是找不到的真正的“未来”,通过顿悟完成这个特别的人向一般的人的认同。
毕加索曾说:“艺术是使人们认识真理的谎言。”因此,这段戏中的“蛐蛐”叫虽然是非写实的,但却含蕴了写实所无法体现的真理。它用一种怪诞奇特的夸张手法融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将来于一体,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人作为罕见的“历史标本”的意义。
其三,对某一具体时空、情境起强化渲染的作用。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探春远嫁”一场戏,“一帆风雨路三千”的歌声穿云裂帛,把探春的痛苦无奈而又难舍难分的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探春是刚强、聪明而有胆识的女性,因此,这段歌曲的旋律配合曲词,先是用压抑低沉的调子表现出探春离家的伤感情绪;又用稍稍扬起、带点通达的旋律慰籍年迈的亲人;再后是凄厉决绝的曲调,人们可以看到探春毅然决然而去的背影;最后,亲人、故乡和岸,都渐渐消失在船的视野中了,凄绝的旋律低下来,变得愁惨哽咽,如泣如诉,仿佛是伫立船首遥望故乡的探春压抑着的泪水和叹息。这支短曲强化了这场戏的艺术效果,使之成为《红楼梦》一剧中的经典段落。
其四,音响(音乐)本身具有的表意性使它有时甚至可与画面并重。如根据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的动画片《高女人和矮丈夫》的音响始终处在强烈的对比中:高女人和矮丈夫协调一致的脚步声传达出某种内心的和谐;而从灰色背景中突然探出的头伴随着泡沫一样琐碎的叽叽喳喳声表达了人的窥视欲和对异己的排斥。高女人死后,矮丈夫高举雨伞站入大雨之中,始终伴随他的和谐宽容的音响变成狂暴沉闷的咚咚声,与众人的一声“吱”形成鲜明的对比。音响(没有语言)的运用与画面配合,透辟地传达了这样的主题:传统的陋习总是以包含着不和谐的表面和谐去专横地破坏深藏在表面不和谐之下的和谐。人与这种陋习,将处在永不停息的冲突和斗争之中。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是一个很值得品味的人物。在她的身上,既有因文化传承而保留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又有因人物个性美而表现出的对传统的背离。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从性心理学角度分析,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反阉割”者的形象。在她的观念里,村长是一村人的家长,村里人有了不对,打是可以的,但“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官司便是由此而发,但当她的官司终于打赢,村长被带走时,她的脸上流露的竟是深深的意外和惶惑。她打官司、告状,依靠的以及想得到的都是她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说法”——在闭塞的黄土高原上因袭而成的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社会中的严格律法,所以当孩子顺利诞生,“阉割”被否定,村长又以实际行动在秋菊心目中恢复了家长的完美形象之后,“法律”就成了完全多余的东西。以强制手段为她讨来的公正使她转而成为忘恩负义的罪人,讨来的“说法”却违背了她心目中的“说法”,这构成了一个带喜剧意味的荒谬悖论。该片语言不多,同一段西北梆子腔(又称秦腔)贯穿始终,形成一个闭合的回旋结构,每当秋菊进城告状,“秦腔”便拉开嗓门伴她上路,一句提头道白“走哇”与人物的动作相映成趣,构成了有点滑稽意味的巧合。更巧的是,影片开头、结尾以及秋菊难产、村长到戏台下找人帮忙时,戏台上唱的都是这同一段秦腔,音乐的设计和运用幽默而带点叹息、带点沉思地传达出了影片的主题。一个有点荒谬的悖论,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现代文明与高原传统文化颇富喜剧性的融合。
音响(音乐)的表意性较之语言的表达更直观,能与人的心灵感受发生更直接的碰撞,并更能产生余音绕梁、耐人寻味的效果。
光线的造型功能
光线是对视觉进行诱导,使眼睛能够有选择有主次地接受画面的重要造型元素。
光线的造型功能之一,是使画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趋向协调和简化。罗格·帕里斯说:“如果将画中的各个物体作出某种特定的安排——使所有的光线都集中照射它们的一个面,从而把另一面完全涂黑,就会把光明和黑暗集中于一个物体之上。这样一来,眼睛在观看它的时候,便不再会游移不定和眼花缭乱。提香把这种方法称为串葡萄法。我们知道,当葡萄处于分离状态时,每一个葡萄的光明部分和黑暗部分都是对半的,这样一来,就容易把人的视线分割成许多束,结果必然会引起混乱。然而,当我们把所有葡萄集合成一束的时候,它们就只有一片光明部分和一片黑暗部分,这时眼睛就会把它们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转引自《艺术与视知觉》〈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我们有许多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轰动效应的影视作品,其画面就由于缺乏光线的集中安排而显得凌乱,缺乏统一的整体感。而影片《死亡诗社》由于用光的讲究,创造出不少具有油画般美感的画面。
光线的造型功能之二,是将画面统摄在某种和谐一致的光调之中,给观众以情绪上的协调和美感。在这里,画面上的所有物体都浴在一层淡淡的光的薄雾之中,呈现出某种朦胧优雅的状态,如《时光倒流》中多用金黄的光调表现超越时间的爱情,这种柔美的状态与其他场景画面对比时,有时也能呈现出为强对比光所体现不出的氛围,诸如神秘、邪恶、美丽、恐怖。如美国影片《闪灵》(又译《幻觉》)中,男主人公杰克患了幽闭恐惧症,精神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走进空无一人的饭店大厅,惊讶地发现那里充满了美丽而可疑的人们,这些“鬼”的光临促成了他的完全疯狂。而这个场景的布光却是淡黄柔和的,与现实时空以阴冷的青白和蓝色为基调的布光形成鲜明的对比,格外邪恶、神秘、恐怖而可疑,这是可构成强烈光效的戏剧性阴森式布光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光的造型功能之三,是利用光的表意性,渲染环境,制造氛围,突出某种情调。如黄昏式的光线效果是溢满着一片“模糊而伤感的幸福”。在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每当女战士们回忆战前的和平生活,就用一种类似“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金黄偏白高调光笼罩那些无限美好的旧日生活画面,与冷静清晰的现实构成对比,表现了这些勇敢的人们对于和平略带感伤的追念。晨式的光线效果则或是充满朝气,或是清冷忧伤,前者如《死亡诗社》中常常出现的景物空镜头:红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的土地、群鸟、河边的小树林,隐现在微红的清晨式的光线中,透露出再森严的制度也难以压抑的青春气息;后者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潇湘馆的布光基调,清冷而带点微寒的光线与怡红院的暖色柔光形成对比,暗示着两位主人公的不同地位和性格特点——黛玉寄人篱下,孤高清傲有诗人风,而宝玉则寄身温柔富贵之乡,有公子哥儿的脾气。昼式布光可利用自然光,也可借助人工光造成多种不同表意效果,如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现实战争画面多采用清晰明亮的自然光造成冷酷现实的效果;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多采用阴天的光线效果凸现少年教养院这一特殊的环境氛围;苏联影片《士兵之歌》和《稻草人》更几乎全部利用阴天拍摄取得特殊而感人至深的光线效果;中国影片《一个和八个》则采用强光差和低调摄影表现苍劲雄浑的风格。夜式光根据表演功能的特殊性可分为原野光、酒吧光和室内光等几种。原野光如《死亡诗社》中孩子们在林中夜奔,如诗如画的光线和色调的蔓延衬托出如诗如画的青春;酒吧光如《鸡尾酒》,喧嚣闪烁而带点混浊的夜晚光把人们带进一个疯狂而放纵的场所,在这里,你可以寻找梦和欢乐,也可以寻求遗忘和刺激……室内光则如《死亡诗社》中尼尔之死的一段戏,深蓝色的夜像大海一样涌动,把闪烁的光点染在尼尔·佩里身上,一声枪响之后,万物趋于静寂,光也似乎停止了波动,带点微光的夜像沉重的绒毯覆盖一切,而又用那小小的绒毛刺激着观众的感觉,光在这里的运用引起了极为微妙的效果——夜景中光的微颤渺小,暗示了青春生命的敏感柔脆和易折。
总之,光可称作是影视艺术的画笔——时而如提斗,浓墨渲染;时而如大小白云,勾勒轮廓;时而又如小红毛,能点出晴蜓翼翅上的斑点般微妙的细节。
画面(取景构图)的造型功能
画面在造型上所起的作用和表意功能可以说是最影视化和最个性化的了。连续画面运动是电影电视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最大特征,又是最能体现编导匠心和个人风格的领域,因此,对于画面造型功能的运用在国内已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成功的画面表意,与人的视知觉经验是分不开的。格式塔心理学对于人视知觉的特点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和归纳,认为当视觉主体观看眼前的对象时,总是不自觉地将之进行简化,使之趋向于主体视觉记忆中的某些物象的形态或常规构图,从而唤醒视觉记忆,取得异质共构的快乐。一般来说,儿童是不会对一个视觉对象“触景生情”的,而一个有着丰富经历并将之沉淀为潜意识或记忆的成年人,却会对某些事物和情景感慨不已,深受震动,这是视觉记忆被唤起并引起了心理记忆和深层潜意识的苏醒。因此成功的画面表意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经过观众视知觉简化后能被归纳为经验中的常规构图、从而引起感触的画面设计。如凌子风的《边城》中翠翠摇着渡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画面,就切合了观众心目中关于中国画山水意境的常规构图,从而引起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再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兰拉着板车,带着身心均受重创的罗群远去,雪地上留有的足迹又是一个“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土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的构图,既切合观众的知觉模式,又能使主体的感受融入一种深泛的人生经验当中,激发深刻的人生感悟。
画面构图除要贴近观众的视觉记忆和经验之外,还要具备某种统一感和整体性,即“画面的简化趋势”。人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将眼前的视觉形象进行简化,如将一丛灌木看成一个球形,将一棵树看成有向上趋势的三角形等。这种简洁、均衡、有统一感的构图会在观众心目中造成平衡和愉悦,而“在一件艺术品中,组成它的所有要素的分布必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带有象征意义的不均衡之所以能够感人,仍然是由于它得到了那些互相平衡的因素的肯定的缘故”(以上两段引文均引自《艺术与视知觉》〈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因此,有简化趋势的构图,也就是使画面的所有因素达到平衡,给人的视觉以简化统一的快感的构图。但简化不是简单,而是内容复杂,涵义量大但结构简单,如美国影片《马耳他之鹰》中的一个颇受称道的画面,是由处在对立斗争中的私人侦探斯佩德、神秘女人布丽吉、歹徒古特曼和凯罗组成的一个开放的半圆形,侦探处于画面左侧,他的对手、肥硕的古特曼在右侧,与他相对,布丽吉与凯罗补充了二人中间的空白,布丽吉微向前倾,表现出她与二歹徒的不同和与侦探的不寻常关系,斯佩德看着三人,三人则紧盯他手中的鹰。虽然人物关系复杂,危机四伏,但整个画面的构图却给人以简化统一的均衡感,给人的视知觉带来了愉悦的审美感受。
画面不但要简化、均衡,还要具备一种潜在的力感。阿恩海姆认为,物体的形状和形态是产生这个客观事物内在力量的外在表现。一幅画面的产生总伴随着某种或某几种力的作用,而且是这几种力暂时达到均衡的结果。因此一幅成功的画面中的各个因素是不应各自为政彼此疏离的,而应共同组成该画面的力感趋势。在电视连续剧《渴望》中有几个空镜头的运用,就是通过静物的组合以及静物中蕴含的力的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传达某种视觉意象以及心理含蕴。如台灯下面,一杯袅袅地冒着热气的茶,挂在墙上的钟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就形成了一个平稳而坚实的力感趋势,这是一种沉积型的力感趋势,这些物品又符合观众视觉经验中的常规构图,因此给了观众以沉稳宁静的视觉体验和心理感受。明明是静物,观众却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以及生活的运行。
画面根据色彩、影调、构图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分成硬式构图和软式构图两类,编导可根据不同风格进行选择,以便更精确地传达含义。硬性构图追求强烈的个性和力度,注重对比和戏剧性,侧重造型。如《死亡诗社》的结尾画面中,学生们纷纷登上课桌向即将离去的基蒂先生表明: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视角去看世界。最后一个画面,是用一个学生站在课桌上的两腿占据了画面的两侧,摄影机从他的两腿中间拍过去,是心情激动难以自持,有了自觉意识的学生安德森,打在他身上的明亮的光使他了与画面两侧的暗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整个画面构图看起来象是卢浮宫的一幅名画《烛光》,具有极强的造型感,而且传达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电视连续剧《高山下的花环》、电影《菊豆》、《一个和八个》、《大阅兵》等,都大量运用强烈的对比、简洁的轮廓果断地表达含意。
软性构图平和舒缓,戏剧性、对比性不是那么强烈,更着重表现平易流畅的现实空间,追求纪实风格。电视连续剧《渴望》、《阿信》、电影《金色池塘》等,都使用了这种贴切平实的构图风格。
此外,画面构图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风格,即诗意风格,它既不突出强调画面的对比和戏剧造型,也不采用平易柔缓的软式构图,而是构造出意境深远、饱含诗意的画面,传达某种深沉淡远的人生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