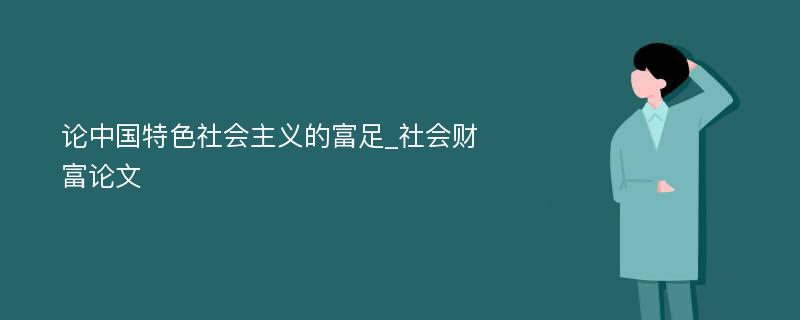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2-0001-03
党的十六大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明确了发展的要旨、力量、途径和条件,也廓清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论”。
一、“三个代表”和“全面小康”赋予财富新内涵
财富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从分析财富入手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以后的经济学家也都对此作过论述,马克思对于财富有更为科学的界定。十六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财富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
首先,把财富同社会主义本质和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使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坚实而充裕的物质基础。当然,广义的财富包括精神财富,不过物质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主体,是精神财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就是财富的短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做到民富国强,并走向更富裕的阶段。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明确,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要旨就在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就在于创造质优量大的社会财富,这也是衡量一切得失利弊的一把尺子。
其次,把财富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联系起来,既增加国家的财富,也增加居民个人的财富。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看,突出的特点是使中国的老百姓得到实惠:“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连六个“更加”,体现了社会财富全面倍增的特征,勾勒了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其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首要的是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按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要求,那就是GDP总量达到36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按照汇率现价计算)4.2万亿美元,赶上现在的日本,超过德、英、法,在世界的经济总量中可居第二或第三位。按人均计算,可达到3000多美元;如果人口不超过14亿,年增长率按7.2%计算,则可达到4200美元,就是说,人均GDP等于现在的4.5倍。这是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跨越。
再次,把财富的范围进一步拓宽,带有时代的特点。“三个代表”思想中不但包括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包括先进文化的发展;“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六个“更加”,也包括政治文明、文化道德素质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指标。社会财富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既有有形财富,也有无形财富;既含财富的数量,又含财富的质量,特别是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这就从狭义的财富观念中解放出来。
同时,把创造社会财富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拓展了劳动价值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个概念比之有关价值的概念更丰富,更易于接受,而实质上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就是从“财富”开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财富即一切实用价值的总称,而价值则是“抽象财富”,它构成“财富的实质的东西”(当然二者也有所区别)。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涵盖一切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创造财富实质上就是创造价值。我们不应再拘泥于原有的价值和价值创造的观念,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演化和更新原有的理论认识。而且,由于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可以使财富集成、演化为更新的形态,使原有的财富增值,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促进财富的价值增值,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建立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财富的创业机制
怎样才能加快社会财富的创造?十六大要求建立一种高效的经济机制。从经济学上说就是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之产生日益增大的效率,或者说更多地实现价值增值。所谓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以及各种自然资源,而且将这些集成为一个经济运行系统。如果仅靠某一种要素,那无异于“孤掌难鸣”。尤其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成了主导因素(发达国家科技贡献率为60%~70%),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贡献率为20%左右),资本则是一切要素黏合、生长发育的土壤,而这一切要素的组合和转化又要通过各种劳动过程来实现。
具体说,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创造社会财富之路,就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过去由于底子薄,又走了一些弯路,实事求是地估计,我国目前也只是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所以,“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能够再用2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与信息化互动,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那就是一个飞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但如果掌握了它的发展规律则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则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大大缩短这个自然过程。这就需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同世界经济接轨,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社会财富。
江泽民同志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创业机制,是对我党一贯思想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挥。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观点。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强调要更充分更广泛地调动一切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贡献的积极因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国内外各个阶层和个人。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进而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潜能,通过广泛积极的创业来广泛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
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之相适应,需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整个社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激励人们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分配原则,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效率优先(初次分配)、兼顾公平(再分配)的原则,鼓励全体人民积极创造日益倍增的社会财富。实质上,这正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辩证的具体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与生产关系形式的多样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相互耦合。这就是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财富的制度保证。
一些同志之所以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存有疑虑,就是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最广大的各类人士为创造日益倍增的社会财富做出贡献。我国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须知,各种要素都是由人来运作的,各类困难也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来克服。拿社会问题说,就业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难点,单靠政府和国有企业解决不了,更大量的要靠职工自主就业和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就业。如果不发展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和各式各样的服务产业,那就没有出路。
三、形成与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思想观念
首先,我们应当全面看待今天的劳动。十六大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论劳动的形式如何(体力还是脑力,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它们都属于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论是创造有形价值的,还是创造无形价值的,都属于劳动范畴。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智力劳动更应予以承认和尊重。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成为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管理也是重要因素,没有这些劳动,现代生产就无法运行。其他服务劳动也在以不同方式创造不同形态的价值,或者减少负价值,同样也必须尊重。这“四个尊重”体现了对劳动和价值的理论创新,打破了以前所说的“生产劳动”的狭隘眼界,既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点,也鼓励先富者更多地创造财富。
同时,要从新的实际出发,对于阶级、剥削等也要有新的认识,而不以人们的财产多少简单地判定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因为社会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现在只要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财富,那就应当视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应当以此作为衡量先进与否的标准。
从理论上说,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过去长期运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是从经济地位上划分阶级的。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包括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内,都是从经济地位、财产的多寡来确定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的。而目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过去近50年,原有的经济关系早巳不复存在,20多年前就已经给所谓地主、富农、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摘了帽子。又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经济关系产生了更大的变动,即使共产党员也有去经营私营企业的。有的私营企业主把资产奉献给国家和集体或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他们的正当经营是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在人民政权起主要作用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他们的地位、作用、社会关系都与以前不同了。从社会发展看,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这些正在变化的人群(少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违法者和破坏者除外)都在总体上为社会创造着财富。所以,必须按照十六大的精神,用新观点看待他们,并在经济上实行以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对于私营企业的剥削问题也应当有科学的分析: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管理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二要考虑生产要素(提供资本)对创造财富和扩大就业的贡献,三要认识它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功效。所以,不能将今日的私营企业主与过去的剥削者完全同日而语,不能将其营利行为一概视为剥削和笼统地反对剥削。目前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要充分调动他们提供生产要素(管理与资本等)贡献于社会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积极性同社会发展生产力是一致的。当然,还要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积极引导,抑制其负面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
再者,对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些生产要素和活跃了市场。除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收入外,还有股票收入、股息分红、房租、外商投资回报等(有的同志把科技成果所得也算做非劳动收入,是不对的,因为科技成果属于脑力劳动结晶),与在银行存款获取利息是同一个道理,是正当的经济回报。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中需要更多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匹配,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中介组织在生产、流通、消费、结算以及各种法律咨询方面提供服务,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社会成员中将有更多的人参加交易、融资、服务等各种增加和集成社会财富的活动,加上人员的频繁流动,这就必然产生大量的自由职业者,产生所谓“中间阶层”。事实上,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层也是越来越大(恩格斯早就指出,中间阶层的存在带有必然性),他们的收入方式也会多种多样,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对于这些有益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行为,同样要鼓励,给以法律保护,而将其收入与那些危害社会的非法收入严格加以区别。今后,我们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有能力者去当大大小小的老板,既增加个人财富,又增加社会财富。而对过高收入,国家通过再分配加以调节,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简言之,总原则是鼓励发财,遵守法律,调节分配。
所有这些,都是立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这不仅是个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正是基于这个要旨,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应当用十六大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论来统一认识,促进新的创业机制和社会氛围形成与完善起来,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