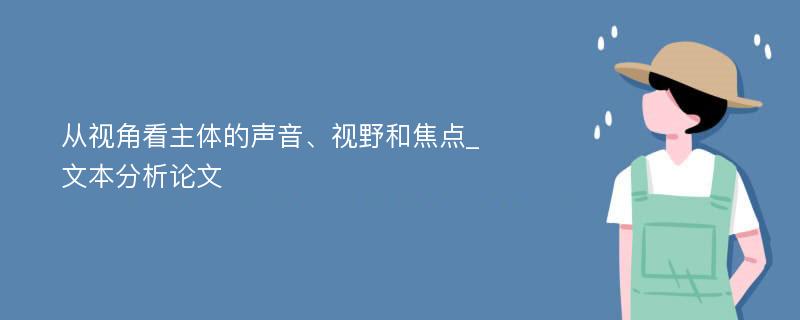
视角主体的声音、眼光与聚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主体论文,眼光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3-0058-05
一 问题的提出
“声音”与“眼光”即“谁看”和“谁说”的二分,其初衷就是把故事世界中的“现实”主体和故事世界之外的话语行为主体区别开来,以利于主体辨识范畴的清晰和意义把握。因此对虚构叙事话语的“声音”、“眼光”与“聚焦”的判定,相当于对文本内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判定。但由于常规上允许人物充当“叙述者”,概念明显不对称,不利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论分析。例如:
(1)I had seen an unicorn.(我看见过一只独角兽。)
(2)He had seen an unicorn.(他看见过一只独角兽。)
首先,(1)句声音眼光统一于同一主体“我”,(2)句则分裂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主客体对立:潜在的声音主体“我”与显在于故事层面的人物“他”的眼光对立。其次,将眼光细分为“叙述者”的和人物的,(1)句叙述者的事后性、反思性眼光包容人物的当下性历事眼光,(2)句“叙述者”眼光则外在于人物眼光,既可陈述事实(两个眼光重合于对象“独角兽”),也可暗示人物看到的是幻觉(两个眼光不重合)。第三,(1)句的声音和眼光都与“独角兽”有虚拟四维时空内的现实关系(所谓同故事叙事),(2)句的潜在的“我”则否(所谓异故事叙事)。第四,(1)句的声音必然处在眼光之后并且对眼光中的内容有所缩减,即声音小于眼光;(2)句的叙述者声音则设定在事后故事外,人物眼光内容不能多于声音的赋予,即声音等于眼光。从此可以看到,一旦涉及人称,现行叙事学概念就呈现出逻辑不对称[1]。
二 声音、眼光与形式叙述者
从现象学观点看,话语的意义首先就来自真实作者的原始意向投射,即作者“投射出一个小说世界”(projection of a fictional world)的话语行为。但授予者的意向性与词语的意向性是不同的实体,作者意向转化为词语意向之后,文本内虚构叙事话语行为主体只能是叙述者。叙述者视角在线性展开的文本上的投影即“词的意向性投射”,是叙述者创造出意向性客体的主体投射行为。这个投影再次转化为虚拟四维时空中一个可能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主客体,即虚构叙述符号及其所指对象的组合。虚拟世界中的对象性存在又可以有自己的话语行为,即作为第二、三级的投射主体把自己的主体存在投射到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之上[2]。由于虚拟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类本质迥异的主体:处于文本虚拟世界之外的创造出该世界的叙述者,和处于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之内、在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被动地见证既定存在的“形式叙述者”[2](第2章)。
形式叙述者既是叙述者虚构叙述符号操作行为投射出来的对象性产物,又是虚构世界中的“现实”存在即第二级的投射主体。“展现在这样一个文本中的世界实际上就像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又从视角上返回去与主体的眼睛相联系”[4],即与某个视角主体相联系。(2)句中这样的视角主体存在于对象性人物“他”行事的当下,持有自己的不同于人物的眼光,见证了人物“看见某某”这一“现实”行为。同样,(1)句的形式叙述者“我”也以外在于人物“我”的眼光见证了人物“看见某某”这一“现实”行为。形式叙述者可以有身体,也可以没有身体而“无形地存在”,可分别称为“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和“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很适合无实体形式叙述者:“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身体而却没有身体的地方,我们就会说,那儿有一个精神。”[5](27页)
无实体形式叙述者有两个形态,在作见证时,它是无形的眼光主体,存在于故事世界之中;在作事后性的报道时,它是声音主体,存在于话语之中。由于“说”的时间必然晚于“看”的时间,声音主体总在事后才能报道对象的情况,动词过去时态就同时标识无形的“声音”主体的事后位置。而对于眼光主体而言,句子中动词的过去时态实际上是现在时态[6](139页);“过去可以读作现在”[7](256页),即(1)、(2)句外在于人物的形式叙述者的眼光总在人物行事(看某某)的当下,而叙述的声音只能感在事后。再将例句(1)、(2)改为“同时性叙述”:
(3)我正在看(I'm seeing)一只独角兽。
(4)他正在看(He's seeing)一只独角兽。
在例句(1)、(3)中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眼光见证了人物“我”和独角兽的时空同一性,正如在例句(2)、(4)中见证了人物“他”和独角兽的时空同一性一样。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眼光可以完全重合在人物的当下性眼光之上,其声音则既可以客观地转述对象性人物的眼光内容,也可以对人物眼光内容有所取舍即将自己的理解加入到叙述之中去。
(1)、(3)句的形式叙述者往往被误认作与人物即“经验自我”主体同一的“叙述自我”。这种同一是“我”字引起的幻觉。如果将例句(1)或(3)改为“我(现在)抓住了一只独角兽,后来我被它咬死了”,那么死掉的人物“我”就不是在故事进展的当下见证人物死亡过程的无形眼光主体,更不是事后报道相应内容的声音主体。再者,例句中对象性的人物“我”或“他”都可以比如说是一只猫,看见猫的无形眼光主体必须外在于猫,而声音主体更进一步,还必须是一个理性的话语行为主体。阅读的直觉经验依据一个“我”字简并了不同主体,这种含糊的感觉不是理论分析的依据而是理论探究的对象。再考虑:
(5)我正梦见我抓住了一只独角兽。
(6)他正梦见他抓住了一只独角兽。
做梦者不能说梦,在人物做梦的时候说梦的主体因此不是人物“我”或“他”。我们将这个区别于无实体形式叙述者、与人物主体同一因而能够进入人物梦境和内心世界的形式叙述者称之为“有实体形式叙述者”。(5)句首先是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在人物做梦的当下所作的直接叙述,然后才是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转述。(6)句与人物主客对立的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眼光只能见证“他”正在睡觉之类外在事实,不可能见证人物的梦境;梦中“独角兽”的具体样态除了人物本身以外任何人不可能知道,因此报道梦的内容的主体必须像(5)句一样与人物主体同一;梦的内容首先是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在人物的梦境中见证“一只独角兽”被“抓住”的过程,并且用一个声音将梦的内容叙述出来,然后无实体形式叙述者再依据有实体形式叙述者提供的叙述进行转述[8]。阅读既可以将叙述内容理解为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转述,也可以理解为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直接叙述。在不同主体视角中,同一对象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两句上下文对独角兽展开具体描写,阅读将描写内容理解为转述还是直接叙述,获得的意义将大不相同。
由于两类形式叙述者都是潜在于句外的“我”,常规阅读依据同一人称合并不同主体,(5)句无实体和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在同一个“我”之间的转述关系对阅读不再有效,句子才被理解为人物梦醒后的自述。但句子的动词现在时至少标明了人物既未觉醒也未在梦境中自述,“我”字的强大简并作用并不能使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存在被完全忽略。理论分析的逻辑性要求严格区分对称主体,常规阅读中不同主体的简并不能成为理论分析的依据。
除此之外,如高概指出的那样,人物作为“述体”也“制造一个世界”,因此在叙述层变换的情况下,具有叙事功能的人物视角主体也可以称之为“有实体形式叙述者”,无论其被第几人称指涉。“述体,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空间和时间中移动的中心”,空间、时间和述体共同构成了“位置场”[3](38页)。应当注意,感受而不表达的人物只能是高概所说的非主体或“激情非主体”,即只能是形式叙述者的视角对象而不能是视角主体,不能成为有实体形式叙述者。
三 聚焦
从现象学观点看,在作为纯粹意向关联物的文本中任何意识都是内在于视角主体的关于某物的意识,任何某物都是某个视角中的某物,因此被视角主体聚焦的任何对象都必须与一定主体的视角相关而不能独立,同时被聚焦的对象也标识相对的主体视角的存在。此处的主客体关系正像胡塞尔所描述的那样:“注意的视线从纯粹自我中射出并呈现着自身,并终止于对象。客体被击中后被置入对自我的关系中。”[9](235页)视角主体“通过每一实显的我思指向对象。这种目光射线是随着每一我思而改变的”[9](151页)。反过来说,任何主体都必定通过视角对象而显现,“‘我思’必定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9](151页),“各种内在性知觉都必然保证其对象的存在”[9](126页)。据此,形式叙述者的声音和眼光所触及的对象的集合,就是视角主体投射出来的对象性意义世界。
由于文本内主体的多层次分布,视角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也是多重的。叙述者相对于形式叙述者是本源述体,形式叙述者是叙述者的投射述体。形式叙述者相对于对象世界是本源述体,对象是形式叙述者的投射述体。人物既是叙述者的也是形式叙述者的投射述体,人物面对自己的视阈对象时,人物本身又是本源述体。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看,聚焦总要涉及聚焦者和被聚焦者的关系,凡本源述体都是聚焦者,投射述体都是被聚焦者,因此谈论聚焦必然涉及视角主体分辨。
在视角主体方面,聚焦是视域中心的主动或被动确定;在客体方面,聚焦是对象成为相关主体的投射述体。按照热奈特的意思,聚焦不限于视觉方面的主体行为,也包括其他的心理行为,因此形式叙述者(包括持有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及其事后性声音都标识聚焦。里蒙-凯南已经看出“聚焦属于故事和叙述两个方面”的不对称,并提出“应从文本分析中消除”[10](153页)这种不对称。于是巴尔规定“聚焦是看者和被看见者之间的视觉关系,是故事的组成部分,是叙事文本的内容”[11](206页),这样就必然将聚焦等同于眼光,在强调眼光聚焦的同时排斥声音的聚焦。查特曼反复指出: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定,“叙述者”将不时从话语中走出来,作为“看不见的主体”进入故事世界[12](120页)。为此查特曼用slant、agent、filter等术语指涉故事内的聚焦主体。这样做无非是将不能走出话语的主体和能够进入故事世界的主体进行分类罢了,并没有区分出叙述者和形式叙述者的相对时空位置。查特曼还说,同故事的“叙述者所传达的只能是对故事内知觉和感想的回忆,而不是知觉和感想本身”[13](194页),这就肯定了“叙述者”和人物的时空同一性,即把叙述置于事之后,实际上是用形式叙述者取代了叙述者。查特曼所说的“对故事内知觉和感想的回忆”属于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的事后声音,“知觉和感想本身”则属于形式叙述者和人物的当下眼光。因此,即使按照查特曼的思路,在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除现实性的“眼光”表示聚焦主体外,事前性和事后性的“声音”也都可以标识聚焦主体,其中回忆的眼光必然对应一个同时的声音,事后的声音必然依据一个早先的眼光。
由于叙述者只能在话语层面上定义,其叙述符号操作行为是生产出客体的行为,文本内除了叙述符号之外没有任何外在于叙述者的被叙述的客体性存在,因此叙述者仅仅是事前性质的叙述“声音”主体而不是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的“现实”主体,不能对任何作为其叙述行为产物的外在对象聚焦。换言之,由于叙事文本是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产物,文本全部内容都必须通过叙述者的主观意图来形成,因此叙述者作为聚焦者只能有一种聚焦方式——对叙述符号而不是对已经存在的对象聚焦。为此,叙述者视角永远是全知视角,他在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外的声音聚焦标识叙述者的叙述符号操作行为。他的创世声音体现在文本形式结构各层面上,包括人物关系设计、结构布局、主题、风格等等,高于任何局限于被动地理解故事世界的事后性声音。
两类形式叙述者在话语和故事两层面上的聚焦行为,都只能是受到叙述者控制的非自主行为。形式叙述者都有被叙述者控制的事后性质的讲述声音,也都有被动地面对“现实”的眼光。因此形式叙述者既可以用声音聚焦也可以用眼光聚焦。眼光直接面对客体进行聚焦,声音除了转述眼光内容外,还对例如评价调侃,以及情绪、回忆、评论等内容直接聚焦。
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的主体关系就是聚焦关系,也就是视角关系。这样看“聚焦”就是传统的“视角”概念的变种了。阿丹姆斯看到了声音和眼光这对概念的可互换性,认为声音和眼光之分可以归结为叙述方式之分[14](18-19页)。阿丹姆斯的“叙述者”位置也在事后,事前位置则留给作者,他认为这种划分与热奈特的“声音和眼光”平行,还能够解释“看”与“说”所不能区别的叙述现象。例如,按照热奈特的区分,“零聚焦意味着没有人见证或经历事件,因此事件不可能被说”[15](32页)。事实上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既可以是当下性的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对事件的眼光见证和声音传达方式,也可以是事后性的无实体形式叙述者对事件的回忆或解释的方式,还可以是事前性叙述者对事件和叙述视角的设计方式。为此,考虑聚焦关系必须以对视角主体的清晰分辨为前提。
四 实例
下面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自杀前的昆丁想起早年经历情景的意识流描写,属于第一人称叙事:
(7)a.乡下人真是可怜见的他们绝大部分从来未见过汽车喇叭b.呀凯丹斯c.好让d.她都不愿意把眼睛转过来看我e.他们会让路的f都不愿看我(李文俊译文)
从时间上区分,a、c、e是过去了的第一个场面中康普生太太坐车兜风时说的话,d、f中的“她”指昆丁的妹妹凯丹斯,“我”指早年昆丁。a、c、e作为外在对象,d、f作为内在情感,首先一同出现于早年昆丁当时的视角中,然后再出现于后来的将要自杀的昆丁视角中,两种情况下的视角主体昆丁与其对象,共同构成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报道内容。在早年昆丁当下性的视角中,“我”只有眼光而无声音,其历事的眼光属于故事。将要自杀的昆丁则除了回忆性的内心声音外还有两个眼光。一个是回忆的眼光,这个“过去的眼光”“可以着借记性再成了一种实在的知觉”[15](60页),即成为现在的内心知觉眼光。一般而论,如果“叙述自我”叙述的是“经验自我”的回忆的内容,就会出现两个互相包含的声音和四个眼光;加上虚构叙述者的声音,就有三个声音和四个眼光共七种聚焦。声音聚焦有:①叙述者零聚焦的虚构叙事声音(没有眼光,因为眼光意味着对象事先已经存在);②无实体形式叙述者外聚焦的客观地“转述”有实体形式叙述者自述话语的声音;③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内聚焦的表达出将要自杀的昆丁心理内容的“叙述”声音。②③是①设立的“事后”声音,②与③不必一致,但上引文没有加入无实体形式叙述者自己的主观色彩,两个声音之间有聚焦重合。眼光聚焦则有:④早年昆丁在过去当下的历事眼光,此眼光对a、b、c、e外聚焦,对d、f内聚焦;⑤将要自杀的昆丁知觉现在外在世界的内聚焦或外聚焦眼光,上面的引文不包括这个眼光;⑥将要自杀的昆丁的内聚焦回忆眼光,这个眼光包容了早年昆丁的内聚焦和外聚焦眼光;⑦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零聚焦眼光,该眼光自由地存在于早年和先在昆丁的历事现场,见证了所有场面上内在外在于昆丁视角的对象。当人物既是聚焦者又是被聚焦者,就必然出现佩里所说的combined point-of-views,即有实体形式叙述者和无实体形式叙述者两类视角的重合[16]:⑦重合在⑥、⑤、④上;⑥重合在⑤、④上;⑤重合在④上。本例⑥在a、b、c、e中重合在④的人物外视角上,在d、f中重合在④的人物内视角上,这就是所谓的多重聚焦。
第一人称叙事中的视角重合必然是时间关系上的彼此包容,第三人称叙事则未必:
(8)Now in his mind he saw a railway station at Karagatch and he was standing with his pack and that was the headlight of the Simplon-Orient cutting the dark now and he was leaving Thracethen after the treat.(Hemingway:The Snows of Kilimanjaro,着重号引者加)现在,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在卡拉加奇的一座火车站,他正背着背包站在那里,现在正是辛普伦—奥连特列车的前灯划破了黑暗,当时在撤退后他正准备离开色雷斯。
从视角结构看,在故事外对故事内容聚焦的声音有三个:①叙述者零聚焦的虚构性创世声音;②无实体形式叙述者外聚焦的事后转述声音(第一个Now,动词过去时);③无实体形式叙述者零聚焦的当场报道声音(第二个Now,动词过去时)。①和②之间有焦点变换,即流动聚焦。由于话语表层是第三人称叙事,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声音被②和③覆盖,不能显现。眼光则有四个:④在第一个“现在”场面上,面对着正在进行回忆的垂死的“他”的有实体形式叙述者“我”的内聚焦眼光;⑤在第二个“现在”场面上,有实体形式叙述者与“他”共同面对火车的外聚焦眼光,此眼光又以零聚焦方式重合在人物视角⑥、⑦上;⑥垂死的“他”的回忆性内聚焦眼光,从此眼光可以看到作为对象的火车站和当时背着背包的“他”自己;⑦早年的“他”的过去历事外聚焦眼光,从此可以看到火车但看不到当时的自己。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的“眼光”和“声音”都是叙述者手中的叙事符号,是叙述者将④重合在⑤、⑥、⑦上,将⑤重合在⑥、⑦上,⑥重合在⑦上,时间位置靠后的视角总比时间位置靠前的视角大一些。从前面诸句到最后一句有所谓的焦点变换:“当时在撤退后他正准备离开色雷斯”只能出现在无实体和有实体形式叙述者的声音中,并且是零聚焦,对当下性的人物眼光⑥来说此句无意义。
聚焦变换即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多重聚焦、不定聚焦等变换有两种情况,其一,聚焦方式随同一视角主体投射出的对象而转移,如例(7)早年昆丁视角从a、c、e转移到d、f;其二,不同视角主体之间的聚焦方式不同,如例(8),不同主体以不同聚焦方式重合在同一个对象“火车”上。话语意义复杂化的关键因素就是聚焦关系,而叙事话语中的聚焦方式或类型只有在清晰的主体辨识的基础上才能确定。
